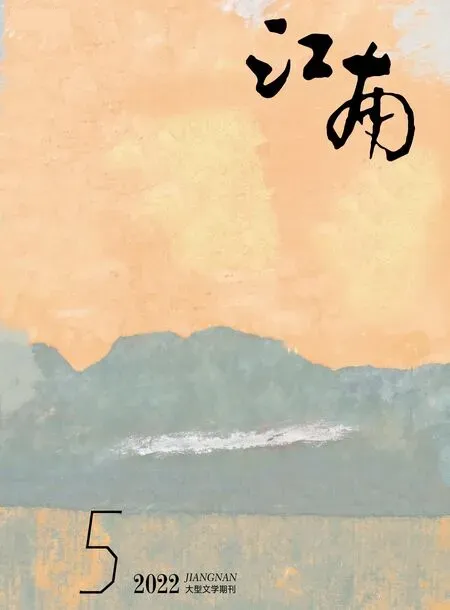史家的心法与文学的笔法
——朱晓军《中国农民城》读札
2022-11-25周保欣
□ 周保欣
一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我不知道在英语世界里这三个概念怎么区分,但是在汉语世界里,很显然,“非虚构”意味着一种写作的理念和手段,它对应的是虚构,虚构或非虚构,都是中性的概念。纪实文学中的“纪实”,突出的是事实、真相,它对应的,是容易被遮蔽的“真实”,或被常识扭曲的虚假和假象。至于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它所强调的,理当是重大的事件或情况,因为,唯有是“重大的”,才有向民众和社会“报告”的必要和理由。至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曾一度因为总是能够抓住“重大的”、人们关切的事件,总能及时地把握到我们所处时代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而产生诸多轰动当时、震撼人心的优秀甚至是伟大的作品。
在这种意义上,我更愿意认为,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是部“报告文学”的杰作,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题材,符合我所说的“重大的”标准。作品以三十万字的篇幅,为一座小城写传,写温州龙港从四十年前东海之滨,青龙江边的一片滩涂、五片渔村,一跃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历史。从题材上看,这是个再好不过的素材,因为它符合人类审美心理中最具震撼力的美学图式——“创世神话”。众所周知,世界诸文明,早期解释宇宙、人类与万物的起源时,都是从创世神话开始的,所以,创世神话内在地包含着英雄、创造、意志、力量等精神意涵。退而求其次,即便不以神而是以人为主角,创世故事同样会折射出英雄、创造、理想、信念等精神光芒。《中国农民城》叙写海边一个荒滩,四十年时间白手起家,矗立起一座新兴的城市,这怎么说,都是具有神话气质的大创造。但是,在题材的处理上,朱晓军几乎不涉任何的精神、信念、英雄、理想、荣耀、奉献之类的修辞,更不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等大词。尽管整部作品,我们可以随处归纳出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但那是我们的事,朱晓军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向历史靠近,向事实本身靠近,去还原那个滩涂起新城的艰难、复杂的过程。朱晓军不想把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处理成具有强烈宣传意味的作品,这是他警惕的地方。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城市本就是从无到有、应“用”而生的,其功能,作品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在视察龙港时有段精彩的议论,“过去,‘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现在,‘城’的防御作用小了,‘市’的交易作用大了,因此,城市建设中重点要放在‘市’上,要把交通搞上去”。[1]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278。早期城市国家、城邦国家,城市的功能,军事的、政治的、宗教的要占主导的地位,后来,随着人类社会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型,城市渐渐增多,经济的、交通的、移民的、生活的,等等,城市的功能也多元化起来。但是,每个城市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史。相比较而言,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新型城市的,龙港可以比拟者,不唯深圳,还有更早的香港、上海。然而我们知道,深圳之所以会成为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因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深圳崛起的背后是有国家力量主导的;而更早的香港和上海,除了它们自身的条件,更是系列历史大事件、历史运动塑造的产物。这些城市的崛起,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历史的外势在推动,不崛起都不行,而龙港则不同,如果说龙港有历史的外势,这个外势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催生出龙港这样的城市,龙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况且即便要有,也可以是虎港,或其他什么港,可以在浙江温州,也可以在浙江其他什么地方,或者说其他省外地方,何以是温州?
对这个历史逻辑的探究,实际上是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的某种辩证,他既然不想把《中国农民城》处理成带有宣传意味的作品,不想以那些个司空见惯的语词去解读龙港这座城市的生命起源,那么,他就必须要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内生力量,去诠释龙港四十年时间何以滩涂起新城。朱晓军找到的这个内生力量,就是人性的普遍力量,即人们对贫穷、贫困的畏惧;或者换句话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部作品中,朱晓军无论是地理环境描写,还是人物描写,或者是时代氛围描写,都有一个持续的推动力,就是贫穷。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分离出来,当时温州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资本主义泛滥。”平阳本来就是贫困县,分出来的苍南比平阳还要贫困,它地处偏僻,交通落后,很多地方不通公路,人们出行或者靠船,或者步行。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没有港口,经济发展不起来,且地处山海相连的地方,没有耕地,靠海为生的渔民尚可勉强度日,农民的生活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困难。
朱晓军写贫困,有直观的方法,比如说,以人物回忆的方式,叙述当地农民吃地瓜,吃米糠,吃地瓜藤,吃树皮,吃野草,等等。但更多的地方,他还是运用文学的方法,注意细节描写和刻画,如写没有见过汽车的乡下孩子,看见“一个像小房子似的东西从远处疾速而来,孩子们欢呼起来,张开双臂迎上去。老师吓坏了……嘀嘀汽车叫了起来,尖厉而急促。孩子们吓一跳,落荒而逃,有的跳进路边水田。”[2]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106。写李其铁随着父亲去鳌江,父亲给他买了根油条,从没有吃过油条的李其铁,吃油条的细节,都刻画得很直接,很有力量。
朱晓军写贫困不是皮相地写,他写到骨头里去了,写出贫困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联系,写出贫困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写出贫困与人的命运的关系,写出贫困中的鄙夷、羞辱,写出贫困者的文化性格,等等。陈定模的哥哥喜欢吹牛,陈定模问他为什么,他哥哥说:“你讲少了,人家也不给你。讲多了,家里富裕点嘛,借钱好借嘛。”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和贫困人格。在贫困面前,人的泼辣与强悍一文不值,就像阿慧妈妈一样,心气再高,也不得不向贫困的现实低头。因为写的是“江南人”,且报告文学有它的特殊性,需要隐蔽作家的主体性,求得“真实”,所以,朱晓军的整体视点是下降的,下降到了以“江南人”的视角看问题。他们对贫困的自我发现,不是以抽象的贫困,或者说是感性的贫困,而是以江对面的“鳌江人”作为参照的,鳌江镇是“千年古镇,百年商港”,素有“瓯闽小上海”之称。那边处处是高楼大厦,夜晚是灯火通明,而反观这边,荒野滩涂,路没有路,灯没有灯。对岸人称这边人是“傻瓜农民”,是“江南鬼”。
“一江之隔,我们这边是农民、渔民,他们那边是城里人。我们这边最好的鱼啊,虾啊,要挑过去卖给他们吃。我们吃不饱,到那边买地瓜丝;柴不够烧,也要到那边买。”[1]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107。
这种“那边人”给“这边人”带来的俯视和压迫感,造成“这边人”的内心挫败感。然而,贫困以及贫困造成的挫败感,既可以让人自卑、沉沦,将人打落尘埃,同时亦可让人奋进,与命运抗争。朱晓军写龙港新城的崛起,抓住的就是温州人的不甘、不屈与不服,抓住的就是温州人骨子里的硬气。这种硬气,是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意志的一种蓬勃野蛮的生长。《中国农民城》中,“猴子”们脑子灵活,会来事,走南闯北,敢想敢干,就是温州人野蛮生长的生存意志的体现。龙港从荒滩到新城,从无到有,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贫困逼迫的结果,是人反抗贫困的结果,当然,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每个乡下人都有一个进城梦,进而为之努力的结果。
朱晓军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性的作家。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知道,龙港滩涂起新城,新城从无到有这个题材,如果处理成一个一般性的人类不屈服于环境,进而开拓、创造出新生事物的创世故事,自然是成立的;但是朱晓军却打开了这个题材,在这个题材当中融入了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内涵,那就是“脱贫”“乡村建设”“共同富裕”等,这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是说朱晓军如何机灵,而是说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朱晓军,必须要抓住报告文学的时代感问题,报告文学必须与时代共振,必须与人心共振。
报告文学不同于报告,它是文学,报告可以叙事为主,以人为辅,而报告文学必须是以人为核心,事由人生,事中见人。《中国农民城》中,荒滩变高城,是“事”,是作品的“纲领”,而另一个“纲领”,就是写人。朱晓军写到的人物很多,奇迹的创造,需要有一个奇人群体,需要有运筹帷幄者,需要有决胜千里者,需要有形形色色的“猴子”,还需要平平凡凡的普通人。统观整部作品,其核心人物就是陈定模。朱晓军于纵横勾连、聚散开合之中写陈定模。就像整部作品的基调处理一样,朱晓军刻意规避这个题材的宣传意味,因此在人物刻画上,他实际上有很多棘手的地方,特别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写成宣传性的作品。朱晓军当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写陈定模,首即在写其“心”,写他推动龙港建设的“初心”。陈定模其貌不扬,身材瘦小。刚到龙港镇时,背着行李卷儿,拎着装有洗漱用品的网兜,就像一个农民工。这个身材瘦小的人,身体里却蓄积着无穷的力量。他像大多数温州人一样出身寒苦,曾经饱尝生活的艰辛,饱尝了贫困中的屈辱,所以,改变命运的安排,是他内心强劲的动力,这个动力,让他做出选择,去龙港,带领龙港人绘制美好的未来蓝图。陈定模其实也是一个“猴子”,他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有创造的冲动和激情。事实上,“猴子”的必要条件,是要有“胆”,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去“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没有石头可摸,也要过河,因为,要想做成特定条件下很难做成的事情,就必须要突破特定条件中的“特定”。陈定模所处的时代,还是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无论是观念层面,还是政策、制度环境,都有很大的限定性,需要突破的地方太多。陈定模要想有超常规作为,必须要经常去触碰政策、制度,乃至人们观念的天花板,所以陈定模不得不搞“变通”,或者说是“打擦边球”。有所不同的是,陈定模是政治上的“猴子”,不是一般生意上的“猴子”,生意上的“猴子”,输赢胜负尽在一家一己的利益,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但是政治上的“猴子”不行,他没有那么多的试错机会,别人也不可能给他那么多的试错机会,所以,政治上的“猴子”陈定模,除了要有“胆”,还更需要有“识”;如果他没有“识”,“胆”越大,栽跟头的可能就越大。正是如此,朱晓军写陈定模,也聚焦于他超越同时代人的识断,“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是他的识断;计划修五十米宽的马路,这还是出于他的识断;申报龙港镇为“市”,这同样是他超常的识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跨越性的四十年,常人可能连五年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未必能看到,而陈定模在四十年前做出的决断,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能站得住,由此可见,成大事者,必有他的根因。就人物的刻画而言,《中国农民城》对陈定模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唯一的遗憾,是后面由盛转衰时过于仓促,叙事逻辑不够清晰。
二
无论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皆属叙事文学范畴。在中国,叙事文学与史学同宗同源,其宗为巫,其流为史,为小说,乃至后面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等,均从叙事而出。章学诚论“传记”时说:“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之为传;叙事迹者,区之为记”。[1]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2014:231、232。章氏所论,便是史学与文学在写人、叙事方面的同源性关系。所区别者,历史所记之人和所叙之事是实有的,不容虚构增饰,而文学则不同,虚构增饰,本就是小说家的本事。此外,史学家写人、叙事,当会有所选择。史学有史学的担当,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穷究天人,通古今之变”。但是,小说、报告文学与史学有个内在的不同,就是小说虽不以真实为要务,但小说的真实,可能比历史的真实更真实,因为小说追求的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而历史所求的,多不过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真实。比较而言,小说与报告文学同属文学,但是小说可以有所取舍,就是在事实与真实间,取真实而舍事实,小说家可以以想象和假设,去达到所谓的真实;但是报告文学却不行,它必须要以事实为基础,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去达到所谓的真实。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历史学家,他们需要有史家的“心法”,去抓住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从中去勘探历史隐秘的肌理。
《中国农民城》,从外部看是写一个时代、一个人、一座城的崛起,但是,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问题。建一座城不难,城,不外是砖石、道路、土地和财富的问题,只要有政策,只要有规划,只要有资金,建一座城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朱晓军写的却是中国的“农民城”,这就涉及到“农村/城市”“农民/市民”“传统/现代”诸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从大的历史上看,人类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比如高山、草原、丘陵、盆地、戈壁、平原、雨林、海滨等地区,必然会形成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活在不同的社区形态,如农村或城市,人们同样会形成相应的生活方式、价值态度和人际伦理关系。简单地说,农村地区,因为人们多依靠血缘、亲缘、地缘组成而成,熟人社会最重视的就是亲疏远近。而城市则不同,以家庭、社区、单位为单元,人际之间,更多时候是原子化的,多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因此,共同的规则和价值遵守是城市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其间的差异性,是历史阶段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朱晓军写《中国农民城》,就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朱晓军有一个他自己的深刻思考:农民进了城,农民在城里买地置房,所建之城,是不是就是“城市”?这个是也不是。是,是因为它有了城市的外观,有了高楼大厦,有了住宅小区,有了学校、医院、商场、影院、酒店等;说不是,是因为朱晓军知道,城市有城市的文化、价值、规范、规则和理性。农民、农村,无论是日常生活、伦理生活,还是人际交往理性等,都与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民城》对温州苍南地区的乡村文化的刻画,甚是用力。这个地方,宗教的风习浓厚,寺庙、教堂密布。在农民心目中,观音菩萨、释迦摩尼、上帝耶稣,是可以为他们救苦脱困的。我们知道,苍南人对宗教的“信”,不是信仰,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的“信”,都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信”,是底层社会贫困阶层贫困人格的反应,他们没有能力通过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菩萨和神的身上。
朱晓军写苍南的民间文化,再一个就是写他们的宗族观念。这里的人宗族意识浓重,建筑讲究“高大上”的,除了寺庙、教堂就是祠堂,“仅江南区域内,祠堂就达一千多处”,在农民心目中,观音菩萨、释迦摩尼、基督耶稣和祖先同等重要。这里重男轻女,生了女孩而没有男孩的家庭,除了在村里抬不起头,还时时处处受人欺负。这里的人认姓不认官,不认公、检、法。苍南地方陈姓是大姓,到这个地方做地方官的小姓,甚至被迫改姓陈。这里宗族姓氏械斗成风,规模巨大,严重的时候还抢劫军用仓库,或者购买武器、弹药,打死、打伤人,烧毁、拆毁民房的现象经常出现,姓氏与姓氏之间积怨甚深……陈定模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很善于跟农民打交道,知道跟他们讲道理、讲政策法规行不通,只能跟他们讲情义、讲关系。陈定模跟村支书们的沟通,是半月一聚,按年龄大小排序,轮流做东,吃农家菜,喝家酿老酒,说知心话儿,他们把这个称为“半月谈”。
朱晓军以如此多的笔墨,写苍南民风之硬、之老旧、之野蛮,其意即在以报告文学的写实,去呈现两个层面的意涵:一个是社会改造之必要和急迫,一个是“中国农民城”建设之难。就前一点而言,社会改造,人的改造,是百年中国现代启蒙的一个基本叙述。朱晓军写到的苍南人,物质上的贫困,当然是急于要改变的现实,但是民众精神系统、价值系统、观念系统的贫困和落后,可能是一个更要急迫改变的现状。毕竟,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已逾百年,而这些古老、蛮荒、陈旧的习俗,恰恰是社会现代转型必须要跨越、突破的东西,它们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是反过来说,这些陈旧、野蛮的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恰恰又构成社会现代转型的障碍和绊脚石,严重阻碍着现代文明的发育。于是,“农民城”,一个词语,便包含着两个文明形态、两个文明阶段、两种悖反的文化力量。其中的内在张力,朱晓军把握得非常到位。他一方面,以超强的洞察力看到苍南人的苦难,看到农民们“进城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他以史家的笔法,记录着进城农民“第一代学会走红绿灯,第二代学会讲卫生”的艰难蜕变。农民们进城后,旧的习惯不改,从楼上往下扔垃圾、吐痰、泼脏水,大街小巷飘零着白的、红的、蓝的塑料袋,像飞舞的灵幡。作家叶永烈在龙港的街头看到,一堵刚刚砌成的、尚未粉刷的墙上,黑墨写着一行大字标语:“谁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乌龟”两字不是文字写成,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这些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可能需要一年、两年;而精神、观念、思维、价值层面的改变,则显然更为艰难,特别是涉及到利益上的纠缠,则更难改变。作品中写道,龙港原住民和外来者,因为观念、思维、风俗、语言不同,冲突不断,原住民瞧不起外来人,外来人也瞧不起原住民。原住民“秃头阿许”等,土地被征,征地款拿到了,却还把原来的土地当成自己的,欺行霸市,敲竹杠。凡此种种,皆为“农民城”之复杂性所在,内涵着不同文明层累的内在冲突。
说朱晓军有史家的“心法”,是因为他能够穿透事物本身。报告文学虽然说对事实、真实负责,但是,事实和真实究竟在哪?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原始的事实和真实。作家之所得、之所呈现,全在一个“看”字,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就是人对世界把握的不同方法。朱晓军的“看”法,是具有大历史视野的,他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结构中,去把握“中国农民城”的文化、文明内涵的,所以,他之所“见”、之所“得”,自有他的高度、深度和宽阔之处。“农民城”的文明二元性,文明体内部的各种冲突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必要的过程,唯有经过冲突,融创出新的文明形态,方是“中国农民城”的方正大道。而温州龙港这座“农民城”,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和价值,就是做中国城市改革、城市治理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试验田。“龙港经验”,其意义不在龙港,而在中国,在未来。
朱晓军写龙港,但不限于一隅,全书纵横开阖,以龙港为聚焦点,写到县、市、省和中央各层级,写到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龙港这个农民城能够从无到有,陈定模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势,陈定模不可能成功,“农民城”也不可能成功。而这当中,陈定模和“农民城”的成功,也归功于陈定模遇到了开明的县委书记胡万里、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时也运也,时运的叠加,成就了陈定模,成就了“农民城”。
三
作为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的材料运用非常扎实,涉及到的面很广。朱晓军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获取哪些材料,获取到什么程度,如何获取,获取的材料如何使用?朱晓军心知肚明。他的田野调查功夫,在《中国农民城》这部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材料搜集和田野调查上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少,举凡苍南的地理、疆域、建制、人口、交通、港口、耕地,以及不同时期的GDP、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率等经济数据,朱晓军掌握得非常详尽,这些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充实的数据支持。比如在写到江南人历史上的历次宗族群体械斗时,《中国农民城》动用了大量的数据,具体的年代、械斗的场次、死伤人数、烧毁房屋间数、财产损失数量等,俱以数据说话。其中涉及到的1967—1991年间,全以数据说话,“共发生大小宗族械斗1000多起(其中,发生于1979年底以前的,约700—800起,发生于1980—1983年间的65起),死亡20人,伤39人(其中重伤8人),烧毁房屋218间,直接经济损失在300万元以上”。《中国农民城》所涉材料,有的来自作家对当事人的访谈,有的来自作家的田野调查,有的来自政府的官方文件和会议决议记录等,有的来自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有的则来自作家自己的文献搜集。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形成的是一个立体的材料支撑系统。
朱晓军创作中突入材料之深,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写陈定模一家逃荒的线路,具体到每一个地名:先是亲戚划船送他们去桥墩镇,船过灵溪,他们在桥墩三十六村上岸,然后过崎岖陡峭、狭窄险恶的枫树湾,最后到达福建桐山,一家四口人,最后在山下祠堂的戏台下安顿了下来。这些清晰的细节,见出朱晓军的用心、用力。他甚至对温州的方言体系都做了深入细致的了解,知道苍南的方言包括瓯话、闽南语、蛮话、金乡话、畲话等。他还知道具体的方言地理分布,如说蛮话的主要是南垟片区,包括钱库镇、炎亭镇、金乡镇、望里镇等。在《中国农民城》中,朱晓军不时穿插着苍南地区的方言,包括地方的风俗、土语、饮食等,如温州的蛮话“清谈清谈”“阿娘阿娘没想”等,写到金乡的小吃,如“油锅”;写到金乡的风俗,如“暖灶”等。温州方言本就繁复难懂,朱晓军以一个东北人的语言、思维和习惯,去切近温州的语言、风俗和习惯,自然是不可能的。朱晓军的目的,自然也不是想去掌握温州的方言。他是尽自己的可能,去把他所叙述到的人物、事件,还原到温州的特定场域中。而这种将叙述对象还原到特定叙述场景中的做法,恰恰是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专业素养和自我高要求的体现。正是因为对温州方言地理的了解,所以在写陈定模到龙港后的第一次镇委、镇政府会议时,朱晓军才能够写出会场上镇委、镇政府几个人参会时,因为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会场上大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的丰富细节,有的说蛮话,有的说闽南话,有的说金乡话,有的讲宜山话,语言各自不同,且不相通,又极为难懂。语言的“隔”,意味着人心的“散”,意味着“农民城”建设的不易。
我们知道,报告文学是需要材料作为支撑的,因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事实与真实,作家获得事实与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事实调查和获取材料。没有完备的材料,想写出有深度的、有现场感的、高质量的报告文学,是绝无可能的。但是,材料又不是报告文学的决定性要素,否则,处在事件现场的经历者、知情者、旁观者,可以写出更为精彩的报告文学,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加原始、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材料。这就是说,材料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重要的,没有材料,报告文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反过来看,作家对材料的重要性,则显得更为根本,因为,作家对材料的处理和运用,是赋予材料以灵魂,让材料“说出”报告文学需要的事实和真相的最核心的手段。正是如此,作家创作报告文学,材料并非是以多多益善为妙,而是以合理的运用、独具匠心的运用,为报告文学的最高境界。
就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来看,他处理材料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朱晓军仿佛有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策略与智慧。他的材料运用的第一个妙处,就是回到材料的地方感、现场感,以“深描”之法,去描写一个地方的地理事物。就像人类学家对一个地方的描写那样,朱晓军所抓住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然后去理解这个文化,描述这样一种文化,在一个文化的具体场景中,去复建报告文学涉及到的人和事物的具象性的场景,以及人和事物得以产生的地方性逻辑。所以,朱晓军写苍南和龙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的描写,是他对苍南和龙港人的文化性格的一种把握形式。作品中,朱晓军多次写到龙港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下,人的特定的观念、心理、态度、情绪的形成,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他们价值观念世界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揭示出“农民城”建设的初衷和逻辑。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做过不少分析。朱晓军“深描”之法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写出“地方”的历史感。比如写方岩下村,就写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坊额下”。在当地,方岩与坊额音谐,以地处元代乡贤林约仲所立石碑坊下获名。写方岩下的一个内河渡口,则溯其原始,原称“安澜渡”,清同治七年所建,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些都是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再比如写金乡,他写道,“那是一座古镇,古称瀛洲,濒临东海,三面环山,山外环海,山海回环。传说三国时周瑜在那训练过水军。明洪武二十年置卫筑城,称金乡卫”。[1]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131。金乡本就是城,且据说金乡人大多是戚继光的后裔,“讲着接近上海话和宁波话的金乡话”,所以,金乡人从不讲蛮话和闽南话,他们只讲金乡话,这是由他们的历史感和地理优越感决定的。
《中国农民城》中,朱晓军驾驭材料的另一个特点,即是“深描”其时代感。作品涉及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但是又不局限在八十年代,而是上下勾连,贯通起一个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到新世纪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朱晓军渲染时代感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使用历史图片。整本书中,朱晓军动用了30幅左右的历史图片,这些图片包括地图、人口地理分布图、建筑图像、地表图像、规划图、个人生活肖像、集体合影、媒体图像等。图像的背后,隐伏的是国家的大历史和个人的小历史,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也是一个时代的肖像,更是一个时代人们文化心理的呈现。如书中有一幅图,1988年,龙港的标志性建筑“七层楼”,此楼由农民企业家林上木所建。这是当时龙港最高的楼,但是最醒目的,并不是这个“七层楼”,而是楼顶赫然建起的一层钟楼。钟楼和鼓楼,是古人报时之用。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宵禁开始;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钟楼和鼓楼多建于宫廷、寺庙、都城。那时候的林上木,不仅建起镇上最高的“七层楼”,还建起令人仰视的“钟楼”。这样一幅图片,唤起的是人们对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暴发户气质的历史记忆。图像,是历史想象的方法,朱晓军通过图像的形式,将读者拉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除图像外,《中国农民城》之为一个时代赋形,还有服饰、饮食、语言等手段。如作品中写到的尿素袋子。“文革”后期,中国从日本进口大量尿素,因为白色的尿素袋子是人造棉(化纤成分),所以化肥用完后,袋子多被人用来做衣服穿,“来个社干部,穿个化肥裤。前面‘日本产’,后头是‘尿素’”“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此一场景,就是极具时代感的一个场景。今天的人看来未免有些滑稽可笑,但在那时的人眼里,能有“飘飘裤”穿,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陈定模倘若不是在供销社工作,就难有这近水楼台之便,根本不可能给他大哥送尿素袋子。再比如语言方面,朱晓军也尽量以还原之法,将人物的语言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如写李其铁和陈迎春谈恋爱:“我比较喜欢你”——恋爱六年后,李其铁对陈迎春说。陈迎春说:“我也比较欣赏你。”“喜欢”和“欣赏”,既弥漫着那个时代的拘谨气息,也显示出男女有别的分寸感;而再加一个“比较”,则更显得那个时候的拘谨和分寸了。
总的来说,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无论是写人还是纪事,都有其独特的、成功的地方,写人,则重在同其心,叙事,则重在原其理。朱晓军善于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提炼出具有说服力、冲击力的材料,去构造报告文学的“事实”,构造报告文学的“事理”,构造出作品中富有戏剧性、形式感和文学化的情节和情境。朱晓军以文学择取本事,敷衍本事而为文学,《中国农民城》当之无愧是一部有历史感、时代感,且有文化深刻性和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