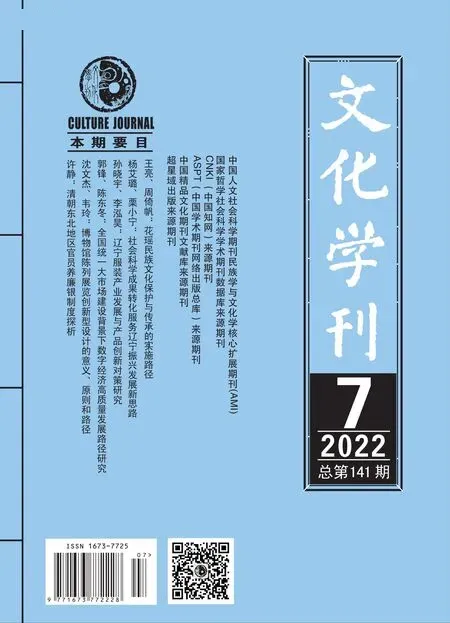地域空间的自觉书写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析双雪涛小说
2022-11-25肖振宇
王 超 肖振宇
近年来,一批“80后”东北作家集中涌现,让我们看到东北白山黑水间蕴藏的文学力量。黄平等学者以包括双雪涛在内的“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双雪涛自201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翅鬼》获奖到2021年《刺杀小说家》搬上荧屏,再到《刺客爱人》发表,凭借其优质的小说创作,成为“80后”小说家中不可忽视的存在,而他的创作与东北的地理历史和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本文尝试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把双雪涛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小说中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意象,思考双雪涛小说和特定文学空间的精神联系。
一、空间地域与文化精神的自觉
故乡是人们的精神皈依,人们受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影响,形成独特的地方感。“每一个作家都要有自己的领地,最终把这领地建立起一个文学王国……这个领地一般而言就是生养你的故乡。”[1]双雪涛的小说常把东北地区的地理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这源自于他的地域文化精神的自觉。
(一)自然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
东北地区的密林河泽,朔风大雪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生长于此的儿女,塑造着双雪涛的地理感知和地理视野,赋予作家独特的性情和取之不尽的题材。
双雪涛的文学风格像朔风一般冷峻、干脆直白;像雪一样静默,旁观苦难又掩藏着苦痛,雪化后又留下一丝温情。这与东北四季分明的气候,尤其是严寒漫长的冬季有关。钟嵘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2]意思是气候变化引起物质世界改变,使人感情激动,“形诸舞咏”,创作出了文学文本。王富仁评论东北作家心里都有一块磐石压抑着许多不可名状的情绪,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东北的天气一般荒凉寒冷。东北的气候影响双雪涛日常生活的性格,甚至是创作个性,分析小说的言语组织和文体特色可以感受他的文学风格。双雪涛多写中短篇小说,语言较少运用地方方言却常用东北人惯用的语序和句式,叙述简练利落,这种带有地方风格的语言有利于双雪涛小说地理空间的建构。他在《光明堂》中通过张国富、张默父子三言两语的对话勾勒出“艳粉街”地图。无论是《自由落体》里“我们”对待外公死亡的态度,还是《我的朋友安德烈》里他对集体观火化的描写,语言都冷静内敛如钢铁般坚硬,坚硬外壳下隐藏着他的人文关怀,蕴藏着对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正如双雪涛所说:“感谢我的家乡每年准时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这寒冷使我更加坚定地去靠近某种温暖的东西”[3]。
双雪涛对自己生长的环境熟稔,写起东北的相关题材也轻车熟路。东北地理环境对小说情节展开和人物选择发挥作用。双雪涛把沈阳、铁西、锦州、玻璃城子等具体地方设置为人物的活动空间,便于书写在这样环境下生长的具有独特气质的人们。即便他在完成《飞行家》之后开始转型,移居到北京拓展了地理视野,小说中的东北印记却始终存在。他把一些人物的故乡设置为东北小城,将现实与东北记忆连接。极具地域特色的物候导致东北拥有独特的文学内部景观。双雪涛常常把冬景作为小说的自然环境。
(二)人文环境对精神品格的塑造
人文环境泛指人类为求生存发展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要素,孕育了独特的文化,从而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影响人们对待人生境遇的态度。双雪涛透过城市图景观察时代变革中人们的选择及命运走向,并将冷静克制的笔触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塑造面对苦难仍保持坚韧的人物形象。东北自古以来民族众多,文化成分复杂,是由渔猎游牧文化、明清以来关内移民传播的农耕文化、俄日侵占带来的外来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长期交流融合而成。东北文化多元,人们有包容心态,接纳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同时,生存的苦难锻造了东北人阳刚坚韧、勇敢进取的精神。
双雪涛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在写作方面博采众长。东北人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心态对其创作产生一定影响。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多元文化冲击,东北在文学方面打破现实主义统一局面出现紧跟文学潮流的先锋小说,双雪涛学习先锋小说家“上接传统,外学西人,自明道路”[4]的经验,以现代的眼光对东北文化进行切合时代的汲取和重构,因此,可以从小说中挖掘出东北的一些地域文化因素。
双雪涛出生于沈阳这个东北工业城市,成长在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间节点上,目睹了工业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把现代社会景观投射在小说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逐渐成为东北现代化的支柱产业,而东北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工厂改制成为一个区域的时代“阵痛”。双雪涛将个人与城市的历史同步,小说多以“子一代”的视角通过回忆或其他方式聚焦那些被历史前进的车轮落在后面的群体。双雪涛把工厂关闭、城区拆迁等事件和烟囱、旧铁道、停摆的工厂等工业景观写入小说。在《北方化为乌有》等小说里通过人物间接描绘20世纪末期东北下岗潮来袭时的社会图景。
工厂是折射社会变化的典型,“父一辈”的命运与没落的工厂同步,双雪涛笔下的“父一辈”背负家庭重任,在苦难中展现出乐观坚韧的品质。下岗的工人们秉承艰苦奋斗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困顿的生活中不断找寻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例如,《大师》中的父亲痴迷下棋,通过下棋获得成就感来弥合残酷的现实生活带给他的创伤,获得短暂的停歇。《飞行家》中的工人李明奇热衷于制造飞行器,不断追求技术的突破,并在黑暗的屋顶上表明梦想,积极反抗既有的现实,倔强地守护自己的尊严和梦想,给予了小说中的“我”这些“子一代”们力量。双雪涛通过描写这些满怀伤痛却有一腔孤勇的父辈,展现底层群众对东北地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表达自己对人情人性的理解。
二、地理因素与文学空间的建设
双雪涛凭借对东北的记忆和想象构建了独特的地理空间。接下来重点分析双雪涛小说构建的地理空间和描绘的典型地理意象。
(一)艳粉街: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
“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5]在双雪涛小说中,“艳粉街”便是他参照现实地点建构的文学地理空间。现实中的“艳粉街”是一个位于沈阳铁西区的坐标性地点,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工厂拔地而起步入城市化,后来棚户区改造,高楼大厦蜂起,见证了沈阳的城市化进程,承载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部记忆。双雪涛凭借地理基因和地理想象通过描绘孙育新诊所、教堂、煤电四营、影子湖等地方和人们的日常活动逐步填充地理空间。在《光明堂》里,双雪涛通过张国富为儿子指路时口头描绘的艳粉街地图和张默的行踪构建出艳粉街地理空间。“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6]
“艳粉街”作为一个文学虚构空间重构、再现和超越了真实空间。“艳粉街”及里面的人与物都是双雪涛基于现实的一种虚构和想象,是代表作者情感的符号,是承载故事的记忆场。《走出格勒》明确“艳粉街”是一片位于城郊结合区的旧城,在现实中早已经历大规模改造不复旧貌,双雪涛深知文学源于现实高于生活,为避免读者按图索骥,故意留下线索提醒读者想象与现实的边界。“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而在现实中位于铁西区,而不在市东区。《光明堂》中的“艳粉街”在张国富看来是圆环状的,令人感觉封闭,可在地图上显示四通八达。这说明了再现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历史并非其写作目的,而是为小说人物行动和情感转变构筑一个专属的地理空间。
因此,揭示双雪涛塑造的“艳粉街”地理空间的意义很必要,他在小说中构建的独特空间一方面利于主题表达与人物塑造,另一方面也利于体现个人的审美个性与创作理想。作者记忆中的“艳粉街”早已不在,他把城市记忆与个人经验融合并以低机位视角环顾“艳粉街”,使其容纳了底层群众挣扎存活的生存状态、集体记忆和东北普遍性的历史经验。艳粉街成为作者观察、想象和讲述的地方,是故事不断上演的场所,更是将回忆、当下和未来的时间沟通,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打破的地理空间。
(二)雪:空间意象的营造
双雪涛笔下典型的地理意象就是“雪”,这是最能彰显小说地域色彩的意象。张伟然认为,“文学地理学所讲的地理意象,是可以被文学家一再书写、被文学读者一再感知的。”[7]双雪涛在访谈中说:“我是个东北人,那儿老下雪……天然的影响了我的思维。”[8]在他的文本中,“雪”是形象可感的地理景观,也是东北地域空间里的意蕴丰富的地理意象。
“雪”几乎是双雪涛小说永恒的故事背景。东北大地漫天飞雪,万物凋零。《长眠》中“我”与老萧初遇时“雪片很大,密密麻麻地落下。”雪是小说的背景环境,推动着情节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双雪涛重要的叙述手段。在《间距》中,雪呈现了多种不同的形态:从雨到完全变成雪,再到疯马快喝完威士忌时雪连成线,最终“过了一会儿,外面的雪停了。”双雪涛以雪状态的不同对应情节的转变,雪的变化暗示了小说情节发展。这与《光明堂》里“雪”的作用一致,第一场粉末状的雪对应父亲离开,傍晚的大雪与林牧师布道呼应,大雪飞舞与林牧师被杀对应。当“我”和姑鸟儿寻找真相时,雪的状态与作者的叙述节奏相互呼应,雪在无形中被赋予了场景转换、人物命运暗示的功能。
“雪”作为书中的地理意象,也是一个文化聚合体,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重要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双雪涛第一次去台湾领奖时,南北方冬季的差异给他灵感,将自己对雪的感受与雪自身承载的社会文化意蕴结合在一起。“雪”是东北的一种地域景观,象征着永恒和不变,并以自己的不变见证社会的变迁,见证底层群众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状态,记录城市历史和市民的生活故事。“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很黏”[9]这是《光明堂》里李默看见的场景,屋外飘雪,母亲离开父亲下岗,少年被迫成长。双雪涛在小说中经常塑造以“默”字为名的安静且好学的少年形象,通过少年的视角书写一代人自身不足为外人道的压抑和苦难。而这里关于雪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以局外人的身份见证了一代东北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和心路历程。
三、结语
双雪涛是东北土生土长的作家。东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双雪涛的审美倾向和创作风格,他凭借自己的地理想象和地理基因,把现实空间投射到小说的文学空间构筑中。即使如今的双雪涛寻求创作方面的转型,刻意地与家乡保持一定距离,努力从定型化的塑造中挣脱,但东北的地域文化已然融入到作家生命中,凝聚了双雪涛的地理感知和情感诉求,东北已经内化为双雪涛小说的一个地理符号、写作背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段记忆和这一空间纳入小说创作中。通过这种书写方式,把现实与虚构融合,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去呈现和赋形底层群众在“百年大变局”中的身体的创痛与精神灵魂的深度蜕变。本文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思考双雪涛的文学创作和作品,探索东北对他创作的影响,希望为读者理解双雪涛小说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