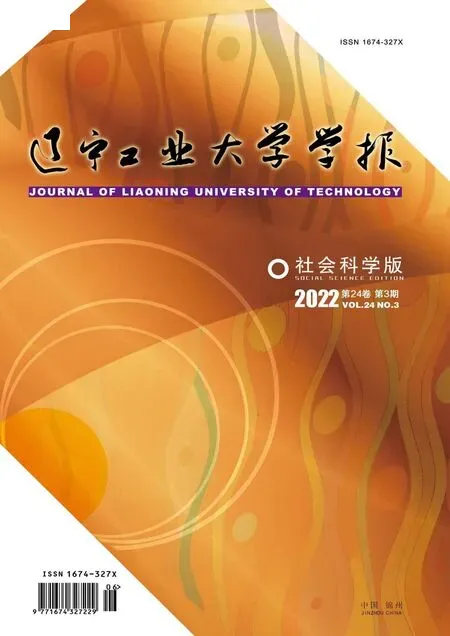《诗经》狩猎诗的文化解读
2022-11-25张清清
张清清
《诗经》狩猎诗的文化解读
张清清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狩猎活动是古代先民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与军事活动密切相连。在《诗经》中有重要的体现,涉及的诗歌有十四篇之多,无论是关于狩猎场景、猎人形象的记载,还是同狩猎有关的生活记载,都是先民们生产活动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诗歌既是对先民们尚武精神的赞美,又是美刺劝诫的结合,更是对社会习俗的遵循,亦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
《诗经》;狩猎诗;文化解读
狩猎活动是古代先民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常见的创作题材。最早关于狩猎的文化记载是原始歌谣,《吴越春秋》卷五《弹歌》中写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1]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却记载了先民们从制造狩猎工具到实施整个狩猎活动的全过程。《诗经》被称为中国古代狩猎诗的第一个小高峰,也包含了丰富的狩猎文化内容,305篇作品中涉及到狩猎的诗歌有14篇之多,这些诗歌均是先民们生产活动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学价值。
一、《诗经》中“狩猎”的记载
《诗经》中有14篇是狩猎诗,按其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描写狩猎的场面,具体作品包括《郑风·大叔于田》《秦风·驷驖》《车攻》和《吉日》4首;第二类是猎手风姿的记载,涉及的作品有《周南·兔罝》《召南·驺虞》《郑风·叔于田》《齐风·还》《齐风·卢令》《齐风·猗嗟》6首;第三类是与狩猎有关的生活的记载,主要作品有《召南·野有死麕》《郑风·女曰鸡鸣》《魏风·伐檀》《豳风·七月》4首。
(一)狩猎场景的记载
《诗经》中有4首狩猎诗是关于狩猎场景的记载,诗人对于这些狩猎场景的描绘可谓是既生动又细致,短短的几句话语就刻画出了围猎的壮观与复杂。
《郑风·大叔于田》用不长的篇幅展现出猎人娴熟的驾车技能,高超的射技。“执辔如组,两骖如舞”[2]244“两服上襄,两骖雁行”[2]245“两服齐首,两骖如手”[2]246等词交代了古代车马的具体部件,既生动刻画出骏马的矫健,又巧妙地写出了狩猎人的身份高贵。接着,用“火烈具举”[2]244“袒裼暴虎”[2]244等详细的射击动作以及空手打虎的细节刻画出了一个勇猛的青年猎手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全诗有张有弛,既有紧张气氛的渲染,也有舒缓的节奏,动静结合,富有韵味,运用精工细描的手法将整个狩猎场景写活了,诚如姚际恒在《诗经通论》所言:“描摹工绝,铺张亦复,淋漓尽致,便为《长杨》《羽猎》之祖。”[3]可见,这种精工细描的手法所产生的影响之大。《秦风·驷驖》中对狩猎场景的描绘更加精妙,以少胜多,以简寓繁。“驷驖孔阜,六辔在手”[2]361首章以四匹高头大马切入,将整个场景带入严整肃穆的氛围中。“奉时辰牡,辰牡孔硕”[2]362,讲述了具体的狩猎场景,听到正式开始的锣鼓响起,在牢圈樊笼里的时令兽被狩猎官取出,众人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最后用“輶车鸾镳,载猃歇骄”[2]362一句,将先前的紧张与现实的闲适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车攻》将狩猎场景描写得更加浩大,更加精妙,“它将西周时期王侯田猎生活情景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手法,将情、景、声、态等集于一诗。”[4]全诗分为八章,首章写的是车马备好,即将启程的场景,第二、三章点明了狩猎的意图以及所带车马的华美高大和军队的声势浩大,第四章写出了各路诸侯会合的场景,第五、六两章写出了狩猎时的盛况,车夫驾车技术非常娴熟,射手狩猎水平非常高超,第七章是狩猎结束之后的欢乐场景,末章用赞叹之词结尾,凸显出了严肃的气氛。《吉日》则是一篇周宣王以狩猎活动来宴享群臣的诗篇,《毛诗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5]251全诗分为四章,首章仍旧是写狩猎前的准备,车马已备好,准备出猎,二、三章交代了狩猎之地的环境,那里猎物群集,壮大肥美,末章写出了狩猎的结果,射手一射即中,场景十分壮观,结尾仍旧以赞叹之词结尾,展现出严肃的氛围。
(二)猎人形象的记载
猎人在《诗经》写得极其生动,无论是贵族田猎、求仕武夫还是平民猎手,都得到了极其详尽的刻画。在描述中这些形象不是重复敷衍的,而是展现着不同阶层不同活动中猎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特征。
《周南·兔罝》展现了一场利用智谋进行捕猎的捕兽大战,武夫们将捕兽的网结得又紧又密,放置在分岔路口等待着猎物上钩,身为公候心腹的将士,各个意气昂扬,誓将猎物捕获。虽然整首诗对于盛大的狩猎过程没有进行具体的描述,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对狩猎将士的热烈赞美和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诗人赞美了猎手设网捕兔过程中的智慧、本领和英姿,进而想到了年轻的猎手是保家卫国的勇士,用“干城”[2]21“好仇”[2]22“腹心”[2]22层层推进将年轻的猎手的才能叙写得十分形象。《召南·驺虞》是一首赞叹驺虞善射的短歌,“彼茁者葭”[2]64“彼茁者蓬”[2]65写出了猎人射击用的武器是芦苇和蓬蒿,“壹发五豵”[2]65则说明了猎人的射击过程和射击结果,把对这位猎手的所有赞美都体现在这声惊叹中。《郑风·叔于田》也是赞美猎人的诗歌,用女子的口吻写出了对仰慕之人的赞美之情。用“巷无居人”[2]242“巷无饮酒”[2]242“巷无服马”[2]243“岂无居人”[2]242“岂无饮酒”[2]242“岂无服马”[2]243“不如叔也”[2]242“洵美且仁”[2]242“洵美且好”[2]242“洵美且武”[2]243来铺叙对年轻男子的赞叹,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一位美好仁慈、漂亮清秀、英武勇敢的年轻猎人形象。
《齐风·还》描写了两个初次见面的猎人协同打猎的场景,诗人用简练的笔墨诉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短短数句,男人的直率、火热、有情、矫健便跃然纸上,把读者带到了那个质朴而又纯真的狩猎时代。首句开口便赞誉,将对方射手的轻捷脱口而出,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由衷的仰慕之情,以诉说的口吻把作者所要表达的喜悦之情推向了高潮。《齐风·卢令》用“美且仁”[2]300“美且鬈”[2]300“美且偲”[2]301夸赞了主人公优秀的品行和才干。《齐风·猗嗟》赞美的是少年射手,采用铺陈的手法,以赞美的口语,夸张的笔调,从各个角度描述了少年射手的出众才华,细致生动。
(三)狩猎生活的记载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有描摹和保存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物象的作用[6]。狩猎在周代仍占重要地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祭祀、经济、政治、军事和娱乐等多种意义,在《诗经》中也有重要的体现。
《召南·野有死麕》是表现男女约会的诗篇。诗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猎手,女主人公是一位姑娘,文字十分朴实率真,以旁观者的角度娓娓道来,将卿卿我我的言语表现得十分生动,从侧面表现了男子的炽热直接和女子的含羞谨慎。尤其是最后一段中男子送女子的礼物是他打来的猎物,在他们这段恋情上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7]30。《郑风·女曰鸡鸣》描写了一对平民夫妻在天色未明刚醒来时的对话。诗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猎手,勤勉持家,以打猎作为生活的手段,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由此可见,这两首诗都是反映日常男女的生活方式,初读可能少有新意,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是多么淳朴和谐,让人的生活都多了一丝宁静。
《魏风·伐檀》用“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2]322“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2]323“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2]324来讽刺剥削阶级的坐享其成。全诗使用质问的口吻,来表达诗人对不平命运的愤怒。狩猎本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辛辛苦苦获得的猎物却要上交给统治者,统治者不思如何巩固社稷,整日坐享其成搜刮劳动人民,将他们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现出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豳风·七月》以“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2]440写出奴隶们打来的猎物,还要清理好皮毛才能给那些贵族做皮袄用,打来的大猪要贡献给那些王公,只有小猪才能留下自己吃,再次深刻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奴隶的剥削。
二、《诗经》中“狩猎”活动的文化内涵
狩猎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特定活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中有着重要意义[7]30。这些诗歌,既是对先民尚武精神的一种赞美,又是美刺劝诫的结合,更是对社会习俗的遵循,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对尚武精神的赞美
古人认为国家要强盛离不开文治武功,体魄强健,好勇善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以这种标准与眼光来衡量和观察各种人物,男子是否有尚武精神,也成为一种审美取向。射击作为六艺之一是男子必备的技能,也是男子具有尚武精神的一种重要表现。
《诗经》中有11首诗歌赞美了猎手的尚武精神。《周南·兔罝》赞美的是年轻猎手的勇猛,夸赞他们是“公侯干城”[2]21“公侯好仇”[2]22“公侯腹心”[2]22;《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男主人公因为自己的狩猎水平赢得了女子的芳心;《召南·驺虞》赞美的是一名管理囿园的年轻射手的高超技艺;《郑风·叔于田》用“洵美且仁”[2]242“洵美且好”[2]242“洵美且武”[2]243来层层夸赞射手的勇敢;《郑风·大叔于田》用“叔善射忌,又良御忌”[2]245进行夸赞;《郑风·女曰鸡鸣》通过普通夫妻的对话来夸赞射手的勤勉持家;《齐风·还》更加细腻,以“还”“儇”“茂”“好”“昌”“臧”等带有美好性质的词夸赞年轻的猎手;《齐风·卢令》用“美且仁”[2]300“美且鬈”[2]300“美且偲”[2]301夸赞射手美好的品质;《齐风·猗嗟》以“猗嗟昌兮,颀而长兮”[2]307“射则贯兮,四矢反兮”[2]308来赞叹射手们超群的技艺;《秦风·驷驖》用“舍拔则获”[2]362来赞叹武士们的勇武;《车攻》和《吉日》整篇都对狩猎的男子充满赞赏的口吻。他们都具有强健的体魄,矫健的身手,高超的技艺,是古代尚武精神的代表者。
(二)美刺劝诫的结合
《诗经》是中国讽刺文学的源头,揭露和讽刺剥削阶级是《诗经》的主旨之一。而讽刺的目的也在于告诫当朝统治者应当吸取教训,做到政治清明,百姓爱戴。《诗经》中带有讽刺性质的狩猎诗有9首之多。
《召南·驺虞》既是赞颂诗,又是劝诫诗。《毛诗序》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笺:“应者,应德,自远而至。”[5]32《毛诗序》认为,《驺虞》其实赞颂的是周文王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的景象,用以劝诫当朝统治者应当行仁政,施教化。《郑风·叔于田》和《郑风·大叔于田》都是讽刺郑庄公的诗作,《毛诗序》曰:“《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悦而归之。”[5]104“《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笺》:“缮之言善也。甲,铠也。”[5]105叔特指共叔段,诗歌虽是在写射手的勇敢,善于骑射,实则暗含了郑庄公对弟弟的放纵。方玉润《诗经原始》:“案此诗与前篇同为刺庄公纵弟游猎之作,但前篇虚写,此篇实赋,前篇私游,此篇从猎,而愈矜其勇也。”[8]206由此可见,这两篇诗作都是委婉的讽刺劝诫庄公之作。
《齐风·还》也是一首讽刺诗,《毛诗序》曰:“《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笺》:“荒谓政事废乱。”[5]135这首诗作是讽刺齐哀公荒废政事,把狩猎当作风俗,成为游手好闲之辈,导致民不聊生。《齐风·卢令》亦是讽刺君主之作。《毛诗序》:“《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笺》:“毕,噣也。弋,缴射也。”[5]132这首诗歌讽刺的是齐国另一个君主,齐襄公爱好狩猎,荒废政事,使得百姓苦不堪言。《齐风·猗嗟》是讽刺鲁庄公之作。《毛诗序》曰:“《猗嗟》,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5]136鲁庄公才艺出众,然而未尽到为人子的本分,让人唏嘘。
《郑风·女曰鸡鸣》描写了一对平民夫妻宁静而温馨的对话,塑造的主人公是一对勤勉的夫妻,通过他们的对话来劝诫人们应当学会勤俭持家,有德行。《毛诗序》曰:“《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笺》:“德,谓士大夫宾客有德者。”[5]110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道:“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辞。”称“贤妇警夫以成德也。”[8]211方玉润认为一个好的家庭应当是妻子贤惠,丈夫勤奋,妻子应当时常劝诫自己的丈夫要勤俭持家才会生活得和睦而温馨。《魏风·伐檀》和《豳风·七月》都以打猎来讽刺剥削者、统治者对平民百姓的迫害,感叹社会的不公。《毛诗序》曰:“《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5]143《笺》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禄。”[5]143在诗中,统治者不用打猎,就可以有肉吃,有美味佳肴,有锦帽貂裘,穷人打了猎,却依旧只能吃到和用到很少的一部分。
(三)社会习俗的遵循
狩猎活动是对社会习俗的遵循。不管是作为一种自然时令到来时的生活手段,还是与政治相关,都是一种社会习俗。《豳风·七月》和《小雅·车攻》是其典型代表。
在《豳风·七月》中,诗人是按照月份将劳动进行了划分,反映了自然的时序。诗中所对应的十一月是捕狩禽兽的时间。《吉日》是一首周王室田猎宴宾的诗歌。《毛诗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5]251这首诗是与政治相联系的,周天子以田猎来设宴款待群臣,反映了西周时期常规性岁典活动的情况,歌颂了当局者的政治清明。
三、《诗经》“狩猎诗”的文学价值
《诗经》狩猎诗的文学价值亦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对后世文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种文体上,一种是赋,另一种便是诗歌。同时,也是中国讽刺文学的源头。
(一)《诗经》狩猎诗对赋的影响
从《诗经》开始,狩猎主题便成为中国文学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对于汉代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在汉代,赋是一种主要的文体,十分盛行,枚乘的《七发》应该作为狩猎题材的首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以狩猎为题材,对汉赋具有开拓意义。扬雄的《羽猎赋》亦是狩猎题材的典型代表。东汉时期,班固的《东都赋》和《西都赋》更是吸收了《诗经》中狩猎诗的文化精髓。
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借用子虚的口吻讲述齐王田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9]126,以此来表现汉王朝的强盛。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在写大肆捕猎之后,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认为“此大奢侈”,于是“解酒罢猎”[9]128。由此可见,在汉赋中,狩猎题材的作品主题仍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二)《诗经》狩猎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以狩猎为题材的诗歌在后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0]。曹丕写有《游猎诗》,刘桢写有《射鸢诗》北朝时的庾信写有《伏闻游猎诗》,它们都是狩猎题材文学的典型代表。以狩猎为题材的诗歌,至唐代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唐宋时期的王维写有《观猎》、苏轼写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均是对《诗经》中狩猎诗的继承和发展。
(三)《诗经》狩猎诗开创了讽刺文学的先河
《诗经》里的狩猎诗是最具有现实精神和最富有战斗性的诗篇[11],其作者群体性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产物,开创了我国讽刺文学的先河,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屈原忧愤深广的政治抒情诗《离骚》和抒发“郁结纡轸”之怀的《九章》、司马迁“发愤著书”创作的《史记》就直承《诗经》狩猎诗中的怨刺讽喻精神。此后,关注民生的建安诗人形成的建安风骨、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的吟咏、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意识,也正是上承《诗经》狩猎诗中的这种传统。
总之,《诗经》中的狩猎诗的描写广泛而又细致,类型多样,一方面记录了当时的日常生活活动,另一方面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使得狩猎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题材,为后期的赋、诗歌、散文增添了新的成分,开创了我国讽刺文学的先河,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1] 刘贵华. 先秦狩猎诗论[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6): 27.
[2]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3] 姚际恒. 诗经通论[M].邵杰, 点校.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58: 95.
[4] 殷光熹. 诗经中的田猎诗[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1): 04.
[5]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6] 刘昌安. 《诗经》二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38.
[7] 黄琳斌. 论《诗经》中的狩猎诗[J]. 凯里学院学报, 2000(2): 30.
[8] 方玉润. 诗经原始[M].李先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9]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0] 樊晶晖. 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D]. 福州: 华侨大学, 2019.
[11] 任慧. 《诗经》怨刺诗研究[D].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14.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3.016
I207
A
1674-327X (2022)03-0067-04
2021-12-09
张清清(1996-),女,陕西城固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