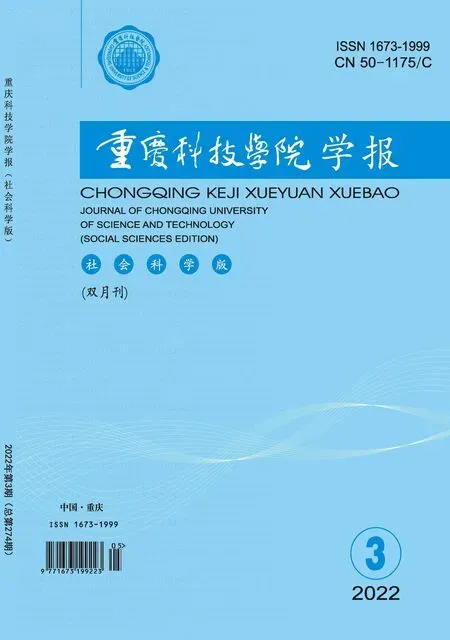诗词翻译中的转喻现象
2022-11-24侯奕茜
侯奕茜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加工过程,翻译活动必然要触及语言背后的“认知”和“现实”两个基本要素。语言转换仅是外在的、表面的,认知运作才是内在的、深层的。翻译表面上是在处理文字,实质上是一种心智活动,它背后存在大量的认知方式。人类思维的共通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但人类的认知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主观性,完全对等的翻译并不存在[1]。
概念转喻是人类日常思维方式的构成部分,翻译过程中也存在大量转喻现象。虽已有学者对其进行探讨,但切入点主要为非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相比,文学文本具有更强的民族性、文化性、地域性,它根植于创作民族的认知结构中。
本研究尝试以常用翻译技巧为切入点,以中国古代诗词英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对比,梳理诗词翻译这一认知加工活动中的转喻机制,分析背后的认知动因,以进一步探索翻译活动的本质。
一、概念转喻
(一)转喻的本质
“Metonymy”(转喻)一词源于拉丁文 denominatio,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1世纪的《修辞和解释》(Rhetorica ad Herennium)一书中。传统转喻研究将转喻视为一种修辞格、一种语言表达形式。Ullmann将转喻定义为词语义项之间的邻近性[2]。换言之,转喻即用事物A去替代事物B,A和B虽不同,但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转喻研究的认知转向。拉考夫和特纳将其定义为同一认知域中从源概念到目标概念的映射过程[3]。莱登和考威塞斯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即某个概念实体(转体)为处于同一认知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内另一概念实体(喻体)创造心理通道[4]35。兰盖克将转喻视为一种参照点现象,即用转喻表达的实体作为参照点为目标体提供心理通道[5]。潘森和索恩博格认为,概念转喻是同一认知域中源概念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认知操作过程。其中,源概念处于突显位置,而目标概念被虚化。两个概念域之间的关系是或然的,其连接强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概念距离和源域的突显程度[6]。
由此,转喻从修辞手段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人们通过源概念理解、表达目标概念。同隐喻一样,转喻也是人类日常思维方式的构成部分,也是人们认识、理解、概念化客观世界的工具。两者的区别在于,隐喻基于相似性,而转喻基于邻近性。隐喻涉及认知域的跨域映射,而转喻发生在同一认知域中。此外,虽然两者皆源于人的体验,但由于不同文化中(包括亚文化)人们体验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相关,使转喻比隐喻更具文化特征[7]。
(二)概念转喻的制约原则
基于转喻的本质,概念转喻需要遵循3条认知原则。一是邻近性原则。源概念和目标概念处于同一认知域中,认知过程不涉及跨域。二是凸显性原则。人类更易注意到事物中最突出、最易理解的属性,即相对凸显的属性。三是可及性原则。话语者采用表示不同属性的可及性的指称词语,接受者随后解读该指称关系,构建间接语境。此外,转喻的生成还受到交际原则的制约。为了满足交际的准确性和经济性,人们通常选取清楚明白、相关性强的事物去转指模糊不清、相关性弱的事物[8]。
(三)转喻的分类
在认知框架中,门多萨根据转喻中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互作用,将其分为源域寓于目标域的转喻和目标域寓于源域的转喻[9]。莱登和考威塞斯对转喻的分类最为系统、全面、合理,他们根据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关系将其分为两大类: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4]24-43。本研究依据莱登和考威塞斯的分类原则,将转喻拆分为3类: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部分代部分。整体和部分只是相对概念,前者指相对完整的概念,后者指附属于整体概念的局部概念[10]。
整体代部分。例如:这车该洗洗了。“车”有多个组成部分,包括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系统等。洗“车”指清洗“车身”。该句中,“车”转指“车身”,属整体代构成部分。
部分代整体。例如:He isreadingRomeo and Juliet.阅读事件域由一系列动作构成,包括坐、站、躺等姿势,将书置于手中或其他物体之上、打开书、翻页、移动视线等动作。“reading”属阅读事件中的主要动作,构成部分代整体转喻。又如:小张需要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属止痛药的一种,成员转指范畴,乃部分代整体。
部分代部分。例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为夏朝国君、传说中的酿酒始祖。句中“杜康”转指酒,乃生产者代产品,构成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互代。
(四)概念转喻与翻译
国内外概念转喻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主要分为转喻翻译(translating metonymy)和翻译转喻(metonymic translation)。前者指认知框架下转喻表达的翻译,后者指翻译活动中的转喻思维。铁木钦科提出了翻译转喻学(Metonymics of Translatoin),认为翻译活动具有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联系/创造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两个方面[11]。卢卫中等以非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翻译技巧“替换”背后的转喻机制,发现转喻是该技巧背后的重要认知动因,且翻译过程中译语和源语存在转喻关系[10]。王斌提出借代式(转喻)翻译,认为该策略有助于彰显个性化体认结构、构建新的共注观、整合译文概念结构[7]。王寅基于英语电影名汉译,在翻译转喻学的基础上建构了翻译的隐转喻学(Metaphtonymics),强调翻译过程既有隐喻性纵向选择词语的操作,也有转喻性横向组词成句的过程,它们始终混合运作,缺一不可[12]。本研究尝试在认知翻译框架下,从常用翻译技巧出发,梳理诗词翻译过程中的转喻现象,分析翻译技巧背后的认知动因。
二、诗词翻译中的转喻机制
翻译策略分为直译和意译,后者的实现依赖一系列翻译技巧。我们以中国古代诗词英译为例,梳理选词法、转换法、增译法、省略法等4种常用翻译技巧涉及的转喻操作,分析其背后的认知动因。
(一)选词法
各个民族将对现实的体验进行认知加工,便形成了语言形式。不同语言的语符根植于各民族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中。对同一事物,没有两个民族的体验和认知完全相同。英汉语言中看似对等的词汇,其语义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淑女”和“lady”,“淑女”一词源自《诗经·周南·关雎》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该词原指贤淑美好的女子,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同时代其语义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淑女兼具传统美德与现代价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lady”,其语义涵盖礼貌、有教养、举止文雅、贵妇人、(陌生)女士等。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对语符的意义反复斟酌。选词法包括选择词汇的情感意义、语法意义、语境意义以及文体意义。
1.情感意义
情感意义指词汇资源所承载的情感和态度。
例(1)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译文:
A maiden mute andtall,
Trysts me at corner wall.
I can find her nowhere,
Perplexed,I scratch my hair.
《静女》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幽会。“踟蹰”本意为原地打转,乃肢体动作。“Perplexed”意为“confused or worried”,它和“踟蹰”之前存在因果关系。男子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却迟迟不见心上人,内心开始迷惑焦虑,于是抓耳搔头、原地打转。“Perplexed”为因,“踟蹰”为果,译者用原因转指结果,体现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思维。
2.语法意义
英语讲求形合。一个完整句子中,主语会明确单复数,谓语会明确时态。这体现了英语民族对数量和时态的重视,才会将其反映在句法中。而汉语讲求意合,经常省略数量和时态。翻译时,译者需要在单复数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等时态中进行选择。
例(2)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译文 a:
Ican barely wake upin spring slumber,
As the chirping of birds is heard there and here.
译文 b:
In drowsy spring Isleptuntil daybreak,
When the birds cry here and there,I awake.
原文中“不觉晓”并未道明时态,需要通过语境推断。译文a选择了一般现在时“can”,译文b选择了过去时“slept”。这反映出两位译者对原文有不同的体验和认知。两个版本都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
例(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译文:
The peach treeis slender and sturdy,
Flaming red are itsblossoms.
原文“桃”指桃树,并未道明具体棵数。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体验——桃树映射文中即将出嫁的女子,将其译为单数“the peach tree”。原文“华”指果实,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及现实的体验——果树结果数量很多,通常为复数,同时“华”由“灼灼”修饰,从而将其译为复数“blossoms”。从句法角度讲,两种处理方式都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
3.语境意义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
例(4)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译文:
I presume you lie in thatheartbreakingplace year after year,
In that small round covered with pines mere,
Under the moon bright and clear.
“断肠”为隐喻,映射悲伤到极点。但此概念映射过程并不存在于译语读者的认知结构中。若直译,受众难免一头雾水。在英汉双语中,心碎/heartbreaking都可以映射极度悲伤。“断肠”和“heartbreaking”相比邻,译者采取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译法。
例(5)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译文 a:
Bright moon,when wast thou made?Holding mycup,I ask of the blue sky.
译文 b:
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Wine cupin my hand,I ask the sky.
酒种类繁多,如啤酒、红酒、白酒、黄酒、药酒等。根据创作的时代背景(唐朝)判断,诗人笔下的酒有3种可能——谷物发酵酒(米酒)、果酒(以葡萄酒为主)和配制酒。译文a中,译者以“cup”代替“酒”,体现了容器转指容纳物的转喻操作。译文b中,译者采用了双重转喻操作,首先以容器转指内容,其次以“wine”(葡萄酒)代替酒,属成员代范畴。
4.文体意义
不同的词汇虽然可以表示相似的语义,但却可以构成不同的文体特征。
例(6)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译文:
I lift my drink and sing asong,
For who knows if life be short orlong.
Man's life is but the morningdew.
Past days many,future onesfew.
原文押尾韵“e”和“u”,译文虽也押尾韵,但韵脚变成了“ong”和“ew”,构成韵脚之间的互代,属于部分代部分。原文由4字排比组成,内容上言简意赅,形式上整齐匀称,语音上顺口悦耳。4字结构并不存在于英语民族的认知中,译者未能传达原文词汇建构的文体意义,属于部分代整体。
(二)转换法
转换法可细分为词类转换、句子成分转换、句型转换、视角转换以及文体转换等。
1.词类转换
例(7)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译文:
Cloudsfloat like works of art,
Starsshoot with grief at heart.
Across the Milky Way the Cowherd meets the Maid.
“纤云”指轻盈的云彩,“飞星”指流星,亦指牛郎星、织女星。原文中,“纤”和“飞”为形容词,译文将其转换为动词。原文选择凸显属性、译文选择凸显动作,以动作代属性,构成部分代部分。“弄巧”指云彩在天空中幻化多变,“传恨”指流星传递着憾恨之情。原文凸显动作,译文凸显属性“like works of art”“with grief at heart”,以属性代动作,亦体现部分与部分的互代。
2.成分转换
例(8)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译文:
In oblivion allthose sages have died.History knows onlygreat drinkers.
原文中“寂寞”为表语,译文将其转换为状语“In oblivion”,状态代性质,属于部分代部分;“饮者”为主语,译文将其转换为宾语“great drinkers”,受事代施事,属于部分代部分。
3.句型转换
例(9)空方丈、散花何碍。
译文:
Fear not the flower petals thatdo no harm,
Though the heavenly maiden scatters them around.
原文虽以句号结尾,实则为反问句,答案不言自明,译文则将其转换为陈述句。问题“何碍”和答案“do no harm”位于同一认知域,构成邻近关系。以答案代问题,体现了转喻的认知操作过程。
例(10)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译文:
From hill to hill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no man in sight.
译者将“鸟飞绝”和“人踪灭”处理为“no bird in flight”和“no man in sight”,原文的肯定句变为否定句,不同的概念结构通向相似的语义。原文和译文调动不同的句型结构激活目标概念,体现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思维。
例(11)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译文:
At dusk it threatens snow,
Won't you come for a cup?
译者将一般疑问句“能饮一杯否?”处理为否定疑问句“Won't you come for a cup?”。原文和译文分别采用不同类型的问句表示邀约,属于部分代部分。
例(12)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
译文:
When time's due course doth age with white hair crown…
原文由两个并列名词短语“白发”“苍颜”构成。译文将其转化为“when”引导的状语从句,句型为SVO。原文通过名词短语凸显“白发苍颜”这一年龄增长的结果;译文通过SVO句型同时凸显原因“time's due course doth age”和结果“white hair crown”。体现了整体代部分的转喻思维。
4.视角转换
中文讲求意合,诗词中常省略主语。翻译中文诗词时,译者往往需要凭借自己对原文的体验和自己的认知集合增加主语。伴随着主语的增加,视角便发生转换。
例(13)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译文:
Even if we meet again, you can hardly recognize me by the way,
Formyface is fully covered with dust,
Andmytemples have as frost turned grey.
原文无主语,可以是任何视角,译文中“we”“my”将视角限定在第一人称,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操作。
例(14)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far from home isthe heartbroken me.
“断肠人”将视角锁定在第三人称,而译者将其处理为“the heartbroken me”,视角转为第一人称。不同视角之间的互代体现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思维。
5.文体转换
例(15)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餐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译文:
When time's due course doth age with white hair crown,
And Vimalakirti so well doth one become,
Fear not the flower petals that do not harm,
Though the heavenly maiden scatters them around.
Thy cherry lips woo, and thy hair glorifies,
So this eternal cycle of life goes on,
Because this sentient heart of love is fond,
Engenders human gestures and mortal ties.
I see thee sit with a sweetly pensive smile,
Setting thy curls or letting them archly fall.
Tomorrow is Tuanwu Day!Come,I shall
Pick thee a corsage of orchids,with a poets wile.
Discover the best poem that can be found,
And write it on the flowing lines of thy gown.
原文为苏轼所著《殢人娇·或云赠朝云》。殢人娇为词牌名。词为中国古代宴乐乐曲的歌词,乃诗的别体。它萌芽于南朝,兴起于隋唐,于宋进入鼎盛时期。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单句长、声韵等方面都有不同。《或云赠朝云》为双调68字,前后段各7句、四仄韵。林语堂将其转译成了一首十四行诗(Sonnet)。Sonnet萌芽于意大利,后传到欧洲其他国家。译文共14行,分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两节4行诗构成,第二部分由3节两行诗构成。为了韵脚的需要,第二部分第二节本为意义连贯的一句,但被拆为两行。整首诗共5个韵脚,排列为ABBC,DACD,EE,EE,CA。此外,译文每行轻重音搭配。之所以将译文称为类十四行诗,是因为词对英语人士来说是陌生而异域的,他们更熟悉十四行诗。它在结构、韵律方面虽然并不符合十四行诗的3种主流——彼得拉克体、莎士比亚体和斯宾塞体,但却具备该文体的基本特征。译者用一种文体代替另一种文体,实行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操作。
(三)增补法
增补法包括结构性增补和语义性增补。
1.结构性增补
例(16)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译文:
Thethread in mother's hand,
Agown for parting son.
译文中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均属结构性增补,使译文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原文和译文采用不同的句法结构指向相似的语义概念,体现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思维。
2.语义性增补
例(17)空方丈,散花何碍。
译文:
Thoughthe heavenly maidenscatters them (flower petals) around.
原文并没有道出 “散花”的动作发出者,只是通过语境可判断其为作者苏轼的侍妾。“heavenly maiden”的增加将中国古代官员的侍妾替换为西方侍女,体现了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操作。
例(18)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译文:
A thousand milesfrom home, I'm grieved at autumn's plight,
Ill now and then for years,alone I'm on this height.
Living in times so hard, at frosted hair I pine,
Cast downby poverty,I have to give up wine.
《登高》倾诉了杜甫常年漂泊异乡,老来体弱病残、穷困潦倒的复杂感情。译文中“from home”以及“by poverty”都属于增译,其目的是减少译文读者理解此诗的认知努力。其背后的转喻操作为整体代部分。
(四)省略法
省略法包括语义省略和文体省略。
1.语义省略
例(19)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
译文:
Flowers fade and fall and fly about up in the sky,
But who pities the loss of your fragrance when you die?
译者省去了原文“满”和“红绡”这两个概念,未能完整传达原文意象,换言之,原文只有局部意象得以再现,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
2.文体省略
例(20)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
I saw the moonlight before my couch,
And wondered if it were not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
《静夜思》为李白所作五言古诗。该诗体虽然对格律要求不严格,用韵较自由,不限长短也不讲平仄,但每句有且只有5个字。唐朝的古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翻译时,译者未能映射五言诗体,因为它本不存在于英语民族的文体库中,原文的文体风格未能成功再现。文体上的省略依然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操作。
三、翻译过程中转喻操作的认知动因
第三部分列出的诗歌翻译过程中的转喻现象涉及语义、句法、语境、文体等4个层面。概念转喻的生成需遵循3条认知原则:邻近性原则,源概念和目标概念处于同一认知域;凸显性原则,源概念比目标概念处于更加凸显的位置;可及性原则,源概念为目标概念提供认知可及的心理通道。这3条原则同样构成翻译过程中4个层面的转喻操作的认知动因。
(一)语义层面
例(1)中,“踟蹰”“perplexed”位于同一认知域。不同的情感会引发不同的肢体动作。悲痛时,人们捶胸顿足;高兴时,人们手舞足蹈;生气时,人们吹胡子瞪眼睛。情感为因,肢体动作为果,肢体语言乃情感的具象化。英汉民族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具有相通之处,译者通过“踟蹰”体验到人物的内心活动。但译者对原文和客观世界的体验又具有个人特色,在他的认知结构中,原因和结果相比,原因处于更加凸显的位置。因此,译者选择用情感替代肢体动作,通过“perplexed”激活译语读者对源概念“踟蹰”的认知。
例(5)中,两位译者分别用“cup”和“wine cup”替换原文的“酒”。“酒”“cup”“wine”都处于同一认知域,乃容器和内容的关系。当表达举起(盛酒的)酒杯时,作者选择“把酒”,但实际把的是酒杯。因为酒乃液体,只有盛在酒杯里才能把握。在作者认知中,内容比容器更加凸显。但在英语民族认知中,情况刚好相反,容器比内容更加凸显。英语母语者在祝酒时,往往会说raise your glass,而不是raise your wine。所以译者选择使用“cup”激活源概念“酒”。
(二)句法层面
语言来自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1]。民族不同,体验不同,语言不同。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语言。但语言和语言之间存在邻近关系,它们共同构成整个世界的交流系统。不同语言存在不同的语法、词汇资源。在表达基本对等的语义时,人类会调动不同的语法词汇资源。 例(2)(3)(7) (8)(9)(10)(11)(16) 中,鉴于汉语和英语在句法上面的差异,译者都采取了不同于原文、存在于译语读者认知结构,以及用他们所熟悉的语法资源构建基本对等的语义概念等翻译方法。不同的词汇资源为基本对等的语义概念提供了认知可及的心理通道。
(三)语境层面
将文本从源语读者的认知域转移到译语读者的认知域,必然会涉及语境的切换。两个语境相邻,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转喻操作。转喻思维不仅体现在文本外,也体现在文本内。例(15)(17)中,译者通过“the heavenly maiden”的增译,将作者苏轼的侍妾朝云替换为西方淑女,和朝云相关的描述也被替换,“hair”代“髻鬟”(环形发髻),“setting thy curls or letting them archly fall”代“敛云凝黛”, “a corsage of orchids”(西方女子佩戴于礼服或手腕上的小花束)代“(纫)兰为佩”(系于腰带上),“flowing lines of your gown”(饰边)代“裙带”(腰带)。对译语读者来说,他们更熟悉的西方社会的淑女在他们认知结构中足够凸显,而北宋女子对他们来说则是异域陌生人,转喻的操作使读者更能体验到原文中朝云的可爱美好,以及作者对她的喜爱和赞美。
(四)文体层面
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系统,它们都属于世界文学系统的一部分。翻译活动在两个文学系统之间建立了邻近关系。和语言一样,文学作品也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不同文学系统拥有自己的文学资源库,不同文学资源库存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不同文学资源库之间可能相交,但绝不重叠。一种文学体裁为一个民族所熟悉,但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艰深晦涩。例(15)中,译者模仿十四行诗替代了原文的词。因为英语民族熟悉喜爱十四行诗,更能理解它所承载的语义概念,该文学体裁为英语读者体验原文的语义概念提供了认知心理通道。
四、结语
本研究在认知翻译的框架下,以文学翻译为例,梳理了选词法、转换法、增补法、省略法背后的认知机制,含盖语义、句法、语境和文体等4个层面。此外,我们认为,诗词翻译活动中的转喻操作同样受到概念转喻生成原则即邻近性原则、凸显性原则、可及性原则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