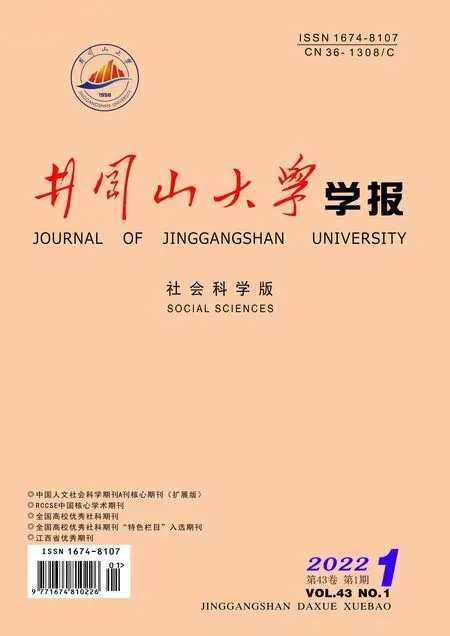“出世”情怀下的“入世”精神
——论明代岭南诗派美学系统构建的影响因子
2022-11-24潘林
潘 林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岭南诗派是在中国诗坛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地方诗派之一,亦称“广东诗派”或“粤东诗派”。汪辟疆言:“岭南诗派,肇自曲江”,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认为(汉)杨孚、(汉)张买、(晋)冯融、(梁)安都等人均开岭南风雅之先,至于张九龄,岭南诗歌已兴盛。(《屈大均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2页)[1](P39)自唐以来,岭南诗歌得以不断发展与传承,明代孙蕡、王佐、李德、黄佐、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等人先后结社南园而大倡岭南诗歌。近年来,有学者对岭南诗派的存在持否定或者怀疑态度,主要观点莫过于岭南诗派共同的东西甚少,基本都是个人写个人的,他们没有一个流派所具有的共同宗旨和追求。[2](P29)不过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身在岭南的诗人们历经千年的诗学积淀,他们虽没有像“江西诗派”那样以明确的口号存于同一时期,但是其内在的风格与美学思想是统一的、稳定的。
明代是岭南诗派的形成期,在他们的诗里有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而浑身散发着岭南独有的雄健朴直之气,他们仕途多为坎坷却又怀抱“兼济天下”之心,他们关注民生、讽刺黑暗却又能进退自如、通达自然地保持节操,正如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言:“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究其美学系统构建的影响因子,则与岭南诗派“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有着紧密联系,进而两者交织又伴随着岭南诗人的一生。
一、“拟向溪头理钓船”——岭南诗派的出世情怀
岭南偏于一隅,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南国气候与风土人情,生长于斯、结社于此的岭南诗派对家园有着深深的眷念。在诗中频繁表达对佛、道出世生活的向往,要么寻求佛、道之行,游仙、炼丹、交游,要么参悟佛、道之性,诵经、静悟、脱尘。同时,他们又美化隐逸生活,抒发山水隐逸情怀,仰慕陶渊明等人的归隐田园以表达避世之心。岭南自古受佛、道影响深远,自东汉始,牟子、康僧会、六祖、鲍靓、葛洪、单道开等人先后在此生活和修炼,罗浮山、南华寺更被视为佛、道圣地。岭南诗人多与僧侣、道徒交往,创作诸多飞仙诗、游仙诗。诗里诗人或借鹤、苍兕等仙家骑行工具翱游于天地之间,或与仙人同游,抒发与尘世的诀别之情。如欧大任“思归欲借缑山鹤,骑入罗浮七洞天”(《思归》),表达了对佛道的向往“学道何妨老一毡”,而对四年的“金闺”生活的厌烦,“遗经仅得守师传”,向往精神上的自由,能够借缑山鹤云游罗浮山。黄哲盼望彻底抛弃尘缨,借苍兕而遨游于太乙、上清之间“笑骑苍兕骖太乙,稽首银台超上清。”(《游泰山》)赵介诗渴望能与仙人同游天际而抛却尘世:“永从众仙去,天风摇佩琚”。(《步虚词》)黄佐《梦游仙吟》“天真皇人见我笑,示我丹诠启玄窍。”在梦中游仙,并与仙人天真皇人交流借此获得道家真谛。而这种急切的情绪一旦在梦中醒来,又演化为对飞仙深深的渴望,如孙蕡《飞仙归来词》:“飞仙兮归来,无留恋乎高轩”。
岭南诗派不仅追求游仙,还积极炼丹、焚香、诵经,他们爱好山水,与佛、道交游,黄哲诗:“罗浮道士还丹熟,相许携琴入翠”,(《喜孙仲衍归自京师》)他盼望入罗浮与道士一同归隐青山,牧斋即说他“性好山水,结庐蒲涧,往来罗浮、峡山、南华诸名胜。”[3](P147)梁有誉渴望拜访葛洪,以便结庐山林:“何当归访葛洪去,四百峰头好结庐。”(《王元美席上赋得怀罗浮》)又寻求追随“九仙”归隐山林,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成仙得路径,“愿从九仙隐,愧无三鸟翮。”(《送傅木虚返闽中》)黎民表则盼望能够借助佛家的焚香诵经,寻求支遁的自由逍遥,“遥想焚香诵经处,更寻支遁问逍遥。”(《和梁思伯宿宝陀寺》)李德则认为佛、道本有共同之处,“清虚”正是两者能够自然结合的点“道人养清虚,适与高僧处”。(《栖云庵》)除此之外,岭南诗人们渴求得到道、佛家的仙药、仙丹,“三秀”、“三花”和“朱草”更是诗歌中不可或缺的追求,如欧大任诗:“吾将采三花,还山炼金液。”(《游嵩山》)“洞中拾朱草,日暮依苍桂。”(《罗浮》)显然,诗人既渴望通过炼丹获得长生之外,还向往道家那种“依苍桂”的淡薄隐逸的生活。
岭南诗人在寻求交游的同时还参悟佛、道经典,从中获得启迪,借此洗涤尘世之心。黄佐言赵介:“浮屠老子之书靡所不究。”[4](P108)他们对道家的内外篇更是由衷的着迷,希望能够脱离尘世的名利,跟随丹箓、内外篇去学道,如黎民表诗“蚤从丹箓学神仙,脱悟真乘了内篇。”(《送丁戊山人还闽中诗》)“更欲逃名去,知成内外篇。”(《少壑为蔡山人赋》)诗人盼望能够从丹箓中悟得学神仙的方法,逃离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进而通过内外篇更深层的理解道家真谛。再如黄哲、梁有誉,他们明确提出对入世的否定,要么想借参悟道家《内景篇》来逃离“人间事”:“颇弃人间事,来参《内景篇》。”(《寄道士萧止庵二首》)要么想吟诵《绿苔篇》来脱离尘世,“终然脱尘网,来颂绿苔篇。”(《江上望匡庐》)同样,李时行在诗里也盼望通过与支遁的交流,获得洗涤尘心的目的:“欣陪支遁语,聊此涤尘膺。”(《秋日游道场山伏虎寺》)孙蕡在送致仕的友人回乡时,更表达了对他遁世的羡慕之情“龙江关吏如相识,应止青牛乞著书。”(《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在追求佛、道的背后根本点意在脱离尘世羁绊,寻求出世的精神家园。他们时而感慨“尘网”“尘缨”“虞罗”的束缚,表达皈依佛、道,清除内心“尘滓”的愿望,梁有誉诗“无生如可学,从此脱尘缨”,(《夜宿鸡鸣山寺》)黄佐“洪洋秉清真,胸次无尘滓。”(《赵黄门》)时而表达自己已悟得佛、道出世的境界,感受到这种清虚、逍遥所带来的快乐,黄佐“已悟逍遥化,从今结静缘”,(《修复粤洲草堂经始桃源坞》)孙蕡“随缘僧供里,予亦长禅心”。(《光孝寺》)
岭南诗派除了对佛、道追求之外,还积极抒发回归山林的隐逸情怀,借此得到出世的目的。首先表现在对隐逸诗人、作品的肯定与学习,其中陶渊明更是岭南诗派最为青睐的诗人,在诗中鲜明地留下陶渊明的印痕,要么直接肯定陶渊明遁世忘俗人格精神,要么与陶渊明归隐田园作品唱和。如李时行“吾爱陶彭泽,达观忘俗筌。”(《感咏》)朱彝尊言赵介:“伯贞绝意仕进,植双松于庭,榜曰临清,盖以渊明自拟也。”[5](P77)如孙蕡诗“罗浮清赏如堪载,同赋陶潜《归去篇》。”(《题黄万户德清罗浮图》)黄佐就此印证“(孙蕡)尝和陶潜《归去来兮辞》,以写其情。”[4](P109)除此之外,他们还模拟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例如欧大任即有《田舍》诗“结庐向东皋,僻居绝尘鞅”,“长吟古氏《招隐诗》,寻尔持竿钓湖雪。”(《刘子修归湖上居》)其表达的归隐之情显然受到陶渊明影响,黎民表《园居杂兴》也同样描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
其次,诗人们虽身在朝廷,但是恋恋不忘山林,黎民表在诗中多次表达上书乞归“种田”的愿望,“止辇上书劳圣主,乞归吾欲种春田”,(《经韶石闻汝源报捷志喜》)“殿头频上乞休书”,(《奉大司马王公还河东》)《广州人物传》记载王佐“性不喜乐枢要,居官二载,即乞骸骨。”他们将这种归隐之情、避世之心常常寄托给那些象征自由的“飞鸟”“白鸥”“云中雁”意象,如孙蕡“愿为云中雁,寥廓恣高翔。”(《东城高且长》)李德“飞鸟欣有托,吾生念归休”,(《留题郎步山庄》)黄佐“尘心今已净,应有白鸥知。”(《秋日游迎祥寺至玉泉与张杨赵陆四子同分韵得松知二字》)诗人们反复申诉他们志在山水而对尘世的厌倦,黄哲“予志在山水,宜从云外参。”(《题蒲涧读书处》)黎民表“不是夷门宾客在,风尘吾已倦弹冠。”(《集广惠寺》)但更多是抒发归隐之心而放浪形骸,他们要么“变名姓”或者谢绝与“时人”交往而逃避世俗的喧嚣,如欧大任“市隐变名姓,岩栖避嚣喧。”(《夏月斋中作》)李德“何当谢时人,来作尘外侣。”(《栖云庵》)要么挣脱“世网”而得以闲身隐居山林,如黎民表“便当舍此去,息影穷山居。”(《和陶征君饮酒》),要么如吴旦通过静坐来收敛俗念而感悟归隐之心“独坐寡尘虑,微吟生隐心。”(《翠峰草堂》)
最后,岭南诗派在诗中常常描写理想中隐逸生活的美好,他们大多“性好山水,结庐蒲涧,栖息其中,往来罗浮峡山南华诸名胜。”又渴望能够成为行走江湖的“钓徒”“樵夫”“采薇客”“野夫”,如孙蕡“临水钓游鱼,凌风弋高禽”,(《南园夏日饮》)“无风无浪安稳眠,湖中有鱼鱼得钱。”(《捕鱼图》)他畅想自己能够临水钓鱼、凌风弋禽,过着无风无浪的平安隐居生活。黄佐既羡慕渔樵无名利追求的“轩冕”梦:“高枕更无轩冕梦,梦中犹自咏渔樵”(《梦后偶成》),又追求“野夫”甘于贫穷,坦然于心的淡薄境界:“自笑野夫贫亦得,小楼高枕胜蓬莱。”(《梦游洞庭》)不仅如此,他们还表达对乡野“采薇客”由衷的羡慕,李德“寄言采薇客,吾与尔同游。”(《观白鹭》)黎民表甚至羡慕大贾那种不乏钱财却又能浮于江湖的自由:“不如大贾浮江湖,明珠满载无官逋。”(《运丁行》)显然,岭南诗派那种迷恋隐逸生活或是在心灵上皈依佛、道其根本点还是意在摆脱世俗的羁绊而怀有出世的情怀。
二、“击壤无忘报国心”——岭南诗派的入世精神
我们在探讨岭南诗派出世情怀时,又不得不提他们所坚持的入世精神。诗歌包含诗人对功名的博取,对国家的关注,他们时而直抒报国之情,时而为国分忧,最终人生、命运于国家融为一体,而且这种思想强烈地伴随着诗人的一生。但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并没有形成冲突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岭南诗派诗歌创作的始终。
岭南诗派大力塑造抒情主体的“丈夫”形象,这种形象带有积极博取功名的动力,正如黄哲所言“封侯意气本雄豪,谁积沙场汗马劳?”(《战城南》)在诗中他们既不断为“丈夫”的志向与抱负呐喊,又时刻在告诫自己不能像蓬蒿那样碌碌无为。如黄哲“丈夫成名垂不朽,彭生早试穿杨手”,(《将进酒赠彭生秉德》)欧大任“丈夫志四海,岂能甘一邱?”(《送梁思伯》)梁有誉“丈夫立功勋,无使殷忧绕”,(《登徐州城楼北望》)黎民表“垂名本是丈夫事,莫谓扬雄壮不为”,(《答欧桢伯长歌见怀之作》)“丈夫遭逢信不偶,雌伏雄飞会有时”,(《答徐山人》)“丈夫”具有极强的追求功名的意识,具有崇高的形象,吴旦对“丈夫”的行为做出鲜明的解释即他们能够“朝射双狼暮射虎,弯弧百万窥黄河。”(《无人》)即使面对困境,诗人们也在不断告诫激励自己要勇敢面对苦难,如欧大任“封侯想见从军乐,报主休嗟行路难。”(《送萧八出塞》),如黎民表“处灾拯难多奇勣,万里封侯早致身。”(《舞剑篇赠王叔廉》)哪怕是诗人老了,也是烈士暮年,仍然壮心不已,如李时行“安能甘逸豫,岁晚徒慨慷”,(《咏怀》)梁有誉“岂学蓬蒿子,白首徒苦辛”等(《五子诗》)。在期望成为“丈夫”的背后,现实大多与理想产生巨大反差,由此诗人们开始反复申诉自己未能获取功名的悲哀。如王佐哀叹时光流逝,理想中的功名与现状相违背,“年光随水去,事业与心违”。(《忆舍弟彦常》)李德也感慨现状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升沉凋壮节,匡济负初心。”(《济南寄孙仲衍》)黎民表回首已是暮年,壮志不在,“委运属壮齿,建功惭暮年”(《和陶征君饮酒》),欧大任则担心自己的功名卑薄,不能记载于“旂常”之上,“功名恐卑薄,不得铭旂常。”(《长歌行》)区大相表达自己未立寸功,却陷入“谗害”:“论功无分寸,谗害复相寻。”(《东鲁豪士行》)总之,“丈夫”形象一直是岭南诗派入世精神下的追求与梦想,哪怕在失败后仍然在孜孜寻求,在他们身上能够体味出无限的艰辛与深深的无奈。
“丈夫”形象不仅是为了个人建功立业,更为主要的是为报效国家,在诗中他们关注国情,积极分忧国难,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情。孙蕡诗中充满了爱国之语,渴求国家清明,盼望国家昌盛,由此“召至上前,皆忠爱语,特命释之。”孙蕡在《寄郑进士毅德宏》:“王道今清夷,缙绅若云来”,他赞扬王道清平,渴求人才像云一样回归朝廷,为国效力,国家也因此日渐隆昌。黄哲、陈邦彦、欧大任则表达出国家在困难时自己深深的忧虑,他们渴求国家太平、百姓安宁、君王无忧。如“巍巍功可成,河水浑复清”(《河浑浑》),“雨旸时若民乃康,孰令熯旱忧吾王”,(《祷雨获应》)“谁为纾长策,毋令藿食忧?”(《群盗》)明末,社会动荡不安,陈邦彦对国家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咄哉祀人愚,忧国岂其质。”(《九月晦日》)除此之外,岭南诗派还积极关注国事,如黎民表在得知寇退之后用“倒裳衣”将激动喜悦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柴门候远使,喜极倒裳衣。”(《八月虏入京师,十月广州始得寇退消息二首》)欧大任则盼望国家日渐昌盛,万国来会“万国来王会,秋风战马闲。”(《晚霁过梅关》)当然,对于历史上那些误国误民导致国家混乱不堪的的奸贼,诗人们表示出痛恨。如李时行“奸谀误国情堪愤,闽广图安势已偏。”(《崖山吊古》)吴旦“误国由来一字间,上方无剑讨神奸。”(《崖门吊古》)更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做出无情的揭露,如屈大均“猛虎纵横行,餍饫亦逐逐。朝饮惟贪泉,暮依惟恶木。”(《猛虎行》)
诗人们在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国事的深切关注同时,还参与其中表达为国分忧的愿望。孙蕡诗歌《长安篇》《上京行》刻画了为国建功的游侠形象,杂诗五首更是将报国之情托付于少年,盼望少年能够分国忧“少年有奇志,思欲分国忧”。在面对国家动荡时,又渴望能够拥有仙翁的法术去保家卫国“此时安得仙翁术,化作潼关百万兵?”(《题唐仙方技图》)梁有誉则抒发自己愿意积极投身其中的愿望,他要么与少年英雄一起报国从戎“结交思报国,挥袂远从戎。”(《结客少年场》)要么盼望早日走上战场,为国厮杀“鹿塞烟尘合,何时斩月支。”(《杂兴》)哪怕是年老,这种为国请缨的意念仍然不改“堪笑腐儒通籍晚,艰危心折请缨才。”(《暮春病中述怀》)李时行在诗中表达出随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一旦羽书至,愿言分国忧。”(《出自蓟北门行》)黎民表则认为即使白首也可以为国奉献,只是对无法“请缨”透出深深的羞愧“白首戎旃应不误,疏才今愧请缨难。”(《答景武》)欧大任在送刘伯玄兄弟北上时,为他们的报国行为呐喊“借君千尺如虹笔,长扫妖氛北斗旁”(《送刘伯玄兄弟北上作黄鹄篇》)。
岭南诗派流露出对家国的无限热爱,报国与报君之心一生存于胸中,在诗中他们尽情抒发报国、报君之情,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黎民表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深刻,他的多首诗里渴望能够长久陪伴君王,“谁能和得阳春曲,长奉君王万岁欢。”(《燕京书事》)又希望自己能够放下隐逸生活去侍奉君王“释耒趋阙庭,洁身奉君子。”(《予告出京师》)“平生匡济心犹在,归去田园鬓未斑”,(《寄寿大司徒石渚马公》)哪怕是在白发后仍然不忘报国恩“椒花秫酒供残岁,白首毋忘报汉恩。”(《登观音阁》)黄哲更表达甘为君王献身永为阶石的愿望,“愿为宝阶千岁石,长近君王双履綦。”(《白苎词》)黄佐、王佐发出铮铮誓言,至死也要为忠臣报国“犒以钱刀,暮用为乐,愿为忠臣死报国。”(《战城南》)“相看已是康衢叟,击壤无忘报国心。”(《发龙湾别王惟吉张廷彦》)在梦中仍然渴望碧天能够保佑“皇州”,“银汉有章回紫极,碧天如幕护皇州。”(《梦游洞庭作》)欧大任则希望赐予他“灵觉力”来保护“孝陵”,“愿资灵觉力,长护孝陵园。”(《灵谷寺》)
三、“穷达隐显自随时”——出世与入世的融通
岭南诗派所追求的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看似对立,但是在他们身上并没有产生激烈的冲突,反而得以融会贯通。究其根源则是诗人心中那种通达自然的情操与独善其身的品质紧密联系,因而能够做到“穷达隐显自随时”。
就通达自然而言,首先表现在对荣辱贫富的通达。岭南诗派不论是“出世”还是“入世”始终对贫富坦然待之,安于贫穷。李时行认为荣华就像“圆景”一样不可常驻,因此对穷富应自随坦然处之,“圆景不可驻,荣华安足凭。”(《赠潘时乘内翰》)对此,他保持两种心态:穷则自修,达则有为,“穷居乃自修,深栖晦其迹。达则大有为,安邦拯民厄。穷达自随时,隐显谁能识?”(《感咏》)孙蕡认为富贵为过眼烟云,不如开心及时行乐“高堂与大宅,终作荆棘场。蓬莱隔弱水,仙说成荒唐。及时且行乐,勿用徒悲伤。”(《驱车出东门》)欧大任强调无论富贵还是贫贱不可过分苛求,保持乐观心态,一切随意即好:“富贵不可求,贫贱不可去,上有沧浪天,勿复虑。”(《豫章行》)黄佐则甘于贫穷,向往"野夫"即使贫困但通达心安的神仙生活:“自笑野夫贫亦得,小楼高枕胜蓬莱。”(《苦雨》)梁有誉、邝露同样在内心表达甘于贫贱,一切随遇而安,不有意弃世也不慕荣华“弃世吾不为,荣华吾不慕”,(《李中郎攀龙》)“春华吾不羡,岁寒吾不欺。”(《述征》)因此只要心安,哪怕是艰难困苦也摧抑不了自己的初心:“贫贱心所安,顑颔岂摧抑。”(《五子诗》)黄哲则时时告诫自己在享受富贵和成功的时候,更应该以淡然的心态去看待,功成身退不再留恋富贵,“功成乃慕赤松去,富贵浮云非所干”。(《行路难》)
其次表现在显隐的通达。岭南诗派的诗人虽然积极追求功名,但并非不能甘于归隐,不论是对待功名还是隐逸都能够做到通达自适。就对待功名的态度而言,诗人大多能坦然待之,视其为“浮云”“浮烟”“浮名”。如黄佐认为功名不值得留恋,应该把“轩冕”置于“形骸”之外:“酒酣为子歌慷概,轩冕且付形骸外。”(《月夜登王子小楼放歌》)同样,欧大任认为应该功名其视为“蒯缑”而甘于“餐菰米”,“十年生事餐菰米,万里功名视蒯缑”,(《送李子新还扬州》)李时行则表达不愿为“浮名”所束缚,应当在功成之后,推却荣华富贵而及时退隐江湖,“功成泛湖去,拂衣且辞荣。隐居齐鲁间,遂著陶朱名。”(《感咏》)王佐认为人生自适即心安,何必苦苦谋求功名,犹如李白、陈抟那样的生活岂不让人更加羡慕“人生适意此为乐,何须苦觅扬州鹤。李白佯狂乐自如,陈抟鼻息呼难起。”(《醉梦轩为钱公铉赋》)就对待隐逸的态度而言,诗人们追求随遇而安,如黎民表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哪怕在功名上无所作为,“平生任性无羁束,蹋翼尘途成碌碌。”(《思归引》)李德感叹人生退进盛衰的无常,生死都有一定的规律不可强求“盛衰无常理,生死乃其宜。”(《杂诗》)黄佐持有两种坦然自适的心态,既认为仕途得志亦不必过于欣喜,又指出不要羡慕“游凫”般的隐居江湖的生活,“扶摇自有适,何必羡游凫。”(《舟度彭蠡遇风作》)这两种心态在李时行身上也得到深刻体现,“吾爱陶彭泽,达观忘俗筌。一官但适意,不为生产牵。万事不著念,平生任自然。”(《感咏》)诗中李时行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但抱有达观心态去看待陶渊明的隐居,同样对于出世博取功名也是以“适意”为心态,最终归纳为一切事物“任自然”。
诗人在进退自由的同时更追求独善其身,保持节操是其进退的底线。诗中出现大量带有气节的意象以表达诗人的节操,例如“朱草”“苍桂”“松竹”“仙鹤”,欧大任向“洞中拾朱草,日暮倚苍桂。”(《罗浮》)孙蕡“观里松竹皆住鹤,烂醉仙人白玉壶。”(《罗浮游息》)这些高洁的意象代表了诗人的追求,相反对那些没有节操的意象则加以否定,例如李德诗“中藏千万绪,处污恒自守。不学杨白花,随风入床牖。”(《亭亭水上蕖》)诗中,李德告诫自己即使身处污境,也要坚守节操,更不能像杨白花那样随风改变自己。诗中对陶渊明的隐逸生活赞美的同时更欣赏陶不向权贵低眉折腰的人格精神,朱彝尊评赵介对陶渊明的效仿:“伯贞绝意仕进,植双松于庭,榜其曰临清,盖以渊明自拟也。”李德仰慕陶渊明的节操,表达了跟随他的急切愿望“渊明节概士,远慕羲皇风。此士不再得,吾生焉所从?”(《题陶渊明像》)黎民表则模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告诫自己要甘于贫贱而不改节操的行为,“迷途幸非远,回驾方自兹……委运属壮齿,建功惭暮年……退隐守寒贱,无令兹愿违。”(《和陶征君饮酒》)诗中直接表达自己的节操。如梁有誉明确表达不事权贵的骨气,“不肯敛衽事七贵,不学低眉谒五侯。”(《燕京侠客吟》)黄哲则认为“贞士”必须经过磨炼,只有隐居涧陲才能陶冶情操,“贞士多苦节,考槃依涧陲。”(《简涂叔良朱仲雅二博士》)黎民表讽刺那些追逐名利的人,自己要保持“逸轨”,其他任其逍遥淡然处之,“营营当途子,所徇利与名”(《和陶征君饮酒》)。
四、余论:岭南诗派美学系统构建的背后
明代是岭南诗派的形成期,也是其美学系统的确立期,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又能够前后传承。在他们诗里有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而散发着岭南独有的雄健朴直之气,他们仕途多为坎坷却又怀抱“兼济天下”之心,他们关注民生、讽刺黑暗却又能进退自如、通达自然地保持节操,由此岭南诗歌美学影响因子里形成了出世情怀下的入世精神。究其原因,除了与诗人所处时代联系紧密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释道在岭南交融的影响。岭南是最早登上儒释道融通大舞台的地区,佛学家牟子、康僧会、六祖惠能和道学家鲍靓、葛洪等人在岭南倡导佛、道思想时,无一例外促使了儒释道相互交融。举例而言,东汉岭南佛学家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位由儒而道、而佛的人。”[6](P69)东晋葛洪隐居罗浮山,著有《内篇》《外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外篇·自叙》)他把扶危解困、去恶从善以及儒家的忠孝伦理道德作为修道前提,如其言“崇尚儒术,搏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抱朴子外篇·崇教》)六祖惠能在岭南创立的南派禅宗则融入了儒家伦理道德观、人文精神和道家自然无为的处世态度,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性。也因此佛道融入儒家之后,“他们这种逃逸于世俗社会之外的自由精神树立了一种轻世傲俗的风范,对于‘改换人间情’起了潜化作用。”[7](P6)在这场交融中,儒释道均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并早于其他地区而深深扎根于岭南,与此同时儒释道融通的历程也持续影响了岭南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至于那些“顺应自然”“人性自然”的哲学观对岭南诗歌表现出恬淡自然意境,蕴涵着热爱自然情趣的风格影响深远。事实上岭南地诗人也与儒释道有着紧密联系,唐宋岭南诗人张九龄、邵谒、余靖、崔与之和李昴英等人无一例外融入其中,而这些岭南诗人更是岭南诗派美学思想的开创者。后来南宋末年,岭南诗人群体初步形成,例如爱国诗人区士衡、赵必 、李春叟、陈纪等均沿着岭南诗歌儒释道交融的传统进行创作,明清时期遵其创作传统的诗人更是此起彼伏。
第二,“曲江规矩”的传承。张九龄精忠爱国、刚正不阿、通达自然的道德节操以及富有“雅正”诗学创作理论与实践开创了岭南百代诗风,特别是对岭南诗派的萌发、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启迪作用,从而逐步形成了岭南诗派的独特风格,故后人把岭南诗派美学标准被遵循为“曲江规矩”。正如张邦翼《岭南文献》言这种承继:“自曲江公树帜以来,而岭海诗歌不减北地、河东矣。 ”[8](P5)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多次强调“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岭南诗自张曲江倡正始之音”[9](P345-346)又言曲江诗风对岭南创作的影响,“吾粤诗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开风气,千余年以来,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户汉魏,皆谨守曲江规矩,无敢以新声野体而伤大雅,与天下之为袁、徐,为钟、谭,为宋、元者俱变。故推诗风之正者,吾粤为先。 ”[10](P43)黄子高《粤诗蒐逸序》同样指出曲江诗歌创作的影响:“专于诗者,《岭南五朝诗选》《广东诗粹》《广东诗海》,大抵以广收并蓄,表扬前哲为主。顾每观各选,俱首曲江,一似曲江以前无诗者。”[11](P1)这种影响对岭南诗派最为明显,其中明代又以孙蕡对张九龄诗学审美的接受为开端,陈子升言明代兴盛时期“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诗数变,独粤中犹奉先正典型。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12](P43)这种“先正典型”正是曲江规矩的精髓,薛始亨指出孙蕡等人受到的影响:“自孙典籍而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12](P272)清代梁泉也指出:“广东诗自张曲江开宗,至南园五先生为继,则孙西庵者,又南园之小宗乎。”[13](P103)黄佐论诗重唐诗,对张九龄也格外推崇。其《夏夜对月用张曲江韵四首》显示其读过《曲江文集》,作品也明显模拟了张九龄《感遇诗》,其《过岭瞻望张丞相祠》则直接表达了对张九龄道德文章的仰望。正如黎遂球理清的发展脉络“然于唐诗有张文献,于我明有五先生。粤昔者称之,盖无异词云……所以倡五先生者,嗣音继响,相与鼓吹休明,如唐初之有中盛哉。 ”[14](P394-395)
第三,岭南奋进通达的民风。岭南被南海与五岭阻断,自古乃“南州远徼”“偏方之地”,因此“在古代的历史文化圈中,岭南属于‘荒服’,沿袭至唐,此处仍被朝廷视为谪贬放逐之地。其地‘人杂夷獠’,‘人强吏懦’,民风躁急轻悍。”[15](P166)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岭南奋进通达的民风,粤人性情豪?纵直率,独立自强,勇于进取,敢于抗争。其土著越族更是性情强悍,敢于抗争,他们“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四且无悔。”[16](P160)《庄子·山木》言越人直朴“寡欲”而“不求报”:“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据黄佐《广东通志》载共有隋、唐及五代51位岭南人物传记,明记或悍直,或狷介,或急躁性格者占26人,张九龄、邵谒等岭南诗人名列其中。这种民风因封闭地域的影响,具有持久性,王士禛即言:“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17](P251)
由此,这种奋进通达的民风特性影响了岭南诗歌创作,又因地处偏远,诗派人物成长期较少与中原相接,不随时代风气而转移,从而长期保持较为一致的审美风格,正如陈恭尹言岭南诗人:“其所自守者,亦往往执而不移,地气使然也。”[18](P891)潘耒《羊城杂咏》也说“地僻未染诸家病,风竞堪张一旅军。”这种持久的诗歌审美便是“雄直”“自然”诗风的精神基础,《粤东诗海序》言:“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发。故民生其间者,类皆忠贞而文明,不肯屈辱以阿世,习而成风。故其发于诗歌,往往瑰奇雄伟,輘轹今古,以开辟成一家言。其次者亦温厚和平,兢兢先正典型,不为淫邪佻荡之者,以与世推移。”[19](P23)因此在地方诗坛持续千年而稳定的诗歌美学风格正是后期岭南诗派有别与其他诗派形成的重要原因。
明代岭南诗派美学系统寻根溯源与其构建的影响因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造就了明清时期岭南诗派的形成也与其他诗派有所差异,在此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传统诗派划定形成的标准,非要同一时代,提同一口号,而应该探寻其核心,即其美学系统的统一性、稳定性。当前研究虽然认识到岭南诗派存在共同诗歌风格特色及诗学审美,[20](P15)但是这种风格与美学是如何建立的,是如何传承的,其根源在哪里等系列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厘清,难免会有学者提出岭南诗派是否真正存在的质疑。[21](P125)因此,本文即是在论述岭南诗坛共同的美学追求之后,再探讨明代岭南诗派诗歌美学形成的背后因素,进而揭示岭南诗派形成的原因,让学界从真正意义上认识、理解并接纳岭南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