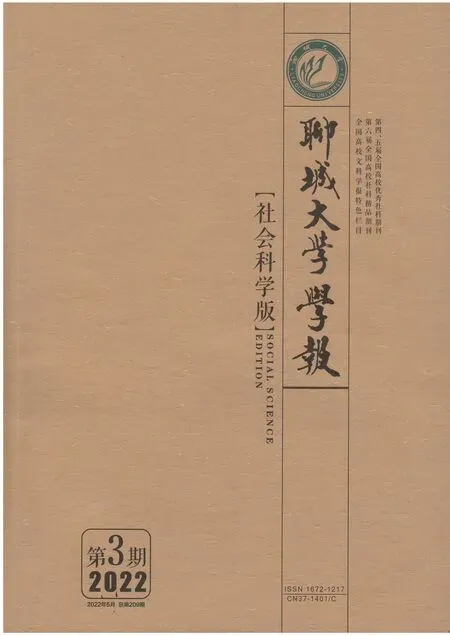新世纪二十年老舍幽默研究述评
2022-11-24石兴泽
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在新世纪老舍研究的海量文章中,标有“老舍幽默研究”字样的有50篇左右。幽默是老舍创作风格的主调,在语言、人物、情节的很多方面都有表现,无论整体研究还是具体分析,针对的是文本还是人本,都涉及幽默。“涉及者”数量多且杂,无法统计在册。作为老舍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幽默研究显示着近二十年老舍研究的发展态势和成就问题。盘点考察,以标题显著者为主,适当论及新意丰盈的“涉及”研究。难免遗珠之憾和留椟之叹,因未进入考察视野者有可能是颇有创获的解读,而进入考察视野者虽有缘由但未必就有新见。从促进研究深入且有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值得关注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老舍创作幽默的重新评价
新世纪老舍幽默研究是在前数十年基础上开始的,作为一个显在话题,数十年研究积累深厚,很多问题得到清晰阐释,但仍有再解读的空间。这既与话题内涵的复杂性和生命力相关,也与学术界的重评思潮有关——颠覆与重评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既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也是学术文化发展建设的动力。进入或者说还没完全进入新世纪,重评思潮就已涌现,数不清的作家作品、创作现象进入重评视野,连几千年的结论共识都被质疑、刷新甚至颠覆,就不要说老舍幽默这个存在诸多开掘空间的话题了。重评中既有故作惊人的炒冷饭晒牙慧,也有隔膜研究历史状况的障目者言,而建立在学术自觉之上的刷新阐释和颠覆之论也常见不鲜。
重评和重复混杂,常识和新见交叉,老舍幽默研究水浑水宽,鱼类难辨。如《试论老舍小说中的幽默》《试论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老舍小说幽默风格探究》《浅论老舍小说中“幽默”的界定》《老舍幽默风格试析》《老舍作品的幽默特质及成因探析》《老舍幽默的艺术成因初探》《论老舍创作中的幽默特质》《老舍幽默特质探微》《论老舍的幽默》《论老舍的幽默艺术》……之类,在研究已经触及幽默肌理深处的情况下,再选这些大路边的题目做文章很难避免重复;而分析流于表面,阐释简单浅显,甚至东拼西凑也屡见不鲜。有些论者虽然试图刷新,但学养所限无法突破已知的重围。如有文章为老舍幽默“正名”,说“老舍短篇小说中的幽默并不闲适,并不性灵,不是麻醉剂,而是医治民族灵魂的‘清醒剂’”。①吕国中:《跳出“性灵闲适”圈子的老舍幽默》,《滁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话虽不错,无奈“误读”早就解除,研究也超越“清凉剂”而触摸到更本质的内容。也有研究说,将老舍幽默概括为“笑中带泪”“从总体上抓住了老舍小说的审美特征,但在整体上却给人以笼统、模糊之感”。老舍小说的审美风格复杂多变,“若不加分别地一概而论,必然会造成模糊感和偏差感”。论者据此提出,分析判断应首先梳理发展变化,然后进行归纳。①牛鸿英、马晓彬:《含着笑的悲歌:论老舍小说的审美价值》,《鲁行经院学报》2001年第5期。研究可纵可横,也可以纵横结合,纵向梳理或横向概括分别进行也并非不可。“笼统模糊”之虞可有,“症结”和“药方”或偏。两篇文章反映了新世纪初期老舍幽默研究之一斑。
从二十年老舍幽默研究发展态势上看,两篇文章是老舍研究低谷期的产物。低谷期的重评有重复旧论者,也有刷新超越者。《从叙事学角度解读老舍小说的讽刺艺术》②王卫东:《从叙事学角度解读老舍小说的讽刺艺术》,《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避开语言运用和思想态度两个常识性问题,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用“讽刺”而非“幽默”界定和概括,意在弃旧弥新。其实,宽泛地说,讽刺和幽默存在差异,但也有诸多重叠处,没有纯粹讽刺也没有纯粹幽默。书写对象不同作家的情感态度也不相同,老舍小说混合了幽默和讽刺两种笔墨,概念运用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有新意的是,论者认为老舍讽刺幽默博大精深、叹为观止者,在于“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的错综变化”。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有统一,有错位,有对立”,有时“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的态度与隐含作者的态度是统一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一起去讽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和事”,如《断魂枪》《善人》;有时“叙事者与隐含作者对于问题的态度不同或者不尽相同,叙述者常常就是隐含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或者它既是讽刺的主体,又是讽刺的对象”,如《阳光》《老字号》。“隐含作者”是新提法,辨析其与“叙述者”的关系也是新视角,论者在既定的论述系统做了具体分析,显示出运用新理论分析老问题的能力以及思维缜密、力图出新的治学态度,对认识老舍讽刺幽默具有启发意义。
王卫平于老舍研究低谷期撰写了《幽默:生命的支点——老舍幽默风格形成的原因》,③王卫平、穆莹:《幽默:生命的支点——老舍幽默风格形成的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后来又推出《重评老舍早期的讽刺幽默小说:兼谈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④王卫平:《重评老舍早期的讽刺幽默小说——兼谈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前者从“老舍的家庭、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他复杂的情感体验对他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老舍幽默风格形成的原因”,提出老舍是悲剧作家却没有写出伟大的悲剧,反而成了著名幽默作家,看似平淡其实抄根兜底——老舍幽默的成因源于“生命支点”,且与悲剧相关。后者认为,学术界对老舍幽默讽刺小说的贡献和占位,“以往虽有所涉及,但并没有研究透彻,有些看法虽陈陈相因,但未必经得起推敲”,据此提出应该“重新审视与评价”。所说现象确实存在,不仅是老舍幽默研究,老舍创作整体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都存在,而且很严重。研究文章海量出现,究竟有多少有突破和创新?有多少新的发现和发见?多少论述不是陈陈相因?言及老舍早期小说研究,针对“否定多于肯定”的评价现状,论者更是强烈不满,进而指出“过去否定的地方,也许正是作品的情趣所在,也是让读者愉悦的地方”。论者立足喜剧“重评”老舍早期幽默创作,说老舍“打破了由鲁迅、张天翼、沙汀创立的偏严肃的喜剧文学格局,为中国现代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喜剧春风。”但因受到批评,其喜剧精神和喜剧艺术才能没得到充分发挥,致使喜剧文学发展受挫。从喜剧发展视点上看,损失之说是成立的;但离开“喜剧本位”这个观测点,放眼老舍幽默创作整体,“损失”说恐怕要打折扣。当年的批评是否有助于促进老舍幽默的健康发展?老舍早期作品是否存在“为幽默而幽默”的地方?如果存在,则“损失”说似乎存在过于看重喜剧之嫌。
这就涉及如何看待老舍三十年代幽默艺术之发展变化问题。学术界大都肯定其变化,认为老舍自《离婚》开始洗净油滑走向深沉悲愤,《月牙儿》《骆驼祥子》沿着这个路向攀上创作高峰。倘若“理性的旁观态度和调侃的玩笑”不抑制,追求情趣噱头,为笑而笑,顺着《赵子曰》的路走下去,也许可以催动喜剧艺术发展,但创作成就会打折扣。王文所说的“早期”是伦敦三部,“中期”有《大明湖》《猫城记》,《离婚》开始限制幽默,《骆驼祥子》“抛开”幽默,《四世同堂》无法幽默——似与事实有出入;用老舍自己的话论述也缺少说服力,因老舍之言有“时间差”,有的话不太符合创作实情。事实是,《猫城记》(1932年)并非不幽默,《离婚》《牛天赐传》“回归”并放开幽默。《论语》杂志创刊于1932年,文学界对幽默的公开打压是1933年——以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为标志性事件。对压抑幽默不满情绪的表达既不是创作《猫城记》时的心态,也不是《离婚》《牛天赐传》的创作心态,而是1936年前后写《老牛破车》时的心态。“重评”是需要的,对喜剧文学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喜剧艺术的梳理和阐释均具有创见性,说其打开了通往老舍幽默研究深处的一扇窗户也不为过;“偏重”在于过度推崇喜剧,过于强调喜剧精神。而这也说明,即便是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倘“过于”偏重也会做出与事实有距离的阐释——但学术发展史表明,几乎所有研究都存在突出和遮蔽,为证实自己的观点极力突出某些事实,有意识地回避与己无关和不利的事实,几乎是普遍的思维方式;研究者执其一端,“观测点”决定了视线和视野,再好的“观测点”也有“盲区”,也容易失却客观公允,但学术研究的推进往往依赖于创造性“观测点”上的聚焦“偏重”!
新世纪老舍幽默研究散点透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切入,对某些话题做了多方面讨论。有时刷新不言重评,反倒有值得称道的创获。邵宁宁基于文本说人本,直抵老舍情感世界深处,把住了幽默艺术的深层密码。《老舍的感伤及其城市文明哀歌》①邵宁宁:《老舍的感伤及其城市文明哀歌》,《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聚焦老舍与北京城的复杂关系,提出“老舍的幽默以其内在的感伤为底蕴”的命题。为何忧伤?因老舍所爱的北平“是一个‘中古的’、乡土的都市,而非现代工商文明中心”;而在北京顺应时代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其所包容之传统生活伦理、美学的眷恋”正逐渐消失,他用创作弹奏“有关‘城’的哀歌”。“感伤”堪称洞察肌理的发现。陆文彬的《老舍与“京味儿”文学的未来生长空间》②陆文彬:《老舍与“京味儿”文学的未来生长空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对老舍幽默也有独到的阐释。文章引用孔特—斯蓬维尔、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以及佛洛依德等学者的幽默理论,以“爱心有无”论得失,说老舍有些幽默包含着高贵品质,有些描写缺少爱心,其“戏谑性写作实质上更多的接近于讽刺和调侃”,被胡适理解为“勉强造作”符合实际。因幽默作为“京味儿”构成之一进入研究视野,有些问题没有展开论述,但非“专门”论述往往深及关键性话题,如区别于讽刺和调侃,如以“爱心有无”考量幽默高低等,均有助于老舍幽默研究往深处和细处发展。
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阅读理解走近研究对象。众研究者走在通往老舍世界的途中,路上挤挤轧轧,走近者很多,抵达幽默深处者很少。王卫平邵宁宁王卫东等努力刷新前论,是老舍幽默世界的走进者或曰走近者。
二、老舍幽默发展变化研究
如上所述,老舍幽默艺术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数十年间摇摆起伏,呈现出动态性和阶段性特点,于是就有了发展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有助于避免一体化概括的简单,研究对象具体,把握相对容易。这自然是基于方法论推演的“应然律”,是否“应然”还要看研究者的学养情况。学养欠缺,即便是分割切块也有把握不准理解不到位的情况。用同样的方法论述相同问题,认识深浅、阐释准确与否均有分野。
老舍幽默艺术发展变化是公知的事实,但阶段划分却存在分歧,阶段性特点及其研判也是见仁见智。崔明芬分析老舍幽默艺术的转换,③崔明芬:《老舍的文化语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说“老舍的幽默艺术历经‘恣意挥洒’(早期3部长篇),继而又‘故意禁止’(《大明湖》《猫城记》),又到‘返归幽默’(《离婚》《骆驼祥子》)这样一个纯熟踏实的发展过程”。在其过程中,老舍“由形式的幽默转向内容幽默”,并对“由‘恣意挥洒’到纯熟踏实”的发展变化展开讨论,分析概括均具体到位。与崔文相比,《老舍先生早期小说的幽默意识》①胡少逸:《老舍先生早期小说的幽默意识》,《商情》(财经研究)2008年第4期。系专门探讨,但论述比较简单。《老舍后期幽默艺术刍议》②董克林:《老舍后期幽默艺术刍议》,《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言“刍议”但力求充分,文章以《离婚》为界将老舍幽默分作前后两个时期,不厌其详地讲述前后期区别,认为老舍前期刻意追求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描写没有多少事实,后期剖析社会、透视人生、幽默背后是严肃深沉的思考,艺术也日臻成熟——大体符合创作实际。但前后期划分和称谓似乎“生硬”。老舍创作的幽默艺术长达四十年,跨越两个时代多个阶段,经历了很多变异,《离婚》是第九个年头的创作;分期虽不能以时间长短做标准,但将《离婚》后的创作统称“后期”无论怎么说都不妥。“后期”漫长如此,幽默艺术变化多端,艺术追求和创作特点都难概括研判,怎么与“前期”比对并讨论其发展变化?
孙洁主要研究老舍山东阶段的创作,两篇文章专门讨论幽默。《论老舍山东时期的幽默主题》③孙洁:《论老舍山东时期的幽默主题》,《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归纳了三大主题:“对国事的忧忍,对文化的焦虑,对人生虚妄感的开掘”——三个“对”涵盖了深刻内容,而老舍幽默的内核是“忧郁和悲观”,因为“忧郁和悲观”才有“含泪的笑”的风格,则昭示了老舍山东时期创作的内在原因。《绝望中的礼貌:论老舍山东时期的幽默创作与适度原则的关系》④孙洁:《绝望中的礼貌:论老舍山东时期的幽默创作与适度原则的关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探讨幽默适度问题,思维架构来自鲍里·维昂的“幽默三原则”——“悲郁的内核,同情的态度和适度的表现”。用外国理论观点和套路研究中国文学是开放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时尚,有人生搬硬套,煮的是夹生饭;有的运用得当,点铁成金。得失之别在于是否符合作家创作实际,孙文属于后者。鲍里·维昂有名言曰“笑是绝望中的礼貌”,孙用此概括老舍山东时期创作,说老舍“注意适度机智,防止油滑;适度同情,疏离讽刺;适度优越,以免解体幽默”,显示出成熟的幽默艺术作家的创作个性,表述醒目,启人深思,关键词“沉郁”“绝望”准确到位。而“悲郁在助成幽默的同时对幽默还有着巨大的化解作用。幽默与悲观的矛盾与身俱来,以悲观为动因进行幽默创作的作家必然为此承受代价。老舍的幽默,终于因无法承受(化解)他的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的重重悲观而反为悲观所化解”也非泛泛之论。老舍的幽默“化解”了悲剧和批判是学术界的共识,孙文从“幽默与悲观的矛盾”论述,深中肯綮。阶段性研究着眼于阶段但不限于阶段,“瞻前顾后”是较为寻常的逻辑思路。孙文说老舍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相当成功的幽默作品,首先应当归功于山东时期对幽默机制和幽默规律的不懈探索”,辐射致远的余墨显示的不只是开阔的视阈。
分析发展变化有多种形式,阶段性论述之外还有“动脉”梳理。老舍幽默可以抽取若干动脉,借助动脉的强弱断续考察发展变化是智者的选题。把脉和命名因人而异。汤景泰、翟德耀以“内在对话”为脉络分析老舍幽默小说转型,《内在对话性的生成:论老舍幽默小说的转型》⑤汤景泰、翟德耀:《内在对话性的生成:论老舍幽默小说的转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做的是“内视性”文章。这种努力值得肯定,分析也有一定深度。该文认为,老舍初期的幽默创作,“悲剧性人物与喜剧性人物界限分明,分工明确”,从《离婚》开始,出现了“两种处世方式、两种命运模式”的矛盾纠结,“那类命运步步下滑的人生类型中内蕴着深沉的时代悲剧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又逐渐生发出喜剧性;而那些喜剧性的人生类型因这种深沉的时代悲剧意识观照也透露出普泛的悲剧性。但在这种普遍的悲剧性中,老舍又在出走或坚守等生命姿态中带着超然的笑声”——表述有点“绕”,且“内在对话”的统摄作用渐弱,但界标划分和转型前后的解读均符合老舍幽默发展实际。
对老舍幽默发展变化进行“内视性”考察多有创获的是刘勇的《论老舍自由写作与严谨写作的矛盾》⑥刘勇:《论老舍自由写作与严谨写作的矛盾》,《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从自由写作和严谨写作矛盾入手考察抗战前老舍幽默的发展变化,涉及很多有深度的话题,论者在对生成的内在机制做出深度解读的同时,顾及外在因素即“写作场域”的影响,发展变化得到思辨性很强的阐释和评判。“自由写作”是说老舍早期创作无规划,“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信口开河,大胆放野,肆无遮拦,充分发挥幽默艺术天性,呈现出发散性艺术思维特征;这种艺术思维既与欧洲幽默文学刺激相关,也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北京地域文化如相声、小曲和说书艺术的深刻浸染有关。“严谨写作”是理性主义、整体主义原则掌控下的创作。受革命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严谨写作具体到题材、结构和主题等层面,形成中国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潮流。受此影响,老舍回国后的创作不仅有意识地限制幽默,而且强化了创作的计划性和艺术结构的整体性,创作内容则由国民性反思走向社会现实批判。三十年代老舍回国后既有自由写作的追求,也有严谨写作的自觉。“当老舍‘放野’时,他往往以严谨写作美学准则加以审视,而当他在幽默文艺中引入技巧、节制时,又感到它们压制了自己‘想象的充分活动’和‘真挚的天性’”。老舍在自由写作和严谨写作的矛盾中探索前进,《骆驼祥子》比较妥善地解决了矛盾,在“启蒙眼光、批判精神、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对民俗世相的描写、俗白生动的语言”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矛盾的提炼概括和创作情形的分析均值得回味。
综论老舍的幽默艺术及矛盾心态,文章认为老舍经历了“大胆放野—禁止幽默—返归幽默—抛开幽默的创作过程”。其创作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大胆放野’和‘返归’的写作,多以高度风格化的叙述语言和幽默笔调,通过对市民庸俗气的描绘,展开国民性反思批判;一类是禁止、抛开幽默的写作,以‘社会自觉’的姿态和‘科学’的精神,通过小人物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悲剧,展开社会现实批判。它们的相互穿插构成了复杂的艺术成长道路,其间是存在某种断裂或摇摆的……老舍高度肯定欧洲幽默大师那‘粗莽爽利的写法’和‘撒野’艺术,在对禁止幽默、返归幽默的反思中,他又表达了强烈的‘放野’冲动,并力求论证其合法性。因此,老舍早期创作的某些写作艺术特征,也不能一般地视为初试写作时的幼稚生涩,而是幽默的艺术思维特性使然,而老舍很珍视其中想象的‘充分活动’、随笔所至的‘自然情趣’和信口开河所表现的‘真挚天性’,并未将其视为必将被‘成熟’义无反顾地抛弃的东西。”老舍晚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就以“活跃的叙述者形象,充满反讽的俏皮语言,对人物善意戏谑的描写,以及场景与对古老风习兴趣盎然的点染的穿插”而“再次展现了他想象充分活动和随笔所致的自然情趣”。窃以为,这些论述深刻透彻,对于认识老舍幽默的发展变化及其心理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重视者还有徐仲佳和赵凯的研究。前者以《离婚》的版本变化为凭藉考察老舍“幽默的变迁”,显示出值得赞赏的学术智慧。①徐仲佳:《“幽默”的变迁:论文学场对老舍的塑造:以〈离婚〉的三个版本为例》,《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离婚》是老舍十分看重的作品,出版后有过两次较大删改;作为老舍幽默艺术变化的拐点,其版本变化所体现的幽默变化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论者对三个版本两次删改做了细致分析,说“幽默是老舍在文学场顺利占位的主要的区隔性资本。文学场相对自主性原则的存在使得1933年本《离婚》中的有节制幽默、文化批判的‘底气’以及‘简洁清新’的‘文字风格’成为老舍习性的集中体现。”受政治文学高度一体化语境影响,“1952年本《离婚》的大幅删改主要毁弃其中的幽默”。对此,老舍或有不甘,故1963年“小阳春”气候下改动时出现“对幽默的隐蔽恢复”。《离婚》删减透露的老舍幽默态度和审美心态值得回味,论者于抑扬顿挫间显示的研判功力也值得点赞。后者从悲喜剧转换和美学品格入手探究老舍幽默艺术变化,角度较新但分析论述与寻常差异不很大,有新意的是将《骆驼祥子》视为转换标志——前述刘勇也以《骆驼祥子》为“标志性”占位,但论述与此有异。赵文分析比较细致,认为老舍的众多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将悲剧性的社会人生内容以喜剧化的手法给予假定性的处理;以幽默的手法结构全篇,其人物性格的发展往往是在可笑而可悲的形式中完成的”;而成熟期后的作品幽默基调发生蜕变,“悲剧性叙事开始成为其文学文本的基本形式”,老舍创作“从灰色命运的社会的表层而伸向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②赵凯:《从幽默书写到悲剧性叙事的审美转换:老舍作品美学品格探究》,《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2期。。这个过程是“从幽默书写到悲剧性叙事”的审美转换,《骆驼祥子》是转换完成的标志,也是最深刻最典型的悲剧作品。谈老舍幽默书写的美学品格,既要有足够丰富的美学知识,还要对老舍幽默创作有系统深入的认识,察其所论,后者虽然不输,但在前者的强光面前略显黯淡。
老舍幽默发展变化研究近二十年,既有切合实际的稳健阐释,也有切口相异的划界分歧。无论彼此都波澜不惊,即便是明显的划界分歧也没有引起争议。“无争论”无助于思维碰撞研究深入,而沉稳行进中却收获了刘勇徐仲佳孙洁等研学者有创见的探索,老舍幽默及其发展变化得到有深度的阐释。
三、老舍幽默艺术的比较分析
比较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新世纪老舍幽默比较研究中,有明确和非明确两种情况。前者写在文章标题上,后者体现在论述过程中。比较对象,中国现当代作家有鲁迅、张天翼、钱钟书等10多位,外国作家狄更斯、康拉德常常出现在比较坐标体系中。整体上看,缺少令人惊喜的创获,但也不乏概括阐释有新意者。
《从比照中看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性》①宋青林:《从比照中看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性》,《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将老舍的幽默艺术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和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进行比照,昭示老舍幽默艺术特性。“以一比多”说明视野开阔,也意味着视点游移论述匆匆,方法和研判均无特别处,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算得上有新意的表述。《重评老舍早期的讽刺幽默小说:兼谈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②王卫平:《重评老舍早期的讽刺幽默小说:兼谈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的学术成就前已评述,在此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略陈一二。“在叙述、描写以及所形成的语体风格上,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大体形成了以鲁迅、张天翼、沙汀为代表的写实与客观呈现的叙述和描写艺术和以老舍、钱钟书为代表的主观化、智慧化的叙述和描写艺术”。与鲁迅等作家的客观写实相比,老舍钱钟书主观化的“讽刺效果、幽默情调”源于“精心营造”、巧妙的语言搭配和修辞以及“文本和语言驾驭上的效应”。“作家善于调动各种手段来营造作品的讽刺幽默效果,夸张渲染、谐谑调侃、荒诞变形、巧用类比、抓住谐音、善用反讽,充分展开想象。”他们“突破了传统喜剧精神的非喜剧化倾向,善于从喜剧的角度观照人和事,使原本平庸、枯燥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主体的喜剧性‘过滤’和‘处理’,变成趣味横生、笑声四溢的喜剧艺术。这种喜剧性固然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丑、矛盾以及可笑性的人和事,但更主要的是靠创作主体的喜剧精神,靠他的喜剧性的‘点化’与‘升华’”。这种幽默是外在的,其“语言艺术更高,文本效果更好。”用客观呈现和主观智慧概括中国现代幽默的语体风格,有深度和新意,论述触及幽默艺术肌理,评判有倾向但基本符合实际。稍后朱秀英比较老舍和钱钟书的幽默讽刺,说他们“共同促进了幽默讽刺艺术的完善以及成熟”③朱秀英:《老舍与钱钟书小说幽默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呼应了王文的某些论述,比较点集中,分析也更具体。
老舍和王朔是不同时代、个性差异明显、作品情趣区别显著的两个作家,因“创作题材和语言与北京地域文化有着共同的联系”而被放置在比较坐标上。《建构与颠覆:老舍与王朔创作中的京味儿比较》④田文兵:《建构与颠覆:老舍与王朔创作中的京味儿比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从叙事题材、语言风格和文化心态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细致,阐述有一定深度。“建构与颠覆”突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但说“老舍是建构的京味叙事”,王朔是颠覆即解构的京味叙事,似有揪住重点罔顾其余之嫌。老舍致力于建设但不长于建构,其对北京市民社会和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明显,成就突出,而王朔虽然擅长讽刺调侃带有嬉皮士味道,但心不很冷,也不全是解构,颠覆背后也有建构。他们都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但品味和境界却有差异,老舍的幽默透着素朴,王朔凭借聪明机智。作者注意到其间的差异并作出相应的分析,有助于对老舍幽默特点的认识。《老舍与梁实秋幽默散文比较》⑤钟燕:《老舍与梁实秋幽默散文比较》,《科教文汇》(上旬刊)2010年第3期。并非沉实力作,甚至可以说分析论述有些浅显,但说“老舍的幽默散文表现出平民式的幽默,而梁实秋的幽默散文则是一种贵族式的幽默”则是值得深究的发现。
比较讲究可比性和学理性。可比性强弱决定着学术含量多寡。就老舍幽默比较而言,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等的可比性较强,与王朔也有较多的可比项;而老舍与徐志摩,一个是写实主义作家,以小说见长,一个是潇洒浪漫的诗人,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文本人本差异都十分明显,可比性弱。可比性与差异性相关但不相等,老舍徐志摩固不能说“不相及”,但过于明显的差异冲淡了可比性。有论者认为,他们都受过英国幽默文化熏陶,接受和表现却迥然不同,并据此立论①黄宇:《老舍和徐志摩的幽默风格之比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开发可比源,索寻可比项,虽有说得过去的成效,但文章仍旧难做。概因幽默与否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英国幽默文化影响只是微弱且幽深的一个因素,就此比较基础单薄且学术内涵略显寡淡。而这也正体现了“泛比较”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所谓“泛比较”,是说论者打破比较研究的学理规范和程序,于古今中外万千世象任意选取某个点与研究对象比照,铺陈成文;此种现象繁衍多年,故称之为“泛比较”时代。“泛比较”可以激活研究思维,扩大研究视域,但深化研究的助力显得不足。
老舍与狄更斯研究无论自觉与否,也无论谈影响接收还是论差异超越,大都离不开幽默比较。《跨文化文学接受下喜中蕴悲的幽默风格:谈狄更斯对老舍的审美影响》《跨文化文学接受下悲中蕴喜的幽默风格:再谈狄更斯对老舍的审美影响》和《狄更斯与老舍悲喜浑成的幽默艺术世界》②见《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社科纵横》2008年第6期、《网络财富》2009年第10期。三篇文章均出自田建平之手,算是系列研究。“跨文化文学”是比较的前提,“接受”是论述中心,围绕“接受”谈老舍与狄更斯幽默艺术之关系,分析老舍幽默特色是题中应有之义。老舍幽默受狄更斯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狄更斯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既与“跨文化文学”有关,也与老舍的接受态度有关。老舍的接受是“积极的”,“积极的文学接受是保证文学创作得以进行的动力和决定作家审美倾向的因素之一”,或许算不上深刻,但也是持续思考的结晶。
总体上看,新世纪二十年老舍幽默比较研究略显平淡,王卫平的“非正式比较”之外,罕见有深度的开掘。且不说与其他话题研究相比,即便是与其他方式的幽默研究相比,也显得单薄——也许我们的期待过高。
四、老舍幽默“底蕴”“关系”及其他研究
老舍幽默是内涵丰富的话题。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切入考察,分发出诸多话题分支。有的选题重复,观点和阐释均无新意,在此忽略不计;有的绕开常规话题寻求突破,于是就有了“底蕴”“关系”及其他解读。
如上所述,老舍幽默的悲剧性已为学界共识,近期并无改变,但新的解读阐释却屡屡出现。孙洁借鉴国外理论提出“悲郁的幽默”说,于遣词用字之间显示出特别的用心。有研究者“顺着说”,认为《猫城记》“以散乱的笔法,向我们阐述了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及其生活在其中的国民们;以低沉的表达方式组织了全篇的文字,形成了一个灰色的文本”,引人发笑,给人以沉重感——“悲郁的幽默”③李芳、王沐:《悲郁的幽默:论老舍〈猫城记〉的艺术特色》,《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呼应”凿实了“悲郁幽默”论。放宽了看,与之相近的还有《论老舍幽默中的悲剧意识》④刘雄平:《论老舍幽默中的悲剧意识》,《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悲剧”和“悲郁”以及“沉郁”“悲悯”“悲观”等有区别,但都基于“悲情”这个内核,也都与寻常所说的“含泪的笑”属于同一认知范畴,论述有深浅,举例不相同。宽泛地说,举凡认真的阅读思考,无论“积极呼应”还是“接着说”“顺着说”,都强化了老舍幽默实质研究。
老舍幽默内涵复杂,研究者按照自己的阅读理解分类切割,将“幽默世界”分成若干板块,有很多切入点也有很多“命名”。“穷人的幽默”便是其中之一。“穷人的幽默”语出舒乙,史鸿敏认同这一说法,并作了具体阐释,《最具灵性的幽默:论老舍先生的“穷人的幽默”》⑤史鸿敏:《最具灵性的幽默:论老舍先生的“穷人的幽默”》,《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浅显却不失其新。“穷人的幽默”是富有意味的说法,把住了老舍幽默的命门。幽默是智慧的,穷人不乏智者;幽默与否,与贫穷富有没有关系,与富人相比,穷人更愿意用幽默摆脱生活困境。老舍有高贵的精神品格,也有穷人的心理“灶影”。“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是他深刻的生活和心理体验。穷人心理影响创作,他将穷人的灰色社会和苦难人生做了幽默化处理,苦中取乐显示出积极达观的生活态度,但也影响了社会批判力度。“穷人的幽默”其实是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的话题,期待深入开掘。
《论作者—读者交往关系中的老舍幽默艺术》①刘勇:《论作者——读者交往关系中的老舍幽默艺术》,《咸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和《老舍的“幽默”作家形象与〈论语〉杂志之关系》②胡安定:《老舍的“幽默”作家形象与〈论语〉杂志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都是很用心的选题。后者更见史料功夫。老舍与《论语》关系密切,有些幽默作品发表于此。当年《论语》以“幽默”为旗帜聚集了趣味共同体,其“话语策略、文化立场,与老舍当时的创作倾向十分契合”,他在这里找到了心理平台和说话园地。论者检索老舍在《论语》上发表的文章,以翔实的数字说明其间的深密关系及其对老舍幽默艺术的积极影响,显示出严谨的研究态度。前者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谈老舍幽默,可谓独辟奇径;说老舍“在创作上标举幽默艺术的本意之一,就是确立一种平等亲切的作者—读者交往关系”,算得上有新意的阐释。老舍或许有意用幽默建立与读者“平等亲切”的关系,因为幽默的确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分析似乎还须具体深入,譬如这种“用意”在众多影响源中占多大分量?有待深究。张金朔结合老舍的宗教情感谈幽默,《风格即思想:幽默语言与悲剧主题的结合——老舍灵魂关怀的宗教情感》③张金朔:《风格即思想:幽默语言与悲剧主题的结合——老舍灵魂关怀的宗教情感》,《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指出,老舍把“幽默语言与悲剧主题”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深厚、辽远的宗教情感,一种灵魂关怀的宗教思想。”与灵魂关怀相对的应该是现实关怀,是生活和生存关怀,老舍重视灵魂关怀也重视生活生存关怀,从灵魂关怀层面上分析幽默,且与风格、语言、悲剧、宗教等结合起来,有些深奥,阐释还算得体——因为这几项原本就存在某些联系。
古世仓、吴小美分析老舍幽默成因,归结为主客体统一,似无新意。大凡幽默探源都会论及这两个方面;但明确提出主客体统一、聚焦透视者是本文。论者从幽默心理与对象之关系的角度讨论老舍幽默成因,所说如“老舍的喜剧意识来自他深层心理的悲剧意识,即来自他对所表现的那些令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的悲剧必然性的认识”、“老舍的幽默主要是出自于主体的压抑及其升华,而不是出自于主体的悲观。幽默、诙谐是主体超越对象的产物,要求主体与对象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老舍沉郁的个性气质与他文化人的学养对象化”使其创作具有沉重抑郁的艺术氛围等见解,④古世仓、吴小美:《论老舍“幽默”的主客体统一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均启人深思。颇有新意者是“伪饰”论。所谓“伪饰”,即寻常所说的“含泪的笑”,也就是老舍用幽默掩饰内心悲苦——幽默具有保存和稀释内心“悲郁”的意义。“伪饰”是贬义词,初看很难接受,细读便见论者拨开遮掩昭示本性的努力。联系“老舍的幽默,实际是他与中国现代革命复杂微妙关系的折射或投影”说,更见其复原事实本相的用心。论者致力于“老舍与中国革命”课题研究,“主客体统一”以及“伪饰”其实是关联甚广的话题。
高丽芳论述老舍儿童作品的幽默风格,⑤高丽芳:《论老舍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风格》,《语文学刊》2000年第3期。也是比较用心的选题——避免了选题重复,也避免了论述宽泛。将儿童叙事与成人分开是对老舍创作的细心体察,对认识老舍幽默乃至整个创作心理都有意义。老舍在幽默创作中注意区分对象,儿童幽默注重情趣,成人幽默指向世道人心的丑恶虚伪带有讽刺性和悲剧性。老舍热爱儿童,满怀深切的关爱构建儿童世界,不愿意把丑恶和眼泪带进来,于是就有了“儿童式”幽默。儿童式幽默“源于儿童,立足儿童,在把握儿童特殊的心理、生理机制的基础上,把儿童的个性特点与品质与幽默这一美学形态的内在特质巧妙结合,表现出儿童所特有的幽默形态”。老舍“以一种游戏心境”,“在儿童思维逻辑的特殊性基础上”用“形象化浅语”营构的幽默是“亲切的”“游戏化的生活形态的幽默”,“在给儿童送去笑声之余也输入了生长的养料”。论者分析老舍儿童作品的幽默特点,解读其所体现的老舍情感心理,体察细致,阐释到位。
好的选题和切口是成功的开端,但老舍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很难再找到。学术研究既要有好选题好切口,也需要独具特色的分析;提出迥异于人的见解固然是好,倘若做出有新意的表述也应该得到赞赏。《试论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①宋青林:《试论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3期。用“喜感”和“悲感”、两种心态(“笑的哲人”心态和“改造国民性”救治心态)、“自然”和“智慧”两套词语做出与众无大异的阐释,概括表述均有助于产生新的感想和联想。《温柔的手术刀与犀利的推拿术:谈老舍作品的幽默特色》②史鸿敏:《温柔的手术刀与犀利的推拿术:谈老舍作品的幽默特色》,《沧桑》2008年第2期。说老舍幽默“对强暴者的虚伪、可憎是温柔的手术刀,对弱小者的无知、可笑是犀利的推拿术”也给人以新鲜感。老舍幽默面对两大对象:强者和弱者,用手术刀和推拿术做比喻符合老舍创作实际。但以此概括老舍的幽默特色还有待深化——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个比喻强调了功能,用于说明幽默特色尚欠精确。《笑永远是自觉的:论老舍的幽默创作风格》③王晓琴:《笑永远是自觉的:论老舍的幽默创作风格》,《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全面考察老舍的幽默艺术:“其理论主张:寓理于谐、寓悲于谐、寓讽于谐、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其幽默创作风格形成原因,在于家庭、民族、社会、时代的影响,以及中外喜剧艺术的滋养;而发展历程,可谓历经波折,多方探索,才终至出神入化妙境;其主要艺术技巧:夸张渲染、嗜癖重复、语言错位、自相矛盾、巧用比喻和谐趣句式。”每项概括分析都显示出资深研究者对老舍幽默艺术的熟稔掌控。因为熟悉,所以要全面阐释;而遗憾也在于“全面”:周全有时影响开掘深度,选点聚焦更容易突破。
考察老舍幽默研究,欣慰于收获之余,也有个幽深而强烈的感受,进而形成偏见:学术研究与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一样,创新型思维和超越性发现是深度的,往往也是“偏激”和“偏颇”的;避免偏激和“偏颇”最好的办法是说常识,变换角度和材料说常识;说常识没有偏激和“偏颇”,容易得到认可,但说了等于不说,白说——这是“泛学术”时代经常出现的现象,它制造了学术研究发展繁荣的假象,却无助于学术文化发展。此种现象在老舍幽默研究中也常见。而那些推进研究深化的成果,有可能因“洞察”失之周全、严密甚至稳健,为刷新常识、颠覆定论而偏激锐进,甚至剑走偏锋出现“偏颇”,但有助于改变认识,激活思维,促进研究深入。学术研究不希望四平八稳,更不允许重复常识,但允许偏激和“偏颇”!在重复、庸论风气弥漫的“泛学术”时期,尤其如此。幽默是老舍研究的常规话题,若想突破常识密锁的重围,在理论、方法和阐释等方面寻求进展,或可寄希望于执着的偏激和认真的“偏颇”——也许这感受本身就透着偏激和偏颇,但挥之不去,因为它强烈而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