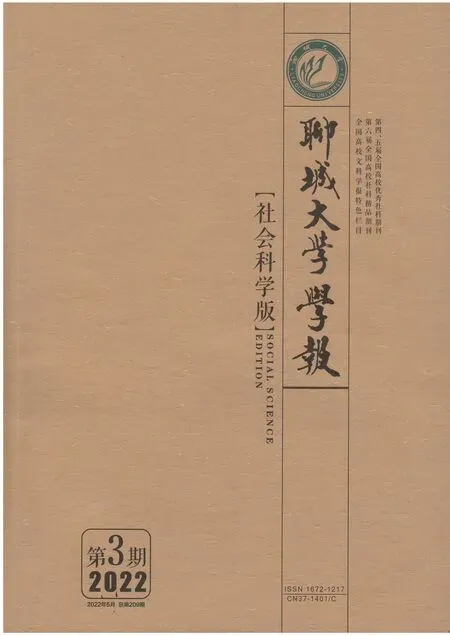明清鲁西运河区域显宦家族的崛起
——以明清聊城八大家族为中心
2022-11-24郭学信
郭学信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地方世家望族兴起时曾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页。陈寅恪先生所讲的“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历经隋唐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更是得以凸显。仅就鲁西运河区域而言,明清时期大量的世家望族接踵而至,其中除了聊城“御史傅”家族、任氏家族、邓氏家族、朱鼎延家族、朱延禧家族、耿氏家族、“阁老傅”家族、杨氏家族等著名的“八大家”之外,还涌现出许多较有名的地域性世家望族。据有学者的研究成果统计,活跃于聊城地域的地方世家有67家②参见吴亮:《明清鲁西北望族与基层社会》,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明清时期鲁西世家望族之盛,由此略见一斑。以下仅以明清聊城八大家族为中心,对其家族的崛起、家族兴盛的原因以及家族的特点进行考察和论析。
一、明清聊城八大家族的崛起
在明清鲁西接踵而至的世家望族中,尤以聊城八大家族最为著名,其家族对地方社会乃至全国皆有着重大影响。
(一)“御史傅”家族
“御史傅”家族崛起于明代中期,官至礼部尚书的明代著名文学家于慎行在为“御史傅”家族族人傅光宅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其“上世山西洪洞人,远祖居敬,国初徙聊城”③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载[明]焦竤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台北:明文书局印行,第62页。。由此可知傅居敬为东昌府聊城“御史傅”家族之始祖,他于明初与其两个弟弟由山西洪洞县迁徙至聊城。“御史傅”家族至七世祖傅相则因学问有所成就官至陕西米脂县令、八世祖傅学易乡试考中举人,其家族开始崛起。傅相则之孙傅光宅则是“御史傅”家族的振兴者。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傅光宅“举省试高等,入游太学,试冠六馆”,而后于万历五年(1577)一举进士及第①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载[明]焦竤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62页。。傅光宅进士及第后,初授地方知县、知府,后擢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工部郎中、按察司副使、提督四川学政等显宦要职。傅光宅进士功名的取得及其官位的显赫,将傅氏家族推向发展兴盛时期,之后的聊城“御史傅”家族族人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者源源不断,使“御史傅”家族一跃成为明清东昌府著名的显宦家族。
(二)“阁老傅”家族
“阁老傅”是崛起于明清之际的显宦家族,据“阁老傅”家族后人傅乐成先生撰文记载,“阁老傅”家族先祖为江西吉安府永丰人傅回祖,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出任东昌府冠县令,任职期满后回归故里。据称其夫人李氏“精勘舆之学,认为如卜居聊城,后世必可胜达,因此独寓聊城”。为了服侍夫人,傅回祖留下三子,其中一子寓居博平,一子寓居冠县,次子傅祥则随母亲落户聊城,此后其后代子孙皆寓居聊城,以耕读和经营商业为主②另据清初人撰写的傅氏碑文称,傅回祖任职东昌府冠县令期间,因“颇有善政,百姓不忍其离去,回祖公乃三子以抚慰之。”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先世》,《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第55页。。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傅以渐是“阁老傅”家族崛起、振兴的关键人物,他于清顺治三年(1646)参加了清政府首次举行的开科取士的科举考试,结果状元及第。自此以后,家族取得科举功名以及仕宦者不断,其中,傅以渐官至内秘书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国史院大学士等高官,傅绳勋进士及第后官至军机处章京、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浙江和江西巡抚等官职。
(三)任氏家族
任氏家族是明清时期东昌府著名的名门望族。任氏家族始祖任义系军籍出身。元明之际,跟随朱元璋助其平定天下的任义被赐予明威将军、平山卫指挥佥事,不久迁至聊城。自任义之后,其后代子孙如任义之子任宏、孙子任嵩、曾孙任铎、玄孙任昂皆因袭军籍。任义曾孙任镇,在明代中期出任礼部司务,自此以后,任氏家族族人大都转入文职,由此开启了任氏家族由武向文的转变。任克溥则是任氏家族由武向文转变的关键人物。清顺治四年(1647),已在乡试中举的任克溥进士及第,历任南阳府推官、会试同考官、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刑部侍郎等职。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南巡还跸东昌,幸其所居园,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64《任克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22页。,成为正一品官位的朝中高官。自任克溥进士及第后,任氏家族通过科举获得知府、知县以及其它官位者不断,是明清时期享誉鲁西运河区域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名门望族。
(四)邓氏家族
同任氏家族一样,邓氏家族也是由军籍起家的。元明之际,祖籍江西的邓氏家族族人邓瑜跟随朱元璋统率的元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因履立战功被诏封为昭勇将军,镇守东昌。自此而后,邓瑜有八代子孙世袭昭勇将军之职,是明朝时期“一门九将军”的名门望族。不过,邓氏家族真正成为东昌府名门望族则是在以武起家的同时因文而盛。自邓邦之后,邓氏家族“学而优则仕”者代不乏人,人才辈出,而清康熙六十年(1721)邓氏家族族人邓钟岳状元及第,荣登高官,则将东昌府邓氏家族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也使其家族成为自明代开国到清代中期著名的名门望族。
(五)朱氏家族(朱鼎延家族)
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朱氏家族祖籍安徽,据《明史·朱亮祖传》记载,朱氏先祖朱亮祖原为元代义兵元帅,后被朱元璋擒获归降,在追随朱元璋征伐元军战争中,因战功卓著被封赏为永嘉侯④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32《朱亮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60页。。洪武年间,朱亮祖先后与其子朱暹、朱昱被朱元璋连坐杀害,保全性命的朱氏族人迫不得已逃难至山东平阴。明朝末年,战乱频繁,为远离战乱带来的流离之苦,朱氏家族族人朱鼎延率部分族人从平阴迁至东昌府聊城。朱鼎延读书好学,学识渊博,他本人于明朝末年进士及第,清顺治年间先后出任礼部主事、郎中、云南道御史、太常寺卿、通政使、工部左右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在朱鼎延博取科举功名的影响下,有清一代朱氏家族科举及第者不绝于世,是清代著名的科举显宦家族。号称清代聊城第一大院的朱府大院,占地近20亩,悬挂在朱府大院院门上的“世进士第”和“传胪”六个大字的匾额,无不映射出清代东昌府朱氏家族科第功名的辉煌和荣光。
(六)耿氏家族
耿氏家族兴起于明朝初期,祖籍河北馆陶,明宣宗宣德年间,原隶属军籍的耿邃自馆陶移居聊城。第四代族人耿明是耿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明孝宗弘治年间,耿明进士及第,官至江西左参政,耿氏家族由此开启了由武转文的路径。自此以后,耿氏家族人才荟萃,由科举而步入仕途者代不乏人,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明代官至山西巡抚、左都御史的耿如杞(耿明曾孙),官至正五品尚宝寺卿的耿章光(耿如杞次子),清代则有高密训导耿含光,官至刑部湖广司主事、官阶为正六品承德郎的耿大光,官至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的耿愿鲁(耿含光之子),武定府教授耿贤举(耿愿鲁长子),贤良方正出身的道员耿寿平,知州耿锡观等人,其他出任知县的耿氏族人更是绵延不绝。
(七)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是崛起于明清时代的著名望族,宣统《重修聊城县志》所附《耆献文征》卷中记载,杨氏家族“先世秦人,自华阴迁晋洪洞。入明,以指挥籍临清。国朝改为东昌卫,著聊城籍”。据此可知,清代开始世居东昌府的杨氏家族,在明代是一个世袭军籍的家族,进入清代,后人入籍东昌府聊城。杨氏家族真正开始由武向文的转化始于清代,像杨氏族人杨宪章以文学著称;才智杰出、博学多识的杨兆煜“出入试选……得一学官”①钱仪吉:《赠资政大夫陕西巡抚故山东莱州府即墨县学教谕熙崖杨公墓碑铭》,载丁延峰、周广骞:《杨以增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杨氏家族的振兴者杨以增,道光二年(1822)进士及第后仕途通达,先后出任过同知、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盐运使、布政使等官职,最后官至陕甘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自杨以增之后,杨氏族人仕宦者不断,其中高官厚禄者不乏其人,如官至云南大理府通判的杨绍谷(杨以增长子),先后出任过内阁中书、军机处记名、翰林院侍读、通议大夫等职的杨绍和(杨以增次子),官至内阁中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杨保彝(杨以增之孙)等。
(八)朱氏家族(朱延禧家族)
明清时期东昌府还有另一著名的朱氏家族,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朝初年由祖籍地迁居东昌府聊城,家族著名代表人物为朱延禧。朱氏家族是明代以文起家的典型,明清时期有多人因科举功名而入仕为官。据宣统《聊城县志》卷8《人物》记载,朱延禧祖父朱应聘嘉靖年间因取得举人功名而入仕,官至知府;而朱延禧则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入仕后先后出任翰林院检讨、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职,朱延禧之子朱予昇官至清代户部主事,进士出身的朱训诰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
二、明清聊城八大家族兴盛的原因
明清时期聊城显宦家族的崛起与兴盛有一定的时空因素。
(一)它与明清聊城区位优势紧密相关。
聊城历史悠久,据考古史料证明,自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经龙山文化时期,聊城地域文化就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也正是在早期文明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程中,聊城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区位优势的中心地位得以形成并确立。
(1)明清聊城区位政治优势的确立。早在唐宋金时代,州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这一时期,博州州治治所就设立于聊城,管辖聊城、武水(县治今聊城西南)、清平(县治今临清市东南)、博平、高唐、莘亭(县治今莘县北)、堂邑、茌平。聊城博州州治治所的设立,意味着聊城区位政治优势地位的形成。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则是在行中书省下设置的路,其中东昌路路治治所设置于聊城,管辖聊城、莘县、茌平、博平、堂邑属县。明清两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在布政司之下设立的府,州则是与府平行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明清两代,山东布政司东昌府府治治所皆设置于聊城,管制聊城、冠县、莘县、茌平、博平、堂邑、清平等属县。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随着临清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临清行政区划地位上升,从原来的县级地方行政机构上置为州级地方行政机构,谓之临清州,管制临清、馆陶、丘县。清代与府并行的地方行政机构临清州、高唐州,其州治治所则分别设置于临清、高唐。唐、宋、金、元、明、清六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聊城的设立,无疑标志着聊城区位政治优势地位的确立。
(2)受益于聊城区位政治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元、明、清大运河的全面开通,运河沿岸的聊城地域经济与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聊城由此成为鲁西运河区域经济和文教事业空前繁荣的中心地区。
聊城成为鲁西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与大运河的开凿紧密相关。大部分学者认为,春秋末是运河兴建的开始,当时统治者出于军事目的,开挖了从射阳湖经淮安入淮河、全长1700公里的邗沟(又称“里运河”)。贯通南北大运河的真正开凿始于隋朝。隋朝大运河中的永济渠(宋代又谓之御河、卫运河),据《元和郡县图志》叙述:“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贝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6页。由此可知,自隋朝开始,大运河的重要河段、贯通整个华北平原的永济渠便流经贝丘县南偏的今聊城市临清地区。由此,临清已发展为隋唐以后大运河上的水运要冲地带。元代,开凿了以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的济州河,向北直通临清的卫运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丞相桑哥建议下,元政府又开挖了新河会通河,新河起济州河最北端的东昌路徐城县安山(今梁山县)西南,经寿张(今梁山县寿张集)西北,过张秋(聊城市阳谷县张秋镇)),至聊城,又向西北达临清,接通卫运河②参见马亮宽:《聊城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会通河的挖通,使“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③宋濂等:《元史》卷64《河渠一·会通河》,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12页。。明清时期,随着对运河特别是会通河的疏浚,京杭大运河畅行无阻,所谓“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而海陆运俱废”④张廷玉等:《明史》卷85《河渠志·运河上》,第2078页。,由此,鲁西聊城、临清、张秋等运河沿岸城市成为京杭大运河繁忙的水运要道之地。
有专家学者指出:“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⑤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历史事实正是这样,以明清东昌府为例,大运河开通之前,聊城地区因交通不便,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工商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运河特别是济州河、会通河修凿通航之后,聊城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在农业发展的同时,聊城的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经济迅速兴起并走向发展繁荣之路,聊城、临清因此成为鲁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镇。如聊城地域中的临清自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⑥皮日休:《文薮》卷4《汴河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旅往还,船乘不绝”⑦刘昫:《旧唐书》卷67《李绩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74页。,运河沿岸一带的城镇经济得以迅速繁荣起来。如据乾隆《临清州志》卷3《城池志》记载,明代临清城中有许多专门以商品名称或者手工业部门命名的街巷,如茶叶店街、草店街、冰窖街、酱棚街等手工业部门;市则有锅市、马市、鸡市、清碗市、姜市、饭市、菜市、猪市、米市、羊市、牛市等;巷则有果子巷、大白布巷、小白布巷、白纸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琵琶巷、箍桶巷、崇米巷、纸马巷、曲巷、故衣巷、手帕巷、弓巷、鞍子巷、豆腐巷、皮巷、油篓巷等①参见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页,第10页。。临清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极大提高了临清区域经济地位,以至于“广平以南,四方水路,毕汇于临清,转漕京师,辐辏而进”②章潢:《图书编》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聊城更是发展成为鲁西繁华的经济中心,据文献史料记载,明清时代,聊城运河两岸的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经济异常繁盛,“帆樯如林,百货山集,当其鼎盛时,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③民国《临清县志》卷8《商业》。。由于交通的便利,加之商业的繁荣,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纷纷荟聚于聊城,建立各种会馆,像明清时代山西、陕西的商人在聊城城区建立的至今仍屹立在聊城的商人会馆——山陕会馆。据同治年间山陕会馆内所立碑刻《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记载,除明清时代在聊城建立的山陕会馆外,还有康熙年间山西太原府、汾阳府的商贾建立的太汾公所,苏州商人建立的苏州会馆;道光年间,则有江西商人建立的江西会馆和赣江会馆,杭州商人建立的杭州会馆④山陕会馆碑刻《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山陕会馆等商贸会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进了聊城的商贸活动。当时琳琅满目、各种类型的商业店铺遍布聊城城中大街小巷和流经聊城的运河沿岸,从京杭大运河运到聊城沿岸的货物聚集成堆。由于聊城商业经济在明清时代的繁荣,聊城不仅成为鲁西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且也是整个华北区域手工业和商贸活动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而聊城所属的临清和张秋则因运河的畅通,成为与苏州和杭州争奇斗艳、相互媲美的繁华城市,明清时期在民间流行的“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一语便是对当时临清和张秋经济高度发展的形象概括。
伴随着聊城区域性政治中心和区域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尤其是大运河的畅通无阻,促进了聊城地域文教事业的空前繁盛。运河学研究专家李泉曾这样论述道:运河文化是运河本体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结合体,运河本体文化是运河开挖修治、工程建设、河务管理系统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是特定文化区域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它是历史文化的层层积累⑤参见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页,第10页。。此论颇为精到。对明清时代的东昌府而言,文化无疑是区域文化和运河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明清时期聊城地域文教事业的发展、繁荣,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人文荟萃,文风昌盛。人们以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为尚,尤其注重家族子弟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有所谓“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⑥宣统《聊城县志·风俗》。之说。像乾隆年间的临清“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胜于他邑”⑦康熙《临清州志》卷1《风俗》。。据文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聊城所辖地域崇文重教兴学之风兴隆,文士包括农家子弟志存高远,他们以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⑧于奎战:《中国历代名人家风家训家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2017年,第152页。的信念,勤奋向学,文风昌炽。可以说,明清聊城科举业兴盛以及刻书印书业的发展,无不与文风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其二,教育事业的繁荣。聊城区域中心地位的优势,加之运河贯通带来聊城地域经济的繁荣,也极大带动了聊城地域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明清时期,学校类型有官办学校的官学——府州县学,还有大量私立学校——如社学、私学、私塾、义学等各种类型的学校教育系统,另外还有官方聚徒授学、同时兼具藏书和教学以及研究为一体的书院。明清时代,聊城地域各种类型的学校教育皆有了很大发展。那些衣冠贵族、官宦子弟一般在官办的府州县学学习,而那些贫寒子弟则在收费比较低廉的社学、私学、私塾、义学学习。聊城地域教育事业的繁荣,在书院方面更是有着鲜明的体现。明清时代,聊城各县几乎遍布书院。据有学者统计,明代聊城共建书院13所,占整个山东省新建书院五分之一;清代山东书院总数213所,聊城境内的书院则有23所⑨杨朝亮:《刻书藏书与聊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像清朝聊城及所属县域创建的聊西书院、光岳书院、少岱书院、雁泉书院、启文书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院。其三,明清东昌府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也极大促进了东昌府刻书印书业和公私藏书业的繁荣昌盛。明清两代,东昌府刻书印书业迅速发展,有学者考证,最迟至明代晚期,运河沿岸城市临清有了刻书印书业私家作坊,聊城还有达官贵人家族的刻书印刷作坊①杨朝亮:《刻书藏书与聊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在清朝,聊城则有数十家刻书印刷作坊,其中势力雄厚的有号称“四大书庄”的书业德、宝兴堂、有益堂、善成堂最为知名。刻书印书业的发展繁荣带动了聊城公私藏书业的发展,其中清朝“海源阁”藏书楼最为有名。“海源阁”藏书楼是由杨以增所创建,经过其家族数代人的尽心努力和守护,其藏书量日益增多。同是著名藏书家、并且在校书、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中对海源阁所藏图书给予高度赞誉,称“综名家论定观之,是海源阁藏书为海内之甲观,而四经四史又海源阁中之甲观”,是为公允之论。其所藏图书数量之多、版本之精,为世人叹服。
总之,明清时代,在历代传承、发展基础上,聊诚已经发展成为鲁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有清一代,康熙帝在外出巡视中,曾前后4次巡视过东昌府,而乾隆帝则先后9次巡幸聊城。这无疑映射出鲁西聊城区域在明清时代的区位优势。明清时代形成的以聊城地域为中心的区位优势,毫无疑问为东昌府八大家族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当然,聊城区域八大显宦家族的崛起绝非偶然的社会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的。诚如运河学研究专家吴欣教授在论述《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府、御史傅”为中心》一文中所说,以二傅为代表的运河区域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它们的发展与这一区域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宗族借助于运河之利,积蓄了较大的经济资本,为其宗族势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聊城作为东昌府址,运河沿岸较大的军事重镇与货运码头,其“中心地”的地位使充分融合了各方的文化与政治资源。处在这样的“地望”之中,二傅家族自我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又加之其自身优厚的道德、文化资源的建立,使得其“东昌望族”的地位不断被巩固②参阅吴欣:《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府、御史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9年第5 期。。这何尝不是东昌府“八大家”发展、昌盛的因素。
(二)明清聊城八大家族的涌现,亦与儒家文化对其家族长期熏陶与影响紧密相连。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自创建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家园的源泉,其传承的忠、孝、仁、义、廉、耻、礼、智、信等传统伦理对世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聊城地域毗邻春秋时代鲁国的西部,即“邹鲁之乡”,是儒学的发源地,所以“近邹鲁之乡”的聊城地域文化自古就“沾孔孟之化”③《山东通志》卷23《风俗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儒学文化影响来看,儒家伦理对鲁西聊城地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宣统《续修聊城县志》称聊城“得邹鲁…其人多尚好儒学”。在聊城下辖茌平县“地近圣居,重礼教而矜名节”④《山东通志》卷23《风俗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聊城辖区的博平县,无论是力耕作的丈夫,还是勤纺织的妇女,亦或诵诗读书的经生,皆“雅尚名节,重齿譲,畏刑罚,邻里和睦,讼讦希有”⑤《山东通志》卷23《风俗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聊城辖区的高唐民众也是将尊孔读经作为精神世界的建构者。如清代知州毕一谦在《重修州学圣庙记》谓“地接邹鲁之区”的高唐,“家诵孔孟之书,是以人材蔚起,自汉唐以迄元明至于我鼎兴,理学文章列名科目彪炳史册者不乏人。何莫非圣人之教泽有以熏陶而化成之也”。从东昌府八大家所遵循的家学家风不难窥见,为了维系和保证家族以儒学相传的文化优势,特别鼓励后代子孙重视和传承儒家所倡导的忠君报国、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规范,以维持世家望族的名声与社会地位的长盛不衰。如“阁老傅”家族的傅以渐,7岁入私塾学习儒家经典,曾拜师当时名儒孙肇兴明义理之学⑥马亮宽:《聊城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傅永鋍也表现出孝悌、勤政思想,史载傅永鋍仕宦期间所经过的地方,“莫不以教孝悌……恤茕独为先务”⑦宣统《聊城县志·人物志·傅永鋍》。。《东郡傅氏族谱》中记载的“阁老傅”家族还制定了族规,要求家族成员严格遵守儒家对老人尽孝的道德准则。朱氏家族成员朱鼎延也凸显出鲜明的儒者风范,其教子以耕读传家、忠孝节义、勤俭节约、清廉节操为是。史称朱鼎延仕宦期间“潜心程朱之学,时以正心诚意持已,训人素甘淡泊,虽位至司空,全不经营资产,东郡考院,倾圯捐金修整”⑧《山东通志》卷28之4《人物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所行所为,正反映了朱氏家学家风的基本理念。出身于“孝友性成”的任氏家族成员任克溥,史籍赞誉其“急难好施,客居二十余年,捐偿学庙等,祀乡贤”,“人以为有范文正之风,遇人极谦谨难比,闾耆必与为礼,不念旧怨……仁心义质,为时所重。”①宣统《聊城县志·人物志·任克溥》。。居官清正廉明的杨氏家族的杨兆煜,在出任莱州府即墨县教官时,为了照顾母亲,便将母亲迎来即墨县官舍居住。任职期间因政绩突出,上司欲推荐其出任高官,而杨兆煜“释然不愿以去”,其原因“蓋一以顺适其亲之志,城不忍身一日离于左右也,故舍彼取此”。随子回乡的母亲数年之后,“猝中风,半体拘挛”,为此杨兆煜“废寝室食,精思营度医药”。在杨兆煜精心照料下,其母以92岁的高龄逝世②参见[清]钱仪吉《赠资政大夫陕西巡抚故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教谕熙崖杨公墓牌铭》,载丁延峰、周广骞《杨以增年谱》,第2页。。这种孝亲之举在宣统《续修聊城县志》中也有记载,文中称其“奉母承色笑,日取元人诸院本或小说家言之佳者,郎朗雒诵,母乐甚。母或时不悦,必长跪陈启,至欢慰乃起”。除了孝亲的道德品质外,杨兆煜为人还表现出“仁恕而质直……处朋友诤而无后言,急人急若在己。尝欲有所利济与世,而绌于力,若旁近桥梁道路之属,一为之即罄其所有”③参见[清]钱仪吉《赠资政大夫陕西巡抚故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教谕熙崖杨公墓牌铭》,载丁延峰、周广骞《杨以增年谱》,第2页。的文化品格。其子杨以坊,也继承了其父孝亲的道德规范,“从公家居”④参见[清]钱仪吉《赠资政大夫陕西巡抚故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教谕熙崖杨公墓牌铭》,载丁延峰、周广骞《杨以增年谱》,第2页。,以方便对长辈的照顾。邓氏家族和耿氏家族以军籍起家,家族成员特别重视儒家忠节观,对朝廷社稷忠心耿耿。如耿氏家族一门以忠孝节义著称,其家族仕宦者为官期间,大都呈现出清正廉洁、勇于直谏、奉公执法、不讲私情、正身立朝、除暴安良等行为特征,对朝廷可谓忠心无贰。除此之外,以军籍起家的邓氏和耿氏二家族成员亦凸显出儒家倡导的大量优秀文化品格,如邓氏家族成员除皆具“性至孝”⑤宋士功:《聊城旧县志点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2页。的道德品质外,还具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邓钟岳说过这样一段话:“鹁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聚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罗网以为食,蝼蚁塞穴以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社而不至,信也。”他进而指出:“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⑥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文员会:《东昌望族》,济南: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第37页。这不仅仅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赞扬,而且也是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再如朱氏家族的朱延禧,仕宦期间以忠君、“勤政”彰显于世,并得到皇帝圣旨的称誉,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事君以忠”⑦《论语·八佾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4页。的道德规范和要求。
由以上论述可知,明清聊城八大家族仕宦期间,皆表现出儒家孝悌、忠君报国、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讲,聊城八大家之所以能走向兴旺之路,与儒家文化对其家族所带来的长期熏陶与影响是紧密相连的。史籍记载,汉代丞相韦贤“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而其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⑧班固:《汉书》卷73《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7页。。这段史籍和谚语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虽然家中有满箱的黄金,但它总有散尽的那一天,不会永久的享用。如果人们重视学习研读儒家经典,心中藏有经书礼仪,一生才会有无尽的享用,不仅利己,会使自己得到福报,而且会让自己的家族兴旺发达、数代绵延。诚如有学者所说:“‘世代治儒’的家族传统为家族的长久承续所提供的支撑比单纯地将政治仕途作为家族发展的凭托,其力度要大得多。”⑨张卫东、陈翔:《唐代文儒孙逖家族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此论颇为精湛。
(三)将家族子孙的文化教育置于重要地位。
纵观明清聊城八大家族,都非常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以期通过家族子弟的文化学习使显贵的家族门第得以持续发展。像作为明清时代典型的藏书之家杨氏家族,其家族子弟的好学之风表现得异常突出。如“博学英特”的杨兆煜,对读书情有独钟,不仅喜咏古人诗作,而且对“论帖、读诗、品画具有鉴裁”⑩丁延峰、周广骞:《杨以增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年老时仍“日取元人诸原本或小说家言之佳者,郎朗雒诵”⑪王延庆:《孝直先生传》》,载宣统《聊城县志·耆献文征》卷中。。杨兆煜之子杨以增也是勤奋好学的典范,宣统《聊城县志》卷8《人物志》赞其“幼而颖异,博览群籍”。由于他对诗词尤为喜好,以至于“宦游垂四十载,虽文书填委,军报倥偬之际,退食少暇,未尝废吟咏,至老犹孜孜不倦”①杨绍和:《宋本〈陶靖先生诗〉题识》,《楹书偶录》卷4,光绪二十年杨保彝刻本。。因为对读书的喜好,杨以增在其父杨兆煜藏书的基础上,又购买、收藏了大量图书典籍,并于家乡聊城住宅区建有海源阁藏书楼以保存图书。杨氏家族藏书,不仅满足了杨以增自身及族人的读书需求,而且弘扬和传承了优秀的历史文化。朱鼎延家族先祖朱详本人不仅“极重读书……攻业最严”,而且对家族子孙的文化学习极为重视,不时对家族子孙耳提面命。他曾训诫幼少的族孙朱鼎延,称“尔等不读书,异日差徭累,自悔之迟矣”②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昌望族》,第54页。。在先祖教育下,朱鼎延家族子弟始终牢记读书为本的祖训,发奋学习,因而家族人才辈出。“阁老傅”家族对家庭子女的教育也异常严格,有学者指出:“傅氏家族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傅氏家族中,长辈严课子弟读书,族人学有所长者,则教授他人,不论辈分;二是延聘名家为师,教授子弟,就学于大家,以求真知。”③李泉:《清代聊城傅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2页。这是实事求是的公允之论。仅就前者而论,像“阁老傅”家族中“性倜傥不羁”的傅伦,虽然其洒脱豪放,不受拘束,但其督察考核家族子孙读书学习“严甚”④《晓窗肖窗心海傅公三代神道碑》,载宣统《聊城县志·耆献文征》卷下。。正因为阁老傅”家族重视家庭教育,所以其家族子弟取得科举功名者连续不断。同“阁老傅”家族一样,“御史傅”家族对家族成员的读书教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傅光宅在家族先辈严格要求下,“四岁诵诗,十六经术通明……夙慕方外之游,于内典、玄宗,无不深诣。谈说名理,指画世故,挥麈悬河,风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为虚论,听者为之醉心。……其才博大通敏,无所不宜”⑤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明)焦竤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62、63页。,其好学之风体现得异常突出。傅光宅家族也是这样。据明代于慎行《四川按察使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记载,傅光宅对家族成员要求“量材授赀,使修生业”,而对那些“集其俊少,肄之家塾”者,傅光宅则“朝夕亲督课之”⑥焦竤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63页。。邓氏家族虽然出身将军之门,也极为重视家族成员的学习教育。邓堂本人不仅博学多识,而且对后代子孙的文化教育极为重视,教导家族子弟要通过读书明辨是非。在先辈教诲下,邓氏家族遵崇先训教诲,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像邓堂之子邓邦及其孙邓守清、邓守渐,以及“于书无所不读”⑦宣统《聊城县志·人物志·邓钟岳》。、涉猎领域极为广泛的邓钟岳等人,皆通过自身的勤奋好学获取科举功名。其他如耿氏家族、朱延禧家族、任氏家族,其家族皆体现出对家庭子弟十分严格的文化教育,亦是明清时代因文而盛的典范代表。
总之,前辈严格而又以身作则的家庭文化教育,使家族子孙处在一种优良的家族文化环境中滋润成长,明清时代聊城八大家族之所以能绵延数代,与整个家族世代相袭的家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三、明清聊城八大家族的特点
(一)起家类型虽然不同,但家族发展都是通过科举使家族走上兴盛发展之路的
家族的兴起与发展势必受其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受明清鲁西运河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明清时期聊城八大家族形成了耕读起家、军功起家、经商起家三种不同的起家类型。虽然起家类型各异,但家族的发展路径却是相同的,都是因读书举业而使家族走上兴盛发展之路。
适应宋朝“兴文教,抑武事”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天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4页。的时代需要,宋代立国后打破了以往重视血统和门第观念的限制,科举考试中“取士不问家世”①郑樵:《通志》卷25《氏族序·氏族略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像开国皇帝宋太祖鉴于“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状况,决定“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戊辰,第336页。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则谓:“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岩野无遗憾。”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天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第547页。正是在“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考试中,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④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丁卷8《陈尧咨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0页。。正由于宋代科举考试打破了门第与血统关系的限制,所以自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成为人们“步入政治的主要阶梯,也是影响家族荣枯的重要因素”⑤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7页。,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因科第起家的名门望族源源不断地涌现。明清鲁西运河区域涌现出的显宦家族亦不例外,也凸显了以科第兴家的这一时代特征。像依靠耕读和经商起家的“阁老傅”家族,自傅以渐取得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的科举功名之后,家族日益兴隆。傅以渐状元及第后,不仅其曾祖父、祖父、父亲因傅以渐的荣光被朝廷加官进爵,而且其家族通过科举功名获得官位者不断,至清代“阁老傅”家族已成为东昌府有名的显宦大族。明代以军籍起家的杨氏家族,有明一代,因其族人主要是一些以武职出身的官员,官位不显。而自杨以增父亲杨兆煜擢童子举后,杨氏家族走上了科举兴家之路,杨以增清道光二年(1822)取得进士第二甲的科举功名之后,杨氏家族通过科举之路逐渐发展成世代簪缨相继的世家望族。如前所述,同样军籍出身的任氏家族,虽然长期以来其族人世袭军职,但任氏家族非常注重家族子孙的文化教育,重视科举功名和由武向文的转变,尤其清顺治六年(1649)任克溥获取科举功名后,任氏家族官宦不断,一跃成为清代东昌府著名的世家大族,当时被世人崇奉为“东昌第一望族”。邓氏家族虽然是靠军籍起家的显宦望族,但其家族的发展也是因科举功名而走向兴盛。正是在“学而优则仕”科举文化熏陶下,邓氏家族人才兴旺,取得科举功名者代不乏人,前后发展兴盛长达四百多年之久。原隶属军籍的耿氏家族,在其家族发展过程中,亦是沿着由武向文转化的路径发展。像其族人耿明、耿如杞、耿章光的科举入仕,使耿氏家族显宦不绝、荣光无限。在明清聊城八大家中,朱延禧家族、朱鼎延家族、傅光宅家族是以耕读起家名门望族,他们虽然力田立家,但家族的振兴和发展皆是靠家族子孙的读书举业尤其是科甲之盛而使家族走上荣光之路的。
(二)家族成员亦官亦文亦学术,勤于著书立说,表现出典型的文化家族特征。
注重家族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积淀,是世家望族长期存续的主要因素。在明清聊城八大家族中,不仅其家族成员世代为宦,并且因其家族子孙好学,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也有不菲的成就。他们勤于著书立说,家族中的文化名人辈出,属于典型的文化家族。所谓文化家族,就是家族成员能著书立说,有著作问世。总览明清聊城八大家族,许多人不仅精通儒家治国安邦之术,有文采,而且在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有许多作品问世,属于典型的文化家族。像耿氏家族虽然是以军籍崛起的世家望族,但其家族的著书立说者代不乏人。如耿氏家族始祖耿邃曾孙耿明,撰有《外集》《风云亭稿》;天资聪慧的耿如杞,著有《抚晋疏稿》《楯墨》《中丞公集》《延枝议》《外集》;耿如杞次子耿章光,撰有《玺卿集》一书;耿如杞之孙耿愿鲁,不仅“通经史,善诗”,而且还有著作问世,“著有《韦斋集》七卷”⑥《山东通志》卷28之4《人物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耿如杞曾孙耿贤举著有诗作《缓斋诗草》。邓氏家族学识广博的邓钟岳,在诗文、书法创作领域颇有擅长,著述有《寒香阁文集》《知非录》《寒香阁诗集》。邓秉恒则著有《春秋直解》《名堂集》《大清律签释》《名臣奏议录》,并对《邓氏家谱》进行修撰。“阁老傅”家族中“读书奢学,手不释卷”⑦耿贤举:《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一级傅公家传》,载《东郡傅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嘉荫亭藏版。的傅以渐,仕宦之余,写有大量著述,耿氏家族的耿贤举曾撰文赞誉他“自诸生以迄通籍,垂四十年……凡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无不讨论。手集十三经、二十一史《性理》、《通鉴》及诸子百家,咸荟萃成书”①耿贤举:《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一级傅公家传》,载《东郡傅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嘉荫亭藏版。。由于傅以渐对经学颇有造诣,因而有《内则衍义》《四书易经制义》《诗经礼记春秋诗说》《易经通注》(与曹本荣合撰)等著述;因精通史学,他还以总裁的身份负责撰修清《太宗实录》《明史》,以及清太祖、清太宗《圣训》《通鉴全书》与地方志《聊城县志》的编撰②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卷238,第9496页。,并著有《中规篇》《狐白解太史名篇》;因擅长诗文作品的创作,他还有《贞固斋诗集》作品问世。傅以渐五世孙傅绳勋曾负责撰修《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以及《重修东昌试院记》《朱母王安人传》《重修东昌光岳楼记》等。傅绳勋的祖父傅永綍,也有作品创作,撰有《重修江心寺西塔碑记》《重修永嘉县学庙记》。另外,“阁老傅”家族中的傅绳勋、傅继勋兄弟二人有《东郡傅氏族谱》一书问世,有文名的傅旭安则有《东平教案记》面世。再像朱氏家族中的朱鼎延著有《知年初集》《蘧未菴诗集》《奏疏》,朱鼎延曾孙朱续志,曾撰修过《朱氏家训》和地方志《郾城县志》。朱鼎延嫡孙朱辉钰著有《餐英书屋诗文集》。而杨氏家族喜好读书的杨兆煜之子杨以增,撰有《古韵分部谐声》《志学箴》《退思庐文存》;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一生著述丰富,著有《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楹书隅录》《仪晋观堂诗抄》《海源阁书目》等;杨绍和之子杨保彝,不仅参与撰写《山东通史》《海源阁书目》,还著有《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金石书画目录》。再像“博大通敏,无所不宜”③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明)焦竤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63页。的御史傅”家族族人傅光宅,读书广博,著述丰富,撰有《四书讲艺臆说》与《吴门燕市》《奏疏》《巽曲》等诗文,以及诸如《勒建圣寿万年寺碑记》《重修龙王庙碑记》《重修佛舍利塔记》《重修高阳陵庙记》《重修湖心亭碑记》等碑记。由军籍崛起的任氏家族中的任克溥,著有《占鳌蓑奄诗集》《任克溥奏议》,以及《东昌府重修庙学记》。另一朱氏家族的朱延禧,著有诗集《畸斋诗文集》,并具体负责编撰过《神宗显皇帝实录》《光宗贞皇帝实录》。
(三)多名甚至十余名进士涌现于一门显宦家族中。
明清时代,运河的畅通带来聊城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加之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世家望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因而明清时代聊城地域出现了大量的进士家族。有学者通过对宣统《聊城县志·选举志》勘误的考证得出整个明清时代,聊城地域共有进士91人④范景华:《明清聊城进士考辨——清宣统〈聊城县志·选举志〉勘误》,《国学季刊》第7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在这91人之中,有的显宦家族一门涌现出多名甚至十余名进士。以下不妨以明清聊城八大家族为例加以说明。
阁老傅家族是一个典型的进士家族,先后有6人取得进士功名。据史料表明,阁老傅家族第一名进士是傅以渐,清顺治二年(1645),傅以渐参加了由州、府主持的考试——乡试,结果中得举人;次年,傅以渐又参加了由礼部主持、在京举行的科举考试(进士考试),结果一举中得贡士。而后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中,傅以渐被皇帝钦点为一甲进士第一名,从而成为清代“大魁天下”的开国状元。自傅以渐中得状元后,阁老府家族先后有几代人取得科举功名,其中傅正揆为康熙年间进士,傅绳勋、傅京辉为嘉庆年间进士,傅浚为道光年间进士。除此之外,明清时代得中举人、国子监生、秀才等各级功名者数不胜数。任氏家族共有3位得中进士,其中任克溥清顺治年间获取进士,任克溥玄孙任兆熙为乾隆年间得中进士,任郿祐为嘉庆年间进士。另外还有多人获取举人、拔贡生的功名。邓氏家族有进士3人,另有武进士1人。其中邓秉恒为顺治年间进士,邓汝勤为乾隆年间进士,邓秉谦为万历年间武进士,而邓钟岳在康熙年间科举考试中获得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清朝聊城史上获得状元的第二位文化名人。另外还有8人取得举人功名。“世进士第”的朱鼎延家族有进士11人,其中,朱鼎延于明崇祯年间取得举人功名,崇祯十六年(1643)又得中进士;朱辉钰为康熙年间进士,朱作元、朱续志、朱续晫为雍正年间进士,朱光碞、朱熊光为乾隆年间进士,朱崇庆于道光年间进士及第,朱学笃道光二十九年(1849)取得举人功名,咸丰年间进士及第;朱学钱于咸丰年间进士及第,朱学籛为同治年间进士。另外还有十余人取得举人、拔贡、贡生的功名。因其家族成员取得科举功名者甚多,所以清代对朱氏家族有“父子祖孙同登乙榜,兄弟叔侄并列甲科”的赞美。朱延禧家族有进士2位,其中朱延禧为万历年间进士,朱训诰为顺治年间进士。除此之外,朱应聘、朱鳌分别在嘉靖年间和雍正年间得中举人与拔贡的功名。耿氏家族有5名进士及第,其中,耿明先取得举人的功名,明孝宗弘治年间又中得进士;耿明曾孙耿如杞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得举人后,次年又中得进士。与耿如杞一样,其子耿章光先中得举人,又于崇祯年间进士及第;耿如杞之孙耿愿鲁,于清康熙年间中得进士二甲第四名。耿愿鲁之子耿贤举,不负先辈愿望,也于清乾隆年间进士及第。除进士外,还有数十人考中秀才、举人、国子监生等。杨氏家族有2人得中进士,为杨以增父子二人,杨以增先取得举人功名,道光年间进士及第。与其父一样,杨绍和在取得举人功名之后,同治年间又参加进士科考试得中进士。除此之外,杨以增父亲杨兆煜、杨绍和之子杨保彝,分别于嘉庆年间、同治年间取得举人功名。
总之,明清时代,在聊城八大家族中,取得各种科举功名的家族成员无数,仅就进士而论,朱鼎延家族有11人进士及第,阁老府家族有6人得中进士,耿氏家族有5人进士及第,任氏家族和邓氏家族各有3人获得进士,朱延禧家族和杨氏家族分别有2人取得进士功名,共32人,大约占明清时代整个聊城地域进士家族总数(91人)的32%,进士数量不可谓不多。另外,在明清进士的科举考试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有学者统计,明清山东一共出现10名状元。而在这10名状员中,聊城八大家就占了2人,即为清朝“阁老府”家族顺治年间出现的状元傅以渐,康熙年间邓氏家族状元邓钟岳,占明清整个山东地域状元家族总数20%。明清时代,整个山东有大量的进士家族涌现,如果从聊城八大家族与山东整个进士家族状元出现的比例上看,聊城八大家族状元出现的总数亦不可谓不多。
综上所论,明清时期聊城八大家族的崛起绝非偶然,既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家族自身的因素。明清聊城八大家族所体现出的多重特性,尤其是亦官亦文亦学术,以及一门有多位或十余位进士的涌现,不仅使聊城八大家族能绵延数代并走上繁荣昌盛,而且他们凭借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文化上的优势和个人所体现的社会能力,积极踊跃地投身于基层社会建设的各项活动中,成为地方社会建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为聊城地域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道之统在圣,而其寄在贤”①叶盛:《水东日记》卷23《许可用乡贤祠堂记》,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