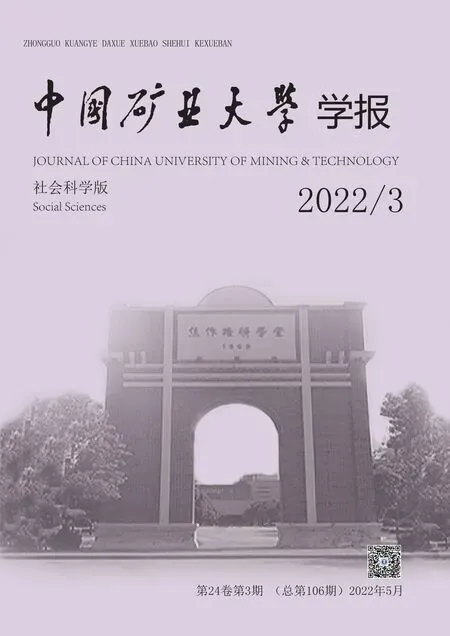公共事项言论的刑法规制研究
2022-11-23胡杰
胡 杰
公共事项言论是公民对政府监督权的具体化。公共事项言论超出了公民日常生活规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网络监督公众人物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面。根据诽谤罪的成立条件,公民在监督时需要证明公共言论所涉事实的真实性,从而给公民增加了过多的“自我检阅”任务,最终必然会限制公民监督权的行使。为平衡人格权保障与言论自由的冲突,理论界首先需要建构以宪法基本权利为出发点的规范机制及思考方法(1)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308-309 页。。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原告的涉及公共事项言论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如要胜诉,就需要证明被告有关监督言论的事实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和根据的捏造事实;或者有关事实虽然有一定的资料和根据,但是有关资料和根据或者是错误的、捏造的;或者资料和根据与监督言论的事实没有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从结果来看,特定公共事项言论虽然有可能侵犯刑法中的名誉权,但同时存在着行使表现自由权的一面,这样的行为符合对优越法益保护的要求。从特定行为来看,有关的公共事项言论符合“正当目的的相当手段”的正当性条件,而且符合从“目的说”排除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本文对于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诽谤罪入罪界限和公共事项言论的刑法规制,亦即刑法对公民监督言论如何实施具体有效的保护进行讨论。
一、公共事项言论的刑事违法性
有关公共事项言论客观事实的真实性证明作为免除责任的条件,是不充分的。就公共事项言论的违法性判断而言,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发生时对于公共事项言论的事实根据具有真实性认识,那么即使没有客观的事实,也应当认定这种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公民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行为,通常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因而不宜轻易认定为犯罪,否则,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目的就会落空(2)张明楷:《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中国法学》2015 年第3 期。。公共事项言论即使不通过错误论的解释,就其违法性判断而言,公共事项言论本身就是阻却违法性的。但是,我国刑法并未规定违法性阻却的一般适用原则,也没有其他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满足怎样的条件就可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如何从刑法角度解释此类行为违法性的性质以及满足怎样的条件即可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我国需要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的经验。公共事项言论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在德国与日本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德国刑法第193 条规定了“正当利益拥护”的行为,该条规定是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理解;日本刑法第230 条第2 款有“真实性证明,不罚”的规定,因此,如果满足日本刑法第35 条有关“正当行为”规定的言论,也应当阻却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被处罚。这两种不同的阻却违法性的解释,对于我国公共事项言论的违法性阻却的讨论具有借鉴意义。
二、德国刑法第193 条与公共事项言论保护
(一)德国刑法193 条规定
德国刑法第193 条规定:“有关科学、艺术、职业上的成就所进行的批判,或与此类似的履行或为了保护权益,或代表正当权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上级对下属的训诫与责备,官员职务上的告发或判断,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原则上不处罚。该项从该条文可以看出,虽然该条文包括的情形比较多,但是作为正当理由在德国刑法的总论部分已经有所规定,在分则中的规定只是进一步进行强调。例如,上级对下属的训诫与责备,官员职务上的告发或判断都属于正当行使职责的行为。而有关科学、艺术、职业上的成就所进行的批评,则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与其他的行为有所区分。一般来说,不仅一个简单的作品就可以作为该条的适用对象,还应当注意与有关的原创者本身进行综合的考虑,客观上允许批评的不只是作品本身,而且还可以针对艺术家的广泛创造力等进行批评。
与上述情形均有所不同的是,有关“正当利益保护”的规定仅是“或代表正当利益所发表的言论”,有关这种正当利益的保护并没有适用的对象、适用的范围、适用的条件等任何具体的规定,可以说,这种规定是相当抽象的。但是,正是这种抽象性扩大了对符合正当目的、正当手段的言论的保护范围。
正当利益保护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上述正当利益保护的抽象性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正当利益保护的抽象性,其适用的范围才具有广泛性。由于德国刑法第193条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德国司法判例原则上限制了行为人自身利益代表的行为,但又不得不将自身利益这一概念广泛定义,特别是与行为人个人“紧密联系”的他人(如协会、阶层代表、社区成员)利益纳入保护(3)Hermann Blei,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1983,S.105.。所谓的“共同利益”(如政治、宗教、世界观等),德国学界认为,只有在行为人由于其特殊的职位而代表相应的利益时,才符合德国刑法第193 条的规定(4)Reinhart Maurach,Deutsches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1964,S152.。
德国刑法第193 条中有关“正当利益的保护”的规定具有特殊性。正当利益保护作为一项概括性规定只是在侵犯名誉的犯罪上适用的违法阻却事由,在其他的正当理由中都没有类似的论述。一般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只是在总论中进行规定,而德国刑法第193 条是一条分则条文,却使用了类似总论的概括性描述,这体现了德国刑法对公共事项言论的特殊保护。在德国,既有的判例和学说将刑法第193条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规定进行把握,但是刑法第193 条在本质上并非责任阻却事由,而是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进行规定的。现在的德国学界通说是将刑法第193条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被害人承诺等一般的正当化事由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进行理解(5)Reinhart Maurach,Deutsches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1964,S149.。
对于德国刑法第193 条,有研究者提出,根据不同的情况对所保护的利益及侵害的利益进行比较衡量,与侵害的利益相比,如果所保护的利益具有“压倒性优势”,相关言论是作为免于起诉的条件;如果两种利益无法进行具体的比较,则相关言论体现的是公民的辩护权(6)Hermann Blei,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1983,S.107.。但是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德国刑法第193 条有关正当利益的保护,关注点并非所保护的利益是否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是所保护的利益本身,即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利益”。
一般来说,德国刑法第193 条的适用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是不能排除适用的,这种适用是补充性的,只有在总则规定的一般违法性阻却事由无法适用时才作为在分则上个别适用的特殊的正当化事由。因此,“正当利益的保护”的规定只是发挥了辅助作用,而学界对这种“辅助作用”的理解存在争议。具体来说,有关正当利益的保护的规定是发挥着“创造性作用”还是“宣告性作用”(7)Reinhart Maurach,Deutsches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1964,S148.存在争议。
(二)创造性作用的刑法界定
所谓创造性作用是指正当利益的规定,虽然作为总论的原则性规定无法直接适用时的辅助性规定,但是这种规定本身保护的对象与价值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在必要的情形下,可以不同于一般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宣告性作用是指,正当利益保护的对象仅是总论中的一般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具体化,不能够与一般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相背离。但是,无论是对创造性作用的理解还是对宣告性作用的解释,对于正当利益的保护都认为是法律所认可的完全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法院在按照规定判断行为人是否追求合法利益时,如果仅仅一公共事项言论未违反法律及社会道德,或者公共事项言论符合一般的社会观念以及正当性观念,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合法的话,这种限制是不够的。因为不仅需要行为目的是正当的,还需要实现这一正当目的的方式也是正当的。因此,不仅利益诉求要合法,实现利益的具体行为也应该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目的与具体行为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才可以认为行为人从事了代表合法利益的行为。所谓的目的与行为之间不存在必要联系且二者都合法,例如,一个报刊的编辑为了提升报刊的销量,对于并不属于该报刊阅读范围的人发表侵犯其名誉权的轰动性的报道。就该行为而言,行为人虽然是出于正当的目的,但是其行为并非该正当目的下应有的行为,因而并不能根据德国刑法第193 条排除该行为的违法性。
尽管合法代表利益的存在赋予了行为人一个证明合法性的法律途径,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德国刑法规定的所有侮辱诽谤行为是不是都适用该项法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一些言论本身具有违法性,因为其行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以至于即使符合合法代表利益的情形也不应当排除其违法性。具体来说,就是德国刑法第193 条是否适用于第189 条对于死者的诽谤以及第187 条恶意诽谤的情形。第189 条是对死者的名誉毁损的规定,一般来说,对严重损害名誉的行为的处罚相较于一般的名誉毁损处罚更为严厉;而第187 条则规定的恶意诽谤是指有意识、有目的地扭曲事实真相的言论。在德国的司法判例中,原则上排除第193 条在上述情形下的适用,当然也并非绝对,在少数情况下也存在例外的情形,特别是当行为人所谓的违背真实性的举证是其唯一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的情形。德国学界大部分都支持这个观点,小部分则完全反对刑法典第193 条适用于187 条与189 条的。虽然这两种意见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是都认可刑法第193 条的辅助性特征。
三、日本刑法公共事项言论的保护路径
在日本刑法中,对名誉权进行保护的规定主要有日本刑法第230 条,第230 条将对名誉毁损的行为作为处罚对象,但除了死者的名誉外,一般情形下,无论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涉及的事实真实与否都被认定为损害名誉的行为而进行处罚。有关事实指摘毁损了虚名,虚名作为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社会评价,是人的一种利益,对其实施保护是很有必要的。日本刑法第230 条规定,对他人公然进行事实的指摘,毁损他人名誉者均以毁损名誉罪论处(不问这种事实的真伪)。
(一)虚名保护的争议
公民的虚名如何保护?对于公民虚名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也对公民的社会评价造成损害?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争议。公共事项言论是公民对政府的正当批判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与这种利益相比,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虚名保护不得不后退。所谓的优越利益保护原则,即对于虚名保护有关的利益在与表现自由权保护的利益相比时,后者的利益更为优先与重要。因此,有关公共事项言论在保护名誉的同时,也需要对表现自由权进行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新宪法包含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体现新宪法精神的日本刑法修正案对事实证明的规定重新进行了设定,这就是日本刑法第230 条第2 款的规定。根据该款规定,公共事项言论,并非损害他人名誉的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事实的真实性就可以免除刑罚。具体来说,如果相关言论能够满足摘示事实的公共性、目的的公共性以及事实的真实性证明这三个条件,那么行为人都可以免除处罚。如果不能证明事实的真实性时,刑法第230 条第2 款是不能适用的。可以说,刑法第230 条第2 款对公民行使表现自由权具有积极保护意义。在公共事项问题讨论时,并以不损害他人名誉为条件,如果是真实的事实,这样的言论能够获得法律的保护。
前文从行为无价值论出发,对公共事项言论进行正当化的论述,但是由于行为无价值论并非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所以遭到了结果无价值论者的反驳。正当化事由的事实前提是误认没有过失的场合,即行为正当化的主张包含非常重大的伦理价值,必须慎重地检讨。前述结论作为行为无价值、主观违法论情形表示的典型,根据行为无价值论的强调与刑法的主观化和伦理化相关联,表明客观的违法论、基本的结果无价值论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名誉毁损行为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根据有关真实性的证明,其行为并非行为后的事情,而是行为时存在的事情,从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以及对名誉的保护在宪法上调和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有关阻却违法的要求仅以事实的公共性和合理的根据为要件,与刑法第230 条第2款的要求相比更为宽松,对于表现自由权过度保护的倾向也是存在疑问的。
(二)刑法中真实性证明的性质
随着新的刑法条文的规定,新的讨论也随之而来。公共事项言论是否仅指在诉讼中完成真实性证明的言论?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真实性证明作为一种事后的、诉讼意义上的活动,在行为人言论的时候,如果以确保在事后的诉讼中能够证明真实性为限,这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是过于严苛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行为人在言论时,根据必要的资料、依据能够相信有关事实的真实性,但在诉讼中未能完成真实性证明,如果不对这样的言论进行保护,将不利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不利于宪法权利的维护。
事实证明,前述规定的法律性质的论证对事实真实性的误信情形处理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对于犯罪行为是否成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扩大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对于日本刑法第230 条第2 款事实真实性证明的法的性质,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从阻却违法性角度对公共事项言论的保护,也就是从所谓违法性的方法入手,将公共事项言论解释为符合日本刑法第35 条的“法令或正当业务的行为”,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有关公共利害相关的事实,出于公益目的,应将公众的知悉权纳入正当权利的保障范围,必须完全排除刑罚制裁的观点;出于对真实性言论的保护,即使未能证明对伤害他人名誉言论的真实性,行为时事实盖然性较高的言论的发表,亦即根据确实的资料、根据对真实性相信的言论,并不应当接受刑事制裁,这是作为正当权利的行使,也是作为法律保障的要求(8)藤木英雄:《事実の真実性の誤信と名誉毀損罪》,《法学学会雑誌》第86卷第7-12号,1972 年,第1104-1124 页。。有关真实性的确信的资料、根据的场合是指,根据事实的真实性,优势证据是具有客观盖然性的证据。
名誉毁损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名誉保护的平衡,根据对有关真实性的合理确信,有关事实的摘示,如果相关行为缺乏客观的过失,是应当作为正当行为阻却违法性的。对于他人名誉毁损的行为,如果已经履行了必要的调查义务,则应当免除名誉毁损罪的罪责,所谓言论自由的保障与名誉保护调和的观点是妥当的。基于合理的根据,有关真实性误信的场合作为阻却违法事由,行为者在行为的时候根据相当的资料、依据,也就是对这种事实的摘示有相当的理由,即使没有客观的事实的场合,这种行为也可以作为违法性欠缺的解释。但是,事实前提误认,在没有过失的场合可以作为正当化的事由,而这种真实性的误信在没有过失的场合根据刑法第35 条阻却违法性(9)藤木英雄:《名誉毀損罪における事実の証明——事実を真実であると誤信した場合の罪責(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上不法な利益——刑法第246条第2項の罪の成立要件)》,Jurist(増刊),东京:有斐閣,1967年,第208-211页。。可以说,这是从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以及行为无价值重视的立场上得出的观点。
“事实的真实性”问题也是“表现自由的界限”问题,而非“虚名保护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名誉,“表现自由的界限”作为问题,并非“虚名剥夺的界限”的问题。从这个立场来说,表现自由是否仅仅在有关虚名保护时具有优越性,不具有真实名誉时表现自由是否需要充分保护,必须进行慎重的检讨(10)平川宗信:《名誉毀損罪と表現の自由》,东京:有斐閣,1983 年,第85-109 页。。表现自由认可的场合,最初仅限于虚名剥夺的场合,不能论证作为事实的前提。但是,对于言论是错误的场合,也应当予以考虑,是作为“表现自由界限”的问题进行考虑,从更广泛的范围和从表现自由的角度进行考虑。
(三)刑法规范中的宪法价值保护
根据宪法论反映的违法论的观点,基于合理的根据进行事实的摘示,以日本宪法第21 条言论自由的根据作为法令的行为阻却违法性,也就是说,根据刑法第35条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另外,刑法第230 条第2 款是基于合理根据的违法阻却事由以及基于真实性证明的处罚阻却事由的规定。为了达到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对与名誉保护进行调和的目的,一方面,毁损他人名誉、进行事实的摘示者,慎重地对有关要求履行调查义务并给予合理根据摘示的场合,无论事后有关真实性证明的有无,否定名誉毁损罪的成立;另一方面,即使轻率地对有关事实给予摘示,如果事后有关真实性被成功证明,名誉毁损罪虽然成立,但是免予除处罚。
事实的真实性与否以及言论的违法阻却,作为表现自由与名誉保护在宪法上的调和,宪法第21 条对有关问题的规定,侧重于对必要、有益情报的流通的保障。而这种保障相较于对其他一般权利的保障具有优越的地位,应当优先予以保障。对表现自由的保障,比对名誉的保障而言处于优先的地位(11)平川宗信:《名誉毀損罪——表現の自由と名誉の保護》,阿部純二、板倉宏、内田文昭、香川達夫、川端博、曽根威彦编:《刑法基本講座》第6 卷《各論の諸問題》,法学書院1998 年版,第110-122 页。。对他人名誉侵害的事实构成犯罪必须具有正当性,否则言论是不具有违法性的,这种保障范围,是为了防止“自己检阅”,对于自由讨论的保障并不充分。因此,即使并非真实的事实,有关事实的真实性推测是基于相当合理的根据、资料时,可以认为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为了保护表现自由,作为阻却违法性的问题,有关合法言论成立的条件是:第一,有关问题属于宪法中公共事项的问题,事实具有公共性。第二,有关事实的真实性、有关推测的程度,有相当的根据,是基于这种相当根据的言论。仅以表现自由“知的权利”为限的作为“自由情报流通的权利”,言论的违法性源于言论的内容,以及作为样态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的判断,所谓的“真实性的确信”以及“为了公共利益”并不作为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要件,检察官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特别是检察官在对“相当的根据”存在无法立证的时候,阻却违法性。违法阻却事由的错误,也就是基于合理的根据存在误信的场合,作为事实的错误阻却故意的成立。
平川教授的观点是,基于合理的根据进行的事实摘示是正当行为,阻却违法性,这与藤木教授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平川教授的观点比藤木教授的观点更为彻底。也就是说,藤木教授有关公共事项的言论是按照第230 条第2款的真实性证明来阻却刑罚的,只有在真实性无法证明且行为人是基于合理的资料、根据的时候,根据刑法第35 条的正当事由阻却刑罚;而平川教授则认为,基于合理的根据进行事实摘示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5 条阻却违法性,只有根据第35 条无法阻却违法性并且能够进行真实性证明的时候,阻却处罚。此外,根据平川教授的观点,有关事实的真实性符合大致推测的程度,并且具有相当合理的根据时证据就已经充分,而藤木教授认为,有关真实性的事实,必须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真实的事实,真实性的判断必须达到无过失的程度,需要有确实的资料、根据。同时,藤木教授认为需要行为人有关的目的公益性以及真实性确信的主观要件作为必要的条件,而平川教授则认为并不需要。可以说,平川教授对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识要求比藤木教授更为宽松,行为人主观方面即使存在过失,也并不影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另外,根据平川教授的观点,有关真实性的举证责任的要求,是需要由检察官来承担的,而藤木教授则仍然认为应当由被告人来承担。从这一点来看,平川教授对于被告人的保护更加充分。
四、公共事项言论刑法规制的本土化路径
德国刑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共事项言论的特别保护条款,而是在第193 条作为“正当利益拥护”的言论中的一种情形,作为一般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排除了言论的违法性。有关“正当利益拥护”的言论,虽然在法条中规定得比较抽象,但是德国刑法学者通过刑法总则的理论支撑,对该项规定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解释。德国刑法中辅助性条款规定了一般违法性阻却事由,而我国刑法总论中缺少一般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正当利益的拥护”作为分则有关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需要以总则相关违法性阻却的一般性原则作为成立的必要基础。在我国有关违法性阻却的讨论仅限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并没有作为一般的、原则性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
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成立条件,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限制条件,才使作为正当利益的拥护的规定具有非常充分的成立的前提性规定。即使没有分则有关“正当利益拥护”的规定,根据刑法的一般原则,有关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成立条件充足的情况,也可以作为有关公共事项言论阻却违法性成立的依据。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类似德国刑法中“正当利益拥护”这种抽象性、概括性的条文。一般来说,法律的明确性是立法的基本要求,这一特点无论是学者对条文的学理解释,还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操作中的理解,都是必不可缺的前提。在德国,虽然刑法第193 条规定了抽象性的条款,但是,由于对刑法总则部分的解释,该条文的适用范围还是相对明确的,而在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还不具备能与之匹配并且能够准确、翔实地解释条文的能力。因此,对于这种抽象性分则条款如果直接在我国刑法中加以规定,直接借鉴德国刑法规定并不合适。
我国刑法也没有类似日本刑法第35 条对正当行为加以明确规定的条款。但是,日本刑法第35 条作为一项兜底条款,并非必须具有这样的条款才能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对于任何行为,如果不具有违法属性,则必须排除该行为的违法性。公共事项的言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不排除这种言论的违法性,可能会存在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可能。正是出于对宪法表现自由权保护的考量,如果有关行为本身履行了必要的义务,具有正当的目的,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就应该予以保护。从刑法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具有违法性的,当然应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公共事项言论的入罪界限,应充分考虑名誉权与表现自由权的平衡和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维护。公民监督权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处于国家法秩序的顶端,它是国家法治的“血肉”(12)王涛:《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与合理规制》,《法学》2014 年第9 期。。对于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来说,相比拥有广泛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媒体资源的国家工作人员,普通公民的力量是相当弱小的。为了名誉保护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协调,司法者对言论自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合理确信规则使言论自由的宪法规定效力射程及于客观虚假但“主观真实”的事实言论(13)刘艳红:《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10 期。。因此,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所谓的监督言论所必要的资料、根据的搜集也是相当困难的。要求公民的监督言论的事实有充足的资料、根据的论证,并且排除错误事实发生的可能性,是过于严苛的要求。这种过于严格的资料、根据的搜集要求,增加了公民不必要的搜集资料、根据的义务。
为了保护公民的表现自由权,需要降低对公民资料搜集、根据的要求。具体来说,公民发表的监督言论,如果已经履行了资料、根据的搜集义务,并且搜集的资料、根据与监督言论之间具有必要的逻辑因果关系,即使公民对于言论的虚假性具有认识的可能性,也应当认为这种言论符合正当目的的“相当手段”的要求。公众批评可以督促一个法定监督机构对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或另一公权力机构履行制约与监督的法定职责,并可以为法定监督机构提供违法犯罪信息(14)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 年第4 期。。因此,对于监督言论,为了满足“相当手段”的条件,本文认为,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出于公益性目的,且已搜集了一定的资料、根据,并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搜集的资料、根据与监督言论的事实之间已具有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已经满足正当目的的“相当手段”的条件。
(一)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判断标准
对于“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标准的衡量,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如果认为公民的监督言论是虚假的,不具有真实性,则必须出示一定的资料、根据的证明;如果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虚假言论,即使是出于公益性目的的监督言论,也不具有正当性。其次,公民进行监督而发表的错误言论,如果进行了资料、根据的搜集,但是,如果公民搜集的资料、根据与损害他人名誉的错误言论之间完全没有因果联系,例如,“甲官员喜欢笑,所以甲官员是个贪官”的言论,即使搜集了再多甲官员的证据,但是这种证据与最后的言论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这种言论同样不具有正当性。最后,公民如果进行了资料、根据的搜集,搜集的资料、根据与诽谤言论之间具有逻辑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还需要满足必要的条件才能成立。例如,“乙官员是个胖子,所以乙官员公款吃喝”,或许乙官员之所以是个胖子,正是因为乙官员太多的公款吃喝,但是“肥胖的官员就必然公款吃喝”的逻辑性并未达到“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的条件。因此,公民的资料、根据的搜集与监督言论之间必须存在“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至于具体的“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的理解,本文认为,应当符合必要性与适格性的要求。
所谓具有必要性的言论是指,有关公共事项的言论,如果公民在言论时已经做了必要的相当准备,也就是说已经履行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必要义务,在这个前提下,即可以说公民已经排除了言论错误的“危险”,即使在事后未能证明,也应当属于法律所允许的“危险”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就应当认为符合手段的相当性,是具有必要性言论的前提。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言论的必要性,并非指有关言论必须是某一场合的唯一手段。在几种手段同时存在的场合,选择最为稳健的手段也可以认为具有必要性。例如,某人在其小区内,看到乙官员多次开车经过该小区,并在小区停留,该行为人就举报该乙官员与小区内某女子有不正当关系,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这种逻辑关系并不具有高度的应然性。乙官员来到某一小区,或许是为了看望朋友,或许在该小区另有住所,行为人的监督言论仅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并且这种可能远非是最有可能性的一种判断,因此不具有必要性。但是,如果行为人不仅看到乙官员将车停在小区内,而且能够证明该官员在小区内明确的目的地住址,并且该地址的住户是一名年轻女子,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说行为人的言论就是具有必要性的言论。
在这种情形下,该女子可能是该官员的亲属,也可能是该官员的普通朋友,根据行为人搜集的证据、资料,则可以推断在这诸多的可能性中行为人所指称的事实具有相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虽然并非唯一的结论,但是仍然可以认为是具有必要性的结论。又如,如果行为人看到乙官员多次开车经过小区前面的高档会所,并多次出现在会所门口,行为人以此举报该官员公款吃喝。同样地,虽然行为人的证据并不充分,官员出现在某会所门口与该官员公款吃喝,或许并没有完全等同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搜集的证据,并且搜集的证据虽然可以得出多种结论,但是,只要其指称的结论是作为最为稳妥的结论,就应当认为这样的言论具有必要性。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对行为人的监督言论进行保护。
(二)适格性标准
所谓的适格性是指,某一发表公共事项言论的行为在事后来看,是为了正当利益的拥护,为了有效性的促进并能够被法律认可。具体来说,有关公共事项的言论,行为人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其言论并没有明显地超出合理的范围,行为人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造成了损害,由于是依据必要的资料、根据得出的合理结论,可以认为这种言论是一种对社会整体利益进行有效性促进的言论,当这种有效性促进能够被认可,就可以断定是适格性的言论。例如,行为人为了举报官员甲,指出不仅甲官员接受贿赂,而且甲官员的妻子也接受贿赂,同时又举报甲官员的妻子私生活混乱。在这里,对于甲官员及其妻子接受贿赂的举报,是符合监督适格性标准的,是对于官员正当监督的必要言论。但是,对于甲官员妻子私生活混乱的事实,一方面甲官员的妻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甲官员妻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并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这样的言论并不是符合适格性标准的言论,即适格性是有适用范围的。又如,某市的一家报纸刊文指出,在该市打击卖淫活动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抓捕时,该市有官员也一同被抓捕,但是并没有指出是哪些官员。在其他报纸进行转载的过程中,某报纸不仅将该新闻事实予以转载,同时指出涉事的两位官员的姓名。对于后一家报纸来说,虽然是有关公共事项问题的讨论,但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推测的方式指出涉事的官员,这样的言论已经超出了适格性的范围,并不具有正当性。
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会造成对公共事项言论的保护重点不突出的问题。由于正当利益拥护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公共事项言论的保护,原则上为了拥护正当利益的言论,都可以适用该条文。这样的规定当然不存在问题,但是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对于公共事项言论的保护,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会造成重点不突出、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所有为了正当利益拥护的言论,对于公共事项言论的特殊保护更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因此,原则上本文对有关言论的特殊保护,仅限于公共事项的言论。
(三)辅助参考的标准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应当符合“正当目的的相当手段”的条件。即公民在发表有关公共事项言论时,是根据一定的资料、依据而发表的具有必要性与适格性的言论,这种资料、根据需要与监督言论的事实存在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通过“必要性与适格性”作为“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的限定,但是,以“必要的应然逻辑关系”作为认定判断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存在界限不够清晰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言论的具体情状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根据言论的具体的背景、情况,言论的时间、地点,言论行为人的职业等情形进行综合的分析。作为判断的因素,以下几个因素可以作为判断时的辅助参考:
首先,对比分析对名誉权这一法益侵害的程度的范围以及对表现自由权的法益所应当保护程度的范围,对于已经远远超出表现自由权所应当需要保护的范围、严重侵害名誉权法益的言论,原则上不需要保护。如果有关言论所涉的事情越是重要,则有关言论所涉的利益的价值越高,作为诽谤言论的正当利益保护所要求的检讨义务也就相对较低。
其次,有关言论虚假性的应然性程度作为是否具有必要逻辑性辅助的判断标准,如果这种真实性的应然性程度很低,就可以认为有关资料、根据与监督言论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例如,仅仅看到某一官员的轿车停在其他小区的停车场,就认为该官员的作风有问题,这种情形并不能认为具有逻辑关系。
最后,如果对有关资料、根据与言论的事实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联系难以判断抉择时,原则上为了保护公民的表现自由权,应当倾向于认为两者间具有逻辑联系。也就是说,公民所进行的资料、依据的搜集与有关监督言论之间,可以认为具有逻辑关系,也可以认为不具有逻辑关系时,应当以表现自由权的保护作为重要法益的保护,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公民发表的监督言论,如果履行了一定的资料、根据的搜集,就应当排除行为的违法性,但是,这种资料、根据的搜集还不能明确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已经排除了过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