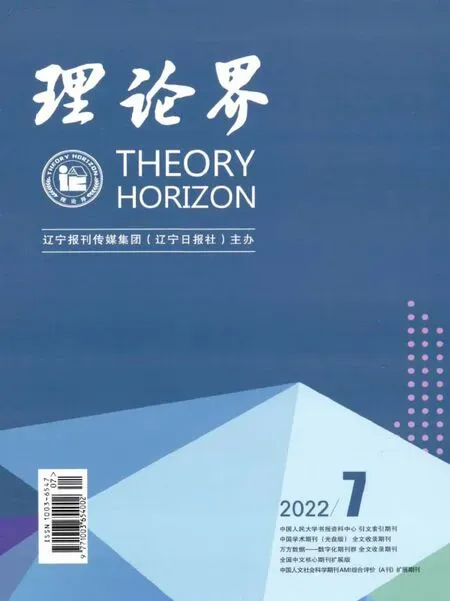宋荦与“江左十五子”交游考
2022-11-23蒋惠雯
蒋惠雯
“江左十五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构建,源自宋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选刻的《江左十五子诗选》(下称《诗选》),秉持“无甲乙,以齿次第”的理念,《诗选》以年龄为序,依次是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杨棆(后改姓为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釪十五人。“十五子”虽皆居于江宁,却散落在长洲、宝应、武进等各处,本无交集,实因一本诗选聚在一处,无论是犹在江宁、尚未发达之时,抑或是身处京都、跻身清华以后,我们都能在诸子诗集中窥见他们互相酬唱、交游的场景。纵览《诗选》收录的“十五子”作品,大多为颂圣酬对、温柔敦厚的“庙堂诗歌”,或大抵是宋荦好尚的格近昌黎、眉山的篇什。由此可见,作为《诗选》选刻者、时任江宁巡抚的宋荦,无疑对十五子群体的形成乃至诗学取向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梳理宋荦与“江左十五子”的交游,不仅是对“十五子”群体形成、诗风确立的过程回溯,也能借此探索其时政治背景与江南文学心态、人事关系相互缠绕的深层机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荦调补江宁巡抚,开启他长达十四年的任职。开府江南期间,宋荦网罗江南文人,大力推行文教,促使江南文化从明末清初战乱残烬中恢复元气,而其作为“风雅总持”,最有影响之举便是辑刻《江左十五子诗选》。宋荦对“十五子”的推举,一方面是出于求声引气、议取门户的需要,借举他人以自举;另一方面则意图将之作为开府江南的文教政绩,消解江南“野遗”主导、与庙堂离立的诗界格局。事实上,“十五子”群体的形成并不是依靠《诗选》的刊刻一蹴而就,在之前近十年的时间里,宋荦与“十五子”逐渐相识,通过诗文酬唱、组织雅集等交游活动,分享自身的诗学理念与审美倾向,对该群体诗风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宋荦与“十五子”的交游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也就是江宁巡抚任上的第二年。其年“四月,观风各郡邑,录士若干人,刻试卷若干首,又刻诗古文各一卷,题曰《吴风》”,〔1〕即宋荦“观风之役”后拔录吴中士子“诗古文辞佳者”〔2〕并刊刻成卷。这场文事活动可视为其初到任的一次试水、《江左十五子诗选》刊刻的先声。也正是在此次选拔中,宋荦关注到后来“十五子”中的顾嗣立、吴士玉二人,对他们的文采极为欣赏,并在《吴风》(卷下)作了收录点评。
顾嗣立,字侠君,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旨钦赐进士,长洲人,著有《元诗选》《寒厅诗话》《秀野草堂诗集》等,乃“江左十五子”中与宋荦交游最为密切者,两人结识后二十余年酬唱赠答从未间断。顾嗣立曾在《闾邱先生自订年谱》中详述与宋荦相识之缘由:“是冬,商丘宋中丞漫堂荦观风七郡,一州之士制义外,复录诗古文辞,厘为二卷,名《吴风》。余《春日泛舟石湖过范文穆公祠观宋孝宗御书歌》亦为采入,因始招至署中赋诗赠答,蒙国士之知焉。”〔3〕同年十二月,宋荦为顾嗣立《元诗选》作序,充分肯定其编选元诗的价值所在。这不是宋荦为顾嗣立唯一所作之序,据《闾丘先生自订年谱》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十五日,寓扬州兴教寺。旋登金焦二山。十月五日,归草堂。有《金焦集》一卷,宋中丞漫堂、邵处士青门长蘅为之序。”又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顾嗣立自闽游历归来有《啖荔集》二卷成,宋荦为之题诗:“迢遥归棹自闽疆,六月登临兴太狂。添得新诗佳绝处,武夷山色荔支香。”除却对其诗文的欣赏,宋荦对顾嗣立的珍重提携也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关怀,如顾嗣立《岁暮宋中丞以菜鸡琥珀光见饷作歌奉谢》云“小园徒依觅诗情,白战残年无寸铁。忽见中丞宣使来,黄鸡火酒还罗列”;大到在顾嗣立入京应试时向诗坛巨擘王士禛、韩菼等人举荐。康熙三十四年(1695)岁末,顾嗣立将入京应试,宋荦特意给王士禛去信:“侠君少年笃学,所选《元百家诗》一时为之纸贵,素仰高山,愿侍函丈,惟先生进而教之,假之羽毛,将来自是我辈后劲也。”面对宋荦的关爱,顾嗣立在归吴途中曾作《寄怀商丘公二首》以表感激之情:“梅花席上赠诗章,又听西风雁数行。年长逢秋悲易入,途穷感德意难忘。……想到公余吟咏处,几宵清梦落沧浪。”此外,顾嗣立还多次陪宋中丞游山赏景赋诗,如雨中元墓探梅、过慈仁寺成周卜寓斋看月、游天宁寺塔院等等,更是积极参与宋荦组织的各类大型文人雅集,足见交谊之深厚。
吴士玉,字荆山,号臞菴,谥文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吴县人,著有《吹剑集》《兰藻堂集》。无论在江宁还是京师,宋荦主持的诗文酬唱中常见吴士玉的身影,仅《江左十五子诗选》收录就有八首。其中有三五人的酌饮唱作,如含清亭赏花赋诗;有与宋荦的诗文奉和,如《奉和漫堂先生舟次仙女庙原韵》;有观赏宋荦藏品所感之作,如《松花江绿石砚歌》《玉带生歌奉和漫堂先生(有序)》《石屏歌为商丘先生赋》;也有参与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小沧浪寿苏、四十二年(1703)小沧浪观演《桃花扇》这类大型活动。此外,宋荦曾为吴士玉《吹剑集》作《题吴荆山吹剑集兼寄韩慕庐王阮亭两尚书》,将此集推荐给韩菼、王士禛,诗中“出口如景宗,直抉骚人髓。尔后衮衮来,杜韩无坚垒。一卷冰雪文,把诵每移晷。吹剑何言谦,雅音实在是”〔4〕的评价可见其对吴士玉诗才之欣赏。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因修沧浪亭而撰的《沧浪小志》初版刻成,这是宋荦“来抚吴且四年”后又一较大规模的文学事件。是书分为上下两卷,下卷收录了宋荦及其友人关于沧浪亭的记、诗、赋三类作品,康熙三十五年后的相关吟咏佳作也陆续被纳入,其中便有“十五子”中的三人作品,分别是王式丹《沧浪杂诗》、吴士玉《春日游沧浪亭观牡丹听澄照上人琴》、李必恒《沧浪亭用欧阳公韵》。可见,在沧浪亭修建完成后,“十五子”积极参与了宋荦在此处举办的各类雅集吟咏,保持着密切往来。
康熙三十六年(1697)闰三月,“西域叛羌噶尔丹就擒,王师荡平五千里。会抚江左者,商丘宋牧仲中丞,檄省属博古士为赋铭歌颂,纪其盛。”〔5〕应此盛事,李必恒于十二月冬作《大恺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一千五百言以献,邵长蘅见之大为叹服,招至府署,将其引荐给宋荦,由是相识。
李必恒,字北岳,一作百药,晚年自号樗巢,高邮人。“十五子中,宰相、尚书,不一而足;惟李百药一人以诸生终。而诗尤超绝。”〔6〕相较“十五子”中的其他人,李必恒一生可谓郁郁不得志,后更是因“耳聋多病,年止中寿”。〔7〕正因出身较寒素,他的诗风也更为现实主义,“居秦邮,故其集中于淮湖水患,三致意焉”,〔8〕不徒以风雅自弄为限者。其“诗格之高,才力之大”令宋荦也为之震惊,旋即致入幕府,待以上宾。李必恒《赠毗陵邵子湘先生》诗前序中对此有记载:“丁丑冬,予奉檄作《大恺铙歌》词,时先生客商丘公,许见鄙作,大惊异之,亟言之公,招致院属。”夏味堂《樗巢先生传》也提到:“先生成《大恺铙歌》十二章,中丞得其卷惊服,敕有司礼以致之。乃游吴,中丞倒屣迎入,与毗陵邵青门敌礼。其后选江左十五子诗,先生与焉。”显然宋荦对李必恒极为欣赏,将其纳入门下,并有“老兴自怜追白傅,惊才近喜得刘叉”表达自己得此才人的振奋惊喜。值得注意的是,在宋荦门下的安逸生活给李必恒的诗歌风格带来了明显的改变,从前期对民生的关注逐渐转向大自然与身心发展上,与宋荦的赠答应和之作明显增加,如《江左十五子诗选》中就收录了《上宋中丞漫堂先生五言古诗一百六十韵》《虎丘次清远道士韵古风一首赋谢漫堂先生》《漫堂先生打鱼沧浪归以飨客叨陪座末即席赋呈一首》《西洋绣球花二十韵应漫堂先生命》《苦雨诗呈漫堂先生》等诗作,均是五六年间与宋荦一同出席各场合交游酬唱留下的诗篇。
二
围绕桃花坞唐寅墓以及沧浪亭等文化景观的修复重建,宋荦不断召集时人诗文唱和并纂刊成集,逐渐将江南文人联系到了一起。随其声望日隆,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起,宋荦在江宁举办各类文人雅集活动开始明显增多且颇具规模,也是在这一年,缪沅、郭元釪、宫鸿历、王式丹、徐昂发、张大受等“十五子”陆续与之产生联络。
三十九年夏,王翚据宋荦三十余年来宦游所遇名胜作“六景图”,庚辰立秋日,宋荦即其事“各系五言诗一章,要一二故人和之”。一时和韵者众多,今可见者在江左十五子中便有缪沅《六境图》、顾嗣立《六境图咏》以及徐昂发《和宋中丞六境图诗》。
缪沅,字湘芷,初名湘,字沅芷,一字澧南。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海陵人,官至少司寇,著有《馀园诗鈔》。缪沅《六境图》序中简述了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六境图为商丘公生平宦游之地,其详见公集中乌目山人王翚绘图纪胜,庚辰冬日谒公于扬州官舍,出图相示,谨和六章。”虽据缪沅所述这组诗作于其年冬日,但这并非意味着此时才与商丘公初识。缪沅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之前,与宋荦已有交集,不过多停留在慕其诗、和其韵的层面,如《剑池再叠商丘公龙井茶韵》《舟行杂诗用商丘公韦菴闲兴韵三首》《蠡山用商丘公丁卯桥韵》等等;二人的频繁交游始自三十九年九月,在此一个月内便有重阳组诗相和、共赏珍宝石砚等诸多交集。
徐昂发,字大临,一字畏垒,榜姓管。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长洲籍,著有《畏垒山人诗集》四卷、《乙味亭诗集》六卷。大临少负才名,博学工诗,为时所称。徐昂发进士入京较早,与宋荦的交流虽不如顾嗣立等人密切,但亦有私交。除却上文提到的《和宋中丞六境图诗》这类雅趣唱和之作,徐昂发对这位为政一方的大员也不乏仰慕,不仅作“公来肉其枯,布宣天子惠……伯仲两贤间,丹青炳仁义。淮海数千里,田畷长嘉穗”扬其为政之德;更有“匠气激徐庾,格凌沈谢上……韩杜诗笔兼,白韦声价两。长啸深净轩,千秋继高唱”〔9〕赞其诗文之才。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宋荦因“已过重阳雨不休”感而作《秋日广陵杂兴八首》,和者累累。除上文谈及的缪沅外,也有郭元釪、宫鸿历等人作“前题用韵”和诗。
郭元釪,字于宫,号双村,江都人。家世业盐,荚饶于资,以诸生终,曾奉命修订《全金集》,另著有《一鹤庵诗集》。郭元釪为“十五子”中最年少者,因其“学博思深,诗笔奇险,商邱宋牧仲荦称为异才”。〔10〕郭元釪也在自己的诗集序言中谈到宋荦对自己的鼓励与帮助,“予二十三岁始从事歌诗……大中丞商丘宋公极相鼓舞,始稍稍于雨寒灯尽时,构思命笔……”郭元釪与宋荦的交游,我们还可以在《诗选》中看到更多痕迹。如沧浪亭的发现与修复,是宋荦文教政绩中较为得意的一笔,郭元釪曾在此处重建后作诗赞曰:“浑忘此兴始开府,欲歌何有于吾公”,肯定了商丘公开府江南给吴地文化景观带来的贡献;又如他曾应邀前往宋荦寓斋欣赏藏画,并作《商丘大中丞寓斋观明宣宗黑白二鼠图》等诗。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宋荦得端州玉带生石砚。玉带生乃文丞相旧物,宋荦得此奇宝,作《玉带生歌》,“诸同人和之”。《西陂类稿》诗后附宫鸿历所作同名诗,除此之外,未见于《类稿》但参与此次唱和的还有缪沅、王式丹。同月,宋荦至白田,雨夜泊舟,招饮王式丹、乔崇烈诸子,并共观名画卷轴,有《白田雨夜次顾黄公贳酒不得韵示王方若乔无功诸子》为证,诗后还附王式丹等次韵诗。
宫鸿历,字友鹿,一作槱麓,号恕堂。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瀛海人,著有《恕堂诗》。宫友鹿“笃学好古,少即以声诗鸣淮海,壮岁游京师”,其诗“剽若奔雄雷,剡如饮渴蝀;险句鬼可泣,强韵山欲动”,宋荦颇为欣赏,引为知己,曾送自己的诗集邀其雅正,恕堂先生为此曾作《商丘公送绵津诗集及近稿数种率成长句赋谢》。康熙三十九年,宫鸿历先后参与了前文提到的九月重阳和诗以及玉带生赠歌;其后入京师,亦可于宋荦故旧门生聚会以及小除日漫堂燕集等雅集中见其身影。
王式丹,字方若,号楼村。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甲一名进士,宝应人,著有《楼村集》二十五卷,“江左十五子”中最年长者,《诗选》列其为首位。他曾“以会、状登第,乡举时本拟元,后改第六,三元嘉话仅一间也”。王式丹受知于宋荦,缘于一联七律,袁枚《随园诗话》载:“余泊高邮,邑中诗人孙芳湖、沈少岑、吴螺峰招游文游台……螺峰云:楼村以七律一联,受知于宋商邱中丞,遂聘在门墙,列江左十五子中,大魁天下。诗云:‘尊中腊酒翻花熟,案上春联带草书。’不过对仗巧耳。前辈之爱才如此。”宋荦对王式丹的寄予厚望从“招邀数子文字饮,周旋拟接昆吾锋……老夫饱吃苏州饭,沧浪射鸭弯竹弓”等诗中亦可见。除此之外,王式丹也积极参与到宋荦组织的雅集酬唱中,作《玉带生歌》《题宋山言学诗图》等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之后,宋荦进京升任吏部尚书,与王式丹的交集则更多,在此不多赘述。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宋荦为徐永宣题《云溪草堂图》,诗中赞曰:“之子江东秀,风流小杜齐。人传秋柳句,家住白云溪。”对其诗歌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徐永宣,字学人,号辛斋,别号茶坪。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武进人,著有《云溪草堂诗》三卷、《荼坪诗钞》十卷,与庄令輿同选《毗陵六逸诗歌鈔》二十四卷。宋荦曾为其诗集作序,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载:“云溪诗三卷,曰《师竹集》,曰《春草集》,曰《力葵集》,宋牧仲作序。”而徐永宣也多次写诗上呈宋荦,如《诗选》中选录的《述德抒情五言六章上宋大中丞漫堂先生》《游沧浪亭呈漫堂先生》《奉怀漫堂先生》等。康熙三十九年腊月,他因冰合所阻未能及时参与宋荦组织的坡翁生朝,但仍呈七言长句一首以致祭,详叙见下文。
三
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沧浪亭修成后,宋荦逐渐将其发展为举办风雅之事的活动中心。在沧浪亭举办历次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为以下三次,分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小沧浪寿苏、康熙四十一年(1702)小沧浪群饮以及康熙四十二年(1703)小沧浪观演《桃花扇》。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或为拜祭,或为送行、会友、娱乐,均属于文人活动的基本范畴,但从参与群体看,则是以宋荦为中心、江南文人为主的文学团体,“江左十五子”也深度参与其中。
康熙三十七年(1698),宋荦曾购得施宿注《苏东坡诗》,因多残缺失次,命邵长蘅、顾嗣立等校补之。康熙三十九年(1700)腊月十九,刊补《施注苏诗》竣,时值苏东坡生日,宋荦率三吴诸生等悬东坡笠屐小像,设肴醴,觞先生于小沧浪之深净轩。商丘公兴致颇高,首倡七言歌行记其盛:“诗注吴兴最称善,梅溪旧本徒区区。断简搜得费补缀,邵(长蘅)冯(景)顾(嗣立)李(必恒)儿至俱。刊成恰当公生日,岁暮霁景堪欢娱。招邀名士肃下拜,小沧浪挂笠屐图。”此次雅集江南名士众多,邵长蘅《东坡先生生日唱和诗序》中记载:“公既倡为七言歌诗记其胜,同时和者如干人,裒然盈卷轴,慕而为之者犹未已也。公辄汇为一编,命蘅序。”可惜此卷未能得以流传,只能从今见和诗中得知部分,如顾嗣立《十九日商丘公以东坡先生生日悬像小沧浪率冯山公汪武曹右衡张日容天申韩祖语吴荆山令子山言及余拜祝因成长歌一章余亦继作》等。“是日也,檐泽拄地,坚冰塞川”,邵长蘅、徐永宣、蒋廷锡、郭元釪虽因冰合未直接到现场,但事后亦有唱和。由是可知,参与的十余人中“十五子”便有六位,分别是顾嗣立、吴士玉、徐永宣、郭元釪、蒋廷锡、张大受。
张大受,字日容,号匠门,长洲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著有《匠门书屋文集》三十卷。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圣祖南巡时与顾嗣立、吴廷桢一道,召见御舟。宋荦组织的三次沧浪亭大型雅集均有参与。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蒋廷锡、张大受、顾嗣立等应试北上,宋荦为之设小沧浪群饮,同朱竹垞饯别诸人于小沧浪,并作诗《壬午冬日小沧浪同朱竹垞送张超然冯文子汪武曹右衡韩祖语张日容顾侠君冯孟容吴卫猗蒋扬孙慕苍玉公交车北上儿至筠同行用方千寄吴磻韵》,可知此次文酒之会的成员主要是包括“十五子”在内的江南后学。
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二月十四日,宋荦招江南文士集沧浪亭观演《桃花扇》,感而作《观桃花扇传奇漫题六绝句》,有诸多唱和。据顾嗣立诗可知参与者有朱彝尊、邵长蘅、张大受、吴士玉、顾嗣立、徐永宣、宋至、宋韦金等。此外,宫鸿历《观桃花扇传奇六绝次商丘原韵》可证其亦在场,即“江左十五子”中有五人参与此次雅集。
由以上三例可见,沧浪亭的修复以及宋荦围绕其组织的一系列诗文酬唱为沧浪亭赋予了更多文化内涵,在得到江南本地文人阶层认同与支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以宋荦为中心、江南后学为主要构成的文学团体。宋荦以这一群体为基础,选其佳者,于康熙四十二年选刻《江左十五子诗选》,并自序之。〔11〕
《诗选》刊刻、弘扬诗名外,宋荦亦关心“十五子”仕途的发展。据顾嗣立《闾丘先生自订年谱》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十二日,巡抚商丘宋公以《江左十五子诗》进呈行宫,特疏荐举张大受、宫鸿历、吴士玉、郭元釪及嗣立五人。至是,亦同御试。”又(四月)十七日,同总督阿山率钦取汪泰来、顾嗣立等于行宫门外引见。有感于知遇之恩,顾嗣立曾作《叙德书情上宋中丞西陂四章》:“清德堂前酒共斟,十年门下和清吟……举袂潜挥知己泪,临觞难惬报恩心。”
“十五子”其余如吴廷桢、杨棆诸位,与宋荦的联系虽不如顾嗣立、吴士玉等人紧密,却也有过诗文唱和,如杨棆曾作《重九日过北兰寺恭和宋大中丞原韵六首兼呈澹公》;宋中丞也曾将《绵津诗集》赠予王图炳品评,有王诗《邗沟旅夜读绵津先生诗集赋呈五绝句》为证;又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圣祖南巡时,宋荦推举吴廷祯一同迎驾于郊野,并指以奏曰:“此吴中才子也”。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圣祖乘舟南巡,宋荦扈从期间得诗七首,编为《迎銮三集》,此集时人题跋颇多,“十五子”中便有吴廷桢、吴士玉及李必恒三人。吴廷桢在跋中赞美宋荦诗之煌煌大美、感念其提携之恩:“忆在己卯,廷桢跧伏田野拟献迎銮诗二十四章,辱公一言之奖。今读公诗煌煌乎如黄钟大镛……仰负师承三复志愧。”〔12〕吴士玉以师称之:“吾师此种诗可定北征南山从来纠纷之论。”〔13〕李必恒则以七言颂之:“健笔凭将答主知,杜韩班马实兼之。他年好上东封颂,不独南山小雅诗。”〔14〕从三人的评价可以看出宋中丞在江南士子中的声望以及对其诗歌风格乃至诗学观念的认同。此后不久,宋荦便升补吏部尚书,离开任职长达十三年之久的江宁,启程赴京,但他给“江左十五子”乃至江南诗坛留下的影响都是深远持久的。
四
“江左十五子”之一的吴廷桢曾盛赞宋荦主持风雅、广事生气给江南文坛带来的影响:“商丘先生倡导风雅政事之余,以诗学教后进,吴中弦诵彬彬向风。今春翠华临幸,公率先作诗导扬盛美、宣达舆情、继卷阿遂,歌之响而一时之士斐然应和,以词章获遇者多至数十人。夫非耳濡目染、服习公之诗教者素与?”在宋中丞的引导与整合下,江南文人逐渐自觉成为盛世元音的吟唱者,诗教功能得以进一步强化。而“江左十五子”显然是宋荦开府江南最得意的文教作品,十五子中有十二位进士,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曾提到:“其后十五人中殿撰一人,位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余任宫詹、入翰林者指不胜屈。”此外,这一群体在康雍诗坛尤其是江南地域还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政治与文学充分结合的代表。作为选刻者,宋荦无论在人事关系还是诗学倾向上都对该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仕途上的珍重提携,在诗文唱和以及文人雅集吟咏诸类交友活动中,宋荦也潜移默化地向“十五子”传达自己的诗学理念与审美倾向。
清初诗学观念经历了从“宋诗热”到“折中唐宋”的转变,而宋荦在这场“唐宋之争”中始终走在前列并发挥了引领、号召作用。他主政江南前期嗜好东坡,在组织补注《施注苏诗》、贺东坡诞辰一系列文事中对“十五子”的审美理念也产生巨大影响。沈德潜谓其:“又尝选《江左十五子诗》,以提唱后学,固风雅之总持也。所作诗古体主奔放,近体立生新,意在规仿东坡。时宗之者非苏不学矣。”〔15〕而后宋荦逐渐意识到宋诗热的弊端:“顾迩来学宋者,遗其骨理,而抖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转而力挽尊宋祧唐之风气。“十五子”作为宋荦的跟随者,亦大多呼应其理念作出转变。以顾嗣立《寒厅诗话》为例,其自序开头便引宋荦所言:“宋中丞西陂先生(荦)曰:‘李于鳞《唐诗选》,境隘而词肤,大类已陈之刍狗……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负,韩之鳌掷鲸呿,尚有所未逮。’持论极当。”〔16〕可见其与宋荦“尊唐祧宋”的诗学观念一脉相承。
在宋荦的文教政策下,江南诗界格局也被重塑,和平雅正的庙堂诗歌成为主流,而“江左十五子”更是引领了康雍乾三朝“以学问入诗,甚而以金石考据入诗”的风格趋向,尤其是该诗群自江左腾飞、跻身显宦后,创作更集中于裁红晕碧、酒筵茶局、题图咏物、吟风弄月等题材以及集句诗、联吟体的结构。如彭启丰为吴廷桢《古剑书屋诗钞》作序时曾评价道:“是钞所存,大都登朝以后之作,其藜采煜耀,音节和雅,适与时地相当。而先皇帝之优礼儒臣,先生之遭逢盛世,俱于诗文中见之。”又如王家相为蒋廷锡《牡丹百咏》作序赞曰:“即其文采风流、炳炳烺烺,发为文章,形诸歌咏,凡朝廷著作、郊庙典章,以及宴游应制之篇,莫不有雍容揄扬之度,以寓其纶扉翼赞之忱,此召公卷阿之什,吉甫丞民之诵,所由来也。”
由是可见,“尊唐祧宋”的诗学观在康雍诗坛成为一时之主流;诗坛的馆阁气氛也因“十五子”的推波助澜而越发浓烈,在这些潮流中我们总能窥见宋荦残留的影响,康熙皇帝选派宋荦巡抚江南以期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目的最终得以达成。而我们也从宋荦与“十五子”的交游考证中,回溯了“十五子”群体的形成过程,更触碰到了清初江南诗坛与政治、社会相互缠绕下的深层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