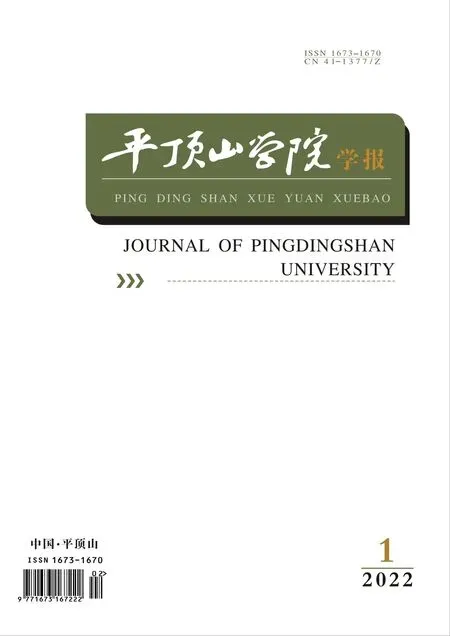折射与对话
——评陈丹晨的《巴金全传》
2022-11-23赵焕亭
赵焕亭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从1947年法国人明兴礼写出《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直到今天,关于巴金的传记专著已经有几十部,其中主要的“巴金传”有徐开垒的《巴金传》、谭兴国的《走进巴金的世界》、李存光的《巴金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等,此外还有陈丹晨在不同时期写的“巴金传”。陈丹晨对巴金的研究一直坚持了四十余年,写出了多部“巴金传”。他最早的“巴金传”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8月出版的《巴金评传》。其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94年2月出版了他的《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在2000年出版了《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续篇》。2003年,陈丹晨整合了后两部传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传》。2014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传》(上下卷)修订版。该传以率真的文字、深邃的思考生动地展示了巴金的百年人生,探寻了巴金的精神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作者陈丹晨自己的精神气质,是一部个性鲜明的作家传记。
一、执着的精神
以“巴金的梦”为关键词是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在章节命名上最为独特的地方,也是其内容组织最突出的特征。他用“梦”这样一个核心词汇贯穿了巴金的整个一生,写出了巴金追梦、圆梦的历程。该传记在关于巴金梦的描述中,既关注了巴金的特征,鲜明地体现了传记作者对传主准确而深刻的认识,也体现了作者陈丹晨本人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执着追求。
(一)写出了巴金的追梦
《巴金全传》以“巴金的梦”为主线,抓住了巴金执着的特点。巴金是个追“梦”的人。爱做梦、爱写梦是巴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巴金来说,人生的每个时期,梦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同的。少年与青年时期的梦,是人生的理想;中年时期的梦,是“文革”带来的惨痛经历;晚年的梦,是为人类而反思的梦。“梦”之于巴金,有多重意义。第一,巴金多梦,这是个生活事实,而且青年时期的梦与老年时期的梦,都是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社会潮流在巴金身上的反映。特别是晚年的巴金,梦时常伴随着他,使他不断受到噩梦的干扰,导致他神经紧张。巴金一生都在做梦,他毕生的成就和挫折都通过梦而有所反映。第二,梦之于巴金,有着特殊的意义。巴金既有真实的梦,也有许多隐喻的梦。他的梦常与命运联系在一起。巴金在《病中集》中写道:“我甚至把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1]这段话道出了“文革”后遗症对巴金精神的戕害。这些各种各样梦的存在正说明了巴金关于历史、关于人性的深度思考。不管是幸福的梦还是痛苦的梦,都是巴金思索人生、追求光明的注脚。无疑,巴金是个永远追梦的人,是个理想主义者。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正是抓住了巴金做梦、写梦、追梦的特点,用“巴金的梦”来结构全书,勾勒巴金的一生。全传七编二十二章的所有标题都含有“梦”这个词。梦是人类最普通最普遍的精神现象。西方弗洛伊德开启了研究梦的先河,认为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梦是梦者愿望的表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梦其实是一种心灵诉求,是一种现实追求的曲折表达。《巴金全传》各编、各章的命名突出了巴金一生的经历和追求,作者以“梦”来结构全传是对传主的一种原创性解读。
优秀的传记作家能够透析传主,对传主的人性和人格做出符合事实的、富有原创性的揭示。陈丹晨以其对巴金长达四十余年的跟踪研究,以其对巴金的近距离接触和沟通,得以在他的《巴金全传》中对传主的人性和人格做出了深刻独到的揭示,而且找到了表现传主生命原初性的技巧,即用“梦”这一核心理念来解释巴金的精神特质。
陈丹晨在《巴金全传》中对巴金的准确把握就在于他找到了阐释巴金的恰当的切入点:“梦”。梦不仅仅指一种生活中的梦境,更多的时候它是隐喻,代表一种理想和追求。不管是快乐的梦还是痛苦的梦,不管是英雄的梦还是世俗的梦,都是巴金精神活动的反映。抓住巴金的“梦”,就是抓住了巴金的精神世界。而厘清巴金的精神世界,正是陈丹晨《巴金全传》的追求。陈丹晨在《巴金全传·自序》中写道:“梦,是属于世界上神秘而难解的一种现象。人人都会有梦,没有一个梦会是一个样。有梦的人,是幸福的;没有梦的人,是悲哀的。”[2]2可见,陈丹晨对于“梦”的作用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不仅在每编、每章的标题上都用“梦”这一核心词语,而且在《自序》中详细解释了以“梦”来结构全篇的原因。他列举了大量的实证来说明巴金爱做梦、爱写梦,连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也爱做梦。
巴金多梦。他说,他从四岁起就做梦,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他说这话是在一九八零年,那时他正七十六岁。他还说他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寐……巴金著作等身,成了世界著名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以梦为题的就有将近二十篇之多……巴金在他的作品中谈到他的梦,描写他的梦,多得几乎俯拾皆是……巴金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好做梦。十多岁时,他最早写的诗歌中就有一篇题为《梦》的小诗,描绘贫困不幸的人们昏睡不醒。[2]2
巴金不仅有题为《梦》的诗歌,而且他的小说《灭亡》中的杜大心、《家》中的觉慧和鸣凤、《火》中的冯文淑和《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有过很多梦。由巴金的这种与梦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出,陈丹晨用“梦”来概括和描述巴金,的确是找到了解读巴金的钥匙。陈丹晨认为仅仅评判巴金一生的成败得失是徒劳无益的。他意在通过对巴金一生“梦”的解析,来探寻巴金心灵的秘密,从而反思那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历程。他通过写梦、解梦的方式,成功地达到这样的写作目的:“从事巴金生平的研究,把巴金在这段历史中坎坷不平的经历,面对史所未有的严峻曲折的现实所发生的心态变化、灵魂浮沉、人格发展以至感情个性的扬抑……真实地描绘出来,希望借此略窥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侧影,进而感受一点近代中国的历史气氛,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2]6可以说,传记采用了恰当的、适合解读巴金的方式。
当代学者秦晋运用荣格的心理学说揭示了梦对于巴金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充分肯定了陈丹晨的“巴金传”对巴金的准确把握。他说:“究竟是现实的思想更有力,还是非现实的梦更强大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相当深奥的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陈丹晨描写的巴金人生,就触及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梦作为一种人的企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这种精神因素却有着巨大的能量,是它造就了意识,并为世界的存在创造了前提……这部传记的特点正是紧紧地抓住了人物的内在现实,在心理现实与社会现实、理智世界与情感世界的相互撞击、缠绕、矛盾中,展示人的生命的艰难和意义。”[3]秦晋科学地揭示了陈丹晨《巴金全传》的独特价值。
为什么说《巴金全传》用“梦”来结构全篇就是准确抓住了巴金的特点?因为巴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单纯和执着,而他的单纯和执着都是建立在理想之梦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在晚年,巴金顶着压力坚持写完了《随想录》,这更是他执着的重要体现。正如巴金自己在《“寻找理想”》中所说:“五十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认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4]这亮光实际上就是巴金心中的理想,心中的“梦”。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具有追“梦”情结。
(二)折射了陈丹晨的执着
传记对巴金追“梦”情结的描述,折射了陈丹晨的执着。陈丹晨像巴金一样是一个执着的追“梦”人。陈丹晨能够从“梦”的角度切入对巴金的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陈丹晨本人也像巴金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那种做事一丝不苟、执着奋斗的精神颇似巴金。仅看他写作“巴金传”的历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谢冕在《追梦的巴金》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陈丹晨写作“巴金传”的艰难历程,并对陈丹晨的坦诚和勇气给予了高度肯定:
要是我的记忆没有错误,这一本《天堂·炼狱·人间》已是陈丹晨关于巴金先生生平历史研究的第三部著作了。他的《巴金评传》写于二十年前。这本书对巴金前半生的事迹写得颇为详尽,但对进入新中国以后的经历未曾详加论述,只用了两个章节(仅占全书七分之一的文字)的篇幅作了交代。作者想弥补这个缺憾,于六年前重写《巴金的梦》,“希望它成为一本比较完备而有一定深度的巴金传记”。 但据作者自述,他想补正先前缺憾的目标,在第二本著作中依然没有实现……久远的追求只是在这第三次的写作中才得到实现。所以,他把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加上了“《巴金的梦——续篇》”的副题。作为读者,我祝贺陈丹晨最后的成功,同时又对这种写作的难以预料的艰辛,不免心生感慨。[5]
梦境往往是美好的,追梦之人常常要经历苦难、承受炼狱之灾而后方能到达理想之境。正如谢冕所讲,陈丹晨的巴金研究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所经历的踌躇和犹疑甚至是心灵的搏斗可以从他不同版本的“巴金传”中寻找到痕迹。从第一部《巴金评传》的侧重史料梳理、回避对巴金后半生的书写到最后一部《巴金全传》的侧重心灵剖析、直面巴金的局限和不足,这就说明了陈丹晨写作“巴金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追梦的过程,一个自我升华和完善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追梦的过程中,陈丹晨在精神气质上愈来愈接近他的研究对象,也愈来愈了解和同情他的研究对象。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道:“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6]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传记作者与他所选择的传主之间心灵相通的关系。我们喜欢某人,往往是因为此人在性格、气质、待人处事等方面与自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林语堂喜欢苏东坡,理解和认同苏东坡是因为他在精神气质上如幽默、智慧等方面与苏东坡有相通之处。正是这种相通使他把苏东坡写活了,他的《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中国四大名人传记之一。陈丹晨与他的传主巴金在精神气质上也是相通的,因而对巴金的理解和描述也是透彻的。这也是《巴金全传》能够运用“梦”来结构整部传记的秘密所在。
二、正直的人格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不仅对巴金本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而且对其他相关历史人物的臧否态度也十分鲜明,这充分显示了陈丹晨刚直不阿、不吐不茹的正直人格。
(一)直面巴金的局限
《巴金全传》直面巴金的局限,显示了传记作者正直的人格。该传对巴金在特殊的政治运动中明哲保身的行为进行了批判。陈丹晨与巴金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颇多相似之处。这里有陈丹晨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有受研究对象——巴金影响的因素。阅读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可以感受到他的率真与朴素颇似巴金,他的愤世嫉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也颇似巴金。他的内心与研究对象是契合的。正是这种契合,使得他准确地把握了巴金的精神世界。他不仅抓住了“梦”这个核心意象来描写巴金,而且对于巴金的缺失也毫不回避。这些缺失如巴金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迫参与批判他人等。对于巴金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胡风的这一行为,陈丹晨评价道:“这是巴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的坠失和对自己信念的反叛。有了这样的开始,就有了后来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例如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柯灵的批判。”[2]336这样的批评对巴金来说可谓锥心之痛,是对于巴金灵魂的拷问。对于巴金在《人民文学》发表批判路翎的文章的行为,陈丹晨的评价是:“巴金在写作这些批评路翎的和胡风的文章时,似乎没有想到早年他的小说中常常写到革命者处于革命与爱情发生冲突的复杂心情中。他曾经那么欣赏过《夜未央》中华西里与安娜牺牲爱情,和为革命献身的殉道精神。他也在自己创作的《灭亡》、《爱情三部曲》中写到过‘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这样的矛盾心情。和现在路翎的描写其实是很相似的。”[2]337这实际上是对巴金为了附和政治运动而写出观点前后矛盾的文章这种行为的相当严厉的质疑和追问。这样的追问是需要洞见和勇气的。
陈丹晨认为巴金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直没有写出很成功的作品,原因不仅仅是作家没有熟悉的生活可写,关键还在于作家迷失了自我,不再独立思考,只能在意识形态的严格限定下等因奉此。此外,陈丹晨还详细分析和描述了巴金摆脱“文革”沉重阴影的过程,不仅指出了1977年巴金的“政治结论”刚刚被撤销之时,巴金还无法一下子适应而在写文章时仍然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明确指出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和阅读但丁《神曲》对巴金晚年思想的重要影响。传记写道:“如果说,1976年至1977年间,巴金的思想精力比较集中在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和控诉,比较关注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还我清白的本来面目;同时,却还肯定了‘文革’时对他的批判是有教育意义的,甚至继续赞颂了‘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但同时也对30年来许多社会现象大惑不解,很自然地引起他深沉的思索。他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产生的共鸣和联想,他在阅读但丁的《神曲》过程中获得的启示,他从‘奴在心者’渐渐地变为‘奴在身者’ ……都说明他的思想正处在矛盾中,并开始发生变化和省悟。”[2]616陈丹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考察和解释巴金晚年的思想,这些看法富于真知灼见,符合巴金的思想实际,这是一种主观拥抱客观的认识。
一方面,陈丹晨对巴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迷失没有回避,而是如实记录。这些史实如巴金在“反右”斗争中写了应景文章《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等;在上海第二届人大会议上,参与批判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以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联”;在1966年的一次学习会议上,他检查了自己在上海文代会上发言的“错误”,表示自己写的全是毒草,愿意烧掉自己的全部作品。传记对这些史实的客观记述实质上是对巴金思想精神异化的严峻思考。
另一方面,陈丹晨对巴金的上述行为给予了理解、同情、惋惜和叹息。他认为促使巴金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巴金当时的身份和头衔,使他无法逃避政治性的批判会议;另一个原因是他怕牵连到妻子女儿。所以他时时担心会有灭顶之灾,他想通过积极表态而保全自己。对此,陈丹晨感叹道:“这位从年轻时就坚持不懈地反对一切权威、迷信的战士,这时已被改造成了求神拜佛的虔诚信徒。过去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作为人生格言、不安于现状、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已被残酷的政治斗争改造成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奴隶’。就像《家》中有叛逆精神的觉慧被改造成了逆来顺受、到处打躬作揖的觉新。这是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2]504这些总结和叹息说明了陈丹晨对巴金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反右”斗争和“文革”所持的坚定的批判态度,显示了陈丹晨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直个性。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似乎能够感受到陈丹晨写下这些内容时的沉重心情:“不算前期多年积累收集材料的时间,仅后半部伏案专事写作就花了整整两年半,可说是我个人写作历史中最长最苦的了……借用‘忧世伤生’这句话来形容我斯时斯地的心境实在是十分恰切的,也可说是我人生经历中少有的困顿和抑郁,以至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2]797-798可见,陈丹晨几乎是在用生命写作“巴金传”。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在对巴金心灵的开掘上深刻独特。该传更多地注意到巴金思想的发展历程,详细记述了巴金早期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例如与高德曼的通信;还深入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对巴金一生的影响;同时还披露了巴金在“反右”期间和“文革”中灵魂深处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思想等。
(二)公正评价历史人物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用笔大胆犀利、疾恶如仇。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从不遮遮掩掩,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直抒胸臆。比如传记中对邵荃麟的评价:“邵荃麟是位资深的老党员、理论家,为人善良厚道。”[2]413对姚文元的评价则是:“姚文元是从批判胡风发家的(至少写了13篇以上的批判胡风文章),是一个由政治运动造就的文化打手,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大批判,上面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他最善于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是熟练运用极端思想教条打人的一个极端分子……因此,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正是姚文元这样极端分子深谙其中奥秘而大显身手之时,仅1957年下半年之后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写了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文章多达七八十篇,上海的徐中玉、王若望、施蛰存,北京的丁玲、冯雪峰、艾青、陈涌、秦兆阳、徐懋庸,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探求者’,以及《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都在他的横扫之列。”[2]410-411陈丹晨的爱憎分明由此可见一斑。这样敢于直言的传记对传主精神世界的分析必然是深刻独到的。
总之,陈丹晨《巴金全传》对巴金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客观记述和评价,体现了作者正直的人格。
三、心灵的对话
透过《巴金全传》,可以感受到陈丹晨与巴金心灵的共鸣,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那份真挚的感情令人惊叹。陈丹晨早在1963年2月的4、6、8日,连续三次采访巴金,写成《巴金访问记》,发表在《中国文学》上。因此,后来在“文革”期间,上海作协批判巴金的一张大字报称:“×××专程到上海采访巴金,鼓吹巴金,流毒世界。”又是他,在“文革”期间,趁1973年夏季出差上海的机会去看望巴金,把巴金还健在的消息最早带给了唐弢先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陈丹晨为他的采访对象而深深震撼和心痛:“他真像一个忍辱负重的圣徒,正在以一种极大的坚毅的力量承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他的夫人悲惨去世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打击……他仍是那样委顿、闷声闷气……他说的话,他的神态,好像仍然是在批斗会上似的,使我深深地感到伤痛、心酸。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多年空前的野蛮残酷的折磨摧残下,连起码的尊严都给践踏了。这是什么世道啊!”[7]44-45由此可以看出,陈丹晨对他的传主巴金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同声相求、同气相合的理解、认同和接纳。
陈丹晨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巴金研究中,与巴金的长期交往使得自己也深受巴金思想的影响。因为巴金时常关注他的写作,对这位忘年交充分地信任和关怀,并引为同道。在1981年,陈丹晨因为发表《自由的文学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而受到批判时,巴金对他十分关心。巴金时常告诫他,要潜心研究,埋首写作,少参与是非纠纷和政治斗争,与文艺界的旋涡保持距离。在1984年10月16日—11月3日期间,陈丹晨作为中国作协派出人员,陪同巴金访问香港。这次被派是因为巴金亲自点名要他陪访的。在这次香港之行以后,陈丹晨与巴金在情感上更为深厚。巴金也多次送书给陈丹晨供他研究使用,这些书中有巴金自己的著作,也有工具书《辞海》。陈丹晨曾两次为巴金代笔,一次是在1982年代巴金起草给中国作协的小说诗歌颁奖会的书面致辞;另一次是在1984年年底代巴金为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起草开幕词。这些都体现了两人之间思想的相通。陈丹晨与巴金的这种密切交往使得他的“巴金传”写作能够深入传主内心,把握传主的精神实质。
陈丹晨在不唯上、实事求是等方面与巴金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品质使得他的《巴金全传》对巴金“文革”后创作的《随想录》给予了重点评述:
这个时期,巴金写的《随想录》,在探讨“文革”历史经验的同时,较多地谈到长期以来遇到的一个文艺创作自由的问题,实际上与中国政治体制、人文传统密切相关……到了1979年初,在人们谈论“长官意志”时,他的思考就更深入,批判更尖锐,因而发人深思。[2]648-649
上述内容深刻揭示了巴金“文革”后的思想状况。巴金认为文艺界领导对于作家创作应多鼓励,少干涉,不应该有长官意志,而应该“无为而治”,给文艺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从陈丹晨的诸多评论文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其实也是陈丹晨的思想。当代传记批评学者全展认为:“作者应充分深入传主的心灵深处,只有作者与传主心性接近、身心交契的情况下,作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与传主之间是有较严格的挑选的。彼此必有某种身心交契之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传主,所以鲍斯威尔选了约翰生,钱理群选了周氏兄弟。”[8]陈丹晨选择巴金,就在于他与巴金的心灵相契合。
陈丹晨在《明我长相忆——走进巴金四十年》中写道:“一九八一年,似乎是个多事之秋,文艺界连续发生了许多事……我刚好到杭州、福州、上海、南京走了一圈,组稿、调查研究;发现作家们都满怀热情在努力写作。就如福州一位老散文作家何为所说的那样:‘大家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亟须认认真真做些事情,写些于人民有益的东西。’他的话非常朴实地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当我回到北京时,读到一份宣传部门高官的讲话,称:文艺界有些人冲击党中央,冲击党的三中全会云云。(大意)我对这些吓人的罪状非常反感,就连续写了两篇题为《为了文艺事业……》的报道刊登在文艺报上,来回答这种缺乏与人为善的不实之词。”[7]77由此可以看出陈丹晨耿直的个性,他敢于抵制错误,直言不讳。
陈丹晨的率真、正直还表现在他对1989年11月在上海青浦县举行的第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对1991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国际研讨会的评价上。他对青浦会议的评价是:“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好的研讨会。会议开得很朴实,没有什么铺张虚夸的东西,讨论的气氛也比较活跃……第二天开幕式,安排得很朴素,一点没有平日开会那套繁文缛节的程式,没有设什么主席台,也没有什么党政首长来充当主角。上海文学界的名人们倒差不多都来了,他们也已好久没有这样聚会了。大家随意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旁,轮着谁,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7]171-172这种评价体现了他的平民意识,崇尚简朴,不计形式,提倡民主自由。关于1991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国际研讨会,陈丹晨的评价是这样的:“这次会议,省里很重视,开幕式有党政首长莅会;会议期间,首长还接见了副高职称以上的代表。我想,总共三五十位代表,且是研讨学术,还要分出等级见首长,何其‘隆重’高规格但又无聊的‘礼遇’!”[7]176这里,陈丹晨明确表示了对等级划分、官僚作风的否定和批判。他耿直狷介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陈丹晨耿直狷介的性格的确与巴金有些相似。“文革”刚结束时,巴金就开始发表随想录,反思“文革”。对此,有些人劝巴金要少写这一类东西。巴金并没有止笔,而是继续写作,直到写完150篇。由此可见,巴金的写作不纯粹是为文学,更多的是为一种理想,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他的《随想录》是哲人的思索,是对历史的正视,是民族自信的表现。他晚年的作品,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因而具有一种崇高美。王蒙这样评价巴金写作的崇高性:“他甚至于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不懂得怎么样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他是为祖国,为人民,为青春,为幸福,为光明和真理而文学而艺术的。”[9]王蒙道出了巴金讲真话的根本动力,那就是深沉的爱国为民的情怀和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陈丹晨对巴金这种坚持讲真话的精神是极为赞赏的。陈丹晨对巴金的这种理解和认同使得他在写“巴金传”时,更容易把握巴金追求自由的精神实质。这样,他所塑造的巴金形象更加丰富,更趋于真实。
四、小结
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充分展示了巴金孜孜不倦探求真理的过程,揭示了巴金纯真、执着、正直、善良的品格,是理解和认识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著作。同时,陈丹晨在对巴金的书写中无意识地透露了自己执着、耿直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真正走入传主的心灵深处,写出了真实的巴金。这部传记就是他与巴金之间心灵对话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