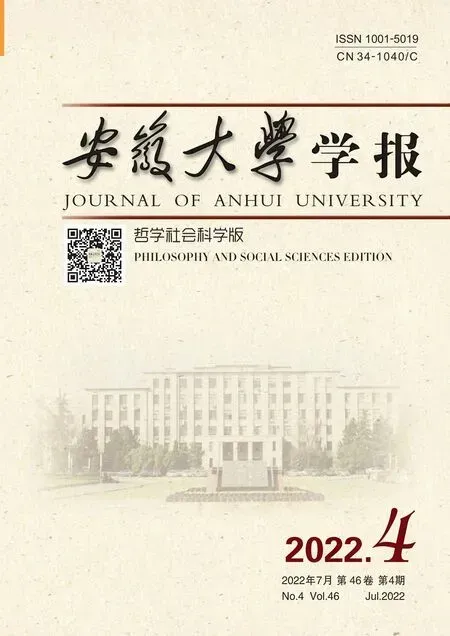再论谐音的修辞学地位
2022-11-23张丽红王卫兵
张丽红,王卫兵
在汉语世界中,从口彩到避讳,从搞笑到算命,从起名到译词,从广告设计到网络聊天,从舞台曲艺创作到日常妙语生成,都可看到谐音的使用。几乎可谓有汉语的地方就有谐音。谐音属于修辞现象,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不过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并未将其作为辞格看待。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学者提出应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对此,学界反响不一,有人强烈反对也有人积极支持。一方面因为谐音的修辞学地位问题无可回避,另一方面因为正确认识其地位问题,对于妥善处置类似修辞现象具有导向意义,本文拟就此开展讨论。
一、关于谐音地位的旧看法和新见解
这里所说的谐音地位问题即是否应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众所周知,汉语辞格的语言学研究滥觞于唐钺1923年出版的《修辞格》,该书认为汉语有27种辞格,即“显比”“隐比”“寓言”“相形”等,“谐音”不在其中(1)唐钺:《修辞格》,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汉语辞格的全面科学研究肇始于陈望道1932年推出的《修辞学发凡》。该书认为汉语有38种辞格,即“譬喻”“借代”“映衬”“摹状”等,“谐音”亦不在其中(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
唐钺未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并非因为轻视语音修辞。《修辞格》出版次年,他在《音韵之隐微的文学功能》一文中专门考察了汉语的语音修辞,并将其归纳为“显态绘声”(即“摹声”)、“隐态绘声”(即所谓“音义同构”)(3)辜正坤:《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兼论汉诗音象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双声”“叠韵”“倒双声”(即韵尾辅音相同)、“半双声”(即声母不同但发音部位相同)、“应响”(即韵母不同但韵腹或韵头相同)、“同调”(即或者毗邻两字调类相同,或者韵文句末字调类相同,或者音步收尾字调类相同,或者距离相近字调类相同)、“和音”(即错综变化地调配语音组合形式)等多种类型(4)唐钺:《国故新探》,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32页。。由此可知,唐钺非常重视语音修辞。他之所以未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是因为在他看来,包括谐音在内的语音修辞,不具备成为辞格的必要条件。
陈望道未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并非因为没有看到谐音在汉语中的广泛运用。《修辞学发凡》多处提及谐音。例如论述“双关”辞格时,所列举的“道是无晴还有晴”便语涉谐音;论述“析字”辞格时,所列举的“柏人者迫于人也”亦语涉谐音(5)“柏人者迫于人也”,其实应当视为“析词”辞格。参见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论述“藏词”辞格时,所列举的“猪头三”也语涉谐音;另外,论述“对偶”辞格时,所列举的“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同样语涉谐音。陈望道之所以未将谐音作为辞格处理,是因为在他看来,谐音虽然有着较宽的涉及面,但充其量只是构成双关、析字、藏词、对偶等辞格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可以自立门户的辞格。
由于唐钺和陈望道这两位辞格研究先驱的影响,汉语修辞学界重视语音修辞但并不认为谐音属于辞格的状况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有了变化。1985年,濮侃在与同事合作编著的《现代汉语》中提出,辞格的分类可以以不同语言材料为基础。据此他将辞格划分为“有关音韵的”“有关汉字的”“有关词语的”“有关句法的”以及“综合的(兼用两种以上材料的)”五大类;同时他认为在第一大类内部,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双声叠韵”“迭音”“谐音”“押韵”“拟声”五小类。在以上分类中,濮先生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6)周靖、濮侃:《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10~311页。。1993年,刘焕辉在《修辞学纲要》中,以言语形式特殊组合为纲,以语义、语音(文字)、话语为目,建构了一个涵括63种辞格的辞格系统。该著将语音和汉字特殊组合构成的辞格分为七类,即“飞白”“谐音”“拟音”“摹状”“析字”“拟字”“镶嵌”。在以上分类中,刘先生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不过两位先生的做法并非完全一致。区别在于,濮先生只是将谐音定位为辞格,既没有阐述理由也没有展示用例;而刘先生则不然,他除了肯定谐音属于辞格,同时还就理由所在以及谐音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表现等,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说明(7)刘焕辉:《修辞学纲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38~340页。。
二、对于谐音地位新见解的学界反应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是汉语修辞学界理论思维较为活跃的时期。面对有关谐音地位的新见解,谭永祥先生旋即作出回应,但不是支持而是反对。他在1992年推出的《汉语修辞美学》中评论道:“谐音是构成多种辞格的手段之一,这已是常识;新出版的一部30多万字的修辞学专著,居然把‘谐音’立为一‘格’!可见,辞格的文章并未做完,单是‘清理整顿’,匡谬纠误的工作就很繁重。”(8)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自序》,《汉语修辞美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所谓“新出版的一部30多万字的修辞学专著”乃是针对《修辞学纲要》而言(9)谭先生曾应华东修辞学会委托,承担过《纲要》审稿工作,故而早已了解其内容;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著作会在《纲要》之前出版,以致有关两著问世先后的说明,与实际情况不符。。高度关注修辞理论建设并积极参与有关讨论的黎运汉,亦不赞成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2006年,在与同事共同主编的《汉语修辞学》中,他直言不讳地说,辞格产生于语言单位的变异使用,任何变异使用的语言单位都离不开语音这一物质载体。“如果把‘语音变异格’列为一大类,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因为语音语义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难以截然分开,比如‘谐音双关’‘谐音飞白’‘谐音曲解’等都存在语音变异的一面,是不是也有理由把他们归入‘语音变异’这一类里?如果这样,就会出现辞格分类的交叉现象,有一小部分辞格既可归入语音变异格内,也可归入语义变异格内”(10)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黎先生认为,以语音变异为根据设定辞格,必然会带来与其他辞格界限不清的麻烦,故其明确表示,不赞成将语音变异作为建立辞格的基础。在已经得知濮著和刘著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的情况下,他所建立的一个包含74种辞格的辞格系统并不包括“谐音”。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支持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1996年,王希杰在与他人共同署名的《谐音:从修辞到文化》一文中说:“谐音,是概括为一个大类,成为一个独立的辞格;还是让它们分散在各有关辞格之中,作为构成这些辞格的一种手段呢?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不过,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谐音’格。我们之所以这样考虑,首先,是因为谐音具有作为独立的辞格的资格。……其次,还因为集中了所有谐音修辞现象的谐音辞格,有利于汉语辞格系统的整齐化和简单化。”(11)李晋荃、王希杰:《谐音:从修辞到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999年,李华在题为《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的文章中亦表示:“谐音有特定的表达需要、方法、结构和作用,完全可以成为一种修辞格。”在该文中,她除了表示支持将谐音作为辞格处理,同时通过对谐音结构方式的分析,亦即指出谐音是建立在“本体”“谐体”以及“相关体”有规律组合基础上,并就此作了论证(12)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当代修辞学》1999年第4期。。2000年,王希杰在《修辞学导论》中表示认可李华的论证,同时再次声言,“谐音”与“摹音”“叠音”“切音”“讹音”“协音”“拗音”一样,同属语音变异格成员(13)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8~490页。。
2003年,王希杰在另一部著作《汉语修辞论》中,又一次论及语音修辞格,尽管这次只提到四种类型,但并没有改变应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的观点(14)王希杰:《汉语修辞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358~361页。。继此之后,李晗蕾(15)李晗蕾:《辞格学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李胜梅(16)李胜梅:《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308~309页。、周武萍和陈宗明(17)周武萍、陈宗明:《汉语修辞式推论》,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邢福义(18)邢福义:《邢福义文集》第11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61页。以及李颖(19)李颖:《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辞格系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州:暨南大学,2014年,第20页。等学者均明确表示,应将谐音作为辞格处理。与此同时,谭学纯、濮侃、沈孟璎则首开先例,将谐音正式写入他们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20)谭学纯、濮侃、沈孟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三、对于谐音地位新旧观点的考察和评述
面对谐音地位问题的不同取向,身为修辞研究者无可回避,而决定如何选择自然是看哪种观点更为合理。认识分歧乃由新观点的登场而产生。新观点的提出者和支持者为何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下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提出和支持新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濮侃、刘焕辉、王希杰、李华、李晗蕾、李胜梅、周武萍和陈宗明以及邢福义等。鉴于刘焕辉、王希杰以及李华的有关论述最具代表性,下面的讨论以这三位学者的观点为基础。
建立任何辞格都需要做好内涵界定和外延说明工作,即一方面通过下定义,揭示其特征所在;另一方面通过举例,说明其具体表现。
在《修辞学纲要》中,刘焕辉为谐音所下定义为:“谐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或汉字来取得言语表达含蓄、幽默、风趣或讽刺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刘先生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乃是认为谐音来自语音特殊组合,而单凭语音特殊组合是无以产生“含蓄、幽默、风趣或讽刺效果”的,不言而喻,前述定义存在结论溢出前提的缺憾。不难想见,刘先生下定义所依据的用例,并非仅仅建立在语音特殊组合基础上。事实正是如此,给出前述定义后,刘先生亮出如下四个例证:一是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二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三是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一切似乎都是外甥打灯笼——照舅”。四是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中的“江桥腐朽已动摇”(21)刘焕辉:《修辞学纲要》,第339页。。以上四例,在其他学者著述中均被作为谐音双关看待。诚如李华所言,刘先生是“把谐音双关的修辞现象概括为谐音格”(22)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当代修辞学》1999年第4期。。
在《修辞学导论》中,王希杰为谐音确立的定义是:“谐音格,就是为达到某种交际效果,对于相同相似相近语音的利用,暂时地有条件地把两个不同的符号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23)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488页。该定义不存在结论溢出前提的问题;不过王先生的举例明显存在与其他辞格外延纠缠的不足。例如他所列举的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云)你想张……/ (旦云)张什么?/ (红云)我张着姐姐哩”,便与“承转”辞格相纠缠;他所列举的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及《子夜四时歌》中的“乘风采芙蓉,夜夜得莲子”,便与双关辞格相纠缠;他所列举的见于《光明日报》(1997年2月12日)的所谓“码家军”以及见于侯宝林《给你道喜》的“乙:我不会跳舞。/甲:你会跳六”,便与仿拟辞格相纠缠(24)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488~490页。。
在《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一文中,李华给谐音确立的定义为:“谐音是表达者利用词语语音相谐,从某个词语引起暗示和联想,由本体向谐体、相关体及隐蔽谐音的词语转化,也就是将能指的意义转换出新的所指的意义,达到符合语境要求的言语表达目的的修辞方式。”(25)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当代修辞学》1999年第4期。该定义视角新颖,对于谐音研究颇具启发性;但它认为与谐音有关的语言单位之间存在“本体”“谐体”“相关体”之别,而不少谐音用例,如谭永祥曾经提到的影院场标“敬、静、净”(26)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第495页。,胡习之曾经提到的演员自戒“汤、糖、躺、烫,容易长胖”(27)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不仅无法确定其中何为“相关体”,同时也无法确定其中何为“本体”何为“谐体”。另外,李华列举的谐音用例明显存在与其他辞格外延交叠的硬伤。例如,她所列举的“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在陈望道看来乃属“析字”辞格的下位类型,即“谐音析字”(28)陈望道:《修辞随录(二)析字格》,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4页。前述“谐音析字”实为“谐音析词”。;她所列举的“你是萍……你凭什么打我的儿子”,在浙江省修辞研究会看来乃属“承转”辞格的下位类型,即“谐音承转”(29)浙江省修辞研究会:《修辞方式例解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9页。;她所列举的“既然老子没谈兵法,孙子还谈什么兵法”,在邢福义看来乃属“飞白”辞格的下位类型,即“谐音飞白”(30)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专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总之,认为应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者,尽管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但在谐音的内涵界定和外延说明上,或者存在结论溢出前提的问题,或者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或者存在与其他辞格划界不清的问题。
反对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的主要理由有两点:其一,谐音只是构成双关、承转、飞白等辞格的辅助手段,自身并不具备独立且自足的修辞形式和修辞功能;其二,谐音隶属积极修辞(positive rhetoric)范畴,积极修辞包括辞格和辞趣(rhetoric taste),谐音隶属后者而非前者。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不赞成将谐音作为辞格处理,主要理由就是这两点。不过第一点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前面提到的“敬、静、净”和“汤、糖、躺、烫”,其中的谐音就并非为构成其他辞格而存在;又如赵元任利用同音字和近音字创作的《饥鸡集机记》:“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其中的谐音亦并非为服务其他辞格构成而使用。据此可知,认为谐音只是构成其他辞格辅助手段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另外第二点也并非坚不可摧。目前学界的普遍见解为:辞格和辞趣都是通过变异语言或言语常态而产生的在形式和功能上具有自身特点的修辞方式;二者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属于可以对其结构规律和语用规律加以总结的传统修辞方式,后者属于难以对其结构规律和语用规律加以总结的新兴修辞方式(31)韩礼德认为,对于“变异”应持广义理解,亦即须将“质偏离”和“量偏离”一并包括在内。笔者认同该观点,本文“变异”概念的使用均立足于此。参见张德禄《功能文体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而积极修辞则包含了辞格与辞趣。毋庸讳言,在是否需要区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以及是否需要区分辞格与辞趣上,学界不无争议。但根据胡习之和霍四通等学者的研究,进行前述区分很有必要,至少说利大于弊(32)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第93页;胡习之:《核心修辞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霍四通:《辞趣与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重读〈修辞学发凡〉第九篇》,《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6期。。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辞格与辞趣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源于语言或言语的变异使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多与传统修辞方式相联系,后者多与新兴修辞方式相联系;前者具备对其结构规律和语用规律加以总结的条件,而后者则不然(33)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第477~534页;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第103页;胡习之:《核心修辞学》,第373~389页;霍四通:《辞趣与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6期。。我们以为,如果说在修辞研究尚显稚嫩的过去,认为谐音只宜作为辞趣处理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修辞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的今天,继续固守过去观点则不免令人难以理喻;毕竟这里论及的谐音并不属于 “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但又不具有明显的模式性或规律性”(34)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第105页。的新兴修辞方式。
综上所述,认为应将谐音作为辞格处理者,尽管未能对此加以成功论证,但所认定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认为应将谐音作为辞趣看待者,尽管观点由来有自,可以理解,但时至今日继续坚持,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如今修辞学界已经具备揭示谐音奥秘的充分条件。
四、与谐音地位有关的两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谐音地位之所以久议不决,究其原委主要因为与此有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认真对待。
问题之一是,“语音变异能否成为辞格基础,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是否可取?”主张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者,主要理由为谐音来自语音变异,变异乃辞格生成基础;而不赞成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者,认为谐音属于声趣范畴(35)例如《汉语语法修辞词典》:“辞趣可分……‘意趣’‘声趣’‘形趣’。”“声趣,可以通过‘叠音’‘摹声’‘谐音’‘双声’‘叠韵’‘声调(平仄) ’‘押韵’‘儿化韵’‘长短音’和‘物象音’(如‘猫’同猫叫的声音相仿,‘瀑’同‘瀑布’的声音相近)、‘音势’等来实现。”参见张涤华等主编《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9页和342页。,反对将语音变异与辞格生成相联系。其实,以语音变异为根据设立辞格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国现代修辞学乃是通过借鉴西方和日本先期经验而建立,而早在我们接受舶来影响之前,西方修辞学家和日本修辞学家就已将辞格研究延伸到语音层面。例如被唐钺《修辞格》列为主要参考书的英国修辞学家纳斯菲尔德(J.C.Nesfield)撰写的《纳氏高级作文法》(SeniorCourseofEnglishComposition,1910),以及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起到重要启发作用的日本修辞学家五十岚力编著的《新文章讲话》(1909),其中都设有语音修辞格(36)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05页;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第121页。。另外,近年来我国外语学界推出的英语修辞学著作,其中多数亦设有语音修辞格(37)徐鲁亚:《西方修辞学导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150页。。或许因为谐音在英语中表现不那么突出,或许因为五十岚力编著《新文章讲话》时过度仿效英语修辞研究范式,前述著作所设语音辞格均不包括谐音(38)日语中谐音修辞有着很高的使用率,按道理讲,谐音应当包括在《新文章讲话》所设语音辞格之中。。不过通过讨论可知,以语音变异为基础设定辞格并非不可;同时通过讨论可知,只要谐音确属变异产物,并具有常用性、稳定性、规律性,将其作为辞格看待则具备学理上的根据。
问题之二是,“作为辞格的谐音是否必须具备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区别性特征?”反对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者,均强调谐音不具备形式和功能上的区别性特征,而主张将谐音纳入辞格系统者,对于谐音是否具有形式和功能上的区别性特征从未给予正面回应。后者之所以如此,似乎因为在其看来,谐音特征主要表现在与其他辞格结合使用中。例如,李华就曾声言:“谐音的模式不仅仅由音律的协调或者语义的双关来体现,谐音的模式还由飞白、仿拟、拈连、镶嵌、用典、对偶、曲解、断取、歇后、巧缀、序换、讳饰体现。”(39)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当代修辞学》1999年第4期。另外周武萍和陈宗明亦曾表示:“在汉语的辞格学中有谐音双关和谐音歇后,似乎没有独立的‘谐音’格。从语音修辞的角度上说,谐音是应当独立成格的,只是在使用过程中通常表现为某种兼格。”(40)周武萍、陈宗明:《汉语修辞式推论》,第206页。
辞格有单用和合用之分,而合用又有“连用”“套用”“兼用”之别。单用是指在仅仅体现某种辞格区别性特征的情况下使用,合用是指在同时体现多种辞格区别性特征的情况下使用(41)辞格“合用”存在同类合用和异类合用之别,前述说法乃就后者而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揭示辞格的区别性特征,说明辞格的具体表现,只应以单用状态为基础。如果声称存在某种辞格,却举不出体现其单用状态的例子,就很难称之为辞格。
对于如何确定谐音的修辞学地位来说,以上两个问题不仅具有前提性同时具有决定性,倘若学界能够就此统一认识,那么其他问题,包括如何认识谐音区别性特征,以及如何给谐音下定义,等等,也就有了顺利解决的可能和保障。
五、关于谐音的区别性特征以及学术定义之我见
从辞格角度,揭示谐音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区别性特征,进而给予科学定义,乃属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吕叔湘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从事理论研究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搞好前期调查,二是要摈弃先入之见(42)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2页。。
在汉语各种修辞现象中,谐音现象最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从结构方式看,其内部存在以下11组类型区别:
(1)本体—谐体对应型和谐体—谐体对应型;
(2)构素同显型、构素同隐型和构素显隐型;
(3)构素同系型与构素异系型;
(4)构素同音同字型与构素同音异字型;
(5)构素整—零对应型与构素零—整对应型;
(6)构素单向延伸型与构素双向延伸型;
(7)构素叠合型与构素相继型;
(8)一底一面型、一底两面型、一底多面型、数底数面型;
(9)有距相谐型与无距相谐型;
(10)语素相谐型、语词相谐型、语句相谐型、段落相谐型、篇章相谐型;
(11)独用型与兼用型。
从语用场合看,其内部存在以下5组类型区别:
(1)自觉创造型与误解导致型;
(2)顺势而为型与曲意构造型;
(3)文化规约型与场合引发型;
(4)实用型与游戏型;
(5)口头型与书面型(43)曹德和:《汉语谐音及其语篇衔接作用》,《北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曹德和:《汉语的衔接》,合肥:黄山书社,2022年。。
谐音现象如此复杂,倘若轻视调查、观察欠充分,有关理论研究则难免步入误区。
在论及谐音的著述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有违实际的表述,如:谐音是“指字或词不同而声音相同或相近”,“谐音的形成过程,就是由基础字转化为目的字”,等等。总结教训,有的是因为思想观念未能与时俱进,未能注意到网络时代修辞现象的新发展;有的是因为调查研究浮光掠影,见表不见里,见此不见彼。吕先生多年前就已告诫我们:“一个人做学问不可能没有一些看法,但是当你进行观察或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那些看法暂时忘掉。……总之,无论观察还是实验,都要把脑筋擦干净,让它像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44)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第11~12页。他还以没有钱串子而有钱与没有钱而有钱串子的比喻为例,告诫我们一定要在“攒钱”上多下功夫,坚决克服小本钱做大买卖不正之风。在从事谐音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谨记在心,并将其作为督促和指导自己行动的座右铭。
“天下的事情,比下定义更难的,恐怕不多”(45)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05页。;但对于治学来说,下定义不仅有助于前期观察思考的梳理和总结,同时有助于后期研究的拓展和提升,因而无论有多难都得上。“对外具有排他性,对内具有普适性”乃为下定义的方法论原则。从辞格角度给谐音下定义,首先需要做好提纯工作,亦即通过单用与合用的区分,将后者从资源对象中剔除出去,从而确保定义工作只是植根于单用考察的基础上。其次需要做好共性发掘工作,通过类似于“提取最大公约数”方法的采用,从前面提到的谐音复杂表现中,将“异中之同”给发掘出来。以具有排他性共同点为基础,似可这样定义谐音,即:“谐音是指以语音相同相近为条件,通过非固定位置上不同语言单位之间照应关系的建立,以满足表达需要的修辞方式。”以上定义之所以强调“非固定位置”,是为了避免与“押韵”等辞格相牵扯;之所以强调“满足表达需要”,是为了避免与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的谐音运用(利用谐音关系创造“谐声字”、利用谐音关系进行“声训”、利用谐音关系翻译外来词)相纠缠。此外,该定义有三个“不限制”:一是不对相谐单位加以语言层级上的限制;二是不对相谐单位的出现先后以及作用主次加以限制;三是不对谐音的修辞功能加以限制(46)实践证明,因为功能具有多样性且不易把握,从功能角度给谐音下定义弊多利少。参见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第254页。。有了这三个不限制,各种谐音现象皆可尽入彀中。
六、结 语
有学者认为将谐音作为辞格看待有利于辞格系统简单化,这想法似乎简单化了。确立谐音的辞格地位后,与其交叉的修辞用法,如谐音双关、谐音承转、谐音仿拟,皆可归于谐音门下;但论及双关、承转、仿拟等辞格时,借助谐音构成的前述辞格仍需再次提及。实践表明,赋予谐音以辞格地位,只会使辞格系统复杂化,但这是尊重事实且符合科学性要求的复杂化。实际上,给予谐音以辞格地位,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其一,有助于谐音研究的系统化。多年来的谐音研究较为零散,20世纪90年代,阮显忠对汉语谐音使用作了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查,结果发现与其存在合用关系的辞格多达13种(47)阮显忠:《汉语谐音与汉族文化》,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语法修辞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 314~324页。。其实,与谐音有着合用关系的辞格远不止这些。曹德和指出,与谐音结合为用的辞格有对偶、排比、反复、复辞、回文、回环、顶真、承转、比喻、借代、异称、用典、序换、断取、仿拟、镶嵌、离合、双关、用歧、别解、闪避、会意、避讳、假对、拈连、对比、衬托、飞白、存真、空设、层递、析数,等等,多达三十多种(48)曹德和:《汉语谐音及其语篇衔接作用》,《北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曹德和:《汉语的衔接》。。辞趣研究与辞格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只是给予对象以个案考察,而后者则是给予对象以综合审视。可见,赋予谐音以辞格地位,可以结束谐音研究的零散状态而将其引入系统化之路。其二,有助于谐音研究的科学化。对于谐音的修辞功能,以及谐音的结构规律,包括相谐单位处于语言或言语哪个层级,相谐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相谐单位以何种面貌呈现(“显”还是“隐”),等等,多年来我国学界可谓众说纷纭。之所以长期莫衷一是,根本原因在于论者始终是以辞趣研究范式研究谐音。辞趣研究与辞格研究的重要区别是,前者以整体把握基础上的印象评点为满足,后者则以条分缕析基础上的本质提炼为追求。将谐音作为辞格加以研究,有助于认识其共性或本质,有助于提升有关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其三,有助于推进其他学术研究。这里所说的其他学术研究,主要指大语法研究和汉文化研究。所谓大语法乃指语义、句法、语用、韵律共同作用下的语言组织法。从谐音与三十多种辞格存在合用关系可知,在汉语组织上,谐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赵金铭(49)赵金铭:《谐音与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阮显忠(50)阮显忠:《汉语谐音与汉族文化》,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语法修辞论》,第 314~324页。、王希杰(51)李晋荃、王希杰:《谐音:从修辞到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曹铁根(52)曹铁根:《谐音·修辞·汉文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潘文国(53)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0~241页。、孟昭泉(54)孟昭泉:《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学者,曾相继就汉语谐音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关系做过研究,他们一致认为,了解汉语谐音对了解汉语特点乃至汉民族文化特点至关重要。由此可知,从辞格角度加强谐音研究,不仅对于全面认识汉语大语法,同时对于深刻体悟汉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之举。综上所述,未来的汉语修辞研究应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