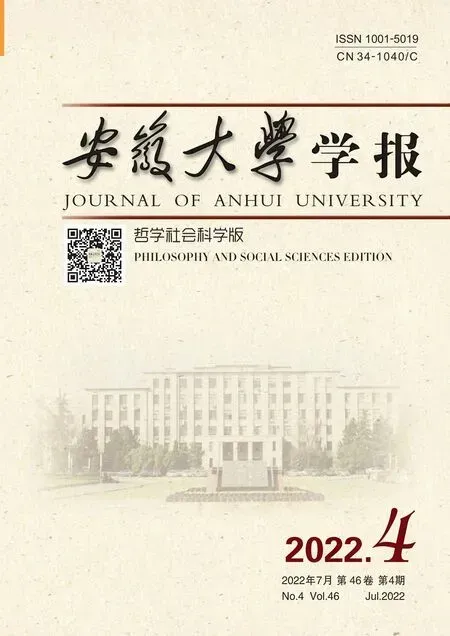“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
——兼与朱熹之比较
2022-11-23乐爱国
乐爱国
康有为《论语注》对宋儒多有批评,尤其是在论及管仲时说:“孔子极重事功,累称管仲,极词赞叹。……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苶尔,中国不振,皆由于此。”(1)(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0页。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对于宋儒(主要是指程朱理学)“轻鄙功利”的批评,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为不少学者所接受(2)李泽厚《论语今读》引述并赞同康有为的说法。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64页。。但是,康有为《论语注》较多引述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读,其注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融合了朱熹《论语集注》的注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3)(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6页。,实际上肯定了朱熹对于义利关系的解读。而且如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汉)班固:《汉书》(八)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4页。。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根据《易传》“利者义之和”,进一步提出“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所肯定,这与朱熹所言“不求利而自无不利”略有不同,有所发明,以至其批评宋儒“轻鄙功利”。康有为的义利观从融合朱熹的义利观出发,但又不同于朱熹,甚至批评宋儒,对朱熹义利观到康有为义利观之变化的考察,不仅表明不可简单地将康有为义利观与朱熹义利观对立起来,而且就此展开讨论,对于如何发展地理解儒家的义利观也不无裨益。
一、融合朱熹的解读
康有为早年从学于朱次琦,推崇朱熹之学,其所撰《教学通义》有“尊朱”一节,称朱熹“学识闳博,独能穷极其力,遍蹑山麓,虽未遽造其极,亦庶几登峰而见天地之全”,“盖孔子之后一人”(5)(清)康有为:《教学通义》,《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5页。。当然,康有为又说:“惟于孔子改制之学,未之深思,析义过微,而经世之业少,注解过多。……至于死时,尚恨礼之未成。幼学则未之思及。设使编成,后世本为师法,于今礼业之精,当不后古人也,此所以为朱子惜也。”(6)(清)康有为:《教学通义》,《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6页。康有为早年这种对朱熹的既尊崇又有某些遗憾,至后来则逐渐转变为对朱熹的较多批评,已有学者就此做了很好的分析(7)参见魏义霞《论康有为对朱熹的态度转变及其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康有为《论语注》既强调“《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又说“曾门之真书亦为刘歆之伪学所乱,而孔子之道益杂羼矣。……有宋朱子,后千载而发明之,其为意至精勤,其诵于学官至久远,盖千年以来,实为曾、朱二圣之范围焉。惜口说既去,无所凭藉,上蔽于守约之曾学,下蔽于杂伪之刘说,于大同神明仁命之微义,皆未有发焉”(8)(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77~378页。。显然,康有为对于朱熹解《论语》,既肯定其“后千载而发明之”,又认为“于大同神明仁命之微义,皆未有发焉”。
然而,康有为《论语注》对朱熹《论语集注》多有引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康有为全集》在《论语注》的按语中指出:“注文多引朱熹《论语集注》原文而未明所自,今均出注说明。”(9)(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76页。根据对所作注的统计,康有为《论语注》对朱熹《论语集注》的直接引述约165处,而实际上可能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尤其是,康有为《论语注》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注释,完全只是对朱熹《论语集注》所言的引述,并加上对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言的摘引。
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1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3页。在这里,朱熹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义”与“利”分别解说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肯定在义利关系上,义为根本;而“利者,人情之所欲”,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其并不是要否定利,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是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朱熹又通过引述程颐强调君子与小人在义利上所喻所好的不同,引述杨氏时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联系起来,以为“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实际上是将“利者,人情之所欲”等同为“生,亦我所欲也”,将义与利的关系解读为义与生的关系,说明义与利都是“我所欲也”,都是人所不可或缺,而不是相互对立,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在于他们所舍所取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指君子与小人在义利上的所舍所取、所喻所好的对立,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而不是讲义与利的相互对立(11)又比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朱熹注曰:“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即并不是讲“德”与“土”“刑”与“惠”的对立,而是讲“君子小人趣向不同”。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朱熹注曰:“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这也并非将道与食对立起来,而是讲“谋食”不同于“谋道”。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8页。。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较朱熹进了一步。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不同,刘宝楠更为强调“君子、小人以位言”,同时引述董仲舒所言“夫皇皇求利,惟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又引述焦循所言“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于利”(1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4~155页。。应当说,刘宝楠的解读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为卿大夫与庶人对于义利的不同选择,消解了朱熹的解读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更体现出其政治价值。
康有为《论语注》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董子曰: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13)(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6页。显然,康有为是以朱熹注为主,而其中所加入的“董子曰: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则很可能来自刘宝楠《论语正义》所引述的董仲舒所言(14)朱熹之后,除日本江户时代荻生徂徕《论语征》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讲“以位言”,稍后,焦循也作了同样的解读,但他们的解读都没有引述董仲舒所言“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焦循之后,刘逢禄《论语述何》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董仲舒所言“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财利,常恐匮乏者,庶人之事也”(案:与《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相比,此处有语序上的不同)论证焦循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其实,董仲舒所言只是讲“卿大夫之事”与“庶人之事”,并非讲“君子”“小人”。刘逢禄以此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论证焦循将“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为后来刘宝楠《论语正义》所接受。参见乐爱国《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兼与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之比较》,《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也就是说,康有为《论语注》吸纳了朱熹注对于义利关系的解读,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而加入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作为补充。
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撰《论语注》之后,与其同门的简朝亮于1918年撰成《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强调“《论语》之经,六经之精也”,而不同于康有为讲“《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而且简朝亮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推崇朱熹注,而不赞同刘宝楠注将此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说:“此《经》小人当自贪利者言矣,皇《疏》言货利,邢《疏》言财利,特其显然者尔。彼小人所喻之微,岂惟货财已邪?论家说云:‘君子小人,或同一事也,而其所喻者则义利不同,盖有小人伪君子焉,公义亦私利也。’”(15)(清)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应当说,无论是简朝亮,还是康有为,他们都赞同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康有为在吸纳朱熹注的同时,又有所不满足。正如康有为所言“《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是对《论语》之学、曾学之学的不满足,康有为对朱熹注的不满足,是在肯定“曾、朱二圣”基础上的不满足,不是否定,而是补充,是融合朱熹解读而试图作出进一步发展。
二、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
与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样,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对此,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并引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在这里,朱熹明确认为“君子未尝不欲利”。这与他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一致的。然而,朱熹又认为,君子欲利,但不能有“利心”,“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不能“以利为心”,“专以利为心则有害”,而且不能求利,“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朱熹还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1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8页。此处既讲“义未尝不利”,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又讲“不可先有个利心”。
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孟子微》认为,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不是要否定利,“《易》言‘乾,元亨利贞’,为四德,又曰‘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始以美利利天下’,‘利国前民’。《书》言‘黎民尚亦有利哉’,《大学》‘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何尝不言利?”而孟子所言是要“言仁义,而戒怀利心”。对此,康有为说:“盖一怀利心,则绝于圣人之途,而无从言者也,故以为第一义。……孟子所戒,是怀争夺心者,不和不均甚矣,是利心不可怀也。……若必怀利心,是乱世与平世之所由异,而太平终无可望之日矣。”(18)(清)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0页。又说:“怀义心者,虽日为利,而亦义。怀利心者,虽日为善,而亦恶。舜、跖之所分别,于其用心之始而已。”(19)(清)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1页。并且还说:“盖学者之大患在志于利禄,一有此心,即终身务外欲速,其志趣卑污,德心不广,举念皆温饱,萦情皆富贵,成就抑可知矣。”(20)(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40页。显然,在义利关系上,无论是朱熹还是康有为,他们都不否定利,而是反对“利心”。
朱熹反对“利心”,强调“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因而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2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8页。认为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不是否定功利,而是反对“专去计较利害”,也就是反对“利心”。
事实上,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同时又讲“兴利”“除害”,说:“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22)(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5页。可见,董仲舒讲“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并非轻视功利。
然而,不少人对董仲舒所言多有误读,以为他否定功利。据《朱子语类》载,浙中诸葛诚之说:“‘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2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八)卷13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63页。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24)(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4页。清初颜元说:“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25)(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1页。又说:“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26)(清)颜元:《四书正误》卷一,《颜元集》,第163页。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严复也说:“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27)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8页。这些都认为董仲舒所言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是排斥功利,而予以批评。
与此不同,康有为《论语注》赞同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对此,朱熹《论语集注》说:“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2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8页。他还说:“学固不为谋禄,然未必不得禄;如耕固不求馁,然未必得食。虽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见道不见禄。如‘先难后获’,‘正义不谋利’,睹当不到那里。”(2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卷45,第1166页。康有为《论语注》对朱熹注作了发挥,说:“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学也者,明其道正其谊,而非为谋利也。故忧道之不明,忧道之不行,而未尝以贫为忧。常人戚戚忧贫,故皇皇谋利,而未见利之可得;君子皇皇谋仁义,未尝谋利,而富贵乃为君子所有。”(30)(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508页。显然,这是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解读朱熹所谓“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而且,康有为所谓“皇皇谋利,而未见利之可得;君子皇皇谋仁义,未尝谋利,而富贵乃为君子所有”,不仅来自董仲舒,而且与以上朱熹所言“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也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说“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论语·颜渊》),朱熹《论语集注》注曰:“先事后得,犹言先难后获也。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专于治己而不责人,则己之恶无所匿矣。”并引述范氏曰:“先事后得,上义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故慝不修。”(3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0页。康有为《论语注》引朱熹《论语集注》范氏曰,并且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日日讼过忏罪,惩忿治怒,皆学者自修之要。”(32)(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78页。此肯定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学者修身之根本(33)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还赞同董仲舒所言“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并说“孔子言义理而不计利害”,并认为董仲舒崇义抑利之说“与《孟子》同,为孔门大义”。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90~392页。。应当说,康有为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其义利观与朱熹多有相似之处(34)关于康有为论朱熹与董仲舒学问的关系,可参见曾亦《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但是,康有为更为强调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对于义利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因此,他推崇董仲舒所言,不只是从义利关系上讲,更多的是针对上层官员而言,强调上层官员应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三、“取利而和,则谓之义”
《论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易传》讲“利者义之和” ,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利”,说:“利,铦也。刀和然后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35)(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页。魏何晏《论语集解》注“子罕言利”,曰:“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36)(魏)何晏、(宋)邢昺:《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07页。,此后的儒家学者多以“利者义之和”解儒家的义利观。朱熹《论语或问》在对《论语集注》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进一步说明时,说:“曰:对义言之,则利为不善,对害言之,则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为,固非欲其不利,何独以喻利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义固所以利也,《易》所谓‘利者义之和’者是也。然自利为之,则反致不夺不厌之害,自义为之,则蒙就义之利而远于利之害矣。”(37)(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4页。这里以“利者义之和”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说明“义固所以利”,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认为君子“自义为之”而有利,小人“自利为之”反致害。朱熹《论语或问》还以“利者义之和”解“子罕言利”:“或问: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义之和也,惟合于义,则利自至;若多言利,则人不知义,而反害于利矣。”(38)(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六),第768页。朱熹还说:“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若只理会利,却是从中间半截做下去,遗了上面一截义底。小人只理会后面半截,君子从头来。”(3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五)卷68,第1705页。认为“利者义之和”讲的是“惟合于义,则利自至”;君子讲义,“义便兼得利”,小人讲利而不讲义,则“反害于利”。
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强调“君子、小人以位言”的同时,又在解“子罕言利”时,以《易传》“利者义之和”予以解读,并且说:“利所以为义之和者,和犹言调适也。义以方外,若但言义不言利,则方外而不能和,故利为义之和。《周语》曰:‘言义必及利。’韦昭曰:‘能利人物,然后为义。’此即‘利物足以和义’之谊,此即‘利’字最初之谊。君子明于义利,当趋而趋,当避而避。其趋者,利也,即义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义也。”这是以为“利”的最初之意就是义,不利就是不义。然而在现实中,君子与小人对于义利有不同看法:小人所谓利,君子可能视为不利;而小人视为不利,君子可能视为义,视为利,也就是说,君子所视之利,不同于小人所视之利,“君子知利不外义,故喻于义;小人知利不知义,故喻于利”(40)(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20页。。刘宝楠既讲君子、小人都“知利”,又讲君子所知之利不同于小人所知之利,强调利与义的不可分离。
与此相同,康有为也以《易传》“利者义之和”解义利关系。他说:“《易》所谓利者,义之和也。《书》、《大学》所谓利者,仁以安仁,是即仁义也。仁为人利,即能我利,义得人和,即得人利。但如此,谓之仁义,不谓之利矣。得其和者,人己之界甚平,无侵无越之谓,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也,《春秋》所谓名分。子贡曰,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义之和也。如此,则利可也。”(41)(清)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0页。在这里,康有为把“利者义之和”解为“义得人和,即得人利”,而所谓“义之和”就是人人平等,没有相互争夺之心,这就是利。康有为《论语注》以“利者义之和”解“子罕言利”(42)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及朱熹《论语集注》中,《论语·子罕》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人。达巷党人曰……”。与此不同,康有为《论语注》则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巷党人曰……”,并且注曰:“罕,希也。上‘与’,即欤,助辞。达,通也。利者,义之和;命者,天之命。记者总括孔子生平言论,最少言者莫如利,最通达多言者莫如命与仁。盖命、利、仁三者,皆人受于天以生,无须臾而能离者也。”见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43页。,并且还说:“利者,人所同好,若再增长附益之,则教猱升木,相习成风,恐因自利而生贪夺,反以害人道矣。故于系《易》,言利为义和,美利天下,而它经寡言之,防流弊也。”(43)(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43页。在康有为看来,利是人之所同好,这与他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采纳朱熹所言“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一致的。但是,康有为又认为,“若再增长附益之”,讲多了,就可能“因自利而生贪夺”,所以孔子“罕言利”,只讲“利者义之和”。这样的解读,既讲“义得人和,即得人利”,又反对过多讲利,与朱熹所谓“利者,义之和也,惟合于义,则利自至;若多言利,则人不知义,而反害于利矣”,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重要的是,康有为《论语注》解“放于利而行,多怨”,发挥了《易传》“利者义之和”,提出了“取利而和,则谓之义”,说:“利者,从刀刈禾,假借为以力有所取益之谓。《易》曰:义者,利之和也(44)《易传·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里所谓“《易》曰:义者,利之和也”,应当为“《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人不能无取,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不谓之利;取利不和,则谓之利,不谓之义。盖人己之间有一定之界,取不侵人之界,则谓之和,和则无怨;取而侵人之界,则谓之利,利自多怨。盖己益则人损矣,损则必怨。故人人皆取于己之界,而不侵人之界,则天下平。”(45)(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5页。显然,康有为是通过许慎《说文解字》解“利”而讲《易传》“利者义之和”,提出“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他认为,人人都要取利,而取利有和与不和之别,“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不谓之利;取利不和,则谓之利,不谓之义”。这里根据“利者义之和”明确提出“取利而和,则谓之义”(46)稍早于康有为《论语注》,陈炽撰《续富国策》,说:“惟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圣人立身行义,舍生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且日亟亟焉谋所以利之者,圣人之仁也,即圣人之义也。……故天下之工于言利者,莫圣人若也。”这里讲“谋所以利之者”,即“圣人之义”。见陈炽《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页。,不仅超越了朱熹讲“惟合于义,则利自至”,而且比刘宝楠《论语正义》讲“君子知利不外义”又进了一步,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阐释。
如前所述,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但是又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47)(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第257页。董仲舒并没有否定利。同时期的刘安《淮南子》则引述楚臣申叔时曰:“君子不弃义以取利。”(48)(汉)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0页。此则明确讲“取利”。南北朝时期皇侃《论语义疏》解“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曰:“夫取利,若非义取,则为人所厌。我夫子见得思义,义而后取,故人不厌其取也。”(49)(梁)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1页。这里也讲“取利”。
宋代杨时曾说:“某窃谓当今政事,惟理财最为急务。考之先王,所谓理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50)(宋)杨时:《杨时集》(二)卷20《答胡康侯》(8),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46~547页。杨时认为对于财利,“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就是义。同时,他又反对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曾批评王安石所谓“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说:“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着隐伏之有?若夫宣着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51)(宋)杨时:《王氏神宗日录辩》,《杨时集》(一),第107页。这里从理财的层面讲“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
但是,由于朱熹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又讲“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以后世儒家大都不讲“谋利”“求利”“取利”,以为“取利非义”。杨时所谓“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虽为明胡广《性理大全书》所引述,但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广,没能上升到道德修养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后世的重视。
尽管如此,宋代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而且后来颜元批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并改之为“正其谊以谋其利”而强调“谋利”。应当说,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既是对朱熹以来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民间俗语所作的理论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在讲朱熹所谓“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基础上,既与朱熹一样,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又不同于朱熹,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但是并没有就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贯通做出更多的理论阐释,因而实际上也没有为后世儒家所关注。
四、批评宋儒“轻鄙功利”
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因而其重视外在的事功,不满意朱熹《论语集注》对于管仲的评价,批评宋儒“轻鄙功利”(52)康有为对宋儒多有批评。他说:“宋贤自朱子染于释氏无欲之说,专以克己,禁一切歌乐之事,其道太觳,近于墨氏,使民情不欢,民气不昌,非孔子道也。”见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62页。又说:“盖施仁大于守义,救人大于殉死。宋儒乃尚不知此义,动以死节责人,而不以施仁望天下。立义隘狭,反乎公理,悖乎圣义,而世俗习而不知其非,宜仁义之日微,而中国之不振。”见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93页。。
对于管仲,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5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4页。其认为管仲有“仁之功”,而“未得为仁人”。康有为《论语注》不赞同这样的解读,明确认为,孔子所言“如其仁!如其仁!”是对管仲之仁的“再三叹美”,并且还说:“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岂知孔子之道,内外本末并举,而无所偏遗哉!”(54)(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92页。还说:“管仲真有存中国之功,令文明世不陷于野蛮……功业高深,可为一世伟人也。孔子极重事功,累称管仲,极词赞叹。……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苶尔,中国不振,皆由于此。”(55)(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90页。显然,康有为明确认为宋儒“轻鄙功利”。
康有为批评宋儒“轻鄙功利”,是围绕着对管仲的评价而提出来的。朱熹《论语集注》注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说:“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5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对此,康有为是赞同的,说:“施伯谓鲁侯曰:管仲,大器也。孔子辩之器小,言其不知圣贤之道,天人之理,正身修德,以致王道。……而惜管仲局量褊浅、规模卑狭。”(57)(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0页。但是,康有为又说:“管仲治国之才,成霸之术,以今观之,自是周公后第一人才……故孔子称其仁。……此由不以王道为志,自以功名足以震矜天下,而内行不必检,所谓器小也。”(58)(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1页。康有为认为管仲虽然“不以王道为志”,“内行不必检”而“器小”,但有“治国之才,成霸之术”,“功名足以震矜天下”而“孔子称其仁”,因而不同于朱熹认为管仲“未得为仁人”。在康有为看来,孔子称管仲为仁,表明“孔子极重事功”,而朱熹认为管仲“未得为仁人”,表明朱熹“轻鄙功利”。
其实,无论是朱熹,还是康有为,他们都讲德才兼备。据《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对此,朱熹注曰:“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5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2页。对此,康有为《论语注》作了引述,略作改动,接着又引申出他自己的看法,说:“若当太平之世,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淘汰,胎教修明,人之智慧、澹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而后为天生之成人也。见利思义则廉节,见危授命则忠烈,久要不忘则诚信,此皆子路所长。而言必信,行必果,实士之末者。然生当乱世,治具未备,科学未张,有此独行,亦可为成人之行矣。盖乱世人之资格,与太平世人之资格迥远,圣人不得不因时世而节取之。若成人之实,则非令普天下人皆备智慧、澹泊、勇力、艺能、礼乐,非治教之至也。”(60)(清)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91页。在康有为看来,圣人是根据世道的不同而对“成人”作出不同的规定;在太平之世,“成人”必须德才兼备,而在乱世,若仍然要求德才兼备,则“非治教之至”。由此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什么强调孔子称管仲为仁,并认为“孔子极重事功”,而批评朱熹“轻鄙功利”。
事实上,朱熹同样也赞赏管仲,认为“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显然是看重管仲“利泽及人”的事功。当然,朱熹更为强调以心性道德为本,要求“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不可“以成败论是非”(6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6),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83页。,也就是说,既要看事功,更要看动机,不能只讲事功。据此,康有为以为朱熹“轻鄙功利”,恐有不妥。如上所述,朱熹讲德才兼备,不可能轻视人的才能和事功。对于康有为讲“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与康有为同时代的朱一新(62)关于朱一新和康有为的关系,可参见江中孝《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 〈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 2006年第5期。说:“《二程遗书》明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尝不欲利,只是以利为心则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害,未有义而遗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是则近人之所据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63)(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2页。在朱一新看来,程颢讲“利,非不善也”,要求“和义”,反对“害义”,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反对“以利为心”,不可能“轻鄙功利”。
当然,康有为批评朱熹“轻鄙功利”,同时又赞同朱熹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既强调义为根本,又对利有所肯定;而且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董仲舒所言为“学者自修之要”,这表明康有为与朱熹一样重视心性道德之本。因此,康有为讲“孔子极重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是要更多地重视事功及重视功利,这就是他所谓“孔子之道,内外本末并举,而无所偏遗哉”,因而其对朱熹虽有批评但非对立,只是殊途同归而已。
五、结 论
自焦循、刘宝楠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其中“君子”“小人”解读为“以位言”之后,学者对于儒家义利观的解读愈加复杂,既要讨论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又要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义与利的相互关系。康有为对于儒家义利观的解读就呈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康有为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加入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述董仲舒所言,讲“君子、小人以位言”,将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做了明确区分,强调上层官员应当“喻于义”而不可“喻于利”,所以应当“戒怀利心”,认为“一怀利心,则绝于圣人之途”,并应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应当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康有为要求上层官员德才兼备,重视事功,甚至批评宋儒“轻鄙功利”。
然而,就一般的义利关系而言,康有为的解读,与朱熹有许多一致之处。他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肯定朱熹所谓“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同时以《易传》“利者义之和”解“子罕言利”,既讲“利者,人所同好”,又反对“再增长附益之”,反对过多讲利,与朱熹所言“若多言利,则人不知义,而反害于利”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康有为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明确的肯定,较朱熹的解读又有新的发展。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于儒家义利观的解读,不仅继承了焦循、刘宝楠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其中“君子”“小人”解读为“以位言”因而不同于朱熹,而且又在义利关系上继承了朱熹的解读,并有所发挥,不仅超越了朱熹讲“惟合于义,则利自至”以及“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实现了从“利自至”“不求利”到“取利而和,则谓之义”的转变,而且较王夫之讲“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64)(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六),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1095页。也进了一步,从而形成了自程朱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到王夫之讲“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再到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的发展脉络(65)参见乐爱国《“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湖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解《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但对于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作出足够的讨论。《易传》“利者义之和”,讲的是“利物足以和义”,其中的“利”,是就利物、利人、利天下百姓而言,而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讲的是“取利”,要求“取利而和”“取不侵人之界”,反对“取利不和”“取而侵人之界”。显然,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与《易传》“利者义之和”在逻辑上并非完全一致;其后,这一解读并未受到重视,其原因概在于此。尽管如此,康有为通过对“利者义之和”的解读,明确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仍不失为一新说,可以为进一步理解儒家的义利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当今社会,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保护,争取合法权利得到肯定,康有为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