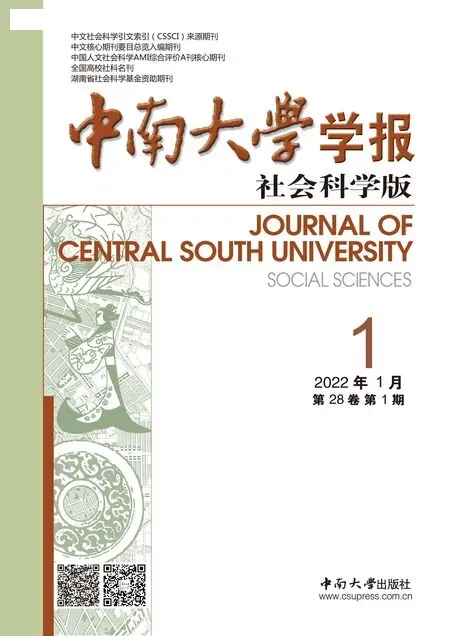想象读者与阅读引介
——孔尚任编创《桃花扇》系列“副文本”的意图及意义
2022-11-23陈志勇
陈志勇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2075)
《桃花扇》现存最早版本是康熙介安堂本[1],此版本的正文之前刻有梁溪梦鹤居士《序》、题辞、小引、凡例、纲领、目录,正文之后则附录有砌末、考据、本末、小识、跋和吴穆《后序》,而且在此刻本的天头和每出戏的末尾皆有长短不一的评点文字,它们共同构成了《桃花扇》的“副文本系统”①。这些副文本功能各有不同,或是主旨主线的引介,或作文本结构和角色布局的推演,或是成书脉络与传播案例的介绍,或具列史料来源的书目清单,它们共同服务和拱卫正文本,形成“一正众副”的《桃花扇》文本群。
通常而言,一部浸润心血的文学作品,它的作者都会企盼得到“理想读者”群体的青睐,而作为酝酿十五载、“三易其稿”的《桃花扇》更是如此。孔尚任在此剧面世至付刻之间的二十年间,陆续创作了十一个副文本,从不同层面为《桃花扇》的阅读补充重要信息,流露出作者与“理想读者”展开交流的强烈意愿。此种不遗余力深度介入读者重建《桃花扇》意义的用心,放眼明清戏曲史和文学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检视《桃花扇》的学术史,学界对正文本研究非常充分,而对副文本则明显关注不够,即便有个别成果涉及《小识》《题辞》等副文本,也只是考订其著作权问题或写作者的身份,属于知识考古范畴的探讨。正是鉴于副文本对于理解《桃花扇》的重要价值,本文尝试改变前人的研究思路,将系列副文本视为整体予以综合考量,既体悟作者编创这些文本的初心,重视正、副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互文”信息系统,亦寻绎副文本群在建构作者与读者新型关系中的独特功能,借此触摸《桃花扇》副文本生成及表述策略背后的丰富意蕴。
一、“理想读者”预设与《桃花扇》的早期受众群
一般而言,作家在作品的构思至成书过程中,都会对目标读者有考量并作基本的定位,孔尚任对《桃花扇》理想读者的想象和预设也是在此过程中渐趋明晰的。一方面,他在湖海治河的三年多时间内广交遗民、踏访遗迹,其幽愤出世思想愈加浓厚,《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2](44)的主旨和线索呼之欲出,成为其想象“理想读者”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桃花扇》所表现题材的敏感性,在清初意识形态紧张氛围下,孔尚任更注重书写技巧,“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2](25),其深意往往潜藏在文字之下。要读懂这番“深意”,读者仅有解读史料的能力还不够,还需要有重建南明历史现场的体验与想象力,而遗民显然是理想的读者群体。
我们知道,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1648),并没有亲历明清鼎革的家国变故,但从他在剧中化身老赞礼表达孤臣遗老故国之痛以及营造桃花源隐逸终局等来看,他在“精神上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明末遗老”[3]。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七,孔尚任在北京的寓所邀请同人,搬演《桃花扇》为母遥贺寿诞②,“今岁增丝竹一部,……小伶奏新声侑之”[4](1619)。这是目前所知《桃花扇》的首次演出。诗序所记参加集会的十八人俱为孔尚任的旧雨新知,其间也有不少是故朝的遗老遗少,如吴镜庵,为前朝恭顺侯之子,潦倒京城时与孔尚任交往甚密;余鸿客,名宾硕,遗民余怀之子;李彦绳、李鼐公兄弟是已故保和殿大学士李霨的孙子。《本末》第七则描写李氏兄弟在自家别墅“寄园”演出《桃花扇》的盛况:
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选优两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杂脚。凡砌抹诸物,莫不应手裕如。优人感其厚赐,亦极力描写,声情俱妙。盖园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5](118−119)
这段文字显示《桃花扇》的接受者基本上是“故臣遗老”,他们观赏后的反应最为强烈,与孔尚任“理想读者”的定位颇为相契,也从侧面印证了剧本创作的成功。
《本末》是《桃花扇》成书和早期传播的“小史”,其中多条文字记载了特定群体观赏此剧的基本信息。某种意义上,观剧也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戏剧情节、领悟剧作思想的方式。孔尚任把这些观演信息和事件的细节予以披露,潜含他对这些接受者身份和情感的认同。如第二则就提及康熙三十八年(1699)回京官户部主事、时任户部左侍郎的田雯“每见必握手索览”,才敦促孔尚任最终完成《桃花扇》。田雯(1635—1704),字纶霞,山东德州人,遗民田绪宗之子。《题辞》首列田雯的《题桃花扇传奇绝句》,其中“南朝剩有伤心泪”“眼底忽成千载恨”等诗句充满浓浓的悲悼情愫[2](9)。《本末》第四则谈到此年秋夕,内廷索要《桃花扇》,孔尚任因“缮本莫知流传何所”而找到“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这位张平州中丞即张勄,字敬止,奉天辽阳人,正黄旗,荫生,曾任遵化知府、山东按察使等职,对《桃花扇》青眼有加[6](305)。第五、六两则记载康熙三十八年除夕,李木庵总宪派人送岁金,索要《桃花扇》,并聘请驰名的“金斗班”于灯节来府中演出。次年四月,又招孔尚任来府观看《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5](118),并推尊孔尚任独居上座。这位李木庵总宪即是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兴化人李柟(字倚江)。其父李清,明崇祯四年进士,弘光朝大理寺丞,入清不仕,后又不赴康熙修《明史》之征召,私家修纂《南渡录》《三垣笔记》等南明史著作。袁世硕先生认为孔尚任在兴化治河期间接触过李柟的族叔李沂(斯时李清已逝),应读过李清所著的这些书[6](244−245),可备一说。
第八则写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孔尚任的好友顾彩受容美土司田舜年之邀前去探访,“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5](119),顾彩作有《客容阳席上观女优演孔东塘户部〈桃花扇〉新剧》诗以纪其事[7](370)。田舜年和孔尚任曾就《桃花扇》而互赠诗歌,二人虽未谋面却引为知己。田舜年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幼时经历了鼎革之变,父、祖辈的亡国之痛与改事新朝的两难处境给他留下了印记。其祖父田玄曾谓:“余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奇遘,赤眉为虐,朱茀多惭,悲感前事,呜咽成诗,以示儿子霈霖、既霖、甘霖辈。”[8](206)又有诗“旧恩难遽释,孤愤岂徒悬”“遗人辞故主,拥鼻增辛酸”,流露出对故朝的无限眷恋和对皇恩的感戴[8](206−207)。
第九则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孔尚任赴时任真定知府的刘雨峰署内观演《桃花扇》的情景,“时群僚高宴,留予观演《桃花扇》”[5](119)。刘中柱,字砥澜,号雨峰,曾任户部郎中,与孔尚任有密切的交往,孔氏《长留集》有多首诗歌提及这位旧友。刘雨峰颇具遗民思想,王源《居业堂集》记载:“雨峰诗风流自赏,有庾开府、何水部之遗。……盖时时与故老、遗民、酒徒为世外交,所谈者多兴亡之事。”[9](211)袁世硕先生认为刘中柱之所以作这种“世外交”,所谈多“兴亡事”,有其家世的原因:他的曾祖刘永澄是万历间进士,东林党人,而祖父刘心学,在明亡后致力于写史,撰《明史摘要》,又辑“神宗以后事”为《四朝大政录》二卷传世[6](300)。第十二则记载《桃花扇》自面世以来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孔尚任久有将之付梓的想法,但苦于囊中羞涩,康熙四十七年(1708)天津人佟鋐(字蔗村)过孔宅,“索抄本读之,才数行,击节叫绝”[5](121),遂捐赠50 两白银襄助此事。佟鋐之所以助捐《桃花扇》刊印,或与其处世态度和方式不无关系,《(乾隆)天津县志》载其父官至河南布政使,六个兄弟皆通籍仕途,惟“鋐以国学生例授别驾,不愿谒选,绝意华膴”[10](191)。以上《本末》中的七个实例记录的是《桃花扇》成书和传播环节受到社会知识阶层尤其是遗民群体欢迎的情状,可谓是早期受众的真实影像。
除《本末》外,《桃花扇》问世后的二十年间有诸多文人阅读(观赏)此剧后留下题剧诗、序跋等文字,介安堂本有所选择地刻入。《题辞》的九位作者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金埴,《跋》的六位作者黄元治、刘中柱、李柟、陈四如、刘凡、叶籓,多是孔尚任的旧朋新友,有些具有遗民身份。在孔尚任看来,他们就是《桃花扇》的“理想读者”。如《题辞》作者之一的陈于王,字健夫,顺天府宛平县人,在淮扬治河期间,孔尚任就与其结交;后来陈于王也入京,二人有密切往来、情感相契,孔尚任的《长留集》多次提及他。另一位作者宋荦(1634—1714),是《桃花扇》中主人公侯方域的同乡,曾参加侯氏主盟的雪园诗社,对侯的事迹知之甚悉,也是侯氏《壮悔堂文集》的编纂者之一。康熙四十六年(1707)宋荦任吏部尚书,“每有宴会,辄演此剧(指《桃花扇》)”[2](22)的情景,被《题辞》的另一位作者、当时正在宋荦府中作幕宾的吴陈琰所记下。吴陈琰,字宝崖,钱塘人,所著《旷园杂志》被孔尚任列入《桃花扇考据》的参考书目。其他跋语的作者也多与孔尚任交往日久,如黄元治,字自先,安徽黟县人,在北京任户部郎中时与孔尚任有交集。他在跋语中盛赞《桃花扇》“寄国家兴亡、君子小人成败死生之大故,贯穿往覆,挥洒淋漓。大旨要归,眼如注矢;凄音楚调,声似回澜”[5](125),可谓深谙《桃花扇》之雅音。
正是基于对这些“知己之爱”的珍视,也是出于推介《桃花扇》的目的,孔尚任将友人所撰题辞、序跋以及记录他们阅读、搬演或观赏《桃花扇》情景的《本末》,按照一定的次序摆放在《桃花扇》文本前后的相应位置。这种做法可以将更多读者带入阅读或观剧的历史现场,使他们感知《桃花扇》早期传播的真实氛围和独特生态,起到干预阅读、引燃情绪的效果。
二、外置副文本与孔尚任的阅读引介
通常而言,文本的阅读者可分为普通读者和知识读者两类。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孔尚任心目中《桃花扇》的目标读者,就是那些亲历南朝旧事,或对这段历史相当熟悉、能对自己的作品产生情感共鸣的文人士大夫,这是个“知识读者”群体。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理念、体例和书写方式,因为剧作的面世首先就要接受他们的“检阅”。
《桃花扇》即将完成之际,孔尚任就迫切地给挚友张潮写信自荐:“《小忽雷》尚未梓完。弟又编《桃花扇》一本,传弘光时事,颇有趣,容一并寄览。”[11](2577)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桃花扇》颇为自得自信的神采和将“好剧”呈献知己的浓浓情味。可是现实中,一部内涵复杂的作品要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同往往需要时间,《桃花扇》刚刚面世亦是如此,“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孔尚任由此甚至产生了“焦虑”情绪:“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2](26)于是,先后编创系列副文本,对此剧的主旨、主线、剧本体例、写作手法、角色体制、砌末分配、排场设计和传播情况予以介绍。虽然这些副文本的功能各有分疏,但向世人推介《桃花扇》的用心却是一致的。
首先,孔尚任通过《小引》《小识》向读者引介《桃花扇》的主旨与主线。《小引》从强调戏曲具有“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批评教化的功能,引出孔尚任编创《桃花扇》的初衷:“《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2](25)这段文字告诉读者,《桃花扇》演绎的不是儿女私情,而是要总结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败、消、歇”的历史经验,以成“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在《桃花扇》“先声”中,作者又借老赞礼的口道出“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2](44)的写作意图,再次强调《小引》提出的主旨。为强化《小引》关于“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意旨,孔尚任在《小识》中特意表明:“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5](123−124)以此提示读者要注意作品关于阉党余孽“结党复仇”线索的书写,因为它正是“隳三百年之帝基”的根源。
细读文本,在侯李情事和南明兴亡这两条线索之间,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成为离合与兴亡情节线的重要推力。从第一出《听稗》由小生吴次尾间接道出“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揭帖》”开始,正式拉开复社文人与阮大铖之间冲突的帷幕。紧接的文庙祭孔殴阮,鸡鸣埭观戏骂座,侯李新婚却奁,秦淮文会辱阮等戏出,皆以复社文人为主动方激化矛盾冲突,为后半场阮大铖衔恨报复张本。第十二出《辞院》,阮大铖诽谤侯方域是左良玉南京就粮的内应,向马士英建议除掉此人,这是阮大铖报复侯方域等复社文人之肇始。此后,得势后的阮大铖向弘光私奏,欲致复社文士周镳、雷縯祚于死地(《选优》);路过书林,下令捉拿复社三公子(《逮社》)。第三十三出《会狱》,侯方域在狱中亲见周镳、雷縯祚二人被处死,又通过柳敬亭之口道出复社“三公子、五秀才之案”。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恩怨,既是公仇,也属私怨,它跨介于国家兴亡和侯李情缘两条线索之间,成为理解《桃花扇》主旨和主线的关键。
其次,孔尚任通过《凡例》向读者介绍《桃花扇》的写作原则。十六则《凡例》以说明性的文字分别介绍此剧的剧名由来、出目安排、曲律规范,以及说白科介、角色化妆、上下场诗、附加戏出等编创体例。具体而言,前四则为创作理念和戏曲排场的总纲。第一则解释剧名由来,将“桃花扇”喻为珠,桃花扇故事之笔为龙,龙“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总不离乎珠”,以一柄桃花扇结撰全篇,构思巧妙,被学者总结为“曲珠中心结构法”[12]。第二则阐明剧作的“虚实原则”,申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事,严格遵循“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信史理念,与《试一出》老赞礼所言“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鼓桴相应。第三则表明“尚奇”的排场原则,此既与《桃花扇》一改传奇大团圆结局的厌套、以悲剧收煞相互照应,亦与《小识》中“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5](123)的戏曲观念相参详。
第五至第九则是填词作曲基本原则的说明,具体包含:每出曲牌数量的“长十短八”原则;所择曲名和套曲的“熟见”原则;遣词造句的“新警”原则;宫调叶韵的“当行”原则。以上原则是孔尚任关于案头填词、场上曲唱的理想状态的阐释,亦是其对《桃花扇》写作境界的自我期许。
第十至第十三则,是关于说白科介之创作原则的解释性文字,提出词句要整练,音节要抑扬铿锵,科诨要趣而不伤雅,道白要个性化,“须眉毕现,引人入胜”。这些观点折射出孔尚任深谙“传奇作法”,对舞台表演极为在行,已探触到舞台表演的精微之处。第十四至第十六则,是关于角色化妆和附加场次的补充说明,分别对丑、净扮饰柳(敬亭)、苏(昆生),下场诗改“集唐”为新作,增益“试闰加续”戏出等做法作出解释,希冀获得读者对这些创新之举的理解与认可。
最后,是孔尚任以《纲领》向读者传达《桃花扇》关于场上人物和角色配置的重要信息。戏曲作为一种高度综合性艺术,既是文学的,也是舞台的,因此剧本承载的不仅是情节构架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时代情绪的蕴蓄,还要兼顾舞台的立体呈现。角色编排可谓是兼跨剧本体制与表演体制的关键性设计,《纲领》即是有关角色配置的一个重要文本。《纲领》对出场的三十个人物进行角色编排,分为叙写侯李离合之象的“色部”、书写弘光兴亡之数的“气部”和参合色、气之场案的“总部”。第一部类“色部”又细分为左、右两部,左部的正色为侯方域,右部的正色为李香君。左部围绕正色有间色陈定生、吴次尾,合色柳敬亭、丁继之、蔡益所,润色沈公宪、张燕筑;右部围绕正色则有间色杨龙友、李贞丽,合色苏昆生、卞玉京、蓝田叔,润色寇白门、郑妥娘。第二部类“气部”细分奇、偶两类,奇部由中气史可法、戾气弘光帝、余气高杰、煞气田雄组成,偶部由中气左良玉、黄得功,戾气马士英、阮大铖,余气袁继咸、黄仲霖,煞气刘良佐、刘泽清组成。第三部类“总部”,由经星张瑶星和纬星老赞礼担任。
在列出角色体系图后,孔尚任又写下“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之锱铢不爽。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以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张道士,方外人也,总结兴亡之案;老赞礼,无名氏也,细参离合之场,明如鉴,平如衡。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2](37−38)这段话,对《纲领》的设计进行总结和阐释。细绎其语,有三层含义:其一,就外而言,角色体系的设计服务并服从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主题、主线的总基调。孔尚任将属于“离合之情”线索上的角色安排在“色部”,“兴亡之数”线索中的人物皆放置于“气部”,而总部的两位“方外人”则横跨两部,起到“总结兴亡之案”和“细参离合之场”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安排,让人物在剧中各得其宜,无论如何游走于剧情,皆有章可循。其二,就体系内部而言,角色有主有次,色部之左,以侯方域为中心;色部之右,以李香君为中心,其他人物皆为“俦伍”。气部亦是如此,气部之奇,以史可法为中心;气部之偶,以左良玉、黄得功为中心。这五位居于中心的人物皆为《桃花扇》极力渲染的正面形象,可见作者在角色体系的设计上饱含忠奸善恶的伦理判断。其三,角色出场讲究“天然对待法”(第八出“闹榭”总评),色部左右对称,气部奇偶两分,总部经纬相参,即如《纲领》所言“明如鉴,平如衡。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含蕴阴阳平衡之为道的辩证思想。这一理念揆之《桃花扇》,显示多处角色和关目皆讲究先后映衬、明暗相照,如第一出侯方域听稗(柳敬亭说鼓词),对应第二出李香君传歌(苏昆生唱昆曲);前有柳敬亭行辕“投书”,后则有苏昆生“寄扇”;前有侯方域与苏昆生的“逢舟”,后有侯方域与柳敬亭的“会狱”。阴阳、忠奸“天然对待法”赋予《桃花扇》结构对称和情节照应的审美体验,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如同写忠臣之死,“奇气”部的史可法和“偶气”部的左良玉、黄得功既相互映照,又各不相同:“左宁南死于气,自气也;黄将军死于刃,自刃也;史阁部死于溺,自溺也。”[5](46)通过对三人赴死方式的差异性描写,左良玉的忠愤、黄得功的忠勇、史可法的忠烈跃然纸上,这些信息对于读者正确阅读与理解《桃花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由上可见,《小引》《小识》《凡例》《纲领》等副文本环绕《桃花扇》正文,大如主旨、主线的介绍,中及角色结构、排场文辞创作原则的说明,小至具体曲词意涵和演述手法的阐释,丝丝缕缕皆彰显孔尚任向读者荐介《桃花扇》创作理念和文本意涵的努力。
三、内置副文本与孔尚任的细节指引
《小引》《小识》《凡例》等是以前置或后置形式合刊的《桃花扇》外置副文本,而由眉批、出评组成的评点系统则是与正文同行的内置副文本。不过,与我国古代文学评点多属“他者”视野下的文学批评不同的是,《桃花扇》的评点由于是孔尚任亲自所为③,其引导阅读的用意颇为明显。
孔尚任对于以“桃花扇”为物件穿插剧情、连缀人物、凸显主题的设计志得意满,其在《凡例》的首则即予点出,特别提醒“观者当用巨眼”看待其以“桃花扇”为道具结撰全剧的“龙珠法”[2](27);《本末》首则也点出:“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5](115)不仅如此,孔尚任又多次以批语的形式拈出“桃花扇”,提点读者不可忽略此扇结构全篇的特殊功用,第二十二出《守楼》总评谓:“《桃花扇》正题本于此折,若无血心,何以有血痕;若无血痕,何以淋漓痛快成四十四折之奇文耶?”[2](316)第二十三出《寄扇》总评又指出:“借血点作桃花,千古新奇之事。既新矣、奇矣,安得不传?既传矣,遂将离合兴亡之故,付于鲜血数点中。闻《桃花扇》之名者,羡其最艳、最韵,而不知其最伤心、最惨目也。”[2](327)第二十八出《题画》总评亦谓:“对血迹看扇,此《桃花扇》之根也;对桃花看扇,此《桃花扇》之影也。偏于此时写桃源图,题桃源诗,此《桃花扇》之月痕灯晕也。情无尽,境亦无尽。”[2](394)在这些批语中,孔尚任反复强调“桃花扇”作为负载侯李的爱情信物,对理解离合线索和“色部”“总部”人物归道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对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既是《桃花扇》的主旨也是主线的设计,孔尚任亦流露出自我怡悦之意态,在剧中不失时机地点出。譬如前八出皆写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冲突以及侯李结缘,而自第九出《抚兵》开始才转入国家兴亡事,故而第八出和第九出总评分别指出“以上八折,皆离合之情”[2](145),“兴亡之感,从此折发端”[2](156),提醒读者注意情节线索的进程与变化。此后,离合与兴亡两条线索交叉推进,批语也时时向读者发出阅读提示,如第二十出《移防》,侯方域为阮大铖迫害而投奔史可法,总批谓:“侯生移,而香君守矣。男女之离合与国家兴亡相关。故并为传出。”[2](275)接着的《媚座》,杨龙友向马士英推荐李香君,为香君罹苦之始,则有“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 焉”[2](305)的总评,道出生旦在《桃花扇》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十五出《选优》写李香君被强选入宫排演《燕子笺》,孔尚任又作批语:“此折写香君入宫,与侯郎隔绝,所谓离合之情也;而南朝君臣荒淫景态,一一摹出,岂非兴亡之感乎?”提醒“读《桃花扇》者,当处处留神也”[2](357−358)。第四十出《入道》,侯李相遇,双双入道,再加批语:“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5](76)以上关于离合、兴亡主线的点评文字构建起一个虚拟的阅读场域,作者与读者同时在场进行文本细节的交流。
事实上,读者在理解作者意图,尤其是那些“深文曲笔”时,往往会感觉到困难,清初文人金圣叹在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时就感慨“谁谓稗史易作,稗史易读乎耶?”[13](897)张竹坡在读《金瓶梅词话》时也遇到“窥作者用笔之意,乃翻卷靡日,不得其故”[14](480)的情形,《桃花扇》同样存在作者寄寓幽深之笔。譬如,桃花源意象的营造和“南朝七作者”的创构就颇为隐晦,若无批语的接引,读者往往难以明悟。桃花源意象是孔尚任渡尽劫难、阅遍人世而大彻大悟的精神追求,寄托他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憧憬[15],是剧中正面人物的理想化归宿。故而,孔尚任从始至终有意留下“闲笔”以存深意,如第一出《听稗》有批语对柳敬亭“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的唱词予以点拨:“此《桃花扇》大旨也,细心领略,莫负渔郎指引之意”[2](60),为读者指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主旨伏脉。《题画》又安排蓝田叔擘画《桃源图》,借此提醒读者“画《桃源图》,有深意存”[2](391),所谓“深意”乃桃花源隐逸之梦想。《会狱》中柳敬亭唱“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乱秦人,同话渔船”的曲词;《余韵》则让众人归结于山林之间,云亭山人不失时机地提点:“天空地阔,放意喊唱,偏有红帽皂隶吓之而逃。谱《桃花扇》之笔,即记桃花源之笔也,可胜慨叹!”[5](96)桃花源情结和意象作为贯穿《桃花扇》的一条隐线,负载着作者对历史的慨叹、对现实的迷惘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等多种复杂情绪,是深入理解《桃花扇》的重要线索,批语将这些复杂情绪提炼出来,很容易引起特定读者的情感共鸣。
与之相连,孔尚任还塑造了一群具有独立人格的“小人物”。在人物结构上,他们是侯李二人的俦伍,甚至成为复社文人的参照之相;在情节结构上,他们又是南朝鼎革的见证者和“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孔尚任通过批语点出“作者七人”(卞玉京、丁继之、张瑶星、蔡益所、蓝田叔、苏昆生和柳敬亭):
玉京独来独去,为南朝第一作者。(《骂筵》)
继之同来自去,是南朝第二作者。(《骂筵》)
张、蔡同去,是南朝第三、第四作者。(《归山》)
蓝田叔归山,是南朝第五作者。(《逃难》)
苏昆生为山中樵夫,柳敬亭为江上渔翁,是南朝第六、第七作者。(《余韵》)
孔尚任在《余韵》中再次对“作者七人”的内涵作出总结性评点:“南朝作者七人,一武弁,一书贾,一画士,一妓女,一串客,一说书人,一唱曲人,全不见一士大夫。表此七人者,愧天下之士大夫也。”[5](97)孔尚任认为这七人的胆识见解远在当时士大夫之上,具有一种精神象征意义,这是他经过历史反思而沉淀下来的真知灼见④。坦率而言,这种思想深藏于文字之间,不经批语特意点出,是难以传达给读者的。
《桃花扇》的字里行间还隐藏着作者的一些“小动作”,这些潜存在文字之下的微言大义容易为人所忽略或令人费解,于是评点就发挥了灵活分散的优势,时时点拨、引发读者的思考。例如第一出《听稗》柳敬亭给侯方域等讲的就是《论语·微子》“太师挚适齐”全章,讲的是鲁哀公时,礼崩乐坏,乐师愧悔交集,纷纷离鲁。《桃花扇》通过柳敬亭之口对此予以描述:“一个个东奔西走,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顷刻冰冷。”坦言之,为何柳敬亭在复社文人面前讲这样一篇稗史,一般读者很难理解,于是此处适时有一句批语:“防乱揭出,柳苏散场,阮衙冰冷,情景可笑。适齐一章,恰合时事。”[2](55)有此批语的点拨,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复社文人刚刚公布《留都防乱揭贴》,使得阮大铖的门客皆知其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通过柳敬亭演说此篇《论语》来讽刺阮大铖劣迹败露、众叛亲离的景态。
在《桃花扇》正文中往往隐藏着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思考,这些创见不易被人察觉,故以批语揭示。如第八出《闹榭》,复社文人在举办丁家河房文会,灯笼上写有“复社会文,闲人免进”的字样,云亭山人批曰:“复社当年过于标榜,故为怨毒所归。”[2](134)整部《桃花扇》除了侯李情缘和南朝旧事,就是复社文人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此处批语点出其矛盾的根源——复社文人的做法也有过当之处。又如第三十一出《草檄》中,对柳敬亭“小阮思报前仇,老马没分寸”的批语“阿党之罪,阮重马轻,平心公论”[2](429),即是对马士英、阮大铖的公允之论。第三十三出“‘不学无术’四字,断倒宁南”[2](453)和第三十四出“黄虎山,忠臣也,亦是不学无术”[2](460)的批语,则是对左良玉和黄得功缺乏全局驾驭和研判能力的定评。再结合《劫宝》总评“南朝三忠:史阁部心在明朝,左宁南心在崇祯,黄靖南心在弘光。心不相同,故力不相协。明朝之亡,亡于流寇也,实亡于四镇也。四镇之中,责尤在黄,何也?黄心在弘光,故党马、阮。党马、阮,故与崇祯为敌。与崇祯为敌,故置明朝于度外。末云明朝天下送在黄得功之手,诛心之论也”[5](35−36)数语,“南明亡于四镇”的结论水到渠成,从而引发读者对明朝覆亡之际重臣、将领、文士等“国之栋梁”所作所为的反思。
这些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批语,包含作者对南明兴亡的思考和文本细节的解析,它们与其他外置副文本共同发挥阅读导引的重要功能。
四、孔尚任《桃花扇》副文本的多重意义
考察孔尚任编创《桃花扇》副文本始末,有三重因素不容忽视: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和读者意识,《桃花扇》“信史”的定位,以及此剧意义系统的丰富性和开放性。这些因素既是催生系列副文本、实现正副文本“互释”的助力,同时它们在作者实施阅读干预的过程中,又赋予了《桃花扇》副文本多重意涵。
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读者接受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作品居中勾连起作者与读者的联系。若从创作论角度看,作家和作品的关系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品作为作家随兴而发的产物,一旦问世,作家无意关注它们的流向和处境,作品与作家彻底分离;而另一种是作品作为精心打造的产物,作者对文本细节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持续的精力、情感投入,十分期待读者的积极回应。显然,孔尚任和《桃花扇》的关系属于后一种情形。孔尚任在构思和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生成了明确的主体意识,通过文本的制作精准投注自己“特定”的思想情感,并依托系列副文本向潜在的读者推销这部剧作,表现出浓厚的“读者意识”。事实上,确如孔尚任所预想的,《桃花扇》在流传之初与读者形成了释读与阅读的“共同体”。
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附属物,少了传奇戏曲的文体约束和书写禁忌,更方便孔尚任以此来陈述《桃花扇》的成书轨迹和创作细节,其鲜明的个体意志和文人气质流淌其间。譬如《凡例》在解释“设科打诨”原则时就指出科诨语言“宁不通俗,不肯伤雅,颇得风人之旨”[5](123),彰显孔尚任在重视《桃花扇》舞台表演性的同时,仍然坚守科白曲词审美风格的文人品格,态度鲜明而笃定。又如,在自创诗句代替集唐作下场诗、改大团圆结局为悲剧收煞的创新上,孔尚任一方面主动解释这些创举的内涵及其合理性逻辑,另一方面则积极谋求读者的认同和接纳,希冀兼顾创作主体性和阅读指向性。客观而论,作者的主体性越强烈,越会通过更丰富的表述形式来承载;细节和款曲越多,也越需要更多的副文本予以揭示,由此,《桃花扇》副文本纷纷面世。这一结论还可从孔尚任给副文本落款的形式和措辞上获得旁证:《小引》题“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小识》题“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本末》《凡例》《考据》《纲领》《砌末》则分别题云亭山人“漫题”“偶拈”“漫摭”“偶定”“漫录”之类。这些由孔尚任编制的副文本,就时间而言,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跨越二十个年头,虽然在落款处刻意强调它们是偶作或漫兴的产物,但当如此多的文本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时,其作者的主体意识无疑得到极大的显扬。因为每一个副文本既是意义丰富、功能独特的作品,统合后又呈现出叙述构架和作者意图的一致性,这样的文本格局和意义系统使得我们更愿意将“偶笔”“漫题”理解为孔尚任精心谋划的文本编制策略。
毋庸置疑,孔尚任基于“理想读者”编创系列副文本,最大的意图就是避免读者误读《桃花扇》。副文本的行文之间,告白、商请、提示等表述方式触目可见,如《本末》第十一则:“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5](120)在此孔尚任特意指出,之所以要将序跋、题辞并刻,就是为了酬答“知己之爱”。他所说的“知己”不正是《桃花扇》的“理想读者”吗?又如《凡例》之末条,在介绍正文四十出之外附入“试闰加续”四场之后,还加上“且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2](31),此语明显带有商请读者注意的意味。再如,第十二出《辞院》,阮大铖得势后开始报复侯方域等复社文人,作者让史可法也来参加马士英主持的朝廷会议,这一关目于史无征,故有批语解释:“至此始出史公及马士英,一忠一奸,阴阳将判,请君细参。”[2](183)我们知道,无论从《纲领》对角色体制的精心配置,还是人物出场、排场设置、事件营造,孔尚任皆追求平衡对称的“对待法”,此处以“请君细参”的口吻再次提醒读者洞悉其此番苦心。这些皆是孔尚任通过系列副文本的襄助深度介入读者阅读过程而留下的痕迹,当“知己”看到作者的这些“留言”,必会心有戚戚焉。如此,作者的“留言”与读者的“会意”发生融通,极大丰富了《桃花扇》的阐释空间和意义系统。
《桃花扇》作为取“南朝新事”的历史剧,很大程度寄寓了作者“以剧存史”的创作目标,然而在“信史”追求与戏剧虚构之间,如何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获得戏剧体验和审美感受,又实现对相关历史知识的验证,是孔尚任必须面对的问题。显然,通过系列副文本介入读者的阅读环节,并适当预设读者对《桃花扇》的理解与阐释,则是孔尚任作为剧作家极富智慧的创举。《考据》即是孔尚任介入阅读的关键性文本,这份书目具体到征引文献的篇章甚至段节,可与《桃花扇》所涉史实一一对照,真实还原了孔尚任对相关史料的择选、删汰和编改的轨迹,为读者深入《桃花扇》成书的细部,解读其编制情节、塑造人物和凝练主旨的策略提供了可能。《考据》胪列十六位作者的二十一种著作⑤,涵盖了野史笔记、诗文集和传奇戏曲等不同文类,从中可见孔尚任搭建《桃花扇》故事结构的史料来源与处理方式:由《樵史》建构南明遗事的基本框架,以《莼乡赘笔》《冥报录》《旷园杂志》等笔记、野史作细节补充;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事,则由《板桥杂记》《壮悔堂集》等数种文人别集中的诗文及其注释细细钩沉,捕捉相关事件的信息,再将这些信息碎片贴补起来,穿插于兴亡国事的全部进程中去,实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结构理念。由此可见,《考据》并不完全像某些研究者所言是清代考据学兴盛的产物[16](125),也不是孔尚任以之躲避朝廷的禁忌而故作狡狯的手法[17](4),而是他向读者展示《桃花扇》“信史”创作理念和原则的史料依据。
除《考据》之外,孔尚任还利用批语不失时机地点明某个历史场景的描写或某条史料的书写是有凭有据的,借此强化“信史”实录的史学追求。例如《选优》一出中,阮大铖向弘光帝进献王铎抄楷字脚本事,批语曰:“王楷书乌丝阑《燕子笺》曲本,今人尚有藏之者,非诬也。”[2](356)传递的就是事有所本的信史原则。再如,《赚将》中许定国用夫人侯氏之计,生擒高杰,批语又谓:“康熙癸酉见侯夫人于京邸,年八十余,犹健也。历历言此事,其智略气概,有名将风。”[2](363)对于文本中未写到用美人计色诱高杰,云亭山人亦予解释:“或传用美人计卧而擒之,曾文侯氏,云:‘未尝有妓也。’”[2](365)又如,闰二十出《闲话》张薇讲述崇祯自缢、下葬的始末,《考据》已指明所关史料来自陈宝崖《旷园杂志》“思宗开圹始末”条,孔尚任在此特意插入批语:“崇祯帝后大行始末,历历分明,皆胜国实录,不可以野史目之。”[2](280)坦率而言,一般读者是不会追究此处所演史实的真实性,更不会去考索是来自正史还是野史,但因为孔氏预设了特定的读者,特此告知这些史实虽来自野史《旷园杂志》,但也是“信史”。类似的评点还可寻及,它们皆是对剧中人物、事件和情景真实性书写的“再确认”,当孔尚任特意点出这些事件书写的真实性时,批语的副文本功能与意义就获得高度统一。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作为充满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越是名家名作,其文本越具开放性,越能向读者提供文本“意义”阐释和重建的巨大空间。孔尚任也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也不会通过《小引》《小识》《考据》和批语反复强调《桃花扇》的创作思想和主要线索。事实上,《桃花扇》的主旨和主线确实存在多种阐释的可能,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根据阅读体验将最强烈的感受凝聚成一种“突出印象”:如果对侯方域、李香君离合之情印象深刻,就会认为《桃花扇》是一部精彩的才子佳人戏;若是对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斗争的戏记忆如新,则会觉得它就是一部明末党争题材的戏曲;假如对南明兴亡留下深沉的痛感,则主张这是一部抒发亡国之痛的历史剧。这三种解读,根据副文本系统的提示,表明前两种都是对孔尚任本意的“别解”,只有后一种才是“正解”。这样的“正解”即是读者依靠副文本的指引,让自己的阅读视野与文本视野相互融合而达成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桃花扇》文本意义重建的过程,也是读者和孔尚任精神相遇,重新触摸与领会作者意图的过程。尽管阅读并不是一个重复他人的行为,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也会存在差异性,但由于有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意向,在核心内容和主体情感的理解上完全可以共通。
在此意义上,孔尚任通过副文本深度介入阅读,帮助读者进入《桃花扇》文本意义重建的最佳状态——准确理解作者的编创意图、读懂作者潜藏于文本中的“深意”。由上可以看出,孔尚任编制系列副文本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桃花扇》文本系统显得美观,而是保证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读者能正确理解自己的创作宗旨和写作手法,“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18]。
五、结语
《桃花扇》被后世视为明清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在主题意蕴、戏剧结构、人物塑造上尤称“杰构”[19](286),而附刻的十一种副文本与《桃花扇》正文所形成的多重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亦是其声名增殖的重要因素。这些副文本不仅与《桃花扇》正文构成阅读语境与意义衍绎的“文本互释”的动态关系,还彰显了孔尚任主动向读者阐释《桃花扇》细节设计和深层意涵的文本编拟策略。
我国古代戏曲作为高度综合的艺术,对其展开研究需要兼及案头与场上、作家与读者、表演者(伶人)与观赏者(受众)等多对范畴,但无疑文本是核心。只有“回归文本”,围绕文本所衍生的学术领地(如作家创作与文本书写、文本阅读与传播、剧本形态与戏曲体制、戏曲生产与消费)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基于这一理念,以及对《桃花扇》所呈现的极为“特别”的副文本现象的关注,本文将介安堂刻本的系列副文本视为一个整体,对作者、文本、读者(观众)以及早期传播的历史语境作综合考量,尝试从文本外围(边缘)触摸孔尚任的创作心态和《桃花扇》意蕴的新思路,或能为这部名剧的讨论生发出更多的话题。
注释:
① 副文本一词,为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主要指那些存在于文学作品正文周围,调节作品与读者关系的材料。参见《热奈特论文选批评译文选》,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 页。
② 从诗句“才挥桃扇春无限,更响银筝趣不同”,“词人满把抛红豆,扇影灯花闹一宵”等诗句可证。徐振贵先生也认为“此诗即为吟咏《桃花扇》初演而作”(徐振贵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三),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621 页),此论甚是。另,洪天桂《知松堂诗钞》卷一《人日孔东塘农部招同余鸿客……分韵得七阳一东》的诗注:“东塘新填桃花扇曲”(《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0 页),亦可证明此日搬演《桃花扇》。
③ 关于介安堂本《桃花扇》批语的作者,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梁启超(《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饮冰室合集》第11 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7 页)、吴新雷(《〈桃花扇〉批语发微》,载《戏曲研究》第61 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 页),皆认为是孔尚任所为。笔者细读全部批语,深以为然。
④ 关于《桃花扇》“作者七人”的独特意涵,可参汪诗珮《追忆、技艺、隐喻:〈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载台湾《戏剧研究》第19 期,2017年1月。
⑤ 贾静子《侯公子传》实际是一篇传记,不计算在内;而《石巢传奇》二种具体是《春灯谜》和《燕子笺》,为两种戏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