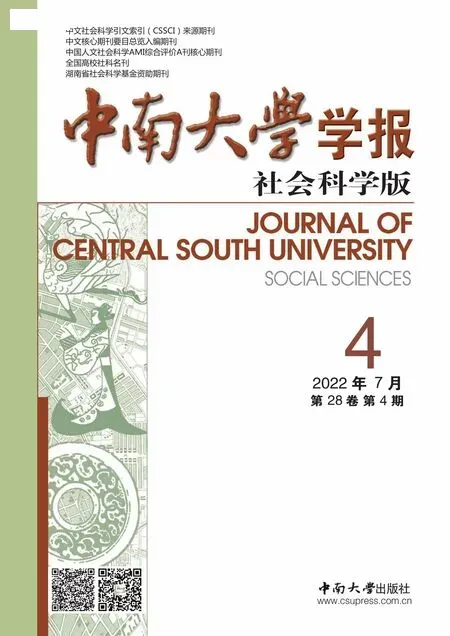《人间词话》摘句批评的基点、旨趣与影响
2022-11-23夏志颖
夏志颖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内容上吸纳、借鉴了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资源,提出了不少关于词乃至文学的新见解,引发了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与之相映成趣的却是,这部词话的外在形态又显得相当保守——相较于此前《红楼梦评论》的论文形式,《人间词话》的具体条目几乎都是陈旧的、寻章摘句的印象式批评,与传统诗话词话面目雷同,以致于很多《人间词话》的拥趸都对此感到意有未惬①。其中,被运用到极致的“摘句”似乎值得特别关注:在手稿本(共125 则)中,王国维仅完整引用了四首诗词,可谓惜墨如金,而经删润发表的初刊本(共64 则),甚至从未完整引用过任何一首诗词,无论该作是多么精彩短小②。
与中国古代众多的诗话词话一样,《人间词话》在表达观点时,并没有精密的理论分析和推衍,而是多采用以摘句为例的批评形式,这显然与静安对“句”的重视有关。但他何以如此重视“句”,“摘句”的外在形式与王国维的词学观以及《人间词话》的部分条目内容是否有内在的呼应,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此类问题作出一些粗浅的回答。
一、名句“得于天”:摘句批评的观念依据
古代诗词,从结构上说,主要有篇、句(整体与局部)之别③,二者的关系是诗词评论中常见的话题。或强调局部的重要性,如“一诗之中,妙在一句,为诗之根本。根本不凡,则花叶自然殊异”[1](28);“词家有作,往往未能竟体无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觉片羽可珍”[2](3174)。或反对追逐佳句之风,如“从来谈诗,必摘古人佳句为证,最是小见”[3](710);“大家出语未尝不警炼,而不乞灵于此,只是篇法之妙,不见有句法”[4](2710)。而在有的论者眼里,是否有名句(佳句、警句)又关乎时代之升降与作品之得失,《沧浪诗话》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5](533)在严羽的评价坐标中,“气象混沌”显然是高于“可以句摘”的。《人间词话》对《沧浪诗话》颇有首肯,但在重视名句这一点上,却有独得之见: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手稿本第97 则)[6](512)
“有篇有句”当然是最完美的,至于“有句而无篇”与“有篇而无句”孰高孰低,考虑到王国维对词史演进所持的负面态度,大概也不难推断。在他看来,南宋词之地位、价值不及唐五代及北宋词。也就是说,如果非要在“篇”“句”中取其一,则“有篇”(南宋名家之词)逊于“有句”(唐五代之词)。这里的“有句”即严羽所说的“句摘”“佳句”。手稿本第31 则初稿作:“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不期工而自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7](65)后王国维改“不期工而自工”为“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将此则列于初刊本之首,可见他对“名句”的重视。而“境界”不仅针对全篇(高格),还有大量的名句本身就自有境界,这样的例子在《人间词话》中随处可见,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手稿本第33 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为小境界(手稿本第48 则),等等。
静安既然以“境界说”统摄初刊本词话,则其开宗明义的第1 则就已交代他重视名句与采用摘句批评的“学理依据”。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本人的诗词创作起步甚早,也确曾以名句见称。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称王氏“偶作诗,亦有妙绪”[8](14926),胪列其“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等十数则名句。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也举出静安诗联多则,以为皆可入《蒲褐山房诗话》《国朝诗人徵略》和摘句图。陈声聪《读词枝语》云:“王静安词主意境,力追五代、北宋。其句如‘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信有华颠’,空际转身,迷离惝恍,信为高境。”[9](76)相信但凡读过静安诗词的人,都会对其中络绎纷呈之妙语佳句印象深刻,诚如《人间词甲稿序》所云“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10](682)。在名句写作上的成功与自负,可能也增强了静安对“名句”的执念④。
当然,对于哪些是词史上真正的“名句”,静安常有不同寻常的判断。《人间词话》提出了一些新名句,也嘲讽过一些旧名句。简单来说,他所认可的名句,必是自有境界、“自然神妙”(手稿本第69 则)、体现出饱满鲜明的生命意志的;他否定的,总是那些衰飒浅薄的。因为前者的写作直接取决于作家的天赋,而这又是静安特别强调且深具自信的。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甲、乙稿二序,《甲稿序》论“天”对名句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君(引者案:即王国维。)自所为词……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乙稿序》中将意境(境界)与“天”联系起来:“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10](682)叔本华“崇拜天才”[6](87),尼采“恶谦虚”[6](89),受他们的影响,王氏的哲学与美学论著极喜言“天”(天才、天赋),如批评清真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6](543)。在作于1906年的《甲稿序》中,静安认为,词“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后出的《人间词话》批宋末诸人“才分有限”,并对南宋的“伪名句”嗤之以鼻。是以真正的名句,必得于“天”,而境界之有无与深浅同样取决于作家的天赋,《人间词话》对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诗句的多次称引就透露出此中消息⑤。此外,在词学批评上对静安影响较大的刘熙载也有类似体认,《艺概·词概》云:“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2](3708)《游艺约言》云:“作书当如自天而来。……昔人所谓‘好诗必是拾得’,书亦如之。”[11](575)“触着”“自天而来”“拾得”云云,其实就是王国维“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另一种表述。《人间词话》引元好问《论诗绝句》也正是此意:“‘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论诗绝句》也。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手稿本第81 则)诚然,与“神助”相对,闭门苦思也可能写出某些“名句”,文学史上还流传着不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之类的故实,但王国维显然看不上后者⑥。
与名句有天才与人力之别相似,句、篇二者仰赖天赋与人工者也各有侧重,如清人余云焕《味蔬斋诗话》所云:“有篇无句,终是天分低;有句无篇,还是人工少。”[12](643)王国维重视名句,因为它源自天赋、神助,篇则不然。所谓“有篇”,是指作品结构妥帖,语意完足,而这些都是人力可致的,是以静安又说:“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手稿本第83 则)只要一个作家持续用功,都可以“有篇”,而“名句”则多是“伫兴而成”(手稿本第28 则)的,“费精神”为之也无济于事。静安对此另有一种表述可供参证:“真正之天才,其制作非必皆神来兴到之作也。以文学论,则虽最优美、最宏壮之文学中,往往书有陪衬之篇,篇有陪衬之章,章有陪衬之句,句有陪衬之字。一切艺术莫不如是。此等神兴枯涸之处,非以古雅弥缝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藉修养之力不可。若优美与宏壮,则固非修养之所能为力也。”[10](110)以后天修养为基础的“弥缝”可以保证篇章的完整,但这只能是“神兴枯涸”时的权宜,如果全凭“弥缝”,虽“一日作百首”,亦无与乎“神来兴到”也。
二、“有句可摘”与南、北宋词的优劣
《人间词话》对名句的偏嗜并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唐圭璋就此评曰:“五代北宋之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13](1028)《人间词话》对“花间”、南唐与北宋之词多有摘句,是举看起来违背了词学史的某种惯常思维。传统词学常常讨论南、北宋词的异同和优劣,要而言之,北宋词多浑成,而南宋词多警句⑦,二者其实是有一点对立的。王国维一反常态,将它们颠倒过来,谓“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难免会让不少论者一时难以接受,但就《人间词话》的论词体系而言,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王国维的言论自有其逻辑理路可循。
初刊本《人间词话》引用历代诗词共70 次,其中引唐五代词13 次,引北宋词20 次,引南宋词10 次。从所引数量上看,南宋词明显处于劣势,而引用南宋词的10 次中,只有4 次属于肯定性评价。手稿本的条目总数虽增加了一倍,但摘句时仍旧重北轻南。王国维既以高格、名句推许五代北宋词,他纠弹南宋词也从这两方面入手。前者以批姜夔为显例:“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手稿本第22 则)“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片语道着。”(手稿本第75则)后者主要体现在解构南宋传诵已久的名句上,如下面几例: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而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手稿本第76 则)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手稿本第85 则)
姜夔在南宋时就以“意到语工”[14](2700)、“句法挺异”[2](255)闻名。“二十四桥仍在”句出自其名篇《扬州慢》(淮左名都),张炎《词源》卷下评之为“平易中有句法”,陆辅之《词旨》所列 “警句”若干则,“二十四桥仍在”句、“高树晚蝉”句均位列其中。“数峰清苦”句,许昂霄《词综偶评》、卓人月《词统》、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均叹赏有加。“二十四桥仍在”云云,作为姜夔炼字写景的成功范例,还得到邓廷桢《双砚斋词话》、李佳《左庵词话》、先著《词洁辑评》的肯定,前人于此皆无异议。但王国维却从“真景物”“真感情”的标准出发,指其为“隔”,又进而将“隔”与“不隔”视为南北宋词的一大差别。王氏所云的“风会”,在古典诗文评论中有些神秘色彩,它难以言诠,而又不可抗拒。
“自怜诗酒瘦”句出自史达祖《喜迁莺》(月波疑滴),也属于《词旨》所列之“警句”;“能几番游”句出自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词洁辑评》赞为“妙语独立”,《左庵词话》也举以为佳句,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续补了一些《词旨》失收的“警句”,其中也有这一句。以上都表明了一个词学史上的共识,即史达祖和张炎皆是以警句见长的词家。陆辅之指出“史梅溪之句法”值得学习,李调元说梅溪词“炼句清新,得未曾有”,“余读其全集,爱不释手,见书佳句,汇为摘句图”[2](1427);《词旨》在“属对三十八则”外,另有“乐笑翁奇对凡二十三则”,在“警句九十二则”外,另有“乐笑翁警句凡十三则”。警句无疑对史、张等南宋诸人词史地位的确立极为重要,《词洁辑评》就曾列举蒋捷、吴文英、张炎的妙语名句,感叹“即此数语,可长留数公天地间”[2](1368)。可静安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频频摘引五代北宋词之名句予以褒扬,另一方面又着力批判南宋词之名句,抓住这一历来公认的最能体现南宋词特点、代表南宋词成就的方面,痛下针砭,大有釜底抽薪之势。知道了这一大前提,我们再反观他对南宋词难得的赞赏:
周介臣(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手稿本第12 则)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手稿本第13则)
此二则连属而下,指向南宋词中最为清人尊奉的两家,寓贬于褒。梦窗词密丽,静安特举其空灵者,白石词“有格而无情”(手稿本第11 则),静安特举其真情流露者。“无足当此”“亦仅”云云决然否定了以吴、姜为代表的南宋词人的努力:他们凭恃“修养”,终生“弥缝”,所得不过如此。实际上,就如上节提到的,对不同的读者来说,何为真正的名句,可能很难说服彼此,但联系到王国维的名句观,他必判定南宋诸家所作与天赋、神助绝无干系。对此,我们在前人有关警句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启发。陆机《文赋》形容警句的功能是“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词有警句,则全首俱动”[2](620);刘熙载云“词眼二字,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2](3701)。也就是说,名句(警句)是一篇作品中最有生命力的地方,系“神光所聚”,有了它,全篇就有了生气,没有它,作品就索然无神采。手稿本第84则因此就可得确解:“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有篇无句,就无“神光”,其结果必然是“枯槁”,这种作品不可能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自然也不可能有境界。
三、诗词之题与“摘句”的使用限度
如上所述,“摘句”批评形式的运用与《人间词话》中抑扬南、北宋词的多则内容有潜在的对应关系。除此以外,词话中有些条目表面上与“摘句”无涉,但仍可相互发明,典型者如手稿本第39 则:
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该则文字在发表时经过较大改动,并录于此,以便比较: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初刊本第55 则)
按手稿之意,文学创作的内容(题目)应当避免功利性之目的,古人之作,其佳者“为自然及人生”,其劣者“美刺投赠”,然而“为自然及人生”者难,为“美刺投赠”者易,是故中材之士群而趋易。《楚辞》继《诗经》而兴,汉五言诗踵辞赋而起,唐五代北宋词承唐诗之后,皆是豪杰之士别开新途且无题者。总之,此论重点着眼于创作动机,称美豪杰之士之原创才力。而改定后的初刊本,其重点则在论述“题”的作用,“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之“题”与手稿本中“题目既误”之“题目”,内涵并不相同。
依常理言,“诗词中之意”即作者之意,能否“以题尽之”,取决于作者。如果作者本人善于拟题、制题,自可以尽其所想,做到题目与诗词本文内容的贴切一致。但王国维此处说的“诗词中之意”更多的应是作品本身可能具有的意义,它的有无、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与作者之意判然有别,而一旦作者已经制题,则读者的理解必然会受到诱导与规约。循此论述逻辑,作品有题,对于作品之意的丰富而言,非但无利,反而有害。《红楼梦评论》云:“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6](76)为了使一般读者不被“名之而已”束缚,诗词之题不必有,也无需有,这就如同一幅山水画,如果被题序之类的标签坐实为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不能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手稿本第37 则),则它作为艺术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两个版本中共有的结论“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一直被后人批评太过武断绝对,但回到各自的语境中,导致这一结论的原因确有差异:手稿本中的“诗亡”“词亡”,其原因在于作者相题而作、拟题运思,以致作品无兴致神趣,“不能佳”;初刊本中的“诗亡”“词亡”,其原因在于诗词之意蕴为题所限,读者失去获致无穷之意的自由,则诗词的生命必将衰竭⑧。
在标题的制约下,读者要自由地探寻作品之意,就平添了几分障碍,而标题中明白无疑的宣示,也会加强与文本的内部联系。当作品的整体性得以巩固时,“摘句”沦为曲解的风险自然也随之增多,静安对此当有切身体会,因为《人间词话》中摘句并对文意作引申者恰恰多出自无题的《诗经》《古诗十九首》与唐五代北宋词: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手稿本第1 则)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种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手稿本第2 则)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莫”之感。(手稿本第5 则)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所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手稿本第118 则)
以上几处摘句的出处,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诗经·秦风·蒹葭》、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诗经·小雅·节南山》、冯延巳《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皆无题,陶潜《饮酒》与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皆短题而似无题者,《饮酒》小序与诗意指向也无直接关系,王国维都能作出超脱原作之意的精彩解读,引向深广的人生感悟。特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三次摘引,却能服务于三个方向的评论旨向,正可说明,摘句脱离了原作整体,反而释放出阐释潜能。王氏自云:“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手稿本第2 则)其意即在于规避曲解的指责。设想一下,如果以上各作均有题目甚至是小序,详细交代了写作之缘起和旨意,那会给摘句者带来怎样的困扰。
对于读者而言,他通过题、序知道的作品背景越多,对其意旨的理解就越僵化,所得也越少。“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2](3877)的道理,王国维想必有自觉体会,他自己的诗词写作,既践行了这一理念,也受益于这一理念。其早期诗作拟题短小而含混(如《杂感》《偶成》《秋夜即事》《过石门》等),或者径取诗首二字标目(如《坐致》《平生》等),词作几乎皆无题,这些反而给予读者广阔的联想空间,试以《虞美人》为例略作说明: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15](657)
此为静安词中名篇,吴昌绶曾评以“深美闳约”[7](25),后世论静安词者也频加引述,尤其是下片末数句,常常被摘句称扬:“这种知其无益而终不抛其掷、已相诀绝而自赏自媚的一往不悔的精神,就使其既视人间为苦海而又难以自拔。”[16](324)佛雏更大加议论道:“‘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意决而辞婉,对某种人生悲剧而以审美的游戏态度出之,此‘镜中人’,作为这位‘簪花’者的‘理念’某一侧面的充分显现,是美的,故对之可以驱散人间的一切尘雾。此种‘坐赏’,虽是暂时的,却和‘镜中人’一道,取得在审美静观中一刹超时空、超因果的存在,又未尝不具有一种‘永恒’的性质和价值。”[17](145)可惜的是,这些理解均已脱离作者之原意了。据罗振常所说,“此词作于吴门,时雪堂(罗振玉)筑室姑苏,有挤之者设辞诬之,乃谢去。观堂见而不平,故有是作。”[18](85)幸好王国维并没有用题序,否则这样的写作背景只会弱化该词的艺术魅力,也会让末二句变得平庸而不值一摘。祖保泉在分析该词时,先肯定其“构思完整,措语绚丽,末尾两句形象生动,有直观美”,但在得知该词系为罗振玉抱不平后,又转而认定“这首词,立意有硬伤,便不足以佳作视之”[19](59)。我们可以原谅祖先生的反复,但这个例子也生动地反映出诗题、词题可能制约佳作、名句的生成。
四、从名句到名篇:“摘句”的衍生效应
在初刊本《人间词话》的第1 则(手稿本第31 则)中,王国维以“高格”与“名句”对举,认为脱离了整篇的名句也可以自有境界,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他发掘了不少遭前人忽视的名句。对王国维来说,名句本身在意义上是可以独立自足的,但后人却忽视了王氏推举名句的基本立场与目的,一厢情愿地将“名句”扩展至“名篇”。这种有意无意的误会,在有关纳兰性德词的评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初刊本第54 则)初刊本《人间词话》的词史论部分大体上以时为序,点评唐至宋末的多位词人词作,就是基于这种有限的文体退化观。王国维推崇五代北宋词,对南宋词,除稼轩外,几无恕辞,对宋末诸家之排击,更是不遗余力,元明两朝则是郐下无讥,不予置评。但他偏又评说了清词中的纳兰性德词,而且只评说这一家,似乎这位清代满族词人并不受始盛终衰文体退化规律的影响。静安对此解释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初刊本第52 则)也就是说,纳兰自有的天赋与清入主中原的时代共同造就了纳兰词超越规律的独特性,这和他批评南宋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手稿本第23 则)的话隐然相应。为了证明纳兰为“豪杰之士”,他还举出了例证: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初刊本第51 则)
本则依旧采用《人间词话》中常见的诗词对勘模式,如果按照这几句诗的标准寻找词史上的“千古壮观”,那“长烟落日孤城闭”(范仲淹《渔家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李清照《渔家傲》),“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水龙吟》)等庶几似之。可静安选择性地忽略了它们,单单拈出纳兰的边塞之作,真可说是用心良苦,因为和艳情、咏物等题材不同,边塞词在词史上相对边缘,“染指遂多,自成习套”的可能性也较小。翻阅清初以来的纳兰词评论,人们关注的都是其人之“深于情”,念兹在兹的是他的悼亡词、友情词,而王国维却独具慧眼,发现了纳兰在边塞词上的成就,也由此开启了后世研究纳兰乃至清代边塞词的路径,这些都好理解,可具体到对《长相思》《如梦令》的评价,情形却又有别。
孟洋详细统计了纳兰词入选清代至民初13种词选的情况[20](275),《长相思》只入选过1 次,《如梦令》从未有选家垂青,在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箧中词》和《艺蘅馆词选》都没选入二作,而它们分别选入纳兰词25 首与19 首。唐圭璋编纂的《词话丛编》汇辑了清代以降的六十多部词话,评及这两首词的,只有《人间词话》这一则。但随着《人间词话》在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走红,各种选本,凡选入纳兰词者,都会留意他的边塞之作,《长相思》与《如梦令》于是成为众多词选乃至文学教材的必选作品:钱仲联选评的《清词三百首》收纳兰词13 首,二作在焉;严迪昌选评的《金元明清词精选》只选纳兰词三首,也有《长相思》;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刊的鉴赏辞典系列在普及古典文学方面影响尤著,其中的《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收纳兰词20首,也有二作;一直作为高校古代文学教材而多次重印的朱东润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于纳兰词,仅选此二作;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说纳兰“长于写边塞北地风光”[21](620),并举出最有名的一首,即《如梦令》。在评析纳兰的这两首词时,各家对《人间词话》或明引,或暗用,这自然说明了《人间词话》的魔力。但问题在于,王国维只是摘引,只是从写出“千古壮观”的角度肯定这两个片段的名句特质,这与后来论著一味赞美二词为杰作不可混为一谈。
《长相思》(山一程)起笔写山水迢递,行役无尽,见出王事靡盬,至“夜深千帐灯”句忽然停顿,境界阔大壮丽,与前数句之倦怠疲惫截然相反,这或可许以某些赏析文章所说的“张力”。但词的下片写人,重又回到凄苦的思归状态,结以“故园无此声”,粗率质直。《如梦令》一调,例有叠词,这也是填写该调能否成功的关键,纳兰之作,前数句尚佳,至“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大是败阙,试与李清照同调名作中“知否。知否”“争渡。争渡”之精妙比较,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陈廷焯批评纳兰词有“措词浅显”[2](3828)的毛病,并没有冤枉他,它们恐怕也难达到《人间词话》中对“深远之致”(手稿本第8 则)的追求。然而,不少评论者对这种至为明显的疵累视而不见,致使相关评析流于肤泛。
得益于《人间词话》摘句的“名篇”也不仅是上面所举的清词,宋词中也有几例值得留意。
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初刊本第36 则)
周邦彦《苏幕遮》(按:王国维误书词调为《青玉案》)的上片写雨后初晴的盎然生意,下片写客居他乡的愁思,只有“叶上”数句咏荷。王国维以之与同样写荷的姜夔二词对比,来说明清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的能力,至于全篇如何,他并不关心。同样不关心该词的,还有古代许多的选家。刘尊明等人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评定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22](174)。据他们统计,在宋、明、清三朝的47 种选本中,这首《苏幕遮》只入选了5 次,而在20世纪以来的60 种选本中,入选次数则高达31 次。在评论方面,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收该词从宋代至近人的评论,在《人间词话》之前,只有周济与陈廷焯的两则,而自《人间词话》对其发表意见后,它的曝光率急剧攀升。20世纪后半期影响较大的几部词选,如《宋词选》(胡云翼)、《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唐宋词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宋词选释》(俞平伯)等在评注《苏幕遮》时都引用了这一则词话。又如初刊本第26则,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本就是《人间词话》中最受人瞩目的文字,其中摘引的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按:王国维认定其为欧阳修词)、辛弃疾《青玉案》三词在20世纪的传播以及各自名篇地位的确立,无疑也与《人间词话》的接受境遇休戚相倚⑨。
五、结语
王国维对名句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却漠视与句相对的篇,其偏嗜之因,盖在于句、篇二者与天分、人工的不同关系。袁枚云:“诗有有篇无句者,通首清老,一气浑成,恰无佳句令人传诵。有有句无篇者,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23](157)在静安看来,文学“为天才游戏之事业”[10](93),他又自负“得于天者独深”,所以在其词话中,屡屡流露出不屑雕章琢句的态度来。不少论者都觉得《人间词话》的缺憾之一是没有涉及词作的章法结构等内部话题⑩,从上面的分析看,他非不能为也,实不愿为也。
“流品别则文体衰,摘句图而诗学蔽。”[24](674)尽管有如此严厉的告诫,“摘句”仍然是中国古代诗话与词话最惯用的批评形式,《人间词话》既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也就势必要接受随之而来的质疑。然而,正如本文所努力说明的,它所采用的批评形式与王氏的文学观念以及词话的内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部文论经典当有助益;而从微观角度言,正是由于《人间词话》的摘引,不少原本无闻的词句才脱颖而出,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静安摘引的诗句大多是历代诗论中递相祖述、津津乐道的,而词作名句中相当一部分则为他首次拈出。
有学者在论及传统诗话中的“摘句”时说,这些“被摘句批评者摘取的诗句,都跟原诗脱离关系而具有独立自主的生命,而摘句批评者再加以批评又无异是在更新它的生命。……这就比让它留在原诗里,或只让它保持同一副面貌要来得有意义”[25](95)。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词话。正是因为有了《人间词话》的表彰,李璟“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名句方拥有了生生不已的生命和多样的面貌。就像朱光潜在摘句评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精义时早已指出的:“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26](35)说到这里,我们大概都会忆及鲁迅对朱光潜的讥讽。鲁迅对“摘句”的否定,颇为后人乐道,他顾及全篇与作者全人的读法肯定无可厚非,但非要说“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27](235),就有些绝对了,毕竟,名句的传播与意义增殖,主要是通过诗话、词话或“句图”、秀句集等的“摘句”行为来实现的。朱、鲁二人各自占据句、篇之一端立论,从学术史的后见之明出发,他们的分歧即便不能调和,至少也可以给论者多一重启示——古典诗词的特性让评论家们热衷于佳句妙语的评赏,摘句批评的载体与成果毋庸辞费。但在20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诗文评体式已趋没落,新的文学史著或选本通常以整篇为评量对象,如何才能合理借鉴摘句批评的历史资源,避免由句到篇的率意转接,确实是一个应当引起警觉的问题。
注释:
① 胡明《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王国维)往往用‘摘句’的手法来表达理论认识与美感觉悟,缺乏科学的精确性与理论说服力——这与他用‘词话’作为新理论的载体一样,同样是缺乏一种自觉突破的先进意识。”(《文学遗产》,1998年第2 期)黄霖等著《人间词话鉴赏辞典》:“王国维很重视词中的佳句,《人间词话》引录前人佳句作为褒扬,或者摘出拙句予以讥贬,书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这虽是词话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是《人间词话》这类情况非常突出,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句’的重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 页)
② 《人间词话》属稿大约在1908年夏秋之际,共计125则,其后,王国维选择其中63 则加以修改,并补写1则,连载于《国粹学报》,共计64 则。本文循学界惯例,分别称之为手稿本、初刊本。手稿本完整引用全篇的四首诗词作品分别是:沈昕伯《蝶恋花》、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和凝《长命女》、龚自珍《己亥杂诗》一首;初刊本完整引用全篇的见于补写的一则(排序第63),为元人散曲《天净沙》一首。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 卷同时收录了初刊本《人间词话》(邬国义点校,戴燕复校)与手稿本《人间词话》(邬国义点校),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对初刊本、手稿本的引用与统计均据此本,为免烦琐,仅于行文中注明版本及条目序号。
③ “章”作为结构单位,介于篇、句之间,这在《诗经》等作品中有直观体现,但后世诗话词话中提到的“章”,多就整部作品(篇)而言,因与本文所论关系不大,不再细分。
④ 王国维自作诗词实不乏刻意经营之作,他甚至自称“为制新词髭尽断”(《浣溪沙》),这与《人间词话》中标举的词论不尽相符,详参叶嘉莹《论王国维词》(《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1、2 期)中的相关论述。具体到“名句观”与实际的名句创造效果,其间自然也可能存在偏差。
⑤ 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 页)这种“神助”之句难以复制、模拟,就像皎然《诗式序》论及诗歌创作时所说:“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 页)
⑥ 钱钟书《谈艺录》第86 则引用西人瓦勒利之说:“作诗得句,有‘赠与句’,若不假思功、天成偶得者也,有‘经营句’,力索冥搜,求其能与‘赠与句’旗鼓当而铢两称者也。”(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60 页)前者可对应王国维所推崇的五代北宋词中的真名句,后者则近乎王氏所否定的南宋词中的伪名句。
⑦ 陈子龙《幽兰草题词》:“(南唐北宋词)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南宋词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他们所说的“高浑”“浑涵”,与《沧浪诗话》中的“气象混沌”可以互参;而历代词论中所举之警句(名句、佳句)显以南宋词居多,本文已有部分引证,不再备举。又,金应珪《词选后序》论“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时,就视“有句而无章”为“假托南宋”之游词的一个特征。
⑧ 林立在讨论清民之际的词体创作时,已注意到“无题与寄托”的关系,他引用了《人间词话》初刊本第55则,并释云:“一旦立了题序,一篇作品的生命便会因为被套上许多事实的枷锁而受到抑制,最终它亦由于缺乏自由生长或予人发掘的空间而步向灭亡。”见林氏著《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 页)。林氏同样注意到“被王国维以读者的‘用心’自由改造文意的词作,都没有题序”(第404 页)。因与本节所论关系甚切,附记于此。
⑨ 据刘尊明等人编制的《宋词300 经典名篇综合数据排行一览表》,晏殊《蝶恋花》排名第151 位,在宋、明、清47 种选本中入选6 次,20世纪以来的60 种选本中入选28 次;柳永《蝶恋花》排名第245 位,在宋、明、清47 种选本中入选3 次,20世纪以来的60 种选本中入选20 次;辛弃疾《青玉案》排名第40 位,在宋、明、清47 种选本中入选7 次,20世纪以来的60 种选本中入选31 次。三词在古、今悬殊的入选阵态与《苏幕遮》如出一辙。参见刘尊明、王兆鹏著《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174 页。
⑩ 《人间词话》中明确提及章法的只有手稿本第56 则,该则赞许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同时强调“非有意为之”,这也反证了“章法”常与“有意”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