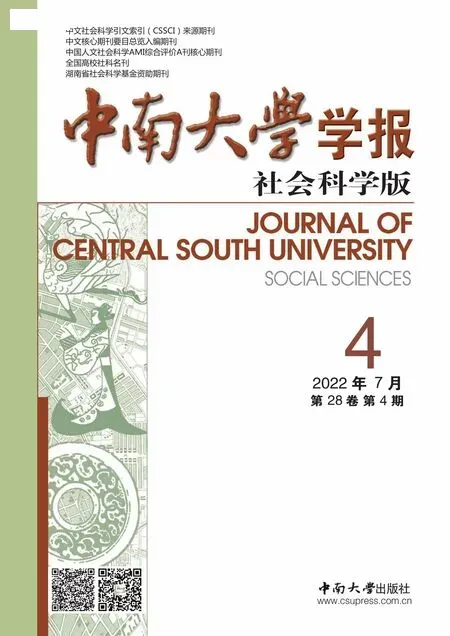王船山诗以达情论的理论特质
2022-11-23丁友芳周群
丁友芳,周群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46)
王船山以情为诗之本体,这已为学界公认,如黄保真等认为船山所说的“诗道”乃是一个以“情”为中心、呈辐射式结构的理论系统[1](178)。诗以达情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充分彰显出船山作为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儒家学者的社会关怀及易代遗民的诗道之悟,其内涵深广、托旨甚大。
“诗缘情”定型于六朝,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群体当中,出于不同的诗论思路或诗学诉求,诗情的内涵呈现出多义性。宋以前,阐释诗情的方向有两种,即汉以《毛诗大序》为代表的伦理之情,魏晋六朝以陆机、钟嵘等为代表的个体自然之情。宋以后,哲学领域对“情”有诸多研究与阐释,诗论领域的诗情说也得以丰富与完善。理学家及理学修养较深的文学家论诗多注重“节情”,强调个体人格涵养与诗歌情志的内在关联,如朱熹、陈献章、王廷相等。至明代中后期,建立在阳明学“心即理”价值基础之上的诗论则以“任情”为主,强调个体自然情感的真实与纯粹,如李贽、袁宏道等。
明国难降临后,作为明末遗民、清初大儒,王船山在亲历明末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及国破家亡之后,提出诗以达情论,自有其特殊的意义赋予,它既不完全符契于理学家的“节情”,也与晚明以来的“任情”有着内涵与境界的不同。长期以来,对王船山的诗论研究,尤其对其诗情的解读,多强调审美意义①。此种阐释路径一方面易将审美与政教对立,忽视儒家诗论在历史流变中内涵不断丰富的事实;另一方面忽略了船山的儒者学术旨趣,使其理论特质得不到较为完整的揭示。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船山如何建构诗以达情为核心议题,结合其儒学思想及文化关怀,兼顾时代与个人体验,揭示其诗学思想中独特的思维方式、浓厚的文化使命、强烈的情感诉求及其诗情所具有的文学乃至文化价值,使船山的诗学研究更深入也更契合船山本意。
一、儒学性情观:诗以达情的学理特质
船山的诗以达情即达性之情。性情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它主要为哲学范畴。传世文献中,《诗大序》首次将性情应用于儒家诗论。至南朝发展成为以个体情感和审美体验为内涵的性情说,完成了从哲学领域向诗学领域的转变,并逐渐从儒家诗论拓展为普遍的诗论共识。而后,宋代理学家对性情做了充分阐发,性情从此成为儒学家和文学家通用的重要诗学术语。明人以性情说诗极为常见,但不同身份的言说者,其性情内涵有所不同。船山以接续理学为其学术旨趣,其诗论的性情说与明代理学家以性情论诗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作为理学文论家,其诗论多有体道哲学的思维路径,在诗情体系的建构中,其儒学性情说为其诗情论建立了学理根柢,体现出天地万物为一气化生的哲学精神。他作为理学文论家,在诗情体系的建构中,以儒学性情说为学理根柢,呈现出体道哲学的思维特征。
(一)诗学之情与哲学之情的逻辑同构
船山身兼哲学家与文论家,其哲学和诗学对“情”均有较多论述,参照两处论述,不难看出其哲学思维和诗学思维在逻辑上的同构性。
哲学上,船山论情的生成稍异于宋儒。宋儒认为心统性情,心之体为性,心之发用为情,或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情一于心。船山虽也认为已发为情,但他重在强调情与性均源于太虚之阴阳,情之生并非性之感物而动。其言:“情元是变合之几,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也。”[2](1068)又说:“变合之几,成喜怒哀乐之发而为情。”[2](1071)与宋儒相比,船山讨论情时弱化了心体的意义,而强调阳变阴合之几,更注重在天地大化的动态变化中讨论情感的生成,将宋儒立足于心体来讨论情扩充到在天地宇宙的变化中来论述情。关于情之生成过程,其言:“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则必不可。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在外,不纯在内,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2](1069)情之产生重在“几”,是吾心之几与物之几相取相引,相互作用,非独在我、非独在物。此情感之生成既不同于传统的感物生情论,亦稍异于理学家所建立的“以情应物”的心物关系。前者强调人心“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3](3327),侧重外物的感发作用;后者如“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4](237),强调我心廓然,物来则应。船山这种心物交合而生情的说法既关注我心之动,又强调外物之感,破除了情之生成的主客对立,消解了情感生成的主体性,这种心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
思维方式本身具有某种独立性,在诗学中,船山论诗情之生成也体现出同样的思维模式。在《诗广传》中,其言“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5](323),他认为情的根源在阴阳之几,有内情之生,外物必不可少。“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响而执之有象”[6](736),在诗情生成中强调心物的往来互动。情景论是船山诗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情景关系中,他十分注重二者的互生性,其言“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7](814),在诗情的生成中,心物互生,情景互藏其宅。类似表述如“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7](824),“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6](749),重情又重景,将情景作为二元主体来论诗情的生成,强调情之生成不离内外。其宾主说亦强调心物的融合,其言“若一情一景,彼疆此界,则宾主杂沓”[8](1012),消解了物我的主客对立,强调情生于心物相合之中,与其在哲学上消解情之生成的主体性说法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萧驰先生曾谈到船山的宇宙生命与诗之生命是两个对应的符号世界,并从话语“语法”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比较[9](72),此亦证明了二者在逻辑上有某种同构性。
另外,船山诗学中的节情论与其儒学工夫论亦有逻辑上的同构之处。就心性论来看,同宋儒一样,船山也肯定情之存在的合理性,但亦认为“性善情恶”。“性善情恶”的观念在汉唐儒者当中已有所体现。在宋代儒者当中,温和者如二程强调要涵养人格于情之未发之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10](201);极端者如邵康节,“情之溺人也,甚于水”[11](179);朱熹与陆九渊均有节情说。船山承祧宋儒,认为情是道心之用,亦是性恶之源,故需存养、省察,因此“节情”“治情”等在船山的道德修养中常被提及。他认为性恶虽源于情,但“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2](1072),道心唯微,为善则非情不为功。因此为了为善去恶,他提出“于不睹、不闻之中,存养其仁义礼智之德;迨其发也,则若决江河,莫之能御,而天下之和自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而人心自听命焉”[2](1145)。在情感未发时,辅以存养工夫,待其发时,人心便听命于道心,情自然得到调节,导向善之一面。当情感已发之时,“则必于动几审之:有其欲而以义胜之,有其怠而以敬胜之,于情治性,于人心存道心”[2](1146)。也就是说,要注意情感最初发动之几,在此几上努力做省察工夫,判断此情之善恶好坏,使性行情中,情趋于善。可见,就心性论而言,船山在情的问题上,同宋儒温和派一致,注重情之未发之前个体的人格涵养,同时也注重对已发情感的省察。在船山诗学中,类似这种“节情”的观念十分常见。如《诗广传》之“导情论”言:“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5](332);“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5](342)强调情之可善可不善,应当“审情之变”“慎乎治情”。这种工夫论视域下的道德修养逻辑在诗情中的运用,自是不言而喻的②。如“恶其迁性以就情”[5](327),即离性则诗情不贞,恶情将起,这和心性论中恶之生成论相同。又说:“审乎情,而知贞与淫之相背,如冰与蝇之不同席也,辨之早矣。”[5](328)这和情之存养、省察工夫如出一辙。另外,有学者还谈到船山诗学中的“忍”亦是一个从哲学心性之修养到诗学性情之调控的范畴[12]。可见船山诗学节情论的哲学修养论之基础,这种节情观与晚明以来文论家的“任情”有着本质的区别,体现了船山诗论的理学底色。
(二)哲学性情在其诗学性情中的展开
除了逻辑上的同构外,船山的诗情亦有对哲学性情的展开与延伸之处。
其一,“性情”的内涵在其哲学与诗学中有共通性。在船山的心性论中,情关涉道心与人心,其功能在于显现道心。他说:“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2](1068)“惟性生情,情以显性,故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2](475)道心即性,性在船山哲学中内涵复杂,其义有二:①人之本源之性(人之所以为人的常道)本于天道,可视为道德理。②具体的个体人性,人之本源之性随着形质不同,所秉承的气和凝聚于气中的理随之不同,由此形成了具体的个人之性。二者是“一本万殊”的关系,人之本源之性是“一”,是道德原理;个体之性是“万”,在实践中各有不同,且需“日生而日成”[13](300),即具体的个体人性需要后天习成。
在诗学上,船山的诗以达情即达性之情,亦即情以显性。其“性”既可以指源于天道的人之本源之性,也可以指具体的个人之性。其言:“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14](1440)诗言情,即言人性之情;诗情桎梏,即人性得不到充分展现。同时,性中有天德、王道等,此必由诗自身来表现,此处诗之性情当与天道相通,指人的本源之性。船山还以诗情论作者之品性,曰“言情诗极足觇人品度”[6](806),评简文帝“顾有艳字而无艳情”[6](793),庾子山“性正情深”[6](820)。此等论说均表明诗情与诗人品性的关系,即以诗情来观诗人个体的人性。另外,船山诗教的发挥亦落实于性情上。他说:“盖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6](677)此乃船山个体人性需要“日生日成”的哲学理论在诗学中的展现。船山诗学上的性情与其哲学上的性情在内涵上有相通之处,诗中之性既可以为天道之性,也可以为诗人个体的人性,而个体的人性需要后天习成则是他的诗教观的理论基础。他将哲学性情观延伸到了诗学中,为其诗学建立了理论根柢。
其二,船山的诗情与天道相通。在诗学中,船山有导情论的主张,然诗情要如何导?船山言:“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无不章。白情以其文。”[5](300)导情之法虽多,从根本而言,要性通方可情顺,情顺即可文成。情生于性而达于文,性通即可成文。如何才能性通呢?船山又说:“而神顺于性,则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为以天道养人也。”[5](300)以天道养性,使阴阳变合顺于性,可使情不滞塞,诗文可成。由此,从天道到诗文便生成如此逻辑:以天道养人—神顺于性—性通情顺—白情以其文。诗文达情,即达人性之情,人性出于天,故而诗之性情亦出于天,也即诗文所达之情,通过性这一中间环节,最终与天道相通。此外,他还数次强调与道同情:“君子匪无情,而与道同情。”[5](310)“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5](310)
可见船山在追溯诗情之源时,强调诗情与天道的接洽,这与大多数理学家认为的性本于天相同,如薛瑄认为“此心惟觉性天通”[15](1617)、湛若水认为“人之性情即天地之性情”[16](619)。只是理学家性情通于天道的思路未曾在诗学中很好地展开,似胡居仁“诗有所自乎,本于天,根于性”[17](39)、吕坤“天机自流,诗人之真味”[18](93)这类说法不多。而船山将哲学性情延伸到诗学层面,既为其诗情论建立了天道之论证,也使其诗情观超越了传统的审美意义,具有较强的哲学色彩,更有助于去掉传统儒家诗论的言志与政教标签。
二、现实关怀:诗以达情的济世特质
船山的诗情论原非对多数文论家之诗情观的泛泛继承,其诗情基于现实思考,源于对明代文学现状的批判与反思,而归于诗教的实现,有着极为厚重的政治价值,体现着遗民士大夫的现实关怀。
其诗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晚明的经世思潮并不同调,像黄宗羲“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19](203)这类诗文不离经术的言论,在船山诗论中不多见。相反,船山认为,“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6](769),还说“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7](807)。他并未趋时顺俗,响应复古风尚,而是在明代文学现状的基础上,经过反思与批判后形成自己的诗论观。于船山而言,以诗观政本质上即以诗情观政,其诗情关涉世运、国运及世风人心③,反映治乱兴衰。在他看来,明季诗风的率性任情或深幽孤峭,实在是士习乖离、世教陵夷的表征。他反对骈俪弱靡的文风:“崇祯间,齐梁风靡,骈俪为虚华。……数十年之士风,每况而愈下;其相趋也,每下而愈况。师媚其生徒,邻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隶,友媚其奔势走货之淫朋。”[20](122)他认为,“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吟舌娇涩,如鸲鹆学语,古今来无此文字,遂以湮塞文人之心者数十年”[7](849),表达了他对晚明因诗风湮塞人心的不满。他对明代诗派林立的现象尤为不悦,认为一立门庭,便无性情,“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7](831)。他中年以后对竟陵派深恶痛绝,认为其诗情酸俗,陈广宏先生指出这“有自己(船山)成长过程中的切肤之感”[21](316)。陈先生还关注到竟陵派在晚明党争事件上有严重的立场问题,而船山曾指责竟陵派“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6](617),认为竟陵派上结品行不端的汤宾尹,下育祸国之首马士英,以致宗社丘墟。他对竟陵派的批判有很大部分是根于政治立场,其现实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他以诗情征世运之几、国运之兆、人心之象,无疑有着明代社会现实的针对性,是基于明季士风乖戾之象、根于明末社会风气与明亡的经验事实的,是一种对政治、世情与诗情关系的深刻洞察之表达。
作为一名以存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船山并未止于对时代疾疴的反思与洞悉,他对社会文化有着全局的胸怀和强烈的救世愿望,“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22](1050)。这种匡世教、救君父、存人道的淑世情怀让船山对诗寄予厚望。首先,船山所倡导的诗情与晚明正面歌颂自然情欲、私欲,倡导人生而有情的“真情”“性灵”有着本质的区别,“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5](325)。诗之言志达情,应言大欲、达公意,表达天下民众的共同欲求、社会生民的共同意志,而非一己之私、一人之欲。其次,他认为诗教是乱世拯救世道人心的重要方式,“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23](479)。又说:“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5](326)他认为诗教可以导人清贞、去人顽鄙、正人品性,还认为“不善说诗,而率天下以祸人道也有余”[5](449)。他在诗论中屡屡谈及诗教,重倡兴观群怨,在《明诗评选》中尤推崇明初诗人,因“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7](832)。
船山并非泛泛重弹传统老调,他切实关注诗教如何实现,并将诗教落实在诗情的传达上。他反复论述诗教与诗情的关系:“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7](829);“盖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6](677);“情事尽见。闻之者足悟,言之者无罪,此真诗教也”[6](784);“《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6](644)船山几乎将诗教等同于诗情,明代理学家以政教阐释诗歌性情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就政教如何实现来说,除了焦竑与顾宪成重申讽谏传统外,其他理学家多注重个体情志修养及心性与诗境的贯通④,这种重哲思理趣的提法具有某种形而上的超越性,似乎唯理学家所可至。船山则将诗教直接与诗情关联,淡化诗情与个体心性修养的关系,只强调诗情的雅正风貌与起兴功用,认为诗情要“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8](893),要做到“君子与君子言,情无嫌于相示也;君子与小人言,非情而无以感之也。……将欲与之言,匡其情而正之”[5](353)。船山的诗教是以诗情来感化人心,诗之动人,即是教化的实现。无论是提倡“诗不关世道,即千万语,皆赘也”[18](93)的理学派,还是诗歌要“劝谕箴贬,以一归于正”[24](911)的经世派,以及倡言作诗要“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25](786)的复古派,他们在承担经世责任、以诗助益教化上,如船山这般具体到可操作者,鲜矣。船山这种诗教观所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表明船山想要给出的是真正能救世的良方。
船山的“诗情通于诗教”与冯梦龙的“《六经》皆以情教”[26](3)有着本质区别。船山对诗情有其个人化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他对诗歌情感状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极为看重,而对诗歌传达的情感志趣则有所宽宥,如他对艳诗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认为若“艳诗不失风骨。雅者自雅,不问题也”[6](808)。他对诗情品性的衡量,看重的是情感风貌而非诗情类别。鉴于此,他提出“念深礼谨,洵大雅之章”[14](1273)的诗情理想。“念深”即诗中之情要真切感人,“引性情以入微”,能够“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使诗之教化进入人心,对人的情感有所导向。“礼谨”即诗情之质与度,诗以达情,非无情不达,亦非无所限度。他力戒情之浮华与淫溺,说“浪子之情,无当诗情”[6](753),对情之贞、淫有泾渭之分,并深恶诗之高谈无情、啼号饥寒之气。“洵大雅之章”表明船山对传统诗学理想的回归,“雅”是其论诗的重要词汇,亦是其评诗的重要标准,其《明诗评选》以“雅”论诗凡见87 次,《唐诗评选》凡见32 次,《古诗评选》凡见75 次,远远高出其他诗评词汇。故船山的诗教重在以诗情化人,他期望以雅正之情来纠正社会人心的乖戾与浮躁,这与以往主张诗歌劝诫讽喻及空倡诗教者不同,船山的诗教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有效性,反映了国破家亡之际士大夫对诗歌能够发挥的社会效应所作出的理性思考与价值期许,其中体现出的伟大而深沉的文化情怀与承平之世的诗论家相比,自不在同一境界。
船山将诗情的价值等同于诗教,并以诗情观政,以诗情来承担反映治世、乱世的安乐与怨怒之责,将诗教重任落实于诗情之上,以诗情之深、之雅来保证诗教的有效实现,以期匡正世风,影响国运。如此一来,诗情既是他现实关怀的具体体现,又是他匡时救弊的途径之一,其诗情已然在发挥着诗教的功效。他这种将诗情与诗教关联的思考方式与传统儒者对诗情的态度大为不同,不仅提升了诗情的价值,更扩展了诗教的内涵,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文艺观念。
三、诗道之悟:诗以达情的诗道特质
船山的诗情论除了以其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明末社会现状为生发之源外,易代兴亡的生命体验及诗艺体味促成的诗道之悟则是其诗情建立的内在动力。
崇祯十七年(1644),船山父子三人百死千难,终于逃过农民军的劫难,却又闻得庄烈帝殉国,年仅26 岁的他又接连遭遇骨肉亲人相继离世,国破家亡的激变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沉痛的伤害,他涕泣数日不食,并作《悲愤诗》。往后在抗清、流亡与退隐中,又不断加强了其情感上的失望与哀痛,短短几十年的人生,他的精神厚度、情感浓度与生命体验的深度已胜过百年承平。故此,他对悲伤之情有着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在《读大学大全说》中,与朱子辩心体境界时,其言:“即忿懥等之‘不得其正’者,岂无事无物时,常怀着忿惧乐患之心?天下乃无此人。……忧宗国之沦亡,覆败无形,而耿耿不寐,亦何妨于正哉?”[2](422)他认为若心中常怀忿懥忧患之情,并非表明此人心体不正,在日常生活中,原不存在心中无忿懥忧患之人,若因宗国沦亡、江山覆灭而日夜不安、耿耿不寐,依然不妨碍其心体之正。船山看似在与朱子辨析理学心性问题,其背后却蕴含着他切身的情感体悟。他将忧患恐惧、忧国忧民之情纳入理性境界的思考,并提升至哲学高度,可知他对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家国兴亡之情有着深度的哲学思考。此外,他时常直言自己的悲伤,如“‘人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魂棲于阴,魄荡其守,高天不能为之居,杲日不能为之照,呼吁沉浮而大命去之。……如蛛丝之萦蝉翼,勇迈以胜之而不克,清涤以离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婴者鲜矣。……则心死而身亟随之,何所容其幸免哉”[5](459-460)。再如“物必有不可复阳者,而况仆乎?颓然任之而已。……数年来俱以一泪而绝。近则两耳皆聩,杜鹃啼屋后树,亦不复闻”[7](873)。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悲凉与哀痛之情,并对个体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幻灭感,可见家国兴亡的悲情,在船山生命体验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
船山在读诗、评诗中对诗情亦深有体会。在面对古今诗人诗作时,他常常在具有悲剧色彩的诗人或悲伤的诗歌中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取向多半与其自身的体验相关。如评刘琨:“无限伤心刺目,……乃使古今怀抱,同入英雄泪底。”[6](598)船山对刘琨饱含相惜之情,自为墓志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20](228)刘琨曾积极筹划北伐中原,志枭逆虏,然事功未成,卒至于败。船山也曾起义衡阳,不久即败;也曾仕事永历,志于恢复,却陷入党争,险些丧命。其“千古英雄无死处,酒徒高唱感夷门”[27](297)的心迹与刘琨的忠义与孤愤何其相似。报国无门的无奈,只剩下泪尽英雄气的悲凉。又如评庾信“泪尽,血尽,唯有荒荒泯泯之魂,随晓风残月而已”[6](561)。船山多次表现出对庾信的偏爱,如“庾信江南老自哀”[27](619)、“庾信长哀江南春”[27](578)、“凄凉庾信江南赋”[28](774)。庾信由南入北,先后侍萧梁、西魏,后又亲历梁亡魏灭,国破家亡之情与船山相通,与其说“荒荒泯泯之魂”是在说庾信,不如说是借庾信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再如评杜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此等题,于‘丹心’‘碧血’‘日月’‘山河’‘哀草’‘夕阳’外,自有无限”[8](1128)。船山有《南窗漫记》,专录早岁与各先生士友往来唱和的残诗碎句,而他们多于国破城陷之时愤世而死,船山大概由此诗忆起故友,感其丹心碧血之情,悲其香零玉碎之境。再如评唐末郑遨《山居三首》“三首一百二十字,字字是泪,却一倍说得闲旷和怡,故曰诗可以怨。……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8](1044)郑遨乃唐末隐士,感于天下大乱,入山修道,数次辞诏于五代统治者,诗中有“祭庙人来说,中原正乱离”,描写唐末五代天下板荡的情形,其境况与体验,大概引起了船山的共鸣。船山太易为悲情所动,他评诗屡屡言及“悲凉生动”“悲思无限”“悲凉有体”“大雅之哀”“府悲神旷”“悲乃以至”“悲不以泪”“荡魄伤魂”“悲江左无人,中原沦陷”,此种悲情之语在其诗论中甚多。他曾自言“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27](817),可见,怀着国土沦亡之情在山中漫长的孤寂时光中,他通过读诗、评诗,切身体验到了古今无数悲苦心灵的痛苦与悲愤。相似的境遇,相同的心境,在诗中,他恢复了这些历史人物鲜活真实的情感面貌,而他们也抚慰了船山,治疗了他的情感创伤,还为他抒发自己明社丘墟、世教陵夷的悲愤之情提供了艺术表达的摹本。
在强烈的情感诉求中,船山在诗歌创作上亦投注了不少心力,他也由此深诣诗道三昧。他十六岁始学诗,一生不废吟咏,四十三岁时,他对诗歌艺术已颇有领会,其论诗言:“有时寂寞坠闲云,忽尔如惊舞鹤群。陆海潘江皆锦浪,易奇诗正各丹坟。无劳粉本摹春雪,一尽零香酿夕醺。肉眼不知看活色,寻苔捕草漫纷纭。”[27](570)他在诗思、诗歌风格及诗材选取上均为深谙诗道者。他曾自述学诗历程,“余年十六,始从里中知四声者问韵”,中经乡人、叔父、复古派、竟陵派,最终尽去所学,至五十一岁自悟诗道,“乃念去古今而传已意”[27](681)。六十三岁,在《广哀诗》序中,其言:“夫之自弱冠幸不为人厌捐,出入丧乱中,亦不知何以独存。……德业、文章、志行,自有等衰,非愚陋所敢定。抑此但述哀情,……杜陵《八哀诗》,窃尝病其破苏李陶谢之体,今乃知悲吟不暇为工,有如此者。”[27](459)在历经半生丧乱,体验过深广的哀情后,他不仅深刻理解了杜甫的《八哀诗》,更体味到“悲吟不暇为工”的情感抒发即使突破温柔敦厚的平和之度,亦不失为风貌动人的诗歌精品。可见赋诗、悟诗贯穿于船山的一生,而随着情感体验的加深,他对诗道的体悟亦日臻完善,“去古今而传已意”的开悟之言乃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转为对诗歌艺术体认的呈现。
他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他对诗道的体悟。在《续落花诗》序中,他说:“拾意言以缀余,缓闲愁之屡亘。夫续其赘矣,赘者放言者也。意往不禁,言来不御,闲或无托,愁亦有云,是以多形似之言,归于放而已矣。”[27](569)其赋《续落花诗》志在拾意放言来缓解连绵不绝的闲愁,实际上该组诗以落花寓亡国之思,而非一般闲愁。在《广落花诗》序中,他说:“迹所本无,情所得有,斯可广焉。……荣悴存乎迹,今昔存乎情。广落花者,言情之都也,况如江文通所云‘仆本恨人’者哉!”[27](574)言明其《广落花诗》志在言情,所言者即兴亡之感、故国遗恨、今昔之悲、人世幻灭,此类情感深埋于心,不可不广。船山对“广”似格外钟情,除了《广落花诗》,尚有《广哀诗》《广遣兴诗》《诗广传》等,他虽只在《广落花诗》序中提到“情所得有,斯可广焉”,但据此亦可推知其“广”即疏泄充溢的情感。结合船山整体诗歌作品来看,其“拾意”及“传已意”主要是指传达自己的情感。其情主导着其诗歌创作,且他能够在情感的调配下自然遣词造句,实现情感真切流露之目的,故而其诗作多是“意往不禁,言来不御”的产物,有情之所至、不得不发的意味。与其他理学家诗作相比,船山诗歌较少有持敬工夫对情感的节制,也不以传达德性义理或心性涵养为主,而带有显著的时代苦难之印记,或言报国之志、倾厦之危,或道隐居之心、汗青之愿,或表达道丧之痛,或发明贞骨之志,时而长歌当哭,间或低吟自嘲,展现出来的精神人格带有易代浓郁的悲情色彩,而其兴亡之感亦在诗歌创作中得以缓解。同时,其诗也突破了他在诗论中提倡的节情或和平温厚的诗学旨趣,呈现出慷慨不平、激越愤懑或忧愁怨抑、凄切哀鸣的真实情感状况。这说明船山在诗作中并未完全遵循自己理性思维设定的诗学理想,而是以情感为导向驭辞立意。故而其诗以达情论不只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诗学观念,更是苦难的灵魂在个体情感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评诗、写诗所形成的一种对诗歌艺术的内在体认。
综上所述,诗以达情是船山生命体验和艺术体悟共同促成的诗学观念。在易代之际,在深悲巨痛的情感笼罩之中,诗学于他而言,有着疗伤的作用。他在穷岩荒谷中读诗、评诗、写诗、悟诗,慰藉经史之外的枯寂时光,诗学支撑起其情感生命的同时,也促使船山成为伟大的诗人与文艺家。他以毕生的生命体验为素材,在体悟前人诗作的基础上,于自身创作实践中深悟诗道,并由此形成诗以达情这一旨意杳远、寓托深重的诗学观念。
四、结语
船山的诗情观念,其重要价值首先在于对儒家文艺观的丰富与拓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儒家文艺观素以言志载道与美刺教化著称,诗缘情似为审美文学观的专属,这其实是一种将审美与政教对立的思维,亦容易将儒家文艺观固化与标签化。事实上,儒家文艺观并非排斥情,只是其合法性多建立在先验的“性”之范畴下,概因情感过于复杂幽微,而文艺又实在化人易深,出于对社会整体民情世风的考虑,汉唐儒者对诗情十分慎重,一般不轻言诗缘情。随着宋儒在理学上对情之探讨的深入,诗道性情则成为儒者论诗的普遍倾向,然整体上仍保有以“性”定情的伦理或道德含义。船山亦复如是,他虽倡言诗以达情,但并未偏离儒者论诗底色,无论伦理之情、道德之情还是性理之情,均被其诗学所倡导和坚守,并且他摒弃了阳明心学思潮下的自然任性之情。但船山论诗情又确实与一般儒者有所不同,他以情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将诗教的实现落实于诗情之上,在诗论中反复倡导诗以达情,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践履之。而其所抒之情又完全突破了理学家和平温厚的诗歌理想,天地间的巨大悲伤,生命中的疼痛体验,历史的悲剧,文明的苦难,这些哀而伤、悲而淫的非伦理、非道德的个体心灵之情,均被船山囊括于其诗情之中,在情的厚度与广度上远胜于此前的理学家。确切言之,船山在坚守儒学价值的前提下,丰富了诗情含义,强化了其寄托旨意,这无疑扩展了儒家文艺观的理论内涵,也提高了诗缘情在儒家文艺中的地位与价值。
另外,诗以达情的诗学观念,既是船山个人的,亦是时代的。它不仅体现出一个传统儒者对诗学本身的思考与领悟,更是一位全力求真的学者面对现实深入探求的结果。诗缘情产生于审美语境中,最终在特殊的易代之际被儒家学者接纳并予以提倡,这表明文学有其时代性,儒家文学尤其要面对现实。对于经历了易代之痛的遗民来说,历史的走向、个人的境遇、理性的思索与现实的困境所造成的情感及思想的激荡与冲突极难让人持守和平温厚的君子之度,而如船山这般一腔悲愤、忧思深重甚至偏激过火而毫不掩饰自己铮铮骨气者,尤其如此。只要敢于直面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文学这种以人的心灵为书写对象的艺术形式中,纵情放言,突破和雅温润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船山诗学让我们感受到他面对自己的时代曾跃动的情感与精神,而那些深层的思考、深情的关切与深广的悲愤也都体现在其学术中,呈现于他的诗学里。他对文学的思考是纷扰多变的苦难现实激发与促进的结果,他的诗学既是个人的价值追求与情感寄托,也是时代社会缔造出的文化成果。
综上所论,王船山的诗情论统合了其哲学思想、现实关怀及文艺思考,诗情即天道、世情、人情,诗以达情,即诗言天道性情、言世道人心、言人情悲苦,体现了诗学与哲学的互渗,诗道与世道的互涉,诗艺与人情的互生。他以天情顺性情,以性情正人情,以人情正诗情,再以诗情匡世情,构筑起上通天道,下关人心,中连朝政的诗学拯救体系,实践着他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文化所应承担的责任,体现出亡国士大夫的历史使命感。同时,在国亡世乱的特殊历史语境中,他以诗学支撑着自己的情感生命,在乱世的悲怆与历史的苦难中,达到了遗民诗学的顶峰,为传统文学与文化贡献了重要内容。
注释:
① 21世纪以来,代表性著作如陶水平《船山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强调船山诗论是“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 (第9 页),该书以诗学范畴为纲,重点论述了船山核心诗学观的儒学立场及其美学化色彩。再如崔海峰《王夫之诗学思想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则提出船山的“政治立场与诗学观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6页),还认为船山的“诗学不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第16 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再如袁愈宗《王夫之〈诗广传〉诗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亦以船山诗学范畴为纲,重点阐释其诗学观念的美学含义。再如刘克稳《王船山诗学内在矛盾性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阐释了船山诗学教化功能与抒情审美之间的矛盾,认为诗之用在政教,诗之体却在审美。我们结合萧驰先生的论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船山的诗学审美理想源自理学,刘氏的体用矛盾之论有待商榷。还有曾守仁的《王夫之诗学理论重构》(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该书在诗学和美学视域下集中阐释相关范畴,揭示船山美学、诗学思想。目前船山诗学或美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范畴论,或对其进行美学阐释,或挖掘新的范畴,这种研究思路实际上与船山自身的学术旨趣已有所偏离。近来有学者试图改变,如陈勇《王夫之诗学考论》(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以文献学与文学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船山诗学观。又如匡代军《船山情感论诗学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以文化诗学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船山诗学深植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不再对船山诗学进行单纯的审美研究。
② 蔡英俊先生曾详细论述过该问题,参见其《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341 页。
③ 船山对诗情与世运、国运及士风人心的关系论述较多,如以诗情观政,其言:“诗之情,几也;诗之才,响也。因诗以知升降,则其知乱治也早矣。”“诗有际。善言诗者,言其际也。……治乱之际,诗以占之。”“善诵诗者,……即其词,审其风,核其政,知其世。”(《诗广传》卷四,《船山全书》第3 册,第479、458、474 页)。再如对诗情与国运的关系,其言“周以情王,以情亡”(《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3 册,第342 页),“情已枯,智已槁而后国家随之”(《诗广传》卷四,《船山全书》第3 册,第475 页),“以欲为乐,以利为良,民之不疾入于乱者几何,而奚望其有固情哉?……崇利以求欲也,不知所止,国之不亡、幸也”(《诗广传》卷二,《船山全书》第3 册,第363—364 页)。可知船山极为重视民众之情对朝政兴亡的影响,他认识到亡国不只是政治失误,更是社会普遍情感之失控。对诗情与世风人心,船山亦有论述:“駤戾之情,迻乎风化,殆乎无中夏之气,而世变随之矣。”(《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3 册,第303 页)还说:“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禂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船山全书》第15 册,第841页)。他认为,元、白之诗,情感表达不正,多闺阁妖冶之情,蠹祸人心,败坏风俗。又说不肖者言诗赋则“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贼民”(《宋论》卷四,《船山全书》第11 册,第133 页)。
④ 关于明代理学家以政教论诗的情况,参见刘洋:《从性情说看明代理学家诗法论的多重向度》,《文学遗产》,2021年第2 期,第119—1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