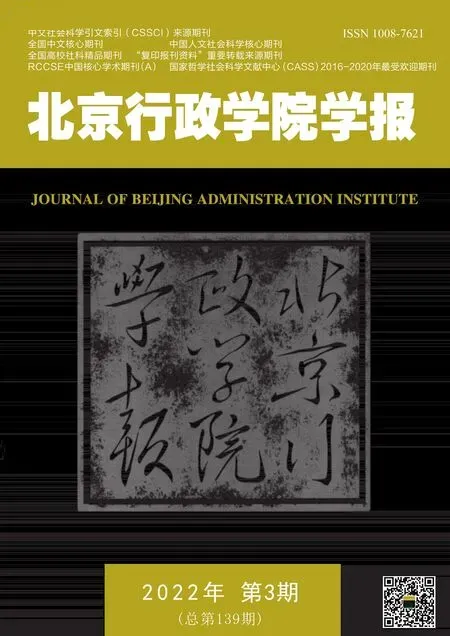晚明社会文化语境下士大夫对西学的接受
2022-11-23高胜兵
□高胜兵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引言
近代的梁启超和张之洞等人使用“西学”一词来指称来自欧美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晚明,徐光启曾把利玛窦传播的知识分成:神学和哲学;几何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李之藻的《天学初函》一书则将“西学”称为“天学”,内容分成天主教知识的“理编”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器编”两大部分。本文所谓的“西学”既指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也指来自欧洲的有关天主教的宗教文化知识。
面对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西学,传统的晚明中国人是怎样回应的?这里所谓对西学的“接受”(reception)①“接受”一词源自对“接受美学理论”的启发,该理论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由德国的文艺理论家们提出,倡导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必须注重研究读者接受的过程——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强调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对文学意义的完成和文学史的构建至关重要,认为读者不只是被动受影响,而且还有主体性的选择和阐释。,是指晚明中国人在接触西学时对西学的主体性理解和认识,即由于受到本土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他们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基于自身的主体性对外来西学在内容上的过滤和曲解,从而产生了“认同”或“排斥”的态度。需要说明的是,晚明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根本原因有两个:其一,传教士推行的主要是“上层传教路线”,所以晚明时期直接接触西学的人大都是士大夫阶层。其二,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晚明中国士大夫阶层影响和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代表晚明中国的整体态度。本文将基于晚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分别从自然科学和宗教文化两个方面分析晚明中国对西学的接受史实,并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阐释西学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接受规律,倡导文化交流应该秉持开放和多元的理念。
一、晚明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接受
史料表明,晚明有不少士大夫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并且采取了鲜明的态度或排斥反对或认同接受。
(一)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排斥与不屑
面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和器具,晚明中国士大夫大都觉得新奇,但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利玛窦曾记载: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1]181。
史料表明,由于没有对西方天文历法和科学技术的深入了解并受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有一些晚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的天文历法和科学技术表示了反对和排斥,这些人也往往都是强烈反对天主教的,例如晚明著名的反教者沈榷①“榷”字原文为“氵”偏旁,不是“木”字偏旁。字库缺此字,因此本文跟随大多人的写法,用“榷”字代替。、许大受、魏濬等,他们较少从西方科技的实用性考虑是否引进,而是更加着眼于是否符合中国的道统,是否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华夏秩序的稳定。比如沈榷认为,西历危害大明的纲维统纪:“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义而来,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体,不异乎中国?臣犹虑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况诞妄不经若此,而可据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乎?”[2]61对于西方器物,沈榷认为它们怪诞迂阔,与中国远古和现有的器物相去甚远,他说道:“即所私创浑天仪、自鸣钟之类,俱怪诞不准于绳,迂阔无当于用。尝考尧舜之世,有‘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法。历代相传,有铜壶滴漏以测晷刻之法,岂无颖异?如王丰肃、庞迪峨等,其人绝不闻有此规制也。”[2]81
(二)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同接受
晚明时期,坚决反对和排斥西方自然科学的中国士大夫并不是很多,产生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应该说,更多的晚明中国士大夫是因为不能很快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与它们保持距离,即使有学识的中国士大夫也可能会因无法很快理解和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例如《几何原本》的翻译就历经了“三进三止”,早在1592 年瞿太素曾出于自己的兴趣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的第一卷,但未能坚持下去。直到1607 年徐光启和利玛窦才接着翻译到《几何原本》第六卷,但仍然还有七卷未翻译。在瞿太素和徐光启之间还有南京的张养默和北京徐光启的友人都曾尝试着去翻译,但因未能顺利地理解和翻译《几何原本》而作罢,正如利玛窦所言“除非是有突出天分的学者,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1]517。
可以说,晚明中国人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接受只是体现在为数极少的“有突出天分的学者”身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在晚明对知识阶层产生了较明显的冲击力,而且影响深远。徐光启、王徵和李之藻就是这些极少数的有突出天分学者的典型,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和接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他们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在晚明中国知识界是空缺的。例如,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中的度数之学乃是中国已“废绝二千年”了的“古学”[3]192,已经是不为当时人所知道的知识了;他也认为晚明传统历法缺少了可以解释“二仪七政,参差往复”的“所以然之故”的知识,而西泰子(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历法书中有“所以然之故”的知识[3]203。
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更是列举在天文历数方面“我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涉及天地形状、地径测法、南北纬度高低与气候的关系、黄道角度与昼夜长短的关系、日月食的原理、节气与太阳高度的关系等,这些知识在中国以前的“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除了天文历法之外,他还列举了“水法之书”“算法之书”“仪象之书”“《万国图志》之书”“医理之书”“乐器之书”“格物穷理之书”“《几何原本》之书”等,指出这些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3]190-191。
王徵在偶读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时,发现书中谈及各种器械能够不假人力,自动运转,遂“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3]226-227后来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和汤若望让王徵翻阅了不下千百种奇器图说的书,令他“心花开爽”[3]227。王徵对西方器物感到如此兴奋充分说明了西方器物的制作在晚明中国是缺少的,是他未见过的——因为王徵早在二十几岁就痴迷了器物的制造,应该见过不少晚明中国时期的器物制造。
其次,他们意识到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力主尽快译介到中国。如果说瞿太素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翻译了《几何原本》,那么徐光启急迫地翻译《几何原本》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几何原本》的重要性——《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翻译此书可以“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裨益当世定复不小”。尽管利玛窦告诉他翻译《几何原本》是件很艰难的事,但他仍然态度坚决,迎难而上,安排利玛窦口授,他自己笔受,勤勤恳恳,致使利玛窦对此事也“不敢承以怠”,很快在两年时间内[4]159(1606—1607)完成了前六卷的整理和翻译。虽然徐光启兴致盎然,想继续完成剩下的七卷(“意方锐,欲竟之”),但是利玛窦拒绝了。
随着和耶稣会士的交往频繁和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和《泰西水法》等书,徐光启越是感觉中西自然科学的差距,从而形成了他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西学思想,最终促成了他以修缮《崇祯历书》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
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指出,西学“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所以上疏皇上尽快翻译这些“有用”的西学之书:“伏惟皇上久道在宥,礼备乐和,儒彦盈廷,不乏载笔供事之臣,不以此时翻译来书以广文教,今日何以昭万国车书会同之盛,将来何以显历数与天无极之业哉?”[3]191急切之情尽显言语之中。
再次,他们以中学为本,会通西学自然科学,以求超胜古人。“会通、超胜”这一思想概念源自徐光启撰写的《历书总目表》:“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数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今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5]在这里,徐光启使用“会通”一词是指“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也就是以中学为本来消化西学为我所用;而“超胜”一词是指“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意味着想借助西学使中学不断进步,振兴华夏。
徐光启的这种思想其实在他翻译《几何原本》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就把《几何原本》的度数之学溯源到了儒家崇尚的“三代”:“唐虞之世,自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乐五官者,非度数不为功。《周官》六艺,数与居一焉,而五艺者,不以度数从事亦不得工也。襄、旷之于音,般、墨之于械,岂有他谬巧哉?精于用法尔已。故尝谓三代而上为此业者盛,有元元本本、师傅曹习之学,而毕丧于祖龙之焰。”[3]192所以在他看来,翻译《几何原本》乃是“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和“裨益当世”[3]192。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会通思想虽然以中学为本,但并不同于后来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的思想,他们并不认为西学是源于中国,而是与李之藻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是一致的。另外,有时以中学为本也是一种话语策略,扫除儒学传统思想对引进西学的阻碍,例如,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为了说明西方器具的技艺也是民生日用和国家振兴的需要,反驳士大夫执着的“君子不器”的儒学教条,他引用了《易传》中孔子的话:“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利天下,莫大乎圣人?”[3]228,这里王徵引用孔子的话其实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更能有效地佐证中学传统也对器具制作很重视,并不只是西学才有。
以中学为本固然表明当时士大夫内心深处仍有“华夏中心主义”思想的驱使,但是正如上文所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西学与中学的不同以及西学自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主张积极译介西学以使中学超胜自我。
最后,与西学天主教信仰相比,西学自然科学对晚明中国产生了较快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在晚明灭亡前,西学中的自然科学受到了官方的重视,朝廷于1610年起用庞迪我、熊三拔等会同徐光启、李之藻等同译西洋历书,将中国传统历法的修订提上日程;二是晚明不少西学自然科学著作在明清间被很多流传颇广的官方和民间编纂的丛书所收录,其中《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就收录在《四库全书·史部》,《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泰西水法》《乾坤体义》和《新法算书》等被收录在《四库全书·子部》[4]15;三是一般认为中国翻译史上有四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至今的现代翻译。而其中第二次高潮是以“科技翻译”为主要特征,足以见得晚明的西学自然科技翻译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之大。
二、晚明士大夫对天主教文化的接受
在接触天主教文化时,不少晚明中国士大夫也表现出两种明确的不同态度:认同接受和排斥反对。
(一)部分晚明士大夫对“天主创世”的理解和认同
1.对“天主”即上帝的认同
最先将《圣经》中的“天主”(Deus)与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等同的是利玛窦。一些亲近利玛窦的晚明士大夫对其是基本认同的,即使在龙华民挑起Deus 译名之争时,这部分人也未公开确认“天主”和“上帝”的区别。比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支持天主就是“上帝”的说法。由徐光启校订的《推源正道论》即以“上帝”“天主”与“天主上帝”混称Deus,并指出古籍中提及的上帝确是“生人之正道”“天地人物之主宰”,且总结道:“此自东方华夏,西方诸国,其理暗合,若符节然。”李之藻在序杨廷筠的《圣水纪言》一书时,亦称天主即“吾儒知天、事天、事上帝之说”。杨廷筠在《代疑续编》一书中,引用《中庸》《易·系辞》和朱熹的章句,认为中国的大儒均知道天有一主,“岂西儒倡为之说哉?”并称:“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古经典一一吻合。”这意味着在杨廷筠看来,“唯一天主”的概念也早已见于中国古籍,非天主教首创①此段有关“三柱石”的“帝天说”材料参考了黄一农的《两头蛇》,第446-44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5月第2次印刷版。。
有学者指出,1627 年12 月至1628 年1 月召开的“嘉定会议”虽然制定了禁止使用“上帝”一词的决议,但是由于本土天主教徒的极力反对,这一决议在实践中无法被有效执行。主持此次会议的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曾指出,李之藻和孙元化都对禁止使用“上帝”一词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徐光启也认为可以使用“上帝”这一词,没有入教的叶向高阁老也认为利玛窦选择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6]。可以说,皈依天主教的晚明士人基本上认同天主教中的“天主”为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上帝”。这意味着晚明的亲教人士往往习惯于把“天主”纳入中国固有传统思想体系中来对其加以理解和接受。
2.对“创世”的多样化认同
《口铎日抄》记录已受洗入教的李九功向艾儒略质疑了有关“创世”的问题,诸如“造物主化成天地,至第六日而原始祖生,则天地万物之成,尚在原祖未生之始,彼造成次第,乌从知而纪之?”[7]364“造物主之生天也(地?),何不使人为可测?而故隐其奇若此乎!”[7]356李氏兄弟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艾儒略及时的回答,他们能否由此而豁然开窍、理解透彻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无疑是认同艾儒略的解答,并记录下来以惠后学。其实,艾儒略的解答无非就是天主万能,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而人类不一定能完全知晓其中的奥妙。作为博学的信徒杨廷筠在《代疑篇》中也振振有词地说“夫造物化工,昭昭在人心目,何须诠解?惟是天主全能。”[8]507如此的“认同”可以称为是“信仰式认同”。
不过,杨廷筠对“创世”的认同并不局限如此,他反驳了宋明理学认为宇宙的形成起自“气”“理”“偶然”或者“自然生成”等观点,认可《圣经》中的创世说。但应该指出的是,杨廷筠最终仍坚持认为,“天主创世”之事只是被宋明理学“掩蚀已久”,被佛道“异学”“驾轶其上”,“反以凛凛上帝者为迂远,为无据,宁知天主如此全能,如许化工,是吾人大父母。”[8]508这里杨廷筠的“认可”可以称为是“中国化的认同”,认为《圣经》中的天主创世与中国先秦古籍中的记载不相矛盾,而且视天主是人类“大父母”——父母生养了我们,而天主生养了万物,所以天主是“大父母”。
一般认为,将天主类比“大父母”起自利玛窦的《天主实义》②有史料表明,早在1590 年罗马教宗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已出现了“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的说法,早《天主实义》五年。参见纪建勋:《明末天主教Deus之“大父母”说法考诠》,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37期2012年秋,第112-113 页;另参见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2页。,而这种类比其实是以《圣经》的天主创世之说为基础,同时巧妙地将天主教教义融入到儒家伦理纲常之中,不少奉教士人的“认可”属于这种。除了杨廷筠,王徵和李之藻等也持有此说③(明)王徵在《仁会约引》中说:“盖天主原吾大父母,爱人之仁,乃其吃紧第一义也。”李之藻在《刻圣水纪言序》中更是反复强调“天主”是“吾六合万国之一大父母”。参见刘耘华:《依天立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
徐光启在《大赞诗》中也大赞了天主创世“维皇大哉,万汇原本;巍巍尊高,造厥胚浑;抟捖众有,以资人灵;无然方命,忝尔所生。”[9]在遣词造句上,他大量使用了中国文化的词汇表述天主创世的内容,如“皇”“胚浑”“抟捖”“人灵”以及“方命”等,从而不难看出,在这里中国本土文化与天主教创世文化达到了“会通”,不仅如此,“无然方命,忝尔所生”一语也是将天主比作了“父母”。
还有一种认同与信仰无关,如非入教人士熊明遇对《圣经》中天主创世的“认同”却是出于追求真知,表现为对天主创世论批判地吸收,并将其纳入中国思想体系中。
首先,他的《大造恒论》[10]371-377吸收了天主创世论中有关概念和思想,如“造者”与“受造者”,“大造之宰,先天无始,后天无终”,以及“生魂、觉魂和灵魂”等,但是他并没有视“天主”为创世者,而且整篇中没有使用天主教至高神“天主”这一词,他用了几乎没有宗教性的词语“大造者”,“大造之真宰”“大造之宰”“真宰”等词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论证了先秦典籍中如《中庸》《老子》《诗经》都记载了“大造之真宰”,并列出了相关词句作为“真宰引据”附在正文之外。在《大造恒论》文末,他总结道:“尝阅天学诸书,备载大造真宰,始终天地万物之故,人有始无终之故。则吾人当置夏虫、井蛙之见,以翔乎寥廓,返照于不歇之灵根,本天亲上矣!”由此可见,他的论述还是旨在将“创世论”引入中国“儒道的道统”中——“本天亲上”。
其次,他的《大造畸说》[10]378-383自称为间接翻译了《圣经》的创世之事,但有研究者指出是熊明遇“引述或改写”自傅汎际翻译、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首卷的相关内容[10]378。我们将两者仔细对照后,会发现熊明遇并不是全文抄袭《寰有诠》,而是大幅度地改写了相关内容,最大的改写便是将《寰有诠》中使用的“天主”一词,统一改为“大造”。从内容上看,熊明遇《大造畸说》基本上和《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内容相匹配,其“译文”之后不时地加上“译注”进行解说,最后一个“译注”参照“西经所载”的“洪水”之事,推测盘古当在此洪水之后人类“分掌天下”之时,并推算了汉哀帝朝与崇祯元年距离大洪水的具体时间,最后解说大禹治水是因为“盖大洪水已消,不过河渠未清”。熊明遇似乎完全认可了《圣经》中的人类史,其实不然,他在另一篇被称为《洪荒辩信》的文章中辨析了这一问题,指出“洪水荡世,仅余诺阨三子,分传天下,则不能无疑焉!”[10]386。总之,熊明遇“翻译”《圣经·创世纪》的内容不是出于宗教的情怀,而是意在向读者具体展示“西经”中的一种“创世畸说”,以充实他已经论述过的“大造论”——应该就是前文论及的《大造恒论》,这是批判性地接受了《圣经》中的创世思想。
(二)反教人士对“天主创世”的排斥
1.否认天主即上帝
南京礼部侍郎沈榷是上书以官方之力驱逐天主教的晚明第一人,他在第一封参疏中就指出了“天主”之名有违晚明官方的“奉天”之旨意。他论证道:“三代之隆也,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诡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者然,使愚民眩惑,何所适从?”[2]59晚明皇帝对国家的统治在政治上声称是沿袭三代的“正统”,是“奉天承运”的结果,“天”已被视为天地万物的主宰,至高无上,因此无所谓再有主宰“天”的“主”,即“天主”,由此论之,传教士尊称他们事奉的最高神为“天主”当然有违晚明的政治理念。另外,在沈榷的第三封参疏中说道:“据其所称,天主乃是彼国一罪人,故欲矫诬称尊,欺诳视听,亦不足辩也”[2]65-66。他应该不明白天主和耶稣的三位一体关系,误认为天主就是一罪人。
沈榷对“天主”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官员中比较普遍,例如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吴尔成在一封公文中,引用了南京礼科给事中宴文辉的一段话,其中认为“天帝一也,以其形体谓之天,以其主宰谓之帝,吾儒论之甚精。而彼刻《天主教要略》云:‘天主生于汉哀帝时,其名曰耶稣,其母曰亚利玛,又云被恶官将十字枷钉死’。是以西洋罪死之鬼为天主也,可乎不可乎?将中国一天,而西洋又一天耶?将汉以前无天主,而汉以后始有天主耶?据斯谬谈,直巫觋之邪术也”[2]79。
另一官员徐如珂在其上书的《处西人王丰肃议》中也论述道“(王丰肃等)莫尊于上帝,而谓为彝女之所生,绘像图形,真同傀儡……以大明之中天,而诳之以西天主”[2]84。他们对天主的驳斥似乎都是因为不太清楚天主和耶稣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天主教中“天主”与中国人的“天”的区别,但其根本原因应该是为了晚明的皇权统治以及维护主导社会意识的传统儒家伦理。1616 年“南京教案”捉拿传教士和信徒后,官方向民众张贴的告示中列举的传教士“邪说欺世惑人”四大罪状中我们也可窥见一斑,其第三罪状为:“大明律禁私家告天,……今彼夷妄称天主,诱人大瞻礼、小瞻礼名色,不为私家告天乎?……”[2]117-118
“南京教案”发生20 年后,民间以黄贞为中心的一批儒士和佛僧批判天主教,他们否认“天主”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天”或“上帝”。蒋德璟是其中一位,他曾经和传教士有过交往,其反教立场基本是温和与理性的,在读了传教士的书籍之后,他指责传教士“窃吾儒事天之旨,以为‘天主’,即吾中国所奉‘上帝’”,当传教士对他说“家主”(按:家庙中的祖先)之上“当更有大主”时,他反击道:“大主则上帝也,吾中国惟天子得祀上帝,余无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学,则畏天敬天,无之非天,安有画像?……[2]139而激进的反教人士黄贞指责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乃举国合谋欲用夷变夏,而括吾中国君师两大权耳……凡可以乱吾圣贤之教,无所不用其极而无忌惮焉。其最受朱紫疑似者,莫若‘上帝’、‘天命’与‘天’之五字。狡夷以为甚得计者在此。吾国吠声之夫与贪货之流,起而和之”[2]156-157。他批判了传教士的用心邪恶,同时也对认同“天主”就是中国的“上帝”或“天”的中国人大加贬斥。
另外,黄贞引用孔子、朱熹等人言论指出“知天莫若夫子矣”,“吾夫子、子路未尝不并言天地也,未尝不并祷天神、地祇也”,从而批判传教士“妖夷混儒之言天、言上帝,而绝不敢言地,不敢言祷于地祇,不敢言即吾心之道,不敢言即吾心之诚,岂非以其害于天主耶稣之说乎哉?而我华人,以夷之天主耶稣,为合吾儒之经书帝天者,何异以鸟空鼠即,为合凤凰之音也与?”①本处引文对原文有修改,原文将“鸟空鼠即”逗开为“鸟空鼠,即”,应该是错误的。“鸟空鼠即”有时作“鸟空鼠唧”,原是佛教大师讥讽有些人其实对佛教一知半解,而总喜欢大谈佛教义理中的“空”和“即”,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因为有种鸟的叫声是“空,空,空……而老鼠的叫声是“唧,唧,唧……”黄贞使用此词也明显具有讥讽的意味。参见黄贞:《尊儒亟镜》,载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建道神学院出版,1996,第157-158页。黄贞断然认为传教士所言的“天主耶稣之说”是不同于中国的“帝天之说”,两者的区别犹如“鸟鼠”和“凤凰”的不同。陈候光在《辩学蒭言》中驳斥了利玛窦引《诗》《书》内容以证明“天主”和“耶稣”就是“上帝”,指出这是对“上帝”的僭越和亵渎,因为在中国礼制中,“上帝”即为“天”,是“至尊无对”,非君主不能祭祀,而利玛窦让“人人祀天”,实为僭越;又中国的“上帝不可形形,不可像像”,而“玛窦执彼土耶稣为天帝,散发披枷,绘其幻相”,实为亵渎[2]245。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集中驳斥了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视天主为上帝的做法,其立论基本和陈候光相似,他认为利玛窦“谬以天主合经书之上帝”[2]289。
许大受在《圣朝佐辟》的《辟诬天》中也指出儒家“圣学何尝不言天,然实非夷之所谓天也”,儒家是“敬天”而天主教是“媚天”,他引证了“夷籍”中的内容,如:“若尔辈毕世为善,而不媚天主,为善无益;若终身为恶,而一息媚天,恶即全消”[2]197-198。他也在《辟窃佛诃佛种种罪过》中为佛教进行了辩护而驳斥天主教[2]212-213。不过,以佛教立场驳斥天主教的“天主”,当以佛教高僧袾宏大师为最,他在《天说》中驳斥了“天主”的至尊,以佛教的思想体系论证了,“天主”只不过是佛教中万千“天主”之一[2]320。袾宏大师把“天主”纳入到佛教体系,便轻易地将“天主”拉下了至尊的位子。然后他论述道:“又言天主者,无形无色无声,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赏罚乎?”[2]320。我们能看出,袾宏大师论述的目的不仅仅要驳斥“天主”的至尊性,更重要的是要指责传教士不懂得佛教的“天之说”而毁谤佛教,他最后对传教士说:“彼虽聪慧,未读佛经,何怪乎立言之舛也!”[2]320
2.认为天主创世“坏乱天下万世学脉”
黄贞在给其师的信中就驳斥了天主教的“创世说”有悖于中国传统对“天”的认识,有悖于中国传统对天地万物生成的认识,因此将会“坏乱天下万世学脉”,他如此论述:“彼教独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天地也,天主也,人也,分为三物,不许合体’。以中国万物一体之说为不是,……。此其坏乱天下万世学脉者”[2]150。他在《尊儒亟镜》中以儒家的“万物生成说”为立足点,驳斥了“创世说”的不合理性。首先,他在《尊贵迷悟相背说》一节中引用《中庸》对“诚”的系列论述质疑“天主耶稣”七日创造天地、生成万物的说法,从而驳斥了天主教“教人乞成乞道于耶稣,乞灵乞贵于天主”[2]160-161。其次,他在《太极理道仲尼不可灭说》一节中,驳斥了“创世之说”是“以天主耶稣灭太极矣”,并指责认同“利先生天学甚精,与吾儒合”的人乃是“太极之乱臣贼子,为素王之恶逆渠魁焉已矣!”[2]163
天主教的“创世”内容还包含天主创造人类元祖亚当和夏娃,而元祖悖逆天主旨意而导致人类原罪的产生。此一创世内容更是受到反教人士的讥讽和批判。例如陈候光指出,“以元初祖先获罪于天主,乃令千百世子孙共受其苦”,不仅表明了“天主之罚太酷”,更是与天主教声称“天主悲悯于人”之说相违背,他进一步讽刺道:“譬之匠人制器,器不适用,非器之罪也,必云拙匠。岂天主知能独巧于造天地万物,而拙于造人耶?”[2]248许大受对“天主造人”与“人类原罪”更是驳斥有力,概括为十大谬误[2]202-203。相比于陈候光条分缕析地驳斥,佛教僧人释如纯的驳斥几乎都是反问句,气势更为咄咄逼人[2]396。
三、晚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对士大夫西学接受的意义
晚明之际,士大夫对西学的接受是晚明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晚明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西学在晚明中国被接受的方式和内容;其二,晚明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西学在晚明的接受效果。
(一)对西学被接受的方式和内容的影响
和平的“学术传教”方式是基于晚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当沙勿略想进入晚明中国内地传教遇阻时,就如何打开晚明中国的大门,天主教会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低估晚明王朝的实力,主张以武力征服晚明中国,如在1569 年、1573 年和1574 年,均有人上书建议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动用武力,甚至狂妄地宣称只需数十名兵士即可攻占城池。即使在耶稣会士进入肇庆建立教堂之后,仍见有类似的建议,如曾任耶稣会日本教区长的Francisco Cabral 国王曾于1584 年上书已兼任葡萄牙王位的菲力普二世,认为只要集结一支一万人以内的舰队,即可控制华南沿海省份。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Alonso Sánchez(1547—1593)也曾于1584年在澳门声称:“我和罗明坚的意见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11]26
而范礼安和沙勿略一样,熟悉晚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派出有学问的传教士和晚明中国士人交往从而被他们接受,而且他强调精通中国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势必需要通过基督教有益于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民众的精神生活才能使得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认为“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1]142。而且,范礼安曾经接受耶稣会长的指示,撰写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此书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文明优越性的认知,列举了中国的七大优越性并重点论述了中国有别于欧洲的官员治理方式及其优越性[12]。
再者,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向晚明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劝化晚明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而不是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传教,传教士们不断研究晚明中国,直至利玛窦之时,他们认识到晚明中国是个注重学术研究的文明国度,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的人往往都是有学问的人。同时,随着利玛窦深入内地,他越感觉晚明有学问的人大都对中国文化充满骄傲,甚至夜郎自大,视其他地方为偏远蛮荒之地,其他民族为野蛮无知之人[1]94-95。因此,“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一旦这种新知识被少数人所知道,它就很快地进入知识阶层的学术领域。由此可以想见欧洲的声誉是怎样在提高的,他们又是如何缓慢地把它和野蛮分开来的,并且将来不好意思把它称作野蛮”[1]347,349。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实践,晚明传教士采取了“学术传教”的策略,在他们传教过程中,一边忙着译介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天主教作品,又一边忙着译介大量的欧洲科技作品,两者同时进行。
(二)对西学接受效果的决定性影响
本文前两部分的史实告诉我们,无论是西方自然科学还是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在晚明士大夫中都存在有排斥反对的人和认同接受的人。具体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天主教文化,晚明中国士大夫的排斥和反对的理由几乎一样,即意在维护晚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秩序(道统),认定传教士是夷狄蛮族,天主教是与儒学迥然不同的邪教,会乱我“学脉”,变我“纲常”。但晚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文化的认同接受的效果却大不一样,即认同接受天主教文化的人其实质还是以儒家为正统,以儒家的典籍为圭臬,以“合儒补儒”为旨归,正如刘耘华教授所言,他们的“深层文化结构依然未变”[13],但认同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人却意识到西学与中学的不同以及西学自身的重要性,而且主张积极译介西学以使中学超胜自我,其高潮是官方主持基于西方天文历法修改中国传统历法。另外,利玛窦死后被朝廷赐葬于皇城北京的主要依据也是其翻译了《几何原本》,传播西方自然科学,而不是其译介了天主教,这也表明晚明中国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同接受程度要远比天主教文化深刻。
因此,天主教文化观念并没有对晚明主流文化形成根本性的冲击,更不能促使其产生变革,但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对晚明中国产生了较快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晚明社会文化语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科举取士的制度传统让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来说,发展水平不高,具有“弱势”的特点,甚至有点“危机”的程度,因此容易受“强势”的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与其他朝代一样,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独尊儒学,与当时西方教会学校兼修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大相径庭。因此晚明的读书人为了在科举中获得功名利禄和光宗耀祖,把精力和智力主要用在背诵“四书”经文和做好八股文。
其次,晚明中国的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生态却让中国人在信仰上相当成熟,自成一体和自我满足,并且比天主教信仰更显得具有理性和现实性,因此有力地“抵抗”了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儒道释并存的晚明多元文化体系是自足的,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满足晚明人们对生活和信仰的追求,解决了个体的存在面临治国(事)、治身和治心这三维的问题。以“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为例,他一生志存高远但命运多舛,不过,最终功德圆满,达到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境界。究其原因是他秉持儒学,出入佛道的结果,黄宗羲曾总结了他的思想“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从而最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14]。王阳明自己也认可其在龙场的“中夜大悟”是儒释道三教共同作用的结晶[15]。
如果说晚明文化的自足性在王阳明身上体现的是,儒释道能提供他足够的思想养料,使他终能在思想精神上达到“自足”的境界,那么晚明文化的自足性在李贽身上体现的是,他满足于出入儒释道追求信仰而无意求助于西方传教士。史料表明,李贽和利玛窦有六次会面,他虽然对利玛窦赞誉之词溢于言表[16]333,但从未有过赞赏基督教的任何之词,甚至找不到他对基督教有什么明确的评论,相反,他对利玛窦来华动机产生困惑和质疑:“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16]333。李贽对天主教文化的反应具有典型性,体现了当时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态度,正如利玛窦曾经抱怨道:“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知识。”[1]94-95反教人士黄贞的老师颜茂猷在《圣朝破邪集》时,开篇的几句话可以视为当时多数士人的心声:“粤自开辟以还,三教并兴,治世治身治心之事,不容减,亦不容增者也。何僻尔奸夷,妄尊耶稣于尧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萨、神仙为鬼魔?其错谬幻惑固已冁然足笑。”[2]143
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成熟稳定和互补自足,天主教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对晚明思想文化产生显著影响,无法撼动其思想文化的根基。而中国士大夫一贯重经不重器的治学传统,使部分晚明士大夫也认识到了西方科学知识的长处,他们惊异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奇特,最终推动其进入官方,促进了中国传统历法的修改,影响深远。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文化在晚明中国的接受情况与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在“多元系统”理论看来,外来文化作为一个系统,一旦与本土社会文化相遇,会不自觉参与本土社会文化这个大系统,但是否发挥作用,且发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本土社会文化的竞争力。外来文化一开始只是处在本土社会文化大系统的边缘位置,然后根据本土社会文化竞争力的大小,逐渐改变其在大系统中的位置相应的作用。西学中的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文化在晚明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正是这样。西方的自然科学、天主教文化对晚明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天主教文化对晚明中国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远不及西方的自然科学,这与晚明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大系统有极大的关系,即科举取士的制度传统让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来说,发展水平不高,具有“弱势”的特点,甚至有点“危机”的程度,所以作为子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相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具有了较大的吸引力,容易进入晚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主流”,发挥作用;而晚明中国的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系统却让中国人在信仰上相当“成熟”,自成一体和自我满足,因此作为子系统的天主教文化相对于中国儒释道文化子系统来说竞争力很弱,很难在晚明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发挥作用,只得持续处于“边缘”。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依据“多元系统”理论,“增殖规律”是系统的普遍规律,它告诉我们,所有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都会力求成为多元系统,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系统会力求多样化,增加可供选择的项目”①参见伊塔玛·埃文-佐哈尔著,张南峰翻译的《多元系统论》的正文和译者张南峰的注释⑦,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4、25页。。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文化大系统的进步发展在于其开放性和多元性,即大系统需要不时地引进新的子系统,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互动,但是这种竞争互动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而应该是求同存异而共存于系统之中,为系统“增加可供选择的项目”以供人们自由选择,最终有利于大系统的整体发展进步,这实际上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中国传统智慧也是不谋而合,异曲同工。理论上来说,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都可以成为多元系统中“可供选择的项目”,让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自由选择,要么是对外来异质文化观念或技术的本土化改造,要么是对本土传统文化观念或技术的推陈出新,这才是“多元系统”需要的开放性竞争,也只有这样的竞争互动才会有利于全人类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