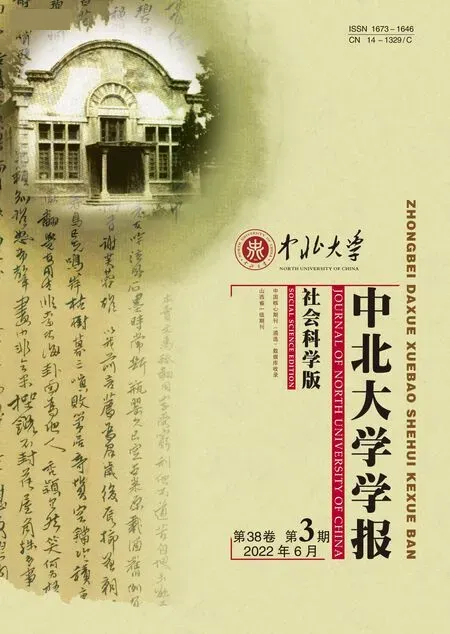现代歌诗复兴视野中的民国电影“再民族化”考论
2022-11-23王潇
王 潇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中国电影……在民国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下,初步探索出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表达风格。”[1]纵览既往有关民国电影的“民族性”研究话语,一方以孟繁华等为代表,在与西方电影的横向标识中,通过现代性语境下革命与启蒙之间的策略游移型塑民国电影的民族性内涵; 另一方以高小健、蓝凡等为代表,以表演艺术的“内部研究”,纵向阐明“中国电影的哲学”及“中国电影史的民族性逻辑”[2]。这两种共时与历时的民国电影民族性研究视域,长期从属于文学界与电影界的逻辑范畴,并存在着文学史与电影史学科间深度对话的匮乏,这具体表现为:近年来文学界着力探寻古今通变意义上的现代歌诗复兴,并以梁笑梅为代表开始研究歌诗与电影传播间的母题关系; 电影艺术界则显现出对“左翼电影音乐”本土立场的自觉,并以高小健为代表触及戏曲与电影等综合性文艺组合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民国电影与文学共同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历史表明:虽然彼时许多“电影—文学”家都意识到“戏剧就和歌谣(Ballet)一般”[3]11,即现代性语境下的表演艺术形式(如:“影戏”)与原始歌诗存在同构关系,但是当前“电影研究—文学研究”对此的深度阐释还明显薄弱。此外,随着1980年代生活现代性主潮的到来,以及文学界对“文学性”、电影界对“电影性”的信仰,学界对国家现代性主潮下的民国电影“再民族化”产生了时代阐释之“隔”。基于此,重拾现代歌诗复兴视域下的民国电影“再民族化”建构之意义便了然可见。
1 历时序列:现代歌诗复兴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之互文图景
歌诗指合乐诵唱的诗歌,而现代歌诗复兴则意指有二:一是现代歌诗作为与古代歌诗相对应的诗体延传,具有在现代性语境下承续与通变的丰富况味; 二是复兴作为针对古代歌诗传统衰微的悖反描述,具有侧面丈量现代歌诗运动向度与限度的驳杂意味。此外,歌诗不同于徒诗仅以语言文字为表现载体,它更侧重以视听媒介为传播载体构成“传播的诗”的景观。深究史实,这类“传播的诗”大量化为电影媒介中的歌曲质素,并以其独特的民族表达与现代意蕴参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建构进程。因此,我们对这类“文学—电影”交集图景的阐释,应提振至“交互主体性”的视域进行考察。
1.1 边界探赜:歌诗史与电影史罅隙中的共生图景
作为现代歌诗的前语境,古代歌诗“在原始社会中就开始扮演着娱乐和教化的两种功能”,同时作为歌诗的两种艺术形式,“以娱乐为主的艺术是以诉诸感性为主的,而以教化为主的艺术是以诉诸理性为主的”[4],而这两者又彼此融通:钱志熙称“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其中歌谣与乐章以其“群体的诗歌”本质融洽着“感性为主的”歌诗,徒诗则以“个体的诗歌”对应着“理性为主的”歌诗。同时,“歌谣和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因而“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5]。由此,共时与历时之维的古代歌诗表现出民间性、人民性与诗人意趣间的内循环结构。然而,现代以来“诗性与歌性呈愈来愈明显的分离趋势,其中的歌性愈来愈弱,而诗性则越来越强”[6]的看法日盛,尤其是国家现代性主潮迭起,文学之徒诗、电影与音乐之歌曲看似将传统歌诗瓜分殆尽,致使其作为传统诗歌流脉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衰微的体式。事实上,无论是彼时鲁迅、朱自清、康白情等对歌诗的推崇,郭沫若、田汉等对歌诗的践行,还是现时王德威、李怡等对“中国新诗的歌谣化运动”为显象的现代歌诗史的梳理,均揭橥了正在浮出地表的现代歌诗复兴之图景。
与之相对,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民国电影,其“再民族化”进程肇端于清末的“戏曲电影”。20世纪初由民间资本丰泰照相馆摄制的《定军山》《青石山》等戏曲影片,已显现出民国电影民族性改造的原初形态,即将传统的京剧等戏曲内容横向移植至电影的新兴媒介载体当中,而这说明戏曲作为包孕中国传统歌诗的重要载体,尽管在国产电影的起始阶段仅与之形式组接,但梁笑梅所揭示的“诗歌和电影既可以在美学上相互渗透,也可以在形式上直接结合”[7]的规律表明,现代性语境下歌诗与民国电影间的“美学互渗”史长期处于隐视之中。
1.2 双向互文:现代歌诗复兴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建构史
1.2.1 “无声电影”时代
现代歌诗溯源于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其基于歌与诗的语言共境凸显出“在国民性乐教中反求诸己、启迪民智,又在现代性伦理中师夷长技、自救自强”[8]的现代性意义。与之相应,电影则在民间资本的助推下,以市场接受为基点操控着其文艺生产所指向的审美情趣,即适应国人审美心理的“讲故事”传统。因此,在1910年与1920年代,民国电影吸纳传统戏曲、民间小说与野史等“讲故事”的通俗文学叙事传统,生产出大量言情、神怪、侦探、犯罪等类型模式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如《海誓》《玉梨魂》《盘丝洞》《阎瑞生》等。而“重写文学史”与“重写电影史”以来,有关乐歌时代与鸳鸯蝴蝶派电影的通俗现代性意义不断阐释,这实质上根源于早期民国知识场域的两大构成:一是作为现代歌诗与电影受众主体的市民阶层,他们以日常生活模式与感性审美心理为渠道体验形而下的现代性语境; 二是作为传统歌诗分流的新诗(徒诗)与“新文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智识阶层,他们则以知识启蒙模式与理性教化心理为渠道接受形而上的现代性语境。也就是说,以市民阶层为鹄的的现代歌诗与电影艺术,具有通俗现代性意义的形而下美学互渗,即石川所讲:“‘鸳鸯蝴蝶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民间文艺有一个自然、直接的传承。” 从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古代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变革至新兴市民阶层背景下的“哀情”叙事模式,“他们把中国民间文艺传统与电影这种西方舶来的新的媒体形式进行了嫁接与融合”[9]。
无声电影时代的歌诗保持着“在场”状态,这不仅表现为它们两者间通俗现代性的美学互涉,还体现为它们在无声境遇下的双向形式耦合。具言之,传统歌诗重在以声音媒介为传播载体建构其听觉艺术的审美边界,而默片时代的歌诗语言在剥离原生的歌性媒介传递形式后,往往通过“音乐视觉化”的手段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声音媒介的彻底缺席,以现场演奏或提前灌录的唱片播放等形式次生的歌性声源的存在,既为歌诗的现场传播提供物质可能性,又为歌诗的综合性立体呈现带来了审美新变的现实基础。针对世界范围内默片色彩单一而氛围沉闷的观影现状,民国电影从业者曾探索“放映中段加演歌舞”的民族性电影美学。演员龚稼农曾回忆默片《良心的复活》中插曲《乳娘曲》的上演情境:
“正式登台时,耐梅的化妆完全与片中一样,等到电影放映到耐梅坐在客厅里唱歌时,银幕升起,舞台灯光渐亮,我们的小型国乐队便在布景后面奏起来,耐梅也就做着片中相同的表情,轻展歌喉,唱出了《乳娘曲》,唱完了,银幕下降,继续放映。”[10]3
这里面糅合着传统戏曲“虚实结合”的智慧,并弥补了无声电影的艺术缺憾。电影中的插曲《乳娘曲》是导演卜万苍等人为立体地传达影片中绿娃连遭被辞、失子等人世变故的情节而专门创作,这是无声电影对歌诗的召唤与体认,其歌词中“秋雨滴梧桐,秋花满地红,瞧那呢喃乳燕掠长空。鸡雏随母走,牛犊引村童,我此身惘惘好似在虚空”等话语融通着“情景交融”的徒诗意蕴,“金钱呀,拆散了人家母子不相逢!阶级呀,你把我的娇儿送了终”则陡然直转至“直抒胸臆”的歌谣诗风,二者的巧妙编织使歌诗整体具有预示更为猛烈的普罗“歌喉”时代到来的丰富意味。总之,无声电影时代下歌诗与电影间的双向耦合,显现出市场机制下歌诗基于“艺术性”自觉而创造性入影,电影基于“民间性”叙事而创造性入乐的历史景观。
1.2.2 “有声电影”时代
1931年,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标志着以声音媒介为原生载体的歌诗与电影之融合,克服了既往无声的技术壁垒而获得更为深度的“视听溶合”的影像基础,并意味着在“红色30年代”的现代性语境下,来自歌诗与电影艺术深处的本体变革将促成它们的灵魂对话与内化叠现。早在民间资本助推的鸳鸯蝴蝶派电影盛行之时,许多掌握文化资本,但不具备经济资本的知识分子深埋着“银色的梦”,及至1930年代普遍的“文艺家—革命家”精神左转,“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11]66的电影观成为时代显声,越来越多的电影—文学家拥蹙电影为“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最良工具”[11]72,那么,“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文艺目的如何实现?显然,“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文盲,我们不能拿诗歌文字给他们看”[12]304的大众文艺共识表明:歌诗作为以声音媒介为传播载体的传统体裁正在“现代复兴”,并成为现代化语境中大众文艺潮流的重要一极,继而充溢在囊括电影在内的各类综合性文艺形式中,共同编织起普遍的“传播的诗”的图景。
这类“传播的诗”或单独传唱,或与电影等综合性艺术形式“文体溶合”,但歌诗与电影间的深度“溶合”是以双向互补为前提的:1930年代国家现代性主潮的冲击,不仅造就“中国新诗的歌谣化运动”,而且引发从事电影生产的大量民间资本在普罗文化市场的影响下转向,如“明星继联华之后也向反帝反封建迈进。艺华便是继它们之后起来的‘进步电影生力军’”[11]178。遭遇观众审美厌弃的旧派市民电影在表现形式、美学思想方面亟需向普罗时代的美学突围,而援引左翼思潮下的民歌体抒情歌诗便成为其突围的重要取向,与此同时,这亦成就了有声电影时代“左翼电影”与“新市民电影”的辉煌。此时的歌诗与电影相“溶合”不止是无声电影时期基于强化艺术叙事与完善视听体验的艺术互补,更是基于两者间结构层面的“精神性对话”的现实考量,特别是左翼电影注重将“打破第四堵墙”的戏剧观植入歌诗与电影的视域中。如联华制作的新市民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反复出现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洲》,其“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呦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呦流浪在街头……”的歌谣体唱词,直接钩沉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古典诗意氛围,直白浅切地传扬出电影基于普罗大众的人民性美学意境。总之,有声电影时代下歌诗与电影间的双向遇合,既是现代歌诗复兴趋向下“传播的诗”成为电影叙事结构性要素的深度交切,又是民国电影在歌诗政治中由民间性指向人民性与民族性本位的改造逻辑。
近来,王海洲集中笔墨梳理新中国电影的“再民族化”道路,并将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意识形态大转折作为区隔“市民电影”与“人民电影”的分水岭。事实上,这种变迁之源包孕在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前路中,并且是在民国现代性语境下的歌诗与电影由艺术自觉向理念自觉的演进中逐步显现的:主流电影工业生产在实践层面推进民间性向人民性的历史转型,其间亦包含着主流价值层面的人民性美学转向,而此中民国电影的“在地性”与“在地者”状貌亦勾勒出其“再民族化”的壮阔景象,并且为新中国电影的“再民族化”馈赠着典型经验与丰富滋养。
2 共时系统:现代歌诗视域下的民国电影“再民族化”之本体内涵
这里所叙的共时系统之考察,意在与前述之历时序列下的现代歌诗复兴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互文图景构成更广义的互文解读,即从本体研究的角度切入二者间的内部肌理,并详勘它们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不断在现代性话语阐释中获得存在的关系本体的淆杂内涵。
2.1 实在本体:基于语言本体的歌诗对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内涵构建
2.1.1 歌诗视域下的电影语言与修辞之辨
民国电影中的现代歌诗从属于实在本体层面的电影语言,这需从三个向度加以剖析:一是现代歌诗本身表征着民族传统文体的现代建构,其歌性与诗性相融合的特殊形式寄寓着化用传统诗歌资源而使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意味。现代以来尽管歌与诗分野后的徒诗占据诗坛显声,但随着电影等综合性大众媒介的兴起,大量“出乐为诗,入乐为歌”的歌词浸润至电影语言“再民族化”的建构进程中,这亦使民国电影在“影戏”的审美概念中确立自身。因此,民国电影中的现代歌诗应纳入中国诗歌史的又一次转折并与民国电影的民族化史交集共生。
二是歌诗融为电影语言的内在肌理,其“求美之术”的诗性本质引发歌诗与电影间双向度的修辞新变。马尔丹在其电影语言理论中认为电影音乐“应该是对影片情节结构保持自主……它应当去自由地阐述,而不是解说,应当细腻地去启示,而不是渲染”[13]95,这表征着将电影音乐视作独立本体的电影结构观,但歌诗并不完全等同于电影音乐,其往往被阐释为徒诗与音乐相结合的电影语言。首先,就文体特征而言,歌诗以歌性与诗性的遇合为支撑,型塑着抒情写意的诗意审美氛围; 电影则以画面与声音的结合为基础,构建着光影表达的视听叙事谱系。因此,电影于歌诗而言实现抒情叙事化,歌诗于电影而言促进叙事抒情化。其次,从“无声电影时代,电影是一种纯视觉艺术”[14]的共识着眼,深究现代歌诗作为电影语言的建构意义,早期“舞台化”的歌诗艺术实质上构成朴素的电影声画关系实践。如默片《良心的复活》中另设现场演出的《乳娘曲》片段,它将声源从沉默的电影画面移至舞台化的实景中,并节选绿娃连遭横祸达到情绪感染之顶峰的时刻予以舞台化视听呈现,形成传播效果强烈的实景“镜头”与“情节”的复调式“蒙太奇”修辞效果,即一方是歌诗语言中“我此身惘惘”的虚化体验与“金钱、阶级”等酿制人世惨象的实境体认间相“剪辑”的有机组合,另一方是泛化的电影语言中默片画面切换至舞台化实景“镜头”。在此中,以舞台化形式呈现的在场“声源”传达出绿娃悲极而歌的内在节奏,延展着默片画面中绿娃失业、失子的外在镜头内涵,并通过受众情感缀想而达到“对比”等对列效果,继而将默片画面中对标蒙太奇的修辞效果延伸至声音(舞台化歌诗艺术)与画面(默片镜头)之间,构建起原初形态的“声画一致”的和谐整体。再次,民国电影由默声进阶至有声并非是直指式的,1930年代初,长达六七年的声默交叠状貌亦揭橥出歌诗作为电影语言的淆杂意涵,突破技术之“隔”的声音逐渐获得完备的电影语言的表现载体,即电影中以对唱、独白、字幕等为代表的“天然语言”与以“视听造型来传情达意”[14]的“非天然语言”,因此,以影片内部深度的声画关系调和而“去舞台化”便成为电影修辞的必然途径。如“默片加唱”下的《渔光曲》画面中单独赋予歌曲以真实声源,尤其是徐小猫在哥哥徐小猴临终之际再次唱起《渔光曲》的镜头,其中,修辞向度上的歌声(电影声音)同电影画面中无穷的帆舟意象诗意融汇,民谣性质的歌诗语言在共情的基础上构筑起“声画调和”的影像表意修辞境界。此外,区隔于歌诗等天然语言,非天然语言如音响的自觉运用亦打破无声电影中机械音响的沉闷体验并拓展着歌诗的诗意氛围,影片《渔光曲》序幕与落幕间山高水远的自然画面与凄怆哀扬的背景音响相呼应,为歌诗的传播载体表现着哀戚隽永的审美基调。及至有声电影的全面普及,歌诗逐渐在“去舞台化”的趋向中脱离体用形合的本体意义,而在镜头运用、画面构成、色彩搭配等维度中丰富其作为电影语言乃至于电影修辞的本体意义,即在电影声画对位的深度“溶合”间确立其本体意义。
三是歌诗与电影语言、电影修辞的渐进关系,凸显着传统诗学与电影美学的媾和图景。马尔丹认为,“由于电影画面尤甚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13]7,这表明西方传统电影理论视野中的语言之维的电影与诗具有同构性。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索绪尔语言观下的电影符号学将电影视为语言加诸描述,而歌诗作为这类更广泛意义上的电影语言的“属性”之一,其“求美之术”的修辞向度凭借作为属性意义的本体存在,模糊了原本作为独立文体意义的电影与歌诗美学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继而显现出进阶的互生共存的电影美学。
2.1.2 作为电影修辞维度的歌诗对电影美学拓展
歌诗以“求美之术”的修辞向度逾越歌性符号与电影语言间的结构联结,它的诗性空间召唤着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并取道“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等传统诗学理念促进民国电影美学的“再民族化”进程。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类进阶的美学范式:
一是传统“抒情”心理下的“哀情”现代体验:晚清诞生的戏曲电影肇启着传统歌诗与电影的体用“形合”,而鸳鸯蝴蝶派电影则寄托着现代歌诗与电影的抒情“意合”。传统诗歌具有抒发个体与社会之情愫的职能,随着民国历史转型与现代体验的推进,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现实与观念的撕裂,个体与社会间普遍怀有自我压抑的现实观感与反抗诉求,如《桃花泣血记》的“宣传曲”则以“人生就像桃花枝,有时开花有时死”的比拟式诗意修辞抒发“文明社会新时代,恋爱自由才应该”的现代体验,而歌诗中关涉琳姑与德恩等的叙事性抒情文字又同电影中琳姑早逝、德恩噬情的“哀情”美学构成深度互文的影像修辞意境。可见,传统“抒情”心理现代体验下的时代情愫,在歌诗与电影的互文性“意合”中表现为“哀情”等的形而下的美学观感与诗境体认。
二是现代“焦虑”心理下的“震惊”现代体验:“现代主义的焦虑”问题折射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体验”的摩登母题的中国化过程,即继黑格尔“艺术的终结”论后,1930年代本雅明从媒介技术的视角阐明“由‘宁静’的欣赏转向对‘震惊’的‘心神涣散’的感知”的历史转型,也即“韵味的没落和震惊的兴起”[15]。这类形而上的媒介现代性理论型塑着民国普遍的形而下“震惊”体验,并营构出1930年代现代派文艺的盛景。如影片《如此繁华》在与“感官上海”的叙事体验一道反复咏现的歌诗质素中,感官机制下的“美人名士,油壁香车/华灯齐上了,谁管夕阳西下”的绮靡意象构砌起“如此繁华,青春无价/愿及时行乐/到处看花,绮窗朱户/山隈水涯,情苗爱叶/随地长出根芽”的震惊体验的影像意境,此处徒诗般的歌诗亦与影片整体的讽刺喜剧氛围交互指涉,并随着片尾指向革命的现实叙事元素,旋使影片的诗思境界逾越“软性电影强调电影的视觉观赏性、娱乐功能性”的美学认同,获得“把感官和物质方面的经验带入现代主义一词的解释中”[16]的“诗电影”的驳杂况味。
三是革命“审美”心理下的“人民”群像体认:启蒙与国家现代性主潮的迭起,使民族国家想象与人民想象成为了时代显声。不同于“哀情”与“震惊”现代体验下以民间性为价值趋归的歌诗及电影美学,这是在“民族形式”的民间性评骘中,进一步建构其以人民性为价值鹄的的左翼美学。具体而言,这存在两类变体:一是经历属性改造后的“新市民电影”中普遍存在的被压迫“人民”的心灵疾呼,如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歌谣体诗《月儿弯弯照九洲》。二是融民间性、革命性、民族性于一炉的人民性歌诗及电影美学,如影片《风云儿女》中“一双双脚,穿鞋的,光脚的,大的,小的”[17]259表征的“人民”群像,在《义勇军进行曲》昂扬复沓的“起来”与“前进”的歌谣体诗性想象空间中唤醒着人民性传统下歌诗“乐教”与“诗教”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抗战的大写的人民群像在解放区的歌性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基于“工农兵”形象本位的人民性美学日益突出,以及民歌体抒情诗与新秧歌运动的迅速兴起。在此之上,以延安电影团为代表的电影学派形成纪实风格,及至抗战胜利后接管长春伪“满映”制片厂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工业,此中的电影生产者在“轮流地深入农村,深入部队,深入工厂去体验生活”的身份自觉中逐步衍生至解放区“人民电影”的美学风格之认同,并与颇具民族性内涵的现代歌诗相紧密融合,并最终过渡到新中国且歌且诗的电影“再民族化”的现实谱系。
2.2 关系本体:现代性语境中的歌诗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历史反思
现代歌诗与现代歌诗复兴作为语言本体与历史现场的横纵向概念阐述,与民国电影的“再民族化”进程构成紧密联结的共同体,而研究话语对这些共同体的认识则处在不断确证的过程,即在历时性话语空间的不断阐释中建构内涵丰富的关系本体。随着20世纪中国启蒙现代性、国家现代性、生活现代性主潮的迭起,现代歌诗复兴及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本体阐释的面貌亦颇显复杂。
在国家现代性主潮弥散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时期(1949年—1976年),左翼歌谣体诗歌实践(尤其是解放区歌谣体诗歌)得到价值肯定与理念延续,在此之外的现代歌诗实践会同“工农兵”题材与主题之外的民国电影均被“革命”导向下的评骘标准厘定为“旧社会”的“反人民”电影,如市民电影便长期被视作“软性电影”。1978年生活现代性主潮兴起,物质基础上的世俗生活与民生标尺成为时代内涵,相应地,以1980年代中后期“哲学—美学”领域“诗化哲学”、文艺理论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话语领域“重写文学史”与“重写电影史”等为代表的知识型构,便有力地搭建起“纯文学”视域下的运作体制,一时间“革命”作为“话语霸权”的表征而渐趋祛魅,而“抒情”与“审美”则被视为文艺“主体性”的存在而迅速复魅。随着1990年代后期迄今的“文学性” “电影性”问题意识的自觉,以贺桂梅与李道新为代表分别表明文学史“自我批判”与电影史研究主体性、整体性、具体性的立场与方法。综上,无论是纯文学标尺下的“现代新诗‘拟歌谣体’在文学史实践上是失败的”论点,还是“走出‘启蒙与救亡’二元模式的闭性循环”[18]后“抒情与审美”话语权力反向推崇的状貌,都充分说明历时语境中无形的话语权力规约下对复归历史现场的现实影响。质言之,现代歌谣体诗歌的兴起及其入影的现象背后,既回应着革命与启蒙的现代性话语的现实需求,又复兴着传统诗歌民间性与人民性的文化内涵,更表达着“战时的文化心理”下真实的“抒情”与“审美”取向。因此,晰清关系本体语境下现代歌诗复兴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淆杂本相,对学界尽可能地复归历史现场大有裨益。
3 结 语
本文基于历时与共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并举的整体性视野,统摄作为文学史与电影史共生现象的现代歌诗复兴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母题,一方面历时梳理现代歌诗在民国由无声向有声电影过渡现场中的特殊“在场”信息,另一方面共时溯源实在本体层面现代歌诗作为电影语言、电影修辞乃至于电影美学本体对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建构作用,以及关系本体层面多维现代性语境交迭下的现代歌诗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历史反思。总之,以交互主体性的关系现场深究现代歌诗与民国电影“再民族化”的本体意涵,在当前“文化自信”的战略背景中对当下歌诗与电影学派而言具有不可回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