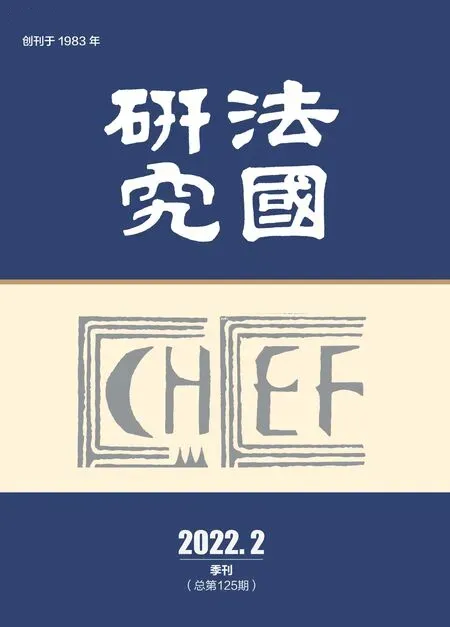从游戏到艺术:论近代法国戏剧的专业化①*
2022-11-23唐运冠
唐运冠
戏剧是什么?许多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文学和艺术。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许多作品未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而它们仍旧是戏剧。笔者认为,戏剧首先是一种表演行为,演出的情境和戏剧的受众是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剧本则不是戏剧的必需要件。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戏剧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戏剧都只有演出而没有剧本。而在剧本文学化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只能阅读而不适合演出的剧本,它们不能算作真正的戏剧。①阿兰·维亚拉也认为戏剧是表演,但又认为它还是艺术和文学,参见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aris: PUF, 2009, pp. 3-40。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诸如16世纪下半叶法国贵族文人创作的不适合演出的“静止剧”并非真正的戏剧。参见陈杰:《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3页。我们还需要分辨中西方艺术概念的细微差别。在西方,art一词在16世纪以前主要指“技术”,其后“艺术”才逐渐变成它的主要含义。但在现代汉语中,“技术”和“艺术”是两个词语、两个概念,这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业已现代化的概念的结果。历史地看,戏剧最初只是一门技艺,技艺精湛到一定程度才变成艺术。尽管古希腊和古罗马已有十分发达的戏剧艺术,但正如让-皮埃尔·博尔迪耶所指出的,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与欧洲中世纪的戏剧之间并没有连续性。②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45.因而要研究近代欧洲戏剧文学化和艺术化的历史,还得首先回到欧洲中世纪的语境中去。
文学化和艺术化之前的戏剧是什么?戏剧史研究者大都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③但有些研究者并不认为戏剧经历过一段从宗教仪式发展成艺术的历史,而是认为(或默认)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并存的。较鲜为人知的是,中世纪的戏剧还是游戏,或一种具有宗教性的游戏。戏剧的这段“游戏史”在许多文化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语言记忆。如汉语的“戏”和“剧”都有“游戏”之意,李白的《长干行》中“折花门前剧”中的“剧”就是如此。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比如《欧洲戏剧文化史·中世纪卷》把“游吟诗人的诗歌,律师、教士、教师、政客们卖力的口头表演,民间舞蹈、游行、宗教仪式等社群节庆活动”都纳入戏剧/游戏的范围,亨利·雷伊-弗洛的《中世纪戏剧研究》甚至把弥撒仪式也视作戏剧/游戏,因为主持弥撒的神父在扮演上帝并表演圣餐变体。④Jody Enders,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Bloomsbury,2017, pp. 2-3; Henri Rey-Flaud, Pour une dramaturgie du Moyen Age, Paris: PUF, 1980, p. 83.就本文而言,这种宽泛的界定尽管为中世纪的戏剧赋予了游戏的性质,却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对于近代法国戏剧专业化的问题,陈杰从16-17世纪专属剧场的出现和职业剧作家的诞生等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⑤参见陈杰:《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十七世纪法国职业文人剧作家的诞生》,《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黎塞留主政时期的法国国家文人保护制度》,《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专属剧院的诞生与十七世纪法国戏剧的职业化进程》,《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西方学者对16-17世纪法国的戏剧有诸多深入的研究,不过专门讨论戏剧从游戏到专业化这一演变进程的研究并不多见。⑥西方学者研究16-17世纪法国戏剧的两部最重要的专著是W. L. 威利的《法国早期的公共戏剧》(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和阿兰·豪的《1600-1649年巴黎的专业戏剧》(Alan Howe et al., Le théâtre professionnel à Paris, 1600-1649, Paris: Centre historiqu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2000),它们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笔者尝试将戏剧专业化的过程置于近代法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下,把戏剧、演员、作家、演出情境、受众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并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揭示其特质,进而从戏剧专业化的进程来考察近代法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戏剧狂欢:作为社群节庆游戏的中世纪戏剧
中世纪人对戏剧的理解与现代人非常不同,他们把戏剧视作游戏而非文学或艺术。相应地,中世纪戏剧的演出方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都与现代戏剧大相径庭。①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并非一个确切的时间范围,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是指文艺复兴语境下的“现代”理念普及之前欧洲旧有世界观影响所及的范畴。就法国戏剧史而言,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是新旧观念的过渡期,因而既是中世纪的,也是近代的。
(一)作为游戏的戏剧
中世纪的戏剧乃游戏,从词源学上有最直观的证明。一直到16世纪,许多法语戏剧均以“游戏”(jeu)命名,比如《亚当戏》(Jeu d’Adam)、《圣尼古拉戏》(Jeu de saint Nicolas)、《林中小屋戏》(Jeu de la Feuillée)、《罗班与玛丽昂戏》(Jeu de Robin et Marion)等。中世纪最常用来描述戏剧的拉丁词语是ludus,法语是jeu,而中世纪法语还有一个现在看来较准确的形容戏剧的词语jeu par personnages(角色扮演游戏)。②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41.在英语中,中世纪最经常用来形容戏剧,也最具有表现力的词语是ludus的英文形式play和game,甚至到了16世纪都还使用Cristemasse game来指代在圣诞节表演的戏剧,17世纪初还使用gamesters来指代戏剧演员。德语中的spiel也是如此。③Verdel A. Kolve, The Play Called Corpus Christ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p. 13-16.
来自法国诺曼底圣莫尔(St Mor)的乡村贵族吉尔·德·古贝维尔(Gilles de Gouberville)写于1549年至1562年的日记④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i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Normandie, t. 31 & 32, Caen: Henri Delesques, 1892 & 1895.提供了直接的日常生活证据。据笔者统计,在13年的日记中,古贝维尔提到戏剧14次⑤这个数字远未能反映当地人对戏剧的热情,因为从日记的记载看,圣莫尔没有戏剧演出,人们需要到附近的瑟堡、瓦洛涅等地去观看,这至少有两到三个小时的路程。,其中有4次直接用jeu、2次用动词jouer的变体来表达。比如,1551年6月7日主日(星期日),古贝维尔的助手兼密友康特皮去瑟堡观看关于雅各的12个儿子的“游戏”(les jeuz qu'on y faisoyt des douze filz de Jacob)。接下来的两个主日,他所在的圣莫尔都有人去瑟堡看神迹剧(miracle),可以推测看的是同一出戏。⑥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t. 32, pp. 163, 165, 167.在这里,jeu和miracle是可以互换的。1554年平安夜,圣莫尔的好些人都到迪哥维尔去看戏(furent à Digoville pour ce qu'on y jouet)。之所以可以判断这里说的“ce qu'on y jouet”指的是演戏,是因为在前一年的平安夜,圣莫尔同样有好些人到迪哥维尔去望弥撒,以便观看弥撒结束后的道德剧(moralité)。①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t. 31, pp. 61, 145.1559年9月17日主日,让·奥夫雷神父和让·弗雷列神父去瓦洛涅也是为了看戏(partys aulx jeux),因为刚刚有人在上一个主日也去那里看过神迹剧。②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t. 31, pp. 516, 518.1560年8月7日,有人从瓦洛涅途经圣莫尔返回瑟堡,他带了一张魔鬼面具给准备表演一出疯剧的瑟堡人使用(pour ceulx de Cherebourg qui doybvent jouer je ne sçay quelle follye)。这张面具想必很快派上了用场,因为接下来的圣母节和主日,都有人去瑟堡看戏(allèrent aux jeux)。③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t. 31, pp. 584-586.到17世纪上半叶,戴面具仍旧是法国演员在戏台上变换身份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一直到16世纪,人们都还把戏剧视作游戏。
不过,jeu和play/game这些表达是否只是在西欧民族语言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对拉丁文ludus的简单直译,所表达的其实是戏剧艺术而非游戏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世纪的人并不把戏剧视作文学或艺术。现代戏剧研究者在讨论中世纪的戏剧时往往先入为主地将现代的戏剧概念强加于中世纪。在法国学者亨利·雷伊-弗洛看来,这些学者“固执得令人吃惊”,因为他们坚持把中世纪的ludus翻译成théâtre liturgique(礼仪戏剧),而拒绝简单直接地译为jeu。④Henri Rey-Flaud, Pour une dramaturgie du Moyen Age, p. 82.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戏剧和剧本区分开来。传统的研究往往把剧本等同于戏剧,但它事实上只是戏剧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中世纪,剧本普遍不具有文学性,它甚至只是戏剧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亨利·雷伊-弗洛对此做了精到地阐述。他指出,在中世纪,戏剧的技术(布景、器械等)可以重复,但文本在原则上必须是新的,是没有使用过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世纪的戏剧并非文学,剧本的文学化始于它被第二次上演之时。⑤Henri Rey-Flaud, Pour une dramaturgie du Moyen Age, p. 77.让-皮埃尔·博尔迪耶也指出,中世纪的剧本不仅十分简单,而且更新得很快。比如在1488年一出戏剧的对白里,20年前的剧本已被认为“太旧”,不适合演出。⑥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p. 67-68.这种对新剧本的追求似乎说明剧本很重要,实则不然。17世纪30年代,法国剧本的文学化仍处在初期阶段,当时巴黎著名的蒙多里剧团有一位女演员报怨高乃依的剧本过于昂贵,她的言论反映了此前的剧本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她说,以前为他们隔夜拼凑起来的剧本只要3埃居,现在高乃依的剧本却要收他们很多钱。⑦Jean Regnault de Segrais, Oeuvres de Monsieur de Segrais, t. 2, Paris: Durand, 1755, pp. 143-144.剧本创作的随意性解释了为何中世纪有许多戏剧,却极少有为后人所知的剧作家,也很少有剧本留存下来。
在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传世文献已经十分丰富的16世纪到17世纪初,法国能够流传下来的剧本仍十分稀少。17世纪初在法国名噪一时的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尔迪就是突出的例证。阿尔迪自称创作了五六百种剧本(这个浮夸的数字本身就表明了剧本的随意性),而留存下来的只有34种。①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252;陈杰:《十七世纪法国职业文人剧作家的诞生》。事实上,中世纪的很多戏剧演出可能根本就没有剧本。亨利·雷伊-弗洛指出,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喜剧确实是中世纪戏剧的继承者,因为它“竟然”拒绝文本,而把即兴表演放在首位。②Henri Rey-Flaud, Pour une dramaturgie du Moyen Age, p. 77.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20年代以前的法国,意大利剧团在法国极受欢迎,从中或可窥见当时的法国人对戏剧和剧本的态度。在戏剧专业化的过渡阶段,即开始出现职业演员和剧作家的那几十年,没有人把这两种人视作艺术家、文学家或地位崇高的人——职业演员名声再大,也仍旧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职业剧作家尽管被称作“诗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剧本是用诗体创作,而非因为剧本的文学性),上流社会对他们(甚至包括高乃依等人)卖文为生的行为却极为鄙视。演员和剧作家的这种地位反映了人们对戏剧和剧本的普遍认知。
其次,中世纪的人们对戏剧和对其他游戏的态度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格伦丁·奥尔森指出了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事实:中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等人把戏剧视为与其他游戏一样“没有超越其本身以外的意义”的东西,而现代人在对电子游戏等提出同样的疑问时却把包括戏剧在内的表演艺术排除在外。③Jody Enders,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123-124.这一现象比较鲜明地揭示了戏剧从游戏到艺术的演变过程。事实上,17世纪以前的许多作者都明确地把戏剧视作一种游戏,其中最典型的是托玛斯·阿奎那,他的《神学大全》第一六八题第二至四节专门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探讨了游戏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戏剧。阿奎那认为游戏是必要的,因为它能消除灵魂的疲劳,就像休息能消除肉体的疲劳一样。他同时指出,游戏必须适当、适度,符合人的身份和时间地点等环境。在此基础上,阿奎那讨论了戏剧的问题。他说,有人认为“那些一生以演戏为目的的演员④阿奎那使用的是officium histrionum一词。中世纪并没有职业演员,阿奎那引用的是西塞罗等古罗马作家的说法,因而这个词应当指的是古罗马时期的职业演员。似乎游戏过多”,而游戏过多可能是有罪的。阿奎那则认为,只要表演得当,既不使用不正当的言语和动作来表演,也不做不适合情境的表演,那么“以使人得到娱乐为目的的演戏”并无不可,演员也并不处在有罪的状态之下。⑤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Augustæ Taurinorum: Typographia Pontificia et Archiepiscopalis, 1891, pp. 210-211;圣多玛斯·阿奎那编著:《神学大全》第十一册第一六八题“论身体外表行动的检制”,周克勤等译,台湾: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2008年,第460-462页。很显然,阿奎那认为戏剧是游戏而非艺术。1600年前后,当新兴的职业演员受到道德家攻击时,他们仍旧援引阿奎那等权威为自己的职业辩护。⑥Robert Henke,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Early Modern Age, London:Bloomsbury, 2017, p. 120.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小托玛斯·普拉特1595年-1600年的旅行日记。在法国、西班牙、尼德兰、英国旅行期间,他记录了众多斯特凡·赫尔费尔德所谓的“属于大众文化的戏剧活动”。赫尔费尔德敏锐地指出,普拉特的戏剧报告对视觉比对语言更感兴趣,因为在这位16世纪末的观众看来,跳跃、舞蹈、斗殴、滑稽、戏仿、幽默的姿态和奇异的故事仍然是戏剧娱乐的精髓。①Robert Henke,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Early Modern Age, pp. 120-122. 普拉特的日记原文为德语,其记载在法国蒙彼利埃生活部分的法语译本参见Félix Platter et Thomas Platter, Félix et Thomas Platter à Montpellier, 1552-1559, 1595-1599, Montpellier: Camille Coulet,1892;记载作者巴黎见闻部分的法语译本参见Thomas Platter, Description de Paris, par Thomas Platter le jeune, de Bâle (1599), trad. par L. Sieber, Paris(原书未注明出版商), 1896;记载作者英国见闻部分的英语译本参见Thomas Platter, Thomas Platter's travels in England 1599, trans. Clare Williams, London: J. Cape, 1937。
(二)中世纪的戏剧与社群公共生活
普拉特的观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世纪戏剧在各个方面都跟后来作为艺术的戏剧十分不同。这既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剧本上,也表现在戏剧演出的方方面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戏剧史研究片面强调剧本的倾向,戏剧的演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我们对中世纪以降的戏剧表演情境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跟随拉伯雷的描述,我们可以对16世纪中叶以前的戏剧演出情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巨人传》第四部第十三章②François Rabelais, Le quart livre des faicts et dicts heroiques du bon Pantagruel, Paris: Michel Fezandat, 1552, pp. 29r-32;中文译本参见拉伯雷:《巨人传》第四部第十三章,成钰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23-726页。写道,晚年退隐普瓦图的诗人维庸为了给人们提供“消遣”(passetemps),用当地的方式和方言排演(entreprint faire jouer)了一部《耶稣受难》剧。角色分派妥当,演员(les joueurs)也齐了,场景也布置好了,维庸告知当地的市长和官员,这出神迹剧可以在尼奥尔集市收市时上演,现在只剩下各个角色的服装需要解决。市长和官员命令人们提供帮助。为了给一个扮演圣父的老农民寻找衣服,维庸要求当地的方济各会当家神父塔波古借给他一件法衣和一件披肩。但塔波古拒不答应,称本省会规严禁把任何东西赠给或借给演戏的人(les jouans)。维庸说会规只涉及闹剧、滑稽戏和诲淫的戏(jeuz dissoluz),但塔波古坚决不借。维庸誓言报复。趁塔波古外出时,维庸组织演员们在城里和集市上排演了一次魔鬼出巡,最后在城外一个农家旁边的大路上,对着归来的塔波古和他的坐骑狂喷烟火,受到惊吓的马匹把塔波古摔下马来,把他踢得脑袋分家、四肢断裂、一命呜呼。最后,维庸心满意足地称赞演员们“演得真好”(que vous jourrez bien)。
这段描写几乎包含了我们想知道的关于中世纪戏剧演出的全部细节。除了和几乎同时的古贝维尔一样用与“游戏”(jeu或jouer)有关的词语来描述戏剧、演员、表演之外,三个方面的细节也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中世纪戏剧的游戏属性。
第一,戏剧演出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上,中世纪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在节庆场合演出的,特别是愚人节(La fête des fous)和狂欢节期间。①传统集市与节庆无异。据成钰亭译本的注释,尼奥尔集市一年只举行三次,可算是盛大的节庆。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已有详细讨论,我们还可以从古贝维尔的日记中得到印证:他提到的14次与戏剧有关的记录几乎都是在节日(圣诞节、圣母节等)和主日,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555年2月12日(星期三)在布雷的圣戈梅修道院跟国王和王室成员一起观看一出法语喜剧。②Eugèn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 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 t. 31, p. 249.而在空间上,维庸的魔鬼出巡表明,在中世纪,一场戏剧并不像现在是在一个戏台上完成,而是走街串巷,把整个社群当作它的表演空间。③尽管上文所引用的《巨人传》段落提到了“剧场”(théâtre),但该词的含义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它可能只是宽泛地指代用于演戏的场所,未必是后来的剧院(后面的魔鬼出巡可以做证)。巴黎乃至全法国的第一个专门剧院在1548年才出现(详见下文)。让-皮埃尔·博尔迪耶提到,1372年,菲利普·德·梅齐耶尔在阿维尼翁的科尔德利耶修道院组织的一场圣母戏就包含了演员或怪物的游行。④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48.这类戏剧游行在中世纪的愚人节等狂欢活动中同样十分普遍。⑤参见拙文《节庆游戏与“共同体”生活——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这里不再一一举例。韦尔代尔·A.科尔韦的研究指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中世纪的英国还使用procession、pageant、show等词语来指称戏剧,⑥Verdel A. Kolve, The Play Called Corpus Christi, p. 13.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戏剧演出方式和演出空间的理解。
第二,戏剧的内涵。戏剧研究者普遍把中世纪的戏剧分成宗教剧、世俗剧等种类。大致来说,宗教剧都与基督教《圣经》的内容有关,世俗剧则被理解为“没有宗教说教”的戏剧。但这些学者也意识到,所谓的“世俗剧”也与节庆紧密联系在一起。⑦参见李道增:《西方戏剧·剧场史》上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6页;郑传寅、黄蓓:《欧洲戏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8-114页。把西欧中世纪的宗教等同于基督教,这种做法可能与对“黑暗世纪”的传统看法有关,即认为中世纪是基督教会实施文化专制和思想钳制的时代。事实上,近几十年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彻底颠覆了这种刻板观念,当时的基督教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绝对统治力,而中世纪事实上在诸多方面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⑧可参见勒华拉杜里关于蒙塔尤、金兹伯格关于弗留利等地的宗教观念的微观研究(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卡洛·金兹伯格:《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及本内特、乔丹等关于欧洲中世纪的研究(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威廉·乔丹等:《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傅翀、吴昕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因此,将中世纪的宗教等同于基督教的做法值得商榷。本文想强调的是:其一,节庆的演出场景决定了中世纪的所有戏剧都具有宗教性;其二,这种宗教内涵绝非局限于传统上理解的基督教,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就包含了大量的民间宗教成分(或“异教”成分,它们将成为宗教改革重点剔除的内容),而后者主要通过狂欢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让-皮埃尔·博尔迪耶也指出,中世纪的戏剧并无宗教剧与世俗剧、严肃剧与喜剧之分,实际上大都是混合剧,而且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剧都带有喜剧成分。①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44.换言之,与节庆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中世纪的戏剧普遍具有狂欢色彩,这正是该时期的戏剧被视作游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狂欢性不仅存在于拉伯雷笔下的神迹剧《耶稣受难》当中,也存在于13世纪的《圣尼古拉戏》《林中小屋戏》等所有被现代学者视为具有较高艺术性的早期法语戏剧中。②详见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p. 41-96.
许多因为没有剧本③拉伯雷笔下维庸的《耶稣受难》似乎也没有剧本。,未被纳入戏剧史研究视野的狂欢游戏亦是如此。比如1497年梅斯的狂欢节巨人游行中,人们做了一个男巨人,让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手提一根巨棒,把他从一位助理法官(eschevin)家里领出来游行。第二天,他们又做了一个女巨人放在另一位助理法官家里。肥美星期二④Mardi gras,指中世纪大斋节来临之前一个可以大快朵颐的狂欢日。这天,人们敲锣打鼓,把男巨人领到女巨人家中,让他们订婚,举行婚礼并跳舞。随后人们在市内举行盛大的凯旋游行,男巨人领着女巨人,后面跟着那两位助理法官和梅斯的其他法官。到了某个地方,一大群乔装打扮的“街坊”迎过来,把男女巨人领到大教堂前面,由一位愚人“神父”给他们念祝词,并给众人讲与巨人结婚有关的笑话。所有人都跟在后面观看。返回时,人们在女巨人家的院子里表演一出“极好极欢乐”的滑稽剧。最后女巨人被送到男方家中,让他们躺在一起,“做生小孩的事情”。⑤J. F. Huguenin, Les Chroniques de la Ville de Metz 900-1552, Metz: S. Lamort, 1838, p.622.整个游戏过程与维庸《耶稣受难》的魔鬼出巡异曲同工,从中也不难看出它的戏剧特征。
这种狂欢游戏尽管没有基督教的说教色彩,但民间宗教的意涵再明显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393年在法国王宫举行的一场闹婚狂欢(charivari):在伊萨博王后为她一名曾两次失去丈夫的女官举行的第三或第四次结婚典礼中,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和若干高级贵族化装成浑身是毛的野蛮人,一边不知所云地号叫,一边挥舞着狼牙棒,“像魔鬼一样”疯狂地舞蹈,还做各种粗野下流的动作。这时国王的兄弟奥尔良公爵突然进来,他将手中的火把朝野人身上扔去,导致四名表演者当场被烧死,国王因为躲在贝里公爵夫人的大裙摆下才躲过一劫。这类闹婚狂欢在中世纪法国民间也十分常见,它具有安抚亡灵等特殊的宗教意味。⑥关于该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参见让·皮埃尔·里乌等主编:《法国文化史》第二卷,傅绍梅、钱林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Susan Crane, The Performance of Self: Ritual, Clothing, and Identity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p. 155-162; J. R. Veenstra, Magic and Divination at the Courts of Burgundy and France: text and context of Laurens Pignon's Contre les Devineurs (1411), Leiden: Brill, 1997, pp.89-96。描绘这场狂欢的一幅中世纪绘画被乔迪·恩德斯新近主编的《欧洲戏剧文化史·中世纪卷》用作封面插图,表明作者也把它视作戏剧。①参见Jody Enders,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Middle Ages。
第三,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总体上说,中世纪不存在职业的戏剧演员,也没有专门的戏剧观众。在拉伯雷笔下,给维庸的戏扮演“天父”的是一位老农民,其他角色尽管并未提及,但估计同样是当地的普通民众。在中世纪,包括戏剧演出在内的节庆活动是由被称作“狂欢社团”(société joyeuse,英文一般称作festive society)的青年兄弟会(后来逐渐变为成年人的社团)主导的,这些社团往往按地域或行业进行组织,并享有官方认可的节庆狂欢和戏剧表演特权。比如从1402年起至1548年,巴黎的耶稣升天兄弟会(la confrérie de la Passion)得到国王特许,拥有表演耶稣、圣徒、圣物的垄断权。②参见拙文《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史学月刊》2017年02期);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p. 72-74。而“青年”在当时更多的是单身而非年龄的概念。正如格林贝格所说,男性“默认的青年时代从……能携带武器的年龄到结婚为止”,青年人相对的自由赋予了他们“管理群体生活,应对某些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并处理本地社群与外部的关系”的特殊使命。③Martine Grinberg, "Carnaval et société urbaine XIV e -XVI e siècles: le royaume dans la ville",Ethnologie française, No. 3 (1974), pp. 215-244.这使戏剧表演成为管理公共生活的手段,演员也不会获得直接的报酬。因此,在中世纪末,当一个以演魔鬼而知名的补鞋匠要求为演出获得补偿时,人们觉得此事实在稀奇,特地把它记录下来。④Alain Viala, e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71.另外,社群的其他成员也并非被动的“观众”:他们有义务为“演员”提供相应的道具,并以此加入戏剧表演中;拒绝提供道具的人将受到惩罚,而惩罚者无须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⑤巴赫金也指出,利用魔鬼出巡的游戏来索要物品(有时还会因为强行索要而涉及暴力)是中世纪法国人常见的习俗(参见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309页)。今天西方国家小孩的万圣节讨物游戏就是这种节日传统的延续。维庸通过“借道具”和魔鬼出巡,把塔波古神父强行拉入戏剧表演之中,从而模糊了所谓的“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当塔波古神父拒绝履行传统义务时,维庸和他的演员借演戏之机给予了他“应得”的惩罚,而他们也不用为神父之死负责。可以说,在中世纪的戏剧表演中,演员和观众乃一个统一体,他们之间远没有后来那种清晰的界限。
在中世纪晚期,唯一不完全属于上述范畴的可能是教会学校的戏剧。它们一般是用拉丁语搬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这使它在学校的围墙之外又竖起一道语言的隔墙,从而把自己排除在了大众文化的范围之外。
二、戏剧演出的日常化和职业化
法国在16世纪下半叶经历了漫长的宗教战争,它可能延缓但并未阻断法国城市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总体进程。战争结束后,法国的绝对王权和以巴黎为首的城市化很快推进到了新的高度。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则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结构,在教会和国家权力的协同压制下,狂欢文化所承载的非正统基督教世界观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①参见拙文《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戏剧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到1600年前后,法国戏剧演出的情境已经与拉伯雷的时代有了根本不同。
(一)戏剧的私人化和世俗化②这里所称的“世俗化”是指戏剧失去了它的宗教性,而非仅指它走出教堂和修道院等教会的空间。
17世纪初,法国宫廷医生让·艾罗阿尔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路易十三从出生到27岁(1601年至1628年)的成长轨迹,其中提到戏剧至少108次。③Jean Héroard, Journal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Louis XIII, 2 vols, Paris: Didot, 1868。由于文献提及戏剧次数众多,除特殊情况外,本文引用时不一一注明页码。W. L. 威利对该日记也有专门的研究,参见W. L. Wiley, "A Royal Child Learns to Like Plays: The Early Years of Louis XIII",Renaissance News, Vol. 9, No. 3 (Autumn, 1956), pp. 135-144.这些记录尽管大都十分简略,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一些结构性的特征,再结合同一时期的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国(尤其是巴黎)戏剧演出的图景。
第一,戏剧演出的时间和空间。从戏剧演出的时间来看,与半个世纪前古贝维尔记录的戏剧演出几乎都在节日或主日不同,在艾罗阿尔的日记里,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巴黎市场上,戏剧演出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有。比如,巴黎大堂(Les Halles)集市北边的勃艮第府(Hôtel de Bourgogne)是这个时期全法国最热闹的演戏场所,也是17世纪40年代以前巴黎唯一的专门剧场。从8岁到13岁,小路易总共有10次去勃艮第府看戏的记录,其中5次是星期日,2次是星期六④星期六在17世纪并非假日,它在基督教中也不像星期日(主日)一样具有特殊地位。,3次是星期三。在1611年9月11日至25日的两个星期里,他接连去了5次之多,这中间并没有特别的节日。我们或许可以将之视为戏剧世俗化的的一种表现,它与宗教改革后法国整体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紧密相连。如果将艾罗阿尔的日记与古贝维尔的日记进行比较,会得到一个有趣的发现:在有关日期的标注方面,两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注明了所记录的每一天的日期和星期。不同的是,只要是节日,古贝维尔都在日期和星期后面详尽地注明当天是什么节日,其中既有复活节等“正统”的基督教节日,也有狂欢节、三王节、圣约翰节等民间宗教或异教氛围浓郁的节日,还有为数众多的保护圣徒的节日。相比之下,艾罗阿尔则极少明确注明节日,偶尔标注的也都是正统的基督教节日,比如圣诞节和复活节。三王节等节日在宗教改革后为天主教和新教同时排斥,艾罗阿尔只在记录路易十三的活动时才偶尔提及它们。
在戏剧演出的空间上,这时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勃艮第府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勃艮第府于1548年建成。由于其拥有者耶稣升天兄弟会得到国王授权,长期垄断了巴黎的戏剧演出,因而它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巴黎唯一的职业剧院。在巴黎进行职业演出的剧团就算不租用勃艮第府,也必须向耶稣升天兄弟会支付租金或罚金。因此,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巴黎市场上最出色的戏剧演出大都在这里进行,以至于包括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在内的王公贵族都被吸引过来。①关于勃艮第府的专门研究,参见W. L. Wiley, "The Hôtel de Bourgogne: Another Look at France's First Public Theatre", Studies in Philology, 70 (1973), pp. 1-114;陈杰:《专属剧院的诞生与十七世纪法国戏剧的职业化进程》。老式网球场也经常被改用作戏剧演出。小托玛斯·普拉特在1596年写道,阿维庸有很多喜剧演员,他们在当地为数众多的老式网球场里表演。1599年,他说有人估计巴黎有1100个老式网球场,就算只有一半,这个数字仍非常可观。②Félix Platter & Thomas Platter, Félix et Thomas Platter à Montpellier, pp. 248-249; Thomas Platter, Description de Paris, p. 42.此后,越来越多的球场被租用作演出场所。③W. L. 威利对此也有专门的研究,参见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pp. 158-177.无法承担剧院和网球场租金的演员则在城市广场上搭建起临时戏台进行表演。总之,到这一时期,拉伯雷笔下那种一出戏在社群空间里巡游展开的演出方式已基本消失。
第二,戏剧演出的主体。在这个时期,职业剧团已经取代中世纪的狂欢社团主导了法国的戏剧演出。在艾罗阿尔的日记中,戏剧表演可分为四种:小路易的游戏式表演、宫廷人士自己排演、耶稣会的戏剧和职业剧团的表演。其中前两种有24次,耶稣会的戏有7次,其余全是职业剧团的演出。他没有提到任何狂欢社团(包括耶稣升天兄弟会)的戏剧,换言之,就演出的主体而言,法国戏剧的职业化在这一时期已大体完成。
戏剧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550年前后。在巴黎,1548年勃艮第府剧院落成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戏剧场所的固定化,还意味着买票入场看戏的时代已经到来。相应地,戏剧表演变成了可以谋生的职业行为。在此背景下,有别于狂欢社团这一地方社群组织的职业剧团开始出现,1556年,一个外地剧团在鲁昂市的一个老式网球场内演出。头两天的演出很顺利,但第三天表演《雅各的生平》时,两个警察闯进来中断表演,要求观众退场。观众“已经为座位付钱”,故而引发骚乱。剧团团长起诉到鲁昂高等法院。法院经调查后裁定,鉴于“这是第一次有剧团以收取门票的方式公开表演”,剧团的“游戏”(jeu)可以照旧进行,但必须满足若干规定,包括只能在主日晚祷后演出,不能敲锣打鼓吸引观众,所有演出必须得体,等等。④Archives du Palais-de-Justice Arrêt du Parlement, 25 octobre 1556. 转 引 自E. Gosselin,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et l'histoire du théâtre à Rouen avant Pierre Corneille, Rouen: E. Cagniard,1868, pp. 41-43.可以推测,演出被中断是因为触及了宗教改革背景下敏感的宗教神经。该事件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一个外地剧团成功地侵入了原先被当地狂欢社团垄断的领地。其二,法院明确声明这是该市第一次收费的戏剧演出。其三,市政权力开始强势介入戏剧演出。这些变化意味着戏剧表演正在从社群活动向私人表演过渡。不过,在这个阶段,狂欢社团的传统演出仍占主导地位。比如在鲁昂,国王亨利二世来到该市时仍点名要观看著名的“笨蛋修道院”的演出,而该社团也继续活跃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①Dylan Reid, "Carnival in Rouen: A History of the Abbaye des Conards",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2, No. 4 (Winter, 2001), pp. 1027-1055.事情在16世纪最后20年有了重要变化。在巴黎,耶稣升天兄弟会于1578年第一次把勃艮第府租给职业演员,而它在1597年最后一次自己演戏的努力也宣告失败。这两个事件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至少在巴黎,本地狂欢社团主导的戏剧演出已经过时,它不再对观众具有吸引力,尽管根据国王特许,该兄弟会仍旧对巴黎的戏剧演出拥有垄断性的管理权。当然,外省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在勃艮第,第戎的“疯妈妈”社团还要活跃到17世纪中叶。②关于巴黎耶稣升天兄弟会出租勃艮第府等的情况,参见W. L. Wiley, The Hôtel de Bourgogne, pp. 7-8。关于兄弟会放弃自己演出的原因,本文赞同陈杰的观点,即业余性的表演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参见陈杰:《专属剧院的诞生与十七世纪法国戏剧的职业化进程》。关于第戎“疯妈妈”社团,参见拙文《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
在法国戏剧职业化的进程中,来自意大利的剧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意大利剧团最早在1572年受邀来到法国,目的是在新教首领、后来的亨利四世与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礼上演出。③Armand Baschet, Les comédiens italiens à la cour de France sous Charles IX, Henri III, Henri IV et Louis XIII, Paris: E. Plon, 1882, pp. 34-43.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自意大利的摄政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影响。不过,这些剧团真正在法国产生重要影响还要等到16世纪晚期宗教战争结束以后。小普拉特在1598年详细记录了一个意大利剧团在阿维庸的演出。④Félix Platter & Thomas Platter, Félix et Thomas Platter à Montpellier, 1552-1559--1595-1599,pp. 391-395.1599年亨利四世邀请意大利剧团来巴黎演出,此后它们在法国的影响日盛。艾罗阿尔在日记中有54次明确说明了观看的是哪国演员表演的戏剧:除了宫廷人士和耶稣会士表演的戏剧外,还包括法国人演出25次,意大利人演出25次,西班牙人演出3次,英国人演出1次。1609年2月8日,小路易去勃艮第府看戏时故意放声大笑,好让人们知道他懂意大利语。可以说,在这个时期的巴黎,意大利剧团与法国剧团大致平分秋色。
职业剧团和职业演员的兴起,意味着戏剧演出与社群生活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断裂。流动剧团的成员显然不再是本地社群的一分子,甚至传统的狂欢社团也开始进行流动的付费戏剧演出。在17世纪前30年的巴黎,那些最成功的剧团和演员基本都来自意大利或法国外省,一旦在巴黎失宠,他们又重回在法国甚至欧洲各地流动演出的老路。⑤关于这个时期在法国有重要影响的意大利和法国剧团及演员,学者已有详细研究(参见Alan Howe et al., Le théâtre professionnel à Paris: 1600-1649, Paris: Centre historiqu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2000; 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等),兹不赘述。由此,演员与观众之间也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观看戏剧变成了一种自愿的经济和文化行为,人们不再负有直接参与戏剧演出或提供道具的义务。前文提到的鞋匠要求为演出获得补偿,塔波古神父根据新的会规拒绝提供道具等行为,都是演员与观众的统一体开始发生裂变的表征。这个断裂的过程在法国各地并不一致,其完成的标志是传统狂欢社团彻底退出戏剧舞台。总体而言,它大约用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第三,戏剧的种类。这一点在艾罗阿尔的日记里表现得极不平衡。在总共108项戏剧记录中,他提到喜剧85次、闹剧9次、悲剧5次、悲喜剧3次、牧歌剧2次、滑稽剧1次。此外,还有4次用jeu指称戏剧。而在半个多世纪前,古贝维尔仅有的14次戏剧记录中,有8次明确提到剧种,包括神迹剧5次、道德剧1次、喜剧1次、闹剧1次;另有6次用jeu或jouer表示。即使考虑到所处地域和阶层的差异(诺曼底乡村与巴黎宫廷),数字(尤其是不同种类的戏剧所占总数的比例)的变化所反映的发展趋势仍旧十分明显。Jeu或jouer使用频次的下降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戏剧-游戏”观念尽管仍残存在人们的文化表达之中,但业已式微,新的戏剧观念正在形成。在这种新观念中,一方面,戏剧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对不同剧种之间的区别也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而这种区分在阿奎那和拉伯雷那里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此前占有重要地位且具有显著宗教意味的神迹剧和道德剧消失了,这是戏剧世俗化的又一明证。与此同时,喜剧和闹剧(艾罗阿尔有时将喜剧和闹剧区分开来,有时又混为一谈①比如,1607年1月27日他记录道:小路易命令蒙格拉特男爵戴上面具表演一出“喜剧”,他自己穿上女孩的连衣裙,戴上蒙格拉特阁下的帽子和天鹅绒面具……“游戏”(le jeu)于八点开始……“闹剧”演完后,他脱下连衣裙跳舞。同一次表演先后用“喜剧”“游戏”“闹剧”来描述。)的占比大幅提高,在艾罗阿尔的记述中占他提到的全部戏剧的九成左右。与此相应的是,艾罗阿尔把所有的戏剧演员都称作“喜剧演员”(comédien),却没有对应的“悲剧演员”,甚至没有中性的“演员”。这种表达习惯在法国至少沿用到17世纪末。此外,尽管记录了这么多次戏剧演出,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没有提到剧目和作者(唯一提到的作者是亚里士多德)。在仅有的8次写明剧目的记录中,悲剧和悲喜剧占了5次(而这两个剧种总共才提到8次),另外3次是喜剧(这个剧种总共提到85次,加上闹剧是94次)。如此悬殊的比例说明,在艾罗阿尔看来,悲剧和悲喜剧比喜剧更有记录的价值,但戏剧市场的实际状况却与此形成鲜明的反差,喜剧和闹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说明,尽管此时法国的戏剧市场十分繁荣,但仍很不成熟。②那个时代的人确实以“喜剧”指称作为整体名称的戏剧(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250),但从艾罗阿尔的日记和其他资料来看,在描述某部戏剧时,他们很清楚喜剧与其他剧种(闹剧除外)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艾罗阿尔在说“喜剧”时指的就是他认为的喜剧(按后来的标准应是闹剧,见下文),而非泛称。
(二)有待成熟的戏剧
从简单的统计数字进入具体戏剧演出情境,我们会发现这种尚不成熟的状况表现得愈加明显。艾罗阿尔很少记述戏剧表演的细节。但在1608年7月3日,他提到小路易在枫丹白露观看法国著名喜剧演员科拉的表演,此人擅长跳跃,从一架直梯上一路跌落下来,却毫发无损。可见这次戏剧表演至少是跟杂耍结合在一起的。小路易还多次去勃艮第府看戏。尽管艾罗阿尔从不说明表演的是什么内容,但我们可以从同时代的其他记录中找到答案。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曾经十分仇视亨利三世宫廷的戏剧演出,但他后来却用欣赏的笔调记录了1601年6月意大利著名的阿勒坎剧团在勃艮第府的表演:一个女孩在悬于半空的一根粗绳上跳舞,如履平地;接着是两个男子倒挂在绳子上表演。而在1599年,小托玛斯·普拉特则详细描绘了“国王的喜剧演员”瓦勒兰在勃艮第府表演的情形。每天晚饭后,瓦勒兰都先表演一出法语韵文“喜剧”,然后是根据巴黎新近发生的风流韵事编排的一出“闹剧”。普拉特重点描述的是后面的闹剧。他说,瓦勒兰把他听来的逸事编排成一出“喜剧”(他同样把喜剧和闹剧混为一谈),中间点缀了令人捧腹的笑料,所有观众(包括只付半价站票的观众和付全款坐票的贵妇人们)都是奔着这出压轴的“闹剧”去的。①Pierre de L'Estoile, Mémoires-journaux 1574-1611, t. 7, Paris: Tallandier, 1879, pp. 299-300;Thomas Platter, Description de Paris, trad. L. Sieber, Paris, 1896, pp. 33-34.可见,“喜剧演员”在勃艮第府表演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戏剧并不完全相同。
小普拉特还说,巴黎也有来自意大利、英国等地方的“喜剧演员”。比如,有一次,他在大学附近看到一个西班牙人,不用手,单靠牙齿就能把一根通常装在干草车上的粗木举到额头或前胸位置,他脖子上的静脉几乎爆裂。这个西班牙人还能用舌头顶住十几片刀刃而不受伤。②Thomas Platter, Description de Paris, pp. 34-35.1598年在阿维庸逗留期间,他也经常去看一些“非常讨人喜欢的喜剧表演”,它们“通常是由意大利剧团,尤其是赞·布拉吉塔的剧团”在临时租用的老式网球场里或在广场上搭建的戏台上演出。这些“非常讨人喜欢的喜剧表演”是什么样的?普拉特并没有记下我们今天认为属于戏剧的内容,他主要记录的是演员惟妙惟肖地模仿鸟和动物的叫声,以及大砍人头的表演,或是在台上唱双簧向观众兜售据称是从土耳其得到的秘药。还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他同样描写了一个来自巴黎的演员在高空绳索上的表演。③Félix Platter & Thomas Platter, Félix et Thomas Platter à Montpellier, 1552-1559--1595-1599,pp. 391-395, 427-429. 换言之,当时的初代职业演员就是由杂耍等行当培育出来的,他们的表演仍带有这些行当的明显痕迹。
这些记录反映两个基本的现象。其一,当时的戏剧演员不仅表演戏剧,也表演杂技、脱口秀或相声(它们甚至成为主要的卖点),或者借助戏剧表演贩卖狗皮膏药等。正如斯特凡·赫尔费尔德所言,在1600年前后,小杂耍团体、意大利喜剧演员和江湖骗子团体仍然主导着喜剧和专业表演的定义,职业演员在技艺上仍然表现出与培育了他们的职业温床之间的联系。④Robert Henke,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atre in the Early Modern Age, p. 122.其二,当时的观察者和观众认为演员们表演的这些东西都是戏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艾罗阿尔的日记中,当时已十分成熟的英国戏剧在巴黎遭受冷遇,并不成熟的法国和意大利戏剧却大行其道,同样也可以解释瓦勒兰试图转向更严肃的戏剧演出时为何会遭遇失败。①瓦勒兰转型失败并被迫离开巴黎,参见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pp. 50-56.
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职业演员和剧作家,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比普通人还低贱。1619年路易十三替“改邪归正”的演员兼剧作家马蒂厄·勒费弗尔正名的诏令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诏令称,勒费弗尔出生于布列塔尼,父母早年让他学习文学,宗教战争期间,他弃学从军,为亨利四世的阵营作战。战争结束后,他以“拉波尔特”的艺名组织了一个剧团,在勃艮第府进行过多年极为成功的戏剧表演,并且成为亨利四世钦定的“国王的喜剧演员”。用诏令的原话说,他“创作过一些悲剧、喜剧、牧歌剧和其他诗歌,既有严肃的也有滑稽的,甚至亲自公开表演”。后来他认识到,“那些最庄重最严肃的人并不赞成该行业,于是他强烈希望退出”。1610年他弃演从商,成为国王诏令中所谓的“马蒂厄·勒费弗尔师傅”,但他仍担心“此前作为喜剧演员的经历会令他遭人反对和指责”,因而希望通过国王诏令为自己正名。路易十三满足了他的愿望,诏令宣布“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不能成为归罪和指责他的理由”,从今以后,他可以“和我们的其他臣民以及和他从事喜剧行业之前一样”享有各种荣誉、尊严和权利。②Emile Campardon, Les comédiens du roi de la troupe française pendant les deux derniers siècles : documents inédits recueilli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H. Champion, 1879, pp. 281-282.很显然,戏剧职业的经历成了勒费弗尔难以抹除的人生污点,甚至使他丧失了一个普通人本应拥有的名誉和权利。由此可见,尽管各种演出受到包括宫廷人士在内几乎所有人的欢迎,但演员们仍只被视作逗乐的小丑,而不是有尊严的个体,当时宫廷人士对一个职业演员的日常举止最大的夸赞是称其“不像演员”。③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p. 87-88.在贵族阶层看来,为金钱而创作和表演是可鄙的行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下面这个传说(无论是否属实)的发生机制就不难理解了:巴黎最著名的街头艺人、曾在1618年款待过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塔巴林退居该市附近一处精美的庄园,他那些具有社会等级意识的邻居却不喜欢有一位前江湖艺人住在附近,因而他在狩猎时被人“意外”地射死。④该传说参见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71.
三、宫廷社会⑤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主要指以王室为中心并围绕王权运转的上流社会。法国的宫廷社会大致在17世纪初形成,在路易十四中晚期达到顶峰。可参见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西欧宫廷社会的研究:诺贝特·埃利亚斯:《宫廷社会》,林荣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与戏剧艺术的诞生
1630年前后,法国戏剧界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件:“王家剧团”永久占据勃艮第府,与之竞争的剧团则逐渐在玛莱区的老式网球场站稳脚跟;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尔迪的剧作集正式出版;关于戏剧创作规则即“三一律”的辩论兴起并日趋白热化;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将戏剧创作、剧作家乃至演员纳入绝对国家①绝对国家(the Absolute State)是对绝对君主制国家的简称。学界对它在法国确立的时间多有争议。笔者认为,绝对国家在法国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16世纪甚至更早便已开始,在宗教战争结束后(尤其是在黎塞留主政时期)明显提速,至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的体制之中;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上演并大获成功。这些事件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法国戏剧发展到了一个质变的节点:戏剧表演和鉴赏正在变成一种艺术行为。
(一)悲剧和喜剧欣赏:宫廷戏剧趣味的“文明化”②这里的“文明化”(civilization)借用了埃利亚斯提出的概念,主要指特定社会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等由粗俗走向高雅的过程。
1636年,高乃依创作的悲剧《熙德》③高乃依最初把这出戏定义为悲喜剧,1648年以后定义为悲剧。在巴黎上演,万人空巷,轰动一时,这是法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学界对该剧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它的文学性上,但本文更看重它的文化史意义:它宣告了悲剧这个此前在法国备受冷落的剧种从此登堂入室,进而取代了闹剧的地位。学者们往往将其视为法国戏剧艺术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悲剧地位的改变并非由《熙德》独力完成的,《熙德》只是在长时间量变的基础上为戏剧的质变提供了爆发的契机,这种变化首先是在法国的宫廷社会中酝酿的。
如前所述,与现代文学艺术的评判标准一样,艾罗阿尔更看重的是悲剧和悲喜剧。然而,他的日记中所记录的戏剧演出状况与此形成鲜明反差,喜剧和闹剧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中并非孤例。让·博丹在1576年出版的《共和六论》中提到,“喜剧和杂耍演员(博丹把他们看作同一种人,后面用单数指代)是人们能设想到的对共同体危害最大的另一类害虫……如今人们总是在悲剧结束后表演闹剧或喜剧,就像在肉里放毒一样”。④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Gabriel Cartier, 1608, pp. 847-848.跟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博丹把喜剧和闹剧捆绑在一起,放到了悲剧的对立面。1615年前后,曾在勃艮第府演出的喜剧演员布吕斯坎比尔在一篇题为《为喜剧辩护》的短文里把喜剧和闹剧明确区分开来。他先是引经据典为喜剧做了诸番辩护,最后说:
“诋毁我们的人最后的反对意见是,我们表演悲剧和喜剧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一场充斥着丑陋言语的闹剧却把一切都糟蹋了,就像一场毒雨毁掉了我们最美丽的花朵。啊!真的,对此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这是谁的错呢?是愚蠢的大众迷信啊!人们认为没有闹剧,其他的表演就一文不值,花一半的钱却没有获得任何乐趣。只要你们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弃它,把它埋到永久遗忘的角落里去;它只会给我们的声誉带来难以承受的重创。实事求是地说,即便最纯洁的意大利喜剧的言行也比之堕落一百倍……”⑤Bruscambille, Les Nouvelles et plaisantes imaginations de Bruscambille, en suitte de ses Fantaisies, Bergerac: Martin la Babille, 1615, p. 120.
可见,在布吕斯坎比尔眼中,喜剧和悲剧具有同等价值,但主流观点显然不这么认为,所以他才有为之辩护的必要。这番言论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戏剧“鄙视链”:悲剧、喜剧、闹剧、意大利喜剧。总之,博丹和布吕斯坎比尔与艾罗阿尔一样更青睐悲剧,但戏剧演出却被观众低下的欣赏趣味“绑架”了。也正因如此,本文才把悲剧在戏剧市场上地位的改变视作法国戏剧成熟的一个风向标。在此种文化氛围下,以喜剧创作为主的阿尔迪在1626年把自己出版的作品集称作“悲剧集”也就不足为奇了。①参见陈杰:《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第108-109页。
不过到17世纪中叶,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戏剧理论家奥比尼亚克神父在1657年出版的《戏剧实践》中表示,在法国宫廷,悲剧比喜剧更受欢迎;而在“市井小民”(le petit peuple)中间,喜剧乃至闹剧和下流的滑稽剧比悲剧更令他们愉快。②Abbé d'Aubignac, La pratique du théâtre, Amsterdam: Jean Frederic Bernard, 1715, p. 64.奥比尼亚克神父早在17世纪40年代就已撰写该书,但由于黎塞留去世等原因,在10多年后才将其出版。他的说法表明,这一时期,法国宫廷社会的戏剧欣赏趣味已经与其他阶层拉开了距离,悲剧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而欣赏悲剧的能力也成了“文明化”的宫廷人士区别于普通大众的文化资本。这时距离高乃依的《熙德》上演不过数年,显然该剧也对这种趣味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悲剧的流行还意味着戏剧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取代了笑料和杂耍,成为吸引观众的核心要素,这是法国戏剧艺术化的重要标志。
奥比尼亚克神父的言论还反映出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让·博丹把喜剧和闹剧都视作“毒药”,作为演员的布吕斯坎比尔则试图把喜剧从闹剧的泥淖里拯救出来。乍一看,奥比尼亚克神父的态度似乎同博丹一样,仍旧把喜剧和闹剧甚至滑稽剧混为一谈。他甚至表示,喜剧、闹剧和滑稽剧根本不配进入戏剧诗的行列,因为它们没有技法,没有结构,没有理性,只适合卑鄙下流之徒,无耻、放荡的言行就是它们的全部魅力。③Abbé d'Aubignac, La pratique du théâtre, p. 132.但仔细分析发现,他只是在论及“市井小民”的戏剧时才把喜剧与闹剧和滑稽剧放在一起,而在宫廷之中则只有悲剧与喜剧之分。事实上,奥比尼亚克神父清楚地认识到,在古希腊罗马,喜剧的地位并不低下;而在“我们”的时代,喜剧之所以“长期以来不仅可耻,而且臭名昭著”,是因为“它堕落成了我们的剧院在悲剧之后必须忍受的闹剧或不得体的滑稽剧”,而这些闹剧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是为了取悦那些“市井小民”。④Abbé d'Aubignac, La pratique du théâtre, pp. 132, 348.换言之,他不仅看到了喜剧欣赏的阶级分化,也看到了喜剧在法国被“污名化”及与闹剧混同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结合布吕斯坎比尔等人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在17世纪20年代以前,无论是鉴赏还是演出,法国人普遍把喜剧和闹剧混淆在一起;1740年前后,这种状况在宫廷之外继续存在,但宫廷人士已经对两者做了区分,并把闹剧排除在了宫廷之外。
实际的戏剧演出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熙德》之前,初出茅庐的高乃依曾在1630年前后创作过若干颇为成功的喜剧,它们主要面向所谓的“高贵之人”(honnêtes gens),即上层社会,以活泼、愉悦为宗旨,从而与追求爆笑的闹剧拉开距离。其他剧作家也跟风创作了许多喜剧作品。阿兰·维亚拉称之为“喜剧的复兴”。①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p. 183-184. 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真正的喜剧此前从未在法国流行过。按照这个新标准,此前人们(包括艾罗阿尔)所谓的“喜剧”恐怕都属于闹剧。
确实,无论是瓦勒兰、拉波尔特、“大胖子”纪尧姆这些先后在勃艮第府演出的“国王的喜剧演员”,或是以塔巴林为代表的极受欢迎的街头表演者,还是来自意大利的演员,在当时都被称作“喜剧演员”,但时人最喜欢的是他们演的闹剧,而后世则称他们为“闹剧演员”(farceurs)。17世纪初,当瓦勒兰试图转而表演更为严肃的戏剧时,就败给了意大利演员以及刚刚冒头的新一代法国闹剧演员。“大胖子”纪尧姆代表了最典型的闹剧演员的形象:据说他个子很矮,却胖得出奇;他身上总是缠着两条皮带,这让他走起路来就像个大酒桶。然而,一直到17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流社会仍然极受欢迎(尽管不受尊重),不少贵族都模仿过他。②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65.这些演员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散文、诗歌和绘画作品中,不过他们的作品很少被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即兴创作的短剧,剧本的文学价值不高。③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p. 59, 62.
这些闹剧对演出的环境要求不高,观众观看时也总是吵闹不休。无论如何,保持安静在这个时期绝非观剧的礼仪要求,哄笑甚至吵闹才是戏剧追求的效果。但1640年前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大胖子”纪尧姆的闹剧被蒙托里和“俏玫瑰”(Bellerose)等更优雅的喜剧和悲剧表演所取代。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被布吕斯坎比尔排在闹剧之后的意大利戏剧也在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失宠了近二十年时间。④参见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145; Alan Howe et al., Le théâtre professionnel à Paris, 1600-1649, pp. 164-166。尽管阿兰·豪的研究表明情况不完全如先前预想的那样,但意大利演员失宠仍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1634年蒙托里的剧团改造玛莱区的老式网球场并入驻之后,驻扎在勃艮第府的“王家剧团”也提出了改建剧院的要求,他们也发现这所建造于80多年前,且至今仍是巴黎唯一专业剧院的场所已经过时,但其主人耶稣升天兄弟会拒绝了剧团的要求。在勃艮第府剧院中,观众可以坐在高层包厢或站在地堂里看戏。夏尔勒·索雷尔在1642年出版的《游戏之屋》中说,因为包厢位置不好,只能从很远的侧面看到演员,所以许多“骑马和坐马车”的上层社会观众宁愿与“走路”的市民挤在地堂里。地堂里鱼龙混杂,拥挤不堪,很不舒服。更重要的是,数以千计的无赖汉总想无事生非地跟“高贵之人”干上一架,他们也会不停地说话、吹口哨和大喊大叫。⑤Charles Sorel, La maison des jeux, Paris: Antoine de Sommaville, 1657, pp. 406-407, 463-464.索雷尔的话语中隐含着一种对安静的观戏秩序的新要求。无独有偶,根据1633年出版的古热诺的《喜剧演员的喜剧》,演员“俏玫瑰”也在演出前特别赞扬了观众安静和守秩序的品质。①Nicolas Gougenot, La comédie des comédiens, Paris: Pierre David,1633, pp. 1-5.
索雷尔还说,勃艮第府以前只是一群粗鲁无礼的街头卖艺者的寓所,只有巴黎的社会渣滓才去那里看戏,但现在那里有了杰出的喜剧演员,他们由国王和王公贵族供养,表演严肃认真的戏剧,值得品性高尚之人和严肃的哲学家一看。在此之前,除了阿尔迪,没有剧作家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演员的海报上,因为他们不敢宣布自己是那些烂戏的作者。如今情况不同了,现在的喜剧写得非常好,在海报上署名能给人带来荣誉。②Charles Sorel, La maison des jeux, pp. 409-410.对于索雷尔之前所谓的只有“巴黎的社会渣滓”才去勃艮第府看戏的说法,我们不必太当真,因为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以及许多贵族都在那里看过戏。萨拉·比恩则指出,没有证据显示最贫穷的巴黎人去过勃艮第府,相反,观众都是识字的市民,甚至是巴黎的贵族。③Sara Bean, Laughing Matters: Farce and the Making of Absolutism in France,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9.因此,我们或许应当把这种言论视作索雷尔这一代人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法,其目的是表明时代风尚的进步。不过,他的话仍然表明,巴黎的戏剧创作水平在这些年有了很大的提升。索雷尔还表示,有一些顽固坚持身份的上等人认为到地堂看戏是一种耻辱;而在听到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小丑说的话时,他们就会不屑地说那是讲给地堂的人听的笑话,尽管地堂里并不缺少上等人和有鉴赏力的“诗人”。④Charles Sorel, La maison des jeux, pp. 463-464.迪尔考夫-霍尔斯波尔夫人在罗列勃艮第府的不足时,同样对不同阶层的观众混杂在一起表达了不满。⑤Alan Howe et al., Le théâtre professionnel à Paris, 1600-1649, p. 155.因此,尽管在同一所剧院里看戏,但不同阶层的欣赏趣味已经明显分化,上层社会甚至出现了在物理距离上与市民阶层区隔开来的愿望。1644年被焚毁后重建的玛莱剧院,1647年最终得到翻新的勃艮第府,1641年落成的黎塞留的宫廷剧院,加上一众新兴的王家剧场,最终在不同层次上解决了上层观众的关切。同时,这些新剧场大量引入了机械装置以实现奇观效果,它们帮助演员摆脱了杂耍艺人的身份,而专注于戏剧表演本身。
与闹剧分离令喜剧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不过,奥比尼亚克神父的评价也表明,即使在宫廷,喜剧在此时仍无法与悲剧比肩。喜剧真正实现艺术化还要等到莫里哀的出现。无论如何,到17世纪中叶,戏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体裁的地位已经确立:从1642年高乃依的《辛纳》(Cinna)开始,文学财产权利适用于戏剧的原则得到了认可,意味着一直被称作“诗”的戏剧真正获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⑥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166.
(二)绝对国家与戏剧地位的提升
闹剧的衰落以及悲剧和喜剧的流行使法国戏剧的文学艺术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绝对国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直接地、决定性地提升了戏剧及其从业者的地位。虽然法国的职业剧团一直向国家和贵族寻求保护(后者也乐于提供这种保护),并以国王或大贵族的“喜剧演员”或“国王的诗人”自居,但真正的制度化运作始于1629年黎塞留主政时期。这位首相在法国戏剧制度化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国王路易十三。对于这个问题,W. L.威利、阿兰·维亚拉、卡特琳·吉约、陈杰等学者都有过较深入的探讨。①参 见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Catherine Guillot, "Richelieu et le Théâtre", Transversalités, 2011/1 N° 117, pp. 85-102;陈杰:《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总的来说,绝对国家干预戏剧生活的主要手段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保护和赞助剧作家及其创作。比如将剧作家纳入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为其提供年金,开展有组织的戏剧创作等。对于这一问题,前述学者已有诸多研究,这里主要就学者们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做一点探讨。前文引述过一份路易十三于1619年为“弃戏从商”的演员兼剧作家拉波尔特恢复名誉的文献,它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剧团的当家演员兼任剧本作者应当是当时法国主流的戏剧创作模式,像亚历山大·阿尔迪这样的职业剧作家屈指可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17世纪2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剧本不多且质量不高。其次,在上层社会人的眼中,职业剧作家和演员的地位都不高,甚至低于普通市民。但演员和职业剧作家遭到歧视的原因并不相同:对前者的歧视主要是出于道德和宗教的原因,看不起后者则因为卖文为生辱没了上流社会极为看重的文化的尊严,甚至在高乃依因为《熙德》一剧声名大噪之后,掌握了文学权力的宫廷贵族夏普兰仍旧把他视作可鄙的“为钱而创作的诗人”(poète mercenaire)。②参见陈杰:《十七世纪法国职业文人剧作家的诞生》,第89-90页。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学者未曾充分探讨的问题,它在高乃依事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634年,黎塞留组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他的戏剧理想的“五人剧作家”团队,以创作符合“三一律”③Règle des trois unités,即“三个统一的规则”:戏剧活动集中在一个主要事件上,于24小时之内在同一个地点展开。新规则、宣扬“文明化”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宏大的戏剧叙事和演出场面宣扬黎塞留和法国在欧洲的突出地位的戏剧作品,其中许多戏剧都是他本人的“命题作文”。高乃依原本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但不久便退出,很可能是因为他受不了这种刻板的创作模式。退出之后,他很快就创作了引起巨大轰动的《熙德》。尽管《熙德》在市场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它同时也遭到主张新戏剧规则的“规则派”剧作家的口诛笔伐,以致法兰西学院在黎塞留的授意下做出了不利于高乃依的裁决。对高乃依不满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人不满他表现的英雄主义情怀,特别是他正面表现被绝对国家反复明令禁止的贵族决斗;有些人非议他违反首相主导的戏剧创作规则;有些人则纯粹是文人相轻。此外,高乃依“市侩”(“不高贵”)的创作方式也是他受到非议的一个原因。因为在退出“五人剧作家”团队,离开黎塞留的庇护之后,高乃依主要为玛莱和勃艮第府剧院的职业剧团创作,而不再服务于以黎塞留为代表的掌权者。相比之下,有些人则明确宣布自己就是为了取悦黎塞留才创作的,甚至在黎塞留死后便放弃了戏剧创作。①参见Catherine Guillot, Richelieu et le Théâtre。换言之,在他们以及当时大部分宫廷权贵看来,剧作家为市场效力是可耻的,为体制和当权者效力才是光荣且高尚的。
这种源自法国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的观念是17世纪法国贵族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许多贵族作家都以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为耻。塞维涅夫人说:“在图书馆里或者更糟糕的是在集市上的书店里见到自己的作品,这不仅有失体面,也有损于高贵的出身。”斯居代里小姐则说:“写作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高贵。”所以,塞维涅夫人的书信最初仅在一个特定的圈子内流传,它的出版纯属意外;斯居代里小姐最早的小说是用她哥哥的名字出版的;拉法耶特夫人至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克莱夫王妃》的作者。在18世纪的英国,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仍然反复强调高贵的男人和女人不应该出版作品,所以在她死后,她的女儿觉得应该把母亲的日记烧掉。②N. Z. Davis and Arlette Farge, ed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III: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Paradoxe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1-412.出于同样的道理,黎塞留尽管经常指定“五人剧作家”的创作主题,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夏普兰则只肯在戏剧演出时承认自己是作者,却拒绝在出版的剧本上署名。③参见陈杰:《十七世纪法国职业文人剧作家的诞生》,第115-116页。与此相应的是,有学者指出,在17世纪,贵族教育的宗旨并非造就饱读诗书的学者,即文化作品的生产者,而是培养“在行的观众”,即文化作品的鉴赏者。④Donna Bohanan, Crown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4.由此看来,在宫廷贵族眼中,文化欣赏比文化生产高贵,为体制创作比为市场创作高贵。
总之,尽管剧作家分为不同等级,但通过国王、大臣和宫廷社会,他们被纳入国家的文化体制之内,这一做法既显著提高了剧作家的收入,也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⑤此前剧作家主要依靠市场获得收入,主要包括演出和出版两个方面,参见J. Lough,"The Earnings of Playwrigh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42,No. 3 (Jul., 1947), pp. 321-336。黎塞留死后,国家一度停止保护和资助,导致剧作家的收入和地位急剧下滑。17世纪的安托万·菲勒蒂埃称,此时的剧作家不得不依靠演员和出版商提供的微薄版税度日,他们有些人“屈尊为喜剧演员、画家和出版商服务,……或为生计所迫,做点……翻译活计”。⑥Antoine Furetière, Nouvelle allégorique ou Histoire des derniers troubles arrivez au royaume d'éloquence, Amsterdam, 1658, pp. 98-101. 转引自J. Lough, The Earnings of Playwrigh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p. 325.另外,绝对国家则通过这种依附关系空前地加强了其权威和对剧作家的控制,违背绝对国家意志的剧作家将受到制裁。对戏剧创作而言,这种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16世纪曾经十分盛行的政治和宗教讽刺戏剧在17世纪头几十年逐渐消失①这方面的研究参见Sara Bean, Laughing Matters: Farce and the Making of Absolutism in France。,戏剧转而为从宫廷社会开启的“文明化”进程服务,并在18世纪将这种“文明化”推广到市民阶层。
第二,为演员正名。尽管剧作家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但他们的收入仍远低于演员,而后者也并不乐于付钱给剧作家。17世纪的拉布吕耶尔对剧作家与演员之间的这种反差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喜剧演员躺在豪华的四轮马车里,车轮甩起的泥浆溅在步行的高乃依脸上。”②Jean de La Bruyère, Les caractères, Paris: Flammarion, 1880, p. 261.确实,曾以主演高乃依戏剧出名的演员蒙多里在1638年因为舌肌麻痹症而过早退出舞台,但他在十年后仍有能力向国王的司库提供高达26,760里弗的贷款。③Alan Howe et al., Le théâtre professionnel à Paris, 1600-1649, p. 189.相比之下,高乃依只能在穷困中度过晚年。莫里哀的演出收入同样远超过他的版税收入。④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170.不过,就社会地位而言,尽管有些职业演员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就已获得“国王的喜剧演员”的称号,但后来他们的整体社会地位却日渐低于剧作家。
17世纪30年代前后,在勃艮第府和玛莱剧院演出的职业演员与街头表演者的差距明显拉大。闹剧逐渐淡出这些舞台,被更高雅的悲剧和喜剧取而代之,演员在舞台上下的举止也更加符合上流社会的规范。比如勃艮第府的“俏玫瑰”力图以一种更自然的表演风格取代其法国和意大利前辈们的粗俗华丽和夸张滑稽;玛莱剧院的蒙多里经常出入宫廷的文人雅士圈子,举止优雅得体,被奥比尼亚克神父称作“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在这一背景下,演员们也迫切希望把自己与臭名昭著的街头艺人区别开来。⑤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p. 81, 98; Catherine Guillot, Richelieu et le Théâtre.
绝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演员们的愿望。勃艮第府和玛莱剧院的演员们与剧作家一样,也得到了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保护。黎塞留甚至设想合并巴黎的职业剧团,并由国家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和控制,这个设想最终在路易十四时代得以实现,即1680年法兰西剧院的成立。⑥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271.路易十三在1641年颁布的一份诏书经常被学者引用,它通常被描述为国王替演员这一职业辩护的诏令。该诏书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宗教立场谴责“喜剧演员”们不体面的表演给观众带来的心理危害,故而“明令禁止任何喜剧演员进行任何可能有违公序良俗的不道德表演,或使用淫秽或双关的言语,违者将被宣布为失德并处以其他处罚”;第二部分宣布,“只要喜剧演员的戏剧表演无任何不雅内容,朕不希望他们由于那些让人们远离恶事的无罪表演而遭受指责,或因此令他们的公共名誉受损”。①诏令原文参见Charles Mazouer: Le théâtre français de l’âge classique, t. 1,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6, pp. 139-140.该诏令实际上是以国王的名义正式宣告传统的闹剧为非法的表演,并从表演的方式和内容上在闹剧演员和较严肃的戏剧演员之间做了区分,反映了后者的时代诉求。同时,它也体现了王权把戏剧纳入绝对国家体制的强烈愿望。与1619年诏令相比,1641年的王室诏令不再把从事戏剧职业本身视作原罪,并声明“正经”职业演员的名誉是无可指摘的。
尽管W. L. 威利指出法国的职业演员直到18世纪才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②W. L. Wiley, The Early Public Theatre in France, p. 81.,但绝对国家的上述努力在17世纪已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保尔·斯卡龙在17世纪中叶表示,在他那个时代,演员的职业在某些方面已经得到认可,他们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评价。③Paul Scarron, Le roman comique, t. I, Paris: P. Jannet, 1857, pp. 315-316.
第三,制定并大力推行戏剧创作的新规则,推动剧本的文学化和戏剧演出的艺术化。1628年以前,法国人不怎么关注戏剧创作的规则问题,戏剧的语言和情境也很随意。但在这一年,法国戏剧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戏剧及其创作规则的激烈辩论,围绕“三一律”等创作规则,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从此分成“规则派”和“反规则派”两个阵营。1630年,黎塞留身边掌握着文学权力、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创始成员的夏普兰写了一封影响深远的《关于二十四小时规则的信》,标志着“规则派”理论的体系化,戏剧创作规则的问题由此进入绝对国家体制的视野。1636年高乃依的《熙德》上演,戏剧规则之争趋于白热化,许多剧作家要求新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就《熙德》的问题做出裁决。1637年底,经黎塞留授意,由夏普兰执笔,法兰西学院裁定《熙德》在诸多方面违反戏剧创作的规则,标志着“规则派”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在这之后,高乃依也努力使自己的创作符合“三一律”的规则。通过介入戏剧规则之争,绝对国家在戏剧创作领域获得了最高的权威。
另外,对创作规则的空前关注(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些规则),也使剧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维度。在此之前,法国戏剧的剧本基本上都是为舞台演出而临时拼凑的,这样的剧本不可能有多少文学性。戏剧规则之争促使戏剧界对剧本的创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剧本从此同时具备了既适合舞台演出又适合阅读的特性。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戏剧舞台对剧本的要求不再是一味求新,剧本变得可以重复排演,戏剧演出由此走向经典化、规范化、艺术化。
奥比尼亚克神父在17世纪中叶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为他那部《戏剧实践》起了一个很长的副标题——“愿意从事戏剧诗写作、公开诵读或观看其演出的人的必备读物”,其实也说明了戏剧创作和表演已经成为正当的职业,同时它还意味着戏剧欣赏不再是人人皆可为之,而是变成了具有艺术门槛的高雅的文化活动。同一时期的保尔·斯卡龙也说,人们在戏剧中发现了一种最纯真的消遣方式,它既能给人以启发,又能给人以快乐;至少在巴黎,戏剧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放荡。①Paul Scarron, Le roman comique, t. I, pp. 315-316.因此可以说,法国戏剧的艺术化之路到17世纪中叶已基本完成,尽管要等到路易十四时代才得以完善并走向巅峰,②可参见洪庆明:《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史林》,2016年06期,第155-164页。到18世纪才最终扩展到市民阶层之中。
结语
在近代早期的法国,随着专业化和艺术化的戏剧占领乃至垄断了戏剧舞台,传统“游戏-戏剧”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并走向衰落,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狂欢文化和狂欢社团的衰落。③关于近代早期法国狂欢文化和狂欢社团的衰落,参见拙文《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即使这些“游戏-戏剧”在下层社会仍零星存在,但它们在精英阶层主导的话语体系里已不被视作真正的戏剧。而且如前文所见,从17世纪开始,法国人逐渐不再用jeu来指称戏剧。对于城市中上层来说,戏剧不再关乎世界观,而变成了一种休闲活动。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戏剧的表演和接受,相对忽略对剧作家和戏剧文本的探讨,原因之一在于剧本在现代戏剧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历史上,至少在戏剧文学化之前,剧本远不如表演和接受来得重要,而有关后者的史料却往往零散乃至阙如。即使在戏剧文学化和艺术化之后,表演和接受仍是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阿兰·维亚拉提出,莫里哀的许多戏剧只有加上了幕间插曲和芭蕾舞才具有完整的意义。④Alain Viala, Le théâtre en France, p. 195.这个提示尽管有益,但仍然忽略了受众的重要性。没有表演和接受的戏剧史研究是不完整的,甚至容易失之偏颇。而且,这两个维度也有助于将戏剧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楚地揭示戏剧发展的脉络及其与整体社会的联系。
关注表演和接受也有助于解释戏剧史研究的其他问题。比如,为何意大利有灿烂的诗歌和绘画,却没能出现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辉煌的古典戏剧?这也许是因为与诗歌和绘画相比,戏剧需要有更广的受众群体。意大利拥有相对早熟且足够庞大的市民阶层,能够支持市民戏剧特别是闹剧的发展,因而这些意大利戏剧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就高雅戏剧来说,意大利各城邦的小宫廷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宫廷规模则没有这种问题。另外,尽管意大利的市民戏剧相当发达,但它们在文学史上却没有相应的地位。这无疑是片面关注剧本失之偏颇的一个例证。再比如,戏剧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本文对此有所涉及,但仍远远不够。亨利·雷伊-弗洛曾提出,在中世纪的社群戏剧时代,方言差异强化了戏剧(游戏)的自由度,使得戏剧和语言一样促进了社会和认同的分裂。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与其他的城镇或省份不一样,而戏剧也是其身份特殊性的表达之一。①Henri Rey-Flaud, Pour une dramaturgie du Moyen Age, p. 78.推而言之,或许我们还可以探讨17世纪由法兰西学院主导的戏剧规范化运动和用语更加规范的文学化戏剧的流行与绝对王权的建构,以及与法兰西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