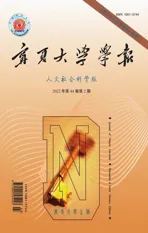从古代文学嘲谑传统看陆游自嘲诗创作
2022-11-22朱子良
朱子良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自嘲诗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我对话性质的诗歌题材,对创作者的情感状态有较强的揭橥作用,往往能成为读者观照创作主体的一面镜子,这是本文赖以展开陆游研究的逻辑起点。陆游一生创作颇丰,曾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出版、由钱仲联校注的《剑南诗稿校注》就载录其诗九千余首。笔者在阅读这些诗歌的过程中发现了陆游创作的大量以《自嘲》《自笑》为诗题或诗题中包含“自嘲”“自笑”字样的自嘲诗(狭义的自嘲诗),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诸如《自咏》《自述》《迂拙》《砭愚》等为题语涉“自嘲”特征鲜明的自嘲诗(广义的自嘲诗),两项共计200 余首。然而古代文学界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赋体文学中“自嘲”意识的溯源。如胡春润、石观海《东方朔的〈答客难〉在文学史上的功创》(《求索》,2008年第2 期)一文就肯定了东方朔《答客难》在“设论”赋体诗上的首创之功与其中的“自嘲自解”意味,并揭示了此篇对扬雄、班固等人一系列“设论”解嘲文学创作的启发与影响。伏俊琏《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辽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 期)亦持此论,认为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重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嘲谑”“诙谐”传统,但尚缺乏对自嘲诗形成脉络的清晰观照。刘佳宁《北宋中期俳谐诗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偲《魏晋南北朝俳谐诗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相关研究梳理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嘲谑文学或俳谐传统的发展与流变,自嘲诗作为其全面鸟瞰式考察中之一隅仅获得了较为粗略的论涉。其他关于自嘲诗这一题材的研究则基本囿于对唐一代少数名家以及苏轼、黄庭坚等的考察。陆游的自嘲诗还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少,且不够深入,仅有一些论著对此作了初步探讨。笔者目力所及的如周斌《宋代俳谐诗研究》(浙江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有涉及陆游自嘲诗的评述,文章剖析了陆游以“自嘲”的心态对“衰老”“贫困”等诗歌题材中哀感悲情的稀释与淡化。此外,陶文鹏《自嘲的丰富情味》(《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 1 期)、王德明《从陆游的“戏作”看其诗歌创作的幽默调侃风格》(《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 2 期)、商宇琦《陆游“戏作”诗的独创性》(《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2 期)以及李华云《陆游巴蜀诗歌的戏谑书写》(《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 3 期)、蒋瑜《宋士人自我书写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亦涉及了陆游的自嘲诗创作,但论述的篇幅均不长,探析亦不够全面,不能算作专门的研究。陆游的自嘲诗研究还存在较大可供开拓的学术空间。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嘲谑传统的维度考察陆游的自嘲诗创作,以期厘清自先秦文学以来嘲谑基因下自嘲诗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兼述陆游自嘲诗在此发展脉络中的独特风貌与价值,并以自嘲诗这一特殊题材的探析推动古典诗史中更为立体全面的陆游形象建构。
一 中国古典文学中自嘲诗的孳萌进程
沿着自嘲诗的发展谱系回溯,先秦典籍中的嘲谑描写无疑是这一诗歌题材的渊薮。《诗经》中有一些作品刻画了善于调笑的人物形象或描写了相互戏谑的生活画面,如《卫风·淇奥》中便有“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2]的句子。《诗经》中的某些比喻亦常常带有强烈的嘲谑意味,如《豳风·狼跋》中的“狼”、《邶风·新台》中的“蘧篨”“戚施”、《魏风·硕鼠》《鄘风·相鼠》中的“鼠”等等。诸子散文中亦有众多诙谐嘲谑书写,主要表现在怪诞滑稽的艺术形象、诙谐机巧的言语说辞以及喜剧性的情节冲突与滑稽的人物行为方面。尤其是诸子散文中为数众多的“愚人”形象更是中国古典嘲谑文学的滥觞,如《庄子·秋水》中“邯郸学步”的燕人形象、《孟子·公孙丑上》“揠苗助长”的宋人形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买椟还珠”的郑人形象等等。当然,作为自嘲文学的直接源头,先秦文学中的自嘲意识无疑与自嘲诗具有更密切的基因关系。《诗经·邶风·简兮》一诗之主旨历来解读不一,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观点乃以朱熹为代表的“失意玩世”说。《诗集传》解此诗云“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3]朱说影响颇大,后世从其论者甚多,如清刘熙载《艺概》亦云:“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4]。此外《诗经·陈风·衡门》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5]魏裕铭论此诗“骨子里充满着对昔日的自豪、对今日的沉痛、自嘲和自慰”[6],也点出了《诗经》中的自嘲色彩。其他典籍如《左传·僖公三十年》中烛之武面对郑伯的征辟时所言:“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7]这段话虽然是烛之武以退为进之策,婉讽郑伯不重人才,但却也带有明显的自嘲意味。《道德经》中“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8]以及《庄子·外篇·秋水》中“庄子钓于濮水”一段,庄子把自己比作一只在烂泥摇尾的乌龟——“吾将曳尾于涂中”[9],都隐约带着几分自我调侃的味道。还值得注意的作品是《楚辞》中的《招魂》一篇,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论此篇“故为不检之言以自嘲”[10],联系该篇悲愤谐谩的特点,所言不为无据。以上带有自嘲意识的作品实可视为自嘲诗之椎轮。
降至汉魏六朝,俳谐赋中的自嘲意识开始逐渐凸显。目前已知最早的自嘲俳谐赋是东方朔的《答客难》。《答客难》假托一客难己而自予辩驳,实际上是东方朔的自嘲与自解。《答客难》用设论赋体开创了一条文人通过自我对话、自我嘲谑从而达到自我慰藉的门径,体例的创新赋予了这种设论体自嘲赋蓬勃的生命力,而风格的诙谐则为文人在表达愤慨与自我嘲谑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从而既不在立意上显得剑拔弩张,也出离了纯粹的滑稽调笑,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类似作品的规摹范本。自东方朔《答客难》之后,扬雄《解嘲》继之,班固《答宾戏》承之,汉魏六朝出现了一大批设论辩难的赋作,主要有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答讥》、蔡邕《释诲》、陈琳《应讥》、郤正《释讥》、郭璞《客傲》等等,自嘲类俳谐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阶段嘲谑意识也开始在诗歌领域凸显,嘲人诗(按指嘲谑他人的诗作,与自嘲诗别为一类)创作逐渐兴盛,产生了诸如费祎《嘲吴群臣》(凤皇来翔)、薛综《嘲蜀使张奉》(有犬为独)、程晓《嘲热客诗》(平生三伏时)、习凿齿《嘲道安诗》(大鹏从南来)等大量作品。与先秦时期的嘲谑作品相比,汉魏六朝嘲人诗的嘲谑目的更为直接与明显,嘲谑对象更为精准而集中,嘲谑效果更为生动和强烈。虽然此时成熟的自嘲诗还未出现,但一些诗篇中的自嘲意识已经颇为强烈,如陶潜《乞食》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一联就被明人黄文焕认为“是落落不治生产面孔,自嘲实自誉”[11]之语,《杂诗十二首》其八亦被黄认为乃“自嘲自解”[12]之作。此外,应璩的《百一诗》中已经存在集中且明显的自嘲章节:“少壮面目泽,长大色丑粗。丑粗人所恶,拔白自洗苏。平生发完全,变化似浮屠。醉酒巾帻落,秃顶赤如壶。”[13]这些诗均可视作自嘲诗的雏形。
唐宋时期嘲诮诗高度繁荣,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无一例外都有嘲诮诗的创作。尤其在宋代,不论是普通文人,还是理学大家,亦或是僧道高士都普遍以诗歌相嘲诮,嘲诮诗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交手段,成为文人互相切磋、增进情谊的方式之一。其中自嘲诗也最终走向成熟,自嘲作品大量涌现,体裁完备,成为诗人凸显生命意识、表达主体诉求、抒发人生感慨的重要载体。贫穷、老丑、迂阔、失志是唐宋自嘲诗的四大经典主题,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为失志类自嘲诗,代表作如杜甫的《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王禹偁的《自嘲》(三月降霜花木死)等等。宋代失志类自嘲诗数量尤为丰赡,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宋代党争激烈,文人的迁谪频繁,苏轼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黄庭坚《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肉食相)、陆游《自笑》(宦途昔似伏辕驹)等都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唐宋自嘲风气异常浓郁的时代背景下,陆游创作了大量情感丰沛、艺术精湛的自嘲诗。
二 陆游自嘲诗内涵的多维指向
陆游的自嘲诗大多以游戏心态出之,主要表现出他对贫困的自我戏谑、衰老的自我慰藉以及功名的自我嘲诮,反映了陆游旷达萧散的性格特征,侧面揭示了宋代士子理性通脱的时代气质,更显示了陆游诗风幽默诙谐的一面。当然其中亦有不少“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14]的作品。
《论语》中“孔颜乐处”思想对中国传统士子的贫居态度影响颇巨,这可以从贯穿于扬雄《逐贫赋》以降的一系列咏贫作品的主旨中得到证明。在陆游的自嘲诗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种思想对宋代士子人格的锻造。试看《自笑》诗:
自笑谋生事事疏,年来锥与地俱无。平章春韭秋菘味,拆补天吴紫凤图。食肉定知无骨相,珥貂空自诳头颅。惟余数卷残书在,破箧萧然笑獠奴。[15]
诗的首联以“自笑谋生事事疏,年来锥与地俱无”狠狠嘲谑了自己一把,“贫无立锥之地”已是贫极,可陆游却说穷得连锥都没有。这种打趣是宋诗的一大特性,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机锋的影响,《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记香严禅师偈:“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无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16]可示此句渊源。颔联“平章春韭秋菘味,拆补天吴紫凤图”连用二典以谑清贫,典雅而不失幽默。出句用周颙事写食物之粗,《南史·周颙传》载:“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17]对句则化老杜诗写衣物之敝,杜甫《北征》诗有“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18]几句状小女衣物补绽颠倒之况。与上诗意味略近的还有《饭后自嘲》诗:
岁熟家弥困,天寒酒阙倾。仅能炊稻饭,敢望糁藜羹。一榻解腰卧,四廊摩腹行。诗人要疏瘦,此日愧膨脝。[19]
诗人以“岁熟家困,天寒缺酒”自状其穷,颔联说今天难得吃了一顿饱饭,于是以“一榻解腰卧,四廊摩腹行”来描写自己的快意。惬意之余他又用宋代诗人惯有的机趣嘲谑了自己一番,诗人要的是清癯的形象,今日得以饱腹,倒有损了平日里仙风道骨的诗人气质。诗人的幽默、旷达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此类诗如《戏作治生绝句》(治生何用学陶朱)、《戏作贫诗二首》(垂老贫弥甚)、《苦贫戏作》(五穷作祟不容支)、《岁暮贫甚戏书》(阿堵元知不受呼)等,均可视作儒家“孔颜之乐”思想潜流在文人生命意识中的注脚,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讲到。
嗟叹“衰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题材。刘熙载云:“《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20]指出《诗经》时代人们就已经在诗歌中流露出对生命衰老陨落的忧惧意识。宋人超迈理性的时代风气使当时的士人较能通脱地对待生命的陨落,甚至以自己的衰老自谑自嘲,陆游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朋侪什九堕丘墟,自笑身如脱网鱼。委命已悲吾道丧,垂名真负此心初。齿残仅可决濡肉,眼涩知难读细书。家事岂容关老子,儿曹努力事耕锄。(《叹老》)[21]
此诗作于陆游七十四岁高龄(按文中涉及陆游诗歌之创作时地,主要依据为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与于北山《陆游年谱》——作者注),首联“朋侪什九堕丘墟,自笑身如脱网鱼”既是对死神的戏谑,同时也是寿高者孤独的自嘲。陆游一生期以武功垂世,然而蹉跎到老,却只空赢得诗坛高名,这正是颔联“委命已悲吾道丧,垂名真负此心初”的潜悲所在,用陆游评价杜甫的一联诗以申此诗之旨是再合适不过了——“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22]这与朱东润所言:“陆游对于自己的估计,是一位深通经术、能为国家担当大事的人物”[23]的结论是相牟的。此类自嘲如《白发》(白发今年一倍增)、《晨镜》(晨起览清镜)、《自嘲》(天公大度一何奇)等大多是以通脱的心态进行自我开解与勉励,颇可照证宋人乐观旷达之文化性格。
“痴顽”也是陆游常常自我揶揄的一个视角,但此类自嘲诗往往具有多重意蕴,不可一概而论,下面试举典型三例稍作探析:
痴顽老子老无能,游惰农夫酒肉僧。闭著庵门终日睡,任人来唤不曾应。(《龟堂杂题·其二》)[24]
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放开绳棰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日落苔矶闲把钓,雨馀篷舵乱堆蓑。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自咏》)[25]
小市朝行药,明灯夜读书。虽殊带箭鹤,要是脱钩鱼。有饭已多矣,无衣亦晏如。坚顽君勿怪,岂失遂吾初。(《坚顽》)[26]
从上面的诗歌可以看出,陆游自嘲诗中的“痴顽”主要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含义即“无用”,意在调侃自己不通世务、难堪时用,我们从《龟堂杂题·其二》首联“痴顽老子老无能,游惰农夫酒肉僧”即可读到这个意思。《剑南诗稿》中还有许多自嘲诗句与此类似,如“老去痴顽百不能,非醒非醉日腾腾”(《野兴四首》其二)、“无材无德痴顽老,尔来对客惟称好”(《醉歌》)等。第二层含义则体现了陆游玩世不恭、人生如梦的思想,我们看上列《自咏》诗首联“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正表达了这个意思。这样的作品在陆游诗集中也有不少,我们再举一例以佐,《遣兴》诗云:“老子痴顽惯转蓬,残年懒复问穷通。赦书虽未除诗债,盟府犹当策酒功。桐岭市回人踏月,柘冈月落鸟呼风。浮生触处无真实,岂独南柯是梦中。”[27]。第三层含义则表达了陆游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的精神。朱东润评陆词《鹧鸪天·葭萌驿作》(看尽巴山看蜀山)时曾云:“‘顽’是陆游的秘诀。正因为他顽强,他从夔州匹马北上,家室的牵挂,道途的困难,一切都不放在心头。”[28]上举《坚顽》诗中“坚顽君勿怪,岂失遂吾初”等句之意蕴亦庶几近之,均可视作陆游“顽强”性格之写照。
毋庸讳言,陆游身上也具有传统士子“一边要建立一番功业,一边又因为遭到谗言而灰心消极”[29]的矛盾性格,这种矛盾性格的集中体现即其诗歌中一再流露出的对于功名执念的自嘲与林泉高风的向往。隆兴元年(1163年)陆游遭贬出都,距上次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以敕令所罢”[30]才甫过一载。陆游的开始出仕是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担任福州宁德县主簿,短短五年他已经历经多次贬官了,对此他时借诗歌以发深喟。比如作于此次被贬时的《出都》诗:
重入修门甫岁余,又携琴剑返江湖。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缘熟且为莲社客,伻来喜对草堂图。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31]
从“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一联来看,仕途的频繁波动已经让年轻的陆游在“仕”与“隐”的问题上有了一些模糊的思考,“自愚”正透露出这种关于自我价值思考的讯息。颈、尾二联则是这种思考的进一步延伸,他似乎完全表露出自己的隐逸之心了,决定效仿慧远、谢灵运等人结社匡庐的高风逸行,安心过“草堂”“西厢”“高枕看云”的隐士生活,但这只是文人的一种牢骚,是大可不必当真的。这一类诗歌通常是陆游在仕途受挫后情绪低靡的反映,这固然显示了陆游身上具有传统士子畏葸的通病,但也侧面凸显了陆游在与这种人性弱点反复斗争下的伟岸与坚毅。《剑南诗稿》中《书怀》(武担山上望京都)、《自笑》(三间茅屋寄沧浪)、《闲中自嘲》(镜湖西畔有渔扉)、《遣兴》(鹤料无多又扫空)等诗均属此类,这类自嘲诗是最能体现朱光潜所谓“诗在有谐趣时,欢欣与哀怨往往并行不悖”[32]之特点的,乃陆游自嘲诗中情感蕴含最勃郁的一类。
三 陆游自嘲诗的艺术风貌与突破
陆游作为宋代诗坛的一代巨擘,在自嘲诗的创作数量上颇为可观,在笔者通过检阅《剑南诗稿校注》发现的200 余首自嘲诗中,直接以《自嘲》《自笑》为题或题中嵌入“自嘲”或“自笑”二字的就达30 余首。尤其是其老年时期创作了数量较多、成就突出的自嘲诗,相当一部分颇见诗人匠心,实现了自嘲诗这一诗歌题材的拓展与新变以及对中国古典嘲谑文学抒情传统的推进。
(一)万象入诗——普泛的取材与卑俗的喻体
相较而言,唐代自嘲诗的创作态度还较为严肃,很少以纯粹戏谑的心态自我调侃,更很少将生活中的细微、鄙陋之事纳入自嘲诗的创作。白居易《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33]两首中,因为元稹与自己老年得子这种日常之事写诗自嘲,韩愈《落齿》中以“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34]来对齿落这件小事进行自我打趣的情况比较罕见。到了宋代,自嘲诗题材开始进一步拓展,呈现出生活化、卑锁化的崭新面目,并蔚成风气,典型的如梅尧臣《次韵和酬刁景纯春雪戏意》:“我贫始觉今朝富,大片如钱不解穿”[35],东坡《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36],《丁公默送蝤蛑》:“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37]等,借生活常见琐屑之事自嘲,但数量不太多,且自嘲意味并不十分强烈。
这一情况在陆游的创作上发生了较大改变,他以化俗为雅的比喻手法,发兴无端的灵感闪现极大地推动了自嘲诗的生活化,这种生活化的表现之一即诗中大量出现以日常卑陋之物如“瓠壶”“败屐”“饭囊”等设喻自嘲的情况,此乃上承梅尧臣等人写俗摹丑之诗风而更申之以谑己。典型的如《解嘲》诗:
心如顽石忘荣辱,身似孤云任去留。酒瓮饭囊君勿诮,也胜满腹贮闲愁。[38]
此诗语辞通俗、风格轻快,我们很难牵强附会地说它具有何种深层的政治隐喻或精神象征,而其中以大俗之“饭囊”自谑解嘲的倾向却是不言而喻的。
诗人有时发兴无端,寻常的生活小事亦能激发自嘲。如下列二诗:
痴顽老子老无能,游惰农夫酒肉僧。闭著庵门终日睡,任人来唤不曾应。(《龟堂杂题·其二》)[39]
岁熟家弥困,天寒酒阙倾。仅能炊稻饭,敢望糁藜羹。一榻解腰卧,四廊摩腹行。诗人要疏瘦,此日愧膨脝。”(《饭后自嘲》)[40]
这两首诗借“昼眠”“饭饱摩腹”等日常习见之事自我调侃,均是无甚深意而有妙趣之笔。陆游此类自嘲诗还有一个突出现象,即频繁以自己“饥餐困眠”甚至与儒家礼法相抵牾的“昼眠”形象自谑,笔者以为这正是诗人深受禅宗“平常心是道”思想的体现。“平常心是道”为南禅宗马祖禅的核心理念,所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41],讲究在日常生活中参禅修行,认为日常举止即佛性真如之所在。陆游与禅宗渊源颇深,与马祖道一的三传弟子临济义玄所开创的临济派交游尤为密切,《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中就有许多与临济派禅师交游的痕迹,如《诗稿》卷一《寄黄龙升老》中就有“快哉天马不可羁,开口便呼临济儿”之句;《诗稿》卷二十七《送佛照光老赴径山》亦有“从来宗门语,只要句不死”等句,所谓“死句”“活句”即是临济派“看话禅”的宗门语。关于陆游自嘲诗与禅宗之渊源,笔者拟另撰专文讨论。总之,陆游自嘲诗中的生活化倾向与马祖禅思想有不可忽视的联系。这类自嘲诗的出现,说明在陆游手中自嘲诗已较大程度摆脱了作为理想失落与生命衰亡感喟工具的命运,开始向自我愉悦、自我对话媒介的转变。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转变是承续白居易、韩愈、苏轼等人的自嘲诗而实现的,但相较之下,陆游此类自嘲诗中的语言更为俗化、创作数量更为丰赡、作为自娱适性的自我对话媒介的特点更为突出。
(二)敷情抑理——对自嘲文学抒情传统的承变
中国古典自嘲文学较早形成了一个情感蕴含丰沛的抒情传统,这一点从东方朔、扬雄等人创作的一系列设论体俳谐赋中可以得到验证。然而唐诗中的自嘲却并没有续接汉魏六朝以来情感盛沛、语势磅礴的传统,像白居易“持杯祝愿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其二)、罗隐“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偶题》,一作《嘲钟陵妓云英》)这样的句子已经算是唐代自嘲诗情感浓度极致的代表了。宋代诗坛弥漫着“以理节情”的创作思维,自嘲诗的整体情感蕴含并不比唐代自嘲诗来得浓烈。我们看司马光的《自嘲》:“英名愧终贾,高节谢巢由。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羞。浮沈乖俗好,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霜毛不待秋。”[42]与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3]前诗平淡,后诗隐忍,两诗的情绪都显得含蓄内敛、蕴而不发,尤其是司马氏那首几乎已经看不出情感的波澜了,这实际上代表了北宋诗坛自嘲诗创作的经典面貌。
陆游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代自嘲诗情感内敛、压抑的面目,使得自嘲诗这一题材重新上接汉魏六朝的自嘲传统,呈现出对强烈抒情传统的复归,而且较汉魏六朝俳谐赋中的情感更为集中与强烈,表达方式更为直露大胆,乃是对汉魏六朝俳谐赋抒情传统的一种螺旋式推进,颇可照证吉川幸次郎所谓陆诗有对“过于冷静的北宋诗风进行反拨的倾向”[44]一说。我们且看下列二诗:
酒量愁翻减,诗声老转低。日高羹马齿,霜冷驾鸡栖。已判功名迕,宁论簿领迷。赖无权入手,软弱实如泥。(《遣兴》)[45]
君不见城中小儿计不疏,卖浆卖饼活有馀,夜归无事唤俦侣,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见垄头男子手把锄,丁字不识称农夫,筋力虽劳忧患少,春秋社饮常欢娱。可怜秀才最误计,一生衣食囊中书,声名镵出众毁集,中道不复能他图,抱书饿死在空谷,人虽可罪汝亦愚。呜呼,人虽可罪汝亦愚,曼倩岂即贤侏儒!《书生叹》[46]
像上面二诗中“赖无权入手,软弱实如泥”“抱书饿死在空谷,人虽可罪汝亦愚”这样的句子与前文罗举的白居易、罗隐、司马光、苏轼的句子,以及欧阳修《眼有黑花自遣》(洛阳三见牡丹月)、梅尧臣的《自感二首·其二》(我不嫌髭白)、黄庭坚的《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肉食相)等诸诗参看,便可知陆游这种突破理性的禁锢任由情感喷薄的抒情方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陆游的自嘲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纯粹是任由情感自由倾泻,汪洋恣肆,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喷薄而出,并不考虑诗歌的曲折回环、婉转幽邃,是用情感的吐露将理性的思维拒之门外,毫不留情地对自我进行嘲讽与谑骂,推动了魏晋俳谐赋中脱略风度、高蹈气象与自嘲精神在宋代的重塑,并以情绪的极度贲张与饱满实现了表达效果上的超越。此类诗歌尚有《自嘲解嘲二首·其一》(世变真难料)、《寒夜歌》(陆子七十犹穷人)、《信笔三首·其一》(为善得祸吁可悲)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感的炽热不可避免地对自嘲诗轻松诙谐的语言风格造成灼伤,有时显得过于凝重沉郁。
(三)铁马冰河———自嘲意象的军事化书写
将边塞诗的军事意象纳入自嘲诗这种诗歌题材是陆游的一大创举。在具有军事意象的自嘲诗中,陆游成就最高的一类是对过去军事记忆与军事体验的激发与唤醒,典型的如《书事》一首:
北征谈笑取关河,盟府何人策战多?扫尽烟尘归铁马,剪空荆棘出铜驼。史臣历纪平戎策,壮士遥传入塞歌。自笑书生无寸效,十年枉是枕雕戈。[47]
此诗作于嘉泰四年(1204年)闲居山阴期间,在此前一年韩侂胄拜太师,朝野骤其恢复之议,随即薛叔似、辛弃疾等主战派都被重新起用,此诗首联“北征谈笑取关河,盟府何人策战多”似指此事。颔联与颈联则是陆游想象王师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画面,充满了激昂慷慨之情。而尾联则意脉陡转,以自己老无寸功作结,特以有为志士的意气风发与自己的衰颓无用形成对比,突出年华之叹与闲置之悲。诗中诸如“关河”“铁马”“雕戈”等多出现于边塞诗中的军事意象之密集使用,与诗人的自嘲主题、人生经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毫无枘凿之感,全诗遒劲雄浑,允称佳构。
陆游的自嘲诗也善于以当下的落拓潦倒与昔日自己在军事场所与活动中的英姿飒爽作强烈的对比,如《春残》: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48]
此诗写于淳熙三年(1176年)二月,陆游当时的身份乃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但职事上“没有实际的任务”[49],是以此诗颔联有“时平壮士无功老”云云。围猎是陆游诗中屡屡提及的激昂往事,尤其是自己南郑猎虎的壮举,虽然关于此事之真伪学界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陆游在诗中曾屡次提及自己猎虎的事迹,如“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至今传军中,尚愧壮士颜”(《怀昔》)、“南山射虎漫豪雄,投老还乡一秃翁。”(《感秋》)等。在这首诗中陆游又一次将自己在往昔围猎时的英雄身手与自己此时“倦游”“摧颓”的两种形象比对而出——“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自嘲之意不言自明。
陆游有的自嘲诗甚至能以巧妙的比喻手法将日常的自然之景军事意象化,如《夜雨》一首:
齿牙摇动鬓毛疏,四壁萧然卧草庐。急雨声酣战丛竹,孤灯焰短伴残书。壮心未减从戎日,苦学犹如觅举初。自笑坚顽谁得似?同侪太半已丘墟。[50]
这本是一首由寻常景色触动感发而自嘲之作,但其中“急雨声酣战丛竹”一句,却将暴风骤雨、万竿欹斜的场景妙喻为敌我双方争夺厮杀的战场,将自然界中雨来叶翻的物理现象在极具动感的拟人手法中转化为恢宏的战争场面,是典型的化平淡为奇壮之笔,这无疑是陆游对自己军人身份的一种潜意识体认。
四 陆游自嘲诗的生成契机与文化面相
关于前人嘲谑作品尤其是自嘲类创作对陆游所产生的导夫先路之意义,已申说于前了。下文将主要从时代风气、宗教思想与个人经历三个维度考察陆游自嘲诗的生成语境与创作背景。
首先,嘲谑时风对陆游自嘲意识的激促。宋代嘲谑时风的体现之一即市民阶层的娱乐调笑。宋代市民阶层日趋壮大,娱乐行业大规模发展,说唱曲艺是宋代勾栏瓦子中颇受欢迎的表演形式之一,其中说诨话一项即是专以逗笑观众为目的的说唱类表演,常常以十七字诗、长短句的形式呈现,具有强烈的俳谐色彩,所谓“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北宋艺人“张山人”即以说诨话而著称,王灼《碧鸡漫志》言其“以诙谐独步京师”[51]。两宋发达的诨名、谑名文化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底层市井的嘲谑风气。据考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就记录了当时杭城各色艺人共522 位的姓名与谑名[52],足证当时风气之盛。此外两宋兴盛的谚谣文化亦是凸显宋代市民阶级嘲谑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如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就记载了时人利用谐音揶揄权臣童贯、蔡京的一则谣谚:“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53]而宋代谣谚的突出特点即诙谐意味与嘲弄倾向[54]。在宋代表演艺术中,宋杂剧亦是当时嘲谑风气浓盛的突出表征。宋杂剧中存在大量的诙谐剧目,并且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喜剧手法以制造演出效果,如滑稽扮相、插科打诨等等。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等典籍即记载了宋时众多街头市井杂扮笑耍之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间嘲谑文化随着宋代“化俗为雅”文学观念的盛行渗入到了士人阶层的文学创作中,影响了宋代文学景观的形成。“街谈市语,皆可入诗”(《竹坡诗话》)[55]“作诗正如作杂剧”(《王直方诗话》)[56]等论调以及“引谚入诗”[57]风气的流行,无疑丰富了宋代自嘲诗的语料来源与表现形式,是宋代自嘲诗兴盛的重要契机之一。
宋代嘲谑时风更重要的一个表现维度当然还是文坛士林的俳谐嘲谑。赵宋之世文人地位整体较高,加之官俸优渥、言论相对自由,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旷达的胸襟,乐观风趣几乎成为宋代文人性格的普遍写照,见诸典籍者比比皆是,如“王丞相(王安石)嗜谐谑”(《中山诗话》)[58]、“东坡好戏谑”(《晁氏客语》)[59]、“黄鲁直爱与郭功父戏谑嘲调”(《彦周诗话》)[60]等。宋人诗集中以“戏咏”“戏题”“戏赠”等为题的作品更俯拾皆是。宋代士林这种俳谐调笑之风的形成与当时宴饮雅集活动、“以诗为戏”的文学思潮,以及禅门“游戏三昧”的思想密切相关。频繁的宴饮酬唱为宋代文人提供了互相交流、彼此切磋的契机,令许多佳作“于尊俎笑谈间顷刻而成”[61]。宋人雅集通常伴随着人物的品评、诗法的探讨甚至是世局的指摘,是文人互嘲互谑、相切相磋的重要场域与载体。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涵养了宋人博赡的学殖,文人借谐谑以逞才使学的风气极为浓厚,正如周裕锴所言:“谐谑作为一种智力优越、学识渊博的显示,娱己且玩人”[62]。宋代回文诗、集句诗、药名诗、姓名诗、白战体等游戏诗体的大量创作就集中反映了宋人“以诗为戏”的创作心理与调笑自适的人生态度。宋人的自嘲风气与宋代禅宗“游戏三昧”的思想亦不无渊源,禅宗“游戏三昧”“打诨通禅”的态度随着北宋中叶士大夫禅悦之风的兴盛在文学领域普遍蔓延开来,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学景观。“以诗为戏”与“游戏三昧”思潮极大推促了宋代自嘲诗的繁荣,宋代善于“以诗为戏”或与禅门联系密切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大多是自嘲诗创作的大家。
其次,罢黜经历对陆游自嘲心态的影响。笔者依据于北山《陆游年谱》与朱东润《陆游传》发现,陆游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入仕迄庆元五年(1199年)致仕,四十一年宦海生涯数遭贬谪(如隆兴元年(1163年)、乾道二年(1166年)、淳熙三年(1176年)、淳熙七年(1180年)、淳熙八年(1181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频繁的弹劾与贬谪,对陆游的自嘲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笔者初步检阅,陆游一生创作的自嘲诗共计200 余首,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按陆游自此年罢归山阴至下世,除了应诏短暂出山修史,前后闲置凡二十年)以后的达130 余首,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致仕以后的计90 余首。当然《剑南诗稿》中早年作品由于删削留存不多是导致其自嘲诗在年龄线上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但就陆游现存自嘲诗的创作动机与主题来看,贬官与闲置是陆游绝大部分自嘲诗产生的催化剂,核心的主旨即是壮志难酬,陆游自嘲诗的其他主题如困顿、痴愚、衰老等许多也是围绕着这一主旨衍生、催发而来,典型的如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的《眉州驿舍睡起》:
平生百无能,一懒每自喜。胡为八年间,逐食走万里。身如盘汞转,心似炉丹死。事君未免愧,富贵不如已。雨馀古驿凉,昼寐无错履。澹然得高卧,睡思极清美。心平了无梦,惊魇何自起。尚嫌漆园蝶,肯作南柯蚁!斜阳生木影,龙蛇满窗纸。煎茶倘已熟,一笑问童子。[63]
陆游于淳熙三年(1176年)罢黜后虚辖台州崇道观,自号“放翁”,在成都领祠俸,时范成大在蜀,过从甚密。淳熙四年(1177年)夏范成大还朝,陆游送至眉州,此诗即作于当时。诗首联曰:“平生百无能,一懒每自喜”当指罢官一事,“百无能”当然是自嘲之语,但由于罢官而“懒”至“自喜”的地步,则纯粹是自慰的话了。陆游曾在另一首诗中说:“非关爱疏懒,无事可成忙”(《村舍》)恐怕才是实际情况。此诗虽为贬官期间的牢骚之语,由于作品结撰所需、意脉流动所至,情绪稍有低昂起伏,但贯穿全篇的依然是作者悠游的自由精神与旷达态度,结尾“煎茶倘已熟,一笑问童子”一联即是明证。需要指出的是,此诗纯粹从贬谪赋闲状态感喟而来,开篇即是“平生百无能,一懒每自喜”,这种全无回旋、遽然而驰的起调即奠定了全诗的情感走向,因而接下来的“逐食”之叹、“富贵”之嘲、“澹然”之欢、“梦幻”之感全都由此兴发牵引而来。陆游此类自嘲作品尚有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奉祠期间的《夜中起读书戏作二首·其二》(灭虏区区计本疏)、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罢归山阴期间的《自责》(穷途敢恃舌犹存)等诗。综上可知,贬谪生涯带来的精神冲击与思想洞彻对陆游自嘲诗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衍生出的壮志不酬、青春不永、与世不谐和及时行乐、今是昨非等思想都成为了陆游自嘲诗创作的动力,这些思想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贬谪后逐渐浓烈,并在庆元五年(1199年)致仕后走向顶峰,推动了陆游自嘲诗创作的繁荣。
最后,三教文化对陆游自嘲思维的塑造。宋代三教融合的思想对陆游自嘲诗的内涵意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共同促使陆游的自嘲诗跳脱出尖刻怒兀和无聊打诨的两种极端,摆脱了自怨自艾的寒俭之气与滑稽轻薄的庸俗之态,呈现出饱满的生命意识与多维的文化形态。但儒、佛、道三家思想又具体地作用于陆游不同内容的自嘲诗,比如儒家“孔颜乐处”思想主要影响了陆游咏贫自嘲诗的文化面相,而佛家“虚空”思想以及道家“致虚守静”的思想则主要体现在陆游以壮志未酬为主题的自嘲诗中。下面我们试加论析。
作于开禧元年(1205年)的《贫居即事》六首是陆游咏贫自嘲诗的代表之作,我们以其中一首为例:
意绪丧家狗,形骸槁木枝。曲肱虽自适,纵理固当饥。买絮初寒后,畦蔬小雨时。穷途何用卜,吾道即蓍龟。[64]
此诗需特别着意的是“曲肱虽自适,纵理固当饥”一联,这对《论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65]的化用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对我们探析陆游咏贫自嘲诗的思想渊源极为重要。通过检阅,我们还发现了放翁大量化用《论语》中此句以咏贫之作,如“曲肱饮水彼何人,汝独何为厌贱贫”(《自规》)、“饮水读书贫亦乐,杜门养病老何伤”(《白发》)、“饭蔬饮水平生惯,耻向天公更乞怜”(《霜天杂兴三首》其二)“但令吾道常无坠,饮水何妨枕曲肱”(《秋夜读书有感二首》其一)等。这一类诗表达了陆游德性操守之乐、心性晏如之乐,是对“孔颜之乐”中安于贫贱、以道自守的心性义理之承续与发展。朱刚在《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中指出,宋代士人通过对颜子之学的探讨,越来越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内在的精神天地[66],揆诸陆游的创作实际,可谓洞中肯綮。
体现在陆游自嘲诗中的释老思想则主要是佛家的“虚空”观以及道家的“致虚守静”思想,二家思想使得陆游的自嘲诗时常显露出不汲汲于功名、不营营于官场的态度,当然也同时为陆游诗歌印上了一些虚无主义的色彩。典型的如《寓叹》(其二):
醉抚酒壶怜矲矮,卧看香岫爱嶙峋。旧时京洛尘埃面,今作江湖风月民。幻世界中均起灭,太虚空里孰冤亲?可齐入定论千劫,说与天魔任恼人。[67]
此诗以“旧时京洛尘埃面,今作江湖风月民”自嘲昔之奔趋与今之闲置。全诗多处叠用佛家语典,如“世界”“起灭”“虚空”“冤亲”“千劫”“天魔”等,而其中“幻世界中均起灭,太虚空里孰冤亲”一联更是集中体现了陆游在佛家“虚空”思想影响下的暮年功名观,与《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68]所表达的思想如出一辙。此外,《秋夜歌》[69]一诗中“架上故裘破见肘,床头残酒倾到脚。问君何以鏖霜风,悠然卧听山城角”等句子与“孔颜乐处”思想也无疑是相通的,而该诗中“人言富贵堕骇机”等句又似乎隐约透露出一点佛家“虚空”与道家“远害”的思想。这并不是作无根之谈,该诗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这段时间前后正是陆游与刘道士、陈道人、萤师、平老、印老等释、道人士往来密切的时期[70]。这些诗歌正体现了三教汇通思想对陆游诗歌创作所施加的综合影响,它们使陆游的自嘲诗呈现出一片浑涵通脱的文化面相,赋予了陆游自嘲诗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哲思。
五 结论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嘲谑传统源远流长,以《诗经》及诸子典籍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先秦作品中的嘲谑色彩尤其是自嘲意识,对中国的文学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形塑作用。在中国古典自嘲诗的演变历程中,汉魏六朝俳谐赋中的自嘲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夫先路之意义,成为了后世文人创作此类作品的规摹范本与精神源头。与此同时,六朝嘲诮诗中嘲人诗的兴起与自嘲诗的萌生则为后世自嘲诗的勃兴提供了体裁标矩与书写范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维影响下,自嘲诗在唐宋时期完全成熟并走向繁荣,并于宋代形成了创作大观,证之于文学史,则是宋代直接以“自嘲”为题的诗歌大量涌现。陆游是南宋乃至整个宋代自嘲诗创作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自嘲诗,并以其深厚的情感蕴含、超诣的艺术创造、独特的诗歌风貌为中国嘲谑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色彩。物质贫穷、肌体老病、理想失落等促使陆游对人生作出深刻的思索并寻求心灵解脱,自嘲诗成为他宣示情绪的一种手段,它们较为细腻真实地再现了陆游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反映了陆游通脱旷达的性格特质与固穷守拙的品德操持,显示了陆游诗风幽默诙谐的一面,更从侧面折射出宋代士子理性圆通的时代气质。与前代或同代诗人相较,陆游的自嘲诗不仅以化俗为雅的修辞手法、发兴无端的灵感闪现极大地推动了自嘲诗题材的生活化新变,推动了自嘲诗由理想失落的寄托与生命衰亡的感喟工具,向自我愉悦、自我对话媒介的转变,还突破了宋诗“以理节情”的时代禁锢,实现了对汉魏六朝俳谐赋自嘲抒情传统的续接,大大增强了宋代自嘲诗的情感浓度,实现了自嘲诗抒情方式的解放,更创造性地把军事意象纳入自嘲诗的创作中,以化平淡为奇壮之笔为自嘲诗的日常书写提供了另类的书写策略与路向。远绍前人的自嘲传统是陆游自嘲诗得以大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兴盛的时代嘲谑风气、罢黜赋闲的人生经历以及三教汇通的思想体系是陆游自嘲诗创作的三大契机,它们分别构成了陆游自嘲诗生成语境中社会背景、现实触机以及文化动因之维,并交互立体地建构了陆游自嘲诗中的独特艺术风貌与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