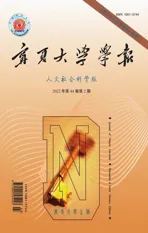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逃兵》中后现代伦理的互文叙事
2022-11-22钱亚萍
钱亚萍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北京 100101)
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从后现代西方伦理学视角阐释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揭示文学文本所描写的后现代“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后现代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后现代伦理教诲和道德经验[1]。以多角度观察、多叙事者、多声部、现代多样杂糅等技巧为特征的狂欢化叙事,及以平行结构、戏仿、直接引用等为手段的互文叙事是后现代文学常用的后现代伦理叙事策略。英国当代小说家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发表于 2000年的中篇小说《逃兵》(The Discharge)运用平行结构、戏仿和直接引用等互文叙事方法,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传达了对后现代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哲思,蕴涵其中的伦理思想指向人类的未来。
一 隐性的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指将某个观点或论题分解成有一定联系、地位平等、平行展开的若干方面加以论述,以揭示、阐发中心论点的属性和思想意义。《逃兵》建构了一个众声喧哗、内涵芜杂的文本空间,将主人公的战争、艺术、记忆、成长与对家园的寻求几大版块共时推进,搭建了隐性的平行框架,勾勒了“我”历时、多面、立体的人生,形成“我”多种意识、视野和声音的互文关系,表现了以“我”为代表的人在人类文明中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寰宇间生存个体对和平、伦理、道德、自由的强烈渴求。
“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2]从人类起源到远古部落纷争再到现代战争,从核轰炸到无差别杀戮的恐怖主义,战争从未间断,也从未远离人类。战争,植根于人类的意识深处,并与人类文明共同演化。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类文明的欲望。《逃兵》以“我”在弱冠之年回首人生过往开篇:“我是一名士兵……战争已逼近其第三个千年的尽头,我在一个征召部队中服役。”[3]然而,世界上最大的无主地、巉岩冻河遍布的南大陆虽无战争的迹象,没有枪林弹雨,但士兵们必须严守以待。据说,这场战争永不会终结。在这场战争中,“我”身心俱损,百无聊赖。面对难捱的四年兵役生涯,在“我”踏上战场之初,逃离军队、自我解除兵役枷锁的种子便已在心中萌发了。终于,在纪念战争爆发三千年庆典八天前的夜晚,“我”毅然与硝烟诀别。普瑞斯特通过对横亘近三千年战争的描述,实则指出,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苏格拉底说:“战争、革命和战斗都只受肉体和欲望的支配。”[4]在非正义的战争中,人的价值与尊严损耗殆尽,人的生命被掠夺吞噬。在无声的战火中,“我”求生的欲望战胜了生命的虚掷,人性因子抵御了兽性因子的肆虐[5]。借“我”之口,普瑞斯特讨伐了战争,揭露了战争残酷的本质,反战的伦理观清晰可见。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一词只有经济的意义,是一种经历,“在短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强有力的刺激,致使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应付抑或适应,从而导致心灵的能量分配方式受到永久性的干扰”[6]。逃离军队后,“我”辗转于各个岛屿,以绘画谋生,创作时常被黑帽军警打断,恐惧常令“我”不安。“我”继承并发展了埃基左纳开创的触觉主义绘画艺术,成为一位艺术家,描绘“我”在战争中所经历的极度惊恐。绘画淡化了“我”的创伤,使“我”在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平静与慰藉,通过艺术,“我”的伤痛在愈渐弥合。在凯西·卡鲁斯看来,创伤“通常是大声说出来的伤痛故事,讲给我们,试图让我们了解事实或真相,否则,它就会被淹没”[7]。“为继续存活,幸存者需讲出自己的故事”[8]。“我”恰是通过自白式的绘画与艺术,重构创伤故事,以此宣泄愤懑、获得解脱。因此,《逃兵》亦是一部创伤小说。
巴赫金称,记忆告诉我们,时间不等同于自身[9]。《逃兵》中,“我”对记忆的寻觅贯穿于“我”的战争、艺术之路,形成了独特的记忆话语。在随军南行的途中,对生命的知觉在“我”的体内猛烈撞击。“我”是一个失忆的躯壳,无可依傍。飘浮在失忆的阴云中,穆里西伊岛和埃基左纳是“我”唯一知晓的现实。“我”发现,触觉主义艺术会对观赏者造成诸如记忆力下降等创伤性影响,而沉浸绘画之中方可重拾记忆。欣赏触觉主义画作使“我”失忆,但反之,创作触觉主义绘画却使记忆重返。失忆是禁闭的一种表现,受创者会将自己从创伤记忆中分离出来,甚至故意压抑记忆,而这使禁闭很难被发觉。在带有毁灭性的战争与绘画的威力之下,“我”经历了失忆的梦魇,在逃离战争与超越艺术引领者之后,记忆方渐返大脑。“我”对真正的艺术、艺术伦理、审美伦理的吁求昭然若揭。
巴赫金指出,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动态的统一体,成长小说即人的成长小说[10]。《逃兵》中,“我”年少从军,有近四年的军旅生涯;在穆里西伊岛的舞厅,“我”被妓女诱惑,丑陋的现实打破了“我”对审美的希冀;“我”参透了战争的实质,自我解除了兵役的锁链,追寻自由与尊严;“我”不相信所谓的宿命,坚信自己是生命的主宰。“那个男孩不见了,成为了军人。”[11]在逃亡之际,“我”将时过境迁的艺术推陈出新,从一名鉴赏者成长为书写人世的画者;“我”颠沛流离,用画作消灭了猎捕者。那个军人不见了,成为了艺术家。《逃兵》兼具经典和(后)现代成长小说的特点与内涵,展现了“我”的成长历程,揭示了“我”成长过程中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的精神、道德、伦理问题,个人与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动态发展得到了描写。
社会加给我们许多法则,这使“陌异感”与焦虑伴随着我们的生命。自我建构中包含了重重的“不安的陌异感”。每个人都是“异乡人”,每个人在自我深处都有异质的存在[12]。漂泊于汪洋大海、流浪于梦幻群岛的“我”亦是一个异乡人。即便在人群之中,“我”也仅是聆听者和观察者,肉眼可视的具象物质家园遥不可及,可安定栖居的精神家园更不知何处。岛屿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敦促我走向前方[13]。主人公的路在何方?“我”可觅得一个属于“我”的家园?小说以开放式的结尾作结,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因此,战争、艺术、记忆、成长、家园构成《逃兵》的五大轨迹,纵横捭阖,并行不悖,架构了一个时空交错的空间。其间,以“我”这一个体为代表的人类的生存与挣扎历历可见。
二 后现代语境下对经典的戏仿
巴赫金认为,戏仿既是一种“双声”形式,又是基于对比和不一致的形式。哈桑认为,戏仿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后现代”世界的疯狂。发展了“后现代”戏仿观的理论家超越了将戏仿视为滑稽或元小说的现代做法,他们认为,戏仿是文本内部更复杂的文学分析,是“考古”“互文”再创造的工具,是积极、正面的技巧[14]。在索尔莱斯看来,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15]。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16]。就文本而言,《逃兵》与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及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相近,不啻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这些经典的戏仿。
在付梓于1895年的《红色英勇勋章》中,克莱恩多用“他”指代弗莱明,与《逃兵》中的“我”这个称谓同指向无定指的人类。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入伍时都是青葱少年,都作过逃兵,对战争都心怀恐惧,都在战场上得到了历练,最终都走向了成熟。但《逃兵》与《红色英勇勋章》亦有诸多不同,如“他”是怀着浪漫的英雄主义观念、怀着对战争传奇生活的向往、不顾母亲的劝阻欣然加入北方军的,而“我”则是被动地应召入伍;“他”的军营生活虽艰辛,但不乏战友间的关爱,而“我”即便在四千多士兵的队伍中,仍形单影只;“他”作了一次逃兵,弃阵而逃,“我”则作了永久的逃兵,虽未目睹枪林弹雨,却作别了武器;“他”重返战场,成为战斗英雄,“我”却追自由而去,被军警追捕;“他”是现代社会的英雄,“我”则是后现代社会的反英雄;“他”沦为了战争棋局中的棋子,“我”则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命运;虽知战场即屠场,是红色的野兽、吸血的瘟神[17],但为了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英雄”[18],“他”依旧坚定地“成了一位疯狂而野蛮的异教徒。他甘愿作出崇高的牺牲,光荣地死去”[19],而“我”却在绵亘三千年之久的战争面前用理性意志进行判断,作出善恶的选择。马丁·艾米斯指出,戏仿可用来暗示一个疯狂、断裂的世界。通过对《红色英勇勋章》的戏仿,一个为权力、金钱与性疯狂的世界真实可感,一种悲剧性的戏谑在《逃兵》中业已达成。
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画家霍尔沃德被道林·格雷俊美的容颜、超凡的气质所吸引,与对格雷产生极度的爱慕之情类似,《逃兵》中的“我”着迷于埃基左纳画笔下妖冶的女性。对霍尔沃德而言,格雷是艺术的源动力;之于“我”,埃基左纳乃创作的灵感所在,其笔下的女性是引领“我”走入艺术殿堂的女神。因而,霍尔沃德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格雷,在为格雷所画的画像中暴露了他自身灵魂的秘密;“我”亦将自我置身于绘画之中。霍尔沃德为格雷作画时在“颜料里掺了一些该死的有毒矿物”[20],他的那幅画毁了格雷的一生;埃基左纳的触觉主义作品使用一种经超声微电路处理,将光线、颜色、声音等融为一体的颜料,而用这种颜料画出来的形象会使欣赏者抑郁和长期失忆。格雷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和青春,霍尔沃德对其持有的“爱是米开朗琪罗、蒙田、温克尔曼和莎士比亚所了解的爱”[21];埃基左纳画作中的女子有性感的动作和曼妙的身姿,“我”对她的兴致仅是欲望的驱动使然。为青春永驻,格雷一步步坠入罪恶的渊薮;似画中人的妓女虽以出卖肉体为生,却可向漂泊的游子伸出援手。霍尔沃德失去了为格雷精心绘制的画像,画像被后者藏于住所的顶层;“我”始终是自己画作的所有者和掌管者,虽也将众多作品藏匿起来。霍尔沃德因绘画被格雷杀害;“我”的画作却拯救了“我”的性命,使军警葬身火海。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22]。普瑞斯特对萨特推崇备至,而萨特恰是对唯美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文学为人类社会担负着责任,应通过“介入”揭露社会问题,改变生存处境,而“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23]。从此视角判断,《逃兵》或是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讽刺性模仿。
伍尔夫擅长于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揭露和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予以讽刺、揭露与讨伐,对被欺凌、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24],在 1925年面世的《达洛卫夫人》中也未有例外。在《达洛卫夫人》《逃兵》中,赛普蒂默斯与“我”均曾戎装在身,但前者是一位曾荣获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后者是一名逃兵;前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拯救英国,加入了第一批自愿入伍者的行列,到法国作战,后者被征召入伍,在南大陆的苔原苟且存活;前者在战争中经历了全部过程——友情、欧洲大战与死亡,后者未服完兵役,逃离了战场;前者患上炮弹休克后遗症,丧失了感觉能力,看上去疯疯癫癫,后者关于自我的记忆丧失,四处流亡,却头脑清醒;前者有伦敦名医医治、妻子陪伴,后者仅自我疗伤,身边唯有妓女;前者哀嚎:“我要自杀!”[25]后者无言,默默前行;前者“唯一的出路是窗子……打开窗子,跳下去——麻烦,叫人厌烦,像闹剧”[26],后者的出路在前方;前者以死抗议压制与迫害,以消极的方式护卫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后者用积极的策略摆脱世俗的桎梏,追求自我与为人的尊严。伍尔夫这般形容:“他,赛普蒂默斯,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员,刚经历了由生到死的考验,他是降临人间重建社会的上帝……他永远受苦受难,他是替罪羊,永恒的受难者……”[27];对于“我”,普瑞斯特未作任何评论,给读者留下了思忖的空间。布雷德伯里指出,我们身处一个漂浮的能指时代,一个戏仿与拼贴、疑问与引用的世界[28]。戏仿作为双重赋码策略绝不止于嘲弄,《逃兵》对《达洛卫夫人》的戏仿是严肃、认真的。
戏拟主要指作者吸收模仿、借用前人文本或其他艺术风格,以期达到讽刺或其他特定的效果[29]。就艺术风格、题材、主题而论,《逃兵》与发表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颇为相近,均使用了第一人称,主人公都在讲述自身经历,语言均口语化。在霍尔顿和“我”的成长故事中,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精神危机,如异化、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自我疏离、无能为力、无意义等均浮出地表,放眼望去,世界便是一片污浊的泥沼。《逃兵》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题,虽仅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时间的跨度更大,视野更为广阔,指意更加完整,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吸收和整合。对布鲁姆而言,互文性是“影响的焦虑”的产物[30]。一切创作者感受到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31]。
作品的记忆是一个不定的空间,里面满是遗忘、稍纵即逝的回忆、猛然的回响、暂时的忘却。互文手法告诉我们,一个时代、一群人、一个作者如何记取在他们之前产生或与他们同时存在的作品[32]。“埃基左纳的塞壬女妖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33]《逃兵》中的“塞壬女妖”指埃基左纳画笔下妖艳的女性,与《奥德赛》中的塞壬相对应。当然,《逃兵》与《奥德赛》在情节上亦有几分相似,如二者均涉及“归还”题材,但奥德修斯有明确的目的地——伊萨卡,而“我”注定浪迹天涯。又如两位主人公均为飘零人、外乡人,必须忍受风餐露宿、漂泊不定之苦;再如两位男子均流落于诸多海岛,并多奇遇。尽管两位主角间有共鸣之音,但与奥德修斯是位人所称颂的英雄不同,“我”是逃兵,是反英雄。且前者有神明庇佑,一路虽多磨难,但最终得以返回家园,而后者却不信任何宿命,独闯天下。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实,反偶像崇拜”,反对或躲避崇高,书写丑陋、粗俗、虚无、死寂、卑微的题材。后现代主义文学常追求其有限性,接受其“枯竭”,与自己的表现形式较量,把卑琐性与不可表现性引入表征模式[34]。普瑞斯特运用碎片化的语言游戏与异质性的小型叙事,消解了强调同一性与整体价值,以及有关解放、自由、思辨与真理的宏大叙事,消解了传统作者的权威。
《逃兵》以古代、近现代文学经典为参考,对经典进行了或戏谑、或嘲讽、或尊重、或严肃、或悲剧的戏仿,从而使老作品不断进入新一轮意义的循环,并赋予新的作品以新的内涵。同时,借由对经典文本的戏仿,与其产生另类共鸣与和声,引发读者深入思考当下与未来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及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
三 对萨特的直接引用
巴赫金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35]。安东尼·孔帕尼翁将引用描述为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将其视作所有文学写作中需进行转换和组合的标志[36]。“与举天下的寻梦人别无二致,我错将梦幻当作真实。”《逃兵》中,萨特的法文引语开篇与《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有异曲同工之妙。萨莫瓦约指出,无论何种情况,卷首语都是一种既基本又典型的互文性手法。与主体文本相分离,凌驾于主体文本,或是从某种意义上引出主体文本,卷首语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把生活粘贴在艺术里,将生活不加改动地体现出来,于是,艺术、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抹煞了[37]。普瑞斯特用引文代替了对世界的描绘。萨特的话语隐喻出一幅真假共存的混沌世界图景,折射了人类此时、彼时与未来的生存状况与困境。
哈桑指出,包括模糊性、断裂性、移置体验在内的非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特征。《逃兵》中,“我”的故事发生在梦幻群岛,穆里西伊岛舞厅里的妓女称“我”看到的便是“我”所追寻的梦,“我”来到的恰是“梦的圣殿”。埃基左纳的绘画让“我”沉迷,“我”的头脑中充斥着假象和幻想,虚妄的世界与“梦”紧密相连,梦境与现实交融,虚实难辨。这种如梦如幻的模糊性、断裂性、移置体验恰是非确定性世界与世事的印证。与马尔克斯将真实的拉丁美洲缩影在虚幻的马贡多城中类似,普瑞斯特借助艺术虚构的叙事方法,编织了“真实的谎言”,模糊了真假虚实的界限。“我”是在黑暗中醒着、在光明中睡着的灵魂。普瑞斯特实借萨特之语指明人生如梦、世事不定,人人皆在梦中,梦中的权势、金钱、名利、美色让人迷失本性,不知何时方醒。普瑞斯特对梦境一直情有独钟,常以梦境为题,如《威塞克斯之梦》(A Dream of Wessex,1977年)、《梦幻群岛》(The Dream Archipelago,1999年),而萨特的这句原文及对应英译曾两次被用作题记。一个虚构世界的诸多层面可以借助于互文标志得到扩展[38],《逃兵》便是如此。
萨特之语频频出现在普瑞斯特的作品中,并以卷首语这一形式被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对作者的影响。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是一个人无法脱离的真实体。人亦先于本质而存在,除了自己外,别无立法者,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或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39]。人在行动中创造自己的本质。“自从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40]。“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41]。萨特说:“所谓自由,不是有能力去实现你的志愿,而是愿意实现你能做的事。”自由决定了我们的存在和本质,是我们所承担的一种沉重命运。在重要的道德意义上,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世界[42]。但荒谬是一种事实状态,悲剧是命运的一面镜子,存在着给自由加上枷锁的环境。因而,“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43],但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有通向彼岸的自由。人应对自己负责,而对自己负责即对他人负责。“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44]。存在主义者所考虑的是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的伦理学。“人只是自己设计的生活图景,人只在自己成为现实时才存在,人只是自己行为的总和”[45]。此处,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背景,便不难理解“我”为何走上逃兵之路了。
互文性既是一个广义的理论,又是一种方法。泼费斯特提出: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和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46]。互文手法使文本产生新的内容,使文学成为一种延续的和集体的记忆[47]。《逃兵》成功运用了平行结构、戏仿、直接引用的互文叙事策略,文字虽精简,却浸润着深刻的后现代伦理思想,表达了当下与未来人类的后现代伦理需求。普瑞斯特通过这一后现代寓言,传达了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伦理关怀。“艺术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48]。“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自由……作家与小说家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从这个观点来表现为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揭示人所处的环境,人所面临的危险以及改变的可能性”[49]。普瑞斯特在《逃兵》中遵循萨特的遗愿,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