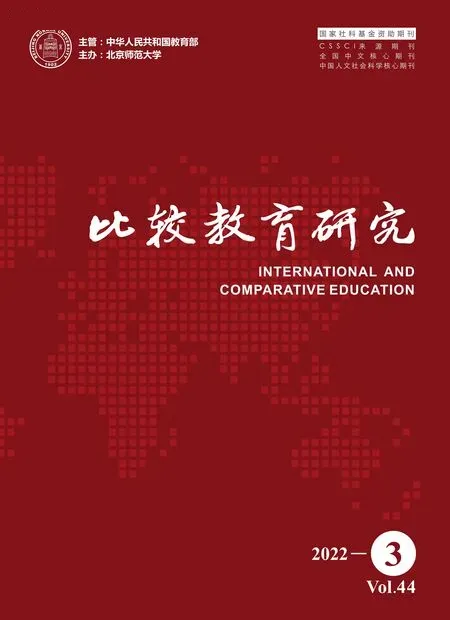日本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教育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2022-11-22李冬梅
李冬梅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国民对于追求学历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应运而生并发展迅猛。20世纪60—90年代,学习塾的业务聚焦于学校课堂的补习与预习,提供针对升学的考试对策服务,这一时期学习塾受到了诸多批判,如助长考试竞争和学历社会、导致教育的商品化现象、扭曲学校教育等。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与社会大众对学习塾的态度及相关政策却发生了变化,开始引导和支持学习塾与政府、学校加强合作,以共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从而更好地保障学生学习权利。与学校教育互补共生、形成合力,成为近年来日本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主旋律。
一、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合作的背景
自2000年以来,伴随中央政府对学习塾的态度从批判为主转为接受认可,日本公立学校及地方政府与学习塾之间的协同合作迅速推广,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从以往的不可调和转向协同发展[1],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力政策转变,学习塾价值凸显
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围绕学力政策的主流观点从以往的宽松教育转向扎实的学力,学习塾作为学力提升专业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价值开始凸显。宽松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为了纠正过度“填鸭式”教育与考试竞争所引发的校园欺凌、学生厌学等教育病理现象,日本开始推行以减少教育内容、增加学生社会体验、注重兴趣和态度为核心的宽松教育措施。然而,宽松教育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导致日本学生整体学力的下降,引发了被称为“РISА 危机”的批评浪潮。[2]2007年起,日本启动一年一度的“全国学力学习状况调查”,通过各地结果的横向对比来确认教学成果,进而改进教学活动。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订《学习指导要领》,提出扎实的学力政策,开始增加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由此,日本各地政府及学校开始协同学习塾,意欲通过聘请学习塾讲师到校指导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学力。
(二)“通塾①在日本,到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进行补习的行为被称为“通塾”。机会不均等”带来教育不公平问题
日本政府推行的宽松教育政策并没有弱化学历竞争,反而激化了教育不公平现象,带来了因经济差距、地理原因导致的“通塾机会不均等”问题。学生家长普遍认为“宽松主义”下的公立教育无法满足学生需求,因此经济较富裕家庭的学生就会通过进入学习塾“回炉”,来提高其在升学考试中的竞争力。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学生来说,无法进入学习塾学习就会使其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通塾机会不均等”引发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焦点。[3]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各地方教委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缩小通塾差距,由此政府协同学习塾面向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补助的问题解决路径应运而生。[4]
(三)学习塾得到政策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1999年,日本文部省(2001年起,更名为文部科学省)终身学习审议会指出,虽然过度参与校外补习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但学习塾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可以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育并不相同的多样化学习与体验机会。同年,文部省将学习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纳入社会教育体系,受到文部省终身学习局的监管。[5]自2000年以来,学习塾行业的人数规模和整体效益均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文部科学省开展的学生通塾率相关调查显示,中小学生参加学习塾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其中小学六年级学生的通塾率从2008年的25.9%增至2017年的46.4%,初中三年级学生的通塾率则从2008年的53.5%增至2017年的61.2%。[6]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20年度“特定服务产业动态统计调查”显示,学习塾的学生总数约为1362万人,从业者总数约为18万人,其中讲师人数约为13万人,全年收益达到4958亿日元,均实现了连续三年的递增。[7]可以说,学习塾已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也成为其与学校教育协同合作的重要基础。
(四)公立教育系统出现弊端,需协同学习塾加以变革
学者深谷昌志认为日本学校教育积存已久的“顽疾”,恰恰导致了学习塾的增长普及,学校教育忽视学生个体间的学力差异,过度追求均等而无法开展基于个体差异的教学。今津孝次郎则进一步指出,日本学校的“官僚化”,即学校教育的管理主义阻碍了学生、家长、教师之间的交流,加剧了学校的封闭性,无法适应学校体制的学生就会成为差生,也就需要到校外培训机构补习。[8]
日本内阁府于2005年发布的“围绕学校制度的家长调查”结果显示,在提升学生学力方面,有高达70.1%的家长认为学习塾比学校更有方法、更具成效,而认为学校比学习塾更出色的家长仅占4.3%。[9]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市区町村教育委员会及初中校长关于学校与外部力量合作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与1994年的调查相比,2012年对于学校与学习塾协同合作持肯定态度的公立初中校长比例显著增加,从27.3%上涨到50.2%;认为可聘用学习塾讲师到公立学校任教的校长比例,也从1994年的19.1%上涨至2012年的46.3%。[10]可以说,日本绝大多数的地方教委及学校校长都认为,应当通过学校与学习塾在内的民间机构合作,来积极推进体验型学习、劳动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内容。
二、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合作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措施
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开展合作是政府科学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的一大产物,学习塾的科学良性发展是其与学校教育开展合作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两者开展合作与日本教育领域的系列改革一脉相承。政府的科学治理和教育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一)制度保障
1.政府科学治理是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合作的先决条件
被比喻为“光与影” “日与月”关系的学校教育和学习塾[11],前者是代表官方的主流教育,而后者代表了民间资本和民间教育力量,两者之间根据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政府采取的态度与措施呈现出动态的关联。20世纪60—90年代初,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面临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激烈的学历竞争带来学习塾数量的暴涨,因“利益至上”造成的学习塾只追求短期成绩效应与加重学生负担等负面影响,使日本政府与社会对学习塾持批判态度。1990年3月发生了著名的“拒绝补习班学生入学”事件,这一年日本关西某私立中学因报考学生过度参加校外补习,以其在小学阶段缺勤天数过多为由,拒绝录取已达到分数线的考生,学习塾因威胁到教育“主阵地”的学校地位,而引发了学校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抨击。[12]这一时期,学习塾与学校教育是对立抗衡的关系。
面对学习塾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媒体大众对学习塾的批判呼声,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采取对学习塾的规范管理措施。1988年,日本通商产业省(2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开始管辖学习塾,主要从经济运营角度对学习塾加以规约。在学习塾教育教学活动开展以及讲师劳动权利保障方面,则分别由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加以监督。同年,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由通商产业省委托成立,该协会致力于学习塾的行业自治,通过制定行业准则与出台学习塾讲师审定制度等,促进学习塾的自主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特定商业交易法》《消费者契约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基准法》《最低工资法》等相关法律,以确保学生与家长等消费者以及学习塾讲师的合法权益,约束并规范学习塾的办学行为。因学习塾带来的产业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学习塾行业的监管措施,侧重于以扶持促治理、以引导促发展。[13]
可以说,基于法律保障、支持行业自律、重在扶持和引导的政府治理措施,极大地助推了学习塾的科学健康发展。对比治理之前的学习塾,日本学者佐久间邦友认为,学习塾可被社会灵活运用,发挥其对地方政府的教育协助作用[14],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从以往的对立抗衡走向协同合作。
2.教育政策法规助推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合作
2013年10月,在全国学习塾协会举办的“2013年度学习塾研讨会”中,时任文部科学省终身学习政策局社会教育科科长的坪田广知发出号召,希望学习塾积极协同政府、学校参与到课后服务及周六教育活动中,为构建丰富的教育环境作出贡献。2013年11月,文部科学省修订《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从法令的高度将学习塾与政府和学校协同推进周六教育活动,升格为学习塾应当履行的义务。2014年,作为文部科学省教育决策咨询机构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指出,学习塾等民办教育机构能够在仅靠政府和学校无法充分应对的教育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因此要求日本各地政府及教委加强与学习塾等民办教育机构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课后教育服务及学童保育相关事业。201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进一步发布《面向新时代教育及地方创生的学校与区域社会协同机制及推进方针》审议报告,突出强调了学校协同区域社会相关主体的重要性,意欲构建学校与区域社会之间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逐步摆脱以往仅依附学校的教育发展机制。[15]伴随上述政策法规的颁布,日本各地政府及学校愈发积极地开展与学习塾之间的合作。
(二)基本措施
1.学习塾讲师提供课余辅导,助力提升学生学力
2005年,东京都足立区启动相关计划,派遣学习塾讲师到区立中学开展补习讲座;东京都江东区也开始在部分小学引入学习塾讲师协助班主任授课的教学指导模式。2008年,为了给以升学为目标的优等生进一步提高学力,东京都杉并区和田中学聘请了主打升学考试的学习塾“SАРIХ①SAPIX,分别取Science,Art,Philosophy,Identity的首字母,再加上代表未知数的X构成,该机构致力于以优质的教育教学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卓越人才。中等部”讲师来学校,为学生开展放学后的有偿补习授课,随后仅面向优等生的补习授课进一步扩展为面向所有具备补习意愿的学生。2010年起,大阪府大东市推出“学力提升辅导班”计划,由市教委与全国学习塾协会合作,委托该协会派遣教师并制定课程教案,课余辅导的时间为每周六,辅导对象为市内公立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学生以及公立初中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辅导课程为小学的算数、初中的数学和英语。根据全国学习塾协会发布的资料,2013年“学力提升辅导班”共计开设44次,总共有351名学生参加;市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约404万日元,主要用于活动开展的人事费和场地费,学生家长仅需交纳少量学费,小学生每月1000日元、初中生每月2000日元。[16]大东市的“学力提升辅导班”持续开展至今,因参与学生之多、学生及家长满意度之高、学习成效显著等原因备受瞩目,成为政府与学习塾协同合作中的典范[17],2013年起文部科学省将其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2.学习塾涉入学校运营与教师培训,助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2005年,日本北陆地区最大规模的学习塾“育英中心”设立的“学校法人片山学园初中部”正式开学,随后2008年又开设了“片山学园高中部”,成为日本富山县首个私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该校校长将“把学生送进东京大学及国立大学医学部”作为办学目标,大力集结“育英中心”的讲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升学对策指导,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吸引了众多学生慕名前来报考。该校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2021年,该校共有51名学生成功考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排名前十的重点国立大学,成为当地颇有人气的重点学校。2015年,日本佐贺县武雄市教委协同学习塾“花丸学习会”,创设了将“花丸学习会”教学方法引入武雄市内公立小学的官民一体化学校“武雄花丸学园”,其协同方式不仅包括了定期派遣学习塾讲师到校授课,还将学习塾的教材、指导方法等一并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课程。[18]以上,学习塾通过直接创设私立学校或响应政府号召的方式涉入学校运营。前者由学习塾全权掌控办学运营的模式,仅限于私立学校领域;后者官民一体化办学的“武雄花丸学园”,仅限将学习塾的优质课程与教材等引入公立学校,并不允许学习塾相关人员到校任职。
此外,不少日本地方教委还将学习塾的教学指导经验用于教师培训。例如,东京都足立区教委与大型连锁学习塾“早稻田学术”合作,面向足立区公立小学和初中的新任教师开展研修;东京都葛饰区教委自2011—2015年,已连续四年协同学习塾“把握未来”(Z-KАI holdings)开展面向初中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升项目;埼玉县户田市教委则与日本知名教育培训机构倍乐生(Веnеssе)集团合作,着重帮助学校教师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教学指导能力。[19]学习塾因其在学力提升、完善教育教学方面的丰富经验,逐步涉入学校运营和教师培训,开始为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提供支持。
3.协同解决教育公平、拒绝上学等社会性问题,逐步提升公益性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18年《幼儿园与中小学生学习费用调查》显示,学习塾费用占据校外活动费用支出的比例分别为,公立初中67%、私立初中46%,公立高中61%、私立高中52%。[20]可见,日本初高中阶段的学习塾费用占据了学生家庭校外活动支出的大半壁江山。近年来,日本政府关注到一些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进入学习塾学习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开始协同学习塾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费用补助,“通塾机会均等”措施应运而生。
东京都持续推进的“中考、高考学生拔高支援贷款项目”,面向有需求的初三、高三学生提供通塾所需费用的贷款支持,贷款上限为20万日元,接受贷款的学生如若顺利考入高中或大学,则无须返还贷款;大阪市推出的“通塾补助项目”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初中生,为其提供用于学习塾、家庭教师、文体活动等所需费用相关的补助,每月补助上限为1万日元。[21]与此同时,2011年起日本各地开始涌现被称为“免费塾”的学习塾,如“走近你,帮助你”(Stер uр)、“心连心”(Kizuki) 等。这些学习塾或面向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校外学习支援,或面向拒绝上学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业务领域不仅包括知识学习,还包括了户外体验、饮食教育、志愿者活动与心理咨询等。[22]“免费塾”的运营费用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或社会捐赠。
4.“公费支援型学习塾”助推区域社会的振兴和发展
为解决因家庭经济困难原因无法通塾,导致的放弃高中升学或中途退学等教育问题,除了由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直接的费用补助以外,日本各地还出现了很多地方教委主导、协同学习塾行业的“公费支援型学习塾”。这种新样态学习塾的特点包括:利用学校或社会教育设施等公办教育机构作为学习服务提供的场所,由政府或学校对学习塾的教育内容与运营等进行监督和管理,学生与家长可根据实际需求决定是否参与,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可减免费用等。[23]
2007年,日本福岛县川内村创设了村教委主导下的“川内兴学塾”,该学习塾致力于提升村内学生竞争意识、缓解家庭教育过分依赖学校的情况。创办之初的“兴学塾”面向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生提供学习支援,其中为小学生提供国语、算数辅导,为初中生提供中考科目(英语、数学、国语、社会、理科)辅导。2011年,因遭受东日本大地震,川内村居民只能住在临时住宅,学生的家庭学习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此,川内村教委将“兴学塾”的招生对象扩展至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在为小学生提供国语、算数、英语辅导的基础上,开始为初中生提供基于个人需求的、更有针对性的学科指导和在线教学。[24]
2011年,日本岛根县饭南町教委创办了“饭南学习支援馆”,面向辖区内的农村学生提供学习支援,同时帮助高中生顺利考入大学。该支援馆的指导对象为饭南町内公立初高中学生,2011年的学科辅导为英语和数学,2012年起增加了初中生的国语,并开始面向高中生提供专门针对高考的远程授课。该远程授课由协同教委的学习塾提供内部教材与教学指导,高中生可根据需求选择英语和数学以外的其他高考科目。支援馆计划取得了喜人成效,2013年饭南高中入学人数为70人,相比2005年的58人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来自饭南町以外的学生占比从2005年的13.8%提升至2013年的48.6%。[25]支援馆计划通过打造更为完善的教育环境,提升了公立高中的吸引力。
可以说,“公费支援型学习塾”不仅实现了提高学生学力的初衷,还在满足学生与家长需求、提升学校魅力、促进区域振兴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开展合作的特点和反思
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学习塾行业逐步从赋予其合法地位到认可其价值,再到升级为对学习塾等民办教育机构具备的教育和社会资源加以运用,主动提出协同合作的需求。而学习塾也通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断提升自身在日本社会的口碑和影响力。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逐步形成合力,两者的协同发展呈现一些特点的同时,也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特点
1.政府主导是核心
日本政府在承认并尊重学习塾的市场化机制、学校教育的制度化机制基础上,积极推动两者的有机协同,通过互利共存赢取更多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契机。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与代表官方的学校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两者的协同合作并不代表学习塾能够取代学校,日本也在坚决杜绝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位置颠倒、地位错乱。[26]伴随日本少子化进程的加剧,日本包括了都市在内的多数地区都不得不开展学校间的统合撤并,日本学界预测文部科学省极有可能会把其监管的私立学校运营或改造等委托给学习塾。但公立学校的办学管辖权还是会牢牢把握在政府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27]
2.自上而下、由浅入深
以1999年文部省正式确认学习塾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合法地位为转折点,日本各地政府及公立学校与学习塾的协同合作迅速发展,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学校教育与学习塾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扎实学力,丰富学生的多样化体验,进而构建更为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教育体系。2013年以来,伴随教育领域系列法律政策的颁布出台,学校教育与学习塾的合作进一步普及深入,合作领域从教师派遣、课余辅导、教材提供到教学方法引进、教师研修开展、新样态学习塾创设等,两者的协同合作由浅入深,更为聚焦学生需求、更快回应社会问题、更多引领学校变革,也让日本学习塾的发展逐步走向公益性和多元化。
3.促使学习塾功能内涵发生转变
在学习塾与学校教育开展合作之前,日本学习塾的功能多被认为是营利主义下的升学考试和课后补习。伴随学习塾与政府及学校协同机制的确立,学习塾本身的内涵边界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能提高学生学力,还能助力解决教育公平、社会福利、青少年发展、家庭教育、区域振兴等诸多领域的问题。[28]2018年,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会长安藤大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教育好比一艘行驶的大船,些许的潮流变化并不会影响大局,基于诸多法律法规的学校教育,并不能针对时刻变化的社会需求一一给予回应,也因此,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进行有效缝合的,恰恰就是包括学习塾在内的民办教育机构。[29]学校教育并不能包罗万象,能够起到补充、拓展和深挖作用的学习塾,作为国民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在今后秉承责任意识,为日本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二)反思
学习塾虽已涉入学校的教师培训,但双方的人才交流机制还未形成。虽然日本已经开展了很多由学习塾面向学校教师的研修活动,或邀请学习塾讲师参与学校的课堂研究会,然而这些活动的成效并非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教委或校长主导下的研修活动,因其权威命令的性质以及增加一线教师的繁忙程度而引发教师的抵触感,直接导致相关研修质量低下。许多学校教师并不认可学习塾的考试训练方式,也不愿意他人干涉自己的教育教学[30],双方之间的意识壁垒、固有的偏见都在阻碍相互间的促进和交流。针对这些问题,有日本学者提出改善建议,包括以线上影像的方式观看对方的课堂授课,而不是直接进入课堂;由教委、校长之外的第三方来主导并策划双方间的探讨交流活动,如由学习塾经营企业创办的日本教育大学院大学等。[31]
日本学者早坂惠对学校和学习塾课堂教学的对比研究发现,在知识点讲解通俗易懂、提问环节巧妙穿插、说话方式抑扬顿挫、要点说明醍醐灌顶、讲师教学热情昂扬等方面,学习塾均比学校表现突出、更具成效;而在学生兴趣培养、课堂参与、小组活动方面,学校比学习塾更为重视和强调落实。[32]因此,在利用学习塾开展的教师研修活动中,可有所侧重地将学习塾的课堂教学优势传授给学校教师。同时,在学习塾讲师和学校教师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基于各自不同的课堂教学重点和优势,相互取长补短,以便于在各自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优势,同时有意识地根据学生需求调整教育教学。
此外,近年来不少日本学生家长均提出建议,希望在学生成长支援方面,学校与学习塾还能开展进一步的协同合作。[33]为了多角度观察并理解学生,学校和学习塾应当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原则,实现信息共享,在确保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征求学校、学习塾、家长等相关人员意见,开展个别的案例研究和实践等。
四、结语
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的过程中,常因过度的学历竞争而让学生饱受压力,并助长了校外培训行业的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学习塾的存在不再是与主流的学校教育进行对立竞争,而是有其独特的现实价值。日本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合作表明,公共性与私有性并非不能调和,学习塾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系统的辅助力量,让原本“私有性、自由选择性”的补习教育行为也能具备公共性,并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处。[34]总之,学习塾并没有因为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以及升学竞争的趋缓变成衰退产业[35],而是在快速回应社会需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协同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行业发展态势平稳有力、逐步趋向公益多元的实践创新之路。学习塾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为日本教育生态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