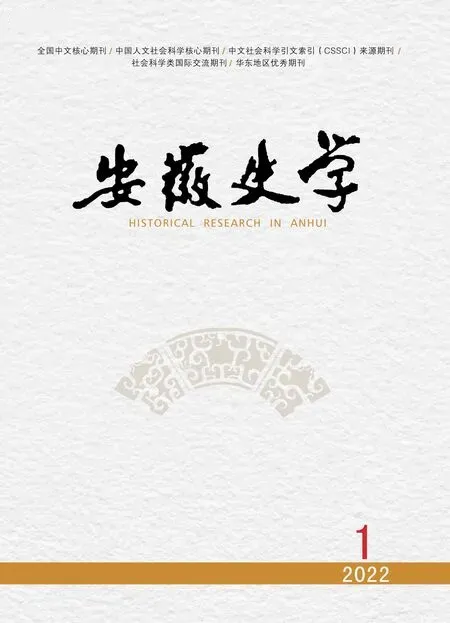华洋诉讼中的法理与国权:熊希龄与华昌公司案研究
2022-11-22侯庆斌
侯庆斌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44)
1926年6月28日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到上海中国国民拒毒会发表演说,被巡捕强行带走,理由是熊希龄被控卷入一起华洋纠纷。1922年美国人怀德(T.C.White)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湖南华昌炼矿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拖欠工资和借款,起诉对象为熊希龄等股东。虽然原告胜诉,但华昌公司已宣布破产,股东们无意执行判决,导致此案迁延甚久。1926年法庭拘传熊希龄一事除涉及前政府要员外,还正值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的关键时刻,故引发各界关注。熊希龄称华昌公司总部在长沙,会审公廨受理此案有违属地管辖原则,妄图染指内地司法,藐视中国主权。舆论声援熊希龄,要求政府彻底收回利权。该案于1927年底审结,新组建的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撤销了对熊希龄个人的指控。
华昌公司案反映了各方对法典成例和会审公廨权限的分歧,其审理过程与五卅后中国政府收回利权的历程相鼓荡。学界对华昌公司案的介绍多点到为止,缺乏法理层面的分析,未能将争议事项置于北洋政府力图取消治外法权的背景下加以详察。(1)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讨论,一类是熊希龄生平研究,有论者注意到华昌讼案引发的舆论,但未作展开。另一类研究考察中方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经过,但没有讨论那些由会审公廨受理但由临时法院审结的案件,未能揭示法权变迁与司法实践的互动,参见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陈策:《从会审公廨到特区法院——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丽:《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始末》,《史林》2013年第5期。本文试图梳理华昌公司案的经过,关注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与华昌公司案的互动,从微观视角揭示北洋时期上海租界司法变迁。
一、华昌公司案的缘起
湖南省锑矿资源丰富。1900年官办板溪矿场经营不善,由热衷实业救国的湖南举人梁焕奎接办。(2)《祖光勋撰湖南华昌炼锑公司节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在同乡好友杨度的帮助下,梁焕奎获得清政府无息垫款,购得法国冶矿技术,事业渐有起色。(3)1903年杨度和梁焕奎参加经济特科廷试,遂成挚交。1907年10月杨度帮助梁焕奎联络张之洞和袁世凯,共筹得直鲁湘鄂苏五省补助款合计16万两。参见梁奇:《华昌炼锑公司及其创办人梁焕奎》,《湖南历史资料》(2),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1908年2月梁焕奎与杨度等募资组建华昌炼矿公司。1909年经杨度向农工商部申请,华昌公司获得锑矿开采的专办权(4)彭国兴:《湖南华昌炼矿公司兴衰史》,《长沙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长沙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印行,第110—112页。,逐渐成为湖南最成功的企业,与汉冶萍、开滦等公司齐名。北洋初期,华昌公司的锑矿专办权因得到内阁要员熊希龄和湖南省长谭延闿的支持而得以维持。1915年华昌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6年熊希龄应邀入股公司,股金由长沙商人垫付。(5)《乞公代垫华昌股款致长沙刘艾堂电》(1916年10月26日),《熊希龄集》第5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32页。1917年熊希龄出任总董(chairman),汪诒书任总理(president)。(6)人事信息出自上海出版的《行名录》。1919年9月股东周扶九曾一度担任代理总董,参见《梁焕奎年谱》,梁晓新、李自强整理:《梁焕奎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312页。熊希龄并非大股东,不插手公司经营,股东们看重的是他的资望和政界人脉。正如后来熊希龄所言,总董不过名号,公司事务一贯由总理负责。(7)《拒毒会欢迎熊希龄之波折》,《新闻报》1926年6月29日,第4张第2版。一战期间华昌公司出口的纯锑占世界市场的60%,分公司遍及上海、汉口、北京和纽约。(8)陈子玉:《湘省矿业概况》,《实业杂志》第187期,1933年11月,第62页。战后华昌公司内外交困,经营状况急转直下。1919年汪诒书辞职,股东们推举董事杨度为代总理。(9)彭国兴编:《杨度生平年表》,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1920年债台高筑的华昌公司尝试加股与并购均告失败。1921年底华昌公司宣布破产,被债权团托管重组,直至1927年彻底倒闭。(10)梁培肃:《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略述》,《实业杂志》第178期,1933年2月,第8—15页。
怀德与华昌公司的纠纷源于两份合同。1921年5月4日华昌公司总理杨度聘请怀德担任总经理(general manager),负责长沙、上海和纽约等地业务,聘期五年,年薪2.5万元,可预支第一年薪金,其余按月支付。合同规定“总经理如能筹得巨款偿还公司债务时,除薪金旅费外,应有相当之酬金”。(11)《华昌与怀德案之文件》,《益世报》1926年7月21日,第1张第4版。怀德在上海经商多年“获利颇丰”(12)《美商控华昌案复审供词》,《新闻报》1923年5月4日,第3张第2版。,被告知华昌公司正欲改组,不久将有转机。(13)《华昌控案之研讯》,《时报》1923年5月3日,第3张第6版。当时华昌公司与一家英国公司接洽,拟出让50%股份成立合营公司。由此推知,杨度聘用怀德的初衷是为了联络外商和筹措资金。1921年6月13日杨度又以华昌公司总理之名与怀德签订借款合同。怀德借给华昌公司5万元,为期1年,每半年付息一次,担保品为华昌公司在湖南益阳的铁轨、车辆和枕木等,估价不低于10万元。合同规定如到期公司无力偿还本息,而又不能及时将抵押品交割时,“债权人得随时移挪变卖其所指定之公司之其他资产”。由于可预支一年薪水,怀德理论上支出2.5万元,便可获得对华昌公司5万元债权,还款期限仅1年,如此高回报足够诱人。此后怀德募资无果,中外合资计划被搁置。1921年底华昌公司宣布破产。借款合同期满后,1922年7月怀德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华昌公司拒不履行合同,要求支付薪金、借款本息并赔偿损失。
1869年设立于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由中方谳员和外国陪审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为被告的案件。清政府要求在租界内享有传拘权并且在审断华洋讼案时适用清律。不过,外人掌握租界市政、警务等大权,不断蚕食中方谳员的权限,很快主导了会审公廨的司法实践。辛亥鼎革之际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撤销上诉法庭,自行委任中方谳员,斩断其与中国政府的联系。从1918年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承认中国新订法典和大理院判例在租界的适用性,但考虑到中国成文法资源的不足,仍须兼顾普通法法理、租界法规和先例。(14)A.M.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Shanghai: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Limited,1925,pp.292-293.会审公廨是一个颇受争议司法机构,其管辖权、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的特殊性,使华昌公司案的审理过程一波三折。
二、会审公廨的初审与判决
1922年华昌公司案被告包括总董熊希龄,总理杨度,董事袁思亮、谭泽闿、周扶九和股东谭延闿共6人。原告索偿合计20余万元。彼时周扶九过世,杨度和熊希龄分别居住于北京和天津,故7月19日首次开庭时仅有身居上海的三位被告到庭。鉴于华昌公司正处于破产清偿中,法庭允许被告交保外出理事,熊希龄和杨度限三周内投案。(15)《华昌矿务公司借款控案》,《民国日报》1922年7月20日,第3张第11版。7月25日法庭证实杨度与怀德的合同未得到董事会许可。在董事会的抵制下,怀德没能就职,但仍听命于杨度,以“总经理”头衔与外商谈判并购事宜。另外,怀德的借款落入杨度手中,无法证明被用于华昌公司。被告律师称华昌公司系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们“对于公司债务,除股本外,不负丝毫责任”,相关债务应由杨度负责。(16)《华昌公司控案之辨诉》,《民国日报》1922年7月26日,第3张第11版。
庭审期间熊希龄没有出庭,仅委托律师马斯德代为辩护。身居天津的他通过电报为谭延闿等出庭被告出谋划策。熊希龄指出杨度与怀德的“私定合同”未经董事会许可。即便有效,由于华昌公司位于长沙,会审公廨无权受理。(17)《为华昌讼案事致友人函》(1922年8月1日)、《探寻华昌案讨论办法致某君函》(1922年8月1日),《熊希龄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80—581页。他还进一步强调会审公廨“袒护外商,擅自受理,实属不平已极”。此案不仅事关华商利益,而且于“国家主权有碍”。(18)《说明华昌公司讼案缘由致刘治州等函》(1922年7月),《熊希龄集》第7册,第542页。按:原文注明发出时间为“5月13日”。然而怀德起诉时间为1922年7月,结合信函内容推知,该函发出时间在8月之前。引文已修正。在熊希龄的影响下,华昌公司案出庭被告的应诉策略是首先质疑会审公廨的管辖权,继而将杨度与华昌公司剥离,认定合同无效,华昌公司不负违约责任,要求原告向杨度索偿。会审公廨遂令双方庭外调解。1922年底华昌公司股东们曾讨论本案,杨度出席并“承认由他一人负责”。(19)《华昌公司之整理办法》,《实业杂志》第62期,1922年12月,第10页。不过,此后杨度无任何偿债举动。庭外和解失败。
1923年初怀德进一步起诉左宗澍等其他华昌公司在沪股东。同年2月熊希龄、左宗澍等人致电北洋政府农商部,一方面称杨度所立乃“未成立之契约”,另一方面抗议会审公廨逾权受理本案,认为“内地公司不蒙外人滥诉公堂滥受”。农商部咨请江苏省省长转饬外交部驻江苏省交涉员,要求务必据理力争。(20)《关于华昌公司诉案之部咨》,《新闻报》1923年2月6日,第3张第1版。此后庭审时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
第一,会审公廨是否有权受理华昌公司案。3月3日庭审时被告律师坚称华昌公司总部在长沙,会审公廨无权受理本案。原告以新版《行名录》为证,指出华昌公司上海分公司位于公共租界宁波路9号。(21)《行名录》显示,1917年华昌上海分公司在公共租界内成立,最初位于江西路A51号,次年迁至宁波路9号。参见“Wah Chang Mining&Smelting Co.,Ld,”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January 1918,p.364.法官据此认定会审公廨的管辖权不容质疑。(22)《华昌炼矿公司控案复讯》,《民国日报》1923年3月4日,第3张第11版。3月7日原告律师又出示一封杨度具名且盖有“上海华昌炼矿公司”图章的信函为证。《民事诉讼法草案》第20条规定违约纠纷中如果双方规定了合同的履行地,“得由履行地之法院管辖”。(23)③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36、1159、1160、1163页。雇佣合同写明怀德为华昌公司在上海等地分公司总经理,且1922年上海分公司仍然存在,故怀德有权在上海发起诉讼。(24)《美商控华昌公司案之辩论》,《新闻报》1923年3月8日,第3张第2版。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何种责任。原告据合同要求以华昌公司财产抵债。被告称相关抵押品在杨度签约之时已作为公司债券的担保品。目前公司名下财产用于破产清偿,已无余资。《公司条例》第126条规定“各股东之责任以缴清其所原认或接受之股份银数为限”。(25)③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36、1159、1160、1163页。被告律师据此声明股东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随着华昌公司财产被债权团接收,被告们的责任已履行完毕。法庭认为原告不能直接要求某位或某几位股东承担全部债务,但作为公司的代表,在沪董事和主要股东须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26)《华昌控案正式开审》,《时报》1923年4月26日,第3张第6版。
第三,怀德所持合同是否有效。被告称合同未经董事会批准,系杨度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7)《华昌借款案继续辨论》,《民国日报》1923年5月2日,第3张第11版。参与签约的华昌公司协理熊某和翻译赵某证实,董事会因薪水过高反对雇佣怀德,对借款一事不知情。(28)《华昌讼案之续审》,《时报》1923年6月8日,第3张第6版。合同签字时,怀德提出应得到两位以上董事的签字,但杨度称他有权代表公司并保证相关财产并未抵押他人。(29)《华昌公司讼案续审》,《时报》1923年6月10日,第3张第6版。法庭认为合同反映了双方的合意,具备签字、印章等要件,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杨度和怀德合谋诈欺,所以合同有效。不过,杨度冒用公司名义签约,致使怀德无法就职,还将已出抵的财产二次抵押,其行为涉嫌欺诈。《公司条例》第163款规定:“董事于公司业务,应遵守章程,妥慎经理,如违背此义务,致公司受损害时,对于公司,应负赔偿之责。董事如有违背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行为,虽系由股东决议而行者,对于第三者不能免损害赔偿之责。”(30)③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36、1159、1160、1163页。
据此华昌公司应承担两个合同导致的债务,并有权向杨度追偿。1923年11月19日会审公廨宣判。首先,契约有效性的关键是杨度是否代表公司。法庭认为华昌公司经营不善,董事们散居各地,“其执行公司业务负责任者,仅总理杨度一人”。考虑到华昌公司曾在会审公廨追讨他人所欠款项,有被告称借款合同仅有杨度印章,以不合程序为由试图免责。杨度的代表辩称华昌公司的事务均由总理决定,董事会事后追认。此类债务诉讼不止一例,故会审公廨根据先例认定杨度与怀德的签约程序符合华昌公司一般习惯,并援用中国法典成例进一步解释:“依《公司条例》第32条,以章程或各股东之同意所加于代表权之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之第三者。又,大理院五年上字271号判例,受任人违反委任人之指示时,虽得要求受任人负担责任,然不得以此对抗善意之第三人,而主张该受任人处理委理事务为无效。”(31)《华昌与怀德案之文件(续)》,《益世报》1926年7月22日,第1张第4版。所以怀德的合同有效,华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因抵押品重押一事,杨度故意欺诈行为成立。第三,股东责任适用《公司条例》第126条,“原告仅能对于公司有所请求,不能使董事股东等个人负何等责任”。(32)《华昌与怀德案之文件(二续)》,《益世报》1926年7月23日,第1张第4版。最后,法庭判华昌公司支付原告工资、借款本息及相应损失共计25万余元,同时驳回原告对股东个人的索偿要求。初审判决后华昌公司没有对杨度追责,原因或许是公司陷于破产后管理混乱,董事们分居各处,事不关己,无人任事。
就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而言,《公司条例》第223条规定若债权人未能在有效期限内加入债权团或清算人名单,那么仅能在公司清偿各债后的剩余财产中索偿。(33)③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36、1159、1160、1163页。华昌公司破产后组建了债权团,怀德不在其中。华昌公司变卖资产后尚欠40余万元,遂由债权团接管矿山另行集股经营,华昌公司得其中五成利润,用于摊还已登记的债权人的债务。(34)《华昌公司筹还债务之办法》,《实业杂志》第74期,1923年12月,第98—99页。怀德也难以从中获得补偿。1924年会审公廨要求华昌公司董事们“协助执行”判决,依旧无人响应。怀德又联系美国驻长沙领事协助,对方称华洋诉讼积案甚多无能为力。(35)《美商控华昌案之执行问题》,《新闻报》1924年1月15日,第3张第1版北洋政府外交部驻江苏省交涉员许沅出面协调沪湘当局。湖南省交涉员致函许沅,质疑会审公廨的判决能否在长沙执行。许沅复函称会审公廨与内地官厅“彼此均有协助,已成惯例”,请长沙地方审判厅执行判决,但对方未有回应。(36)《沪交署复函湖南交署》,《时报》1924年2月26日,第3张第5版。考虑到华昌公司股东与政界多有勾连,不难理解湖南地方当局的冷漠,这也是怀德不愿到长沙发起诉讼的原因。
1924年11月6日原告律师请求法庭令被告交保限期履行判决,又称杨度和熊希龄从未出庭,指责二人“藐视法庭”,要求“移提杨度熊希龄到案交保”。会审公廨分别致函京津地方审判厅要求移提二人到庭。(37)《美商控华昌公司案近闻》,《新闻报》1924年11月7日,第3张第2版。京津两地审判厅未作回复。1925年2月美国驻长沙领事与湖南政府多次交涉无果。湖南省交涉署和长沙地方审判厅依旧质疑会审公廨的判决在内地的效力,认为此案系杨度与怀德之间的纠纷,应在长沙起诉。华昌公司留守董事们开会讨论此事,亦无结果。美国驻长沙领事认为股东们“不愿清理”,各方“意在延宕”,他也无能为力。(38)《华昌炼矿公司案续闻》,《民国日报》1925年2月14日,第3张第11版。怀德及其律师多次敦促执行判决毫无进展,华昌公司案彻底陷入僵局。
三、华昌公司案的重启
1926年熊希龄被拘传一事被称为“熊案”,由此开启了华昌公司案的续审。1921年会审公廨规定:“即使居所在租界之外的人在租界逗留期间也受会审公廨的管辖。”(39)A.M.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290.据此,法庭虽有权传唤熊希龄,但用1924年的过期传票传唤被告已属违规。另外选择“拘传”这一刑事诉讼程序颇为不妥,反映了会审公廨对熊希龄长期缺席庭审的不满。熊希龄此次访问中国国民拒毒会不同于以往访沪,中外报纸早有预告,甚至列出熊希龄南下行程和抵达上海后发表演讲的时间和地点。(40)“From day to day,”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ne 17,1926,p.10;“Personal notes,” The North China Herald,June 19,1926,p.543;《拒毒会将欢迎熊希龄》,《民国日报》1926年6月24日,第2张第1版。原告和会审公廨由此获知信息,熊希龄遂于第一时间被拘传到案。6月28日晚庭审时旁听者包括许沅、丁文江和各界人士40余人。熊希龄称华昌公司破产后他已卸任董事,拒绝代公司偿债。在缴纳1万两保证金后,熊希龄当庭获释。(41)《熊希龄因华昌矿案被拘》,《时报》1926年6月29日,第2张第3版。
熊案引发轩然大波。6月28日晚拒毒会发表声明称熊希龄“平日资格声望,久为国人所钦仰”,此番拘传“显系有意侮辱”。请求许沅提出严正交涉,尽快收回会审公廨,保障公民人格与国权。(42)《拒毒会抗议会审公廨无故拘捕熊希龄致江苏交涉员许沅函》(1926年6月28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16—817页。6月29日上海工商学团体联席会议谴责会审公廨,称擅自拘传是对熊希龄人格和中国国家体面的双重羞辱,要求许沅代为抗议并“积极进行收回公廨运动”。(43)《熊希龄被传保出后之所闻》,《新闻报》1926年6月30日,第1版第4张。7月3日“各团体抗争熊案联席会”向许沅请愿,抗议会审公廨的行径。(44)《各团体昨日会议熊案》,《时报》1926年7月4日,第2张第4版。上海总商会和北京各团体也声援熊案,要求北洋政府与上海领事团交涉。(45)《总商会关于熊案之公函》,《申报》1927年7月3日,第13版;《本馆专电》,《时报》1926年7月5日,第1张第3版;《熊希龄案尚未了结》,《益世报》1926年7月7日,第2张第6—7版。
与1922年相比,1926年舆论对华昌公司案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各界只关注熊案,无关华昌公司与怀德的纠纷。一方面源于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的特殊身份及其出庭方式。例如7月3日拒毒会召集各团体商讨对策,认为熊案中值得注意的是“熊君之身份地位”。(46)《关于熊案昨讯》,《申报》1926年7月4日,第13版。另有言论支持维权,但反对将熊希龄人格等同国格,建议参考中外章约揭露会审公廨的执法不公。(47)《姚公鹤论熊希龄被捕案》,《民国日报》1926年6月30日,第2张第1版。《益世报》社论也批评熊希龄将个人事务与国家体面相联系,提醒读者无人关注华昌公司的违约责任。(48)《熊希龄案之无聊》,《益世报》1926年7月16日,第1张第2版。不过,上述建议很快被声援熊案的声浪淹没。
另一方面,熊案发生时正值中外谈判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关键时刻。列强以租界治安恶化和中国新法尚不完备为借口,要求保留在会审公廨中的权力。(49)A.M.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273.北洋政府态度强硬,双方互不相让。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中外交涉难以继续,转由江苏省政府接手谈判。当时孙传芳初定江浙,上海律师公会建议他“亟应做几件有利于国家及大众所期望而中央不能解决之事”,又称“会审公廨为上海居民受害最深、最不合理之制度,如能收回法权,定得上海商民拥护”。(50)赵晋卿:《收回会审公廨交涉的经过》,陆坚心等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孙传芳遂指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会同许沅负责谈判事宜。为尽快收回会审公廨,孙传芳一改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采取妥协姿态。6月21日协定草案达成,丁文江等挽回部分利权,例如收回民事诉讼审判权、取消领袖领事在传拘票上的签字权,但保留了外国领事在刑事案件中的观审权等。(5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版,第591—593页。各界的期待落空,纷纷要求收回全部利权。(52)《沪廨协定宣布以后之形势》,湖南《大公报》1926年7月24日,第2—3版。熊案的发生恰为舆论抨击会审制度提供了契机。
7月3日熊希龄发布声明,继续质疑会审公廨的管辖权,抗议拘传程序。他不忘强调前国务总理身份,认为个人受辱事小,商民受累事大,呼吁“今当开议收回公廨之时,吾国有识之士,必须加以研究,使此有累商民之制度改为完密,而后乃可保全良善也”。(53)《条陈鸦片与治外法权解决之法致拒毒会函》(1926年7月3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16页。这是熊希龄在庭审后首次袒露心迹,即绕过华昌公司案中的违约纠纷,否认法庭的管辖权,利用收回会审公廨之际,由个人受辱推及会审公廨藐视中国国体与主权,向中外施压。这一应诉策略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制造舆论。各报有关拘传过程的新闻稿全部出自大华通信社记者宋某,而宋某恰是拒毒会的秘书。熊希龄一方统一了报界的信息源,以致上海小报自嘲已无事可做。(54)《熊希龄案》,《上海滩》1926年7月3日,第2版。7月2日收回会审公廨协议草案泄露。舆论纷纷谴责孙传芳。(55)《沪廨案杂讯》,《民国日报》1926年7月5日,第2张第1版。7月5日拒毒会致电孙传芳,称“上海会审公堂常年藐视吾国国体与法律,久为国人所公愤”,请求政府迅速收回会审公廨,“以全国体而保主权”。(56)《熊希龄案之抗争理由》,《民国日报》1926年7月5日,第2张第1版。前湖南省长赵恒惕、前内阁总理王士珍、孙宝琦、赵尔巽等纷纷响应,声援熊案。(57)《本馆专电》,《时报》1926年7月8日,第1张第3版;《赵恒惕电孙传芳》,《时报》1926年7月9日,第1张第3版。各团体抗争熊案委员会向许沅提交抗议书,并以“征询意见”为名寄送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同时致电外交部、司法部、孙传芳和丁文江,要求将熊案纳入收回会审公廨中办理,以免类似事件的重演。(58)《关于熊案昨讯》,《申报》1926年7月9日,第13版;《交涉员令公廨撤熊希龄保案》,《民国日报》1926年7月10日,第2张第1版。熊希龄还谋求将抗议书刊于英文报纸以扩大影响。(59)《请将委托律师电稿译成英文登报致王云五函》(1926年7月10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17页。
第二步,直接与官方接洽。主持收回会审公廨的丁文江与熊希龄同在中国国民拒毒会共事。熊希龄被拘时,丁文江曾向巡捕据理力争,随后旁听庭审,全力支持熊希龄维权。7月3日熊希龄与许沅会面。(60)《许秋帆明日延请熊希龄》,《时报》1926年7月2日,第2张第4版。随后许沅发表声明称华昌公司案须依照《民事诉讼法草案》第16条第2项,由原告就被告,会审公廨无管辖权。此外熊希龄被强行拘传有违民事诉讼程序,应销案并归还保证金。(61)《交涉员令公廨撤熊希龄保案》,《民国日报》1926年7月10日,第2张第1版。但许沅似有保留,对收回会审公廨未置一词。熊希龄随后赴南京寻求孙传芳的支持。7月10日孙传芳公开宣称会审公廨在华昌公司案和拘传熊希龄一事上违法越权,敦促许沅核办。(62)《本馆专电》,《时报》1926年7月11日,第1张第2版。
前两步就绪后,7月11日熊希龄从南京向代理律师连发三封急电,禁止他们在庭审时参与辩论。(63)《告知华昌公司控案应在管辖权回复后方能议及致古沃律师电》(1926年7月11日)、《告知不出庭并就管辖权问题提出抗议致古沃律师电》(1926年7月11日)、《告知已发急电并再抄稿寄呈致古沃律师函》(1926年7月11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17—819页。他再次强调“希龄与其他董事不同”,“作为前国务总理,有维护国家主权之责,不能冒昧接受会审公廨的审理”。(64)《告知不出庭并就管辖权问题提出抗议致古沃律师电》(1926年7月11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19页。7月12日开庭时,熊希龄自称因公滞留南京,由律师代其出庭。本次庭审因熊希龄的抵制而草草收场,全程仅15分钟。(65)《熊案开审纪》,《新闻报》1926年7月13日,第3张第1版。诚如记者所见,“此案之法律问题及外间所争之管辖问题,均无一言辩论及之”。(66)《熊希龄案昨日开审》,《民国日报》1926年7月13日,第2张第1版。熊希龄拒不出庭的姿态得到各界支持。(67)《本馆专电》,《时报》1926年7月13日,第1张第2版;“New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ly 19,1926,p.18.7月14日熊希龄分别致电北洋政府、孙传芳和许沅,建议将此案发回长沙审理。他借口一旦出庭,等同于承认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又称会审公廨无上诉机构,此案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自然不必出庭。(68)《请电江苏交涉员严重交涉致蔡廷乾、罗文乾电》(1926年7月14日)、《申述熊案只能在政治外交上解决致许沅电》(1926年7月14日),《熊希龄集》第7册,第821—822页。7月26日熊希龄函告各界不再来沪,声明华昌公司案由许沅办理。(69)《熊希龄函告不再来沪》,《民国日报》1926年7月27日,第2张第1版。7月29日外交部致电拒毒会和各团体抗争熊案联席会称,英美驻沪领事同意协助,已要求会审公廨设法补救。(70)《英美领事允协助》,《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第2张第1版。此后会审公廨中止了华昌公司案的审理。
纵观这一阶段的庭审,会审公廨以废票拘传熊希龄,已属违规,又要求他承担华昌公司的债务,有违一审判决。舆情和中外交涉主导了熊案的走向。许沅曾试图劝止中国政府的介入。他电告北洋政府外交部称会审公廨管辖权问题在华昌公司案一审判决中已经解决毋庸再议。但外交部认定会审公廨越权受理华昌公司案有辱国权,严厉申斥许沅“借故推诿”“忽视职务”,要求务必提出抗议。(71)《外部电责许沅》,《时报》1926年7月13日,第2张第3版。许沅不得不从命。舆论发挥作用与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有关。报人林白水撰文认为熊案“足见外人之藐视吾国,此而不争,中国从此可以不必再言收回法权矣”。他要求当局借此机会与北京公使团交涉,取消会审公廨。(72)《上海公廨收回之时机已到》(1926年7月17日),林伟功主编:《林白水文集》,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2006年印行,第1170页。《国闻周报》社论指出熊希龄身份特殊,因此熊案“不能以普通私人间之纠葛视之也”,“官场得此刺激,当亦恍然,公廨弱点,暴露无遗。然则熊氏所有助于收回公廨运动者实多矣”。(73)慎予:《熊希龄案之舆论》,《国闻周报》第3卷第26期,1926年7月11日,第2—3页。熊案助长了舆论对华洋会审制度的不满,扼制了孙传芳集团对外交涉中的妥协姿态。1926年7月至8月中外继续修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草案,于8月31日正式签字。与初稿相比,丁文江等人在管辖权等原则问题上未再让步。面对汹汹舆情,会审公廨的冷处理实属迫不得已。如果销案则坐实对华昌公司案无管辖权,自认诉讼程序有误。正如舆论所见,“惟闻公廨方面已不便为正式表示,此事即以延搁了案”。(74)《熊希龄案之结果》,《民国日报》1926年8月9日,第2张第1版。总之,1926年华昌公司案的重启与搁置的过程中,熊希龄利用舆论将该案升级为交涉事件,不仅暂时摆脱了官司,而且间接推动了中方收回租界法权的进程。
四、熊希龄的上诉与华昌公司案的审结
1927年1月1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被改组为上海临时法院,新法庭再次启动华昌公司案的审理。熊希龄仍强调租界法庭无权受理并索要保证金。1月24日上海临时法院重申1926年会审公廨的判决,拒绝销案和退还保证金。江苏省政府收回会审公廨后,熊希龄失去了从外交渠道解决华昌公司案的借口,加之孙传芳忙于对抗国民革命军,所以熊希龄的要求难以得到地方政府和舆论的关注。该案的解决只能重新诉诸司法渠道。
1926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曾根据《民事诉讼法草案》第16条第2项声明会审公廨无权受理华昌公司案。熊希龄亦沿用此说。揆诸法典可知,该解释虽有利于舆论和外交,但在法理层面存在疏漏。《民事诉讼法草案》第16条第2项规定“私法人及其他得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切团体,其普通审判籍,依总事务所所在地定之”。(75)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第836、837页。据此华昌公司案原告应到长沙起诉。但这一解释无视《民事诉讼法草案》第20条对第16条的补充规定,即双方合同约定的履约地法庭同样有权受理违约纠纷。这便是上海临时法院拒绝销案的原因。1927年7月熊希龄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官对管辖权做出解释,并免除熊希龄对于华昌公司的债务责任,退还保证金。(76)《熊希龄之上诉理由书》,《新闻报》1927年7月23日,第4张第4版。由于前会审公廨积案甚多,加之北伐时期临时法院人事动荡,熊希龄的上诉迟迟未排定开审日期。12月14日华昌公司召开最后一次股东会,与债权团清理账目,正式宣布破产。至于所欠怀德款项,股东们不愿协助,宣称“杨皙子(笔者按:即杨度)已承认由他一人负责”。(77)《华昌公司之整理办法》,《大公报》1927年12月16日,第4版。
12月28日上海临时法院做出裁决。就管辖权问题,法庭除援引《民事诉讼法草案》第20条外,还援引了第34条,即同一诉讼数处法院有权管辖者,原告可择其中一处起诉。(78)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民国十三年编订法令大全》,第836、837页。法院查得合同中注明怀德履行总经理职务的地点为“长沙、上海、纽约以及公司将来新开之营业处所”,故1922年会审公廨有权受理本案。就责任问题,法院承认1923年11月会审公廨的初审判决,即原告不得向公司董事个人索偿。法院据中国判例认定在民事诉讼中,除经正式上诉和复审程序外,“不得因当事人之声请,自将前判撤销或变更之”。1924年1月会审公廨要求被告等“协助执行”判决一事,法院认为既然董事个人不承担责任,岂可强制要求董事们“协助执行”。会审公廨将董事们拒不协助的行为视作“藐视法庭”,时隔近两年以废票拘传熊希龄,有违会审公廨民事诉讼惯例。因此,上海临时法院同意撤销前会审公廨对熊希龄的处分,归还保证金。(79)《熊希龄与怀德上诉案宣告结束》,《新闻报》1928年1月4日,第4张第4版。《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关于熊希龄请发还保银的文件》(192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179-1-111。本案至此审结,怀德依旧胜诉。随着华昌公司彻底破产,怀德后续维权结果不详,但注定困难重重。
结 论
华昌公司案历经近六年审理终告一段落。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驳回熊希龄对法庭管辖权的质疑,免除股东个人的债务责任,这与1923年会审公廨一审判决一致。从结果来看,1926年熊案的爆发和各界的声援是对华昌公司案审理的一次干扰。可见时局变迁是该案的审理一波三折而又重回原点的重要原因。
华昌公司案在舆论中的隐与显,以及会审公廨的管辖权不断被“问题化”,都反映了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渐高涨和北洋政府收回利权的努力。初审期间,原被双方致力于从法理出发辩明公司性质、股东责任和合同效力。熊希龄等被告对会审公廨管辖权的质疑被驳回。这在舆论中毫无反响。会审公廨缺乏在租界之外执法的理据和资源。一旦判决无法执行,会审公廨只能在租界范围内诉诸激烈手段迫使被告就范,遂有1926年华昌公司案以拘传熊希龄的方式重启。熊希龄本可重申一审判决摆脱个人的清偿责任,并对传唤程序提出抗辩。但实际上,熊希龄强调前国务总理的身份,由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引申为中国主权受辱,将缺席庭审解释为消极抵抗以保国权,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会审公廨司法管辖权问题本已在一审期间解决,此番成为各方抨击的焦点,与彼时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密切相关。1925年五卅运动后各界的主权观念加强,舆论呼吁维护国权与北洋政府收回利权的行动交织,使这起违约纠纷被高度政治化。熊希龄诉诸外交途径摆脱个人困境,得益于舆论环境,也间接推动了中方收回会审公廨。1927年中国政府收回会审公廨后,熊希龄的应诉策略变得无的放矢,只得重新诉诸司法渠道。华昌公司案的审结经历了从司法途径,到中外交涉,再回归到司法理性的过程,其中法理与国权的变奏展现了中外关系对华洋诉讼的影响,亦构成租界法权变迁和近代中国取消治外法权历程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