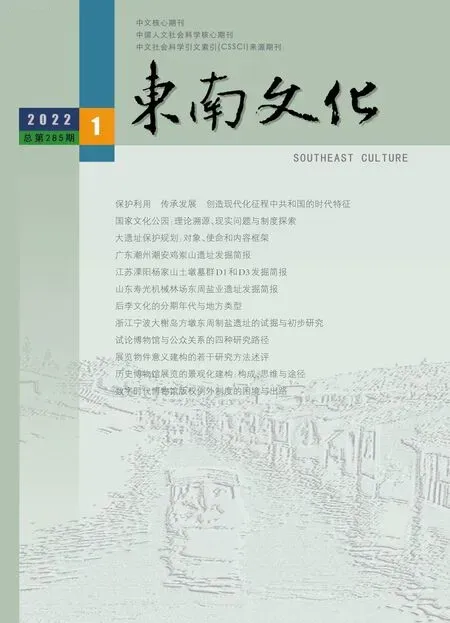博物馆融入多元人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
2022-11-22王思渝
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西方博物馆学研究在关注博物馆与“人”的问题时存在着一类倾向,即愈发强调人群的多元性。这种倾向以强调曾经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人群以及人群内在的差别性为主要特点,同时,学界也惯于以“官方”与“非官方”这样的二元关系解释此类现象。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博物馆已有诸多收藏、展览、教育等实践均呈现出关照多元人群的一面,但从其关照的人群范围以及关照方式的角度来看,其在全面性和系统性上仍存在局限。同时,从中国的博物馆实践来看,“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并非截然二元对立。官方基于社会服务、吸纳多元人群等诉求存在着向非官方的贴近,在具体的博物馆案例当中也能看到“官方”与“非官方”相互交杂的一面。
如果今天进一步去梳理西方博物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不难意识到有大量的研究都将目光投向博物馆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或文化力量的关系,尤其是博物馆与“人”的关系问题已逐步成为西方学界的热议话题。我国博物馆学界对此类问题也曾有不同程度或不同侧面的关注。例如,在所谓的“新博物馆学”最初影响我国之时,甄朔南先生曾以“以人为本”概括新博物馆学的特质[1];再如,近年来,随着博物馆教育以及观众研究等领域的发展,我国的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学研究对于“观众”“受众”等概念愈发重视。那么,新博物馆学所讨论的“人”、博物馆教育或观众研究所关心的“人”是否便已经等同于西方博物馆学中所有关于“人”的讨论?在我们的目光从理论回到现实实践之后,又将看到怎样的图景?
本文将通过简要的理论回顾,指出西方博物馆学研究在论及“人”的问题时所存在的一类倾向,即对多元人群的强调。同时,本文也将立足于我国的实践,进一步指出对多元人群的关照并非仅是西方博物馆学的产物,在我国博物馆世界当中也有诸多实践涉及此类问题。当然,我国的实践也自然存在着基于我国国情而面临的特定挑战。在这当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现象,即在西方博物馆学所建构起来的这套博物馆与多元人群之间的理论关系当中,时常伴随着一种“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二元关系视角。那么,以我国的情况为例,应如何理解这样的二元关系?本文也将对此作出回应。
一、西方博物馆学研究中的多元人群
1.多元人群的特点
西方博物馆学的发展历来热衷于讨论博物馆与“人”的关系问题。如果重读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博物馆学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大量讨论所涉及的“人”并非全然是一种泛化的概念,本文将其归纳为一种对多元人群的关照。具体来说,这些作品介入多元人群议题的路径又有所不同,至少存在下文三种情况。
其一,以伊凡·卡普(Ivan Karp)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更多是在文化研究或符号学传统下,将该问题向博物馆展览如何实现人群“表征”问题的讨论引导。在这类讨论当中,展览被视为一类文本,不同人群的“身份”在文本的书写过程中被解构和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8年、1990年和2006年的三次讨论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其间所涉及的“人群”并非是简单的博物馆受众群体的扩张。这三次讨论展现了一条在人群的问题上从所谓的主流族群逐步扩张到少数族裔、社会边缘人群再到全球化语境下的“他者”的路径[2]。人群之间的差别性明显、人群内部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
其二,在大量的以“新博物馆学”为旗号的研究当中,其所涉及的人群指向也是在一个文化多元性基础上的有差别人群。尹凯以我国的情况为基础强调了其间的“民族”和“地方”身份[3],这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博物馆学思想在人类学和地方发展运动的影响之下对特定人群的差别性关照。
其三,该问题也可弥散为更广泛地关注博物馆的政治性或公共性问题,诸如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詹妮弗·巴雷特(Jennifer Barrett)等学者的工作,均在进一步反思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兴起之后,博物馆是否真的成为话语空间和人群身份的多元性得以孕育和发酵的重要场域[4]。在这类讨论当中,受一个更为经典的“公共”(public)定义影响,人群的多元化同样不只限于博物馆参观人群的数量提升,而更强调社会分层和文化身份上有差别的多元人群在博物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的介入。同时,人群的讨论还可以呼应博物馆学领域内一系列对于阶级问题的关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以文化资本和社会区隔为视角切入讨论阶级身份与博物馆审美,至今在博物馆学领域仍有深远的影响[5]。在继承布尔迪厄研究传统的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对这种阶级冲突论色彩浓厚的研究展开反思,回到更细致的博物馆生成过程中,展现出以文化依存关系替代传统讨论的意图[6]。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简要的理论回顾,本文可将西方博物馆学中所存在的多元人群倾向概括为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受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影响明显,其所重点关照的人群多是在一个整体社会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差别性人群,其目的导向是通过对该类人群的重新重视以构建一个整体的多元社会;第二,受社会学或文化研究传统下对“身份”(identity)或“社区”(community)概念的影响,对人群内部的差别性、流动性和权力空间予以重视,寻找更为细致化的博物馆与人群间的合作模式。
2.何以推动对多元人群的关照
此外,当论及博物馆对多元人群的关照时,国际国内学界均热衷于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便在于博物馆为何要关照多元人群以及是怎样的力量推动博物馆关照多元人群。在这当中,一种“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关系常被作为重要的解释框架。
“官方”与“非官方”的问题在上文已提及的西方博物馆学文献当中,本身便已出现了多次并能看到诸多例证。例如,“博物馆热”曾一度是国际国内学者热衷讨论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直接体现为博物馆参观人数、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以及博物馆类型的多元化等现象。其中,尤其是关于博物馆类型的多元化,王思渝通过对《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杂志的分析,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博物馆发展所呈现出的重要现象之一便是大量以大众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的发展[7]。这与本文所关注的多元人群也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正是这类人群构成了大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主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我们如何解释此类博物馆的出现与发展。苏东海、安来顺等学者也曾经讨论过“博物馆热”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国家的出现及其背后成因[8]。在这些讨论当中,一种以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为主导的中小型博物馆模式常被学界重视[9]。从某种程度上,这类博物馆的发展近乎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在建馆、办展模式上“非官方”力量的增长,借此实现对于权威的消解、权力的赋予以及官方话语权的破除。再如,回到更具体的案例之上,沈辰在介绍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的情况时也有大量篇幅论及“文身”“第三性”等特定的差别性人群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论述当中也能明显看到“非官方”的社会团体与社会资本的成长为这种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10]。
总体来说,以上文献借助“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二元关系所强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导力量层面的公权力问题,其二则是“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一种对立性。那么,这种二元关系是否便是解释多元人群关照得以形成的唯一方式?这种二元性是否截然对立,抑或存在更为交融的可能性?下文将结合我国的情况进一步展开论述。
二、中国博物馆的实践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博物馆与多元人群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将目光投向国内的现实实践。
1.现状
我国博物馆曾长期被认为带有过于浓重的“官方”色彩,在机构定位上仍未从知识本位走向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博物馆在多元人群的问题上是截然缺席的。这可简要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我国已建成一批与多元人群密切相关的博物馆,在“为了明天而收藏今天”等理念影响下,形成了一套与当代多元人群身份相结合的收藏体系。例如,更具“官方”性质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以及更具“非官方”性质的建川博物馆群、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主题博物馆均已建立并有所发展。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新博物馆运动在我国的落地也以带有差别性身份的多元人群为基础。上海虹桥机场新村自2020年建成社区参与型博物馆以来,便以小博物馆展示空间的形态纳入所在地社区这一独特群体的集体记忆和物证[11],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视为更广泛的赋权理念下与社区博物馆形态之间的一种默契。从博物馆主题的角度进行清点,在国家文物局官方登记备案的博物馆中,以电影、服装、汽车、地铁乃至玩具等大众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早已不再缺席。首都博物馆对胡同文化、国庆阅兵等相关物证的征集,新冠疫情之后以湖北省博物馆等为代表的博物馆对疫情相关物证的收藏,均可视为博物馆将触角不断延伸至一个更为当代的多元人群的体现。
其次,从博物馆展览的角度,国内诸多博物馆展览近年来在实践层面对女性、民族、在地社区等有特定文化身份的人群均呈现出难得的重视,且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拼图”式的囊括,而是开始以该人群为本位、着力于刻画特定身份人群内部的多元化。以女性题材为例,女性身份在博物馆展览当中不再仅以温婉、柔弱等单一的面相呈现,展览或开始强调整体历史叙事当中女性身份的参与度,或开始借用展览对女性形象的重塑以隐喻当下的社会现状,由此,让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成为展览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母题。首都博物馆“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等展览均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此类展览在国内已经引发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讨论显示出此类展览的“反本质主义”[12]的色彩及其对身份问题的重塑。
最后,从广义社教的角度,在“三贴近”等原则的影响下,我国博物馆在人群的多元化问题上也有了更为长久的积累。甚至相较于展览而言,我国博物馆在所谓的“教育”过程中对多元人群的考量反而显得更为明显。以2019年的《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为例,在提及“展示”时仅使用了“观众需求”“社会效益”等在人群意识上较为泛化的提法,而提及“教育”时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要有“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社会教育计划”以及“服务学校、工厂、社区和农村等不同观众群体”。在具体的教育手段上,与中小学甚至更低幼人群的合作已渐成为博物馆行业内的常态化做法。面向残障人群的专场活动、以志愿者的形态实现博物馆与更多元人群的联结,均已在国内博物馆行业内常见。
2.反思系统性与全面性
前文的讨论展现了我国博物馆面对多元人群时的基本现状。但是,从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于我国博物馆而言,人群的覆盖是否足够全面?现有的覆盖面是基于怎样的机制形成的?这种机制是否足够具备系统性?大卫·赫斯孟德夫(David Hesmondhalgh)在论及音乐、电视、广告等更具市场化推动力的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时曾注意到,“繁荣”并不等同于“多元”,量的累进并不完全意味着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关系有了本质性的改变[13]。这样的提醒对于我国博物馆行业来说同样重要。基于此,下文以上文已提及的面向多元人群的展览和教育为例反思其系统性和全面性。
首先,在博物馆展览的问题上,上文已提及的面向女性、地方或民族身份多元性展览的出现,一方面呈现了博物馆作为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在面对当下特定的人群文化时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这种反应仍然有诸多不充分之处。从展览内容来看,其最核心的局限之一在于这类反本质主义式的做法在对特定身份进行进一步展示时,仍主要是对立性或解构性的。其在主流的学术或大众形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差异化的新版本,但是展览对于这个新版本本身内部的层次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并没有表达出更多更成系统的企图。以对在地社区的展览为例,展览在展示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人群时,往往优先强调其异于“他者”的特殊性表征,但是对于这个人群“自我”的内部分层、历史流动性、与“外界”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该群体更为自洽的日常性生活则显得关注不够,也缺乏以此为基础的更具系统性的收藏与展示计划。学界在讨论我国早期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问题时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14],而此类问题实际上在生态博物馆更为后期的实践以及更广泛的博物馆类型当中仍可窥见。
其次,在社教问题上,博物馆对特定人群的关照仍然多基于博物馆自身的机构理性而言,易于引发在内容上的偏向以及在人群全面性问题上的局限。以博物馆对青少年人群的重视为例,当下,面向青少年人群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已成为诸多博物馆正在追赶的“热潮”。博物馆对这一群体的重视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推动力:其一,分众化的营销策略和观众研究在博物馆领域内对于更广范围的博物馆教育框架的影响;其二,相较于展览而言,对教育活动的分众化设计更为可行和容易;其三,近年来我国整体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在社会教育的大潮当中寻找到自身的位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经专文讨论此问题[15]。在这样的“热潮”之下,这是否意味着博物馆教育已实现了对多元人群的合理建构?对这个问题的质疑,首先涉及博物馆教育内容的偏向。我国的博物馆目前所呈现的教育内容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导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所述的19世纪晚期以来博物馆智识中心地位的丧失[16],在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博物馆所施教的知识仍然是传播和服务性质的,缺乏对知识的自主生产能力、对启发性知识的灵敏度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呼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教育所呈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便在于,我国的教育体系常遵循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分的体系,在此体系下,整个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间的既要寻求区别又要寻求联系的张力一直存在。在此背景下,相较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应该教导的内容却一直未有相对稳定的结论,教育内容受市场需求的摆动仍然较大,尤其是随着博物馆在教育项目上的可营利化,大众市场也的确能转换为直接购买力,与博物馆之间形成一套直接的供需关系。如此一来,博物馆所主导的、面向多元人群的教育内容是否具备系统性,这便更值得质疑。并且,从人群覆盖面的角度来说,这种供需关系的形成容易造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这意味着一个更全面的分众化过程得以在博物馆教育领域内实现;其二,这也预示着博物馆教育将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以资本为导向的特征,而对于那些本身便缺乏购买力、时常被主流文化机构忽视的人群而言,他们则更有可能被这样的浪潮淹没。
综上可见,无论是从展览还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博物馆所面对的多元人群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均有所缺失。这与我国在公共文化领域面对此类议题时,整体政策动力不足、社会力量有限、博物馆自身的行为理性常仅基于自我的机构立场而出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三、走出二元对立
在看到我国博物馆的上述实践之后,再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留有一个问题尚未回答,即我们如何理解隐藏在博物馆与多元人群背后的“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二元关系。对此问题的理解,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厘清两方面问题。
其一,在强调这种二元关系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官方”面向“非官方”议题时的主动贴近,“非官方”不一定便是多元人群寻求自我文化身份权力表达的唯一途径。
以同样在上文提及的大众文化主题博物馆为例。这类博物馆在我国的成长过程中受两方面的力量影响明显:一方面是由官方的具体职能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直接推动,包括我们通常所提的“行业博物馆”,如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等;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企业(其中不乏诸多大型国有资本影响下的企业)为推动,如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玩具博物馆等。如果说我们将大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成长看作代表了更为“草根”或拥有特定爱好的多元人群的身份与声音,那么在主导动机和推动力的问题上,上述情况至少表明这类博物馆在我国的成长并没有受限于完全遵循一套“西方式”的官方支持,从而将话语空间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组织的模式,它所体现的更多是来自官方对多元人群的自发贴近。尤其是在我国的官方和大型资本实体当中,公共性理念日益得到强调,衍生出了愈发浓郁的社会“服务”意识,例如我们从绝大多数的行业“大馆”或企业博物馆的建馆企图及其实际运营当中也都能看出这一层色彩。
其二,所谓的“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关系在更多情况下时常是相互依附而非对立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类主体力量的问题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同一个案例当中,我们常能看到所谓的“官方”“资本”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更为交杂的一面。
以北京市近年来常见的社区空间的博物馆化为例[17]。它的主体交杂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官方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这并不一定体现为直接的官方办馆,但是博物馆产权和开发权的协调自然离不开官方的首肯。如此一来,官方的态度便成为此类博物馆项目能否成形的起始条件。从政策层面而言,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诸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15〕28号)、《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京发〔2019〕1号)等政策,这意味着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官方愈发强调让多元人群体现出更多自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让多元人群重塑自己的身份表征;官方可以赋予基层更自主化的空间,同时也愿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构成了官方乐于与非官方力量更为密切合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博物馆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类实体项目,需要资本的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的介入构成此类项目的重要助力,甚至成为影响其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例如,北京老城白塔寺地区的改造便离不开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早期资本力量的撬动[18]。这类企业资本的介入,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带上了非营利和公益性的色彩;另一方面,关于这类项目,企业也需要考虑后续的经营问题,毕竟资本的回报性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法避而不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解释了一个广义的“文创”问题在此类博物馆化的项目当中为何会如此广泛地出现。最后,在地社区也并非截然缺位。在地社区本身的诉求和在运营过程中的活跃构成了这类项目得以实现其初衷的基石。虽然在国内对于此类项目常见的批评当中,存在在地社区缺乏自发组织形成社团的能力、项目启动初期缺乏在地社区参与等声音,但是若据此便将在地社区完全理解为缺位,这也是一种不尽完善的看法。在这类项目当中,通过下放话语权、多主体间的对话、志愿者培训等手段来尽量协调在地社区的生活模式与基本诉求、寻求在地社区的合作与介入也已是常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对西方博物馆学的审视,旨在强调如下两方面:其一,在处理博物馆自身与“人”的关系时,多元人群的问题是当下西方博物馆学研究的一类倾向;其二,博物馆学研究不应对“人”的讨论过于泛化处理。之后,本文再将视线投回国内。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多元人群的问题在我国博物馆语境当中并没有完全缺席,其在我国各类博物馆或博物馆的各个业务环节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声、解构和重塑,只不过从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角度而言又都面临着局限;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的实践也在进一步提示我们不必局限于在一套过于“铁板一块”的“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理解多元人群问题,在这套二元对立关系以外,“官方”更为主动地贴近、多元主体力量的交融与妥协往往共同决定了特定的博物馆的生成与去向。
借助上文的讨论,本文也想指出,我国博物馆在“多元”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值得被进一步观察。多元人群是否完全不具备更大程度地融入博物馆后台的能力和必要性,以及“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如何寻求更为有效的融合,都将成为影响我国博物馆在此问题上未来去向的重要因素,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就此类问题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