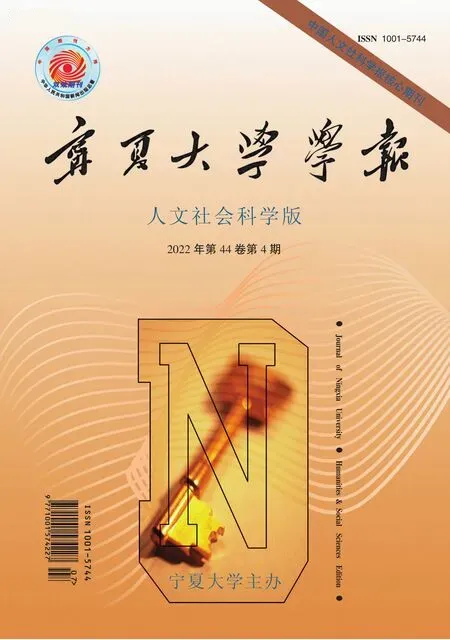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述论
2022-11-22龚艳
龚 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唐代隐逸文学名家辈出,名作迭出,然而其研究进程却与此榫枘不合。究其原因在于学界对隐逸的态度有所偏颇。章嵚认为隐士“其名隐而不隐,其事逸而不逸,于是历史上遂多一闲人之位置”[1];鲁迅则认为所谓的隐士不过是打着“隐士”的招牌来实现“噉饭之道”[2];朱光潜对隐士故作清高、消极避世的行为亦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往往以‘超然物表’‘遗世独立’相高尚”[3]。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系统研究隐士及隐逸文学的开山之作,但该书对隐士的人生观颇为不满,其云:“无论国家承平或国家危急的时候,隐士和隐士的人生观都要不得,假使每一个国民都是独善其身的许由巢父,国家安得不危急!?”[4]职是之故,唐代隐逸文学的相关研究在民国时期颇为寥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主线,隐逸文学的专门研究停滞不前。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思想领域的争鸣与解放,学界对隐逸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学者不再为隐逸是“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的偏见所拘囿,唐代隐逸文学研究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在此期间,学界在研究方法、研究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对此有作一全面系统整理的必要,以笔者所见,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沿着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 唐代隐逸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以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是近年学界新兴的研究方法,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以及霍松林《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等著作皆引进了研究唐代文学的新方法。新时期学者亦借鉴这一方法,将唐代隐逸文学置于广阔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元下,全面考察唐代隐逸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唐代隐逸文学与科举
唐代科举制对士人的心态、生活方式以及文学创作皆产生了重要影响,科举与隐逸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考察科举制对士人仕隐观念的影响,但该文着力探讨科举制对士人出仕观念的支配,而对科举制如何支配隐逸观念语焉不详[5]。李红霞《论科举对唐代隐逸风尚兴盛的影响》论述了科举对隐逸的影响。该文认为科举促进了隐逸之风的兴盛,这主要表现在士人隐居求学,以隐逸来应制举以及因考试失意而归隐山林等方面[6]。值得注意的是,制举是否促动隐逸,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查正贤《论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的关系》认为制举塑造了唐人的隐逸意识,而且这一隐逸意识及这一塑造活动本身,都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7]。另有学者表示反对,如鞠岩《制举并未促成唐代隐逸风尚》一文明确指出唐代制举从设科到考试都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其目的是选拔高层次的经世治国之才,因此塑造出的是士人积极参与政治的淑世情怀,而非隐逸意识[8]。
(二)唐代隐逸文学与儒释道思想
唐代隐逸以儒、释、道为思想基石,是多种思想碰撞融合后的产物。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对儒家和道家的隐逸思想进行了精要辨析,指出了儒、道两家对隐逸的不同影响,颇有研究深度[9]。屈小宁着重于儒家隐逸思想研究,其论文《儒家隐逸观与自然观自先秦至唐的演变》对儒家隐逸观展开了历时性的研究,认为唐儒的隐逸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10];其另一文《唐代儒隐的基本模式》则指出唐儒隐逸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不仕则隐,独善其身;二是终南捷径,以退为进;三是休沐田居,亦退亦隐[11]。
道教的势力在唐代扩展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唐代隐逸风尚的形成也具有促进作用。伍微微《盛世背后的落寞与精神追求——道教与盛唐山水隐逸诗论说》主要从盛唐诗人的创作思想、审美趣味等方面入手,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形成离不开道教文化的渗透[12]。李春辉、王继增《道教与初盛唐文人的隐逸之风》则探讨道教与隐逸的关系,认为初盛唐的隐逸在道教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新变,这表现在文人的隐逸方式、隐逸观念都与之前有所不同[13]。总的来说,目前学界认为道教对隐逸的刺激作用大致体现在:一是唐初帝王尊崇老庄而宽待隐士,促成了隐逸风尚的形成;二是老庄崇尚自然本真的生存方式与隐逸观念相契合,使得众多士人归趋隐逸。
唐代隐逸亦深受佛教的影响。胡遂《论佛教对于隐逸的超越意义——以晚唐诗人为例》从整体着眼,探讨佛教对隐逸的促进作用,他认为佛教促进了晚唐士人心态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诗风上的转变[14]。尚永亮《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其超越途径》则从个体诗人入手,深入分析佛教对白居易的影响,他认为白居易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使得他始终能关注个体生命,并在感性中寻求超越[15]。王树海、曲成艳《论韦应物诗歌的佛禅韵味》从文本出发,探讨禅味在韦应物诗歌中的体现,认为这种禅味是韦应物的诗歌能在大历时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16]。
(三)唐代隐逸文学与园林
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园林别业成为了士人生活的重要场所。遍稽唐代诗歌,可发现唐代士人将园林视为亦仕亦隐的理想境地。园林别业在士人群体的普及,是促进隐逸风尚在唐代兴盛的物质条件。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与文人隐逸的关系》结合地理学、史学、文化学等内容,全面考察了唐代园林别业与隐逸思想和隐者的相互作用关系[17]。李红霞《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则指出园林是沟通闹市与自然的中间地带,文人能在此弥补失意后的心理失衡,因此可以说唐代园林的发展是文人融合仕隐矛盾的物质保障[18]。左鹏《论唐代长安的园林别业与隐逸风习》阐述了长安的园林别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数量的消长情况,进而探讨园林别业与隐逸风气形成之关系[19]。相关研究还可参看西北大学房本文2010 年硕士论文《唐代园林经济与生活》以及西北大学马玉2010 年的硕士论文《唐代长安园林与唐诗》。《唐代园林经济与生活》一文从唐代文人园林的获得、经营和收支三方面入手,探讨园林经济状况与文人仕隐心态及生活方式的关系,所论颇有见地。《唐代长安园林与唐诗》一文对唐代长安园林的地域优势、文人生活、诗歌创作等方面做了综合论述,有利于我们把握唐代园林与隐逸的关系。
(四)唐代隐逸文学与绘画
从绘画的角度来解读隐逸文学,是新时期学者的创见。戴一菲《唐诗中的隐逸传统与高士图的流变》认为唐代隐逸与绘画这两者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隐逸群体的扩张导致高士图人物走向泛化,诗歌中的自然景观影响绘画背景的选择,文本的叙事结构转化为绘画的空间层次表达[20]。该文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绘画与写作的双向互动关系,颇有可取之处。
二 唐代隐逸文学的主题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主题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主题学研究也以其研究实绩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十个主题,出处主题位列其中[21]。陶东风《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也将隐逸作为中国文学的四大主题之一[22]。随着主题研究走入学界视野,唐代隐逸文学的主题研究也得以深入开展,以下拈取成果较为突出的吏隐主题、中隐主题加以论述。
(一)唐诗中的吏隐主题
“吏隐”是唐代隐逸文学的重要主题,学界为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对吏隐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举凡吏隐的动机、历史发展、实现方式等重要问题,皆有深刻论述[23]。李红霞《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吏隐在唐朝各时期的流变加以考索,认为“唐诗吏隐主题呈示出一条清晰的从‘兼吏隐’到‘以吏为隐’的流变轨迹”,并判断唐人的吏隐心态由此完成了从“身心相离”到“心迹合一”的转变[24]。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则对吏隐的内涵、郡斋诗的概念等问题阐幽发微,对中晚唐文人的隐逸心态及郡斋诗的创作主体“沧州吏”的解读尤为独到[25]。此三家虽对吏隐的研究各有创获,但对吏隐的内涵却莫衷一是。蒋寅将吏隐的主体界定为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诗人,李红霞秉持吏隐的主体为地方官的观点,葛晓音则认为吏隐的主体应涵盖地方官和京官。
(二)唐诗中的中隐主题
“中隐”是唐代隐逸的另一重要主题。据目前研究来看,学界对“中隐”的看法可分两种:其一是将“中隐”与“吏隐”等同视之,如汪国林《论白居易吏隐思想及其对宋代文人的影响——以苏轼为考察对象》[26];另一观点则认为“中隐”与“吏隐”有所分别,如杜学霞《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27]、邵明珍《论白居易的“知足”与“不足”——兼论其忠州起复后之仕隐心态》[28]等论文。以上论文各以不同角度切入中隐之研究:汪国林一文从接受学的角度考察中隐在宋代的传播机制,杜学霞一文纵向剖析白居易走上中隐之心路历程,邵明珍一文则对白居易“省分知足”的中隐思想中的“不足”方面加以抉发。另有华东师范大学鲍乐2011 年的硕士论文《从仕宦履历看白居易“中隐”递嬗及其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姜树景的硕士论文《白居易洛阳时期的“中隐”思想与诗歌创作研究》等学位论文对中隐主题展开了系统且较为全面的研究,可以参看。
三 唐代隐逸文学的文本研究
学界引进新方法和新理念来进行文学研究,虽对构建文学的理论系统以及全面审视文学现象有所助益,但也应警惕文学研究走入理论突出而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性被淡化的歧路。新时期学者对唐代隐逸文学的文本研究稍显薄弱,涉及面广而深度欠缺。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创作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唐诗中隐逸意象的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以下就此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隐逸与山水田园诗
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在唐代臻于极盛,因此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与唐代隐逸风尚的相互作用关系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学者为此作出不少努力。他们各从隐逸与山水田园诗派之关系、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山水田园诗中的隐逸传统等方面来完善这一课题。1993 年,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重点探讨了山水诗和田园诗合流的现象,指出合流的原因之一是盛唐文人实行的待仕之隐。章尚正《山水诗与隐士文化》[29]与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30]则探讨了山水诗的审美意蕴与隐逸文化之关系。章尚正一文从唐朝士人的隐逸心态入手,认为士人心性的隐士化促使唐朝山水诗形成“任真之趣与悠远之韵相谐”的主体风格;霍然一文则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时代美学观念的变化,剖析盛唐山水田园诗之清淡静幽的美学意境与唐代隐逸之关系。另有学者对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隐逸传统提出质疑,姜玉琴《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指明盛唐田园山水诗的兴盛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逻辑,认为盛唐的隐逸乃“姜太公钓鱼式的隐逸”[31],或可备一说。
(二)唐诗中的隐逸意象
随着对唐代隐逸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隐逸意象也被纳入学术视野,学界对此的探讨集中于“云”“垂钓”“渔樵”“严子陵”等意象。葛兆光《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认为“云”在魏晋为“飘泊无依的悲哀象征”,随着唐人的心境诗思及观物方式的改变,到唐诗中则成为“澹泊、清净生活与闲散、自由心境的象征”,这种象征往往与出世相联系[32]。王春庭《渔樵:隐逸文学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一文揭示“渔樵”一词在唐诗中具有隐逸的内涵,指出其在唐诗中“大多是隐逸者的形象,是倾注了诗人审美理想和主观感情色彩的文学形象”[33]。李红霞《论唐诗中的垂钓意象》认为“垂钓”很早就具有表达江湖隐逸的意味,在唐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表现为“归返自然的放旷闲适之趣”及“高蹈志趣的呈示”两个特点[34]。吕红光《严子陵隐逸意象在唐五代诗歌中的凝定历程》则探讨“严子陵”意象在唐前、盛唐、中唐、唐末的发展过程,认为其隐逸内涵最终在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手中渐趋凝定[35]。
四 唐代隐逸文学的创作主体研究
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的创作主体研究较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体现在对代表性隐逸诗人的多方位探讨以及对中、小隐逸诗人的发掘。王维、孟浩然向来为学界所关注,新时期之前的学者对二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探讨,而此时学界对二人的研究却更为深入与全面。另外,此前为学界所忽视的中、小隐逸诗人也在此时被纳入研究范围,使得唐代隐逸文学的主体更为壮观,内容也更为丰赡。
(一)对代表性隐逸诗人的多方位探讨
王维与孟浩然是唐代隐逸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学界对二人的研究着力甚勤。学界对王维隐逸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对王维隐逸范式的辨析,如陈铁民《谈王维的隐逸》对王维的淇上之隐、终南之隐与辋川之隐的隐逸范式悉加甄别[36]。杨径青《王维的终南隐居——与陈铁民先生商榷》则对陈文中将终南之隐认作辞官之隐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王维此时当为“半官半隐”[37];第二,对王维隐逸思想的分析,如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论证王维的“亦官亦隐”并非子虚乌有,并且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关系密切[38];第三,对王维的隐逸与其诗歌创作关系的探讨,如章尚正在《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一书中探讨王维山水诗的三重境界,认为王维山水诗的形成与其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39]。
学界有关孟浩然隐逸的研究可归为以下几类:首先,孟浩然隐居的原因引起学界极大关注。陈贻焮《谈孟浩然的“隐逸”》认为仕途不顺是孟浩然走向隐逸的关键原因[40],朱起予《孟浩然隐逸趣尚论》重点探讨地域性因素对孟浩然隐逸的促动作用[41],张安祖《解读孟浩然的隐居》则指出孟浩然“求真”“放性”的本性是其逸乐山林的主要原因[42]。其次,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也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如宁松夫《孟浩然隐逸思想定位论》指出“隐逸思想只是孟浩然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他思想的主流”[43]。再者,孟浩然的隐逸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也为学界所关注,如周凌云《浅淡孟浩然的隐逸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孟浩然的隐逸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诗“清幽、平淡而又不乏壮逸的艺术特色”[44]。
(二)对其他隐逸诗人的发掘
虽然王、孟的隐逸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但新时期学者亦将触角延伸至其他隐逸诗人。由此可见新时期学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以及对唐代隐逸文学之重视。
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王绩、韦应物、白居易亦是学界关注较多的对象。学界对王绩隐逸的原因、其隐逸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加以考察。自王绩被史官列入《隐逸传》以后,王绩是否该被当作隐士就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姜荣刚《驳王绩非隐士说》在细致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考察王绩的思想状况与当时的社会面貌,做出“两《唐书》将其列入《隐逸传》是合理的”判断[45]。张丽《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亦认为王绩是“初唐隐逸诗人的代表”,其归趋自然的生活态度为他的诗风增添了自然、本真的性情之美,也为初唐诗的发展融入了新的元素[46]。韦应物的仕隐心态以及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为学界讨论较多,如童强《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写实倾向》认为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描写的不是理想生活,而是真实的吏隐生活,因而具有很强的写实倾向[47]。邵明珍《韦应物仕隐心态平议——兼论其诗歌主导风格并非“高雅闲淡”》从韦应物的仕隐心态入手,指出韦应物在仕隐问题上并不超然,其诗风也不能以“高雅闲淡”来概括[48]。白居易的隐逸心态亦引起学界的注意,李昌舒《论白居易的独善心态及其审美意蕴》一文探讨白居易独善心态的特点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通过解读白居易诗歌中的“忘”“闲”“墉”“适”四个基本概念来分析其独善心态的审美趣味,并指出这种心态既成为日后文人奉行的生活法则,也对文艺发展中的士人化、雅化倾向具有深刻的影响[49]。
另外,其他隐逸诗人也在这一时期被发掘。李白、杜甫、朱桃椎、刘昚虚、李颀、刘长卿、钱起、贾岛、姚合、许浑、方干、吴融、罗隐、胡曾、唐求、冯涓等悉被纳入研究范围。方干、唐求等人隐逸行迹明显但声名较微,以往研究鲜有涉及。新时期学者洞微烛隐,开掘出这些为世人所忽略的研究对象。李白、杜甫等虽不以隐名世,其隐约透露出的归隐之志亦为新时期学者所发掘。然而有关这些诗人的研究予人以浅尝辄止之感,研究力度尚属薄弱。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与此前相比,呈现出明显的进步和突破:在学术方法上,新时期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文学,运用新视角、新理念发掘了唐代隐逸文化的多方面内容。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学界不再把文学现象看作孤立的个体,而越来越注重将文学现象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整体,着重考察文学内部与外界的联系。
在学术观念上,新时期学者坚守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由于民国学者对隐逸文学秉持的鄙薄态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隐逸与主流价值观念的相悖,隐逸文学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散见的几篇论文也大都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新时期学者不仅冲破了对隐逸的偏见,更是在研究中坚持客观的研究态度,广泛采摭史料,对唐代隐逸文学进行尽可能客观公正的分析,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
在学术视野上,新时期学者的视野更为开阔。纵观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的研究,既涵盖对隐逸诗人的微观研究,也包括对隐逸群体的宏观考察;既分析隐逸现象的横向联系,又梳理隐逸主题的纵向脉络;既展开隐逸文学的文本分析,又追索隐逸文学的文化背景。新时期学者对唐代隐逸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广,取得成果之丰厚,展示出学者们具有深厚扎实的学术积淀以及脚踏实地的学术品格。
尽管新时期的唐代隐逸文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学界的个案研究陷入对某些诗人的反复研究当中,这就造成对其他隐逸诗人抉发力度的缺位;其次,学界对唐代隐逸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角度虽新,但也存在重社会外围要素的探讨而轻文学本质的问题;再者,学界对唐代隐逸文学相关概念的界定交错杂糅,缺乏指导性的论述。另外,唐代隐逸文学虽是断代研究,却又不可为时代所拘囿,若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唐代隐逸文学的发展及影响,或有助于认清唐代隐逸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以上是笔者对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所做的思考与总结。相信在思想意识更为进步、学术观念日益开放的今天,随着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唐代隐逸文学研究的队伍中,唐代隐逸文学研究必将趋向全面与深刻,并朝着更为深远的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