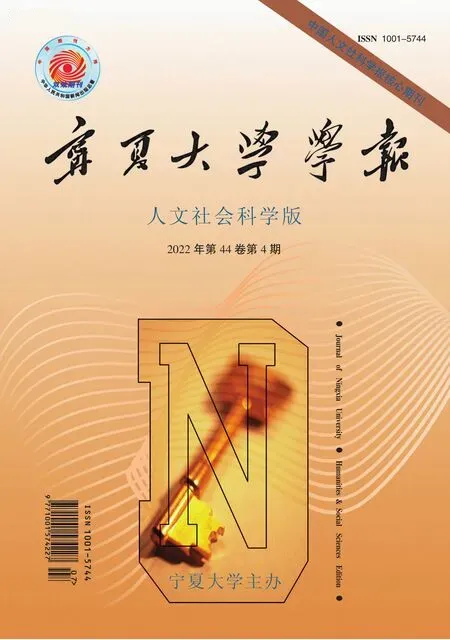论从仪式中分娩的《西游记》叙事
2022-11-22马硕
马 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5)
《西游记》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问世以来,有以陈元之、李贽等为代表的“原旨”说,悟一子、悟元子等为主的“归一”论,叶昼、冥飞、胡适等人的“游戏”说,以及政治说、市井说等论述,可以说,每一种观点都各具依据,但也不免挂一漏万。以《西游记》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已长达四百余年,直到当下仍然方兴未艾。综观已有的成果,从文本的文体研究、话语建构、文化属性,到翻译、影视传播、跨文化比较,不可不谓浩瀚可观,但可以从中看到,随着“西游记学说”的成熟与文本周边的延伸,针对《西游记》本身的叙事分析已经日渐减少,一方面,这是由于在传统叙事理论的视域下,杨义、浦安迪、傅修延等叙事学大家的研究已极为详尽;另一方面,对叙事的研究难以呈现文本的意图,容易落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由于“作者要运用语言创造出形象,再由这些形象表达出其意图,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其意图也难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1],于是,当下的研究更多围绕着文本外部,或是对由《西游记》文本而衍生的电影、电视剧或传播等领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部作品的叙事研究已经穷尽?事实看来并非如此,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陈晨从空间书写的形态展现“宇宙、历时性与变形式”[2]的叙事线索,崔小敬凭借“食色”的叙事看文本的反讽策略[3],还有游走叙事、修炼叙事、宗教叙事等,可见,以非传统叙事学的角度解读《西游记》,能获取与以往研究不同的风景。其中,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仪式叙事,为理解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部作品叙事的形成原因与过程,并从仪式象征的角度展示这部神魔小说的现实意义。
一 作为叙事引擎的仪式
仪式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行为方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对仪式的记载在《诗经》中已见端倪,甚至可以从“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大雅·生民》)中考据祭祀仪式的发端,自此,仪式成为各类文学体裁,特别是小说描写、表现的对象。然而,作为一种小说叙事方法的研究,仪式却始终存在极大的空白,特别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仪式被当作叙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属于故事的情节而非表现目的。尽管已有方克强教授认为《西游记》为成年礼仪式提供了一种原型叙事,但如果将仪式叙事仅仅看作对仪式行为、仪式场景的描写和展示,就会只见皮毛,不见筋骨,更有甚者会对仪式叙事产生误解,认为仪式叙事就是针对仪式的行为叙述。因此,明晰仪式叙事的含义是凭借仪式叙事视角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前提,特别在《西游记》的叙事研究中,更应该注意到,仪式才是叙事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这个结论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如果说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游是由于当时佛教经典无法解决鉴真法师的困惑,不得不西去印度学习更为根本的智慧,但《西游记》作为一部虚构的神魔小说并无这样的“西游”需要,从《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脱胎的艺术再现只是这部作品得以形成的契机,却非叙事结构本身的成因,那么,唐僧师徒四人为何要西去取经,就成了《西游记》在叙事中首先要解决的逻辑问题。
从《西游记》开篇来看,东胜神洲的一块山顶仙石受天地日月精华的滋养,久而通灵,一日迸裂,见风而化出石猴孙悟空。这个人物的设定具人情、备猴性,内在的顽劣品性让其成为打破叙事旧平衡、建立新秩序的最优选择,为了让孙悟空将本领发挥到最大限度,作者更安排其在菩提祖师处学仙论道。菩提作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亦佛亦道,让孙悟空日后有了皈依佛门的基础。叙事到此时仍处于背景交代的过程当中,要引出一个名正言顺的西去取经的理由,就必须打破这种平衡。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个理由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功能:(1)使被打破的平衡能到达一个新的平衡;(2)引出并聚合叙事中的主要人物;(3)足够充分且必要,使无比艰难的西去取经成为无可避免的唯一选项。也就是说,为了使这个理由成立,它必须与大部分人物的利益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正常秩序的运转,倘非如此,西去取经的叙事便无法令人信服。基于以上条件,这个理由首先应该是一项涉及大部分叙事人物的活动。其次,应该具备历史传统性。再次,则应该具有明确的边界线,最后体现出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些前提清晰地显示,这几乎是为仪式行为量身定做的叙事理由,特别是庆典仪式。柯林斯指出,“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4]。其中,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认为,“庆典具有满足个人需求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5]。仪式意义的提出使仪式叙事的概念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为文本的叙事分析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本文认为,仪式叙事是指作者利用仪式参与者、仪式器物、仪式行为、仪式环境等元素,对所要描写的仪式场景进行聚焦,并以一场或几场仪式为中心进行叙事发散,即从仪式中获取仪式发生的原因、经过与结果。然后将不同的仪式进行连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小说叙事。
在《西游记》的叙事中,蟠桃会的庆典仪式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这场仪式直接引出了保护三藏法师西去取经的三个徒弟,并以预叙的方式间接引出取经的关键人物唐僧。第五回写道,蟠桃宴会自有旧规,是王母大开宝阁,宴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这个是五方五老。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齐赴蟠桃嘉会”[6]。这些日后在西游过程中都要露面的神仙们,就先从这场蟠桃会上亮了相,仪式叙事在这里起到了交代人物角色的作用。再从蟠桃会的仪式器物来看,太上老君的仙丹本欲在宴会上进献玉帝,却被悟空偷吃,才有八卦炉里烧大圣,炼出火眼金睛,日后能识变化后的白骨精,又有八百里火焰山的渊源;蟠桃会的仙酒让八戒神智昏昧后调戏嫦娥,受到严厉的惩戒后,成为皈依西去的线索;至于蟠桃会上的玻璃盏、西海龙宫的殿上明珠,又引出了也注定要西去取经赎罪的沙和尚与白龙马。
蟠桃会的变故表明,这次仪式的关键在于孙悟空的参与者身份没有得到认同。依据七仙女的说法,不久前才于蟠桃园起了齐天大圣府的府主也应属被邀之列,但却不曾听说孙大圣受邀,可见,这场几乎囊括了天界所有人物的仪式,刻意回避了孙悟空。但从叙事的考虑来看,孙悟空也必须被回避,原因在于:(1)揭示封建统治者“招安”的虚伪面具。悟空觉察到“弼马温”的官职是对其不谙人事的羞辱之后,弃官而走并自封“齐天大圣”,天庭立即派天兵天将捉拿,不料屡屡受挫,又见悟空只因“官瘾”作祟,便加封空衔。在天庭看来,悟空尽管受封,却非正途,因此在涉及边界划分的仪式场合中,悟空“编外”的身份就显露无遗。(2)制造情绪落差,如果悟空已经受邀却仍破坏蟠桃会,人物就失去了基本道德,神通广大的本领只会遭到厌恶,所有的行为就成了胡搅蛮缠而非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只有他应该受邀却不受邀,才有了被同情的情感基础,大闹天宫即使不合法却也并非毫无缘由,这样一来,孙悟空虽受镇压但终能得救就有了可能。(3)激化矛盾,为扩大冲突作准备。孙悟空是一个天产的石猴,猴类的本性在这个人物身上表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群居性。这种性格特点注定了让悟空无法接受自己被群体排除在外,因此,蟠桃会没有邀请其他人或许尚可,但没有邀请掌管蟠桃园的孙悟空就必然成为不可容忍的挑衅。
由此,作为传统庆典仪式的蟠桃会和被回避的孙悟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可以认为,这场仪式越隆重,天庭对其破坏性的行为就越愤恨,蟠桃、仙丹等仪式器物的失毁必然通过悟空的受罚回归平衡。于是,二郎真君将其捉拿归案后,天庭对其碎剁、火烧、雷劈,甚至用作炼丹,以无比残暴的刑罚维护仪式的尊严。对悟空个人来说,这场因蟠桃会而起的灾难也引发了他更为强烈的反抗,并因此被压于五行山下。孙悟空之后,猪八戒与沙和尚同样因蟠桃会而受罚,在第八回中,观音菩萨奉如来法旨去南赡部洲寻找取经人时经过流沙河,河里怪物自称“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7]菩萨怜悯他受苦,度化他皈依佛门,取名沙悟净,等待西去取经人。又有九十四回八戒在天竺国王面前自白“只因蟠桃酒醉,戏弄嫦娥,谪官衔,遭贬临凡”[8],同样要通过护送西去取经人得到救赎。可见,蟠桃会上仪式器物与人物命运融为一体,构成叙事的完整结构。彭兆荣教授指出:“叙事的过程并非一本流水账,没有衔接,没有阈限,恰恰相反,叙事的过程刻意于事件过程的波澜起伏,仪式的力量在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文本构成了叙事的一个坐标,这个坐标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叙事的‘文本’和‘仪式’构成的纵横相交的形态。”[9]在《西游记》中,蟠桃会、安天大会等仪式的举行不仅关系着人物的出场,更关系着保护唐僧西去取经的叙事逻辑,这时,还需要一个能说明唐僧本人为何西去取经的理由,《西游记》便可以彻底解决叙事的成因问题,而这个理由又一次为仪式承担。
在天界的庆典仪式外,小说通过人世间的死亡、丧葬,以及与之相关的超度仪式搭建起一条人神沟通的渠道。魏徵在梦中斩了泾河龙王后,引出唐王李世民梦入幽冥地府亲见了地狱惨状,于是“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10],以举办盛大的宗教仪式为缘由又引出了关键的叙事人物玄奘法师。宗教仪式不同于一般仪式的习俗化与象征化,它有着最为强大的效力,这不仅是因为信仰中饱含着畏惧的情感,更因为信仰与宗教精神能在仪式行为中互相强化。由此,在法会仪式上既受菩萨指点,又受唐王勉励并建立亲属关系的玄奘法师,西去求经的行为就成为这场宗教仪式的延续,正如金泽所说,宗教仪式的强化作用“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它的目的不是克服任何具体的生命危机,而是维护群体之总的价值”[11],这与玄奘“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12]的叙事达到了绝对吻合。
二 “过渡”仪式的叙事策略
从叙事策略来看,在《西游记》所描绘的九九八十一难中,除主要的叙事人物不变之外,各种劫难因果各异,事事不同。这些叙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读者的想象力,因为男性妖怪总要以唐僧这个“修行十世的好人”之肉为食,然后长生不老,女性妖怪则是盼望与其结亲。如何才能让“吃唐僧肉”与“和唐僧结亲”这两大类叙事避免情节的重复,并展现出紧张活泼、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的艺术魅力,就成了考验文本创作最严肃且最重要的问题,对此,吴承恩智慧地运用仪式叙事解决了问题。因为,仪式的多样性赋予了叙事丰富的表现形式,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或来自天界,或在荒山野岭中自成精怪,不同的来历意味着对不同仪式元素的需要。首先,是仪式场景的变换,水里的妖怪与山上的妖怪在仪式选择上自然各有差异,即使同为水里的妖怪,神仙的亲戚和水族成的精所看重的仪式也不尽相同。其次,是威力无穷但相生相克的法器(仪式器物)的差别,第五十二回中,太上老君的座骑青牛怪使一“白森森的圈子”,连罗汉使用金丹砂也无法将之降伏,老君说,“我那‘金刚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之宝。凭你甚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儿’,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13],又有第七十一回,观音菩萨的座骑金毛犼使一金铃,能放火、放风并能放沙,据菩萨说,“若不是你偷了这铃,莫说一个悟空,就是十个,也不敢近身”[14],可见仪式器物的神圣性也为叙事趣味提供了十足的动力。
取经的路途中,妖怪与唐僧师徒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若要让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困境之中,就需要一些叙事导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仪式器物/符号成了叙事的中介,它负责联系双方,要凸显一方排除万难西去求经,另一方坚决阻止取经人西去之间的矛盾,又要让二者不自觉地受其控制。这些仪式器物可以是吃一口就能长生不老的唐僧肉,可以是孙悟空等人的兵器,也可以是锦襕袈裟、九环锡杖,这些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物质部分,代表着宗教的神圣力量,这就营造出叙事中“顺延”的逻辑思维——即使是妖怪,只要与神圣的部分获得联系,他们就能化为神圣的一部分。第三十二回莲花洞二妖的对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目的。当唐僧师徒经过平顶山时,金角大王命银角大王去巡山抓唐僧师徒来吃,银角大王对这突如其来的差遣表示诧异,说“我们要吃人,哪里不捞几个。这和尚到得那里,让他去吧”,可见他这时虽为妖怪,却善心未泯,认为唐僧跋山涉水走到平顶山十分不易,然而,金角大王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你不晓得。我当年出天界,尝闻得人言: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点元阳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寿长生哩。”[15]但唐僧在没有脱凡成圣之前,肉身即为生命,若为妖怪所食则无法继续西去求经,而真经又只能为唐僧所取,因此,保护唐僧就意味着确保仪式过程得以顺利进行。这样看来,在唐僧一方,每一次磨难都是唐僧遭受捆绑、恫吓,悟空等人经历打斗、受伤的苦行仪式,这个过程中,仪式参与者不断强化信仰,并从中获取力量。涂尔干认为,“所有这些仪轨通常都被表现为一种考验,用来证明这些新人所具有的价值,说明他们是否值得被吸收到宗教社会中来。”[16]也就是说,磨难越大,通过考验之后的仪式参与者的神圣品质就越高。从妖怪的一方来说,吃唐僧肉不仅是欢娱的仪式,还是一种神圣仪式,这个阶段十分必要,不如此则无以实现一种状态的转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妖怪每次抓到唐僧后不立刻吃完了事,而要先洗净搁置。
从仪式的功能来看,它的强化作用不断凝聚并坚定着唐僧师徒对求取真经的渴望,可以说,仪式显现出的阻力越大,仪式参与者在通过仪式考验之后的信仰就越坚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一百回才是《西游记》的叙事高潮,唐僧师徒历尽千难万险后,终于得到佛在灵山授职,从如来佛祖口中听讲,“圣僧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猪悟能,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沙悟净,诚敬迦持,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加升大职正果,为金身罗汉。白马,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马”[17]。这样的结局令人格外期待且荡气回肠,更凭借读者的视野见证了唐僧师徒“取经朝圣”仪式的圆满成功,与另三部古典名著小说相比,是唯一不留任何遗憾的叙事结局。
再回到仪式叙事的角度,就可以看出《西游记》整个文本展现的是一个以“赎罪”为主题的过渡仪式,在大的仪式框架中又包含了若干小仪式,如石猴于花果山称王(第一回)的登基仪式;唐王设朝(第九回)的强化仪式;玄奘演妙经法会(第十二回)、禳星三清观(第四十四回)、陈家庄祭赛(第四十七回)等宗教仪式;庆赏佛衣会(第十七回)、人参果会(第二十六回)、西梁国喜筵(第五十四回)等庆典仪式;五庄观受刑(第二十五回)的惩罚仪式;玄奘超度伯钦父(第十三回)、寇员外命丧强盗(第九十七回)的丧葬仪式;斗法车迟国(第四十六回)、三借芭蕉扇(第六十一回)的竞技仪式;朱紫国医病(第六十八回)的治疗仪式,以及金平府元宵节日(第九十一回)的定期仪式等。由此可见,从唐僧正式离开东土大唐,前往西天逢虎遇难开始,师徒四人的叙事身份与其说是取经者,不如说是各种仪式的参与者。小仪式的叙事展现出大仪式的过程,大仪式的叙事又是小仪式全面展现的结果。
在整个过渡仪式中,为了让叙事的力量更为强烈,仪式三阶段中的每一部分都被作者推向了极致。身份的分隔是仪式叙事的重要发端,用范热内普的话说,“废黜、开除、革出教会等礼仪,实际上是分隔礼仪与定罪礼仪”[18]。五个主要的叙事人物都不得不经受取经的磨难而消除原罪,蟠桃会中被破坏的仪式秩序让孙悟空、猪八戒与沙僧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但他饥时,与他铁丸子吃;渴时,与他融化的铜汁饮”[19],天蓬元帅猪八戒错投猪胎,吃人度日,卷帘大将沙僧“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胸胁百余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又饥寒难忍”[20]。在此之外,被告忤逆的小白龙在惩罚仪式中“被玉帝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21]。福柯指出,“酷刑应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它是惩罚仪式上的一个因素,标明了受刑者,并通过在其身体上留下疤痕,或是通过酷刑的场面,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即使其功能是‘清除’罪障,酷刑也不会就此罢休。它在犯人的身体周围,更准确地说,是在犯人的身体上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记。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忘记示众,戴枷受辱,酷刑和历历在目的痛苦。”[22]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净化,更在于分隔,确立受刑者与非受刑者身份的不同。孙悟空不再是花果山上的猴大王,猪八戒、沙僧更非前世的天蓬元帅与卷帘大将,西海龙王敖闰之子从龙化马,玄奘也因家庭的变故成长于寺院,缺护少荫,更因立誓求取真经而成为一个行脚僧人。
失去原有身份的唐僧一行,因得到菩萨“功成得正果”的允诺,陷入了一种阈限的状态,既不从属于过往的身份,也未被另一个群体接纳,直到经历了西去取经的中间过程,才能跨入新层级获取新身份的阶段。这一阶段可视为过渡仪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延长唐僧师徒取经这一艰难过程的同时,也释放了他们在每一场仪式中凝聚的情感,如五庄观的结拜仪式;伏龙寺获宝擒怪后的送别仪式;朱紫国病愈后的酬谢仪式;天竺国除妖救公主后的佳宴仪式;寇员外的迎送仪式等。不断重复的仪式不但强化了仪式参与者对仪式过程的认可,更加强了身份的转化,从文本叙事的前半部分来看,唐僧师徒还总陷入山岭妖怪之手,除妖降怪在于自保与打通西去之路,到了文本的后半部,除妖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种对当地人民的救赎行为。
另外,过渡仪式还承担着仪式叙事的程式作用,使每一段对磨难经历的叙事都可视为已经完成的仪式程式,让唐僧师徒增添得取真经的资本。在这之中,仪式人物、仪式器物,以及仪式环境等元素在分隔、阈限与聚合中不断变换,构成如同“万花筒”一般的叙事模式,使整个取经过程中的每一次劫难都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样貌。应该说,这种仪式程式越多,叙事越为复杂,叙事结构也越受考验,在第九十九回中可见,诸神皆称赞唐僧四众“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不可言”[23],并从“金蝉遭贬第一难”列到“凌云渡脱胎八十难”,然而菩萨开示佛门九九归真,唐僧师徒仍差一难,这一难以插叙的手法,灵巧地编入过渡仪式的程式当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唐僧已经抛弃了原有的肉身,转凡成圣,如果再安排男妖精吃唐僧肉或女妖精劫走成婚的叙事显然不合情理,于是,最后一次的磨难仍然需要以仪式器具为线索,让“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24]的经卷受损,以另一种形式的“戕害”终结整个过渡仪式。这样看来,过渡仪式中分隔—过渡—聚合的结构让“过渡”在仪式叙事中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过渡越艰难,聚合的价值就越高。
三 仪式在叙事中的象征
象征性是仪式特性在群体性、重复性之外的另一重要内容,也是顺延仪式与交感仪式内在逻辑层面的表达。在仪式行为中,象征不仅包含着积极的一面,也包含了消极的一面,运用在小说叙事当中就是意义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呈现。《西游记》叙事的象征性在历代研究者的论述中已足够清晰明了,而无须赘言,但是,从儒家思想中解读的象征与释道视域下的象征显然不尽相同。荣格令人信服地指出:“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建立起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他自己并不显示出任何象征意义,但对另一个人却可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此外,无疑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的象征性质并不仅仅取决于观察者的态度,而是以它们对观察者具有的象征效果把自己自发地显示出来。这些作品的构成方式决定了人们如果不承认他们有某种象征意义,则它们不具有任何意义”[25]。荣格的观点对胡适指责《西游记》无非是一部游戏小说的缘由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与仪式相关的叙事象征是凭借人类学视角对文本的全新解读,在这一领域中,涉及小说仪式叙事的器物与行为具有比其本身更为丰富的含义,并在仪式叙事中承担了重要的象征寓意。
在《西游记》的仪式叙事中,物是神圣性的重要象征,从文本的叙事结构来看,它起到了推动叙事发展的作用。在唐僧师徒西去取经之前,人物的命运和物紧密相关,对于这些仪式的参与者来说,物象征了需求,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需求’的概念反映了一个令人心安理得的目的世界”[26]。这在孙悟空身上尤为明显,他当上猴王后,发觉人终有年老色衰而不能久享筵席,因贪恋筵席(物)之乐起了学长生不老的念头,学成之后,又发现缺少兵器,需要兵器成为孙悟空强抢东海龙王定海神针的叙事缘由,兵器之外,更要披挂,造成龙王状告玉帝“臣敖广舒身下拜,献神针之铁棒,凤翅之金冠,与那锁子甲、步云履,以礼送出。他仍弄武艺,显神通”[27],才引发了招安“弼马温”和封号“齐天大圣”的一系列事件。到了天界后,孙悟空盗取宴会仪式中的蟠桃、仙酒与仙丹,终于被如来佛祖压于五行山下,成为保护唐僧西去求经的叙事缘由。
这些物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让仪式行为有了物质的依托,没有筵席的欢聚仪式正如打空的拳头,情感在释放的终端失去了承受者,不但不能起到欢愉的效果,反而会造成伤害。如孙悟空从蟠桃会上回花果山举行筵席,这场本该是庆典仪式的叙事被捉拿他的天兵天将打乱,从天界带来的蟠桃、仙酒转瞬之间不再具有仪式器物的效力,而成为孙悟空偷窃的罪证,使群猴的仪式成为一场噩运的开端。其次,物象征着神圣的精神,可分为具体的三种物类进行理解。
第一种是承担着叙事想象的兵器,这些兵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人的战斗力,无论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还是妖怪用以称王称霸的宝物,都伴随着一个原始神话对来历作出介绍,阐明它的效力之余,更标榜了其独一无二的身份与价值。从孙悟空的金箍棒中可见,他个人的高强能力无非是腾云驾雾、七十二变,真正成就其神通广大名号的还是那根“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挨挨儿皮破,擦擦儿筋伤!”[28]的金箍棒,在取经路程中,金箍棒一次被太上老君的青牛怪攫走,一次为玉华国附近的狮子精盗取,孙悟空立即丧失了大半武力,若谈斩杀妖魔还是得先取回兵器。与金箍棒类似,妖怪兵器法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了其战斗力的强弱,即使能使三昧真火的红孩儿,也需火车子助力,更不用说不带雨具就无法降雨的龙王,没有兵器的妖王与小妖并无本质差别。可见,这一类与力量直接联系的神圣器物,因为不承担伦理道德的叙事责任,就可以充分发挥叙事想象,日常装水的葫芦能装人、装天且不分善恶;避暑的芭蕉扇能灭八百里火焰,不论好歹就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方停,几乎可视作现代飞行技术的原始设想。
第二种是构建仪式的物,如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桃、镇元子五庄观里的人参果,以及唐僧身上的肉,这些物因为极度稀缺和珍贵,使其与自身的效力互为因果,这也决定了物的接受者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因而不可能在日常的情况下得以享用。这一类物的神圣性主要在于时间的威力,据桃园土地说,蟠桃园的桃子最少要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最久的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日月齐寿同庚;与之类似的还有人参果,花园的土地说,“这宝贝,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头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有缘的,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29]除此之外的唐僧肉也是因其“十世修行”才具有食之能长生不老的效力。显然,对于生不过百的凡人来说,这种不可想象的时间长度足以令人心怀畏惧,仪式叙事以对时间的无限拉伸暗示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过程,让崇高和神圣自然而然地生长于其中。时间之外,这一类的物还容纳了不同的立场,唐僧肉虽然有长生不老之功,食之却违背了道德伦理,因此只为妖怪所爱,但桃子与果子却不然,它们属于可以分享的仪式器物,使物与仪式相等同,能够在分享的过程中强化与仪式参与者之间的联系。
第三种物属于叙事的物质基础,在《西游记》的文本中即为玄奘法师立誓求取的“三藏经”。它既是叙事主体的起点又是终点,象征着唐僧师徒取经的合理性与道德性,因为这部经可以劝人为善,进一步说即是“《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30],意味着南赡部洲的民众若希求摆脱是非恶海,就必须听闻这“三藏经”。然而,沉沦与得渡之间横亘着唐僧师徒所发的善心善念,也有他们将会遇到的所有艰险。在第二十二回中,猪八戒抱怨路途遥远,取经不易,孙悟空意味深长地教导,“只是师父要穷历异邦,不能够超脱苦海,所以寸步难行也。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就是有能先去见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经善与你我:正叫作‘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31]。悟空之言点明了经卷背后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唐僧师徒救度众生的善心表现,更是对其献祭行为的奖赏,尤为重要的是,“三藏经”自始至终都是利他的,无论唐僧、孙悟空或是菩萨,个体在叙事的伦理道德中微不足道,只有广大需要救度的民众利益才最为重要,这样一来,“三藏经”就成了最为神圣的物,也理所当然地处于仪式叙事的最高点。
在物之外,事件行为与关系中的象征性更为重要,表现在“对故事进行的任何研究都要通过事件,因为它是故事中唯一可以直接把握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是程度不同地隐藏在它后面”[32]。行为和关系是故事可以被观测的表面叙事,它的象征性凭借行为主体的动作和反应,释放出一种潜意识观念,并直接作用于仪式叙事,表达出行为主体对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意义的态度。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仪式人物通过仪式场构建密切相关的亲属关系,让彼此的身份得到黏合,使读者既能获得亲近感,也能获得相当的趣味。主仆、兄弟、师徒是文本中的三种严肃关系,这一类关系始终存在于整个叙事过程。更进一步来说,这些关系并非是唯一的,每一位主要的仪式人物在一个群体中是师父,在另一个群体中又是徒弟,并还分别承担着主人与仆人的不同身份。即使如天产的石猴孙悟空,只要跨入叙事的社会空间,也必须要先建立亲属联系的脉络。在第一回中,孙悟空在群猴的怂恿下找到了水帘洞福地,在群猴的礼拜仪式中称王,建立了第一种具有从属性质的主仆关系,很快又在社交仪式、拜师求艺的仪式中获取了第二种、第三种的兄弟、师徒关系,并因唐僧和猪八戒、沙和尚去西方取经的共同目标又一次在仪式中重新确立师徒、师兄弟的亲属关系。无独有偶,被打入凡尘的金蝉子原本就是西方如来佛祖的二弟子,与佛有着天然的联系,观音菩萨奉佛旨于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人”的行为,本来就暗含了重建关系的象征。为此,菩萨“见得法师坛主,乃是江流儿和尚,正是极乐中降来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长老”,才“十分欢喜,就将佛赐的宝贝,捧上长街,与木叉货卖”[33],于法会仪式中正式确立“天授使命”的求经行为目标。可见,共同利益是促成关系建立行为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行为象征了利益共享的可能,是权利的体现;另一方面即是对有可能出现失败情况的负责,是责任的体现,总体看来就是参与者在特定行为中结成的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即便存在只有利益而不承担责任的仪式行为,也需要亲属关系作支撑,如第十二回,唐王李世民感动于玄奘法师为保其江山,甘愿冒险西去求经时,决定举行互为兄弟的结拜仪式;第二十六回,孙悟空打倒人参果树后,镇元子为活树而甘愿与其结为兄弟的契约仪式。可见,这种行为实际彰显了人对群体环境的依赖心理,是儒家“三纲五常”思维在古典小说中的忠实反映,也是人类心理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原始积淀。尽管《西游记》反映的是虚幻的神魔世界,但从神仙的喜怒哀乐和欲求中,可以看出人类世界的踪影,因此,这种行为的象征性就有了浓厚的文化意蕴。
严肃的关系之外,文本中还有一类非严肃的亲属关系,是言语行为对身体行为的补充,主要表现于孙悟空和妖怪打斗的开场白,不绝于文的“外公”“孙子”“爷爷”“我的儿”等话语,以长辈的身份亮相,却并无血缘关系,这是对规则秩序的明确指向。第七十一回中,孙悟空自称朱紫国请来的外公救娘娘回宫,笑称“想我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九天神将见了我,无一个‘老’字不敢称呼;你叫我声‘外公’,哪里亏了你!”[34]在吴承恩先生的眼中,长辈象征着绝对力量,晚辈立于前必须恭敬服从,显然,孙悟空并无要和妖怪认亲的打算,但仍然以亲属关系的名称称之,除了暗示妖怪行为的不合秩序外,更是对自己拥有合法制裁权的声明。
四 结语
恩格斯曾赞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让其学到了比在职业学者那里更多的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知识,一定程度上,这个评论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将小说的真实性与知识性视为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相较于这种研究倾向,卡尔维诺的观点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文学能够教会我们的并不是实际的方法和需要达到的结果,而仅仅是对待事物的态度”[35]。小说虚构的叙事情节决定了它的故事不会是社会生活的原样复制,特别是《西游记》这类远离现实的神魔小说,读者无须从作品中学习坐禅问道,呼风唤雨——也绝无学到的可能。然而,《西游记》为研究者提供了多面的视角,甚至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视角,没有它不能呈现的样貌。仪式叙事作为非经典叙事阵营中的新锐批评模式,从文本中获取了大量仪式的叙事表现、叙事策略以及叙事象征等无可替代的叙事技巧。事实上,《西游记》中程式化的情节与故事的圆满本身就透露出一种仪式的倾向,在这之外,这部作品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在仪式视域下的文学价值:仪式是物与行为在叙事过程中的载体,它呈现的道德内涵需要读者自己作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