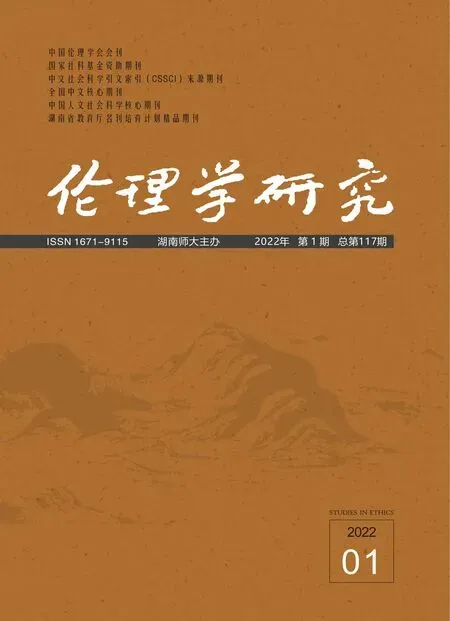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2022-11-22李育书
李育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通常把康德伦理学说看作道义论的典型代表,却很少探讨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问题。20 世纪下半叶,罗尔斯明确站在康德立场上批判功利主义,构建现代正义理论,康德政治道义论的意义变得日益突出。其实,罗尔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正说明了当代政治哲学需要道德的立场,政治离不开普遍的“应该”。当前,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到康德”来为现代政治提供道义论说明,而且,相比于罗尔斯,康德的道义论立场还是一个义务色彩更强、更具必然性的立场,也正因此,对康德政治学说之道义立场的回溯得到了很多当代康德研究者的支持。基于此,本文将首先说明这种回到康德之道义性立场的理论合法性,系统地研究康德哲学所具有的道义性内容,进而说明这些道义性内容的当代意义所在。
一、康德政治道义论的理论界定
道义论(deontology)本意强调的是行为的“应该”和“义务”。康德伦理学是道义论的伦理学,学界对此并无争议,甚至一些康德的批评者都指出康德的义务既是至高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具有“实践必然性”[1](176)。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指出的,人们很少讨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康德主要是在道德问题上强调义务,他专门讨论政治义务的内容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康德明确区分了道德和法权,似乎讨论政治就不必诉诸道德了。实际上,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包含道德与政治的,其义务自然包含了政治义务。对于后者,也正如康德多次指出的,政治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虽然更多被看作“纯技术问题”[2](136)而不需要过多的道德原则,但康德在指出这一点之后马上强调“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2](139),政治离不开道德,它具有道德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康德哲学的道义论特征不能仅限定于伦理学,而应包含他的政治学说。康德的政治学说也要求政治必须遵循义务并以义务为原则,政治应服从权利而不应追求外在的后果,政治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些要求根本上都属于具有道义论特征的“应该”,它们指引并规范现实政治。在康德哲学中,政治的义务源自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虽然康德更多在道德领域讨论绝对命令,但作为义务来源的绝对命令适用于政治领域,因为“定言命令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3](428)。政治与道德共同服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而且政治义务的具体内容也与绝对命令的不同公式正相呼应。
当前的很多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认为康德的法权义务来自绝对命令。当代康德研究者费里克舒(Katrin Flikschuh)区分了康德法权学说研究的契约论和义务论两种路径[4](186-220),从名称上看,似乎义务论路径更主张康德的道义论特征。而实际上,无论契约论路径还是义务论路径,他们的研究都可以支持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政治道义论的根本要求在于政治要以义务为原则,它强调政治的“应该”。而被费里克舒区分为义务论路径研究代表的墨菲(Jeffrie Murphy)和凯尔斯汀(Wolf⁃gang Kersting)都主张政治与道德出自实践哲学的绝对命令。凯尔斯汀认为,康德的“实践法则是一个具有先天综合之地位的实践命题”[4](162),如果绝对命令失败,康德的法权体系就不牢靠。而被费里克舒区分为契约论路径的研究者如路德维希(Bernd Ludwig)和马尔霍兰(Leslie Arthur Mulholland)同样主张法权学说是实践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他们的差别最多在于较多或较少强调法权的经验内容。马尔霍兰同样指出,“如果不诉诸伦理义务,康德就无法建构法权体系”[5](38)。其实,费里克舒提及的思想家、费里克舒本人以及罗尔斯,他们共同认可的是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至高地位。因此,回到前文的观点,所谓政治道义论强调的是政治要以义务为依据,而正是绝对命令规定了政治的基本义务,绝对命令在法权领域的基本规定是权利与他人自由的共存,这是法权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出自绝对命令的演绎,它具有普遍必然性。很多研究者甚至因此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有效性体现为,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根本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理性的必然要求,“源于该契约的规范显然是绝对命令在政治伦理学中的对应物”[4](172)。康德的道义论色彩要强于罗尔斯的道义论的原因也在于此,罗尔斯的契约更多是理性计算后的最合理选择,它并不具备最终达成契约的必然性,而康德的义务是具有必然性的。当然,回到政治的义务来源这个道义论的直接证明问题上,康德的政治学说是必然要接受绝对命令的直接规定的,绝对命令是政治义务的来源,这构成了康德政治道义论特征之理论合法性的根本说明。
在此基础上,康德政治道义论的具体内容来自绝对命令的演绎。按照康德自己的划分,这条绝对命令包含了如下公式——自然法则公式、目的公式和自律公式(自律公式包含了目的王国和尊严)。这个条公式分别对应着康德政治道义论的内容——康德批判功利主义正是要重申实践理性的普遍原则,而本文提出的普遍权利、人是目的、人的尊严三点要求正好对应康德绝对命令的三个公式。绝对命令的不同公式根本上都是绝对命令总公式的演绎,正如罗尔斯指出的,“只存在着一个绝对命令,它具有三个公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等的”[6](246)。而之所以存在三个具体的要求,其根本作用在于使得绝对命令总公式更加具体,这样“我们可以用来使作为理性观念的道德法则更贴近于直观”[6](290)。这三个公式所对应的普遍权利、人是目的与人的尊严等几方面的义务性内容正是绝对命令的具体要求,本文接下来也将详细论述这三方面的内容。
二、康德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道义论要求行为出自义务,而不必追求某种外在的结果。康德对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后果论的批判集中体现了道义论的立场。康德既批判了功利主义所依据的经验性原则,也批判了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后果——幸福——的不确定性。
康德认为,人们不能根据行为产生的经验后果来评价其道德价值,经验性的因素也不能渗入道德原则之中,那些混入经验性原则的学说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哲学。康德之所以批判经验性原则,首先是因为道德原则只能是先天的,它既非出自经验也有别于经验。康德指出,行为的根据不在于质料,而在于先天理性之中,只有出自先天理性才能确保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取决于经验的行为原则只能是特殊的,因为经验内容本身是特殊的,“责任的根据在这里必须不是在人的本性中或者在人被置于其中的世界里面的种种状态中去寻找,而是必须先天地仅仅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3](396)。康德批判经验性原则的原因还在于经验性的内容有损于道德的纯粹性,那些掺杂了质料因素的行为原则不但不能成为普遍的原则,它们还会给道德带来损害,“任何时候,人们添加多少经验性的东西,就也使它们的真正影响和行为不受限制的价值蒙受多少损失”[3](418)。当然,康德之所以反对经验性因素对立法原则的干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经验性内容有损主体的自由。在康德看来,只有服从自己的内在立法根据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反之,如果行为是由外在质料等因素规定的,这样的行为必然是受制于经验内容的、本质上不自由的,此时行为所服从的乃是道德的他律,我们只有仅仅从道德原则出发,而不服从于任何偏好,也不追求任何外在结果,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自律(Autononie)的行为。
在康德的划分中,功利主义便是以经验性的后果为评价依据的。功利主义认为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在于它所能带来的幸福的总额,只要带来的快乐大于它所伴随的痛苦,这一行为就是正当的。在康德看来,功利主义以幸福作为目标是不可接受的。其一,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幸福本身是不确定的。功利主义主张幸福的最大化,生活中几乎人人都期望幸福,但在康德看来,幸福并不存在普遍的标准,所以人们所期望的幸福的内容并不一致,功利主义也无法对幸福作出明确规定:“幸福的概念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以至于每一个人尽管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3](425)康德进一步指出,在生活中人们常把权势、财富、荣誉等看作幸福,但是,这些种类的幸福常常互相冲突,很多时候它们还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甚至可能带来不幸。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康德认为幸福本身不是目的,它最多只能算作行为附带的结果。康德指出,人们常把富裕、强大、健康和一般而言的福祉看作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就不是目的,而主体的道德性才是目的”[7](401)。对于真正的实践理性来说,幸福只能算是一个附带的结果,它可以用来引导那些天生软弱的人;而要让自律主体更具德性,幸福就不是必要的了。这样说来,康德批判功利主义的原因既在于幸福作为后果是没有普遍性的,以幸福作为标准本身包含着不确定性;更在于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是没有实践正当性的。
具体到政治领域中,康德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批判意味着对政治功利主义的否定。政治的功利主义主张以政治行为的后果来评价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有学者认为,政治应该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并极力增加社会福利总额;只要能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样的政治就是正当的且值得称赞的。站在康德哲学的立场上,既然行为的正当性并不取决于它所带来的物质福利,那么无论政治行为带来何种后果,它都无法用后果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因为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根本上只取决于政治原则本身的正当性。不仅如此,政治也不应该以物质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正如康德所批判的那样,幸福本身既是如此不确定,又在根本上与德性原则相悖,因此它不能作为目的,最多只能被当作手段。在现实政治中,如果仅以幸福作为政治的目标而无权利的保障,那么人们最终将一无所获、权财两空。在此,康德虽然直接讨论的是道德行为的一般原则,但这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这一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就是把政治的目标从幸福拉回到权利上来,它确认了发展与福利无法证明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的唯一正当性说明只能在于它所依据的权利原则。
三、政治的权利原则
义务在康德的政治学说中首先体现为政治的权利原则——政治遵循权利的规定而非追求外在的后果。在《道德形而上学》之“法权论”的开始部分,康德就提出了普遍的法权原则,它要求“如此外在的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7](239)。这是一条贯穿康德整个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分析康德政治学说的基本依据。在康德的政治学说中,法权的原则与经验性或目的性的内容无关,虽然它常被批评为“形式主义”,但正如凯尔斯汀在为康德辩护时所指出的,法权虽然不提供具体的内容,但它“具有判准性特性”[4](160)。康德的政治学说始终坚持权利的原则,并把权利原则当作评判政治行为的标准,权利原则确保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具体到对现实政治的规范性意义,康德主张的权利原则包含着如下要求:第一,权利优先;第二,权利本身的可普遍化。
第一,权利优先。正如康德指出的,“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3](406)。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所依据的权利原则,而不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后果等质料性因素,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政治哲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确立了权利优先的原则。权利优先,强调的是政治必须以权利为基本准则,优先尊重和服从权利原则而非优先考虑其后果,只有符合权利原则的政治行为才具有正当性。
康德特别强调首先要考察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权利原则,而不是考察它所带来的可能后果,政治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废弃权利,政治行为必须以权利为最根本的原则,无论私人关系还是公共关系都“是同样地不能回避权利概念的,也不能依赖仅凭智虑(Klugheit)的手腕就可以公开地奠定政治;因而也就决不能废弃任何服从公共权利的概念,而是应使它得到全部应有的尊重”[2](135)。这也就明确宣布,聪明才智与外在福利都不能成为政治行为的根据,政治不能脱离权利,它必须服从权利的原则。康德多次指出,权利的要求高于幸福的要求,“政治准则决不能从每一个国家只要加以遵守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种福利或幸福出发……而是应该从权利义务的纯粹概念出发(从它的原则乃是由纯粹理性所先天给定的‘当然’而出发),无论由此而来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样子”[2](137)。在康德的政治学说中,政治不追求外在善,只有符合权利的规定的政治行为才是高贵并值得赞许的,人们对政治后果的考量不可挑战权利的原则,正如康德指出的,“有用还是无效果,既不能给这价值增添什么,也不能对它有所减损。有用性仿佛只是镶嵌,为的是能够在通常的交易中更好地运用这颗宝石,或者吸引还不够是行家的人们的注意,但不是为了向行家们推荐它,并规定它的价值”[3](401)。因此,根本而言,康德的政治学说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以权利作为政治运转的根本依据,它不以外在后果为目标,更不会拿权利与福利做交易,它只关心政治行为的“应该”和“不应该”,这样的政治必定是道义论的政治,因而也是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康德政治学说最重要的贡献也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应该”,从而确立了政治的道义标准。
第二,权利的普遍性。康德主张的政治权利不仅是优先的,还是普遍的。这种普遍性既指它是所有理性主体所意欲的权利,也指该项权利要向所有的理性主体开放。就前者而言,“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所有为理性所认知的可能世界中都是有效的”[8](41)。它强调当权利被普遍地付诸实践时,对所有的主体都是公平和合理的,其内容也具有合理的成分,能够成为所有主体的行为准则,比如公开运用理性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所有理性主体都意欲享有的权利。就后者而言,它强调该权利是公民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因他的国籍、种族、信仰及身份地位的差别而有不同,它是所有理性主体应该同等享有的权利。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说明莫过于康德所主张的普遍公民法权,康德曾主张理性的个体在法律上享有人的一般权利,这个权利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无差别的权利。康德指出,哪怕是两国交战,战胜国都应尊重并确保战败国的公民享有该项权利,因为战争是两国之间的敌对,并不是针对该国公民的敌对行为。因此,康德也称这项普遍权利为世界公民法权,“这种法权,就它涉及一切民族在其可能交往的某些方面可能的联合而言,可以被称为世界公民法权”[7](363)。世界公民法权进一步体现了人作为人而享有的一般权利,这也是康德政治学说普遍性特征的充分说明,因为它把权利扩展出契约的范围,从而无差别地赋予了所有理性主体,这种理性主体所享有的、无差别的、人作为人的权利正是权利普遍性的内在要求。在权利的普遍性意义上,康德的政治学说既确认了权利的正当性规则,也把这种权利普遍地赋予每一个理性主体,从而具有了鲜明的道德特征。
四、政治的价值目标
康德政治学说的权利原则根本上源自康德实践哲学的绝对命令,绝对命令不仅对道德发号施令,它也对政治发号施令。具体到政治学说中,康德不仅主张政治的权利原则,让权利原则优先于幸福原则,维护权利本身对于福利和幸福的优先地位;它还在权利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政治的价值目标——政治要以人本身为目的,政治要实现人的尊严。当然,政治的价值目标是更高等级的义务,它们也进一步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道义性特征。
第一,人是目的。正如前文指出的,在康德政治哲学中,追求幸福不是政治的目的,政治要以人为目的;而且,人作为目的是内在的、最高的目的。康德区分了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外在目的指的是一物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对另一物有意义,而内在目的则强调一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外物,它自身便是被需要的,人作为内在目的自身便具有价值,它无须通过外物来证明。康德指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都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实存的,在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行为中,我们都必须把理性存在者自身当作目的。经验的偏好作为外在目的只能是有条件的目标,如果条件发生转移,这些偏好也将失去价值,因此它们不能成为目标;相比之下,人本身才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其他目的来取代的目的,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3](436)。在此,康德强调的是人具有内在绝对价值,人作为目的本身具有绝对性,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应该始终以人本身为目的,要服从绝对命令的演绎式,做到“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3](437)。这一要求贯穿康德实践哲学始终,政治领域同样受此规则规范。
第二,人的尊严。康德强调人是目的,其着眼点在于强调人具有内在的绝对价值,而这种绝对价值的重要体现就是人的尊严。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只有人才是具有尊严的存在者,“人唯有作为人格来看,亦即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理性的主体,才超越于一切价格之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人,他不可以仅仅被评价为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达成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是应该被评价为目的自身,也就是说,他拥有一种尊严”[7](445)。尊严本身就是最具内在价值的,它不是经验可以说明的,更不是福利等任何外在之物可以衡量的,它本身具有最高的内在目的。康德指出,“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超越一切价格、从而不容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3](443)。福利和商品是有价格的,而价格作为一般性的衡量因素,其地位甚至要高于商品和福利本身;但人的尊严远远高于任何货币财物所衡量的范畴,自身就具有最高地位,甚至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康德之所以批评功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此种道德观念与人类的基本尊严无法兼容”[8](32)。
康德没有明确规定尊严的具体内容,但他对尊严的论述是重要且深刻的。在康德那里,尊严既承接着“人是目的”的规定,构成人是目的的具体说明,它要求尊重他人,也要求自身获得尊重;尊严还连接并规定着权利,它要求国家实现和维护人的尊严,在很多时候,尊严还具体化为权利,并构成评判权利的正当性标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尊严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或根据”[9](86)。正因此,实现并维护人的尊严就成了政治的一项重要要求,尊严也成了判别政治原则是否正当的标准。具体到现实政治中,其一,尊严是一项普遍性的权利,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尊严,我们不得否定更不能侵犯任何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尊严作为一项权利也得到了各国法律的承认,如《德国基本法》第一条就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其二,尊严高于权利并构成评判权利的标准。尊严具有至高地位,权利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它是否实现并维护了人的尊严,我们不能以尊严作为对价与其他因素进行权衡交易,任何经济发展都不得牺牲人的尊严,政治必须尊重和肯定每一个人的尊严。在康德这里,政治必须维护并实现人的尊严,因为“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不能被任何人纯然当做手段来使用,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同时当做目的来使用,而且他的尊严(人格性)正在于此,由此他使自己高于一切其他不是人、但可能被使用的世间存在者,因而高于一切事物”[7](474)。在现代政治中,唯有以实现人的尊严为目标的政治,才是真正“以人为目的”的政治。
五、康德政治道义论的重要意义
当前,正如费里克舒指出的,“‘回到康德’既是出于学术上的关注,也是出于现实的实质意义上的关注”[4](189)。前文对康德政治道义论之理论合法性的证明是学术上的关注,而对当前政治功利主义的批判正是康德学说的当代意义所在。康德从义务出发,认为政治只应该服从于义务而不应以幸福为目标,并重点批判功利主义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本身既不可能提供普遍标准也不可能确立正当性根据,这一观点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前,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在政治领域影响广泛。在功利主义原则的影响下,政治的目标变成了追求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治合法性往往只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康德的政治道义论则明确宣告,经济发展与富庶在根本上不具备道义的正当性,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还得建立在权利和自由基础之上。墨菲就指出,“康德非常清楚,自由并不需要任何肯定的正当性证明,因为自由本身就是善的”[8](111)。康德自己也指出,“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3](406)。用康德的话来说,只有行为出于道德才具有道德价值,它既不是为了追求外在的幸福,也不是偶然地符合道德法则,这样说来,“从道德的角度上看,康德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点:幸福和自利绝不可能确立起法律和政府的道德价值,除非它同时能够表明这些制度符合于自由和正义的要求”[8](132)。在此意义上,康德政治道义论对于纠正当代政治领域中功利主义泛滥、一味追求发展等现象具有重要作用。现代政治必须立足于权利基础之上,以保护权利、实现人的尊严为目标,在此基础之上的发展才有意义;而且,发展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它带来了更多的物质福利,而在于也只能在于它能扩展人的自由,不让外在福利成为自由的妨碍;发展必须以人本身为目的,进而实现人的尊严,损害人的尊严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在政治的目标这个问题上不可喧宾夺主,不可只注重发展而忽视了人本身。这是康德政治道义论的重要现实启示。
康德的政治学说的道义性特征在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也有重要理论意义。康德的道义论从权利出发,并在权利的基础上提倡道德,所提倡的道德最终又具体化为权利。这一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常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以防止道德与政治的混同而最终政治会滥用道德侵犯权利并走向现代极权政治;但在现实生活中,政治行为又离不开“应该”的规范。康德从政治与道德分界出发,首先维护了权利的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康德明确地阐述了现代政治的道义性内容所在;他主张人的普遍权利,主张以人的尊严为最终评判标准。这些观点既符合权利保护的要求,又超越了权利保护的消极要求,并通过把权利抽象化使之成为普遍的标准,从而使得权利成为“应该”。这样,一方面,康德“重建了以往那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性”[4](156),从而使得他的政治学说具有强烈的道义色彩;不仅如此,康德的义务论立场是强于近代绝大多数思想家的,近代思想家们“均低于康德的法权哲学和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无条件的实践必要性所处的形而上学层次”[4](172),因为康德的权利原则直接来自理性的“绝对命令”,它包含着充分的必然性,要求对一切理性主体具有必然性的效力。当前,我们完全可以说,虽然罗尔斯对于康德规范性意义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但罗尔斯理论的规范性效力是低于康德的,这也是我们主张“直接回到康德”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康德虽主张政治的道义论,但他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权力对道德的侵犯或道德对权利原则的干扰,始终坚持权利与他人的自由共存这一绝对命令的演绎,没有随意扩大“应该”的范围,从而站稳了自由主义权利政治的立场。因此,他不但没有受到自由主义者们的批评,反而成了自由主义的道义榜样,就如墨菲所言,“康德强烈地影响了那些为‘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的自由’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者”[8](159)。当前,康德对政治之道德立场的强调、对普遍权利的捍卫、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都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这些观点源自保护权利的政治目标却又超出了保护权利的范畴,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的道德立场,强化了政治的“应该”特性,最终使得康德的政治学说能够在权利保护的主流政治话语中占据牢固位置并进而成为当代政治的价值标杆,从而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