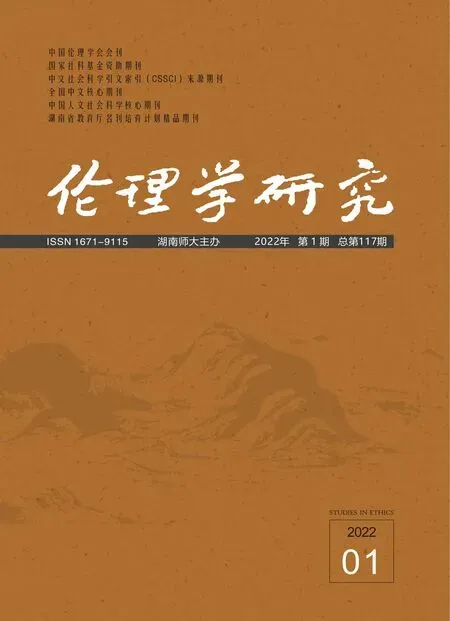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2022-11-22张卫
张 卫
引 言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是技术伦理学的两种进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外在主义进路关注的是技术的消极伦理后果,对技术采取批判的态度,目的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规约;内在主义进路关注的则是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在对象中“嵌入”伦理要素,目的是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换言之,外在主义进路视技术和伦理为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技术总是不断地冲破伦理的限制和束缚,而伦理则尽力把技术控制在它允许的范围和空间之内,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ethics versus technology”或“ethics of technology”;内在主义进路则视技术和伦理为相互支撑的盟友,技术的进步总会对原有的伦理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原来的伦理难题,而伦理观念的进步也会极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ethics by technology”或“ethics for technology”。从辩证的视角看,技术与伦理既存在对立,也存在统一,两种进路各自抓住了技术与伦理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因此是互补的,都是技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外在主义进路的出现明显要比内在主义进路更早,并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近年来技术伦理学的“内在主义”转向,内在主义进路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这主要体现在荷兰学派提出的“道德物化”(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理念中。而除了“道德物化”,学界近年来提出的“道德增强”理念也可纳入内在主义进路之中。如果说“道德物化”是把伦理要素“嵌入”技术人工物,利用技术物的“居间调节”作用助推人的行为向善,“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的“身体”层面,通过对“基因”和“神经”的干预来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增强”是一个比“道德物化”更为激进的理念。与“道德物化”类似,学界对“道德增强”也存在着诸多的伦理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即使在各自的阵营内部,不同的学者给出的辩护和反驳理由也不尽相同。
一、道德增强的含义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增强,人类发明的各种技术、接受的各种教育都是增强的表现。随着“人类增强技术”的出现,人类增强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从体外、缓慢的增强到体内、高效的增强的转变。比如,以前我们可以通过起重机外在地增强人类的体力,而现在则可以通过与大脑神经相连的外骨骼,让无法站立行走的残障人士站立行走;以前我们通过长期的学习积累记忆知识,而现在则可把储存大量知识的芯片和大脑神经直接相连,从而快速高效地记忆知识。这两种增强方式的区别是,前者是一种体外增强,技术只是身体的一种辅助,后者是一种体内增强,技术直接改变人的身体;前者是一种缓慢的增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后者则是一种高效的增强,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
人类增强技术可以对人类的许多方面(认知、体能、记忆、健康、道德、容貌等)进行增强,“道德增强”是其中的一种类型,针对的是道德能力的增强,又称“道德的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英国学者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佩尔森(Ingmar Persson)、萨伏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等人是“道德增强”概念的提出和倡导者,但是目前,不同的学者对“道德增强”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佩尔森和萨伏列斯库的理解是:利用技术或药理学方法去影响人类道德机能的生物层面,以促进合理行为的实现,或消除有问题的行为[1](6)。而拉瓦扎(Andrea Lavazza)的理解则是:对神经系统或基因进行干预,目的是让个体的表现和/或行为——相比于之前——更加利他(像考虑自己的利益那样考虑他人的利益)和公正(在类似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2](16)。尽管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但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共同的目的,即: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3](33)。
“道德增强”可以在“基因”和“神经”两个层面进行。基因层面的道德增强属于基因增强的一种,基因增强又是基因编辑的一种。基因编辑可以是治疗性的基因修复,也可以是增强性的基因操纵,当然,治疗和增强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基因增强目前主要在认知能力增强和生理能力增强方面研究得比较多,道德的基因增强由于涉及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基因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像基因与生理机能的关系那样直接,显得更加隐蔽与多变,因此目前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还缺乏成熟可靠的技术支撑,但相关的探索已经开始。神经层面的道德增强主要是通过药物、激素、电刺激、神经外科手术等手段作用于人的神经,以此来增加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机,从而影响人的道德行为。比如,“百忧解”和“利他林”之类的精神药物可以对“自尊”及“注意力集中”等产生影响[4](177);“催产素”能够增强人的友爱和信任的情感,减弱人的攻击性,增加人的同情心,从而有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友善关系,因此又称“情感纽带荷尔蒙”(bonding hormone)或“快乐荷尔蒙”(happi⁃ness hormone)[5](1072);“血清胺”也会影响人际关系,身体内血清胺含量较低的人不愿意与人合作,反之则会提高人的公平意识[6](402);脑的电刺激目前可以用于抑制癫痫发作和治疗某些精神病,神经外科手术可以通过切断颞叶和下丘脑的联系来治疗非理性暴力病人的极端攻击性行为[4](173-175)。
从上述分析可知,“道德增强”和“道德物化”具有很强的类似性,都是借助技术手段来提高人的道德能力,这与传统的“道德教育”做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是把道德规范内化到人的心灵之中,让人获得道德认知并形成道德情感,从而产生道德行为。同样地,尽管“道德增强”是出于良善的目的,但有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因此目前还面临着诸多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开启了人类道德进化的新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萨伏列斯库、佩尔森、拉基奇(Vojin Rakić)、达纳赫(Join Danaher)、卡特(Sarah Carter)等,反对者则认为这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主要代表人物有哈里斯(Join Harris)、伯林(Isaiah Berlin)、费舍尔(Erik Fischer)、芬顿(Elizabeth Fenton)、阿加(Nicholas Agar)、坦尼森(Michael N.Tennison)、阿劳约(Marcelo de Araujo)等。
二、支持道德增强的理由
由于“道德增强”理念的激进特征,它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和反对,如何对道德增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是道德增强的支持者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他们给出的辩护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之间一直都存在着张力。人的生物进化速度与技术进化速度是不匹配的,后者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而前者的进化节奏则极为缓慢。如果把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压缩为一天,那么现代技术社会的历史可能仅仅是临近午夜前的几秒钟。可以说,人类的生物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范围内几乎可以忽略,人类目前的生理属性几乎还停留在百万年前的原始水平,而这种生理属性与当今高度发达的技术文化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比如,本来适合于打猎的人类视力机制现在却在大部分时间里盯着电子屏幕看,长此以往就会带来视力疾病;人的身体储备脂肪以备食物短缺的属性在原始时代可能是个优势性状,但在当下以瘦为美的文化中则是一个劣势性状。因此,人类有必要进行生理的增强,人为地加快人的生物进化速度,让人类的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的节奏保持协调。
其次,人类的道德心理机制与现代技术之间也是一种“错配”。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但人类道德的心理机制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仍然停留于与原始技术相匹配的水平。具体而言,原始技术的力量是有限的,其规模和影响都是地方性的,比如弓箭,其射程和杀伤力都是有限的,而现代技术的力量则是巨大的,其规模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如果建立在原始技术上的心理机制仍然以这种地方性的思维来处理现代技术,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由于人类的道德本能受限于局部的空间和时间,往往只对当下的、局部的人群比较关心,而对未来人、陌生人缺乏足够关心,因此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核危机、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极端一点儿说,一个道德能力欠缺的物种是没有资格拥有这么强大的技术力量的。因此,人类应该建立一种与现代技术相匹配的道德心理机制。
再次,人类的某些弱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它是由人类的生物、生理、心理机制造成的,而不是后天造成的。这就导致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先天的道德意志不足以提升个人的道德品格,而传统的道德教育、法治建设、制度约束等手段也不能很好地改变这种性状,只能利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类的生物、生理、心理机制进行“增强”,方能缓解或消除植根于人性中的弱点。正如怀斯曼(Harris Wiseman)所说:“人性中潜伏着太多的天生的黑暗面,传统的道德教育途径已经失败了,并且必然失败——因此,介入是必要的。”[7](4)达纳赫也认为,内在增强比外在增强更为可取,其原因在于,内在增强更容易直接与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外在增强则容易忽视有意识的感知和理解[8](49)。如果说道德教育等手段是改变人类道德的后天能力——道德认知,那么道德增强就是改变人类道德的先天能力——生物基础。它试图依靠技术手段使缓慢演变的道德心理机制迅速地赶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建立与现代技术相匹配的道德心理机制,在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来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的情况下,道德增强或许是一种替代方案。
最后,道德增强提升的是基础性、通用性的能力[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并没有限定其未来具体的道德发展方向,相反,它为以后能够进行更多的道德选择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是在增加未来个体的自主性。正如道格拉斯所说:“道德增强对身份改变没有多大的影响,不仅不会限制人的自由,反而还会扩大人的自由。”[9](239-240)因此,和其他技术一样,道德增强技术能够让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提高实现积极目标的能力。当然,这也会引发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基因优势应不应该成为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的范围,这在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三、反对道德增强的理由
与支持道德增强的力量和理由相比,反对的力量和理由似乎更强。反对者认为,道德增强可能会对人的自由和尊严产生挑战,具有“基因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嫌疑,不利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不利于责任意识的培养,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严重的冲击,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引发社会价值的冲突,削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第一,道德增强可能会对人的自由和尊严产生挑战。哈里斯认为,道德增强损害人的自由,因而伤害人的道德判断和决策能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人具有“自由意志”,人可以为自己立法并按此立法行动[10](61)。如果人的道德选择是由技术决定的,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岂不是被剥夺了?如果人失去了意志自由,人还何以保持人的尊严?正如哈里斯所说:“如果你必须做某事,那么就没有美德可言。”[11](104)在他看来,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取消自由就等于取消道德。换言之,当人必须行善时,就失去了道德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以至于不知何为善、何为恶,因此他主张保护人的自由,包括“犯错的自由”(free to fall)[12](82)。
第二,通过改变基因来实现对行为的矫正具有“基因决定论”的嫌疑。基因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是谁和是什么’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基因……我们人类无非就是DNA 和蛋白质,我们的存在不过是那些DNA 和蛋白质各自特性和属性的表现结果。”[13](3-4)在这种观念下,基因成了决定着人类一切的最终依据,从健康、智商到道德都可以在基因中找到根源,通过对基因的取舍与修饰,就可以影响和改变人类的外在形状和行为表现[14](48)。基因的道德增强将会改变道德的人性基础,把人类社会带入所谓的“后人类时代”或“超人类时代”,这将给伦理学带来巨大的冲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本以为脚下的大地是稳固的,而它现在开始晃动,这将会给我们带来眩晕感。”[15](39)
第三,道德增强还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不利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也不利于责任意识的培养。关于人类行为的原因,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先天本性”和“后天养成”的争论,“先天本性”派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生物遗传的影响,“后天养成”派则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两种立场分别轮流主导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当今时代,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编辑、认知神经学、神经药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的进展,“先天本性”派的主张重新被人重视。然而,在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念中,这被视为是“优生学”的死灰复燃,被称为“私人化的(privatized)的优生学”。这样一来,关于道德增强的讨论就从国家是否有权实施优生学的质疑转变为父母是否有权对后代实施优生学的质疑。桑德尔和哈贝马斯都不赞同实施道德增强,他们认为,道德增强和道德教育的不同在于,基因增强是完全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而后天的教育是双向互动的、可逆转的[16](282)。
第四,道德增强将对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严重的冲击,并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道德增强虽然原则上对每个人都开放,看似人人平等,但这只是“形式的平等”,而不是“实质的平等”,因为道德增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是人人都能实施的,或许只有部分有钱人才有足够的资金来为自己或后代实施道德增强,从而增强自己或后代的社会竞争力,这将会导致弱者越弱、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造成严重的冲击。另外,人类的主流价值观更认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不是靠金钱购买的技术来获得某种能力,这只能助长人类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心理,无助于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等传统美德的传承。
第五,道德增强是一种价值傲慢的表现,将会引发社会价值的冲突,并削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基因技术出现之前,人类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只能听任自然的随机安排,基因技术的出现则让父母能够掌控下一代的性别、身高、健康、体能甚至智商。这就让父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一个孩子。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对女同性恋伴侣通过人为“设计”,生出了一个失聪的孩子。这件事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人们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强加到她们孩子的身上,而她们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而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17](3-4)。从中我们发现,“缺陷”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在一个人看来是缺陷的地方在另一个人看来并不一定是缺陷,如果强行对某种所谓的“缺陷”进行治疗或增强,这就等于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另一种价值观之上,这将会让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遭到进一步的打击与排挤,从而削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18](61-63)。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价值傲慢的表现,正如桑德尔指出的那样,该事件所反映的深层的道德疑虑还不在于该父母蓄意将残疾强加给孩子,而是“它所传达出的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在于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的傲慢态度,在于他们想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18](46)。
四、对双方争议的反思
上述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道德增强的利弊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双方的论证和理由也存在一些考虑不周全的问题。首先,由于道德增强的呈现形式是多样的,有自愿和强制之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有强和弱之别、有现实与未来之别,所以泛泛地支持或反对道德增强都有简单化的嫌疑,要么一概否定,要么一味肯定,这种态度显然是片面的。关于道德增强利弊的讨论应该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分析,才能对之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在某些情景中,并不是一味地增强友善、同情心和信任能力就是道德,有时候还需要与之相反的性能,比如,“一个法官在对一个危险的惯犯进行判决时,其同情心是否应该被增强?如果存在别人利用我们的信任而让我们成为受害者的风险,我们的信任感是否应该被增强?当我们目睹一个孩子被性骚扰,我们是否应该抑制自己的进攻性?”[19](294)可见,友善、同情和信任等道德情感并不能无条件地增强,该严苛的时候严苛,该宽容的时候宽容,否则就会导致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从而与其初衷相背离。因此,道德增强不能剥夺行动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和知情同意权,如果用“这是为你好”的理由来强制实施道德增强,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因为自认为好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不一定是好的。正如密尔所说,“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20](11)。因此,道德增强不能以“这是为你好”的理由迫使人们实施道德增强,而应该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
其次,在面对一项新技术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它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秩序,是违反自然的,道德增强也不例外。但是,何为“违反自然”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启了利用技术改变自然以维持生存的技术化生存模式,技术的本性就是按照人的意图对自然进行改变,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这种生存模式,只不过以前的技术只是对外部自然的改造,而现在人类把技术的矛头转向自身,开始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改造,人类才突然意识到这是无法接受的。然而我们反思一下人类以前的做法,对自身的改变和对自然的改变难道不都是对自然过程的介入和改造吗?如果说对自身的改变是违反自然的,那么对自然的改变难道就不是违反自然吗?因此,用违反自然作为反对道德增强的理由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过度依赖“道德增强”,道德增强应是一种补充性的辅助方案。如果让道德增强成为道德建设的主导方法,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为了避免道德增强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的道德教育仍然应该作为主渠道,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或传统道德教育失效的时候,才需要适度地利用道德增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再次,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需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邻避效应”。为了能够拥有更强的生存优势,人们通常都会积极地拥抱那些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长寿、更漂亮的增强技术,但与其他增强技术不同,“更善良”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因为更善良可能导致自己损失更大[21](267)。因此,从福利主义的角度看,道德增强有可能是对个人福利的削弱,而个人福利是普通大众非常现实的考量,这就导致道德增强可能面临如下的现实困境:虽然道德增强旨在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最终有利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增加,但却找不到目标人群,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可能在理论上支持道德增强,但自己却不愿意被道德增强。这就好比“邻避效应”:很有必要,但别在我门口实施。
最后,真正引发我们深思的应是道德增强所引发的“意义”消解问题。通常而言,当一件事情已经有先进的技术可以利用,而再去费时费力地依靠人力或旧技术去做的时候,其努力和奋斗就会显得不合时宜而失去意义,以至于沦为庄子寓言中抱瓮取水的“为圃者”而被人嘲笑。那么,如果人类的道德素养可以由道德增强迅速高效地实现,传统的道德教育和训练又还有何意义?这涉及技术与意义的深层联系,即凡是被技术征服过的地方,那些依靠旧工艺进行的活动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从而导致“意义”的消解和危机。这种危机在高速进步的技术时代变得更为严峻,各种新兴技术像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让人应接不暇,甚至无所适从:当现代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能够高效地生产人类日常用品的时候,传统手工艺就只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下苟延;当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迅速把知识输入人的记忆系统,耗时耗力的记忆活动貌似就失去了意义;当基因增强技术可以让人先天拥有某种强大的天赋,后天的刻苦训练似乎也变成多余的了;当作曲算法能够比巴赫创造的音乐更像巴赫风格时,人类的作曲好像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而当大数据技术能够迅速高效地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到犯罪嫌疑人时,警察的工作也成了辅助性的。
然而,人毕竟是悬挂在自我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22](126)。如果意义之网被技术这头猛兽给撞破了,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意义,重新编制一张新的意义之网?难道我们只能靠不断发明更为先进的技术去寻找意义吗?这不等于饮鸩止渴,越陷越深吗?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去重新思考庄子“抱瓮灌园”的寓言,我们不禁佩服庄子思想的敏锐而深邃,在技术还不发达、技术异化还没有凸显之时,庄子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技术与意义的深层冲突,其“无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的忠告更是穿越两千年的时空,在当今时代的墙壁上激起最强的回声。正如福山所说,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生活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答案或许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要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23](9)
结语
从道德增强的伦理争议可以看出,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本质上是一体的,一项技术在解决伦理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治疗”和“增强”是相对的,用于“治疗”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增强”,所以技术解决和引发伦理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就解决伦理问题而言,“治疗”可以有助于那些先天基因缺陷的人群恢复到正常水平,从而消除人与人之间先天的不平等,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就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而言,“增强”让某些群体获得超出正常人水平之上的新优势,将会加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如果说“治疗”是在解决伦理问题,那么“增强”则可能是在产生新的伦理问题,前者属于内在主义技术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后者属于外在主义技术伦理学的关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