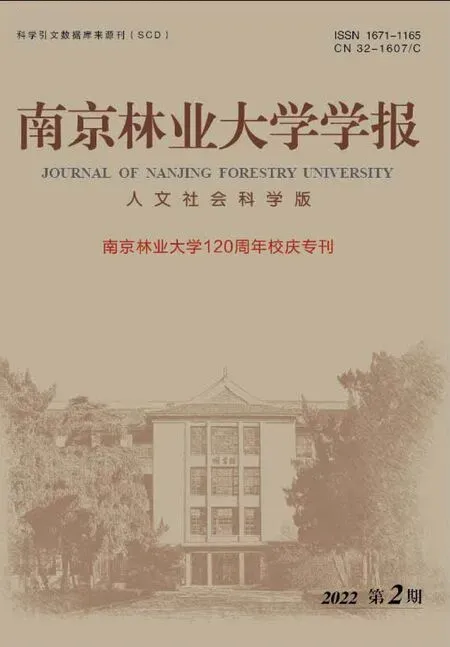21世纪全球环境危机与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物转向”*
2022-11-22韩启群
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值此后疫情时代,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并未因新冠疫情暴发而有所缓解,相反,各种相互关联、叠加的危机持续威胁人类,环境危机构成了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各国围绕日本核废水排污展开的谴责和争议则表明,当前的环境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深刻而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现实中的环境危机不但是作家笔下重要的创作素材,也必然会影响到人文社科领域各种理论思潮的生发、演变,进而塑造文学研究的新选题、新视角和新趋势。本文从21 世纪全球环境危机这一现实语境入手,将具有共同时代孕育土壤的环境危机现实与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相关联,以环境危机现实为轴点观照当前生态文学研究以“物转向”为聚焦点的新趋势,从研究对象“物转向”与理论话语“物转向”两个维度论证21 世纪的环境危机现实不但催生了当前生态文学以凸显“非人类”研究对象为特征的选题新趋势,还推动了以“物转向”“身体转向”“非人类转向”为标志的生态批评话语的迭代更新。
一、21世纪全球环境危机现实与生态文学研究“物转向”的关联
2000年,为了引起人类对于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首次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以气候变化为表征的新地质历史时期。2021 年,克鲁岑辞世,他在20多年前使用的“人类世”概念已经被现实中的气候变化危机所印证。而且,和20 年前相比,全球生态系统益发显得脆弱,生物多样性丧失、美国加州山火与澳大利亚丛林大火、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事件等频见新闻头条。与后疫情时代种种危机现实形成对应的是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目标和决心,如2021年10月在中国云南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正式通过的“昆明宣言”,以及11月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一系列重大协议。作为敏锐感知时代脉搏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当前的各种生态与环境议题构成了生态文学研究领域亟需回应的诸多新话题。
受21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现实影响,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不少学者开始深刻反思传统叙事模式的弊端,呼吁环境批评学者关注哪些研究有助于把“以环境为导向的思维推向未来”,哪些研究会把“环境主义束缚在过时的研究窠臼中”。[1]在著名的《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杂志的创刊号前言中,编辑们一致认为要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叙事格局”,研究并拓展“新的叙事形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实”。[2]学者们将新的叙事需求和环境危机相关联,认为传统的“主流理性叙事”最终导致了“威胁全球生物圈的经济制度的形成”,构成“现代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3]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全球生态与环境人文学》(Global Ecologi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15)的导论中,伊丽莎白·德洛格瑞(Elizabeth DeLoughrey)、杰尔·迪德诺(Jill Didur)和安东尼·凯瑞甘(Anthony Carrigan)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对传统叙事展开“批判性研究对于明确我们如何阐释和减轻环境危机至关重要”,要关注和思考传统叙事在加剧“气候变化、帝国主义、资源开采、全球公域污染和治理、石油资本主义以及自然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等环境危机和灾难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将之作为环境人文领域的重要主题。[4]
现实中的环境危机、文学研究对叙事范式转换的内在需求催生了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物转向”趋势。而就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而言,主要指涉两个维度的转向:一是研究对象的“物转向”,如当前生态文学研究领域与食物、植物、动物、能源、气候乃至海洋等相关的研究选题;二是研究话语的“物转向”。作为一个高度异质的理论空间,“物转向”话语涵盖了众多不同源点的理论话语,而这些理论之所以能被“物转向”所涵盖,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参与了对人类的去中心化”,能够超越“文化和语言学转向”,有效地“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展开批判”。[5]笔者将聚焦生态文学研究领域两个不同维度的“物转向”,结合具体批评实践展开论述。
二、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选题的“物转向”
就“物转向”选题的批评路径而言,研究者往往将批评视角转向文本中的物质细节书写,倡导一种“反向批评模式”[6],即从各类物着手,聚焦文学文本中一直以来像“谦卑的奴仆一般”[7]被边缘化的客体;文学作品中不同形式的物质书写,如礼物、器物、传家宝、建筑、植物、食物、消费物品等都在新的理论观照中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内涵。其次,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中对人物和情节的强调,“物转向”话语倾向于挖掘物的微观细节的审美内涵,如物的质地、颜色、属性、新旧、大小、方位等。在“物转向”研究者看来,“物可以通过自身的性状和形式来传达意义,也可以通过所用的材质与装饰来言说”[8]。这种研究思维和批评路径也体现在生态文学研究对象的“物转向”,如“食物转向”中对于物质毒性成分的聚焦以及有毒物质在多大程度上对身体造成伤害、“植物转向”中对于植物本身生长形态书写的关注等。近两年来国内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会议议题的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譬如在2021 年11 月5 日至6 日以“生态批评:思辨之旅”为主题召开的第十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中,“自然书写”“景观研究”“食物论述”“物件理论”“动物研究”等具体议题的设置体现了明显的生态文学研究选题的“物转向”;而南京林业大学在2021年12月28日召开的“后疫情时代当代外国生态文学前沿研究”高层论坛的议题设置中也体现了类似的“物转向”,如“物与非人类书写”“家园与地方书写”“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的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等。生态文学研究对象的“物转向”有助于对不同类型“非人类”物质环境(如河流、气候、食物、植物等)的危机进行差异化回应,进而有效展示文学作品中环境危机书写的审美异质性。
受“物转向”思潮影响,生态批评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食物转向”,曾经在文学研究中被视为“像大米一样”太普通而不受关注的食物书写,现在却因为“种类多样而成为一种热门的商品”[9]。“食物转向”的一个深层动因在于现实中食物与环境危机的关联。1906 年,美国记者、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小说《屠场》(The Jungle)中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20世纪早期美国肉类加工业令人震惊的卫生违规现象,引起全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强烈反应,直接推动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注射了抗生素的可食用动物致人感染与新型耐抗生素菌株有关的食源性疾病的事件依然时有出现;农药化肥的超标使用不仅造成农作物有毒物质残留,而且还因为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引发更广泛的食品安全问题;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加工生产的转基因食品是否会以慢性暴力的形式对人类基因组产生影响仍是目前科学界和环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食物常常被涵盖在“环境健康运动”(environmental health movement)关注范围内,因为“包括空气、水、食物、土壤、气候和其他生物在内的所有自然因素”都影响着人类健康,而“在一个患病的星球上不会有健康的人类”[10]。鉴于这些危机事实,生态学者积极将不同类别的食物书写纳入考察范畴,呈现了食物研究的不同生态维度。如斯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在阐述“跨躯体”(Trans-corporeality)概念时指出,“最明显的跨躯体物质就是食物,因为进食让植物和动物进入我们的躯体。虽然进食似乎是一项简单的活动,但在从泥土到口腔的过程中,物质特殊的动能可能会显露出来”[11],食物因此串联起身体与生态,成为后人类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切口。此外,一些承载殖民经济历史的食物,如咖啡、蔗糖等,常成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场域:“因殖民地和种植园经济导致的生态恶化,使得后殖民和生态批评研究之间产生了丰富的对话。”[12]近年来,食物研究的学者们敏锐关注到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的《快餐王国》(Fast Food Nation,2001)、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自耕自食:奇迹的一年》(Animal,Vegetable,Miracle:A Year of Food Life,2008)、露丝·尾关(Ruth Ozeki)的《食肉之年》(My Year of Meats,2013)等作品中的食物书写,并将之作为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新路径,藉此反思渗透在食物中的工业污染、生态危机和环境非正义等一系列问题,启发读者关注食物、非人类物质环境与被他者化的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对象的“物转向”不仅表现为“食物转向”,还体现为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小说研究热潮。21世纪以来,全球变暖加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异常天气现象增多(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山火频发等气候变化实例让人类逐渐意识到人类世无法逃避的各种危机。与此同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部分西方政客否认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这种怀疑论调无疑阻碍了全人类应对气候变暖的行动。以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为代表的学者们呼吁在文学创作中给予气候变化迫切回应,以便“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能够被讨论、被感知、被传达”。[13]因此,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化小说(Cli-Fi)作为一个新兴文类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既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等文坛老将创作的作品,也涌现出了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纳撒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等新人的新作。这些作品往往以末世或后末世书写为特征,以科幻体裁形式想象气候变化对未来的影响,通过“未来已来”的环境危机警示唤起公众气候危机意识。气候变化小说这一独特的文类创作吸引了国内外生态学者的广泛关注,批评家们从人类世批评话语、生态世界主义、“超客体”、空间理论、记忆理论等多个角度呈现气候危机本身以及气候变化背后“涉及生物多样性、种群发展、资源利用、城市空间布局、能源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变革、心理创伤治疗等方方面面”[14]的系统性问题,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以科幻形式表现气候变化危机后末世小说,一些以现实主义笔法表现气候危机的小说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研究选题,如重述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拯救骨头》(Salvage the Bones,2011)、回顾1927 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的《倾斜的世界》(The Tilted World,2013)以及关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回忆录《浪》(Wave,2013)等。
除了“食物转向”和气候变化小说研究,能源污染小说也是近年来生态研究选题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虽然能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随着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人类也越来越意识到其中的弊端,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加工和使用直接相关的地表水土流失、水污染、有毒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加拿大学者伊姆雷·史泽曼(Imre Szeman)和美国学者多米尼哥·博伊(Dominic Boyer)立足环境人文学,在2014年首次使用“能源人文”(energy humanities)概念,指出“人类的能源和环境困境根本上而言是伦理、习惯、价值观、制度、信仰和权力的问题——涉及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专业领域”,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并不能彻底解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能充分实现可持续发展。[15]作为能源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学中的能源书写开始得到广泛关注。《石油!》(Oil!,1927)、《皇冠上的宝石》(Crown Jewel,1952)、《格林佛海湾》(Greenvoe,1972)、《九头蛇头》(The Hydra Head,1978)、《盐城》(Cities of Salt,1984)、《德士古》(Texaco,1992)、《石油王国的爱情》(Love in the Kingdom of Oil,2001)等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石油小说进入批评视野。批评家们既提倡从“殖民历史、(新)帝国主义权力以及后殖民主义资源战”等角度厘清能源与政治、历史和权力话语的关系[16],又强调关注能源小说中“生态掠夺”“环境正义”主题[17]。总体而言,目前能源人文学者大多宽泛着眼于能源与现代性、能源与哲学、能源与文学、能源与权力话语、能源与环境科学等关系的论述,因此对生态研究学者而言,如何依托能源人文学,将能源与环境批评有机结合,例如探究能源小说中的慢暴力书写等,是继续深化生态文学中能源研究的重要路径。
除了食物、气候、能源等“物转向”选题趋势,植物、动物、河流等选题近年来也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以植物转向为例,研究者们一方面试图扭转多年来学术界“既不关注环境中的植物,也不承认植物在环境中的价值”的“植物盲视”(Plant Blindness)倾向[18],另一方面呼吁关注“植物的生命”(Botanical Being)[19],关注某种内在于植物本身、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活力”(vitality)[20]。总之,形形色色的“物转向”选题看似琐碎,但却大大拓展了生态文学研究疆域,“食物转向”“植物转向”“动物转向”这些术语的使用表明琐碎的“物转向”选题经过沉淀,逐渐又生成若干以凸显“非人类”物质环境为特征、具有不同研究旨趣的新的生态文学研究空间。
三、当代外国生态文学批评话语的“物转向”
与21 世纪以来全球日益凸显的环境危机形成平行和呼应的是当代西方生态文学批评话语的“物转向”。始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转向”主要以物质文化研究为聚焦点,但到了21 世纪,却逐渐演化为一场引发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如哥白尼革命式“本体论转向”(The Ontological Turn)的哲学大潮[21],背后原因值得深究。对此,“物转向”代表人物比尔·布朗(Bill Brown)将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最珍贵的物——地球——“正在遭到破坏”;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以“代替人工作”的仿生人,因此,“一直以来把物排除在伦理思考之外的人文学科过时了”。[22]近年来的“物转向”也常常和“非人类转向”并置,原因在于这两个转向的核心推力都是21世纪以来的环境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危机、思考危机,正如“非人类转向”的提出者格鲁新(Richard Grusin)所言:从“气候变化、干旱和饥荒”,到“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和隐私”,再到“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和战争”,人类在21 世纪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非人类”相关,因此现在似乎是“非人类转向”的最佳时机。[23]上述学者们的观点表明,受21世纪以来各种环境危机现实的倒逼影响,传统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老旧的理念无法为人文社科领域走出各种悖论提供理论支撑;各种危机现实促使人文社科领域重新思考物的本质,重新定义人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而这种“对物的基本结构的重新阐释”有着“深远的规范和现实意义”[24],成为21 世纪以来文学批评话语“物转向”的核心推力。
作为一个高度异质的理论空间,“物转向”话语涵盖了“物论”(Thing Theory)、“新活力论”(Neovitalism)、“行动元网络理论”(Actant Network Theory)等众多不同源点的理论话语,而这些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建构一种旨在去人类中心的理论模型来重新定位人类在宇宙万物中所处的位置。由于生发和滋养“物转向”话语的土壤与环境危机密切相关,不难发现近10年来最热门的生态研究也源自两股比较明显的环境危机潮流:一是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危机近年来叠加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使得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愈益严峻复杂,推动了以物质生态批评为代表的生态批评“物转向”话语,其核心要旨在于通过强调物质动能(material agency)来构建一种宇宙万物有“活力”,彼此不断生成、纠缠的新理论模型;二是以人工智能、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颠覆性改变引发人类对何为主体性的思考,进而推动了生态批评的“身体转向”和后人类转向,其中以重新定义人类、环境与新型物种关系的后人类生态批评话语为代表。
虽然生态批评的“物转向”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质生态批评,但物质生态批评无疑是生态批评“物转向”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或曰是“物转向”理论话语塑造生态批评前沿的典范。在2014年出版的《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导论中,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和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详细阐述了“物质生态批评”话语范式的起源、主要观点与批评路径,将物质生态批评的研究任务归纳为聚焦“由物质构成的身体、事物、元素、有毒物质、化学物质、有机和无机物质、景观和生物实体,以及物质之间、物质与人类之间的内在互动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能被解读为故事的意义和话语”[25]。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方法,物质生态批评关注非人类物质动能在叙事文本中的体现,以及物质创造意义的叙事能力,凸显出“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文化和文学潜力”,同时,“将人类重新安置在充满无机物质力量的广阔自然环境中”[26]。由此看来,物质生态批评深受“物转向”理论影响,认同万物皆有动能且通过内在互动紧密相连,进而肯定了所有物质自我的平等;此外,通过对物质动能、意义生成与叙事动能的强调,物质生态批评不但颠覆了人类/非人类、心智/身体、语言/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也有效实现了“去人类中心”的批评任务。
如果说物质生态批评所蕴含的“物转向”更多通过对“物质动能”的强调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执念,那么生态批评的“身体转向”和后人类转向则聚焦人类本身的物质性。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推力源自以气候变化、新冠病毒为代表的环境危机。频繁发生的环境灾难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人类面对大灾难时的不堪一击等残酷事实都在提醒人类本就是一个躯体性的存在,和自然界其他动物一样也会生老病死。这种转向的另一个重要推力则在于仿生人等新物种的出现及其对人类情感的介入引发的人类对何为身体的界限、何为人类主体性的思考和担忧。21世纪以来,生物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生物技术能够进行基因治疗、显微手术、辅助生殖技术,能够制造救生假肢装置、药物情绪和行为调节器,以及完成克隆、转基因作物培育和基因杂交。如果说人工智能是让机器模拟并延伸人的智能,那么,基因生物技术就是直接改造人类身体,二者联合推动了21 世纪以来生态批评话语中的后人类转向。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1987 年发表文章《赛博格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将这种“人机合一”的身体称为“赛博格”——“一个控制机体,一个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虚构的产物”;她更是在当时就指出“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27]哈拉维的说法在今天得到了印证,义肢、人工晶状体、心脏起搏器等植入人体以帮助残疾躯体恢复正常功能的工具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使用,除此之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几乎每个人都以虚拟的数字形式在网络空间出现,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哈拉维所说的“我们都是赛博格”的状态;与此同时,相关的伦理风险也相伴而生。在此背景下,后人类生态批评将人类身体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借助“赛博格”“跨躯体”概念审视人类、技术、新型物种关系等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共生关系。近五年来,与生物技术、赛博格、仿生人相关主题的科幻作品成为后人类生态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2021)、麦克尤恩的《像我这样的机器人》(Machines Like Me,2019)、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三部曲”(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等。学者们或聚焦小说中的智能合成生命如何对人的概念发出挑战,或反思遭到生化污染的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生存,体现了后人类生态批评植根于危机现实语境的环境伦理维度。
从上述和物质生态批评、后人类生态批评相关的研究来看,生态文学批评话语的“物转向”和生态批评聚焦环境危机的核心旨趣一脉相承。自1978 年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以来,该批评话语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也推动了力求缓解世界生态危机的绿色思潮。从数十年来生态批评所经历的几波浪潮演变来看,“环境危机”线索依然隐含其中,如以关注荒野书写为标志的生态批评第一波浪潮向聚焦环境公正的第二波浪潮的转变,揭示了环境利益分布不均衡的危机;第三波浪潮以跨文化生态批评为特征,种族、阶级、少数族裔、女性的环境权益受到关注;物质生态批评、后人类生态批评则构成了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核心推力仍然是21世纪以来的环境危机与伦理危机。生态批评与环境危机线索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揭示了生态批评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和政治批判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生态批评在应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论
当前,自2020 年初开始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呈散点多发之势,新冠疫情在改变国际秩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各种虚拟会议、社区团购、云端课堂深刻塑造了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后疫情时代的新型环境危机:一方面,高度的虚拟化、数字化的网络空间将身体与经验世界割离,从而可能会导致人类情感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信息茧房为标志的后真相时代使得人类对现实的掌握日趋薄弱,事实变得益加模糊,有效沟通的可能性也随之大打折扣。新的危机现实也推动了生态批评向第五波浪潮的过渡,其聚焦点在于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和受众的情感反应。对此,国际著名生态学者斯格特·斯诺维克(Scott Slovic)在2019年敏锐地指出,学术界可能正在经历生态批评的第五波浪潮,它“可以追溯到罗伯·尼克松(Rob Nixon)在《慢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2011)一书中对理解(apprehending)环境和社会危机信息之挑战的强调”,在这一阶段,生态学者“越来越关注信息管理、信息加工心理学以及各种传播策略的有效性”。[28]在新的一波浪潮中,生态学者希冀通过重新强调身体、情感与环境的联系扭转数字异化,再次体现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自诞生以来以“缓解世界生态危机”为己任的学术使命和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