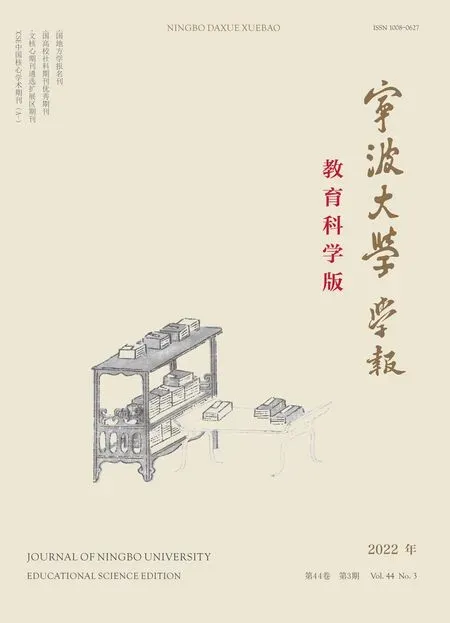探寻生命意义:测量、变化与理论基础
2022-11-22张荣伟
张荣伟
探寻生命意义:测量、变化与理论基础
张荣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108)
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个体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自身存在的意义以避免虚空。尽管生命意义具有人生哲学的韵味,但其量化研究方法已使其不再囿于哲学。生命意义测量方法主要包括自我报告法、作品法及行为表现和生活状态法等,但其主观性特点决定了自我报告法仍是最佳的测量方法。生命意义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积极自我定向获得自尊、积极生活定向获得积极生活概念,而且其变化具有年龄、文化和性别等特点。存在主义心理学、自我决断理论和存在积极心理学是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未来研究还需整合生命意义的多种测量方法,进一步厘清和验证其发展的动力及机制,以及聚焦于整合人的四种属性以理解生命意义的核心目标。概言之,探寻生命意义有助于个体开启自身无限的精神资源以防范化解心理危机,走出困境过上有意义的美好生活。
生命意义;测量;发展变化;理论基础;美好生活
人类对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的探究,始终如一,孜孜不倦,并伴随其整个生命历程。生命意义不再只是深奥的学术命题,更是人类日常生活关心的基本话题。然而,生命意义太抽象,以致不容易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生命意义是人类存在的基本需求,人们需要构建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对抗生命终将终结的焦虑。[1]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精神需求已成为人民的显性需求。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从精神层面去获得有意义的美好生活①是一条可取的路径。
然而,各学科对生命意义这种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解释,均无法令人满意。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那么“人生真谛”或“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感悟与把握。人们就越有可能走向对人、人生、生命,以及生活的真正理解,也将越有可能知道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2]从而,从快乐走向意义,再从意义走向真正的幸福。[3]
笔者认为,生命意义要从学术殿堂走向百姓生活,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需要厘清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微观层面上准确测量生命意义,以确保生命意义研究的科学性;
二是中观层面上把握生命意义发展变化规律,以明确生命意义发展的动机及其机制;
三是宏观层面上从终极目标的角度审视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以便整体上确定人生目的与方向。
因此,本文将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围绕生命意义的测量、发展变化以及理论基础等三个核心问题来探讨,为防范化解民众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以及后续的生命意义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生命意义的测量
生命意义的测量关乎其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对生命意义结构及成分的不同理解带来了其测量方法的多样性。尽管生命意义的定义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均有助于我们从科学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人生,测量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已往研究表明,生命意义主要有三类测量方法:[4]一是自我报告法,二是作品法,三是行为表现和生活状态法。
(一)采用主观的自我报告测量生命意义
生命意义是个体从其经历或经验中主观构建而成,主观性是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特征。[5]我们无法仅仅从某人的客观条件去评价其生活/生命的有意义程度。[6]当问及他人生活意义②的程度时,实质是问他们内在的生活质量,这是无法用外在条件去评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报告法是测量生命意义的最佳方法。[7][
目前,生命意义的测量工具约有59种。[8]常用的测量生命意义的自评式问卷主要包括:生活目的测验(PIL, Purpose in Life Test)、生活定向指标(LRI, Life Regard Index)、一致感量表(SOC,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生命意义问卷(MLQ,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生命意义及来源问卷(SoMe, Source of Meaning an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个人意义剖面(PMP, Personal Meaning Profile),以及用于测量状态生命意义(state meaning in life)的日常意义量表(DMS, Daily Meaning Scale)。[9]也有的研究者综合采用生命意义问卷中的拥有意义分量表(MLQ-P)和生活目的测验(PIL)中测量生命意义的4个题项,以测量感知的生命意义体验。[10]
Steger等人综合生命意义包含目标和重要性两个成分的观点,对生命意义进行界定,并得到普遍的认同。[11]他们认为,生命意义是指人们领会、理解或看到的生活意义,以及随之觉察到自己生命的目的、使命和首要目标,并依此开发了生命意义问卷(MLQ)。此量表也是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个体生命意义测评工具。该量表由10个题项构成,包括拥有生命意义(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LQ-P)和追寻生命意义(search for meaning, MLQ-S)两个维度。[11]所有的题项均采用1-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值越高表示生命意义体验和追寻生命意义动力越强。每个分量表包含5个题项,例如“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正在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样本的研究。[12]
(二)采用客观的作品评估生命意义
然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自我报告法的缺点是信效度不够,被试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意义的时候就做出评价。也就是说测量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因此,他们认为他人对被试提供的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以测量其生命意义水平更为有效。具体而言,就是问被试开放式问题,即什么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然后依此完成一篇短文;接着第三方对短文内容做客观公正地分析,以评价(量化)被试的生命意义高低水平。[13]
例如,要求被试根据下列问题写一遍1000字左右的短文,并且短文要完全覆盖所涉及的问题。问题1:请你认真体会自己生活的有意义程度,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问题2:什么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然后,由4个对此不知情的研究助理对短文进行评价,评估被试的生活有意义程度在哪个分值上,并提供短文中的相应评估依据。1表示“毫无”,6表示“中等”,11表示“十分”。在统计分值时,要先计算4位评价值之间的评估一致性系数(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并以它们的均分作为最后的分值。
(三)采用实际的行为表现和生活状态评判生命意义
也有研究者认为,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在实验室或现实生活中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包括生理指标(behavioral data, including physiological data)和实际生活状态(life outcome data)。行为表现代表着个体实际所做,而生活状态代表行为结果,它们均是更为客观的数据,测量的生态效度更高。[4]比如,在社交场合中,根据被试的语言模式:是否更多讨论自己兴趣或他人兴趣的话题,以及助人行为;或依据个体的生活状况,如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客观信息,来判断其生命意义水平的高低。
但是,实际中很少研究采用行为表现法来评估个体的生命意义。因为研究者无法很好地区分高低生命意义者之间的行为差异。即,被试的某种行为代表多大程度的高或低生命意义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行为数据有太多的疑问。行为表现法使用的前提应有个科学的高低生命意义程度评估指标体系。同样地,生活状态法也很少被单独使用。因为也没有统一的高或低生命意义生活状态指标,即无法说某种生活状态/结果(如职业、教育背景)一定属于多大程度上的高或低生命意义。比如,环卫工人也许正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而白领阶层却体验着工作和生活压力,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二、生命意义的发展变化
生命意义根源于个体对自己、环境以及自己与环境关系的理解。[11]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不同,带来其对自己与环境理解的差异。因而生命意义呈现个体差异,并随年龄增长呈一定规律性发展变化趋势。
(一)不同视角下生命意义的发展变化趋势
从毕生发展的角度看,生命意义随年龄呈现线性和非线性的发展特点。[14]Battista 和Almond认为生命意义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积极自我定向阶段(positive self regard)。[15]这个阶段出现在青少年早中期以前,其主要任务是发展积极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获得自尊(self-esteem)。积极的自我概念或自尊起着反思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与他人保持信任、温暖、开放与和谐关系等功能;第二个阶段是积极生活定向阶段(positive life regard)。这个阶段出现在青少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成年初期(emerging adulthood),其主要任务是发展积极的生活概念(life-concept),觉知生活/生命的意义(perceived meaningful life)。它保障着各种形式的生活目标实现(commitment to fulfillment of life-goals)。
Reker等人用个人意义指标(personal meaning index, PMI)量表测量分布在青少年晚期到老年阶段的2065名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发现生命意义体验的总体趋势是随年龄增加而增长。[16]Steger,Oishi和Kashdan研究生命意义(拥有意义、追寻意义)在成年初期(18-24岁)、青年(25-44岁)、中年(35-64岁)和老年(65岁以上)等四个年龄段的发展趋势。[17]他们发现,年龄较大的群体拥有生命意义体验较高,而年龄较小的群体追寻生命意义动力较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追寻生命意义动力逐渐降低,拥有生命意义体验逐渐提升。
Bodner、Bergman和Cohen-Fridel的研究支持这一结果。[18]他们进一步细化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的变化趋势:追寻意义在成年初期达到高峰,然后呈现下降趋势;而拥有意义在18岁之后开始下降,24岁左右达到低谷,然后又开始呈上升的趋势。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意义的来源渠道增多,[19]因此年长者体验到的生命意义也更多,拥有生命意义更高。
关于生命意义在青少年阶段的发展变化,横断研究发现,起初(初中阶段),我国青少年追寻意义与拥有意义水平相当,然后(高中阶段)追寻意义迅速上升,拥有意义迅速下降,呈 “剪刀差”的发展趋势,最后追寻意义显著高于拥有意义。[20]但是与其他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Kiang和Witkow的追踪研究发现,亚裔美国青少年的追寻意义随年级增长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迅速上升,拥有意义随年级增长而逐渐升高,并不是迅速下降。关于其他某个特定年龄阶段生命意义的发展趋势,鲜有研究涉及。[21]
(二)生命意义发展变化存在个体差异
从个体生命意义发展变化差异的角度看,生命意义存在群体或个体间的差异。[16]从文化角度看,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生命意义可能呈现不同的特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更关注自身的优势、自我展示以及个人成就,更注重加强让自己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各种感觉,因而表现出更高的拥有意义;然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更关注人际和谐、自身的努力及其过程,因而表现出更高的追寻意义。
例如,一项关于生命意义跨文化比较的研究表明,美国人的拥有意义高于日本人,而日本人的追寻意义高于美国人。[22]从年龄角度看,年轻者的意义来源的渠道较少,而且更容易体验与自我成长(personal growth)相关的意义,而年老者的意义来源渠道更多,而且更容易发现与社会价值相关的意义,例如人要为社会多做贡献。[23]从性别角度看,男性更容易经历生命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和存在淡漠(existential indifference),而女性更容易获得生命意义体验(experiencing meaningfulness)。
然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研究鲜少。已有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与验证。
三、生命意义的理论基础
一些人认为金钱是人的毕生追求,金钱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人坚信名誉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人确信没有饥饿、没有痛苦但拥有无限自由的“天堂”才是人的终极目标。Frankl试图用统一的法则来解释和协调这些差异。[24]他认为,人的意义意志(will to meaning,指意义是人最本质的需要)使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过上有价值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他开创性地使用“生命意义”来描述人类存在的基本动机以及人类幸福生活的核心;存在主义心理学强调,人是在关系中追寻意义的存在,人要学会与诸如孤独、痛苦、无意义甚至死亡等人生逆境和谐相处,[25]人需要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对抗这些逆境;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状态,过上有意义生活的权利和能力;[26]传统的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经历和情绪体验才是有意义生活的核心;[27]而存在积极心理学(Existential Positive Psychology, EPP),即第二浪潮积极心理学则倡导,强调积极生活定向的同时应拥抱生活的消极面。[3]
心理学家尝试从不同侧面去解释这一问题,形成关于生命意义的诸多理论观点。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历经多种心理学理论取向,主要有存在主义心理学、自我决断理论以及存在积极心理学等。[28]这三种心理学理论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意义存在,以及阐述个体的生命意义及其构建。
(一)存在主义心理学视域中的生命意义感
存在主义心理学以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为主题,即把生命意义置于心理学思考的中心。它认为,只有人的存在(being)才能将存在的意义彰显出来,存在的核心是意义感。当人的存在丧失意义感,意识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时,就不能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导致心理问题或心理危机;人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才能够超越各种分离,实现自我整合,使各种经验得以连贯和统合,将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联为一体。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有三种存在方式:一是存在于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生理环境;二是存在于人际世界;三是存在于自我世界,即自我意识世界。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自我肯定是存在的核心。在保持此核心的基础上,参与到世界中去,从中获得直接感受,进一步发展自我意识和获得存在感及意义感。[29]
(二)自我决断理论中的生命意义观
相比于其它动机理论,自我决断理论(Self-Determinant Theory, SDT)更强调的是人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对外在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满足个体与生俱来需求的欲望是行为的最核心驱动力。SDT认为,人类有理解和整合的心理动机,其中包括理解世界及世界中的自我。[30]
生命意义的形成(meaning making)建立在个体对自身生活经历和经验清晰理解的基础上。当自身的生活经历/经验能够被妥当解释,明白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即什么对自己而言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和不想要什么,生活的目的感和方向性才会出现。同时,逐渐获得自主赋予生活意义的能力,获得生活连贯性和掌控感。[31]
个体通过自我的自主选择,决定了其自身的存在。SDT认为,能力(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内在动机。[32]内在动机推动个体探索自身的内、外世界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满足了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个体就更愿意自我卷入以探索新环境,接受新挑战,学习新知识和技能,走向心理成长与健康以及自我完善与整合,从而构建了自身的生命意义,过上有意义的人生。[28]
(三)存在积极心理学中的意义建构论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生命意义的研究一直受到忽视。直到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生命意义重新回到心理学家的视野而获得重视。生命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积极心理学吸收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相信人类的优势和潜能,因而把注意点转到人类的积极心理成分与功能方面。
积极心理学认为,快乐论(Hedonia)的幸福体验是短暂的,只有实现论(Eudaimonia)幸福感才是长久的幸福体验。而存在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Wong认为,意义是积极心理学最核心的内容。而且,生命意义的获得源于个体积极地追寻与构建。[33]生活中,顺境与逆境共存,这是不可改变的生命存在事实。我们能做的是从积极情境中发现意义(finding or seeking meaning),从消极情境中构建或创造意义(making or creating meaning),获得存在的意义感。[34]
存在积极心理学关注积极面,也不忽视消极面,从而把积极心理学推向第二浪潮。
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Wong认为应对生活事件时应转变思维方式(A New Algebra for Positive Psychology),即采用新的代数运算等式“4+(-2) = 6”代替旧的等式“4+(-2) = 2”,去理解生活中的积极和消极事件对幸福的累积效应。其中,意义构建能力对生活消极面的积极转化是新的等式成立的关键。[34]
四、生命意义的研究展望
胡塞尔认为,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本源”,既不在于“物”,也不在于“心”,而在于“意义”。他认为“意义”的发现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35][36]然而,哲学层面研究的生命意义(meaning of life)和心理学层面研究的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稍有不同。尽管心理学探究的生命意义仍然具有人生哲学的韵味,但是其量化的研究方法已使其不再囿于哲学。而且,生命意义的探寻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好生活的心理内涵和实现路径。我们必须站于人生的高位,即从整个生命全程的角度去审视“人为什么而活”这个人生哲学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超越已成事实的困境。[37]
(一)整合多种方法测量生命意义
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受到挑战最多的还是其测量方法的准确性问题。[8]研究者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依此开发的不同测量工具,所测量到的生命意义存在差异。所以,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结构及成分,并开发出与文化相适应的测评工具。另外,在生命意义的测量方面,后两种的客观测量方法在实际研究中仍较少采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生命意义的主观性特点决定着自我报告法是最佳方法,其它方法只能作为补充或佐证。Tolstoy认为,有时仅仅通过个体的外在条件、外在表现或生活状态很难判断其感受的生命意义体验。[38]
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仍试图把主观和客观的测量方法相结合。在未来研究中,我们仍要尽可能整合多种方法,如结合内隐测验的方法获得内隐感知的生命意义,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生命意义测量结果。整合不同的线索能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体验。正如人们所说,看起来像鸭子,游泳也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就极可能是鸭子。[4]
(二)厘清生命意义发展的动力及机制
意义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39]人生每个阶段都需要“意义”以整合个体琐碎的生活内容或事件。因而,在不同人生阶段,个体的生命意义呈现不同的内容和发展特点。尽管已往研究已经大致勾勒出生命意义发展呈现积极自我定向和积极生活定向两个阶段、生命意义的两个方面(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总体发展趋势,以及生命意义在文化、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澄清:
第一,生命意义最早出现在什么年龄阶段?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和水平如何?
第二,依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可知,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是主客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个体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是其心理发展的动力场;而且,控制论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模型,平衡化是其动力机制。[40]
据此,是否可推演出生命意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即,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事件进行意义构建(同化和顺应的平衡化过程),使事件的意义与自己内在的一般意义相一致,满足个体自身的、以自我价值感为核心的心理需求,消除主客体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整合人的四种属性以全面理解生命意义的核心目标
从理论上看,生命意义的核心目标是要解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人生命题。厘清“人是什么”是回答这个命题的逻辑起点,从而构成了生命意义研究的三个主要理论基础。
第一,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存在的根本事实是“人乃是与其它存在体相接触并追寻意义以实现自身的存在”,即人是在关系中追求“意义”的存在。[41]从这点上看,人活着是为了“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在关系背景中自主构建而成的。
第二,然而,自我决断理论被视为是解释人类行为、发展以及幸福的基本动机理论。[26]该理论认为,自主、掌控和联结是人类的基本心理动机(需求)。而且,当这些基本心理需求被满足后,自我将不断完善与整合,自我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依此可知,人活着是为了满足这些基本心理需求。
第三,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人活着是为了幸福。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PP)的发展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PP1.0)重视人的积极情绪、优势和潜能,但忽视了人类的消极和阴暗面;第二阶段(PP2.0)同时重视人类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在第二浪潮积极心理学背景下,Wong倡导,我们应该拥抱,而不是回避消极事件,并提炼消极事件中的积极意义,从而把“坏事”变成“好事”。[33]
那么,人的追求就从快乐论的幸福过渡到实现论的幸福,最终获得真正的幸福(mature happiness)。
尽管人们仍然无法对“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但现代心理学对意义的研究成果为之画了一个范围。生命意义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追求。或许神经科学认为,生命本是无意义的;生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命意义只是大脑中负责奖励的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后出现的一种认知和体验。[42]
其实,个体生命存在及其意义解读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仅从单一角度去回答生命意义这一普遍原则性问题。人具有生物性、心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等四种属性,并且人性维度贯穿其中。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人的四种属性的整合视角,即从以人性为主线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模式来解读个体的生命意义,保持意义的无意识解构和有意识建构的动态平衡,以帮助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找到生活的方向和目标,过上有价值的美好生活。
总而言之,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是人对自身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生境遇的一种反思。人类在孜孜不倦的哲学探索中会发现自身的价值,人在哲学思考中存在。[43]人既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又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物质世界的运作法则是规则,而精神世界的运行法则是自由。人类总是期望通过金钱、名誉或权力在物质世界中获得自由,结果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其实,真正的自由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将物质世界的规则法则套用在精神世界,是人类产生心理问题阻碍幸福的根源;当然,人类也不能用精神世界的自由法则去放纵物质世界的规则生活。人的最高存在是活在精神世界中。[43]探寻生命意义是开启人类自身宝贵且无限的精神资源的一把钥匙,也是新时代人们防范化解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以通往精神性美好生活的路径。
① 根据加拿大华裔心理学家Paul Wong的观点,包含意义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mature happiness),拥有真正幸福感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Wong, 2017)。
②一般而言,生活意义、人生意义等同于生命意义。
[1] YALOM I D.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M]. Printed in the USA: Basic Books, 1980: 3-20.
[2] 高毅. 人生真谛[J]. 经理人, 2016 (10): 98.
[3] WONG P T P. Meaning-centered approach to research and therapy,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J].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2017, 45(3): 1-10.
[4] SCHLEGEL R J, HICKS J A.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eaning in life [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2017, 30(1): 26-31.
[5] HICKS J A, KING L A. Meaning in Life as a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a lived experience [J].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9, 3(4): 638- 653.
[6] KLINGER E. Meaning and void: inner experience and the incentives in people’s live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21-26.
[7] HEINTZELMAN S J, KING L A. The Origins of meaning: objective reality, the unconscious mind, and awareness [M].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3: 11-16.
[8] BRANDSTATTER M, BAUMANN U, BORASIO G D,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meaning in life assessment instruments [J]. Psycho-Oncology, 2012, 21(10): 1034–1052.
[9] STEGER M F, KASHDAN T B, OISHI S. Being good by doing good: daily eudaimonic activity and well-being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8, 42(1): 22-42.
[10]Hicks J A, King L A. Meaning inlife and seeing the big picture: positive affect and global focus [J]. Cognition & Emotion, 2007, 21(7): 1577-1584.
[11]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KALER M.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1), 80-93.
[12]CHAN W C H.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caregivers [J]. Health & Social Work, 2014, 39(3): 135-143
[13]LAMBERT N M, STILLMAN T F, HICKS J A, et al. To belong is to matter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3, 39(11): 1418-1427.
[14]ALLAN B A, DUFFY R D, DOUGLASS R. Meaning in life and work: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5, 10(4): 323-331.
[15]BATTISTA J, ALMOND R.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in life [J]. Psychiatry, 1973, 36(4): 409-427.
[16]REKER G T, PEACOCK E J, WONG P T. Meaning and purpose in life and well-being: a life-spa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87, 42(1): 44-49.
[17]STEGER M F, OISHI S, KASHDAN T B. Meaning in life across the life span: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 from emerging adulthood to older adulthood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9, 4(1): 43-52.
[18]BODNER E, BERGMAN Y S, COHEN-FRIDEL S. Do attachment styles affect the presenc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4, 15(5): 1041-1059.
[19]READ S, WESTERHOF G J, DITTMANN-KOHLI F. Degree and content of negative meaning in four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Germany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2005, 61(2): 85-104.
[20]覃丽, 王鑫强, 张大均. 中学生生命意义感发展特点及与学习动机、学习成绩的关系[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10): 165-170.
[21]KIANG L, WITKOW M R. Normative changes in meaning in life and links to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s from Asian American backgrounds [J].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5, 6(2): 164-173.
[22]STEGER M F, KAWABATA Y, SHIMAI S, et al. The meaningful lif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8, 42(3): 660-678.
[23]GROUDEN M E, JOSE P E. How do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vary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factors? [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43(3): 29-38.
[24]FRANKL V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34.
[25]CRAIG M, VOS J, COOPER M, CORREIA EA.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ies[M]//D. J. Cain, K. Keenan, S. Rubin, D. J. Cain, K. Keenan & S. Rubin (Eds.), Humanistic psychotherapies: Handbook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6: 283-317.
[26]DECI E L, RYAN R M.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 [J].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canadienne, 2008, 49(3), 182-185.
[27]SELIGMAN M E P.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therapy [M].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2: 3-12.
[28]WONG P T P.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M]. New York, N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3-22.
[29]MAY R. Existential bases of psychotherapy[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60, 30(4): 685-695.
[30]RYAN R M, DECI E L.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social,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supports for autonomy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well-being[M]// V. I. Chirkov, R. M. Ryan & K. M. Sheldon (Eds.), Human Autonomy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the psychology of agency, Freedom, and Well-Being.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45-64.
[31]WONG P T P, FRY P S.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 [J].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998(7): 187-188.
[32]DECI E L, RYAN R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M]. New York, NY: Springer US, 1985: 51-66.
[33]WONG P T P. Courage, faith, meaning, and mature happiness in dangerous times[EB/OL]. (2017-05-16) http: // www. drpaulwong. com / inpm-presidents– report-may-2017/.
[34]WONG P T P. Positive psychology 2.0: Towards a balanced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good life [J].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canadienne, 2011, 52(2): 69-81.
[35]胡塞尔. 逻辑研究[M]. 倪梁康,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11-21.
[36]叶秀山. 思·史·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16.
[37]张荣伟, 李丹. 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基于生命意义理论模型的整合[J].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4): 744-760.
[38]ROBERTS P. Tolstoy, edu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M]. Springer Singapore, 2017: 31-76.
[39]FRANKL V E. 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 (New ed.)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15-24.
[40]程利国. 发展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201-316.
[41]HEINE S J, PROULX T, VOHS K D.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6, 10(2): 88-110.
[42]包爱民, 迪克·斯瓦伯. 自杀和生命的意义——来自脑科学研究的解读[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45(4): 109-120.
[43]COTTINGHAM J. On the meaning of Life [M]. Louisville, Kentucky: Presbyterian Publishing Corp, 2004: 11-16.
A Quest for Meaning in Life: Measures,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ZHANG Rong-wei
(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Fuzhou 350108, China )
Individuals never stop exploring the meaning in lifetime. Although the explor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remains the point of philosophy of life,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has made it no longer be confined to philosophy. Currently,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meaning in life mainly includes self report, creative works,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life outcomes. However, its subjectivity decides that the measurement by self-report is still the best way. Meaning in life develops across the two stages: positive self-regard and positive life-regard that present differences in age, culture and gender in its development whil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covering existential psychology, self-determinant theor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Future research may focus on integrating various measure methods, clarifying its’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re goal of meaning in life from the humans four attribute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humans will develop their own unlimited spiritual resources against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live a decent life by improving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meaning in life; measur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ecent life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资助(2021-12-7)
张荣伟(1978-),男,福建永定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命意义、心理健康及社会心态培育。E-mail:roway2014@163.com
G40-02
A
1008-0627(2022)03-0083-09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