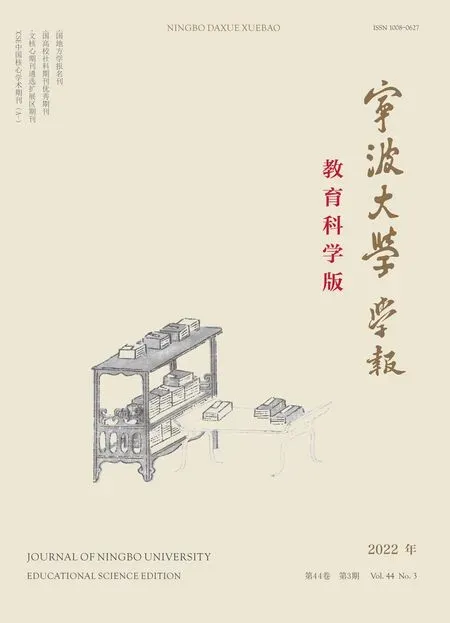“生活·实践”教育的哲学辨识
2022-11-22高伟
高 伟
“生活·实践”教育的哲学辨识
高 伟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生活·实践”教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策略或路径,更是一个思想方案。它所聚焦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教育何以在本质上是“生活·实践”的。在教育本质研究的历史与传统中,教育“真理话语”主要有形而上学-神逻辑、历史-经验逻辑、生活-实践逻辑三种解释范式。“生活·实践”教育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具有深厚的本体论意蕴。教育之所以在本质上是“生活·实践”的,是因为人的本质是生成的而非预成的,是在“生活·实践”中生成的,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生活·实践”教育理论如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观念系统,就有必要在本体论研究上着紧用力。
生活;实践;教育哲学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生活教育观念,还是实践教育观念,都不是现代教育的新发明,它们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普遍的教育观念。东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都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生活的、实践的。教育天然是生活。生活天然是教育。这种源始的统一性表现在人总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而教育不仅本身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能对美好生活有所作为。人总得生活,人总得追求美好一些、更美好一些的生活,这种认识近乎人类的本能或者类本质。在阶级的、不平等的古老中国,孔子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改变人的命运这一理念并且终其一生予以实施,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伟大的意义。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柏拉图曾专门讨论过教育问题,他说教育在最高意义上就是哲学,教育是实现良序城邦的“技艺”,哲人必须熟练地掌握这门艺术以教化人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讨论过教育问题,但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不难看出,他倾向于将教育看成是一种综合的政治、伦理实践。因此可以说,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关涉美好生活且助益美好生活的。当然,东西方对美好生活的诠解有着相当的差异。
生活教育观念、实践教育观念在近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个断裂所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几乎近现代所有教育改革都围绕着这一点进行,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教育作为生活实践活动,在古典时期至少有两个根本性特征,即它是构成生活的部分,又是生活的动力部分。作为生活的构成部分,教育不脱离生活,也不会脱离生活,它就是在生活中发生,并在生活中发展着的;作为生活的动力部分,教育念兹在兹的目的即是生活本身,它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着的,并非其它。这两个根本性的特征基本形塑了古典教育的风格与样式。问题仅仅在于,究竟何谓美好生活在理解上有着哲学的、文化的差异。然而,随着一种被称为“现代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兴起,古典教育的这种智慧被摧毁乃至消解于无形了,自此以降,生活不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也不再是实践而是材料的制作。造成此种断裂的主要有以下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建基于教育现代性之上:一是近代学校教育的专业化与专门化。近现代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它由专业人员、专业知识与专业管理组织起来,用以服从于专门的目的,这一专门的目的就是工业化所催逼的目的,即向适龄人群提供专门化的知识与能力,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这几乎就已经注定了,专业化组织起来的学校教育以知识授受与专业训练为目的,它不需要与生活联系,而是独立于生活之外。二是世俗生活的日渐形成。近代以来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关注生活,比如斯宾塞的“生活准备说”,但这里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的生活,而是世俗的、欲望的生活,与古典时期生活的源初性相比已经缺失了其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因此这里的生活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对生活的截断,而这种所谓的生活不多不少正指向于对生活的宰制,这一彻底的生活转向与第三个因素有关,即伴随着现代性而产生的个人主义。
古典时期教育目的、教育价值的思考单位由家、国、城邦、天下构成,这四种价值单位基本上决定了教育的何所由来、何所作为。在这种价值谱系中,个人没有优先性,换句话说,当且仅当个人融入到家、国、城邦、天下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其生活才有价值。在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以及基督教平等观念的孕育,个人价值逐渐变得殊异,生活意义的获得也就逐渐进入了私人领域,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可欲性则取决于个人偏好。这样一来,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生活意义的天然关系就被彻底撕裂了。外在化造成了脱节,或者它本身就是脱节,即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知识与实践脱节,这是教育现代性最为根本的特征,也是超越教育现代性最根本的动因之所在。所有现代教育改革所着力解决的,根本上讲,就是这三个问题链。
中国近代所开启的教育现代性情况更为复杂。这一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常识理性的,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因此谈不上世俗社会的兴起,它源初就是世俗性的。这一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教育现代性的特殊性。因于厚重的家国同构传统,个人的发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这一特殊性中,在西方屡受诟病的个人的发现当与超越、突破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的时候,个人价值就获得了某种微妙的积极意义。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体话语、生活叙事才小心翼翼地进入了教育视野。生活、实践在中国近现代更像是一个“隐喻”,更具有某些批判的或解放的味道,它意味着教育必须去寻找一个全新的基础,即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人的,是为了人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实践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时代以来,生活、实践教育理论更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特色教育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成为有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的标示性特征,对生活、实践的创造性诠释也作为创新中国教育话语的必要路径而被一再提及,重新获得了宏大叙事的意义。
中国教育学界对生活、实践问题的探讨,其初始动机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这些教育问题,既有教育现代性所带来的普遍问题,也有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生活实践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抱负,即它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教育本质的探索孜孜以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教育界求本质之心可以说恒久如常。这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本质主义。哲学界所反对的本质主义并非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有其本质这一认识,而是本质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如果事物的唯一绝对的本质得到认识和把握,那么一切其它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教育问题是如此复杂,如果能发现教育的本质,对于解决教育问题自然事半功倍,这也正是本质主义在中国教育学界影响如此深远的根本原因。中国教育学界历经半个世纪虽然未能实现其初心和抱负,但在探讨教育本质的过程中依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附带效果,即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教育本质研究还表明,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和对何谓好教育的追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教育的本质追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何谓好教育的追问。今天教育学界喜用的所谓“回归本真的教育”,就是要回到教育的原初意义上,回到教育的本质上来。生活实践教育既是时代性的,又是回归性的,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策略或路径,更是一个思想方案。有必要把生活实践理论视为新时代教育本质研究的一种突破与发展,它所聚焦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教育何以在本质上是生活实践的。
二、教育本质的逻辑起点与类型
本质主义虽广受责难,但仍然有着一种积极的效应,那就是它会带来清晰和专注。透过纷纭不定的教育现象揭示教育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教育学科的自我决定。教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教育的真理性知识。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执着,有两个基本的动机,一是要对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的价值究竟在哪些问题有个根本性的了解,二是希望基于这一根本性的了解以明定教育规范。前者是理性的,后者则是实践的。这两个基本的动机所指向的是这样一种教育理解,即如果教育在本质上是如此这般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如其所是地去认识,并如此这般地去实践。
然而,对教育本质认识取向的不同决定了教育本质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产生,根本上讲是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福柯的著名命题“话语即权力”即揭示了这个深刻的道理。教育本质研究,说到底是建构教育的“真理话语”。在教育本质研究的历史与传统中,教育“真理话语”主要有三种解释范式,这三种范式基于不同的逻辑起点,各自建立了、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观念系统,也正是这三种范式,构成了教育发展的观念史,形塑了对教育本质的理解。
(一)第一种范式是形而上学-神的逻辑
西方理性主义教育传统、宗教-神学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神道设教的传统均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展开的,其主要信赖的路径是本质主义和人性论。这种解释学范式首先预设教育有某一确定不疑、恒久不变的本质,而教育之所以拥有如此之本质,要么是因为人性拥有确定且恒久的本质,要么因为神义如此,人将自己交付出去以拯救自身,要么则从属于某种前设的哲学观念。这种教育哲学因为首先预设了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演绎式的思维方式。演绎式的教育哲学试图表明,如果没有首先对教育绝对本质的界定,就不会有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只能是一种盲目的想象。
所有基于形而上学-神的逻辑对教育本质的追问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先验性。先验主义致力于探寻终极的教育本质,它假定社会按照某种虚拟的契约运作,而且社会中所有个体的行为都遵循同一种理想模式。可以说,先验主义所描绘的理想主义蓝图是通过重新塑造社会基本结构来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良序社会。先验主义不是不关心人们事实上究竟能过一种怎样的生活,而是预成性地认为正是有了这种不证而明的价值,教育才有了一个不可置疑的目的。
先验主义在认识论上坚持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观点,它并不是认为教育是被某一简单要素单纯决定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大致如此),而是特别地注重夸大某一要素并对其进行极端重要的权数赋值。如此一来,影响教育的多个潜在相互冲突的要素或原则就被缩减至具有排他性的“一个”,教育的绝对本质从而教育实践的唯一模式才被确立下来。
(二)第二种范式是历史-经验的逻辑
与先验主义相反,基于历史-经验逻辑的教育哲学一方面不认为教育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本质,一方面也不认为这一本质是一种先验性的预设。基于历史—经验逻辑的教育哲学与其说关注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不如说更关注教育的功用与价值。这种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如果有本质,这种本质也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的,所谓教育本质也就是教育在因应不同的时代精神、时代要求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因此教育本质并非某种先验性的观念,而是从个人或者历史的发展经验当中能够得出来的具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换言之,对教育本质的探寻,只能在历史-经验中发生,并在历史与经验中寻找。
在历史主义看来,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是在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既是人类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工具与手段,也是人们基于历史-经验的自觉建构。教育并没有一种先验性的本质,其本质只能在历史-经验的发生变化中显现并真实地反映个体性和社会性需求的变化,所谓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教育在历史-经验中的“何所为”“何所应为”。
有必要指出,教育这种历史-经验的解释逻辑更侧重将教育的价值、意义或者本质“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将对教育的理解放置在人对世界的经验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教育的解释逻辑的确拒绝了教育的超越性维度,从而使教育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存在,但它绝对不是某种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东西,或者某种“权宜之计”,恰恰相反,历史-经验的解释逻辑显豁了教育存在的丰富性,开启了教育理解新的道路,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多元性的文化,从而世界的意义、教育的意义、经验的意义,不再仅仅从客观性上得到解释,它本身已经构成人类主动地创造世界、建构意义结构的一部分。
(三)第三个范式是生活-实践逻辑
生活-实践逻辑的解释范式与历史-经验的解释范式比较接近,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更强调在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实践的关系框架中领会教育的起源与根本价值。在这种视角下,教育既是生活的,又是实践的,或者是“生活·实践”的。教育的生活逻辑和教育的实践逻辑是并不等同的两种逻辑。教育的生活逻辑是说教育是从生活出发,以生活为本的,斯宾塞的“生活准备说”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均是在此逻辑下展开的,区别仅仅在于教育究竟应该如何满足未来生活和当下生活的需要;教育的实践逻辑一般来说是与教育的理论逻辑相对而言的,教育的实践逻辑所遵循的不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研究的“话语逻辑”而是教育实践者在具体教育情境中教育行为、教育行动的发生逻辑。教育的生活逻辑更侧重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教育的实践逻辑更侧重实践的基础性和拓展性。
但教育的生活逻辑和实践逻辑仍然是可以相容的两种逻辑,这两种理解范式具有大致相同的旨趣。首先,这两种逻辑都以现实的人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核心,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在致思逻辑上,这两种逻辑都坚持教育的批判逻辑、人学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强调生活与实践的根本性和优先性;最后,这两种逻辑也都体现了生活与实践的统一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8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教育的生活和实践逻辑才本然地统一了起来,教育的“生活·实践”逻辑才成为可能。
这三种逻辑不仅形塑了教育理解的类型,也体现了教育理解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历程表明,教育越来越贴近人在生活实践中的本质生成。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回归到人自身,回到现实的人,回到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活动。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发生并依赖人的生活实践的生成与创造。这一思想成就,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创造。
三、“生活·实践”的教育本体论意蕴
生活教育观念和实践教育观念都不是现代的教育观念,古已有之,但“生活·实践”教育观念只有建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才是可能的。事实上,哲学只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生活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32正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实践就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成为解释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内,生活与实践并非两个相区隔的范畴,而是相互联系,互为本质的。正是以此为基础,对于何谓“教育”,周洪宇指出,“生活·实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积极探索实践育人方式变革,是源于生活与实践的教育,是通过生活与实践来实施的教育,也是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2]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定义。“生活·实践”教育源于生活与实践,通过生活与实践,为了生活与实践,它以生命为源起,以生活为内容,以实践为方式,以此探索一种对教育的新理解。“生活·实践”教育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革命,即作为现代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突破,把“生活·实践”视为教育认识的来源与根据,也不仅仅是教育的一般方法论,即从生活实践出发筹划教育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教育本体论的一种可能方案。
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本体论可谓命运多舛。本体论建构与本体论批判几至并举同出。有的哲学理论坚守本体论,但在究竟何谓本体这个问题上各有进路;有的哲学理论则完全反对本体论,因其虚妄空玄。事实上,哪怕是最强烈的反对者,对于本体论问题往往是前门赶出又后门迎回,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本体论承诺”。其根本原因在于,只要哲学还是哲学,只要人类还想获得某种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只要人类还想为其活动、实践找到最终的根据、依据和理由,本体论就总会以某种面目使哲学看起来还像哲学。“生活·实践”教育观念有没有建构生活、实践的本体论呢?从目前的研究看,还没有很明确的界定。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它忽略了本体论维度,或者放逐了本体论维度,恰恰相反,只有当“生活·实践”教育观念有其本体论意蕴,“生活·实践”教育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才是可能的。也正是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生活·实践”教育如其想说明自身,证明自身,如其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观念系统,就有必要在本体论研究上着紧用力。“生活·实践”教育理论通过“生活·实践”这一概念究竟想表达什么,是个问题。为什么恰恰是“生活·实践”而不是其它?何以把“生活·实践”视为教育的根据或依据?解决此类追问的唯一正当有效的方式是在本体论意义上阐明“生活·实践”的何所由来。
笔者认为,教育之所以在本质上是“生活·实践”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密切相联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因由,也就构成了“生活·实践”教育的本体论意蕴:
(一)人的本质是生成的而非预成的
人的本质究竟是生成的,还是预成的,这几乎可以称为教育的“阿基米德点”。应答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路,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教育哲学的类型与风格。预成论的教育哲学基础是传统形而上学,而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痼疾就在于二元论,在于“分离”上。这种“分离”既有表层的分离,也有深层的分离。表层的显而易见的分离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分离;深层的分离则是真理与意见的分离、看者与被看者的分离,这种深层的分离也就是理论界纠缠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所带来的致命的教育后果,并非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庸俗陈词,而是教育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以外在本质强加于人的干涉。如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论与其“教育无目的”论对勘,便不难发现杜威因何、如何批判现代教育的弊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从根本上讲也是取法于此。
人类本质的生成性这一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得到了科学的论证。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把对象、现实和感性等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则抽象发展了主观能动性。[1]16马克思曾多次指出,他的理论出发点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这个“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看来,在“教育”之先,并没有一个抽象的人的本质,或逻各斯,教育所面对的人,就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这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才是教育的出发点,而不是人的抽象本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7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可以说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自身的拥有。对于教育而言,无疑也是一次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意味着教育从此真正“目中有人”。
(二)人的本质是在“生活·实践”中生成的
人的本质既然被认为是生成的,那么人的本质如何生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并通过人的“生活·实践”得以生成。更进一步讲,“生活·实践”的样式与品质,形塑了人的本质的品格。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在纯粹意识中,也不是在感性直观中,而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人有意识,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作为类存在物,也就是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生活·实践”形成人自身。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1]25正是通过“生活·实践”,人一方面把世界改造成了属人的世界,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无论世界还是人类自身,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因此,“生活·实践”也就是人创造自身、形塑自身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形成过程。这种“生活·实践”活动呈现出一种非常清晰的关系结构:人作为主体的出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双重对象化构成人类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人既是“生活·实践”的主体,又是其生“生活·实践”的结果,这种人类本质的双重属性意味着人的本质是不断生成、辩证发展的,而“生活·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人是以其“生活·实践”的方式存在着并生成着的。虽然“生活·实践”教育强化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形式,并在原则上遵循生活化和实践化,以提升其问题解决的针对性,但从根本上讲,“生活·实践”教育的根本旨趣仍然在于揭示教育的本然状态,即教育本质上是生活、实践。人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外在加诸人之上的东西,而恰恰就是“生活·实践”本身。没有所谓脱离生活的教育。教育脱离不了生活,正如陶行知所说的那样,“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3]学界通常所说的教育脱离了生活世界,要回归生活世界等等,不是一组命题,更像是一种“隐喻”,它只是表明教育没有按照生活的逻辑、实践的逻辑而开展。
(三)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追求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梦想贯穿教育发展始终,虽然它以不同的叙事出现,但从未断绝。然而,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建构。人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并通过感性实践活动实现了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改造。感性实践活动的全部展开过程,就是人的存在全部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实现其全面发展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人“生活·实践”中创造自身,同时也能动地创造其“生活·实践”的品格与样态。因此,对人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人通过不断地创造其“生活·实践”而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这一全面发展的所有目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活的目的。生活是自成目的的。[4]一切生活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目的不在生活之外,恰恰它就是生活过程本身。教育的目的也就是生活的目的。教育没有生活之外的目的。现代教育最深刻的危机可能就在于,它以最大的努力服务于最次要的目的,而变成了一种可以任意摆置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只是在“受教育”,但没有过一种教育生活。如果这种教育不是生活的教育,实践的教育,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受教育”。因为在这种“教育”里,人不是主体,不是自我改造的主体,只还是一个被改造的主体,或者说,只还是一个手段。
理论要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生活·实践”教育理论要能立得住,就不能仅仅在逻辑上自洽,非得经过实践的检测不可。我们当下致力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仅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实践的,其理论的普遍影响力取决于其具体的实践效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话语体系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加深教育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加深自我理解的过程。“生活·实践”教育理论,也是走在这个道路上。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 周洪宇. 继承与发展: 从生活教育到“生活·实践”教育[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3): 2-9.
[3]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第二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634.
[4]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12.
Philoso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Life Practice” Education
GAO Wei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
Life-practice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trategy or path to education, but also an ideological scheme, which theoretically focuses on the issue: why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life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studies on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he “truth discourse” of education has three interpretation paradigms: metaphysical and divine logic,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logic, and life and practice logic. The theory of life-practice education, based on Marxist philosophy, has profound ontological meaning. The reason why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life practice is that human nature is generated in life practice, rather than pre-formed. Only in life and practice can people acquire personal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research on ontology is essential to the construct of a complete educational concept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life-practice education.
life; practic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中国教育观念演进研究”(BAA210023)
高伟(1972-),男,山东泗水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哲学。E-mail: gaoweiedu@jsnu.edu.cn
G40-052
A
1008-0627(2022)03-0009-07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