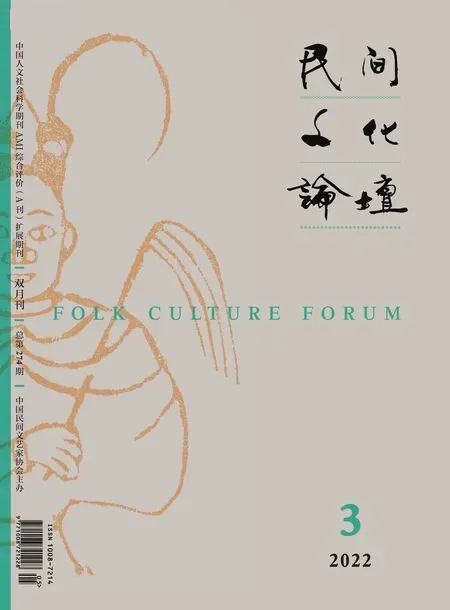亚文本、文本和语境*
2022-11-21阿兰邓迪斯谢亚文
[美]阿兰·邓迪斯 著 谢亚文 译
民俗,作为一个学科术语,在其所有不同的文类(genre)或形式被严格描述之前,永远不会被充分定义(define)。试图用民俗学材料之外的标准来定义民俗注定要失败。例如,我们不能根据讲述者是否相信某个特定的迷信是真实或有效的来准确定义迷信。如果以这种方式定义迷信或民俗的任何其他文类,问题就会随之产生,例如,如果讲述者自己都不相信打破镜子与坏运气有关,又该如何解释“打破镜子会带来七年的坏运气”呢?①从信仰或成因角度定义迷信的民俗学者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陷阱,与此相关的更多讨论参见Alan Dundes, “Brown County Superstitions,” Midwest Folklore, 11 (1961), pp.26-28.
用来定义民俗的最常见的外部标准大概是其传播方式。民俗学者经常说,民俗是“口头传统”或处于“口头传统”之中。②根据多尔森(R. M. Dorson)的观点,民俗之所以被称为民俗,是因为其必须“至少在人们的口头中存活了几代。”Bloodstoppers and Bear-walkers (Cambridge, 1952), p.7. 虽然多尔森提出“传统”一词比“口头”更为重要,但他基本上将民俗定义为口头传统文本。参见 American Folklore (Chicago, 1959), p.2, and Buying the Wind (Chicago, 1964), p.1. 及Francis Lee Utley, “Folk Literature: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J 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4 (1961), p.194.然而,许多形式的民俗根本不是口头传播的。一个男孩可能通过观看其他男孩的游戏来学习打弹珠或用石头打水漂。非口头的民俗,如手势、游戏和民间舞蹈,不能说真正处于口头传统之中。事实上,“口头”和“书面”的二分法标准,经验上说也是不成立的。书面形式的民俗有很多,主要是书面形式的民俗包括:手写的留言手册中的诗句、汽车名称、扉页上的手写韵文(如簿记员所写)、厕所涂鸦和传统信件(如连锁信)等。以传播方式来定义民俗的一个更大的障碍是,文化的许多方面的传播方式与“民俗”的传播方式完全相同。①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认为:“所有的民俗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但并非所有通过口头传播的都是民俗。”参见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JAF, 66 (1953), p.285. (问题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口头传播的”是正确的吗?)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可能通过观察他父亲的驾驶或接受言语的(即口头)的指导,或同时用这两种方法来学习驾驶拖拉机。然而,是否有民俗学者把驾驶拖拉机这件事作为民俗的例子,这点是值得怀疑的。人们还以相同的方式学习在牙刷上涂抹牙膏和在泊车咪表上投币。应该清楚的是,民俗的传播方式不能限定民俗材料,因此,它对界定民俗与其他文化材料的区别帮助有限。由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完全依赖“口头”“传统”和“传播”等术语来定义民俗能否有效地向不知道民俗是什么的人解释民俗。厄特利(Utley)最近试图解决民俗的定义问题,他的结论是所谓的操作性定义,这一定义主要包括“口头传播”的标准。②Francis Lee Utley, “Folk Literature: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JAF, 74 (1961), pp.197, 204.在另一项最近的研究中,马兰达(Maranda)认为,“传播过程是定义什么是民俗的关键。”③Elli-Kaija Köngäs Maranda, “The Concept of Folklore,”Midwest Folklore, 13 (1963), p.85.然而,这两位民俗学家都意识到,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形式都应该是定义民俗的决定性标准。必须用内部标准而不是外部标准来定义民俗。当然,注意到民俗像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被传播是没有坏处的,但应该明白,这并不能对定义民俗、使它区别于以同样方式传播的文化的其他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那么,解决民俗定义问题的关键就可以归结为尽可能详细地阐明民俗的各种形式。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有可能给民俗下一个列举式的定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在这一学科的辉煌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种文类被充分地定义。④对定义的需求也延伸到了民俗研究中最基本的术语。“版本”(version)和“异文”(variant)之间有什么区别?根据汤普森的说法,“人们习惯把一个民俗事象的各个例子称为异文”。但是“如果异文这个概念在说话者的脑海中并不重要,那么他更可能使用‘版本’这个词。”汤普森指出,“除此之外,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区别仅在于民俗学者的主观心态吗?如果研究一个谚语或民间故事的十个文本,人们就能发现版本和异文的区别。和汤普森的说法相反,文本的任何一次重述都是版本,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谚语有十个文本,那么它就有十个版本。那些或多或少偏离较典型形式的版本可以被称为异文。因此,根据上述定义,所有的异文都是版本,但并非所有的版本都是异文。很明显,困难首先在于“典型形式”的界定,其次是一个版本偏离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异文。关于汤普森的观点,参见“variant,” in Maria Leach, ed.,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Vol. Ⅱ (New York, 1950), pp.1154-1155.如果现在一个初学者问他的民俗学老师什么是谚语或什么是迷信,他往往被告知去读一本谚语或迷信的书,完成这项任务后他就会知道什么是谚语或迷信。一本关于谚语的权威著作开篇言及:“定义谚语太难了,不值得去做。”学生被告知:“判定一个句子是不是谚语,靠的是某种不可言喻的特性。”由于不可言喻,“没有任何定义能使我们确定地把一个句子认定为谚语。”⑤Archer Taylor, The Proverb (Hatboro, 1962), p.3. 这种想法与蔡斯(Richard Chase)倡导的神秘主义相似,蔡斯认为判断民俗是否真实,不需要成为“权威”(=专业的民俗学者),“当歌声响起,故事被讲述,曲调奏响,你可以通过感觉,通过头皮的刺痛,通过内心深处难以言喻的感受感知到。”American Folk Tales and Songs (New York, 1956), p.19. 人们不禁要问,未来的民俗学家是否会满足于这种民俗学研究方法?汤普森(Stith Thompson)不仅承认他无法真正回答究竟什么是母题的问题,还辩称“它们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汤普森对定义问题的态度在他对其专长——民间故事的讨论中同样明显。在指出“从来没有人试图给它下过确切的定义”之后,汤普森在为一本民俗学词典撰写民间故事的定义时说,这种缺乏基本定义的情况是“极大的便利……因为它避免了做出决定的必要性,也避免了关于特定故事可能属于某种叙事文类的冗长辩论。”①Stith Thompson, Narrative Motif-Analysis as a Folklore Method,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No. 161 (Helsinki, 1955), p.7;“Folktale,” in Maria Leach, ed.,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Vol. I (New York, 1949), p.408.
在对其他文类的讨论中也发现了同样令人遗憾的情况。尽管有大量关于民谣的学术研究,但要告诉一个从未听过民谣演唱的人究竟什么是民谣,仍然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非洲学生想知道,为什么专注于单一事件的非洲叙事歌曲不是民谣。在自然科学中,一些事物可能在有足够精密的仪器看到它们之前就被定义了,而在民俗学中,材料可能很容易被看到和听到,却始终没有被定义。为了促进对各种形式的民俗进行定义,进而最终定义民俗自身,我想提出三个层次的分析,它们中的每个层次都可以帮助完成定义的任务。②不仅在民间,民俗学界中也有习见的数字。在欧美文化中,民俗学研究和大多数学科一样,很多标准分类方案都是三分法的。民俗学者熟悉的民间叙事的分类: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的分类: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和笑话/轶事;母题分类:角色、事象和单一事件,应该不会被目前的三分法影响。对于任何特定的民俗项目,我们都可以分析其亚文本、文本和语境。只根据其中一个定义某个文类是不可能的,理想的情况是一种文类应根据以上三个方面来定义。
在大多数(包括所有具有口语性质)文类中,亚文本是包含着特殊的音素和语素的话语。因此,在民俗的口头形式中,亚文本特征就是语言特征。例如,谚语的亚文本特征包括韵律和头韵。③关于亚文本的更多讨论,参见Alan Dundes,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A Review Article,”Midwest Folklore, 12 (1962), p.36. 关于特定文类亚文本特征的具体讨论,参见Tomas A. Sebeok, “The texture of a Cheremis incantatio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25 (1962), pp.523-527; Maung Than Sein and Alan Dundes, “Twenty-Three Riddles from Central Burma.” JAF, 77 (1964), pp.72-73.其他常见的亚文本特征包括:重音、音高、语气助词、音调和拟声词。在特定的民俗文类中,亚文本特征越重要,将该文类的例子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越困难。因此,固定短语文类(语法和内容都相当固定的文类)的亚文本实际上可能排除了翻译的可能性。例如,绕口令往往非常依赖亚文本特征,尤其是在相关语言毫无干系的情况下,它们很少从一个语言社区扩散到另一个语言社区。另一方面,不同于绕口令,作为自由短语,民间故事可以更容易地跨越语言的界限。对于民俗的传播理论来说,固定短语和自由短语形式之间的亚文本区别,可能与冯叙多(C. W von Sydow)对传统的主动和被动承担者的区分一样重要。④C. W. v. Sydow, Selected Papers on Folklore (Copenhagen, 1948), pp.12-13.
由于民俗中的亚文本研究基本上是对语言的研究(虽然在民间舞蹈和民间艺术中也有亚文本的类似物),所以亚文本研究一直是由语言学者而不是民俗学者进行的。此外,由于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进步,在一些语言学者中出现了试图仅根据亚文本特征定义民俗文类(folklore genre)的倾向。⑤这方面最详尽的尝试是斯科特(C. T. Scott)未发表的德州大学博士论文“A Linguistic Study of Persian and Arabic Riddles: A Language-Centered Approach to Genre Definition,” (1963).这种倾向就是我所说的“语言学谬误”,即把对民俗的分析简化为对语言的分析。这种方法最明显的理论弱点之一是,亚文本特征很少(如果有的话),只限于某一种民俗形式。韵律可能是谚语的亚文本特征,但谜语中也有韵律,这意味着韵律在区分谚语和谜语方面的价值有限。然而,当某些亚文本特征与从文本和语境分析中获得的特征一起使用时,很可能对界定民俗文类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民俗事象的文本基本上是故事的一个版本或一次讲述、一句谚语的引用、一支民歌的演唱。出于分析的目的,文本可以被认为是独立于其亚文本的。总体而言,亚文本不可翻译,但文本却可以被翻译。谚语文本“咖啡不好煮,煮过滋味无”在理论上可以被翻译成任何语言,但押韵的亚文本特征被翻译出来的几率几乎为零。正如其亚文本可以进行结构分析一样,文本也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的结果将是对民俗结构的划定,而不是基于亚文本分析对语言结构的描述。①关于民俗学结构和语言学结构之间区别的更多讨论,参见Robert A. Georges and Alan Dundes,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AF, 76 (1963), p.117, nn.15, 18.民俗学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文本的,亚文本被留给了感兴趣的语言学者,而作为第三层次分析的语境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一个民俗的语境是该特定事象被实际运用的具体社会情境,这里有必要将语境和功能区分开来。功能本质上是建立在语境基础上的抽象概念。通常,功能是分析者对(他认为的)某一民间文学文类的用途或目的的陈述。因此,神话的功能之一是为当前的行动提供一个神圣的先例,谚语的功能之一则是为当前的行动提供一个世俗的先例(注意,在非洲司法程序中,引用谚语类似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引用案例作为法律先例)。这与某一神话或谚语被使用的实际社会情况不同。当我们说一个氏族起源的神话支持了这个氏族的自我意识时,并不是说这个神话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是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对谁以何种方式说出的。以谜语为例,可以看出功能的一般性讨论和语境的具体详细描述之间具有重要区别。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满足于只发表谜语文本,人类学者则以提及谜语的功能为荣。因此,在后者的谜语集序言中,他们可能会列出谜语的各种功能,如在求爱仪式中使用等。然而,他们也很少说明语料库中哪些谜语是用于何种功能的。②比如Thomas Rhys Williams,“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Rambunan Dusun Riddles,”JAF, 76 (1963), pp.95-110; and John Blacking,“The Social Value of Venda Riddles,”African Studies, 20 (1961), pp.1-32. 即使像这样优秀的研究,也没能提供这种具体的语境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提供了语境,却没有提及单个的文本,因此他们提及的并不是真正的语境。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记录文本(和亚文本)的同时记录语境是如此重要(请注意,如果未能收集民俗的原初母语,那就意味着亚文本不复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有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才有可能去尝试解释一个特定的文本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情况下被使用。让我用一个关于谜语的假说来说明这一点。
在最近一项关于谜语的结构研究中,一种被称为对抗性谜语的谜语被区分出来。③Robert A. Georges and Alan Dundes,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AF, 76 (1963), pp.111-118.在对抗性谜语中,两个描述性的元素似乎相互矛盾,无法在同一整体中共存,例如,“什么东西有眼却不能看?”第一个描述性元素“有眼”和第二个描述性元素“不能看”似乎不属于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或单位。只有在正式宣布答案“土豆”时,这两个独立的元素才能被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回顾谜语在求爱仪式中奇怪而广泛的使用,人们可能会猜想,这种功能的原因可能是对抗性谜语为婚姻提供了微型结构模型,因为婚姻将两个不相关的主体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异族通婚社会的文化中,新娘和新郎正如对抗性谜语中描述性元素那样并不密切相关。那么,在这里,两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家庭单位结合在一起的语境(社会状况)的结构与该语境下使用的文本的结构是一致的。不幸的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肯定或否定这一假设。在那些在求爱仪式中使用谜语的文化中,没有迹象表明对抗性谜语比非对抗性谜语使用得多。“年轻人求爱时使用谜语”或“新郎只有和他的伴郎一起解决了针对他的谜语后才有权坐在新娘身边”的说法也不能对此提供任何参考。①这些典型的说法分别来自Maung Wun, “Burmese Riddles,”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40 (1957), p.2, and Y. M. Sokolov, Russian Folklore, trans. Catherine Ruth Smith (New York, 1950), p.283.唯一的证据是文学上的例子,例如,在民间故事中,为了考验未来的新郎,他们被要求解开一个谜语(参见母题 H 551)。此外,还有一些民谣(蔡尔德编号1、46和47)中,解谜是结婚的条件。这些民俗材料里有使用对抗性谜语的证据。在《卡普塔娜·韦德伯恩的求爱之路》(Captaina Wedderburn’s Courtship)中,有一只没有骨头的鸡,一颗没有核的樱桃等等。在民间故事中,婚姻考验经常包括“不可能的任务”(母题H 1010)或“自相矛盾的任务”(母题H 1050)。矛盾任务的结构通常和对抗性谜语相似:来的时候既非裸体也不穿衣,既带也不带礼物,或既不骑行也不走路。任务的完成正如对抗性谜语的答案解决明显矛盾的描述性元素那样。
求爱谜语可能的心理学意义似乎支持这里提出的假设。长期以来,对“问题和答案”的关注或对梦中考试的恐惧被解释为性无能恐惧的传统表达。因此,强加给民间故事中的英雄的谜语是一种阳痿的威胁。在对抗性谜语中,英雄被要求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使它们保持这种状态,这两样东西(描述性元素)被谜语的提出者放在彼此旁边,只有主人公给出正确的答案,它们才能正确地结合起来。这里性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仅仅知道求爱仪式中是否使用了对抗性谜语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了解到底使用了哪种类型的对抗性谜语。例如,如果采用的是矛盾的对抗性谜语,那么本假设将得到大大的加强。在这种类型的对抗性谜语中,一对描述性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在逻辑或自然属性上构成了对第一个要素的否定。在英语谜语中,大多数缺省矛盾涉及与人体的比较。沃尔芬斯坦(Wolfenstein)在对这种类型的谜语简短而精彩的讨论中,已经提请注意阉割这一明确的主题。②See Martha Wolfenstein, Children’s Humor (Glencoe, 1954), pp.114-115.在大多数的例子中,身体的一个部分未能发挥作用: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腿不能走路,等等。如果这种类型的谜语被用于求爱仪式,那么新郎很可能会被期望消除阉割性阳痿的暗示或威胁,即通过给出正确的传统答案消除身体机能障碍的威胁。
诚然,上述假设具有高度的推测性。然而,不管对最常见的谜语功能之一的假设性解释是否有效,人们都很容易从中看到记录语境的好处或必要性。仅仅知道在这样那样的文化中谜语被用于求偶仪式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谜语被这样使用。对抗性谜语是否比非对抗性谜语用得多?如果使用对抗性谜语,哪种类型的对抗性谜语最常见?最常见的类型是缺省矛盾型吗?应该意识到,即使在没有对基本亚类型进行结构性划分的民俗文类中,单个文本的语境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被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即使收集者不知道一种谜语和另一种谜语之间的区别,但作为基本的田野调查方法,他仍然可以记录语境。
收集语境的重要性在笑话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不记录语境的情况下,记录笑话可能对历史地理学家绘制传播路径、确定认知程度和假设亚类型的发展序列有价值,但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意义不大。语境结构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讲笑话的人和听笑话的人。语境可以影响文本(也可以影响亚文本,比如一个禁忌的词汇在某种情况下会被使用,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不会被使用),这是一个常识,但实际发表的关于这种影响的具体例子并不常见,这部分源于民俗学者对未经修饰的、甚至经常是未经注释的文本的压倒性偏好。以下是1961年从印第安纳州南部一所小学院的男性院长那里收集到的笑话,可以说明观众或受众的影响。
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能做到三件事就会被释放。这三件事是用自己的左手拍打自己的右手腕、右手肘和右肩,边拍边说:“这是我的手腕,这是我的手肘”和“这是我的肩膀”。三位志愿者中的第一位走到精神医生面前轻拍自己的手腕,说:“这是我的手腕。”然而,在测试的第二部分,他错误地再次敲击他的手腕,同时说“这是我的手肘”。“很遗憾,”医生说,“你必须留在这里。”第二个人成功地敲击了他的手腕和手肘,但是当他说“这是我的肩膀”时,他敲击了他的手肘而不是肩膀。第三个人拍对了所有三个目标,并正确地识别了它们。“恭喜你,”医生说,“太好了,你马上就可以被释放了。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得这么好的?”“哦,”那人敲了敲脑袋说,“我只是用了我的屁股。”
这个笑话是在一次海军后备役会议上,一名成年男子向其他四名男子讲述的。这是美国男人试图通过讲带有性内容的笑话来向其他男人展示他们的阳刚之气的典型情境。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这个讲笑话的人说,如果他的听众中有女性,他就会随机应变换个说法,即“哦,我只是用了我的头”。在这种情况下,讲述者拍打他的屁股而不是头。我的讲述人回忆说,有一次在对(男女)混合的观众群讲这个特别的笑话时,他注意到,在讲述期间,一个女性观众皱着眉头,不自觉地扭动身体。很明显,她知道这个笑点“仅限男性”,而且她对“屁股”这个即将说出的禁忌词感到很尴尬。讲述者中断了他的笑话,向这位女士保证这个笑话不会有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观众的行为,例如面部表情,可以影响故事的讲述)。
这里的证据表明,了解语境可以解释文本和亚文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语境信息,民俗学者就会看到笑点交替出现,却不能确定它们这样出现的具体原因。语境不可能总是被猜到。
讲述者的身份和听众的身份一样关键。具体来说,就像观众的性别可以影响文本和亚文本一样,讲故事的人的性别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最近收集到的两个版本的“妻管严”故事来理解这一点。①这个故事是母题N13,丈夫们打赌他们能做妻子要求他们做的事。其英文版本参见E. M. Wilson,“Some Humorous English Folk-Tales, Part Two,”Folk-Lore, 49 (1948), pp.282-283. 最近,赫尔(Julia Hull)重印了最初发表于1840年纽约州北部的一家报纸上的版本。Winner in her article, “Wit and Humor A Century Ago,”New York Folklore Quarterly, 19 (1963), pp.56-61. 本文中的文本由贝蒂·安·亨德森夫人(Mrs. Betty Ann Henderson)1963年5月收集于堪萨斯州(Kansas)的劳伦斯(Lawrence)。
三个“妻管严”丈夫决定报复他们的妻子。因为怕老婆,他们不能真的反抗妻子,所以他们决定服从他们的妻子并完全按照她们的要求去做。
一个多月后,这三个人在一个酒吧里相聚了。第一个人说:“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一小点肉汁洒在了桌布上。我妻子说,‘来吧,把肉汁都撒到桌子上吧!’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把肉汁碗翻过来,把它们弄得满桌都是。我绝对和我妻子扯平了!”
第二个人说:“我进门的时候,门被风吹了一下,关上了。我的妻子对我喊:‘去吧,把它从合页上卸下来。’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我把那扇该死的门从合页上扯下来了。我绝对和我妻子扯平了。”
第三个人说:“我们在床上,我想和我妻子做爱,我正在胡闹,她说,‘切,别闹了!’我就切了,你们没见过那东西吧?”①1962年,我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听到的版本略有不同。第一个丈夫开车回家的时候,拐进车道时不小心轧到了一点草坪,他妻子说,“拐的好!把整个花坛都轧了吧。”第二个丈夫在躺椅上打瞌睡,他的烟不小心碰到了躺椅,把躺椅烧了一个洞。他妻子说:“烧的好!把所有的家具都烧了吧。”第三件事与本文相同,只是讲述者在讲笑话的同时,还做了一个把他的两个手握在一起的手势,好像在掩盖笑话中弄下来的东西。请注意,这个笑话和前面的笑话都很好地验证了美国笑话中三段式模式。
这个笑话是一个三十岁的男教师讲给一个二十二岁的民间文学收集者听的,这是一位已婚女性。讲笑话的时候,讲述者的妻子也在场,笑话结束后,她提出了另一种结尾:
“……我正在胡闹,我妻子说,‘切,别闹了!’(举起一只手像钟摆一样晃了晃),你怎么把这东西再安回去?”
文本变化与语境关联的心理学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男人的版本除掉了女性的生殖器,而妻子的版本则阉割了男性掠夺者。这些替代的双关语支持关于西方文化中男性和女性性行为精神分析的几个假设。然而,这里的重点是,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语境信息,即报告人的性别和关系,文本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前面已经指出,虽然亚文本特征本身不能定义民俗文类,但它们在定义民俗形式时可能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语境特征。单纯的语境并不总能定义一种文类,因为一个特定的社会情景可能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文类中的任何一个。例如,孩子们之间在争强斗胜时,一个孩子可能采用谜语、讽刺、笑话、接龙故事或游戏。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语境信息对于区分一种文类和另一种文类至关重要。其中一种情况涉及谜语或谚语。谜语和谚语都基于主题-评论的结构,这些结构往往是隐喻性的。然而,在谜语中,所指是需要被猜测的,也就是说,提出谜语的人而不是被问者知道答案。在谚语中,说者和听者都已经知道所指。沙科洛夫(Sokolov)认为,谚语到谜语的转变是语调的变化。他说:“有时只通过一个语调的变化,谚语就变成了谜语:‘没有什么伤害它,但它一直在呻吟’,在谚语中,这句话说的是伪君子和乞丐,但在谜语中,同样的话指的是猪。”②Russian Folklore, p.285.但应该清楚的是,谚语和谜语的语境不同,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亚文本(在该情况中是音调)上的区别,但主要的区别是语境。正是不同的语境造成了语调上的差异。要么是A要求B猜出谜语的所指,即猪,要么是A通过谚语向B评论B认识的某人的行为。语境是至关重要的。请看下面的缅甸语文本。
Ma thi thu kyaw thwar:
Thi thu phaw sar:
不知道的人可能从它上面走过去。
知道它的人就会把它挖出来吃掉。
作为一个谜语,其所指(答案)是马铃薯(或任何生长在地下的东西);作为一个谚语,这句话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某人对不容易发现其价值的东西一无所知的情况。在这些例子里,根据语境,这句话就是一句谚语。我的讲述者指出,这段文字作为谚语比作为谜语的作用更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如果只给出文本(特别是如果不记录语调特征),会有多大的误导性。非缅甸人是否能从文本中猜出这可能是一句谚语,这一点很值得怀疑。
语境的收集对于所有民俗文类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谚语和手势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然而,大多数的谚语集只提供文本,这就是缺乏语境的民俗收集。谚语作为民俗的固定短语文类的例子,必须用原始母语记录,这样亚文本也可以被保留下来。但是语境呢?语境和亚文本一样重要,但它几乎从未被记录。作为收集语境必要性的最后说明,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缅甸谚语。
Sait ma so: bu:
Kywè mi: to dè
这句谚语可译为:“我没生气,但水牛的尾巴更短了。”在记录了文本和亚文本之后,我们能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知道这句谚语何时以何种方式被谁使用呢?也许把谚语文本看作类似于水面之上肉眼可见的冰山是有用的。谚语所依据的内容可能是不可见的或在表面之下的,但有经验的民俗学者知道如何探究其深层内涵。换句话说,谚语可以比作艾略特(T. S. Eliot)的 “客观对应物”,因为它往往是对能唤起特定情感态度的特定情况或事件链的表达。①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New Edition (New York, 1950), pp.124-125.因此,讨论谚语而不提及谚语所唤起的东西,就像研究文学典故而不知道典故所暗指的东西一样,是没有结果的。如果有口头文学,就会有口头或本土的文学评释(literary criticism)。民俗学者简单地记录最为基本的文本,并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完成需要的所有分析(或文学评释),这是错误的。讲述者对材料的意见很少被征求,但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征求。民俗学者应该询问讲述者,他们认为材料的意义是什么。本土文学评释的收集并不妨碍民俗学者进行标准类型的分析。但除了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对克拉克默斯奇努克(Clackamas Chinook)口头文学的精彩分析外,还应该有克拉克默斯奇努克人(Clackamas Chinooks)自己的对其同样材料的分析。
关于上述缅甸谚语,显然,没说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要重要得多。事实上,纯文本对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来说几乎毫无意义。首先,就亚洲和非洲文化中的许多谚语来说,谚语是故事中的最后一句。
一个农夫到田里去耕种。他从早上一直工作到中午,在饥饿中等待妻子送来午餐。几个小时后,他不能再等了。他把拉犁的水牛的尾巴切下来,烤熟后吃了。妻子终于带着他的午餐来了,问他是不是生她的气了。他回答说:“我没有生气,但水牛的尾巴短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句谚语的含义,但是它的用途呢?这句谚语是在人们对某人轻微愤怒时使用的。换句话说即:一个人生气了,但他做好了原谅的准备。这句谚语最常在夫妻之间使用。理想情况下,收集者本人应该观察他所记录的文本的语境。然而,在实践中,通常有一个人为的语境,即信息提供者面对着收集者和/或录音机谈话。因此,专业的民俗学者有责任设法在那些他不能直接凭经验观察到的情况中引出语境。一个有用的技巧是要求讲述者创设一个适合引用该谚语的情况。遗憾的是,总体来说,民俗学者倾向于将补充数据限制于“谚语的使用地点、时间和对象”上。换句话说,要在大多数民俗学杂志上发表,只需要提供该谚语的原始文本,并说明它是1962年7月31日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从来自缅甸马圭的芒琛桑(Maung Than Sein)那里收集的。但这能告诉我们这句谚语的含义或用途吗?记录讲述者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收集的地点和日期并无不妥,但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做就记录了语境。这种最低限度的信息数据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亚文本、文本和语境都必须被记录下来。应该注意的是,亚文本、文本和语境都可以进行结构分析。在每个层面上都可以区分非位(etic)和着位(emic)单位①关于“非位”和“着位”的概念辨析和讨论,参见本专栏第二篇文章:《民间故事结构研究:从非位单位到着位单位》。——译者。语境中存在由特定文类的非位例子来填补的着位位置。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位置中,例如涉及社会抗议的语境,可以采用一些不同的文类,如笑话、谚语、手势和民歌。另一方面,一个特定的文类,例如谜语,可以填补数个不同的语境位置。这与文本的结构分析完全一致。以民间故事结构为例,文本中的着位位置可以被不同的非位单位填补,也就是说,不同的母题(母题位变体)可被用于给定的母题位上。此外,相同的母题(非位单位)也可以被用于不同的母题位(着位单位)中。②Alan Dundes,“From Etic to Emic Units in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Folktales,”JAF, 75 (1962), p.102.亚文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进行分析。
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观察。语境的变化显然可以影响亚文本的变化(例如,女性叙述者或听众可能会导致用委婉语代替禁忌词)。在对谚语的先行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亚文本结构是如何凸显文本结构的(例如,一个对称性谚语的两个部分押韵:咖啡不好煮,煮过滋味无)。③Alan Dundes,“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A Review Article,”Midwest Folklore, 12 (1962), p.37.在现行研究中,有人认为谜语文本结构可能是谜语语境结构(即求爱仪式中使用的对抗性谜语)的基础。
关于最初提出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民俗的定义问题,似乎民俗学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分析文本。文本比亚文本和语境的变化要小。就自由短语文类而言,亚文本特征对于定义这些文类可能没有什么价值。在固定短语文类的情况下,亚文本特征可能相当稳定,但它们的分布很少局限于单一文类。语境标准在定义方面的价值也同样有限。然而,各种形式的民俗的定义最好是基于所有三个层次的分析标准。因此,民俗学者把亚文本分析留给语言学者,把语境分析留给文化人类学者,可能是一个错误。周全的民俗学者应该尝试分析所有三个层次。一旦所有的文类都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严格的描述,就不再需要依赖那些取决于传播方式等外部标准的模糊定义了。此外,现在事实上被以文本为导向的民俗学者所忽视的民和俗之间的重要关系,最终可能得到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