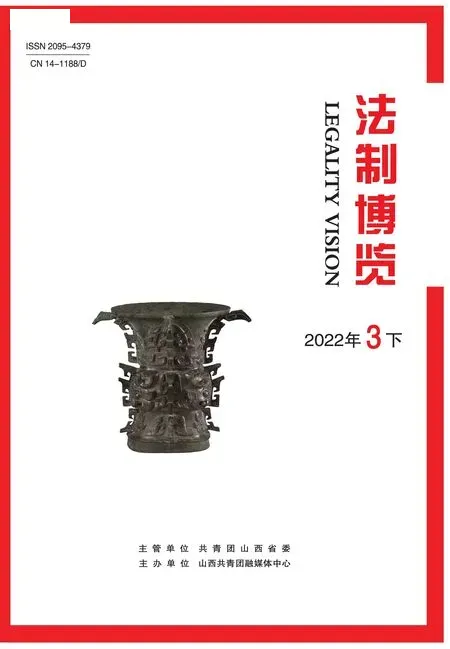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欺诈例外
2022-11-21张荣荣
张荣荣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00
201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再次将“欺诈”纳入司法协助程序中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抗辩理由,但并未对“欺诈”的内涵、范围、审查标准等做直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原《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释明了国内民事行为中欺诈的含义,但此“欺诈”非彼“欺诈”,该意见的指导价值并不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仅规定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需要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但并未明确审查标准。法律依据的缺位造成内地法院面对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法院判决请求时,从未援引过《安排》中的欺诈条款来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港案件,因此《安排》变成一纸空文。本文欲通过司法实践中案例的搜集和剖析,对前述问题予以探讨。
一、司法现状
在《安排》实施之前,实践中内地法院均以内地与香港之间不存在相互承认与执行民事判决事项的协议或者安排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本问题司法实践情况,本文对样本的裁判时间进行了限缩,只选择《安排》开始实施之后出现的样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执行中国香港欺诈”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将“审结时间”设置在2008年8月1日至2021年5月30日,并剔除掉不相关案件及重复案件,仅确定有6件有效判决,其余搜索结果是关于申请认可和执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纠纷。①见(2020)京04认港3号、(2019)最高法民申3689号、(2019)沪认港1号、(2019)沪民终196号、(2019)京04认港4号、(2016)沪01认港1号。从搜索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内地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判决的法律缺位以及替代纠纷解决模式的成熟和易操作性,当事人在实践中会尽量避免采用诉讼的方式,以期达到最终的目的。虽然相关的案例较少,但是通过对司法判例的分析,可以发现2008—2021年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从案件的整体上看,内地法院承认“欺诈”系拒绝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法院判决的抗辩理由,并未将欺诈例外列入公共政策范畴进行考虑,但是我国内地法院至今未援引《安排》中的欺诈例外条款来拒绝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法院做出的判决,《安排》中的欺诈抗辩条款被落空。②除《安排》和《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协助条约均没有将欺诈行为作为拒绝承认民商事判决的抗辩理由,而是将欺诈例外附属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二)内地法院承认外在欺诈能够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我国香港法院判决的基础,即原判决作出地法院管辖权领域的问题,但是被申请执行法院能否审查涉及原审争议实质性事项的内在欺诈事项,目前的司法判例并无体现。
(三)欺诈例外的主体范围模糊。欺诈例外涉及的主体包括有权主张判决是欺诈获得的抗辩主体以及欺诈行为的实施者,相关案例仅显示内地法院承认判决当事人可以作为主张欺诈例外的抗辩主体和欺诈行为主体,但是其他判决债务人是否有权提出抗辩、其他主体的欺诈行为能否构成欺诈抗辩制度中的“欺诈”仍不得而知。
(四)证明标准不明确。内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了欺诈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判决债务人承担,但在个案中法院仅以抗辩者未提供相关证据为由驳回欺诈抗辩请求,并未详细解释证据的范围和证明标准。在判断欺诈行为是否存在时,旧证据能否列入评判范畴?识别欺诈行为时是否需要考虑请求国的法律规定?目前法律规定依然处于空白的状态,相关的案例也并不能看出内地法院的态度。
二、欺诈例外的含义
自Abouloff v Oppenheimer & Co案后,普通法系国家一直秉承“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律原则,但目前国际上对于欺诈例外的含义并无统一的定义。英国作为最早将欺诈例外归入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抗辩事由范畴的国家,至今未明确“欺诈”的含义。仅在司法实践中,被某些法官定义为:“任何一方诉讼当事人,以恶意或不当行为来歪曲事实和欺骗法庭对案件的审查和理解的种种表现”。[1]其他普通法系国家对该定义也大都一笔带过,并未做出详尽的解释说明。此外,2019年7月定稿问世的《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将历届草案中关于“欺诈例外”的含义修正为:“通过欺诈获取的判决”,删除了对欺诈例外的程序性事项的限制,这让本就未在国际社会达成一致意见的欺诈理论更加模糊。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欺诈例外的定义大不相同,但是不难发现这些概念均包含以下内容:1.欺诈抗辩中的“欺诈”行为针对的均是法庭,目的是获取能被承认和执行的判决;2.欺诈例外的行为主体仅限于诉讼当事人和作出判决的法院,有权主张欺诈抗辩的主体应当包括所有判决债务人;3.判决债务人既可能在原审法院作出裁判结果后才发现存在欺诈行为也可能在原诉讼程序推进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
三、欺诈行为的范围
(一)管辖权欺诈与法律适用欺诈
1.合理的欺诈例外:管辖权欺诈
Maxwell v.Stewart案后,管辖权欺诈作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抗辩理由被美国法院广泛认可,并在之后的案件中不断地得到呼应。在美国La Verne v.Jackman 案中,被告以原告的证词中遗漏了某些事实、故意对信息进行改动为由抗辩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伊利诺伊上诉法院认为针对承认与执行程序的欺诈抗辩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欺诈行为使法院无法获得管辖权或者获得的管辖权存在争议,另一种是对抗性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如伪证、使用虚假文件。被告在本案中指控的正是第二种欺诈行为,然而只有在获得管辖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欺诈行为,才会受到附带攻击并妨碍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Macalpine v.Macalpine 案中,英国法院持相同的态度。本案被告认为原审法院是在受欺诈的情形下行使国际管辖权,执行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欺诈抗辩请求。针对法院管辖权问题的欺诈作为当事人抗辩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基础已经在国际上属于共识。
2.欺诈例外的探讨:法律适用欺诈
与管辖权欺诈不同,在法律适用欺诈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在英国法律适用欺诈问题被纳入公共政策例外的特殊情形,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败诉方在法庭陈述的机会被剥夺并不是欺诈设立连接点的必然结局,法庭对案件的审查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此外,法律规避适用于案件的普通审理阶段,而欺诈抗辩则适用于案件的执行阶段,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大不相同。[2]笔者认为此种欺诈情形会使败诉方在法律适用的选择结果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审理过程中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但案件的审查标准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的法律适用基础上,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终究是毒树之果,这样的判决根本无法保证正义的实现,且会鼓励诉讼当事人通过欺诈的手段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法律以获得胜诉。综上所述,我国应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原审法院管辖权或者法律适用所采取的欺诈手段均属于司法协助的抗辩理由。
(二)内在欺诈和外在欺诈
各国依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将欺诈行为进行归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的划分方式。美国法院一般仅认可外在欺诈是承认外国判决的合法抗辩理由,即剥夺一方当事人充分提出其主张或辩护的机会的欺诈。[3]Hartley & Dogauchi 报告列举了一些可以被视为外在欺诈的例子:“原告故意在错误的地址上送达令状或造成令状送达,原告故意向被告提供听证时间、地点的错误信息或任何一方试图腐蚀法官、陪审员或证人,或故意隐藏重要证据”。[4]但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深入,司法界和实践界在执行法院能否审查涉及原审争议实质性事项的欺诈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一方面,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大多数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判决领域仅对外国法院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审查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5]另一方面,外在欺诈和内在欺诈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在当事人提出涉及原审所争议的实质性事项的欺诈问题处理上,如法官受到胁迫或勒索、法庭存在政治偏见、法官与涉案标的存在利害关系等,若一刀切地否认内在欺诈作为抗辩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基础,则败诉方基本不可能从原司法系统得到公平合理的救济结果。笔者以为提高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欺诈例外抗辩的证明标准或能解决上述问题,倘若当事人提出了涉及案件争议实体的欺诈情况,执行法院应当要求抗辩当事人提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根本无法在原司法审判系统中得到公平的判决结果。通过苛加繁重的举证责任,驳回对欺诈的不充分的一般性指控,既突破外在欺诈的局限,也避免受申请法院被诟病为外国法院的“上级法院”。[6]
四、欺诈例外的证明标准
(一)证据范围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概括欺诈制度时认为,“诉讼一方当事人即使未能提交新证据……,其仍然可以欺诈作为抗辩理由”,即我国香港法院在判断“欺诈”是否成立时不仅局限于败诉方提交的新证据,同时也审查全案的证据。[7]内地《民事诉讼法》规定若存在“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或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则可以申请再审。结合上文所述,后者属于可以在受理法院公平上诉的内在欺诈,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适格证据。我国民事再审的实体审查范围广泛,并不局限于判决债务人提交的“新证据”。笔者认为判定欺诈行为是否存在必须基于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所谓“新证据”是相对而言的,是指未在庭审中进行质证过程的证据。“旧证据”已经经过原审法院的审查认定并得出判断,我国再次进行审查很容易产生不尊重和不信任外国法院判决以及违反礼让原则之嫌。
(二)证明标准
美国立法规定美国被告有责任通过“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外国判决存在欺诈行为。加拿大最高法院则要求判决债务人不仅要证明欺诈事实的存在,还要证明其在原审判程序中尽到了相当的注意义务。由此可见,普通法系国家对欺诈例外的证明标准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我国也应以内地司法实践的标准严格要求抗辩当事人,即新证据应具备证明诉讼主体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且导致债务人以及法院无法公正合理参与诉讼的高度盖然性。
五、结语
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民商事判决的自由流通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亟需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欺诈例外条款,推动国际判决的流通。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欺诈例外抗辩制度在普通法系国家已经存在了数十载,我国应当从其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立足司法实践推动制度构建,但需要注意的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属于一国之下的司法协助,参照借鉴外国经验不能墨守成规,应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司法实践的运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