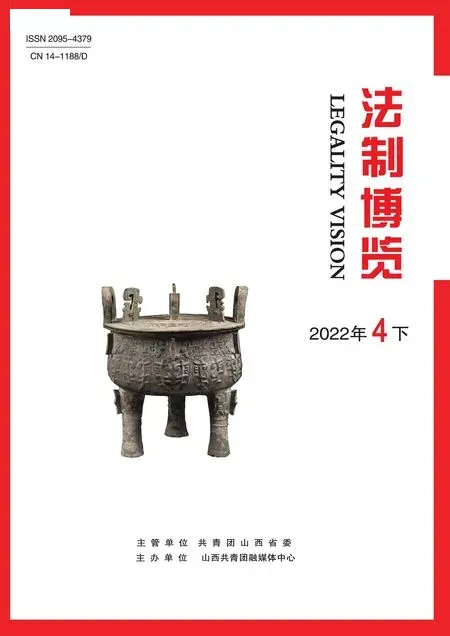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设置的合理性分析
2022-11-21冉旭
冉 旭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产业日益繁荣,网络版权侵权问题也大量出现。在现实中,著作权人一般不会将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作为被告进行追责,而是选择将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被告。所以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版权保护义务进行科学设定至关重要。在互联网发展初期,许多国家对网络版权的保护往往采用“避风港”原则。[1]该原则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通知—删除”规则,即当著作权利人认为网络服务所涉及作品侵犯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可向该网络平台提交含有特定内容的书面通知,要求删除、屏蔽或断开与该作品的链接。随着算法时代的来临,“通知—删除”规则的广泛应用导致互联网侵权通知数量快速增多,其中有不少错误通知和规则滥用的情况,也造成了版权保护效率低下、权利人维权成本增加、网络服务提供商与权利人之间利益失衡等问题。“通知—删除”规则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学界提出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履行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但目前对该义务的设置还存在不少争议,本文旨在对“通知—删除”规则的弊端与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过滤义务设置对细化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借鉴意义。
一、“通知—删除”规则的弊端
(一)版权保护效率低
该问题一方面体现在“通知—删除”规则在防止损失发生层面的滞后性。“通知—删除”规则是一种事后人工审查模式,其版权保护流程是侵权人在网络平台上实施侵权行为后,版权人发现作品被恶意传播时需主动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通知,请求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由于网络信息的高速传播,即使被侵权作品可以删除,但往往在被删除前,版权人利益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还存在通知数量激增的问题。一些规模较大的网络服务提供平台上往往每天都有大量侵权行为发生,平台必须随时接受并审核著作权人请求删除的通知,在工作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很多通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二)著作权利人损失增加
在“通知—删除”规则使用过程中,著作权利人的损失不断增加。一般而言,由独立版权人采用分散方式进行维权,其成本要远远高于建立固定的侵权防治机制集中统一维权的监督模式。网络服务平台中往往储存着大量版权内容。以中国最大的搜索门户百度为例,其网站在2015年日点击量就达到了60亿。因此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而言,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的。根据汉德公式B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假如服务对象认为其提供的网络作品未侵犯他人权利,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恢复被删除的网络作品。网络服务提供商接到书面说明后应迅速予以恢复。①《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13修订)》第十六条中规定: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由于《条例》未规定当平台错误删除作品时需承担的相应责任,导致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此外,对被错误删除作品的救济条款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乐观。由于反通知的提交程序比较繁琐、作品恢复周期较长等原因,即使反通知得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支持,恢复作品内容也需要等待两周左右的时间,许多作品会面临丧失时效性的问题。因此在“通知—删除”规则运作的前提下,网络用户被删除作品后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并不高,造成网络服务提供商与权利人间的利益失衡。 抑制网络侵权现象的关键在于平台治理。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设置版权过滤义务,能够有效打击网络盗版,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对该义务提出质疑,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 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机制属于对网络侵权行为的事前审查方式。有观点认为,设置过滤义务,禁止公民直接使用某种符号或文本发布信息或禁止其进行信息转化,可能会过多地阻止公民传播信息的自由,妨碍公民自由表达思想,这些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2] 有学者指出,该义务的设置有可能加重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负担,提高进入互联网市场的门槛。严格的责任豁免制度会使得网络服务提供商须采用版权过滤技术措施,否则将无法进入该领域。[3]因此,该义务的设置虽加强了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障,但是对运营规模较小的提供商带来过度的限制。有些网络平台流量小,侵权事件发生数量少,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带来的损失与高昂的内容过滤服务成本不相匹配,造成小型网络平台负担过重甚至经营困难。 有观点认为,该义务的设置或将带来侵犯用户隐私的风险。有学者提出,使用网络版权过滤技术会对用户网络协议的地址进行定位,并为了能够更好地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而进一步对用户进行追踪,从而侵害到用户的个人隐私。[4]当用户向网络平台上传内容时,假如网络平台预先启动过滤机制,有可能会出现网络服务商利用事先过滤的合法权利对用户的信息过度收集的现象,乃至威胁到用户的通信秘密与自由。[5] 上述几项质疑对我国不适宜设置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说服力有待商榷。本文将尝试对以上意见作出回应,以达到论证设置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合理性的目的。 首先,可设置较为宽松的版权内容过滤标准。公众思想传达并非必须依靠某种特定表达方式来完成。通常情况下,公众可将意图传达的思想进行语言或图像的重组与建构,而不必担心侵犯他人版权。一般而言,思想与表达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著作权利人通常难以论证他人使用的是其表达,而非思想。由于思想与表达之间难以区分的特性,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并不会单方面损害公众的言论自由。 其次,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是有限度的,不应将保护言论自由作为网络平台消极承担注意义务的借口。在“北京某公司与上海某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中②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76号判决书》。,被告北京某公司主张,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用户间有服务合同关系,在对用户的处理限度方面除了考虑对权利人的保护,也要考虑网络用户的言论自由、对网络空间的自由使用等。如果在无法确定用户发布内容是否侵权时贸然删除,就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法院认为,每个网络服务提供商都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在何种侵权情形下采取何种不同管理措施的具体管理规则,并向其平台的网络用户及权利人公示,保护言论自由不足以成为免责抗辩事由。在实践中,只要合理界定版权内容过滤标准的底线,内容过滤义务的设置不仅可使用户表述思想的权利得到充分保证,还可以大幅降低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更好地平衡用户与权利人的利益。 在我国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实践中可赋予不同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同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承担不同限度的侵权责任。作为平台的管理者,需采取与平台能力相适应的措施确保发布信息不侵权,[6]平台承担过滤义务的强度可根据平台的商业模式予以界定。在“韩某与北京某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①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判决书》。中,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北京某某公司的信息存储平台对韩某的作品应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而该公司并未主动履行该义务,未能积极发挥其反盗版系统的正常功能,也未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来制止某文库中侵权文档的大量传播,只是一味消极等待著作权利人提供作品侵权通知,因此被告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存在主观过错。在现实中,提供电子书、音乐检索或云文档存储等服务的网络平台往往面临更高的侵权行为发生风险,所以此类平台应承担更为严格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 另外,网络平台的服务规模也是限定平台应当承担版权过滤义务范围的一大决定性因素。对过滤义务适用主体范围的限制需充分考虑到内容分享市场中内容分配的布局,对于小型服务商,其平台中的内容不被多数公众所知悉,即使侵权作品存在于平台上,少量访问流量对作品权利的侵害可忽略不计,且依凭原有规则实施通知删除即可救济,无需再强制内容过滤义务。[7]从法理角度分析,权利对等理论也为不同网络服务提供商可根据其享有的权利来承担相应的义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只要合理界定平台义务与责任,网络版权内容过滤制度的构建不会成为网络服务提供商进入市场的阻碍。 首先,可对过滤义务发挥作用的范围进行严格界定。究竟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何种内容,才应统一被技术予以识别过滤,是一个利益权衡问题。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公共知识等机构提出,一个视频应同时符合三个条件才能被侵权过滤技术判定为侵权,一是视频画面与版权人所提交作品相互匹配,二是视频的音频与版权人所提交作品相互匹配;三是基本上全部(接近90%或更多)内容与同一版权作品的内容相同[8]。例如,在“上海某制片厂诉被告浙江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②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730号判决书》。中,法院判定,被引用作品只是作为海报背景来使用,且占海报面积较小,并未突出显示有关形象,处于适度引用范围之内。此外,该海报也未影响到原告作品的正常使用,因此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本案裁判明确了转换性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的审查判断标准,只要是合理使用的作品就不应被纳入识别过滤的范围。通过限缩事先过滤义务发挥作用的范围,可有效降低用户隐私权受到侵犯的风险。 其次,网络服务提供商在实施版权内容过滤行为前,可对用户进行相关政策的公开。网络服务提供商可在服务条款中注明在用户将作品上传到该平台时,平台将采用扫描等手段对作品内容进行审查。如用户明知该条款内容的存在仍上传其作品,即可推定为网络平台实施的内容过滤行为得到了用户默许,进而规避了平台在实施版权内容过滤行为时可能导致侵犯用户隐私权的风险。 平台时代的到来对现行的“通知—删除”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设置为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开辟了新的路径。在网络技术不断升级优化的今天,可通过有效的科技手段规避该义务的设置有可能带来问题的担忧。通过设定合理的内容过滤标准,能保证用户可在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前提下自由表达思想观点。以不同规模平台承担相应过滤义务的分配机制为辅助,能帮助网络服务提供商将过滤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有可能侵犯用户隐私权的部分亦可采取合理的规避措施。因此,建议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设置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以进一步为著作权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保护。(三)网络服务提供商与权利人的利益失衡
二、针对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质疑
(一)设置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或将限制公民言论自由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商负担加重
(三)对隐私保护带来不利影响
三、对以上几点质疑的回应
(一)标准适当不会限制言论自由
(二)根据平台情况可设置相应的义务
(三)采取合理措施规避侵害隐私风险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