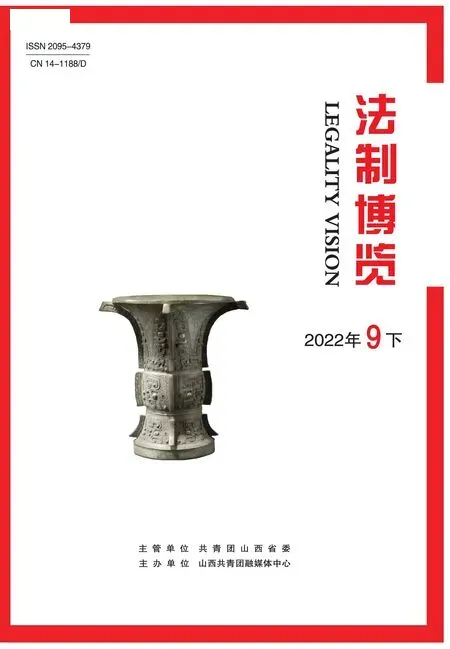法医学致伤工具判断分析
2022-11-21田帅帅
田帅帅 孙 晓
莱西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山东 莱西 266600
目前致伤工具已经成为推测死亡时间以及相关内容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同样的致伤工具作用在人体上以及作用在相同的位置上会产生不同的伤害形态。这对于法医的鉴定工作来讲是非常大的难点,所以在工作中要求检验细致。致伤工具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形态各异。由于接触面的不同,所产生的伤害也会有所不同,所以相关因素对致伤工具的推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致伤工具的推测
针对于致伤工具,一般将其分为三类:钝器伤;锐器伤;火器伤。由于中国的社会特点,一般火器伤很少,法医在鉴定时大多接触的是钝器伤以及锐器伤,所以本文主要关注致伤工具中的钝器和锐器。
(一)钝器的推测
法医学实践工作当中,钝器伤工具主要集中在伤者的头部,由于头部与球体构造非常接近,所以作用面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此时伤害形态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头颅组织结构包含头皮以及颅骨,所以头部比较容易产生创口,尤其是钝器推测中,首先应该关注头部是否有创伤。
(二)伤害的种类
钝器能够产生擦伤、创伤以及骨折等致命伤害。在进行推测时,首先应对创口展开分析,观察是否产生创口、创腔等。主要依据是参照创壁光滑程度以及规则等,可以判断是否为钝器伤害。针对伤害的种类进行判断,首先要分清伤害的类型,例如边缘很薄并属于平面,在使用工具进行快速打击后,此时容易构成锐器伤害。致伤工具是刀,在伤害他人时可能会形成皮肤擦伤,这种伤害与钝器伤害特点非常接近,也是目前伤害判断中的重点[1]。
二、案例分析
2020年5月5日18时许,在某敬老院,李某(77岁)与丁某(70岁)发生口角,丁某使用自己的拐杖击打李某头部,随即二人扭打在一起,李某用右拳连续击打丁某的左侧头面部。次日11时,丁某感到身体不适,遂到某卫生院治疗。5月8日转至某区第三人民医院治疗。5月9日再转至某市人民医院治疗。2020年5月9日,丁某在治疗中死亡。
(一)争议问题
2020年5月11日,侦查机关以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当地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理由是,丁某死因系头部受到外力作用后引起严重颅脑损伤致脑疝、重症肺炎等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检察院依法对本案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审查后认为本案存在两个疑点:一是被鉴定人丁某的左侧头部发生徒手伤后出现了右侧脑挫裂伤及颅内出血,但未见左侧冲击伤,不符合加速损伤的特征;二是病程记录显示,颅脑损伤并非进行性加重,病程中存在减轻后再加重的特征,故死亡原因是否有其他的因素参与,应进行论证。因此,以原鉴定意见书存在关于死亡原因和致伤方式的合理怀疑尚待解决,不同意原鉴定意见并退回补充侦查[2]。
根据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对原有证据进行梳理、补充。2020年10月19日,对证人就案情细节进行再次询问,证实2020年5月7日16时许,丁某在卫生院住院期间上厕所时有摔倒致枕部着地的情况。在本案中,对于两份互相矛盾的鉴定意见,通过专家辅助人帮助检察官审查技术性证据材料,继而以专家讨论会的形式就涉及的科学原理、技术方法、操作过程等进行充分的质疑和讨论,充分听取侦查人员及鉴定人员的意见并当场答复,最终,经过重新鉴定及补充鉴定,确定为徒手伤、摔跌损伤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帮助检察官理性评判、取舍、采信鉴定意见,切实提高检察公信力。
(二)重新鉴定
对此,检察院委托法医鉴定所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意见为:丁某左额颞部头皮下出血、左侧颞肌出血符合钝性机械性暴力所致(如徒手击打等);丁某右枕部头皮下出血、右侧枕骨骨缝增大符合摔跌时枕部着地所致,右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右颞叶脑挫伤符合本次外伤所致;丁某符合颅脑外伤、脑血管血栓形成致颅内出血伴肺部感染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三)组织专家论证
检察院组织法医学专家会诊确认被害人损伤机制。鉴于重新鉴定意见与原鉴定意见存在较大分歧,为了保证案件准确性,且消除侦查机关承办人员的疑惑,经检察长批准,区检察院报请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组织全市法医学专家会诊。2021年1月1日,由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专家主持,聘请政法院校、医学院校、公安及法院系统的法医学专家召开法医学专家讨论会。会上,法医学专家详细听取了案情介绍、技术性证据审查需求及各承办人意见,认真研究了两份鉴定意见,并就专业问题形成一致意见:丁某的基础疾病比较严重(如脑梗、偏瘫、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左侧头面部拳击伤以及枕部着地摔倒的两次损伤可以确定;本案减速性损伤对颅脑的损害大于加速性损伤;拳击外伤造成摔倒可能性不大[3]。
在讨论过程中,专家们认为目前各种间接证据可以证实丁某有两次外伤史,但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未能对摔跌损伤予以验证。为此,检察法医和前期两次鉴定的鉴定人员一道,再次进行法医学检验。对丁某头部损伤进行检验,并提取重要部位检材送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进行病理检验。
最终,法医病理检验与其他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证据链,确证了两次损伤作用于丁某头部的事实。法医结合病历资料、影像学检查资料等其他证据,提出审查意见,解决了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2021年2月3日,检察院根据审查意见认为,无法认定李某的殴打行为与丁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对李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四)案件启示
认真审查案件,高度重视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本案的原鉴定意见中,涉及到的专门性问题焦点在于原发性脑损伤,当暴力作用于头部时,脑颅腔内可有直线、挤压、旋转等几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本案在对技术性证据的审查过程中,检察法医发现按照原鉴定人的思路,外界暴力(徒手伤)击打丁某左颞部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出血、脑挫伤,最终死亡。此时,外界暴力作用于头部,属加速性损伤,应当出现着力点处脑损伤较重、对冲部位脑损伤较轻的特征。但尸体检验发现及损伤后的影像学检查资料证实左侧头皮及头皮下挫伤,左侧颞肌出血,左侧颞骨顶骨枕骨均无骨折,尸体检验发现与法医病理学脑损伤的形成机制原理不符合,故其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存疑。
本案借助有专门知识的人术业专攻,协助补充侦查及重新鉴定,被害人的致死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通过询问案件相关人员、勘查现场、聘请专家讨论等方式对本案被害人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充分论证后,为了寻找更有力的证据,再次进行尸体检验,最终以法医病理学检验确认了损伤的事实,为案件定性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确认识鉴定意见的“专门性”和“意见性”。从鉴定客体或对象的获得,至原理、方法的使用,及具体的操作和结果的得出、意见的形成,难免存在出错的可能性;鼓励在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引入专业力量提供帮助,弥补办案人员专门知识的短板。在本案中,对于两份矛盾的鉴定意见,通过专家辅助人帮助检察官审查技术性证据材料,继而以专家讨论会的形式就涉及的科学原理、技术方法、操作过程等进行充分的质疑和讨论,充分听取侦查人员及鉴定人员的意见并当场答复,最终,经过重新鉴定及补充鉴定为徒手伤、摔跌损伤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帮助检察官理性地评判、取舍、采信鉴定意见,切实提高检察公信力[4]。
三、法医学致伤工具伤害的形态
(一)致伤形态可作为重要判断依据
在法医学中将钝器伤害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规则,另一类是不规则。规则类伤害形成的创口也可细分为三种,一是类矩形;二是类圆形;三是类条形。通过不同的创口可以鉴定出所用工具。例如使用斧头或者是锤子等工具,通过创口可及时进行判断;类条形创口大多是属于使用棍棒之类所产生的创口;通过不规则创口可判断出是否使用砖头以及徒手类工具等。通过创口的形态进行判断,要选择有特征的创口,对致伤工具推测具有很大的价值。根据创口的形态可以对创口进行及时的判断,同时创口长度也可作为判断的标准。例如创口长度超过5cm,可判定为内条形,从而能够判断出所使用的工具为棍棒。如果创口小于3cm,属于不规则类型的伤害,在接触面上会形成不同的创口,此时要以其长度为标准进行判断。根据创口的形态进行判断,首先还需要结合皮下出血的情况以及骨折的状态展开综合判断,尤其是出现了骨折形态,线性骨折较为符合棍棒类工具所带来的伤害。棍棒类工具所导致的伤害创口会导致皮下出血较短,而此时皮下出血也成为了重要的判断依据。
(二)工具的质地
所使用的致伤工具其质地会不同,按照质地可进行推测,首先要考虑工具是否为金属类。根据其质地以及创口所带来的伤害特点进行判断,另外需要观察压痕状态。根据创伤特点首先应该观察边缘是否整齐以及轻重是否均匀,分界是否清楚等。由此可以判断工具的质地是否为金属类。另外还需重点关注伤者骨折的位置,通过挤压缘可以判断工具的质地。
(三)找到致伤方式还原事实真相
从司法鉴定、专家论证,到技术性证据审查,再到听证会,先后经历相对不起诉等阶段,皆因事实逐渐清楚。2019年5月,魏某因琐事与郭某发生争执继而斗殴,在斗殴过程中郭某右手第一掌骨骨折,后被评定为轻伤二级。基于郭某轻伤的鉴定意见和魏某家属积极赔偿取得郭某的谅解,区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对魏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魏某坚称郭某右手第一掌骨骨折不是本人持械(T型铁管)击打所致,而是郭某用拳头攻击魏某时造成,认为区检察院认定事实有误,随后向区检察院提出申诉。
(四)根据伤害情况判定致伤工具
区检察院就郭某右手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成伤机制组织专家会诊,与会专家认为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通常由直接暴力或间接暴力所致,结合案情及骨折影像学表现可排除直接暴力作用于第一掌骨基底部所致,但不能明确是何种间接暴力致伤方式(如郭某摔跌、拳击他人、被他人用拳头或T型工具殴打第一掌骨引起基底部骨折)。区检察院复查后认为,根据专家意见仍不能确认郭某右手第一掌骨骨折系自伤或他伤,故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魏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随后,魏某对区检察院的复查决定不服向市检察院申诉。市检察院受理后,经办检察官委托法医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法医针对成伤方式不清、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的情形,审查后提出委托权威鉴定机构作“骨折成伤机制鉴定”的证据补强建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鉴定意见,明确郭某右手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为间接暴力所致,并排除了间接暴力中的摔跌所致可能性,但仍不能明确是郭某拳击他人还是在特殊条件下被他人用T型工具或拳头殴打右手第一掌骨所致基底部骨折。
(五)根据伤害情况判定案情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市检察院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案件承办人展示了本案鉴定材料、当事人双方体表伤等客观证据,受承办人委托,法医技术人员从专业角度向听证员阐明第一掌骨骨折的直接、间接暴力等四种损伤类型,从生物力学角度对每种骨折的成伤机制进行分析。结合听证员的疑问,法医技术人员结合郭某、魏某互殴时的体表损伤情况,阐明了郭某第一掌骨骨折的可能成伤机制。
因听证员经讨论后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检察官再次与法医进行全案证据分析,法医技术人员从郭某手部表面损伤形态、骨折形态,结合魏某额头上有明显挫伤隆起等法医客观检查记录等,进一步明确了郭某手部可以排除“在特殊条件下被他人用T型工具或拳头殴打形成”的客观依据,阐明了郭某右手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更符合其拳击他人时造成的“拳击手骨折”的情形,分析意见最终被听证员采纳,市检察院依法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至此,这起历经两次改变定性的刑事申诉案件以绝对不起诉办结。
四、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法医学致伤工具判断进行分析,不同的致伤工具会产生不同的伤害,而对案件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案例的分析可知,司法部门的工作是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需要检验的伤者也会非常的仔细认真。通过对伤者的伤情进行判断,最终对案件进行定性。但通过分析可知,不同质地、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工具会带来不同的伤害,由于作用面的关系,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