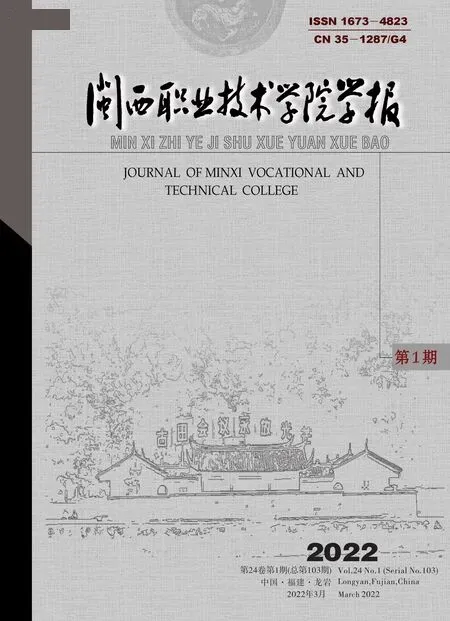创伤记忆与《古诗十九首》及其拟作
2022-11-21卢渠
卢 渠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000)
中国古代的历史以朝代更迭为常态,以记忆为经验基础。当文人士子笃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这种兴衰替换铭记于心,容易在心理保护机制作用下造成记忆的创伤。虽然他们将这段苦难经历压抑到意识层以下,但记忆仍然在发挥作用,影响当事者的行为与情绪,在相似场景中常常被重复唤起,便形成文人士子的创伤记忆。
一、东汉末年的创伤记忆
东汉末年,分崩离析的世变与传统士大夫情结产生激烈矛盾,文人的创伤记忆被唤起。
(一)作为生存信仰的士大夫情结
先秦儒家倡导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首先开创了“士志于道”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鞭策知识分子们争取凭知识、道德与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而“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训诫又让他们将这种晋升途径与事国君、定家邦、安社稷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将建立功业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最高理想。当这种途径与目标被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弟子加深阐释与推广传播时,便形成一种极其稳定且影响巨大的士大夫情结。
东汉王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继续尊奉儒术并推行发展汉武帝以来的养士政策,到了质帝刘缵时代,仅太学生就达三万多人[1]。浓郁的儒者气象更为士大夫情结增添理想化的导向,无数文人成为士大夫情结的忠实拥护者。
(二)国破家亡的世变
古代中国有一个通则,上限为国,下限为家,个人只能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一份子而存在[2]。因此,以国家为存在区间或存在本质的个人,其经受的创伤记忆实质是家国观念的创伤记忆。
东汉文人对政通人和的热切渴望与王朝兴衰相始终,他们在“受命中兴”中,执迷于致仕救难的光亮。然而,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宦官集团玩弄朝政于股掌,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十月至熹平五年(公元172年)两次党锢之祸,使士人正常的晋升途径被破坏,人才选拔方法被变相扭曲[3]。社会隐藏的不稳定因素也集中爆发,农民暴动、经济凋敝、地方割据、四夷侵叛,中央集权丧失控制统一社会的能力,王朝在分崩离析中苟延残喘。由此,国破家亡成为当时文人不得不承受的最大创痛。于是,世变的不幸经历作为一种负面切入,被强行嵌入东汉末年文人的人生体验中,造成意识深部的障碍与匮乏,创伤记忆由此而生。
(三)难以释怀的创伤记忆
一般来说,创伤在哪里,救治便在哪里[2]。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于自我保护机制,文人会本能地选择遗忘。毕竟记忆只是过往经历在人们头脑中的遗存,随着时间流逝和个体的死亡终将变得模糊以致消退[4]。但是,东汉末年的创伤记忆并不是一种个人记忆,而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难以释怀。
根据胡塞尔的意向分析,当创伤记忆作为意识的否定性因素时,既可以向情结固定,也可破坏意识的既与性而敞开某些偏向或越界的可能[2]。所谓情结固定,指的是仕途不幸、人生无依的感受刺激了士大夫精神的喷发,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屈原的殉国。但东汉末年的文人铭记苦难,走向“破坏意识的既与性而敞开某些偏向或越界的可能”,最后越陷越深,选择关照自我,将家国情怀退居身后。而作为文人群体,对创伤记忆的文学书写便成为自我关照的手段。《古诗十九首》作为创伤记忆的载体,体现文人对创伤体验的重构与再现,也成为自我救赎的最有效途径。
二、创伤记忆下《古诗十九首》的悲剧性立义
作为创伤记忆的双重受害者,东汉末年的文人无法忘却世变和失仕的创痛,持续体验创伤、积累创伤记忆。为了救赎人生疏慰自己,他们无限放大内心最原始的心理体验——对异性与致仕的渴求、对死亡与时间流逝的恐惧。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5]共同的遭遇使《古诗十九首》围绕共同的主题——创伤记忆,对当下的感知产生悲剧性立义:对自然的敏感、对情爱的焦炽、对死亡的恐惧、对政途的渴求。
(一)面对自然:节序迁移的敏感与悲叹
中国文学反复咏叹的人生短暂、光阴似箭以及悲秋伤春等意识,都深刻地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6]。《古诗十九首》的题材大多与自然风物相关,但不同于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和咏物诗,它并非专门为了怡情逸性而吟咏,而是作为起兴、用典的工具对悲观的主观情绪作出必要的渲染与衬托。
《古诗十九首》有不少关于植物的描写,以繁花凋零、秋草枯萎、白杨萧索、松柏孤苦的意象呈现,它们或与时序相关,或与生命相联,共同表达节序迁移带来的悲凉与惋惜。偶有叙写植物生命力旺盛的,如“青青园中葵”“郁郁园中柳”,但常常接着发出折芳寄远、伤时感世、功业难成的哀叹[7]。诗中写促织、玄鸟、秋蝉、缕蛤、胡马、越鸟、鸿鹊等动物,被单方面强调生命短暂、远游念归、叫声凄厉等特征,无时无刻不触发文人对生命短促、世途坎坷的感叹。甚至连变幻的风云,也是“凉风率已厉”“北风何惨栗”等感慨时节忽易的悲怆之词[7]。这些自然风物毫无例外地被关联上时间问题的具体感受,汇集形成生命短暂的完整概念,在《古诗十九首》中发出人生无常的感叹[8]。
刘勰称《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9]。实际上动植物与时节风云本身并无情感牵挂,它们不会因生命短促而悲叹,“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血”不过是文人所特有的喜忧悲欢之情的物化或对象化[7]。东汉末年,当作为创伤记忆直接承受者的文人,以人格压抑和自我生命为代价去寻找人生意义时,更是害怕青春短暂、时光消逝,因而对节序的迁移、时间的流逝特别敏感,由此给自然打下悲观的印痕,甚至把它当成舔舐伤口的疏解途径,使《古诗十九首》成为创伤记忆影响下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学作品。
(二)面对情爱:求爱不得的焦炽与无奈
社会动荡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基础,没有了依托。于是文人本能地开启自救,把希望投掷在作为情感支撑的情爱上,通过留下歌咏爱情之词走出孤独[10]。但受创伤记忆的影响,对理想破灭习以为常的文人在本质上对情爱也不完全信任,因此笔下的诗句总透露着一种求而不得的心酸,如:“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的生别离,“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不可见,“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长相思,“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的空独守[7]。这些情真意切的词句背后,笼罩着创伤记忆挥之不去的阴影,投射成为对爱情能否坚持的疑虑和无法长相厮守的无奈[11]。《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直率表达的思慕恋人、渴望情爱,并不是文人早将国破家亡的创痛抛之脑后的昭示,也不是文人自我放弃堕落滥情的体现,而恰恰是创伤记忆下应对孤独心理需要与本能反应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古诗十九首》常常借助女性视角,描写她们丰富敏锐的内心世界,着力塑造思妇这一审美形象。她们留守家中,将所有感情寄托在出游未归的丈夫身上,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等待团聚的未来。其实,这些都是士子的真实心态,不能忘情的思妇实际上就是不能走出创伤阴影的文人。反过来,对爱情的持守反证了士大夫情结的可贵,越发地让文人在遮蔽偏执中久久念着“求而不得”的感伤。
(三)面对死亡:生死皆空的恐惧与反拨
先秦儒家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实用主义激励文人专注现实事业,为奉儒守官的理想而活。但东汉末年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使理想梦境中的文人不得不面对死亡。此时,对死的意识重铸了对生的看法,文人在面对死亡中严肃地反思生、认真地设计生,最终形成“不知死,焉知生”的人生态度[6]。
《古诗十九首》中谈及死亡的主题,表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的观念[12]。“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7],昭示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不得不面对死亡。《古诗十九首》也直接描写墓、丘、坟等意象,如“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等[7]。此时,东汉末年的文人在创伤记忆影响下,在《古诗十九首》中开创面对死亡自我救治的独特方法——由痛苦反拨出及时行乐。
享乐主义是创伤记忆激发下超越死亡的策略,它否定儒家立德建功的不朽冲动,把价值的天平从社会、精神移到个体、肉体[6],趋近杨朱哲学主张的“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12]《古诗十九首》中不时有感慨死亡后提出及时行乐的片段,如“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等,直面人生本质状态的慷慨跃然纸上[7]。从死亡意识觉醒角度看,创伤记忆给文人带来的并不是“士之精神的沉沦”,而是促使他们在触底反弹后重新设计人生,并向自我本真的状态回归。
(四)面对政途:经世济民的渴求与厌弃
致仕是文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东汉末年的文人虽然对政途不再抱有希望,但难以控制自身由此带来的黯然神伤。《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洛阳作为当时的政治首都,本是“争名于朝”的胜地,但当失意文人游到此地,勾起的只是创伤记忆,于是冠带来往、衢巷纵横、宫阙壮丽的繁华都市被看成是对自身“斗酒、驽马”现实的嘲讽,全诗弥漫着忧郁悲凉的无奈。《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仕宦未达,知人者稀,音乐的共鸣刺激内心的创痛,继而发出“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感慨,想从黑暗生活中破空而去的冲动来源于内心对从仕的执念,然而现实的悲怨只能徒增忧愁。[7]
于是,有些文人在享乐主义的驱使下产生背离治国安民的价值导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7],王国维评之为“淫鄙之尤”。的确,诗中羡慕荣禄之心直白急切,不加掩饰,但从创伤记忆的角度看,如果不对自己从思想到人格做转型的双重批判,那么只能在创伤中持续煎熬。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会真选择背离“士之精神”以改变困境,“何不”的反诘、“无为”的劝谏,都只是一种宽慰,创伤记忆带来的痛苦依旧久久影响着东汉末年的文人。
三、《古诗十九首》拟作中的共情与救治
创伤记忆的作用并不止于《古诗十九首》。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与朝代更迭的刺激,使东汉末年的创伤记忆被一次次唤醒。《古诗十九首》“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后世文人极易从中受到这种共情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拟作的书写正是来源于创伤记忆的后遗症——伤痛的共情。怀才不遇、离别伤感、生命无常使隔世相望的诗人成为知己,后世文人围绕强化创伤和走出创伤这两个主题对《古诗十九首》不断扩充,创作《古诗十九首》拟作并成为离群索居之人的归属[13]。
(一)魏晋六朝时的《古诗十九首》拟作
魏晋六朝离东汉末年最近,承继《古诗十九首》遗风的诗作迭出。此时的拟作结构基本承袭原诗,题材离不开游子思妇的失意之嗟与生离死别之苦,基调悲凉消极[14]。但陆机与陶渊明不同,他们不是强化创伤,而是试着走出创伤。
陆机虽然也经历西晋政治阴影,但是他的《拟古十二首》开始探索摆脱创伤记忆的道路,在承袭旧题旧事的同时,减少悲观情感的倾注,着意在形式与语言上“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拟东城一何高》“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刻意锤炼字词,重绮靡之风,与原诗“质而不鄙,浅而能深”有天壤之别。然而,从创伤记忆的自我救治角度看,陆机搁浅情思,转向尚巧,试图通过文字雕功去解绑《古诗十九首》的伤感。[14]
陶渊明选择与陆机相反的路径,继承洗尽铅华的风神意韵,情思回曲,化为己用。表面上,《拟古九首》中的花鸟松柳意象感时事之变、叹交情不终,“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等极力挖掘死亡悲情,仍然延续《古诗十九首》的基调。实际上,陶渊明往往在挣扎之后获得委任运化的通脱,于悲凉之上获得无限超脱与旷达,直面创伤而后走出创伤,顿悟“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后,完成自我救赎。[14]
(二)唐宋时期的《古诗十九首》拟作
唐代《古诗十九首》拟作仅有三十余首[15]。但为数不多的拟作远超前人,李白《拟古十二首》和韦应物《拟古诗十二首》是其中的代表。李白反对靡丽之风,长于瑰丽的想象,为《古诗十九首》拟作增添浪漫色彩。尽管李白同样有“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孤剑难托,悲歌自怜”的创痛,但盛唐给了他求仕路上的希望与信心,推动他走出创伤。《庭中有奇树》“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几句,淡化了原诗的悲凉,令人神往。安史之乱给韦应物带来创伤体验,他侧重从现实生活表现流亡之苦而非致仕之难,拟作中的“孤鸟去不还,缄情向天末”“孤影中自恻,不知双涕零”,比原诗悲切之情更甚,创痛之感更重,表明创伤记忆在中唐氛围刺激下再次强化。[15]
宋代,拟作中的悲情又迎来转机。士大夫情结在这个朝代被文人顽强地重构起来,他们试图以一种积极切入的感知来对抗创伤记忆的负面影响,向治国安邦的理想情怀回归。于是《古诗十九首》的拟作主题不再纠结于蝇头小利、个人宦海浮沉,而是将个人与家国联系在一起,心系民瘼、孝亲忠国。连文凤的《秋怀·其八》“娟娟谁家女,轧轧弄机杼。买丝织未成,催租立当户。下机愁向人,顦顇不敢语。泣涕走深山,深山更风雨”,拟自《迢迢牵牛星》,不以相思之苦为题旨,而是叙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控诉社会战乱与徭役赋税导致民生凋敝。鱼潜拟《青青陵上柏》的《古意》“但恐气习移,古今不同才。寄言去国者,岁晚有余哀”,一改原诗个人对政途的不平之感,转为讽刺变节去国者,疾呼“士之精神”的回归。这首拟作代表部分文人探索到了走出创伤记忆的积极方式——从自我回归家国。[15]
(三)元明清时期的《古诗十九首》拟作
整个元代的《古诗十九首》拟作,几乎是悲凉基调下的自我疏解之语,语言基本承袭原诗的平淡自然,内容并无太大拓展。直到明代,《古诗十九首》拟作才迎来新一轮的创作高峰。明孝宗去世后,武宗朱厚照继位,但武宗荒嬉无度,导致宦官当政、农民起义、宁王反叛等,士大夫满腔治国热情的“求治”希望彻底破灭。加上明代以来复古之风甚盛,文人纷纷通过拟作领悟汉魏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于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创伤记忆又再次复发,在文人笔下阐释出新的面貌。
何景明的《拟古诗十八首》最为典型。从意旨上看,他吸收了原诗相思离别的主题,如“冉冉岁逾迈,念君长别离。别离在万里,道远行不归”,与何景明主张的“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拟诗原则相契合。只是他已不再被《古诗十九首》自带的悲远伤痛所桎梏,而是常常将其化为己用,加入自己的思考,“岂不策高路,高路远且艰。良无万里风,孤翼谁当援”,与原诗“何不策高足”遥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与原作者的对话,两者构成一个开放的空间[13],为创伤记忆续写现世内容。此外,也有部分文人延续士大夫情结的救治道路,在拟作中表现对高洁之志的追求和对家国情怀的深切认同。王世贞拟作《青青河畔草》中的“毁艳以自秘,羞同狭邪传”,一反原诗“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题旨,将空闺寂寞改造成恪守礼法,写女子宁可自毁容颜也不愿趋同流俗,抒发自己的高洁之志,表达绝不与狭邪同流合污的人生追求,此时原诗悲观的创伤影响已经逐渐淡化,拟作被新的思想内涵所占领。[16]
清代王夫之继承了这种新倾向。王夫之亲历明清交替、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世变,这种创伤比东汉末年的伤痛冲击力更强。拟作中双重记忆交叠,刺激了他的忠贞之心,“士之精神”得以重生,并成为对抗创伤、拯救自我的坚固力量。《拟古诗十九首·其十三》“佩之四座惊,旁徨发长叹。所欢非偶尔,白璧当自完”几句,充盈宁死不屈的气节,表明作者完成了强化创伤、直面创伤、走出创伤的救治过程。
四、结语
士大夫情结与世变的激烈碰撞产生了创伤记忆。《古诗十九首》作为一种悲情的疏解,联系着古代文人面对自我与家国的深情厚意。它使人们第一次如此集中而情绪强烈地体会时空无限中生命的伤痛,并将其发展为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之一[17]。钟惺的《古诗归》言:“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18]《古诗十九首》提供了广阔的拟作空间,后代文人群体对其大量模拟。从自己出发追寻作品的本意,在继承、强化创痛之后,最终寻回创伤介入前的士大夫情结,完成自我救赎,也完成创伤记忆与诗歌创作过程的升华。在《古诗十九首》的诗作系统中,文人从家国关照自我,又从自我回归家国,在诗作中徘徊,在时空中寻求个体生命的安置之所,在记忆中探索自我救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