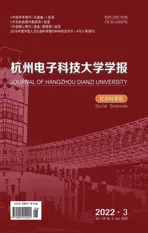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之二重性及启示
2022-11-21田世锭
田世锭,高 翔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是否具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界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确认“资产阶级时代”是由这“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构成的“简单化”社会[1]400-401。然而,尽管有诸如奥尔曼、哈维、塞耶斯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然坚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判断,但该判断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现实变化而受到了诸多质疑。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欧林·赖特及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赖特看来,坚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张是一种“灾难性失败”,因为它难以为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提供令人满意的基础[2]42。剖析赖特的“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为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提供令人满意之基础的基础。
一、“中间阶级的困扰”与“矛盾的阶级定位论”
赖特认为,“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已经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走向极端两极分化的普遍趋势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虽然自我雇佣者所占比例毫无疑问在稳定下降,但在工薪收入者中,专业和技术岗位的增加以及大型企业和政府内管理阶层的扩张(1)赖特对瑞典和美国的“经验调查”表明,“从剥削的三个维度来讲”,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瑞典和美国“都是两极分化的”(参见[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M].刘磊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0-281),但赖特却没有对其两种论断之间的矛盾作出任何解释。,至少已经使简单的两极分化结构产生了“巨大松动”[2]10。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赖特提出,“中间阶级的困扰”以及将“中间阶级”的阶级特征予以理论化,是所有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的研究所面对的“最为突出的重要问题”[2]14。
按照赖特的观点,诸如“新小资产阶级论”“新阶级论”和“中间阶层论”等,都是应对这种“中间阶级困扰”、力图将“中间阶级”的阶级特征予以理论化的结果。然而,赖特认为这些应对都不成功。
第一,“新小资产阶级论”将“非生产性劳动”领域的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人员和脑力劳动者,以及“生产性劳动”领域的管理人员、监督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全部划入“新小资产阶级”,却无法解释秘书、技术人员、管理者、政府中非生产性体力劳动者、售货员等不同类型非生产性工薪收入者,“如何在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质性”并属于“同一阶级”;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非生产性的银行雇员”与“一个自营的面包师”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2]43。
第二,“新阶级论”将各种“非无产阶级”“非资产阶级”阶层构成“一个具有其自身权利的新阶级”,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并不一样,有的是资本主义公司的管理者,直接支配工人,甚至参与控制投资;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公司中的技术雇员,处于管理阶层之外;有的是政府雇员,不可能对其他雇员实施控制,因此,难以主张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相同的地位,分享共同的剥削利益”,从而“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2]44-45。
第三,“中间阶层论”将“似乎不太适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极划分的阶级地位”都简单地标以“中间阶层”,使之“位于基本阶级关系之外”,在阶级斗争中被“夹在中间”,被迫选择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或无产阶级一边,但问题恰恰在于将“中间阶层”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关系之外”,因为,其中许多身份都是直接由“生产体系中的支配和剥削关系”构造的,且“阶层”这一名称还会遮蔽其固有“阶级的特性”[2]45。
于是,赖特提出了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这一理论以“剥削”为核心,基于“资本资产-资本剥削”“组织资产-组织剥削”“技术资产-技术剥削”的模式,确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拥有足够的资本雇用工人而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是“纯粹的剥削者”,而资本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均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纯粹的被剥削者”;“拥有足够的资本雇用工人但也必须工作”的小雇主是剥削者但不是被剥削者,“拥有足够的资本自己工作但不足以雇用工人”的“传统”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而具有技术资产和组织资产的“专家管理者”、具有组织资产的“非专家管理者”和具有技术资产的“非管理者专家”构成的“新中间阶级”既是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正是这种既是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的“在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地位”,使得“新中间阶级”处于“矛盾的阶级定位”[2]90。
赖特指出,“中间阶级”概念的核心是这些阶级地位“同时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正是这种情况说明了他们阶级利益的复杂性,并使他们处于“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定位”。按照赖特的逻辑,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应该是对“中间阶级困扰”的最好应对,也是对“中间阶级”阶级特征最好的理论化,因为这一理论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不同于“传统中间阶级”的“新中间阶级”“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既不属于资产阶级又不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2]288。
赖特说,对“中间阶级”的关注和界定就是要确立“区分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工薪收入者之间的概念分界线”[2]14。而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正是基于是否具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所有权,将“工薪收入者”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和“新中间阶级”。
二、“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之二重性
按照赖特的观点,一方面,虽然这一“新中间阶级”“既不属于资产阶级又不属于无产阶级”,但恰恰由于其“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同时分享”着资本家与工人“固有地对立着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同时“具有多重阶级的特征”并“处于多个阶级之中”[2]29;但是,另一方面,处于矛盾地位的这一“新中间阶级”之阶级性质是“派生出来的”,“以它们所隶属的基本阶级为基础”,因此,这种“矛盾的”地位“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基本矛盾”,而是“来源于这种基本矛盾”[2]46-47。这导致了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在无产阶级“主体性”和“阶级意识”问题上所具有的二重性。
具体而言,一方面,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在主观上消解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
首先,赖特以“剥削形式的依次消亡”为根据,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依次演进确认为“历史发展的总体道路”[2]119,这种单线演进序列否定了作为资本主义直接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直接消解了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虽然赖特也提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组织资产的民主化”,从而“跳过”中央集权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他紧接着便否定了这两者“同时发生的逻辑必然性”[2]119。
其次,赖特指出,“管理者/官僚”等处于“矛盾地位”的“新中间阶级”的存在充分表明,除了无产阶级以外,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其他一些阶级力量”,他们有可能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选择[2]119。这样,在上述单线式“历史发展的总体道路”之外,赖特又描绘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未来的这种“相对开放性”[2]91,虽然没有像上述单线演进序列那样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直接替代物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只是资本主义众多直接替代物中的一种,无产阶级尽管还是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但它已不再是“唯一”[2]291。如果其他阶级基于其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虽然矛盾但却必定优越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完成了其变革资本主义、实现诸如中央集权主义之类的“革命任务”,那么,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赖特以此弱化并消解了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2)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等人所说资本主义的未来“要么是毁灭性的野蛮主义,要么是人道的社会主义”(参见[美]福斯特.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J].陈喜贵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6)),似乎也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相对开放性”,但这与赖特所说的“相对开放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后,按照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只有极少数“纯粹的被剥削者”才是“无产阶级”。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数极少的纯粹弱势群体。如果仅仅依靠资本主义中的极少数“纯粹的被剥削者”来完成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理所当然是十分困难的。难怪赖特会说,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相当部分的位于这些矛盾定位中的人的合作”,要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可能”是“难以想象”的[2]291。可见,赖特将绝大多数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人们归入“新中间阶级”而排出在无产阶级之外,并以此弱化并消解了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虽在主观上消解了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性,但在客观上恰恰表明,要使无产阶级成为现实的主体,关键在于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首先,“矛盾的阶级定位论”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占总人口“相当大的比例”的“新中间阶级”处在“阶级关系内的矛盾地位”,具有“多重阶级的特征”[2]46。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在根本上仍然只是出卖劳动力的“工薪收入者”[2]14,但他们却未必认同无产阶级。而要使这些人认同无产阶级,并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者就亟需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矛盾的多重阶级性质只是“派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才是他们“所隶属的基本阶级”[2]46-47,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的利益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因为,正如赖特本人所言,“要认同一个特定的阶级”,就必须认识到自身“至少在某种可估量的意义上具有依赖于该阶级的利益”[2]256。
其次,“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断言,在阶级斗争中高层管理者更有可能站在资产阶级而不是产业工人一边[2]42。这与伊格尔顿有关高层经理人、管理者和企业高管鉴于其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更有可能认同当前体制”[3]的判断是一致的。实际上,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判断本身恰恰证明了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还表明,“一种地位的关系属性”只是决定着其占据者在关系中定位的“可能性”[2]189。这不仅彰显了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指明了其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410这说明,只要能够“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资产阶级本身都可能而且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更何况本来就属于无产阶级,只不过因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而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的“工薪收入者”呢?
最后,赖特运用“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对瑞典和美国的经验调查充分表明,“在瑞典阶级具有比美国明显更大的意识形态特征:阶级定位和阶级经验对阶级意识具有更大的影响;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两极分化;并且建立在更为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态势上的工人阶级联盟要大得多”[2]282。这意味着,瑞典的阶级结构证明了马克思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日益两极分化的判断,瑞典的无产阶级不仅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且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而美国的阶级意识态势却几乎与此相反。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瑞典的工人运动有效地将白领雇员大量地组织起来,甚至将管理层雇员的一大部分也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作为同样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工薪收入者,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比他们在组织和资格证书剥削方面的不同利益更为重要(3)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释的是,为什么瑞典的工人阶级仍然没有能够展开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反,美国的工人运动却是“无效”的,甚至大部分蓝领雇员都没有能够被组织起来,更不用说白领雇员了,以至于政党和工会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削弱工人阶级意识的行动”[2]282。
三、“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之启示
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之二重性表明,“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本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但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使我们能够从“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中获得如下几点重要启示,以便为正确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奠定基础。
第一,“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是对桑巴特、卢卡奇等人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思想的历史性呼应和实践性证明。
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1906年在其著名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中明确表明,美国之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是因为美国的雇主及生意型政治家都深知怎样在保持所有剥削的前提下,使工人保持良好的情绪而不形成关于自己真实地位的意识,但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喊出“把白人奴隶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和“解放无产阶级”等“更广泛更有力的口号”,“把广大的工人团结到这个纲领下面,并且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那么,所有迄今为止阻碍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因素“都将消失或将转向它们的反面”,社会主义在美国就很有可能出现“最迅速的发展”[4]。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写于1922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同样明确表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阶级意识而使主观条件不具备[5]。
赖特在1985年的《阶级》中所界定和阐发的“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因为在客观上证明和彰显了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故而构成了时隔60—80年以后对桑巴特、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历史性呼应。尤其是赖特运用“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对瑞典和美国的实证调查与分析充分表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践是有效的,那么,结果就是瑞典式“有效的”工人运动;反之,则是美国式“无效的”工人运动。这正是对桑巴特、卢卡奇等人思想正确性的实践性证明。虽然自赖特的《阶级》出版以来,又过去了37年的时间,但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迄今依然存在。
第二,“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是对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艰难的证明及其何以如此艰难的注解。
其实,自“前列宁的列宁主义者”[6]德·利昂,以及德布斯、鲍丁和弗雷纳等早期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塞耶斯等等,都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都在致力于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7-8]。然而,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这充分说明,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使之形成阶级意识,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一个严重困境[8]。
作为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赖特却在主观上以其“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消解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这不仅是对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艰难的一种证明,更是对其何以如此艰难的一种注解。如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都不能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现实变化的现象及其本质,不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反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加以质疑和批判(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而教条主义地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说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成为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前提。否则,马克思本人又要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又如何期望靠其自身只能形成“工联意识”的工人们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呢?列宁所说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9]363,是以能够向工人们“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9]364-365的“灌输者”为前提的。被公认为当代英美“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的奥尔曼[10]曾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的神秘化及其向家庭、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渗透(5)奥尔曼等人之所以被公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是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11]。但是,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却启发我们,缺少能够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灌输者”,或许也是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迄今依然十分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矛盾的阶级定位论”是对当代英美辩证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展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之重要性和正确性的证明。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变成了罗马卡库斯神话中“牛的主人”,他们往往只关注进入其生活的诸如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等具体的“脚印”,而看不到“阶级、阶级斗争、异化”,并因而丧失了其阶级意识[12]。正因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5]以及当代英美辩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奥尔曼[13]等人才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使无产阶级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关系整体来审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拨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迷雾,正确认识其中的阶级关系,从而正确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并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
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之二重性,一方面表明“新中间阶级”具有“多重阶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表明,“新中间阶级”的阶级性质依然来源并取决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恰恰表明,要使“新中间阶级”正确认识这种二重性以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从而正确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体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使赖特所界定的“新中间阶级”超越“专家管理者”“非专家管理者”“非管理者专家”这样的“脚印”,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关系整体,拨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迷雾并揭示其“资本主义”实质,澄清他们自己因没有“资本资产”而依然只不过是“雇佣劳动者”的根本阶级性质和阶级地位及有赖于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阶级利益,从而认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也证明,即便过程艰难,但以奥尔曼、哈维、塞耶斯等为主要代表的当代英美辩证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积极展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就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四、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大公司中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是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高级职业经理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并享有优厚的薪金、职务津贴和董事利润等,具有了与资本家高度一致的利益;蓝领工人越来越少而白领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了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14]242-243。但问题在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否如此巨大以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变得过时,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似乎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它恰恰说明,激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迄今依然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依然十分艰难。
列宁曾明确指出,“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15]463-464。本文的论述表明,列宁所说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也正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而赖特“矛盾的阶级定位论”启发我们,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履行其历史责任、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