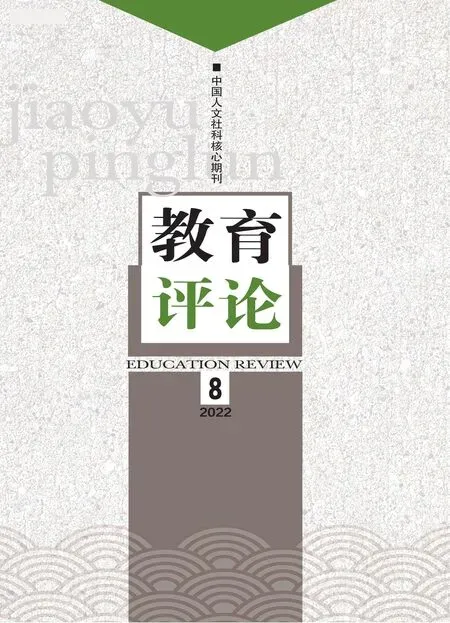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启示
2022-11-18刘慰
●刘 慰
博士制度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重要制度之一,其缘起诸侯割据、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于秦汉王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唐宋元明清时期成熟定型。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西方教育理论的引入,近代以来中国博士制度的称谓和内涵逐渐发生转型,从古代学者、尊长、官职和高级工匠的称谓到近现代的一种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考察和探讨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历史嬗变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积极作用,对推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萌芽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从古文语辞上看,“博士”二字是一个复合词,可拆分为“博”字和“士”字考释。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颜师古、许慎等人都对“博”字进行诠释,荀子和颜师古认为多闻即为“博”,许慎在《说文解字》释“大通也”即为“博”,“博”即为多闻之士,多闻才能通古今,不通古今何以辨然否?“博”与“通”“达”涵义相通。在《新书》《说苑》《白虎通义》《中论》等文献中对“士”都有详细的记载,《新书》中认为“士”必须是遵守道义的人,《说苑》和《白虎通义》中认为“士”必须是能会通古今和辨别然否之人,《中论》中认为“士”必须是能开疆拓土、遵守王法、以礼仪治国之人。从中看出“士”是一种仁义道德、知识文化和治国才能的代表,其自身具有“博”的含义和成分,否则“士”就无法胜任“博”所通达之事。正因为博学之士能守道义、通古今、辨然否、修版图、奉王法、治礼仪,所以“博士”二字从语辞上看带有政治的、学术的和文化的特征。无论是博学之士还是通达之人,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承载着政治制度中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思想中的教育职守,都被社会寄予较高期望并受到尊重,如魏文侯所言[1],“博士”乃国之尊也。因此“博士”二字从语辞上说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就不足为奇了。
从生成印迹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发展国力、称雄争霸,广招人才、礼贤下士,一些学有所长之士受到诸侯王的重用,被称为“博士”,他们通过掌握某一方面知识为诸侯王出谋划策,参与到国家政治中。鲁国、齐国、宋国、齐国、赵国等诸侯国相继出现“博士”,正如《宋书》所记载:“六国时往往有博士”[2],诸如《史记》中记载的鲁国博士公仪休、宋国博士卫平和《说苑·尊贤篇》中记载的齐国博士淳于髡,《五经异义》中记载齐国开始设置博士官,《战国策》中记载郑同被赵王称呼为南方之博士。公仪休、淳于髡、郑同、卫平等人可被称为我国第一批具有“博士”称谓的饱学之士,这些以政绩凸显才能的学者被各诸侯国尊称为“博士”,以体现其学者身份,当然也有个别诸侯国专门设置博士官职或因其学识拜官,如齐国和鲁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博士齐聚稷下学宫讲学,“博士”由一种身份称谓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制度,因此“博士制度”从生成印迹来看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毋庸置疑了。
总之,从古文语辞和生成印迹两方面来分析,我国博士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博士是对博学之士的泛称,是对知识学者群体中学识渊博的一种美誉,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名词。这一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种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印迹,其主要停留在“通古今、辨然否”和以知识渊博的优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层面。
二、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
秦代开始,“博士”正式发展为一种官职,又称“博士官”,博士制度也成为一种正式的官制。这种“博士官”作为社会上有学问和影响的士人,由朝廷较高级官员向皇帝推荐,再由皇帝下诏征辟。接受征辟的“博士官”由皇帝亲自任命为朝廷命官,享受朝廷俸禄,听命于皇帝。据史料记载,秦朝博士的主要职责有三:“辨然否”“通古今”和“典教职”,即可作为皇帝顾问参政议政,作为学者管理图籍、研究百家经典,作为吏师传道授业。在基本职责中以参政议政为先,以自身丰富的知识随时向皇帝建言献策,在国家事务上发表意见供皇帝参考,如参议帝号、禅贤、封禅、分封、礼仪庆典、占卜、作诗等,但在参政角色定位上只有建议权,且大都无实权,当然其建议不一定被皇帝所接受。秦朝博士官的俸禄只有六百石、授予铜印黑色丝带,对比其他官职俸禄二千石以上、授予银印青色丝带[3],可知秦朝博士官俸禄、官阶、身份都比其他官吏低。秦朝博士大部分人来自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这些博士是在秦统一六国前作为门客入秦。在秦统一六国后,博士成为政府委任的一种官职后,人员也逐渐增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侯生卢生相与谋曰: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从中可知秦朝博士有可能多至70人。当然这个数字也有变化,统一六国之初设置博士员数达到70人,但焚书坑儒事件之后博士数目减至30人[4],其中有姓有名者13人[5]。
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博士制度得以存续,博士为太常属官,《史记》中记载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后汉全书》中也有记载随何博士的事迹。汉初博士职责与秦相似,主要是参政议政和“兼给事中”以充当皇帝的顾问。汉武帝为政后,汉朝开始推崇儒家经典学说,重用儒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积极有为国策,在公孙弘的建议下分别以儒家经典《论语》《孝经》《孟子》《易》《礼》设置五经博士。同时,汉武帝为了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培养政治管理人才,以经学为官学,以儒家学说兴办太学,委派五经博士作为授课教师,至此太学教授成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太学学生也被称博士弟子,亦称太学生。
东汉时期,博士主要职责还是教授经学和典礼事宜,参政议政、充当皇帝顾问之制渐废,被称为学官或者礼官。汉朝博士人员数量是不断变化的,汉文帝时博士人员数量70余人[6],武帝时开始设置五经博士,博士人员数量只有5人,但到宣帝时增加12人[7]。王莽当政,在五经基础上增立《乐经》,增加博士人员,博士人员数量按每经各五人计算,六经总共达到30人[8]。东汉光武帝开始,博士人员数量为五经14人,这一设置至东汉王朝覆亡都未更改,从中推断出汉朝博士的选任方式和程序越来越规范和慎重,且逐渐形成一定的试用考察之法。武帝之前采取方式与秦王朝一致,如叔孙通因文学才能被高祖征诏为博士、贾谊在廷尉吴公举荐下被文帝征诏为博士、公孙臣因上书陈述五德始终说被文帝征诏为博士。武帝之后,博士选任采取征诏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策和明经考试,成绩优良者才被皇帝证诏,博士的选任不仅需要通明经义、名声良好、品行高尚外,还需要“试在高府”[9]。
在东汉时期,博士选拔方式又有所改变,选拨程序比西汉更加严格和规范,对选用的博士要求更高。博士官在任用前先由举荐人立“具保状”,“具保状”不仅要保证被举荐人精通儒家经学,还要道德高尚、“行应四科”[10]。无问题后再进行试用,如果在年龄[11](一般不超过50岁)、资历[12](必须曾收受过50个以上的门徒,富有教学经验)、身体状况和政治审核[13]等各方面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再由皇帝征诏。在《后汉书·朱浮传》中就记载因朱浮精通《易》《尚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学,身体无痼疾、政治清白(亲人朋友没有与邪恶之人之事交往)、行应四科,经某官出“具保状”才被皇帝征召为博士。东汉时期的博士选任由专门官员(太常卿)负责,策试以军国大事为主要内容。光武帝时期,朱浮上书建言[14]“博士”作为天下宗师,应扩大博士选任范围,提升博士的水平和质量,这也表明东汉时期博士选任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维护和加强国家统治的日常性工作。由于越来越重视博士制度,汉朝博士身份和名位不断提高,俸禄虽与秦朝相当,但有时可得到皇帝的奖赏和慰问,官阶品位也较秦朝更高、更有晋升空间,与其他官吏差距缩小。
总之,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博士”在称谓上从单纯的学术性名词转变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名词,在基本职责上从仅代表博学之士传道授业到参政议政、藏书授课、制礼试策,在社会功能上从只具有教化育人到依政治而生存,博士制度正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步形成并完善。在这一时期,博士制度与儒家经义相结合,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正式进入中国历史,为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服务。
三、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博士制度历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统治政权更迭频繁,官学教育机构的设置兴废无常。这一时期的博士在内涵、类别、职责和选任方式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博士制度的内涵方面,此时的“博士”已被赋予“师傅”的含义,在《魏书》和《北史》中都有相关记载,如《魏书》中渔阳鲜于制止李业兴驱逐羌博士,是因为羌博士曾作为师傅传授他技艺,还如《北史》中北齐宣帝要杀王昕,杨愔为其说情,是因为王昕作为他的师傅教授他才能。这种“师傅”类似于向民间从事某种专业和技艺学习的老师,无需官方正式任命,“博士”称谓的使用范围也开始从政府到民间。在“博士”的类别和官学教育机构的设置方面,随着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为适应门阀士族政治和皇权统治的需要,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官学教育,官学教育机构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西晋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北朝在太学和国子学基础上还增设了皇宗学、四门学、中书学,随之产生了国子博士、中书博士、皇宗学博士、四门博士等新称谓的学官博士,他们因教授对象的等级不同,其官阶品级也不相同。“太学博士”在这一时期与汉朝相同,都是因太学的成立而配置的教师,但太学的规模和太学博士、太学生的人员数量因朝廷的重视有了较大的增幅。在《晋书》中记载,魏晋两朝博士人员数量达到19人,东晋刚建立时后减至9人,元帝时为11人后又增至16人[15]。《南齐书》记载西晋初太学生达到3000人[16],而《宋书》记载晋武帝时期太学生达到7000人[17]。
同时,太学规模的扩大和太学生的扩招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学生“猥杂”[18]和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形下,晋武帝在太学的基础上另设国子学,在国子学里设置国子祭酒和博士两人。另外,国子学招生标准相比太学而言,有较高的要求和一定的限制,“贵游子弟”[19]和“第五品以上”[20]才能入国子学。北魏元明皇帝时开始设置“中书学博士”,这是“中书学博士”最早记载,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21]。但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官制改革时,北魏朝廷又将中书学改为国子学,国子学和中书学的转换,不仅仅只是名称的变化,更反映出北魏少数民族在不断学习汉族政权先进的官僚和教育制度,在国家管理和教育文化方面逐渐汉化。北魏政权为了加强国家统治和民族融合,要求皇室和贵族成员积极主动地向汉族政权学习,进一步汉化和提升文化水平,文明太后专门为皇室和贵族成员专门设置 “学馆”和选任“师傅”[22],这里设置的“学馆”就是皇宗学,选任“师傅”就是“皇宗学博士”。四门学是在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在国子祭酒刘芳的建议下专门为寒族士子创立的教育机构,其仿照三代郊外小学之制而设立的。《北齐书》卷中记载邢峙和权会曾担任过“四门学博士”,“四门学博士”与“皇宗学博士”相对应,是封建等级制度在教育方面的体现。这些不同中央官学机构,虽然由于教育对象身份的不同而称谓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传授经典知识、教导教育学生、培养治国人才。
同时,在这一时期,统治者更加注重对专科人才的培养,专精一行一艺的“博士”官职纷纷设立,这也直接导致博士设置和类别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是否由朝廷任命分为官方博士和民间博士,按是否以教学为目的分为学官博士和非学官博士,官方博士和学官博士跟以往相同主要说得是五经博士,民间博士和非官学博士大量出现,如律博士、太医博士、算生博士、仙人博士、书法博士等。 三国魏明帝始设律博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博士都隶属于廷尉[23]。太医博士始设于北魏,专门培养保健人员和传授医学知识的官员,官阶从七品下[24]。算生博士是在北魏太武皇帝时设立,殷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算生博士。北魏时期太祖因信奉老子,专门设置仙人博士,专掌道教和炼丹药、辟穀求仙等事宜[25]。书法博士在西晋武帝时设立,以钟繇和胡昭的章程书为教习内容[26]。
“博士”的类别和官学教育机构的设置变化也导致其职责和选任方式发生微妙变化,两晋时期博士职责主要有三[27]:一为“应对殿堂”,即皇帝顾问;二为“参训国子”,即给国子学生授课;三为“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即以祠曹、仪曹和太常的身份负责祭祀和礼仪活动。纵观魏晋南北朝,博士职责也主要涵盖这三项,当然不同的朝代某项职责或中断、或削弱、或加强。无论哪一个官学机构,博士都学识渊博、德才兼备,作为皇帝顾问参政议政,这是自秦始皇以来博士最主要的职责。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博士作为皇帝顾问参政议政的职责与汉朝一样逐渐削弱,博士在朝廷上“人微言轻”,其主要职责开始转向传授知识、弘扬儒术的学官,在官学教育方面,博士们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诸多努力。当然博士在制定礼仪和参与祭祀活动的职责上比以往更明确规范,新设“太常博士”这一官职专门掌“礼仪祭祀”。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士的选任方式主要有举荐、征辟和他官迁转三种,与汉朝对于征召的博士有着明确的诸如德行、身体状况、年龄和政治审核等限制条件不同,这一时期的博士征召未见有如此明确和严格的标准,其选任要求较为宽松,对于征辟、举荐的人员只要身负才学、能为国家和帝王所用即可。虽然在曹魏明帝时曾明确地要“高选博士”[28],要求博士一职必须由精通儒学的侍中或常侍者以上官员担任,但很多学有所长、真才实学的儒者为避祸而对朝廷学官“征而不就”,对“高选博士”这一具有身份和资历的要求就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实施。博士可由高级官员推荐,也可由皇帝召见策试合格者而授予官职,如《梁书》记载吴郡朱异由五经博士明山宾举荐为太学博士、精通明经对策的南阳刘之遴由吏部尚书王瞻举荐成为太学博士。举荐具体可详细分为三类:一类为以秀才和孝廉形式举荐,北魏裴佗被举荐为秀才时,因其成绩优异被任为中书博士;第二类为州郡长官应诏向朝廷举荐,北魏邢栾因文才干练,州郡上表拜为中书博士;第三类为高级官员举荐,北魏时期,当朝任事李冲因欣赏崔亮的才能和志气,举荐其为中书博士。征辟主要是对品行出众、德才兼备的学者,由朝廷征召为博士,北魏张僧浩因涉猎群书,学识渊博有德行、有才能被征召为国子博士。他官迁转也是魏晋南北朝时博士的主要来源,他官迁转具体可详细分为两类:一类为任职升迁,从低级官职升迁到博士官职,在任内时间长有所为,北魏李琰之一开始只是随侍中李彪启著书和撰修国史,后因才能显著而升迁为国子博士;另一类为门阀贵族子弟将博士当作为官入仕的起点,因只是仕途中的一个短暂过渡期,任职时间短致使大都博士在任内无作为,韦真喜作为北魏时期门阀士族子弟以中书博士为仕途起点,后升迁为中书侍郎和冯翊太守。
总之,由于受到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官学兴废无常、官僚体制混乱等原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士在含义和类别开始趋于多样化、专业化、民间化,在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博士选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在博士职责方面,这一时期的博士职责主要与官学教育和礼仪有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已逐步被削弱,博士的职责从政治属性为主又转移到以学官属性为主。在博士选任方面,博士的要求有所降低,虽强调 “高选”,但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和考核标准,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博士水平下降。同时,在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制的影响下,为给贵族和世族子弟提供更多的入仕机会,在太学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子学、中书学、皇宗学、四门学等中央官学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具有明显的世族政治和等级观念色彩,导致大部分博士作为起家官或者迁转官又来自世家大族,从而致使寒门学子更难入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也造就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
四、我国古代博士制度的成熟阶段(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博士”的内涵、类别、职责、选任和设置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扩展并趋于成熟、规范。一方面,是否精通五经和学识渊博已不完全是“博士”的主要适用标准,专精一行一艺的技术型、专业型博士比以往更加普遍和平民化。在《敦煌工匠史料》中出现了“擀毡博士”“起毡博士”“屈木博士”“看写博士”“碨博士”“洗緤博士”“族博士”“画神脚博士”[29]的记载,“擀毡博士”和“起毡博士”指从事制毡的手工艺人,“屈木博士”指木材加工业的博士即木匠,“看写博士”指类似从事打铁铸造的博士即铁匠,“碨博士”指从事粮食加工的博士即手工业匠,“洗緤博士”指类似于洗布染布的工匠,“族博士”指制造弓箭与箭镞的工匠,“画神脚博士”指从事壁画绘制行业的工匠,在《敦煌工匠史料》中还有造银碗博士、古露博士、写博士、点釜博士、烈钥匙博士、旋木碗博士、缝皮鞋博士、油梁博士、泥博士、泥麻沙博士、造塔博士等记录[30],这些充分说明,隋唐时期从事各行各业的工匠被称“博士”是一种普遍现象,博士已趋向于平民化,这一类平民化“博士”还有锉锯博士、团锯博士等十几种博士,在此不一一列举。当然这类“博士”比一般工匠和行业人员的地位更高、技术更好,应该可以定义为:某一行业方面上的专家,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且能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的民间劳动工匠[31]。
需要说明的是,在《敦煌工匠史料》中也有记载从事雕塑和绘画的“博士级”高级工匠,这类工匠技艺高超,工作质量好,有了一定名声和身份后,就开始招收徒弟、传授技艺,而许多技术生疏的一般工匠和手工业者为了掌握娴熟技术和维持生存就需要投拜“师傅”获得学习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师徒关系,而这类高级工匠就具有“师傅”的含义,自然可被称为“博士”,这也继承了在南北朝时期“博士”一词作为“师傅”的意思。劳动工匠被称呼为“博士”,这既是行业分工专精化的一种表现,也体现出“博士”称谓的民间化。“博士”称谓的民间化还表现在《封氏闻见录》中关于“茶博士”、《新唐书》中关于“棋博士”和“祭酒博士”的记载,还有《旧唐书》中关于“按摩博士”和“兽医博士”的记载,还有磨刻博士、音乐博士、煎茶博士、卖酒博士等。另外,“博士”一词不再专指传经授学的官员和教师,也可指精通某种技艺、专司某种职业的人,从而使博士的类别更加广泛,如通晓音律、作乐歌舞的“太乐博士”,精通医术的“术医博士”“医药博士”,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天文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掌教针以通经脉和穴位的“针博士”,掌教咒禁祓除、受斋戒之事的“咒禁博士”。
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创立和兴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和选拔官吏的需要,隋唐时期博士的设置和选任从中央到地方更加严密、规范、系统,上至中央国子监下到州县都有主管教授的博士官,博士官的设置很全面,覆盖了所有的行政机构和各行业领域。各博士官阶和待遇有着明确的规定,官阶和待遇最高的是国子监里的国子博士和五经博士,为正五品上阶,其他博士都是六品以下,属低级官吏,官阶的悬殊显示了隋唐官僚制度的系统化和层次化。同时,唐代的博士官基本上被纳入官方教育系统中,在中央官学机构中设置“六学”和“二馆”,“六学”为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四门学,“二馆”为弘文馆和崇文馆,每一个机构都设有博士官。在博士官的选任方面,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基础,主要通过科举考试、皇帝任命、举荐三个方式。这一时期博士的选任主要以科举考试为主,通过考明经和进士而授予博士的人员最多,如《旧唐书》中记载的韦叔夏、贺知章、褚无量[32]都是通过考明经以科举方式成为太常博士和国子博士。《旧唐书》中还记载文懿被唐高祖直接任命为博士的,为王公子弟授课开讲;徐岱被礼仪使蒋镇举荐为太常博士,负责礼仪事宜,还有被安乐公主举荐为太常博士的闾丘均。同时,隋唐也规定博士官的晋升和考核,前期主要是以资历来授官晋升,“各以资次迁授”[33]。后期因博士负责教授学生,规定博士官的考核成绩与所教授的学生数量和学习成绩相关,根据学生在科举考试中的“中举”情况来考核其成绩和决定是否晋升。隋唐时期的博士的职责基本上承袭魏晋,如官学授课、制礼祭祀等,但职责范围有所扩大,如著书、出使等。在这一时期,博士被纳入官学教育系统中,主要负责“六学”和“两馆”的授课。专门设置太常博士,专掌五礼仪式,负责制定朝廷礼仪和皇帝的封禅、祭祀事宜[34],为已故的皇帝、皇亲贵族或朝廷三品以上重臣拟定谥号[35],同时唐朝太常博士每日都要朝参,有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唐代博士有著书的职责,但凡皇帝授命的博士官就得参与著书,唐代的博士大多有自己的专著,如韩愈、颜师古、李商隐、贺知章、梁述、李淳风等,相传李淳风著有《天文》《律历》《五行志》等书,“著书”是在秦汉时期的“藏书”职责上进一步扩展。唐代博士还有奉诏出使的职责,担任维护礼仪的重任,《旧唐书》记载唐穆宗长庆二年太常博士殷侑奉旨出使回纥,送太和公主去回纥和亲。
总之,隋唐之后,“博士”的内涵、职责、类别、选任和设置无多大变化,博士制度在封建社会已基本成型。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迅速发展,成熟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文化与博士官的发展密切相关、相互促进。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的形成为官员的选任、考课、设置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治保证,由于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的发展和需要,博士的选任、考课、设置更加科学、严密、系统化,博士队伍和职责不断扩大,博士称谓和类别更加平民化、专业化、普遍化。在社会文化上,文化的繁荣为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博士作为高级教授官,是教育发展的领头羊和主要力量,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博士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博士作为学识渊博之人的代名词,是教育领域的代表,承担着传承文化和发展教育的责任,博士官的发展必然带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文化的繁荣。同时一些技术型、专业型博士的设立和发展也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地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五、我国古代博士制度对高等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虽然博士制度的内涵在不断变化和延伸,从受尊崇的学者、长者到朝廷任命的职官、技艺高超的工匠,从掌教礼仪、传道授业到参政议政、民间授艺,但博士作为学识学术精英和文化教育传播者的内涵始终未变。博士制度作为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一,是一种完备但不完善的教育制度,虽不能与当代高等教育相提并论,但从其历史嬗变中仍可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更好地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一)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要义
与当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博士相比,古代博士秩卑而职尊,俸禄和官职虽较卑微,但地位优于其他同级官员且受人尊重。既不用因各种繁琐的职称、待遇、项目事宜而忧心,也拥有较自主的教授、治学氛围和较高的政治地位。博士制度的起源地——稷下学宫,就能充分体现出学术自由的特性,稷下学宫由齐国提供治学场所和办学经费,但并不干涉稷下先生和各学派的学术活动,各学派也没有等级观念和门户之见。只要有名望和学术影响的博学之士都可以到稷下学宫讲学。博学之士来往自由,对于想离开的人,齐国非但不阻拦,而且还赠予路费方便其离开,对离开之后又回来之人也表示由衷地欢迎。稷下学宫开放自由的办学方式和学术氛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治学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这种状态和精神在历朝博士制度中都得以体现并一直延续下去。我国古代历朝博士既为学识学术精英,又为负责和管理高等教育的博士官;博士在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又可以凭其才能发挥其政治和社会功能。博士可以自由、独立地治学,不仅能成为某一领域的学术精英和权威,又可以通过参政议政而获取高官厚禄和提升政治地位。政治地位的提升既是学术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学术发展创造了自由独立的条件。在太学、国子学、中书学、皇宗学、四门学等官学教育机构中,博士拥有较大的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作为学识学术精英和代表,他们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领域的教授权和治学权,在教材选定、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享有 “师法”的至高权威,博士学子必须恪守博士在官学教育机构中制定 “师法”。虽然这种至高学术权威可能有损文化教育的自由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对学术权力的肯定。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精神,是学者和高等教育机构不断追求学术创新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学术自由,人的思想和思维将会停滞和枯竭,从而影响学术发展和创新。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绝不能以牺牲学术自由为代价。各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传播知识和探索学问的学术组织,必须以保障学术自由权为第一任务,要更好地践行高等教育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古代博士制度所蕴涵的学术自由精神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学术自由权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借鉴意义,古代博士具有学术和政治功能的双重身份,博士作为学者型官员,可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宽松环境,这启示当前高等教育机构在不违背国家方针政策、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社会干预和制度限制为学者们做学术研究创造宽松环境,使学者们能从日常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
(二)学术纯粹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
西汉时期,太学兴盛一时,对博士的选拔程序与博士学子的招收要求都有了严格的制度,博士授业和治学有相对的学术纯粹性。在授业目的上,西汉初统治者本以儒家经学为教学内容,通过博士授业方式去选拔和培养官吏,以实现“传先王之业”的政治目的[36],但并不想以太学为平台实现这一目的。但随着汉武帝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将是否精通儒家经典作为培养和选拔政治管理人才的主要标准,而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主要教育机构,众多太学博士学子出于政治目的,为了取得更高官位,进入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博士选拔和职责自然就变得不够纯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机构在不断扩展,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北朝在太学基础上还设立国子学、皇宗学、四门学、中书学,在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制的影响下,更多的世族和豪门贵族弟子进入官学机构,以此捷径步入仕途,更有甚者直接凭借关系入学以谋取官位,官学机构也成为达官贵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这也导致博士选拔和博士学子招收的混乱,博士学子的数量成倍增加,最终影响了官学的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其学术纯粹性受到影响,学术衰败也就成为必然,学术趋利于政治将导致高等教育走向衰败。而在治学方法上,一些博士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私欲,忘却本职和初心,比附政治权势、攀迎贵族高官、曲解儒经典籍以攫取高官厚禄,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纯粹性。诸如西汉后期,由于今文经义已不再适应混乱的政治环境,学术被政治所左右,统治者不得不兴起古文经学。学术纯粹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核心,高等教育做学术研究必须能经受得住功利世俗和高官厚禄的诱惑,有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趋利于政治,不被带入复杂的政治浪潮,否则学术研究将不再纯粹,博士学者们做学术研究也更政治化、功利化,高等教育纯粹的学术环境将被破坏。学术纯粹是教育界的核心价值观,高等教育的学者们要树立独立求真的学术意识,有培养一种 “超凡脱俗 ”的学术品格,要追求一种 “为学术而学术 ”的学术精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知是非,计利害”应该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倡导的主流价值观。
(三)学术去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高等教育机构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学术组织,而不是行政官僚机构,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遵循学术组织的特点,行政化的教育管理模式限制学术权力的发挥。稷下学宫起源于各诸侯国招揽人才的“养士制度”,采取一种将政治与文化教育相分离的模式,开创了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先例。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却开始将以博士官为主的官学教育机构纳入行政官僚体系,对官学教育机构开始采取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同时历代王朝承袭秦朝“以吏为师”的传统,授予博士相应官职和官阶等级。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模式注重服从、命令、执行和等级,从而忽视了学术自身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学问不在于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在于学术水平的高低,真理和知识时常掌握在行政级别较低的人手中,而行政级别较高的人有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形成对学术权力的压制,从而导致学术水平停滞不前。如果官学教育机构始终依附于行政官僚体制,官学教育机构将丧失学术的独立发展空间而成为选拔和培养行政官僚的场所,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学未能获得充足发展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高校)的管理大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党和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引导和管理的一种模式,也是与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相适应的一种表现,与我国古代博士制度一样具有官学的性质。这种模式突出了管理方式中政治和行政权力,而高等教育的学术权力得不到充分的体现,这可能也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之一。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正努力摆脱政治干预和行政体制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遵循学术的本质和特征来调整。因此,新时代高等教育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础上,形成一种“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民主参与、独立发展”的新体制,凸显出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作用,实现“学术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氛围。
隋唐之后,成型的博士制度是古代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一种表现,它促进思想文化的解放和进步,博士制度的专业化、平民化、技术化正是学识和技术共存的一种体现,博士在教授和治学时不似先前朝代仅以五经为教学内容,而是形成一种不拘于一家之术的教育模式,这才是教育发展的本质,对当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古代博士制度毕竟还只是处于高等教育的原始状态,与当代的高等教育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但这种原始状态可以让我们探知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当代社会要发展好高等教育就要把握学术自由这一核心要义,要坚持学术纯粹这一基本原则,要探索学术去行政化这一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