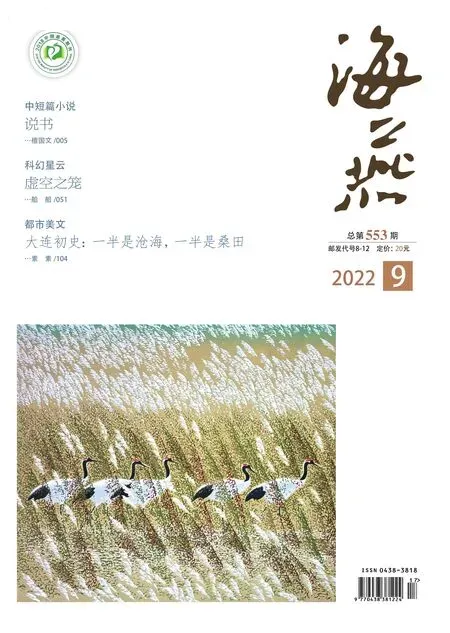说 书
2022-11-17檀国文
文 檀国文
疫情四起时,父亲去了镇上,关停了家里的包子铺。回来的时候,村子上空雪花飘扬。远方,天与地一片白茫茫,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母亲有了心事,她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在雪地里徘徊了好一阵子,头上落满雪花全白了。而我跟在后头。
这是两年前的场景。没料到,疫情会持续至今,时间这么久,对我们来说,似乎无比漫长。现在,我躺在大学的校舍里,常在午夜醒来后久久失眠,想象此刻的父亲也尚未躺下,他在别人家说书。我会从床上爬起来,在卫生间里默默吸烟。没有人看见此时的我,陪伴我的,只有午夜的宁静。它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也向我不断诉说生命里的一切,叫我摸索几年以来家里的痕迹。
店铺被迫歇业,家里顿时断了收入,要过日子,必须动用本就不多的老本。母亲能想明白这回事。那天,她从雪地里回来,一头扎进厨房,整个下午都没有出来过。晚饭时我发现,母亲已经整理好家里所有的粮食。不光是大米和小麦,以前从来不吃的面粉也一袋袋装好,像一只只小猪,憨憨地趴在橱柜里。怕生虫子,母亲又往袋子里埋了包有花椒粒的纸团。
现在我说这些,好像当时什么都明白似的。其实不是,没经历过天灾的我,很难窥见其背后的危机。母亲不同,她见过艰难岁月里那些骨瘦如柴的生活,心里更多几分担忧。她把几张存折铺在床头,用手指去数上面的数字。
“多少?”父亲问。
“八万,这些年攒的,以后怕是要往外取了。”母亲看了看我,又说,“你还要念书,将来还要成家,怎么办呢?”

我无所谓,成家的事远远没有想过。母亲睡不安稳了,常在深夜里发出叹息。黑夜在她眼前静静流淌。
父亲是怎样突然决定说书的,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我家以前有过“说书”这个词的出现。是母亲告诉我的。
“说书?”我问。
“就是有的老人走了,人家会请说书的去,一夜可以赚个几百,是桩好事。”母亲说。
“不做包子了?”
“大概吧。你想,现在店开不了,就算将来开了,恐怕生意也不见得好。”
“怎么学?”
“跟一个老师傅,学费要五千。你想,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
说这些时,我看见母亲眉间舒展,嘴角露出笑意。我从未想过,生活中竟有这么一天,一个微笑是如此要紧的事情。要知道,疫情暴发以来,家里屋院的上空,好似凝结了一层浓厚的愁云。大家都懒得说话,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
邻居们知道后都不看好,说父亲瞎折腾,母亲也糊涂,竟由着他去。他们的意思,大家只该节衣缩食等待疫情结束,不能再往别的地方砸钱。我想像邻居们一样,把自己关在白日的萧条里,也试图在父亲脸上寻找疑虑。但是,当父亲启动车子,我发现自己全错了。
下午四点,父亲出门了。他坐在摩托车上,尾气从车后阵阵扬起,引擎声划破了冬天滞重的空气,将旷日持久的沉寂推得很远。我已经很久不曾听过这种声音了,我家没有,整个村子都不会有。
“晚饭在哪儿吃?”母亲站在车尾说,嗓音从引擎中飘出来。
“你俩不用等我,先吃吧。”父亲说。
“早点回来。”
“外面冷,快回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回屋里,只是站着,目送父亲离开。他沿村路骑下去,到尽头往右一拐,随即消失在一片竹林后面。我走近母亲,跟她肩并肩站着。风推着寒气扑过来,我们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儿,但视野里,竹林仍没有丢失。我突然明白,也许在母亲眼里,父亲身后,牵引着我们整个家的希望。也是在这一刻,我想自己才走进了母亲的心田,感知到她长久以来的担忧。
而这一切,后来都成了寻常。
老师傅有生意时,我家的电话准会响起,那串铃声,给我们带来了整个冬季的热闹。父亲也很下功夫,没有推辞过。有时候天会下雨,北风呼呼地刮过窗户。母亲问:“还去吗?”父亲不说话,默默地钻到储物间里翻雨衣。出来时,雨衣披到身上,朝门外走。
父亲每迈出几步,母亲就会问:“还去吗?天这么冷,还去吗?”回应她的,往往是沉默。我知道,这是他们独有的交流,也懂得,几十年的昼夜晨昏给这种沉默赋予的意义。
那些日子,父亲回来得很晚,过了午夜仍未到家是常有的事。母亲则在黑夜里默默等候。我能听见隔壁屋里的她不时翻身和坐起。
半夜里,一抹车灯掠过,隔壁的狗都吠起来,这是父亲回来了。我躺着,听母亲起床,轻手轻脚地去开门。她怕吵到我,实际上,我也不敢睡,一想到父亲在外面独自抵挡寒夜,心中就莫名难安。有雨的夜晚,我还能听见父亲换衣服的声音。我想看见他,看他衣服是否潮湿,头发是否凌乱。可是,我一次也不曾从假睡中醒来过。我想,我没有勇气去看此刻的父亲。

插图:李金舜
但后来我还是发现,父亲瘦了,也老了不少。当看见他在门前劈柴,我第一次这样想。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脸上有着阳春三月的温暖。父亲脱下棉袄,露出里面的毛衣,深蓝色,空空地罩在身上,像往竹竿上套层塑料袋。木屑从斧口绽出,飘下时,像雪花坠入贫瘠的土地落在父亲肩上。他每劈几次就要停下,手扶在腰上大口喘气。我突然意识到,记忆里那个健硕的父亲,距今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和久远了。他头上的黑色毡帽,提醒我不得不接受他俨然是个老人的事实。
这些心事,我没有人可以诉说。人总是害怕触碰内心的软弱。母亲好像能看透这些,她说:“年纪大了,再做包子怕熬不住,学说书,是桩好事,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相信母亲说的。父亲也学得很快,已经可以独自唱上很长一段了。可惜的是,我和母亲都没有到现场看过,只能听父亲在饭桌上讲起。母亲很乐意听,她自言自语似的说:“诶?什么时候出师就好了。”或者直接问:“诶?你什么时候出师啊?”
父亲没回答。两个月之后,突然要买落地音箱和鼓,都是说书要用到的。母亲心里明白,轻轻点头而脸上只是笑。
我家有一间书房,给我念书用的。不大,一头是书架,一头是书桌。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很少踏足了。父亲看中了它。他推开冷落已久的房门,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陪伴他的,是墙脚的音箱、皮鼓,还有一个被熏黄的旧烟灰缸。
“乾坤悠久,运历数以无差。物转星移,度时光而迅速。叹浮生恍若大梦,嗟去日多如朝露……”这是父亲开始练习了。我跑到书房外,门开着。房间里,一切既陌生又熟悉,它被我遗弃,又被父亲拾起。此刻,蔚蓝的墙纸好似一片港湾,洒遍了父亲的希望。父亲一只手握着响板,另一只手拿着鼓槌,两种声音从他手中流出,交织着,汇成和谐的河流。它向我翩翩袭来,将我的身心冲向一个莫名的地带。在那里,我看见父亲。他背对着我,独自行走在无边夜雨里,枯死的枝叶在身后当风抖落。他每迈出几步,身体就萎矮一分,身影如流般一逝而去。
回过神来,母亲已经站在身旁。她笑了,我却哭了,躲回房间里。
很多个日子,父亲待在书房里不挪地方,屁股下面是我曾坐过很多年的椅子。以前,我为的是升学,而如今,父亲则是为了更为沉重的事情。他买了一本《隋唐演义》,打算编词,用于说书。他担心,从别人嘴里学来的东西恐怕不够用。
父亲没读过几年书,常遇到字不认识,捧着书来我这边问。我于是发现,他的记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有些字竟问了三遍,甚至四遍。而我当时聪明得过头了,竟提出要教他拼音。父亲几分尴尬地笑笑,嘴里念着生字,出去了,房门在身后轻轻掩上。
记忆里,母亲不怎么管我。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她不是在屋前不厌其烦地晒着各种干货,就是在扎苕帚,一把卖十五块钱。她说:“小钱也要抓住了才算是你的。”这些小事,我已经看了二十年。以前我从未理解,而现在时刻面临家道中落的恐慌,我才真正读懂母亲的生命,知道就是这些寻常,承载了母亲的一生。
吃饭时,我们一家终于聚首,像就食的秃鹫从四面飞来。而谈论最多的就是死人。“这些天都没有老人走啊?”“隔壁村小罗家老太快不行了。”我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老人死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说:“学校发了通知,上半年恐怕不用去。”母亲松了口气,这可以省下很大一笔开销,没什么不好。父亲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我多学些东西。“不管是谁家里,怎么难也不会叫孩子在学校里难。”父亲说得很随意,像要掩饰什么。他总是这样,越是认真越是不露痕迹。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我明白过来,父亲终其一生,所做的只是这么一件事情。如此卑微,又如此高贵。
疫情旷日持久,日子过得很难。母亲不舍得一天吃三顿米饭了,她默默把晚饭换成了馒头,就着几口白菜下咽。这让我想起童年里那些青黄不接的时节。我们是南方人,要坚持把馒头当主食是件不容易的事,吃到后来,通常是菜盘子空了,馒头则没动几个。母亲为饭桌上的寒碜感到愧疚,一言不发,仿佛自己做了一桩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说起来,口腹之欲或许容易忍受,邻居的冷嘲热讽则叫人难堪。他们嫌响板和鼓的声音太吵,说父亲想靠说书来养家是白日做梦,现在不可能,往后也将这样下去。一来二去,父亲就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了,出门的次数更少。我感觉,父亲周围有看不见的高墙,将他隔成孤身。
我想听见母亲的话:“你想,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可她没再提起过,像是被邻居的嘲讽卡住了喉咙。我不免担心,母亲的信心是否已被瓦解,转而怀疑以往相信的一切。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我的猜想。
书房以外的世界,父亲只留下了一个影子,而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一天。桌上摆着书和本子,颤颤巍巍地写满唱词。烟灰缸放在桌脚,边上厚厚地积了一层灰,有些烟兴许没有燃尽就从指间滑落,地面有烧过的痕迹。这种杂乱,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母亲不再愿意进去打扫了。她厌倦了这个房间和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也厌倦了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盲目付出。
父亲要钱时,她像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目光却散淡无力。长久以来,因为学艺,父亲已经投入了相当的财力,可没能挣回来哪怕一分钱。面对这种现实,母亲不得不放弃曾经怀揣的幻想。她靠在衣柜前,双手背过去抵住柜门,用身体护住那最后的防线。而父亲的音箱坏了,必须重新买一台。
“只要几百块钱,没有多少。”父亲说。
“不行。”母亲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异常坚定。
“所有那些大钱都花出去了,不差这一点儿。”父亲说。
“我不能看着你把家败光。”母亲声音颤抖了。
她到底没能改变父亲的主意。看着父亲从本就羞涩的钱包里又抽去一些,母亲开始哽咽了,坐在床上久久没有站起。
新音箱搬进书房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母亲,她不知道去了哪里。同时消失的,还有挂在衣柜上的那把锁,柜门开着,钱包磊落。父亲钻进书房,晚饭不吃,一直到深夜,他都没有离开过那间房。更要紧的是,饭桌上,久违的阒寂仿佛又卷土重来。母亲始终一声不响,我因为之前没有帮她说服父亲而有种罪恶感,也没好意思开口。我害怕此刻的孤独,更害怕艰难的岁月湮灭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我想制造一些动静,用手机放歌听。乡下网络很差,歌曲断断续续,当身处无声的空白,我意识到,有声只是拓宽了这个家庭沉默的疆域。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父亲,这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这个时代车轮后的遗弃儿,面对所有人的讥讽,面对妻子的质疑,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想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也许,我想,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然后,他又将重整旗鼓,捡起桌上的笔。笔迹稀松,勾勒出父亲年华点滴流逝的痕迹,凝结了父亲平凡人生的重量。
时至今日,我仍会时常忆起那个夜晚,它像我吹过的秋风,从我们家卷走一切色调,掠去仅有的生机。母亲的反常,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母亲不再过问父亲的事情了,不再关心说书的进展,消失的那把锁,连同钥匙一起出现在垃圾桶里。她每日忙的,只是给一家人洗衣做饭,依然扎苕帚。有时,母亲一个劲儿地清扫我们本就不大的屋子,尽管地板已经光可鉴人,只是那间书房,仍是被她遗弃的角落。其实,母亲想要扫去的并非地上的尘埃,而是父亲人生里的杂沓。
母亲已经不愿去听书房里的声音了。每当父亲的嗓音传来,她就会打开客厅里的电视,不看,却故意把音量调得很大。
父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也很少记恨。面对沉默的母亲,他仍然时常分享,谈起一些有关说书的事情。“今天词写得不少,要是天天都能这样就很好。”“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帮忙介绍生意来着。”母亲选择性地屏蔽了父亲的声音,不说话,走开了,只留下毫不掩饰的冷漠。我不禁认为她未免残忍了些。父亲不大在意,他对我说:“你妈不懂,我的力气不是使在了今天,是使在了以后,这跟说故事一样,结局没来之前,一切都还在路上。”
“结局没来之前,一切都还在路上。”
父亲只念到四年级,但他说的这句话曾在我梦中出现过无数次,有时是午夜惊醒后倏忽而至。我看不见黑暗,眼前浮现的全是父亲的影子。那一定是他胸腔里发出的生命回响,是他庸碌人生里最深的倔强。
父亲相信,他仍在路上。
四月,南方的天气告别了阳春的暖煦。太阳当空,风斜斜一吹,落到人肌肤上有些溽热。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满枝,再几夜,在春泥里蓄了遍地淡紫。
季风如期将春色还给人间,唯独遗忘了我们。
母亲常说:“再这么下去,往后恐怕只能吃土了。”说话时,她眼睛看着我,却不像是说给我听的。有时,父亲在书房里练习说书,母亲故意把嗓音提得很高,试图盖过鼓和响板的声音。像冷水浇灭火苗,书房里的响动戛然而止,随后传来啪嗒一下打火机的声音。
只有一次,父亲拉开了房门。他站着没动,双眼盯着沙发上的母亲,目光冷峻,额前硬朗的皱纹透露着威严。
我第一次看见他这副模样,即便是到了一切早已云散的今天,每每忆起,心中仍会泛起一层细密的战栗。我会想,如果当时父亲真的冲过来扑向母亲,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情。
好在父亲没有。他走出家门,穿过院子,四月的花无声落地。
我久久望着这棵玉兰。它是二十几年前的春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栽下的。那时还没有我。我不曾看见它是如何长高和长粗,只知道,暮去朝来,它见证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也目睹了一切凄风苦雨的岁月。
父亲是第二天回来的。他没坚持到走进卧室,就倒在了沙发上。额头很烫,身上挂着枯黄的稻草。我没想到,父亲在草垛里睡了一夜。
我们不能去买药,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发烧,是会被送去隔离的。那时,大家都不懂所谓隔离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感到恐惧,无端地以为要把人关进一个完全封闭的地方。
是母亲照料父亲的。家里没有药,母亲只好用一块濡湿了的毛巾,不断擦拭父亲的额头和身体。这天傍晚,饭桌上出现了久违的鸡汤,父亲因此多吃了几个馒头。
长久以来我发现,乡邻们已经习惯了疫情相伴的日子,不再抱怨那个吃蝙蝠的人,对疫情结束的渴求不再热烈。如流的时间抚平了那个冬季的恐慌,当春天降临,笑容又爬回人们的脸上。这其中有很多人,或许一辈子也不曾踏出过这座村庄。他们,依旧在村路上留下足迹,拓印着各自不免逼仄的人生。聊天,或者几个人一桌打麻将,成了这个村子不至死去的证明。
而母亲从未忘记。现存确诊的人数,成了她每日生活的焦点。母亲是生在农村的妇女,不认识几个字,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勉强看懂。有时候,同一天的数据,她要反复看上好多次,好像只要她不接受,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疫情依旧泛滥的事实似的。她指望灾难过去,关张已久的店铺能寻回昔日的风光。父亲生病时,母亲坐在床边,对着手机叹了一天。
父亲则听了一天。
不久,我在父亲手中看见了一些老鼠夹,锈迹斑斑。那是爷爷生前用过的东西,他死后,它们也像他一样不再发出声音。父亲要做什么呢?直到他走进我家的自留地,往每个洞穴前安下这些老鼠夹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父亲说:“咱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片土地,到了今天,这里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我原本以为,还在病中的父亲多少会有些虚弱,但他说这句话时,像个重拾信心的战士,眼神果敢坚毅。
早晨天还没亮,父亲从床上爬起来,到田里取下被夹子留住的动物。回来时,地上趴着受伤的兔子、獾,偶尔也会有黄鼠狼,它们眼神凄苦,最后一次同情自己不幸的命运。父亲将它们装进袋子,托人带到镇上卖掉。钱不多,好歹能补贴家用。对于一个老之将至的父亲而言,还有什么是比让家人多吃几口饭更重要的呢?
其他时间,父亲则仍然练习说书。他已经编好了词,我以为他会比以往轻松一些,却忘了,背词不比编词容易多少。有时候,我会给父亲泡一杯茶。他坐在桌前,白发清晰可辨,脸上是如老树皮一般的黑皱。我就知道,岁月的河流底下,父亲一逝不返的人生,已经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那夜我再次失眠,不明白以我的年纪,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父亲和母亲的两股鼾声传来,缠绕着我日夜交织的思绪,像一团乱麻跌进我的梦里。我越来越怀念疫情以前的日子,怀念那些简单而柔软的旧日生活,没有忧虑,我们赖以生存的铺子也没关张。父亲忙完店里的事情,赶在最后一缕晚霞落地前回家。饭桌上常有他带回的烤鸭和鸡腿。母亲在捧起饭碗前,总是执着于弄清一日的收入。碰到生意不好,她会说:“大钱都是这样的小钱积起来的……”
而这些场景,今后再难重现。或许这也是我决定不读书的原因。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念书了,等管控松下来,我去打工挣钱。”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早早结束了学习生涯,有的去做裁缝,有的进了厂,生活不易,却都相继买了车。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去过这种人生呢?
告诉父亲时,他正在摆弄一个铁夹,双手一颤,险些被夹伤。他说:“钱什么时候挣都不迟,只要熬下去,我们只会难在一时,不念书,那才真的要穷一辈子。”他还问我:“要是书也不念了,我和你妈这一生还有什么意思?”
我回答不上来,却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们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别提了,没有人会同意你。”父亲说得很坚定。
他默默走远时,我没有跟着,只是大声说:“难道你就那么迷信读书吗?就算饭都吃不上了也还要读那个鬼书吗?”
父亲猛然回头,想说什么,但没出声。我生气地拔腿跑开,不想在他的视线里多作停留。
学期结束后,疫情形势变得乐观。包子铺重新开业,却没生意,再一次又或是永远地挂上大锁。母亲的脸上也像挂了锁,很少有表情。我到镇上找了一份兼职,在一家教培机构里给初中生上课。因为这件事,母亲几乎要怨恨父亲了。
在教培机构,并非直接就有课可上,首先要做的是招生。老板带着我们一行人,几张桌子往附近学校门口一摆,人或坐或站在路边,对过往的学生和家长尽力地招揽。七月的太阳很毒,躲在伞底下也感觉暑气蒸人,极短的几日里,我的皮肤多次更迭,先是泛黄,很快又变红,最后成了如父亲一样的铜色。看着镜中的自己,我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了父亲的影子里,他年轻时的容颜,穿越了浩瀚的荒野和漫长的岁月,在我面前交叠。一种好像与生俱来的力量,在此刻破土而出。
而母亲心疼我这样,叫我不要再去了。
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做一些事情了。”
“应该?么事叫应该?应该是他去做,去挨晒。”如果是在以前,母亲会说“你爸”,但此后,恐怕只会是“他”了。
我无法答应母亲,仍然每天早上七点钟出门,骑上二十分钟的摩托车到镇里。偶尔,我出门时,碰到父亲要去自留地里。他于是站住,叮嘱我路上要小心,还教我什么时候要将车子换成二挡或者三挡。“好,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走了。”我总是这样回答。说这些时,旧时光里的记忆在眼前飘荡,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每一步都由父亲指着我走。当穿过那片夹道的竹林,我回头看,家门口也有人在望我。微风动叶,向我诉说着父亲曾无数次经过这个地方。而如今,二十岁的我,终于走在了父亲走过的路上。我忽而沮丧,不知道以后的自己是否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家庭岁月长河的源头。更迷茫的是,再往后的路,老去的父亲,没能力指着我走。
我莫名害怕这种人生里不可避免的孤单。
可我不希望父母孤单。不在家的时候,我常想,这两个相对无言的人,他们将如何送走漫长的白昼?我无从得知。我只记得,回家时,门前只有母亲,夕阳将她的身影无声拉长。“回来啦,又晒黑了。”母亲的口吻好像我们阔别已久。
我不在意晒黑,说声没事,问她爸呢。我于是从她的表情中得知他们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几次以后,我就不再问她了。我害怕她对父亲无声的责备,更害怕接受一个家庭陷入冰河的事实。
我恨疫情。
八月中旬,教培机构的课程结束了。我领了四千块的薪水,从镇上带了鸡和肉,并非多么想吃,只是希望这些东西能让家中久违的温馨重聚。我想看见母亲,看她烧好一盆开水,将放过血的鸡泡进去脱毛。厨房里香气缭绕,给这个乡下人家填满最平凡的幸福……
傍晚,到家。果然,母亲脸上卸去了一直以来的那把锁,眉间舒展,眼睛里溢满黄昏下的夕阳。我太久不曾见过如此热烈的快乐了,但很快发现,那并非出于我手里的东西。
“你爸今晚不在家。”母亲说“你爸”了。
“他人呢?”我心里有几分疑惑。
“说书去了,”母亲告诉我,“万全村有老人走了,肺癌让老人在吐出最后一口乌血后彻底断气……”说到这些,母亲描述得很细,好像老人离世时,她正好在旁边看着似的。她已经很久不像今天这样兴味盎然地谈论一件事情了,而背后,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死去。第一次,我感受不到生命应有的沉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希望,有些卑劣,又如晚霞般温暖。
父亲是骑自行车去的,他等不及,早在我和摩托车回来之前就出发了。我担心他晚上路上要摸黑,决定吃过晚饭去找他。母亲说:“要到下半夜才回呢。”我想,正好去凑凑热闹。
去万全村,有七八里路。沿途一边是河,一边是田,路又窄,白天尚且要十分小心才好通过,何况夜晚。我庆幸自己晚饭时的决定。到了万全村,很容易找到办丧事的人家。十里八乡都是一样的风俗,一家发丧,全村帮忙,站在路边一望,哪户人家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准就是了。这时大家都早已吃过饭,我往人堆里一站,就看见中间空地里的父亲。
面对陌生的面孔,面对躺尸的棺材,父亲吸了一支烟,朝棺材拜了三拜,然后开口唱起来。是唱,他口中每一句词都有腔调,故事就在那不疾不徐的旋律里。
“鼓槌一敲闹声喧,人生寥寥三万天。世间代代无穷尽,敢教新土埋旧人。举头试问天上月,看遍古今多少坟。愁思万千抚不去,此后仍为子女根。不解哀乐百年树,阅尽人间说书人。今夜听我唱一段,晋末南北隋替陈……”
观众们有的在录像,有的在拍照,七嘴八舌地说父亲有一副好嗓子。我还听见有人说:“等我家那老鬼死了,也叫他来说一夜书。”我能想象,明天,抖音里会有很多由父亲担任主角的视频,母亲将看到这些,邻居们也将看到。
我想等父亲休息时给他递杯茶,可他一直往下唱,似乎一开口就没想过要停下来。他唱“隋主起兵伐陈”,唱“杨广施馋谋易位”,还唱“秦琼舞锏服三军”……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不知疲倦地说书,又或许他一直在唱,只是我没有听见。一种沉重的酸涩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而如今,在离家数百里之外的桌旁,当深夜在我耳边絮絮低语时,我常能听见那夜的声音。那是父亲向我和母亲发出的呼唤,是他向这个家庭命运发出的呐喊。这声音,蓄满了抵挡乡邻讥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撑起了一个普通父亲的梦想。
那晚我也录了视频,用手机发给家里的母亲。看着人群当中的父亲,看着被无数目光簇拥着的父亲,她会想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手机出奇安静,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而回家时,父亲书房里的灰尘一扫而空。
秋季,开学了,我还是去了学校。是我自己的决定,也是父亲的期望。
接父亲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告诉他拿了四千块工资的事。父亲“哦”了一声,没说什么。这样平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后悔已经说出的话。我不怪他,一辈子碌碌无闻的父亲,一辈子朴实无华的父亲,终究活成了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土地养人,却默默无声。
蛙声唤醒沉睡的月色。我们骑行回家,一路无言。中途,父亲突然开口了。我没听清,回头看他。
“还是得念书哇。”他说得更大声了。
想起之前与父亲的争执,我感到羞愧,为自己的短见而羞愧。这回轮到我沉默了。
“马悔在先,人悔在后,决定不是像你那样做的,还是念书好,你讲对不?”父亲能看透我的心思,给我台阶下。
我心里打消了原先错误的念头,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地埋头骑自行车。父亲则骑摩托车紧跟着我,车灯从身后射过来拨开夜色,让我能清楚看见前方的路。更为要紧的是,人生的路,父亲又指着我走了一程。
校园生活还是老样子,一如从前,该上课时上课,该吃饭时吃饭,只是在查看账户余额时,会想起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家中的现实。我不怎么打开抖音,后来干脆卸载,我不忍看到深夜里仍在外面煎熬的父亲,还有那夜色也无法抹去的白头发。母亲常在电话里问我钱够不够花,叫我不够就吱声,而我每次都感到难以启齿,在短暂挣扎后说出谎言。母亲不拆穿我,却让父亲给我转一笔钱,说是放在我手边上又无妨。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数字,我会折合出那是父亲辛苦耕耘的多少岁月、多少只野兔,或者多少东奔西走的夜晚。
我想找份兼职,但学校的封控让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最后,我去了食堂,在一家窗口给人打菜。管一顿饭,一晚上给三十块钱。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送走了九月的尾巴。
国庆节,学校规定不准回家,可母亲想见我。
父母来看我那天,我跟学校请了假,借口是胃疼去买药。按照惯例,病假才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在学校附近的餐馆订了一餐,有父亲爱吃的红烧肉,也有母亲喜欢的芹菜。本来我在食堂赚了钱,说好由我付账,但父亲还是赶在了我前面。他说:“等将来工作了再请我不迟,到时别拿这样的菜糊弄两个老人咯。”
吃过饭,在公园里闲逛,母亲很快就走不动了。她脚下踩着的是一双女式皮鞋,几年前买的,出门才穿,跟儿高头儿窄,走路一多脚就痛。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母亲讲家里的事给我听,我于是知道,换取开支的方式又多了一样——父亲不说书的晚上,他们到田里捉野黄鳝去卖。下雨的夜里尤其容易抓,黄鳝都从洞里钻出来透气,死了一样蜷在泥面上。
“那你们不也淋湿一身?”我说。
“打伞嘛,不过也跟没打一样。”母亲说。
我心里默默盘算,自己又从父亲手中捉去了多少黄鳝。
母亲要我讲讲学校里的事,快乐的,烦恼的,她都想听。而我却觉得无事可讲,日子如水般过去无痕,只好说说打菜时要如何抖去半勺,还学给她看。母亲说我长大了。父亲没有出声,却在我身后伸出手臂,搭上我的肩膀。他老了,也太瘦削了,曾在他怀抱里驰骋的肩膀,如今他要相当努力才能抱得住了。
父亲也许也意识到了,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挤出一个同他一样的笑脸。那一刻,我们多像一对相视无言的老友,在无声的目光里支撑彼此的生命。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切既陌生又熟悉,父亲成了一个稍显青涩的孩子,却也仍是我旧时光里的回忆。
回去时,空中起了风,有风筝在逆风挣扎。这时父亲和母亲已经搭上返程的火车。父亲给了我一千块钱,我揣在兜里往回走。转头,望向火车驶离的方向,视线总是有限,能看见的只有远方的天空和山野,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在我来时的路上,欣赏我曾路过的风景。
就像在公园里时父亲说:“你一直都在,儿子,真的,你没有离开过这个家。”
我什么也没有说,听他唱了几句说书的词。
“谁知天下窄,不比井中宽。遥想明日事,还从明日来。”父亲嗓音深沉,像要迎接某个夜晚,又像是吟一首动听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