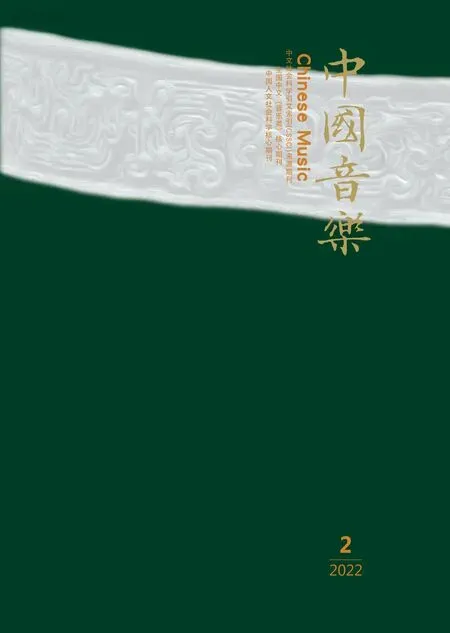阿炳的“朋友圈”
——交往史视域下阿炳的音乐观念与行为探究
2022-11-16○施咏
○ 施 咏
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一生的生活轨迹基本都定位于无锡城内,其社交的圈层主要是由崇安寺图书馆路30号的雷尊殿(即阿炳故居)周边的近邻街坊、阿炳以琴会友的其他民间艺人,以及以刘天华、杨荫浏、黎松寿、宗震名等学院派的音乐家这三种类型构成。与阿炳密切交往的这些友人对他的音乐人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于珍稀零散记载阿炳与诸位好友、先贤宗师之间些许交集的(口述)史料当中,感叹弥足珍贵之余,亦可通过这种“自下而上”“自周边而中心”的交往史之方法视角,以冀更为全面立体地了解阿炳的性情、生平,透析其音乐审美观念,并以此反观对其创作、演奏等音乐活动的影响。阿炳与其(音乐)朋友圈的交往折射出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亦无不引发今人对历史的遥思与无限感怀。
一、阿炳朋友圈交往之史料梳理
(一)阿炳与民间艺人的交往
1.阿炳与道乐好友
几乎所有围绕阿炳的口述史料中都无一例外地共同表明,阿炳的性格总体较为直率、外放,乐意结交朋友。自其少时学习道乐时,就与当时无锡道教界的诸道乐高手,如“东亭乡高新甫、谢梅初、谢桂初,旺庄乡袁亭牧,新安乡尤庭芳,张泾乡朱逸亭,梅村陆逸卿等”①钱铁民:《阿炳与道教》,《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第54-55页。,以及包括号称“南鼓王”的明阳观朱勤甫在内的古琴家阚献之、朱亭贞(鼓、梆胡)、水濂道院的王士贤(二胡)、伍鼎初(鼓板)、火神殿的尤墨坪(三弦)、灵官殿的王云坡(琵琶)、铁索观的谢濂山(笛)、梅村泰伯庙的田琴初(云锣)、赵锡钧(托音二胡、飞钹)等在无锡道乐界负有盛名的“十不拆”道乐诸家都交往甚密,热衷于与其学习交流、同台演奏、切磋技巧。
据“十不拆”之一—火神殿的尤墨坪之子尤武忠②尤武忠(1932—2009年),无锡道教音乐家,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道教音乐)。回忆:每当他们位于阿炳主持的雷尊殿东边隔壁的火神殿举行道场法事,阿炳“也常常来掺和,不管哪张位子都能坐,难不倒他。有时候小道友练功课,想早点歇,做快了。华先生听到了会走过来,自己参加做,把节奏放慢。华先生要求道友按规矩做,不能草草了事”③尤武忠口述:《当年“小墨子”回忆华先生》,褚洪深整理,载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锡惠公园管理处、无锡市道教协会编:《道教音乐传人—民间音乐家华彦钧》,无锡:无锡市星联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第38页。。由这段口述史可见阿炳与道乐同行好友关系之融洽,以及作为“小天师”的阿炳在民族器乐领域十八般乐器的样样精通,还可窥见阿炳对道教音乐仪式的敬重与严谨的作乐态度。正是出于阿炳与各位道乐好友的密切交往,还使得他对“十不拆”(亦称“十个党”)各自的演奏特点也都十分熟悉,并可仅凭借听觉就能一一分清各人,还成为大家合作时常与阿炳互猜逗趣的嬉戏话题。
2.阿炳与俗乐好友
阿炳的习乐从不止于道乐,且其以琴会友、学琴交友的行为也是一直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之中。据说,为了学会《三六》一曲,阿炳就先后拜访过十八位琴师艺人。其中,以阿炳三访袁仁仪学习《三六》的事例最为有名。袁仁仪为第一代滩簧艺人,因其滩簧开场前皆要先演奏《三六》作为闹场,且造诣颇深。1937年袁仁仪从沪回无锡省亲,阿炳闻讯拄着竹竿摸黑跌得满身是泥前来拜师,亦最终感动袁师倾力相传,并表示“轧个朋友吧”④邹鹏:《阿炳穷是穷,但志气蛮高》,载黑陶:《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回忆阿炳》,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6-7页。。不久,袁门的徒弟邢长发以及徒孙邹文标在无锡茶楼坐唱锡剧,阿炳不要报酬每晚过来帮着拉琴,也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抗战前夕,著名苏州评弹艺人张步蟾来无锡的观前街蓬莱书场演出弹词《双金锭》,他在开书前总要先弹一首琵琶曲闹场,阿炳知道后,每次都在他演出时站在入口处聆听,琵琶弹完开始说书时方才离去,风雨无阻。后来张步蟾得知此事,感其诚恳,将《龙船》传授与他。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民间二胡的两位宗师,阿炳与周少梅之间也是有过交集的,两人初识于1920年左右。1934年周少梅从上海百代唱片录音回无锡途中,又拜会了阿炳,两人合乐,尽兴而归。阿炳也曾向周少梅学习过《龙船》,并对其“一口气弹到十三只龙船,每只龙船后都夹有‘丝春’(即锣鼓打击之声)”⑤倪志培:《周少梅的艺术生涯》,载顾山镇人民政府编著:《国乐先辈周少梅》,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38页。赞叹不已,连称高手!
而阿炳认识周少梅,其另一层更大的意义还是通过了周少梅认识了他的学生—刘天华。
(二)阿炳与学院派音乐家的交往
1.阿炳与刘天华
阿炳与刘天华作为近现代中国“民间二胡”和“学院二胡”的杰出代表,两人之间原本并不认识,而是1917年刘天华师从周少梅学习,通过周少梅的介绍后,稍小两岁的刘天华认识了阿炳,并有过两次短暂的交往。
(刘天华)第一次拜访阿炳是在无锡,时间大约在1918年。二人见面后,交流了二胡演奏技巧。当时,阿炳还演奏了“三弦拉戏”,这对刘天华启示很大。第二次会面,是在江阴县顾山镇。那时,阿炳去妻子董翠娣的家乡北漍镇进行数天演奏。归途中,曾在顾山镇周少梅家待了一天,刘天华闻讯从江阴坐船赶来。二人相见,又进行了二胡演技交流。不久,便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了。⑥顾志:《周少梅有关史料(摘录)》,载顾山镇人民政府编著:《国乐先辈周少梅》,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147页。
同样的(口述)史料在阿炳与黎松寿的谈话中所谈及他与刘天华的交往时,阿炳本人也如是叙述呼应:
他(阿炳)又关心地问我关于音乐学院学琴的事来,当听我说正跟储老师学习刘天华学派的二胡时,他截住了我的话茬。插口道:“刘天华,我认识。”阿炳从未提过他和刘天华有过交往,所以有些出乎意料,于是我好奇地问起他是怎样认识的?
说来话长,还是周少梅为我介绍的呢……刘天华态度非常谦虚,横一个“请问”竖一个“讨教”。他拉的二胡恰像他的人品:“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幽雅、文静。另外,他的琵琶功力也颇扎实。据周少梅说,民国十年后,他去了北京,在大学里教二胡琵琶。不料,如此少有的人才,四十不到便去世了,可惜呀!可惜!”⑦黎松寿:《我所知道的阿炳》,《华乐大典·二胡卷(文论篇)》,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这两段口述史料中阿炳与刘天华见面的时间基本一致,即刘天华1922年北上之前的数年左右。阿炳与刘天华在切磋二胡的过程中,两人之间互为知音、惺惺相惜。阿炳还表达了对刘天华英年早逝的扼腕叹息,皆堪为近世音乐史之佳话。
2.阿炳与宗震名
宜兴二胡演奏家宗震名,为周少梅嫡系弟子。1920年前后,宗震名师从正在无锡三师任教的周少梅学习二胡,此期间(1917—1922年)也正值在常州中学任教的刘天华向周少梅集中学习之时。故而,作为周少梅的共同弟子,他与刘天华也有同窗之谊。
而且,在此期间,宗震名曾先后两次与阿炳在无锡的街头相遇,还互拉了几首曲子交流了琴艺。阿炳称宗震名“指音很好”,宗震名也向阿炳请教了民间二胡满手花音的技巧。他的《二胡经》中的部分内容即是根据与阿炳交往的诸多第一手资料撰写而成:“阿炳拉胡琴,用的大筒子,竹筒声音响,木筒声音膛;弦长高把位……阿炳说,我拉胡琴是轻轻重重、快快慢慢、热热闹闹。各个指音要如人说话,死板了的胡琴人跑空。”对于阿炳的满手花音的绝招,则如是记录:“花音是民间二胡的一大宝。单弦独奏不可少,花指花弓奏花曲……”而对于阿炳所拉的《二泉映月》,宗震名则以“运弓好比水中鱼,指风犹如采花蜂”来描绘。较为难得的是,其《二胡经》中还记载了杨荫浏为阿炳录音时,阿炳谦言“叫花子胡琴,油腔滑调,由原来的满手花音改为半手花音,已逊色不少了”⑧岳峰:《宗震名和他的〈二胡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94年,第3期,第31-32页。。
3.阿炳与黎松寿
作为阿炳的同乡,储师竹的高足,二胡演奏家、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黎松寿与阿炳则是保持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与阿炳家是只隔了24户人家的邻居,再加上其舅舅是阿炳的私塾同学,黎松寿很小就结识了阿炳,并耳濡目染得到了阿炳的真传,一直被阿炳及其家人亲切地直呼其小名“松倌”。两人拥有较多的共同话题,成为了贯穿一生的忘年之交。1948年冬天,黎松寿重回无锡,在此期间,阿炳每隔两三天都由其养女搀扶来黎松寿家中谈天说地,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阿炳还时会带上酒菜来黎松寿家中独酌,在一口气好饮三四斤绍兴酒后,常会借黎松寿的二胡拉个不休。⑨黎松寿:《江南民间艺人小传—瞎子阿炳》,原载于《晓报》,1950年5月12日起连载,转载于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锡惠公园管理处、无锡市道教协会编:《道教音乐传人—民间音乐家华彦钧》,无锡:无锡市星联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第215-216;216页。
这段时间,他在黎松寿家中再次较为集中地听了刘天华的二胡曲,尤好《独弦操》。在黎松寿为阿炳写的小传中如是描绘:“……他至少曾叫我为他演奏过(《独弦操》)二十遍以上。西洋乐器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小提琴,我的那部莫扎特所作的弦乐四重奏唱片,他每次来,都要听过一遍才肯动身回家。”⑩黎松寿:《江南民间艺人小传—瞎子阿炳》,原载于《晓报》,1950年5月12日起连载,转载于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锡惠公园管理处、无锡市道教协会编:《道教音乐传人—民间音乐家华彦钧》,无锡:无锡市星联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第215-216;216页。
黎松寿作为一生致力于阿炳及其音乐的发掘、传播者,阿炳与学院派二胡之间的联络人,由其最早向杨荫浏与储师竹推荐了《二泉映月》,从而搭建了学院派与民间二胡的正式会晤。之后,他还参与了阿炳音乐的抢救采录工作,共同编定了《阿炳曲集》,与储师竹一同为《二泉映月》拟订弓指法,《阿炳曲集》中的《阿炳演奏胡琴的姿势》《阿炳胡琴的装配》《阿炳胡琴指法的几个特点》三篇文章亦都是由他撰写,并以亲历者的身份撰写了《我所认识的民间艺人阿炳》《阿炳的绝唱》等文章,都成为阿炳研究中较为珍贵的资料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决定聘请阿炳到校教学,征求阿炳意见的信也是由黎松寿专程送到阿炳家中,因阿炳病重,已无力应聘”⑪黄大岗:《杨荫浏和〈二泉映月〉—曹安和访谈录》,《音乐研究》,1998年,第1期,第12页。。因而,黎松寿是贯穿在阿炳一生始末的重要人物,也是对阿炳举足轻重的挚友。
4.阿炳与杨荫浏
阿炳与其无锡的另一乡党杨荫浏也是故交,在杨荫浏的《阿炳小传》中记载,他与阿炳有过四次比较密切的交往。
第一次是他少时12岁(1911年),即师从长其六岁的阿炳学习在“三弦和琵琶上寻到‘三六’‘四合’和其他一些曲调的弹法”⑫杨荫浏:《阿炳小传》,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但由于杨荫浏的父亲不喜欢阿炳,认为阿炳不甚讲究礼节,处世随便,不如之前陪读的颍泉老实可靠,一度打算不让阿炳再来。但少年杨荫浏与阿炳甚为投机的,“可我执意要向他学音乐,父亲只好依我”⑬乔建中整理:《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10;6页。。而且,“父亲也知道,如果不向阿炳学习乐器,我会更加调皮,这他也不高兴。所以,还是勉强同意我拜阿炳为师。”⑭乔建中整理:《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10;6页。就这样,阿炳两三天来教一次,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直至杨荫浏去天韵社师从吴畹卿后,华杨二人就此话别。可见,华杨二人起自少年小伙伴阶段的友情,亦可见其弥足珍贵。
第二次是时隔25年后,亦如杨荫浏先生回忆中所说“阿炳年轻的时候教过我,他变成瞎子后我又教过他”⑮刘再生记录整理:《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第25页。。1937年春,阿炳向杨荫浏请教他在天韵社师从吴畹卿习得的无锡派《华氏琵琶谱》之武套大曲《将军令》。是时,已经目盲的阿炳要杨荫浏拨着他的手指,在琵琶上摸索《将军令》中“撤鼓”的弹法。
第三次是1946年夏,杨荫浏为无锡道教艺人赴沪演出前排练时,邀请阿炳前来旁听。阿炳听后也表达了对以往乐事的感慨与怀念:“我听着听着,仿佛在和大家一同演奏,以前乐事,重上心头。真是不可多得。”⑯杨荫浏:《阿炳小传》,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
最后一次,即是1950年,在黎松寿、储师竹的适时引荐下,两位步入“天命”之年的无锡籍音乐家,以不同的社会身份,再次相聚故里,并完成了被音乐学界称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田野调查”—对阿炳音乐的采访录音。录音结束之后,阿炳再次提出和杨荫浏合奏一次《三六》,阿炳在琴上拉出各种花腔变化,要杨先生追着他的演奏进行。合奏完了,阿炳觉得十分的痛快,并对杨荫浏感慨道:“可惜我们不大容易会面啊!”⑰杨荫浏:《阿炳小传》,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
与黎松寿一样,杨荫浏也是贯穿阿炳一生的挚友,还是阿炳生命中的贵人。毕竟,如果没有杨荫浏的采录,世人可能至今也不知道这位日后为世界瞩目的瞎子阿炳与他的《二泉映月》。另一方面,阿炳在杨荫浏的一生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少年时代就能遇到阿炳这样一个具有极强个性并带有传奇色彩的天才,“不会不在一个聪颖、敏感的少年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烙印和深刻的、尽管有时是潜在的影响……并有一年的时间沾其恩泽、沐其雨露、从其耳提面授,是杨荫浏的福气”⑱田青:《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页。。
二、交往史视域下阿炳的音乐观念与行为阐释
(一)阿炳与民间艺人圈交往所折射的音乐观念与行为
1.道乐之友—身份认同
通过前文阿炳与民间艺人交往史料的梳理可见,阿炳乐友的第一圈层(按其交友的时间顺序)是以道教乐师为主,尤其在其尚主持雷尊殿,未走向街头卖艺之前,他主要的交友范围是无锡道教界“十不拆”等诸位乐友,且交往甚密,交流频繁。在此过程中,阿炳学习了道乐演奏的技艺,并表明了对其作为道教音乐家的自我定位,对此身份的高度认同,以及深受道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积极入世、倔强的个性,与阴阳互济的哲学世界观。
2.俗乐之友—博采众长
阿炳与俗乐艺人的交往,主要体现为对滩簧与江南丝竹的学习交流。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与《三六》之间的渊源。为了学会这首《三六》,阿炳先后拜访过十八位琴师艺人,包括拄着竹竿拐杖摸黑跌得满身是泥前来拜师三访袁仁仪也只为专学该曲。他与“十不拆”之一尤墨坪的交往中,“两人合奏《三六》,父亲(尤墨坪)操琵琶,阿炳拉二胡,两人就喜欢这一首,不弹其他”⑲尤武忠口述:《最难忘记的是阿炳击鼓》,载黑陶:《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回忆阿炳》,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乃至于与杨荫浏的交往中,两人也是起于少年时教习此曲,止于离世前最后合奏一次《三六》而终。因而这首《三六》也成为这两位20世纪最杰出的演奏家与理论大家之间友谊的见证。
可见,在阿炳的音乐生涯中,博采众长十八家为学《三六》,与多位挚友合奏只弹《三六》。这首贯穿其一生的《三六》与那首被他本人称之为《依心曲》的《二泉映月》一起,亦可算是阿炳内心深处最为钟爱、酷爱的乐曲了,而饱含着十分特殊的分量与意义,并成为其生命的绝响。
这一现象背后亦无不发人深思:首先,终生驻居于苏南锡地的阿炳,自幼熏陶浸润于滩簧与江南丝竹等乐种之中。而这首江南丝竹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三六》,全曲洋溢着明快、灵动、雅致、悠闲之风。因而阿炳对其偏爱,并热衷于以满手的即兴花腔对应表现之,自是情理之中。另一方面,通过阿炳对《三六》的偏爱,还可看出阿炳的音乐审美喜好是偏于奔放刚劲华丽的风格类型,而不喜悲悲戚戚,以及过于委婉细腻之风。这一点在其《听松》《寒春风曲》,乃至《二泉映月》等其他曲目中也可得到更为全面的印证。
(二)阿炳与学院派朋友圈交往所折射的音乐观念与行为
1.民间艺人—学院教授
作为民间艺人的阿炳,处于长期底层生活的境遇,及其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生活的边缘化,尤其是在当时强势政治、军事推动的外来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阿炳对其音乐并无太多的底气,更鲜有文化自信。对于后来成为绝世之作的《二泉映月》,在阿炳的嘴里也一直只是“随便拉拉”的《依心曲》,而当黎松寿告知他将其二胡曲记谱后在音乐学院演奏传播时,阿炳嗫嚅喃言:“你怎么把我的丑出到了音乐院?”当黎提出要听他拉一曲的要求时,阿炳如是回应:“我的老一套,你难道听得还不够?你年轻力壮,正从名师学习,该你拉给我听啦……确实是我随意乱拉的……岂可和刘天华的曲子相比,有谁想学它?”⑳同注⑦,第154-155;154页。
可见,虽然亦不排除阿炳在艺术面前的谦逊态度,但更多还是体现了身为民间艺人的阿炳对于作为知识阶层“文化人”的北大教授、学院派二胡演奏家身份的刘天华及其群体油然而生的一种由底层而上的“仰视”,以及对刘天华个人及其文化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的敬重。尤其在他与刘天华谋面交往后,真切地感受并领略了他“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幽雅、文静”㉑同注⑦,第154-155;154页。的学识人品而更尊重有加。
2.国乐改进—民间传统
对于刘天华的二胡曲,据载,阿炳曾经有过两次较为正式的聆听。第一次是1920年左右,阿炳、刘天华、周少梅三人的第一次会晤时,由当时尚在常州五中任教的刘天华本人演奏了他尚未最后定稿(定名)的《安适》(即《病中吟》)一曲,阿炳听完,表示大开眼界后,评论道:“琴音飘逸清空、斯文而雅,书卷气十足恰如人品。只是韵味稍逊浓郁,阳刚之气不足。若能刚柔兼蓄那就尽善尽美了。”㉒黎松寿:《玉皇殿中三知音》,载顾山镇人民政府编著:《国乐先辈周少梅》,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153页。阿炳第二次较为正式地听刘天华的作品则是1949年4月清明期间,由黎松寿给阿炳演奏了《良宵》与《病中吟》两曲。显然阿炳对于后者更有感触,并首先从民间二胡的审美出发,对用弦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曲子很惹听,只是弦脚太松(空弦定音),外加配用弦线不是丝弦而用钢丝弦,故而味道(音色)太薄太淡。”另一方面,阿炳同时也对学院派文人二胡的曲名发出了由衷的钦佩:“毕竟是读书人学问大,曲名题得多确切漂亮!”㉓同注⑦,第155页。
阿炳对刘天华二胡曲的点评虽言语不多,但却精练、准确地表达了他的音乐美学观。其中,“韵味稍逊浓郁”折射出的也是民间二胡学派对学院派二胡的看法,刘氏“国乐改进”思想下创作的二胡曲,在长期扎根浸润于民间音乐的阿炳听来,第一感觉还是韵味略“淡”而觉得不够过瘾。同样的观点,另一位国乐宗师杨荫浏也曾于只言片语中流露些许:“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是他在民间音乐基础上个人的创作,但不够丰富。”㉔同注⑮。
3.佛家苦修—道家阴阳
阿炳对刘天华二胡曲评论为“阳刚之气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一语击中“要害”。首先,他所听的《病中吟》之创作背景本就是表现刘氏对时局的彷徨无助之情。即便是刘天华的其他同类型表现原苦意识的乐曲如《悲歌》《独弦操》《苦闷之讴》,应也会给阿炳同样的感觉。而能与阿炳内心粗犷、挺拔倔强性格趋向相契合的,估计也只有《光明行》了。其次,究其根源还在于华刘二人不同的家庭出身背景与不同的宗教信仰影响:刘天华的母亲笃信佛教,在刘家学佛的影响下,佛教文化的善果轮回、苦海修行的思想对刘天华的个性塑造及音乐风格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阿炳出生于道士之家,道教文化中顽强的生命意识对其人其乐都影响深刻。在其音乐中,“从未直截了当悲悲切切地诉说自身的苦难,或抗议社会的不平,或多愁善感地流淌痛苦的眼泪……阿炳是淡淡的倔倔的沉沉的阿炳……”㉕赵晓生:《阿炳启示录》,《音乐艺术》,1994年,第1期,第2-3页。其次,道家阴阳(对立、统一、互化)的观念对阿炳的世界观、哲学观、音乐观的形成也是影响深远,如其《二泉映月》中就具有明显的道乐特征:两个主题在旋律形态和性格,以及变奏发展幅度上的对比性都构成了一静一动、一阴一阳的互补关系,体现了阴阳互济之美。
所以,无论是从阿炳与刘天华迥异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社会身份,及其倔强反叛的个性来看,还是其深受道教文化影响下“阴阳相济”的音乐观念来看,在阿炳听来的刘天华的文人二胡曲自然是有些“阳刚之气不足”,而提出“若能刚柔兼蓄那就尽善尽美了”的论点,也体现了阿炳朴素的道家音乐美学观。
4.单薄淡雅—浓厚宏亮
此外,阿炳在聆听黎松寿演奏的刘天华二胡曲时,所提出的诸如“定弦松、味道(音色)太薄太淡,声音也不够响亮”,则首先是源于阿炳的二胡用弦是比通常的琴弦粗一级的老弦、中弦,绷得紧,且千斤高,琴弦的有效长度极长,一般人亦难以驾驭。但在功力深厚的阿炳手里,其琴音出音宏亮、音色醇厚、穿透力强。
当然,在阿炳听来刘氏二胡的“太薄太淡,声音也不够响亮”,还源于两人演奏场域、功用的不同。阿炳的演奏是为了卖艺谋生,因而其或为“行街式”的“边走边拉”,或为在诸如崇安寺这样人流嘈杂之处演奏,在此等室外广场型文化中,也就练就了阿炳出音宏亮且具有压住喧闹穿透而出的琴音特征;而刘天华的学院派文人二胡,则是属于精致抒情的“室内乐”类型,一派娓娓而谈的融洽之风。只发衣食无忧的闲居之吟,而自然无需两弦裂帛之音。这里折射出的是传统的民间托音二胡与现代学院派二胡在制弦的材料(钢铁、蚕丝)、定弦的高度(d1—a1、g—d1)、有效弦长,以及运弓按指等诸多方面差异。
这方面,杨荫浏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民间二胡多以能拉粗弦为贵,如天韵社的沈养卿、南北二陈之“南陈”陈公坦,以及演奏“十番鼓”道士所用的二胡皆为粗弦。而“蒋风之、陈振铎把弦弄得细,用纸卷筒的琴码,声音小,噪音就小了。……可惜刘天华死得太早。阿炳用老、中弦,如果刘天华在,我要告诉他的”。杨先生认为,刘天华的学院派自有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但对于音色的看法仍是认为其“单薄、不浓厚,瞎子阿炳的音色浓厚……”㉖同注⑮。。的确,也唯有醇正厚重之音方能承载阿炳浑然天成、气度磅礴之乐。
综上,阿炳对刘天华二胡曲的乐评,体现的其实是近代二胡发展历程中民间派与学院派的观念碰撞。同时,还体现了阿炳不卑不亢的性格风骨与表达得体恰当的真知灼见。
这对20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位江苏籍二胡宗师,虽同出生于苏南吴文化圈,但一为道士之家,一为知识阶层。一个以街头风雨为伴,惠泉为邻,以道观、市井为其活动的区域,传播其旷世二泉;一个以学校教育为基地,以现代舞台为表演空间,传承其十大名曲。阿炳在其《依心曲》中倾述着一个入世的孤傲灵魂对现实苦难的感受与抗争的张力;刘天华则在其《空山鸟语》中抒发着一个出世文人心态的“闲居之吟”。刘天华“以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身份投入世纪初的文化变革运动……推动整个民族器乐领域的现代化改进浪潮,因此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㉗乔建中:《二胡艺术的一百年》,载《华乐大典·二胡卷(文论篇)》,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3页。。而本止于无锡街头闻名的阿炳则直至20世纪50年代去世,其作品得以(部分)采录整理后,方为世人所知。两人以“同时代不同身世、同地域不同经历、同兴趣不同接受、同自学不同追求、同擅长不同侧重、同演奏不同风格、同创作不同贡献”㉘杨瑞庆:《比较研究刘天华和华彦钧的二胡曲》,《交响》,2001年,第2期,第39-43页。,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中,以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音乐语言风格与创作手法为当代二胡艺术高高树起了两面大旗。
结 语
本文在围绕对阿炳“朋友圈”梳理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与阿炳的心灵对话。可为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阿炳其人其乐提供一些更为鲜活、真切的视角。
遥思历史,阿炳交友为哪般?他结交道友“十不拆”为学道乐,他交袁仁仪、尤墨坪等人为学《三六》,结交张步蟾为旁听剽学《龙船》,他交外出学习、间或回乡的黎松寿,是为了了解更多外面的音乐讯息。
而且,阿炳交友的年龄跨度也很大,既有其自幼学习道乐时年长于他的诸位乐师,也与袁仁仪的徒子徒孙结成忘年之交,还曾向比他小二十多岁的黎松寿学习广东音乐。而对于其道友火神殿尤墨坪的儿子“小墨子”,除了时常“使唤”他“拷四两老酒”,还会每天叫来面前给他念新到的《锡报》和《人报》上的新闻,以捕捉精彩的内容要点供其组织编写卖艺时“说新闻”的素材,方得名“巧嘴阿炳”。
阿炳的朋友圈是强大的,既有“十不拆”这样的道教音乐顶级高手,也有南京、北京的大教授学者。阿炳的朋友圈也是温暖的:1946年,杨荫浏在无锡为道教艺人赴沪演出排练,“阿炳来听,同里道士不让他听,要赶他走。我(杨荫浏)不让他走,还倒茶给他喝,他就在旁边听。他们的调子阿炳都懂的,像十番锣鼓啊,他都懂……”㉙同注⑮。虽世俗小道不识得阿炳之尊贵,但有一代宗师、终生挚友的杨先生将其奉为上宾,并将他的音乐向世界推广、传播,而成为不朽。
阿炳广交朋友,于是乎,他还借助朋友,得以认识朋友的朋友—刘天华。阿炳身处苏南吴地无锡城内,却也借助朋友的讯息,得以听到刘天华的二胡名曲,并做出了在那个时代乃至其后,唯有他方有资格发出对刘天华二胡曲高屋建瓴的弥足珍贵的乐评。通过忘年之交黎松寿家中的唱片机,他还由他的老弦、中弦的二胡世界走出、见识了“g—d1—a1—e2”的四弦小提琴,并对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喜爱有加。由此可见,阿炳兴趣之广泛,胸怀视野之开阔,亦是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象与认知。
所以,“对于阿炳这样一个终身生活在一个狭小天地、没有受过现代专业化音乐教育的盲艺人却能够创造出诸如《二泉映月》《大浪淘沙》等这样堪称伟大的经典之作”㉚施咏:《阿炳及〈二泉映月〉研究述评》,《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9;114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离不开阿炳自少时以来生命历程中结交的这些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朋友,这些友人不但给他带来了温情,还为其打开一扇扇的窗,铺设一条条通往更为广阔天地的路,乃至于为之争取步刘天华之后尘,进入高等学府授琴。只可惜阿炳无缘触及、无福消受而失之交臂。
阿炳交友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对他而言,每个朋友是一本书,每个朋友也都是一首曲。所以,每当问及他技术和曲调的来源,亦正如他自己所说:“也许是从道家学来的吧,也许是从僧家学来的吧,也许是从街上听来的吧……几十年来我听见了什么是我喜爱的音乐,不问教的是谁,我都跟他学;教过我一曲两曲的人太多了,连我自己都无法记得。”㉛杨荫浏:《阿炳技艺的渊源》,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10页。这些似是而非、暗含玄机的话发人深思,正是在这样开阔的视野与胸怀下,阿炳才“超越了家传师承的樊篱,博采众长,并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对音乐的领悟与创新”㉜施咏:《阿炳及〈二泉映月〉研究述评》,《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9;114页。。是其“三人行,必有吾师”的强大的朋友圈,才造就了天才的“阿炳”,绝世的“二泉映月”。
阿炳的交友经历,既是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点滴过往,也是整个社会时代的共同记忆。承载着近代以来以其为代表的诸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家博学多采、融会贯通,进而化用入髓的优良传统;也记载了以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的学院派音乐家扎根民间音乐沃土的优良学风。唯有更好地继承并发扬这些宝贵的传统,才可跨越时空,得以走进阿炳的朋友圈,走进阿炳的内心世界,去更真切地聆听阿炳的怦然心声与其旷世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