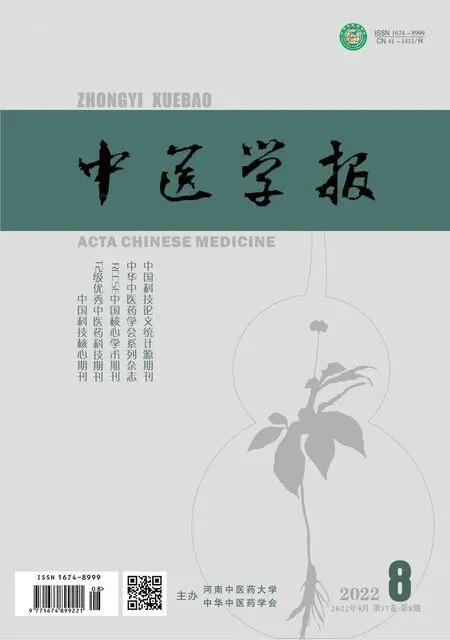王自敏基于血水同病论治肾病综合征水肿*
2022-11-15华琼何飞宋昊昱张国胜邢海燕王自敏
华琼,何飞,宋昊昱,张国胜,邢海燕,王自敏
1.河南省中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3;2.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3.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2;4.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
王自敏教授,国家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创建人、学科带头人,曾任河南省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老临证60余载,衷中参西,博采众方,学验俱丰,疗效颇佳,主张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擅于治疗各类肾脏疾病。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及体征是水肿,尤以双下肢水肿为主,实验室检查常以大量蛋白尿(尿蛋白定量>3.5 g·d-1)、低白蛋白血症(血清白蛋白≤30 g·L-1),或尿蛋白/肌酐值>3.0 mg,或伴有高脂血症为特征的一组综合征[1-2]。激素作为治疗本病的一线用药,是加重高凝状态促使并发血栓、栓塞性疾病的诱发因素,不良反应大、易反复发作[3-5],疗效不尽人意,水肿往往缠绵难消、反复无常。而中医药的干预,恰能弥补其不足,具有增效解毒,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6-8]。王老查阅大量新旧文献并结合自身多年临证经验认为,本病属于中医“水肿”之范畴,病性属本虚标实,因虚致实之证,以脾肾两虚为本,浊邪潴留为标,浊邪即痰浊、水湿、湿热、瘀血等病理产物[9]。王老强调,浊邪是由于脾肾亏虚致使津血输布、转化不利的不同病理表现,根据《黄帝内经》中关于“津血同源”的理论,可将浊邪概括为“血水同病”,血病指血瘀,水病指痰湿、水饮、湿热,两者常相互胶着为病,贯穿始终,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是NS发生发展的核心病机,指导临证每获良效,现总结梳理如下。
1 血水同病的理论基础
1.1 血水生理上同源互用血是运行于脉内之赤色液体,津液是指除血液之外,体内一切生理性水液,津(液)血均由水谷经脾胃化生而来。如《灵枢·营卫生会》云:“中焦亦并胃中……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灵枢·邪客》云:“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两者生理上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紧密相连。一是津(液)与血并行于脉中,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发挥濡润脏腑周身之功能;二是津(液)可滋养血脉,使其脉道通利,血液运行正常;三是津(液)血间相互转化,津液可内渗于脉化生为血,以补血之不足,同理,血液也可外渗于脉化生为津液,以补津(液)之不足。
现代医学认为,生理状态下,血浆和组织液间时刻进行着液体交换,以维持着血管内外液体间的动态平衡[10]。这种生理特点与中医学中津血同源的生理特点一致。津血(血水)同根同源,出入脉道内外,互生共行,周流复始,流注全身,共同维系人体水液的动态平衡。
1.2 血水病理上同病互患王老认为津血(血水)同源、同行、互用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在输布、转化时相互影响,不能将其所产生的痰湿、水饮、湿热、瘀血分而论之,这也决定了两者病理上的互联性,表现为血水同病。如《金匮要略》所述:“血不利则为水。”《血证论》述:“水病而不离乎血,血病而不离乎水。”血脉之寒、热、阴亏、阳虚、气滞均可导致血脉不通利,影响血液之运行,滞而为瘀,同时瘀血阻滞,又可使津液输布、转化不利,化为水湿痰饮,犯溢肌肤,发为水肿,此为由血病累及于水病。倘若津液之输布不得正化,则酿生水湿痰饮发为水病,碍阻气机,血停为瘀,此为由水病累及于血病。血与水既是病理产物,又同为致病因素,相互累及为患。吕仁和认为,NS涉及多个脏腑共同参与,病位在肾脾肺,涉及肝胆胃,属于本虚标实之证,以气血不足、血瘀水湿内停为该病的基本病机,而瘀湿互结贯穿疾病的始终,临证时应重视这一核心环节[11-12]。张喜奎认为水湿和瘀血皆为病理产物,常潜伏于机体形成“固邪”,贯穿疾病发生发展的始末,与诱因引触发病[13]。陈洪宇则认为水肿是NS的典型症状和体征,瘀血则是其典型病理表现,瘀血可以导致(或加重)水肿,反之,水肿又可影响血液的运行而留滞为瘀,血病与水病同时存在,临证应重视这一理论思想[14]。陈志强认为脾肾阳虚、血瘀湿阻是NS的基本病机,而血瘀湿阻则是病机之关键,常壅阻于肾络,致使经络不畅,壅堵三焦,气化不利,湿阻瘀留又成为新的致病因素,如此反复循环,致使本病缠绵难愈[15-16]。
病理状态下,当血栓或瘀血阻滞于血管内,使其流体静脉压升高,血管的通透性增加,引起水钠潴留而发生水肿[17]。反之,水肿的形成,易压迫静脉,改变血流的状态,有利于血栓的形成。这种病理特点与中医学中血水同病的病机特点相一致。
2 血水同病是NS水肿的核心病机
王老认为血水同病不仅影响血水间的正常输布、转化,也影响脏腑的气化功能,是NS水肿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发生发展的核心病机,临证时应予以高度重视。
2.1 水病为先,病势缠绵《景岳全书》曰:“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而痰涎之作……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水谷运化得正,则津液化生有源,反之则转化为水湿痰饮,变生水肿,皆由脾肾亏虚所致。而《灵枢·百病始生》云:“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脾气(阳)不健,水谷、水湿运化失职,一则酿生痰饮,阻碍气机,血聚为瘀;二则困阻脾阳,加重痰饮水湿。肾阳亏虚,一则导致膀胱气化失职,开阖不利,水无所主;二则肾阳不暖脾阳,运化失职,水湿停聚为痰为饮,妄行于肌肤则发为水肿。王老认为,脾肾主宰津液之输布、转化,是痰湿水饮化生的根本因素,而NS水肿以脾肾两虚为本,脾肾一虚必先累及水液之代谢,并以此为主要病理变化,酿生的痰湿水饮一则反克脾肾之脏,影响气化之功能;二则阻碍血液之运行,是由水病累及血病。此时以水病为主,而致病势缠绵。
2.2 血病为终,病久入络虽有由水病而致血瘀者,亦有因脾肾亏虚致瘀也。肾乃先天之本,精藏于此,又赖后天之本脾脏所化精微而充填,元气则化生无穷,而今脾脏一虚,元气化生无源,血无动力而不运,郁滞为瘀。是故“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肾之阴阳主宰一身之阴阳,阴虚则血脉失于充养、濡润,脉道不利而为瘀,或阴消阳长,虚火熬煎阴血亦为血瘀;阳气虚损,内生寒邪,血脉不得温运,凝涩而滞则为瘀,是故阴阳之亏败亦可影响血液正常运行,正如《医林改错》曰:“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血与水其性同属阴,化生同源,血瘀一则影响津液运行,津聚为痰为饮为水,如《血证论》述:“血积即久,亦能化为痰水。”二则阻于脏腑经络,阻碍其气化功能,加重本虚标实之证候。
络病理论认为,肾脏具有丰富的中小、微小血管循环系统,尤其是毛细血管襻,将其称为肾络,是输布精血津液以濡润脏腑组织、四肢官窍和排泄代谢废物的通道,以脉络丰富、血流量大、细小速缓、面向弥散、末端联通,双向流动,津血互换为特点,在病理上具有易留瘀存滞、酿积形成的特征[18-19]。日久肾络微型癥瘕形成,导致肾脏功能和结构的变化[20-22]。王老认为,肾络一旦瘀阻,一方面,肾腑气化失职,或脾阳不得肾阳之温煦,运化不利,水液代谢失常;另一方面,肾络气机受阻,血水输布不畅,血停水阻,是由血病累及水病。此时以血病为主,是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正所谓“久病入络”。
2.3 现代医学对血水同病的认识血水同病贯穿于NS水肿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是水肿反复加重、缠绵难愈的核心环节,现代医学研究也佐证了“血水同病”是NS水肿的核心病机。从病理层面来说,低白蛋白血症一方面引起血管内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水液从血管内渗入组织间隙引发水肿;有效循环血容量下降,激活神经-内分泌调节系统,表现为兴奋交感神经、增加儿茶酚胺的分泌、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增加抗利尿激素的分泌,从而使肾小球血流量和滤过率下降、增加远曲小管对钠的重吸收,导致继发性水钠潴留而发生水肿。另一方面造成肝脏代偿性合成蛋白增加,导致凝血、抗凝和纤溶系统紊乱,加之高脂血症、激素和利尿剂的使用致使血液浓缩、黏稠度增高,使机体一直处于高凝状态,发展为血栓、栓塞性疾病[10,23-24]。
从微观层面来讲,结合NS的病理特点和中医“取类比象”“司外揣内”之思维,有学者将上皮细胞足突融合属于“虚”的范畴,常辨证为肾虚不固;电子致密物的沉积归属于“实”的范畴,常辨证为“湿”邪;肾小球硬化、纤维化常辨证为“瘀”“肾络痹阻”。并以此为微观辨证纲领,结合临床特点的不同,应用于NS的各病理类型,研究发现在每一病理类型中证素常相兼而存,属本虚标实之证,如膜性肾病的病证特点符合“湿”和“瘀”的特性,足突融合符合“肾虚不固”的特性[25]。微观辨证弥补了血水同病在宏观辨证上的不足,针对一些临床症状、体征不典型且无证可辨的患者而言,病理类型的诊断有助于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2.4 激素是加重血水同病的关键因素中医认为激素属纯阳之品,具有温热之性,归属肾经[26],易助阳生热、煎灼阴血、耗气伤津、壅滞气机,酿生痰浊、湿热、血瘀。王老认为,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将导致“壮火食气”的不良反应,随着激素剂量的增减、作用时间长短,NS水肿的病机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使脾肾更虚,血水同病更重,相互夹杂为患。
足量期:温热性激素阴血相搏,阴不胜阳,出现阳偏盛、阴亏虚的病理状态,即阴虚火旺之证候。激素煎阴熬血,或与水湿相合,或酿毒生热,从而酿生血瘀、湿热、热毒,故阴虚火旺常与血瘀、湿热、热毒相兼为病。
减量期:温热之邪逐渐减少,阴精耗损逐渐减轻,但余热稽留、阴气难复,阴伤气耗,表现为气阴两虚证候。一方面气虚则津血运化无力,血瘀、痰饮、水湿内生,加重血水同病;另一方面卫表不固,外邪易侵,产生变证,发生感染性疾病,出现反跳现象或治疗效果不佳,进一步加重气阴亏虚。故气阴两虚多夹有血瘀、痰饮、水湿、外邪。
维持期:阳热之邪进一步减少,阴虚症状进一步减轻,但阴气难复,阴损及阳,导致以阴虚为主的阴阳两虚证候。临床上常在阴虚症状的基础上,伴有畏寒、肢冷、水肿及腰以下为重的阳虚证候。
停药期:阳虚症状显著,阳损及阴,阴气化生无源,此期表现为偏阳虚型的阴阳两虚型证候。临床上常在阳虚症状的基础上,伴有五心烦热、口渴欲饮、失眠盗汗等阴虚证候。
至维持期和停药期时,阴阳两虚证显著,脏腑气化功能失常,温润之力衰退,津血转化不利,加重痰浊、水湿、瘀血,与其相兼共存、相互胶着为患,导致患者既怕冷又怕热,免疫力低下,易罹患他病,使其缠绵难愈。
3 血水同治是NS水肿的核心治则
基于本病以“血水同病”为核心的病机特点,王老提倡以补益脾肾为基本治则,血水同治为核心治则,攻补兼施,与激素联合应用,分期论治。血水同治是指血治和水治并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仅指血治之活血化瘀与水治之利水消肿并用,血治和水治同等重要;从狭义来讲,血治包括活血化瘀、活血通络,水治包括利水消肿、祛湿化痰、温化水饮、清热化湿。血治和水治有主次之分,根据病邪性质及所犯部位不同,灵活选择相应的治则。
足量期常选知柏地黄丸加桃仁、红花滋阴利水、活血化瘀,若夹有湿热、热毒证候者,加入薏苡仁、土茯苓、半边莲;减量期常选参芪地黄丸加益母草、鸡血藤、丹参益气养阴、补益脾肾、活血利水,夹有痰湿、痰浊者常合二陈汤加减以理气化痰,夹有外邪者加用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等;维持期及停药期常选济生肾气丸合桃红四物汤加减,瘀血严重者加水蛭、地龙、土鳖虫活血通络,阴虚甚者合左归丸加减以补肾阴,阳虚甚者合右归丸加减以增强补肾阳之功。
4 典型病例
患者,女,78岁,2019年11月22日初诊。主诉:双下肢水肿反复发作6年,加重1个月。现病史:2013年因双下肢浮肿伴泡沫尿在我院就诊,尿常规:尿蛋白(++),隐血(+);肝功能:白蛋白 28.7 g·L-1,肾功能:尿酸571 μmol·L-1,肌酐及尿素正常值范围;血脂常规:总胆固醇6.71 mmol·L-1,三酰甘油4.13 mmol·L-1;拒绝行肾脏穿刺活检。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日常予以双嘧达莫片(50 mg)、瑞舒伐他汀钙片(10 mg)、阿司匹林肠溶片(100 mg)、缬沙坦胶囊(80 mg)、呋塞米片(20 mg)、雷公藤多苷片(20 mg)及规范化口服强的松片治疗。6年来曾多次在我院门诊及病房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但每次停止口服强的松后水肿即反复,尿蛋白(+~++)。1个月前停止口服强的松后双下肢水肿加重,为求中医治疗,遂来找王老就诊。刻下症见:双下肢凹陷性水肿,畏寒无发热,腰膝酸冷,疲倦乏力,腹部胀满,口渴欲饮,纳差,夜寐不安,尿多,大便正常。舌体胖大,舌质暗红,苔腻,脉沉细涩。2019年11月21日肝肾功能:白蛋白 21.9 g·L-1,肌酐 141.9 μmol·L-1,尿素 13.62 mmol·L-1,尿酸514 μmol·L-1,24小时尿蛋白定量 9 145.8 mg。小便常规:尿蛋白(++)。西医诊断:肾病综合征;中医诊断:水肿(阴阳两虚,瘀阻水停)。治法:温补脾肾,化瘀利水,方选济生肾气丸合桃红四物汤加减,处方:熟地黄30 g,山药 30 g,制附子(先煎) 5 g,茯苓皮30 g,牡丹皮10 g,车前子(包)45 g,川牛膝15 g,桂枝10 g,当归10 g,红花10 g,白芍 15 g,续断15 g,桑寄生30 g,瞿麦 15 g,煅牡蛎 30 g,桃仁10 g,枳壳10 g,大腹皮30 g,木香10 g。7剂,每日1剂,水煎服分两次温服,原西药继续服用。
2019年11月28日二诊,双下肢水肿减轻,畏寒、口渴、腰膝酸冷、疲倦乏力缓解,腹部胀满,纳差,夜寐不安,尿多,大便调。舌脉同前。中药守原方不变,继续服用21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
2019年12月23日三诊,12月19日肝肾功能:白蛋白28.6 g·L-1,肌酐107.7 μmol·L-1,尿素9.2 mmol·L-1,尿酸417 μmol·L-1,24小时尿蛋白定量1 797.9 mg,小便常规:尿蛋白(++)。双下肢水肿已消退,畏寒减轻,无口渴,腰膝酸冷、疲倦乏力明显减轻,腹部胀满减轻,纳食改善,夜寐可,二便调。舌体胖大,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处方:初诊处方中熟地黄加至45 g,加入煅龙骨30 g,厚朴10 g,刘寄奴15 g,酒大黄10 g,神曲20 g,减白芍、续断、桑寄生、木香,桂枝改为肉桂2 g。14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西药继续服用。
服中药半个月后双下肢浮肿未复发,腰膝酸软、疲倦乏力持续好转,腹部无胀满,纳食、夜寐可,二便调。之后以三诊处方继续加减治疗近1年,全身未再见浮肿。于2020年12月14日复查肝肾功能:白蛋白41.2 g·L-1,肌酐97 μmol·L-1,尿酸 238 μmol·L-1,尿素6.3 mmol·L-1,尿酸221 μmol·L-1,24小时尿蛋白定量636.4 mg。小便常规:尿蛋白(-)。
按语:本案为老年女性患者,慢性病程,长期口服强的松,每至停药期水肿、蛋白尿即反复,王老认为长期口服强的松耗阴伤阳、煎灼阴血,引起津血运化不利,血脉瘀滞,津聚水停,泛溢肌肤发为水肿而导致血水同病。瘀水又碍于脏腑经络,阻碍气化之功,加重血瘀水停,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终致正气难复,阴阳两虚。故予以济生肾气丸合桃红四物汤加减以育阴补阳、利水消肿、活血化瘀,方中加入续断、桑寄生滋补肝肾,瞿麦以加强活血利水之效,煅牡蛎固摄精气以固肾元,加入木香、枳壳、大腹皮以理中焦之气,复中焦之运化。活血与利水相配以期血水同治,以“通”促“补”,诸药相配,切中病机。二诊时水肿减轻,且无辨证,效不更方,故守原方继续服药。三诊水肿已消退,但仍畏寒、腹部胀满、尿蛋白仍(++),王老认为此时患者血瘀水湿尚有遗留,且激素停用后,正气难复,湿邪缠绵,津血运行不畅,故在二诊处方中熟地黄加至45 g补肾精、通血脉,桂枝易为肉桂以加强温补肾阳,与煅龙骨、煅牡蛎相配以固摄肾元,木香易为厚朴燥湿行气除满以畅中州,并加入刘寄奴、酒大黄加强活血通络之功,神曲健脾开胃,并减去白芍、续断、桑寄生。诸药相配,标本兼顾,血水同治,切中病机,故临床效果显著。
5 结语
NS水肿属因虚致实、本虚标实之证,其基本病机为脾肾亏虚,但又以血水同病为核心病机,临证时应重视这一核心病机,在辨病与辨证的基础上,以补益脾肾为基本治则,血水同治为核心治则,根据血病和水病之轻重,选择血治和水治之主次,灵活遣方用药,方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