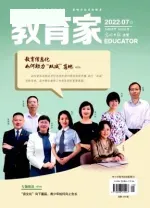“植物人”史军:找准“生态位”做科普
2022-11-11王梓霖
文|王梓霖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里,植物如果没有一点“秘密武器”是无法繁衍的。史军称自己为“植物人”,从一名立志成为科学家的小小少年到科普杂志作家再到系列科普图书策划人,从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系统进化专业博士,史军研究过的植物不下百种,在自然界中他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对很多事物充满好奇。
守护好奇心,并非科普的全部
作为一名80后,那时的教育还没有这么内卷,花鸟鱼虫是史军幼时的忠实玩伴。春天的香椿芽、夏季的荷叶与莲蓬、秋风吹落的核桃树叶以及冬雪飞舞时培育的绿豆芽,都在他的童年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香椿芽为什么由红变绿?荷叶为何一尘不染?核桃皮为什么如此坚硬?绿豆为什么能在冬天发芽?在戏耍间,史军产生了不少疑问。
大学里,将课堂搬到野外的老师让史军真正开始爱上植物,而后的导师让他渐渐明白什么是植物学,幼时的各种疑惑都慢慢有了答案。硕博期间,史军研究的是兰科植物的繁殖与保护,为了研究兜兰属植物的传粉媒介,他每年有3~4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背着相机拍摄图像、观察照片、统计结果,其间观察到兰花等植物的生存方式。自然界的兰花有两万多种,它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有的生长在土壤里、树叶上,有的生长在石缝间,有的喜欢干一点、有的喜欢湿一点,有的喜欢暴晒、有的喜欢全阴。史军说道:“我们常常感叹于那些生长在石壁间或者其他植物叶片上的兰花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但实际上只有那里才适合它们生长,避开了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
自然界中,不同植物有着各自适宜的生长位置,人们认为艰苦的环境或许正是这类植物理想的生活区域。在生态学上,这样特定的生活环境被称为“生态位”。比如,即使在最陡峭的岩壁中,野草也同样能够欢快地摇曳,装点着这个世界。
与植物的生存智慧如出一辙,每个人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如果用一套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去思考问题,你就能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自己要做的事情。”,史军说。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能在激烈的内卷中保持相对的清醒,明白每个人各有其能力边界,不能简单地评估某件事物,而只要找准了“生态位”,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边界内作出一番成就。
博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出于个人爱好,史军开始给《科学世界》杂志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毕业后,他结合现实生活与客观需要,进入《科学世界》杂志社成为一名编辑,专职做科普。“我比较喜欢植物学,做文字科普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说,我很幸运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所以,即便彼时科普工作不算热门,史军也未曾离开过这个看起来似乎并非十分舒适的行业。从面向成人做科普到给孩子们讲科普故事,他在这个领域已工作了14年,现在仍乐此不疲。
他努力的方向是让孩子们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爱上科学,并习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常说,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但这并不是全部。理想的科普是让我们每个人更清晰地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生活。”史军期望孩子们从身边的植物出发,了解不同植物间的关系、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类比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由植物思考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会让人们保持平和,既不会过于‘内卷’,又不会过于‘躺平’。”
科普不等于科研的简单化变形
很多看似简单、割裂的事物,实际上都能以一种类似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进行分析。大学里,史军发现生物学是一门庞杂的学问——植物的毒素如何保护植物生长,实则为化学问题;植物的繁殖效率如何,涉及统计学问题;等等。工作多年后,他真正领悟到各门学科背后的底层逻辑是相近的,也看到了孤立事物背后的联系,比如找到人文、地理、历史、经济与植物间的联系,出版《中国食物·蔬菜史话》《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等著作。于史军而言,这是一个由“术”至“道”的过程。
随着2022版义务教育新课标的实施,学校中跨学科教育的开展恰逢其时,这是教会孩子们将知识融会贯通的“术”。史军说:“跨学科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孩子学会从多个层面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也是我们当前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普及,知道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期望更多人经由科普,主动接触科学,领悟科学背后的“道”。

史军,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科普图书策划人。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植物塑造的人类史》《中国食物·水果史话》《中国食物·蔬菜史话》《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等。作为主编,策划出版了“少年轻科普”系列少儿科普图书。曾担任系列科普视频《植物有话说》《一点植物学》主创,《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水果传》《风味人间》等多部纪录片科学顾问。
有人认为做不了科研的人才会转向科普。“这是极大的误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被称为经典的科普著作,如《时间简史》《物种起源》《从一到无穷大》,都是大科学家写成的。科普同样需要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只是相比于科研工作者需要进行实验,我们更多的是要琢磨怎样将自己学到的科学智慧以更好的方法传播出去。”此外,科普也不是科研之外“捎带手”的事。刚到《科学世界》工作的那一年,单位安排史军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宣传工作,他将杂志的一篇文章做成PPT讲给展台前的公众。“没有人听”,史军说。与同行交流时,他们不需要做太多铺垫,但怎样结合公众的兴趣传播科学,其实是很考验学问的一件事。若不能将科学知识与生活建立起强相关,或是不能做到“话中有梗”,就无法吸引大众去主动了解。
要做好科普,科普工作者除了要保持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还要能因获得新知而感到满足,并且具有分享的欲望。“要给别人分享,自己兜里不能只揣着仨瓜俩枣。”如果某种植物没有见过,或是生长在陌生的区域,都会引起史军极大的兴趣。有时野外郊游途中,大家一起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史军又不见了,一扭头准能发现他蹲在路旁给花草拍照,之后就开始研究起来,原本一段十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他可能需要个把小时。科普杂志编辑出身的史军,最喜欢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科普,在书写的过程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梳理收集到的资料,重新解构、剖析,深入而完整地表达观点。但为了吸引更多受众,书写之外,他也努力挖掘那些公众感兴趣的传播点,制作短视频,开展线下讲座、野外研学,参与节目录制、微博互动,等等,尽可能采取丰富的形式开展科普,将有趣、有料的植物学知识传递给大众。
如今,每天都有不少网友在微博上与史军互动,常见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植物?能吃吗,好吃吗?”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资深的美食爱好者,他总愿意亲自尝一尝没吃过的植物。魔鬼椒让他感觉似乎有手雷在嘴巴里爆炸,神秘果让他喝醋都像是在尝小甜水,宽叶匙羹藤让他吃糖块却感觉在吃小石子。在“吃吃喝喝”中,他写出了《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等,把植物学研究应用到一日三餐中,将科学变得色香味俱全。
科普与科学教育是两码事
有时,线下科普活动结束后孩子们不知道从什么犄角旮旯里找到一片叶子就来问史军,“这是什么”,如果问倒了史军就会格外自豪,而史军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不管怎么说,科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严肃的,如果孩子们能因为我的科普而对科学产生兴趣,就会不满足于我所呈现的内容,继续寻求深入学习的机会。”这正是史军期望达到的重要目的——为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摇旗呐喊”。
随着国家对科学教育的重视,投入其中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教材的编纂吸引了更多科研人员的加入,史军也是其中之一。在开展科普的同时,他还参与到科学教育课程标准和课程资源的编制中。在他看来,科普和科学教育是两码事。科普就像是为科学教育做广告,在不违反科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吸引受众,招揽更多的人主动了解所呈现出的“产品”,愿意关注科学本身。而科学教育是按照体系化的框架教授学生科学知识,进行科研基础能力训练、科学技术应用,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科学知识观与价值观。前者没有特定目的,能调动起人们学习科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人们习惯于以科学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状态。而后者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对明晰的标准和要求,会以较为规范的程式检测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引导他们学会科学探究方法,培养其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教育者不必强求孩子在接受科普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多少知识、掌握多少能力。偶尔有家长在带孩子参与科普活动后找到史军问:“孩子对您讲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怎样才能继续培养他的兴趣,未来朝着科学家的方向发展?”史军认为这不重要,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阶段性的,能否将某种认知真正转变成兴趣,甚至变成事业,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有诸多因素影响最终的结果,家长的主观意愿对孩子并不一定能起到正向效果。若想呵护科学精神的幼苗,家长可以配合学校的科学教育,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与支撑,力所能及地发展其兴趣。比如:陪伴孩子阅读科普书籍,观看纪录片等,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带领孩子游览科技馆、博物馆、动物园等场馆,加深孩子对不同学科的印象;带领孩子走进自然,探索自然。史军既往的工作经验表明,若不能去往野外,菜市场也是认识植物的好场所。辣椒为什么是辣的?苦瓜成熟的时候为什么会变甜?我们喝的可乐中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竟然是玉米。这些都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作为一个“广告人”,科普工作者要有适应不同群体的充足准备,少儿科普尤其如此。“他们不是听不懂我们的表达方式,而是大多数情况下不关心我们表达的内容。”史军很喜欢给孩子们讲科普,因为他们会为有意思的内容而兴奋不已,讲座结束后会来到他的身旁,雀跃地表示“我以后要当一个植物学家”。当然,也会因为觉得没意思而瞬间沉默,以无声的方式表示不感兴趣。他们真实而直接的表达,更利于史军作出必要的调整。史军策划的“少年轻科普”系列图书已连续出版4年,结合7~12岁少年的认知规律,一个个模块化的故事伴着插画呈现出世界的纷纭万千、生命的丰富多样,让科学之美跃然纸上。
“令每个人感到满足的事情不尽相同,但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建立起正向反馈,将获取新知、建立新解与多巴胺通路连接在一起。就像大多数人吃了糖豆都会感到开心,我期望尽可能将科普内容做成‘好吃一点的糖豆’,让孩子们更愿意去品尝,并从中产生愉快的体验”,史军说。当被问及最满意的作品,他回答道“下一部”,随着对不同学科、对科普与科学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正在孕育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