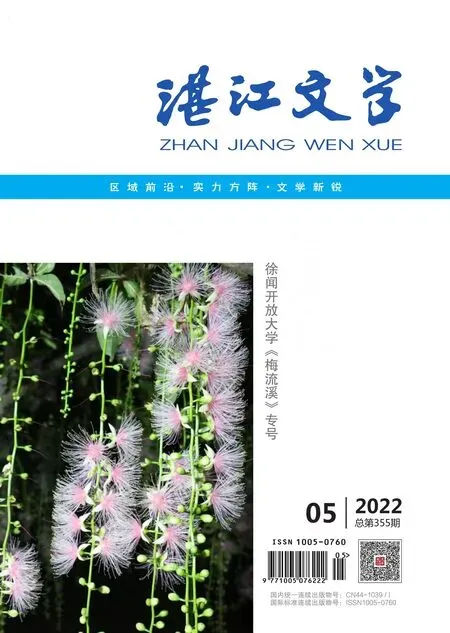怀念父亲
2022-11-11◎李飞
◎ 李 飞
每当想提笔为先父写点什么,却总是心在痛,泪先流,不能成文。清明临近,忍痛泪滴长夜,终成拙稿。
谨以此作为清明的薄礼,祭奠我的父亲。
——题记
惊蛰已过,清明将至,我对父亲的怀念越来越深切。不经意间,父亲离世已近三年。每当回到乡下老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感受到他一生活着的艰辛。
我的父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穷苦家庭,有兄弟姐妹六人,祖母因缺吃少穿而早年去世。由于大伯、二伯相继结婚成家并分家,大姑也外嫁邻村,幼小的父亲便与祖父一起承担了照顾弟妹的重任。那个时候的农村,粮食极度匮乏,一般人家都是只能吃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而米饭很少有,主食绝大多数是番薯、番薯干、木薯居多。当然,番薯叶经常就是座上的“佳肴”,还有的就是小鱼小虾腌制的酱汁。甚至有段时间,能吃上生了虫子的番薯和野菜、红树林结下的果子都算是一种奢侈。当然,父亲一家也不例外。饿得难忍的时候,父亲只好生吃番薯,或者去摘野果子充饥,甚至有“饿了吃盐,渴就喝水”以达到令人心酸的“饱”的艰难经历。好在祖父是远近有点名气的“师傅”,当时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他给六个子女起名都取意于一种花,父亲的名字就带有一个“梅”字。这或许是寄望儿女能遇事坚强、生活美好吧。有时,祖父去给人家操办一些封建迷信的事,主人家按照礼节,送给一点猪头肉、大米捏成的几个公子饼之类的东西,这可减轻了家里一两天的伙食负担,也大解了父亲及弟妹的饥饿和馋嘴。但是,为了不挨冻受饿,吃得饱一些,住得暧一些,父亲产生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毅然辞职不当代课老师,跟祖父学当石匠,想将自家的土坯茅草房建成石头墙体的房子以抵挡风雨,消除危险。后来,小叔长大了,也学会挖石头、当石匠。于是,他们父子三人合力一起,硬是建起了一间三间房的石头墙体的茅草房。好长时间,一家人都感受到了莫大的欣慰。当时,村里地少,没有工业,不搞副业,大部分村民食住还不能自给自足。因而,父亲父子三人几乎没有经常被请去建房的惊喜,一年到头收入有限,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得到多少的改善。穷困,一直是父亲多年记忆犹新的忧伤。后来,父亲还是走不出世俗的套路,结婚后也分了家。时运不齐,命运多舛。父亲孩童生活的艰难,与当时支离破碎、民不聊生的国运息息相关。即使生活给了父亲太多的磨难和羁绊,但是他也没有妥协低头过,反而是与艰难抗争,为未来拼搏,寻求一条能够改变命运的路。
那个年代,教育体制也相当落后。没有开办幼儿园,村里许多小孩子上学普遍都比较晚,10岁、1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读一年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的甚至还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帮忙农活,以增加家中的收入,减轻贫困。可是我的父亲却能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不但能够坚持读完小学,而且还读了高中。一直以来,我很少听说过父亲读书时的成绩,或许那个时候,能坚持读下去就是满满的幸福,成绩在村民们的心目中似乎常常都是被忽略。后来,我听过母亲讲述父亲报考高中遇到“贵人”的经历。因为家贫,父亲初中毕业时,祖父拿不出几毛钱让父亲去报名参加高中考试。也许是出于对全家生活的考虑,也许是出于体谅祖父多年的艰辛劳苦,父亲没有哭着闹着向祖父要钱报名,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在村中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游荡,泪水一直在眼眶打转。也许小孩子的他,已经从生活的艰难中悟出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这个时候,村里一位叫家珍的叔公走近父亲的身边,拉住他问起报名考高中的事,父亲便一五一十地道出了没有参加考试的原由。听到父亲因为没钱不报名参加考试,家珍叔公当即对我的祖父心生责备,并毫不犹豫地从裤袋里掏出5毛钱,硬塞到我父亲的手里,嘱咐父亲明早赶紧去报名,并宽慰说不用还钱,消除父亲的心里压力,让他考好试。有了报名费,父亲甭提有多高兴了,好像已经考上了似的。第二天,他揣紧短裤的口袋,一路狂奔地去报了名。考试那天,父亲将剩下的二毛钱买了包子,吃完后信心满满地参加了考试。苦心人,天不负。父亲一考即中,被当时全县唯一的一间重点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徐闻县第一中学录取。可是令人泪目的是,因为家里支撑不了,父亲没有读完高中就辍学了,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受到辍学的影响的,因为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从来都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可是那次辍学,曾影响过父亲的人生选择,以至于后来错失命运的良机,一直都无法成为城里人,虽然后来他的命运有了较大的改变。
父亲是经我的大姨丈介绍认识我母亲而后结婚的。我的母亲当时是中农家庭出身,是读完了小学的,认字可不成问题的。结婚后,她和父亲两人一起,接续承担了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分家后,在母亲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下,甚至是寒夜里的哭诉下,父亲终于答应再在村里小学当代课老师,直到后来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吃了“皇粮”,端了“铁饭碗”,工资日渐增多,小家庭的生活这才稍微有了改善。转为公办教师的父亲,一直都安心于教学,奉献于教育,深得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赞许。记得70年代,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到远离家约20公里的角尾乡潭鳌小学教书。由于经济困难,加上那时候购买自行车都要有分配指标,交通又极为不便,父亲每周都要走路往返于家校之间。有时候,他也就没能做到每个星期都回家探看年迈的祖父和年幼的子女,直到几年之后,在徐闻盐场工作的小姨丈分配到了购买一辆自行车的指标,才转让出来给父亲购买。母亲卖了一头养了两年多的母猪,加上平时省吃俭用的一点儿积蓄,花了200多元,终于为父亲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结束了父亲依靠双脚走路往返的历史。小时候,我常常听到过潭鳌小学教书的父亲说,很多时候当他上课回来,总会发现菜篮子里放有鱼、虾,而很少知道是谁送的。换下的衣服,也会被偷偷洗干净晾好。周六周日,如果他因路途较远不想回家,常常会被家长邀请去捕鱼吃鱼。活蹦乱跳的鱼一抓上来,便立即洗净切块下锅,甚至整条直接下锅,乐享原汁原味,纯天然生态。每当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父亲总会显露出几分的得意,让我不停流口水,心里羡慕不已。70年代,那是一个饥荒的年代。而当时,村民们并不宽裕啊。父亲调离潭鳌小学的那天,该校几十名学生专程为父亲送行。有的帮着推自行车,有的帮忙提行里,你一前,我一后,一路走着,说着,笑着,还扛了一麻袋的番薯干和几箩筐的小鱼小虾,好不热闹,也足见师生情长。后来,父亲先后到过龙潭小学、迈报小学、那斗小学、大黄中心小学任教,最后回到老家青桐小学任校长直到因多病提前退休。在龙潭小学教书的时候,父亲非常疼爱一位学生,为了让学生有前途有出息,他凭借自己的私人关系,硬是将这位学生转学到县城小学就读,最终他也如愿以偿。那位学生考上了全县的重点中学——徐闻中学,后来考上大学,分配在县城工作,现在也当上了乡科级干部。而那几年来,每个周日,我和弟弟还要跟着父亲在他任教的乡村小学读书。父亲总是用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搭载上我和弟弟二人往返于家校,辗转在不同乡村的乡间小路上,伴随着一个个西下的夕阳,陪伴着我俩走完小学时的求学之路。这时的父亲常常这样感慨,如果是搬运石头,几年后都可以建一间房子了。我明白父亲是在鼓励我们努力读书,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幅美好的生活画卷,抑或是一个穷困家庭凄苍的故事。在大黄中心小学任教的时候,父亲获得了一个进修进阶的机会。但是考虑到去进修花费大,可能无法让我们兄弟继续学业,同时认为自己高中没有毕业,文凭低,不一定能学好,他就让位了别人。两年后,那位进修回来的老师直接分配到县城一间直属中学任教。听母亲说,父亲还曾经因为文凭低自卑,也怕评不上浪费了300多元的评审费,让出了评聘小学高级教师的指标。父亲叶落归根,回到村里任校长的时候,下真功夫狠抓教研教改,全校大多数年级考绩名列全县小学中上水平,扭转了曾一度倒数第二三名的局面,算是对得起了父老乡亲。同时,由于学校音乐老师缺额,父亲聘请了村中一家两兄弟相继代课,满足了素质教育的需求,也为那兄弟两人后来考试进修,成为公办教师搭建了很好的平台。父亲诚实善良的本性,一直都感染着我们兄弟。后来,我也当上了教师,也曾学着父亲热爱、关心学生的教育和成长,尽到了本职责任和做人的本分。弟弟在私立学校教书,他善于转化差生,教出了成绩,也教出了名声,并与个别学生、家长往来互助,亲如同袍。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对于我来说,父亲是我名副其实的小学五年级的老师,他真正教过我的语文科,上过我的语文课,让我轻松自如就考上了徐闻中学。第37个教师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在教师节那天给父亲一个感恩的馈赠,还欠着父亲一个回报的礼敬。这是我心头永久的结,也是我永远无法抚平的疼。
在那个物资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父亲却琴棋书画诗对等都能略懂一二,而尤其擅长于书法和对联。80年代初,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是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节目。虽然市面上能买到印有《每周一歌》所播出歌曲的小卡片,但是由于缺少收音机、录音机,许多人短时间内也只是能哼上几句,难于完整唱响,过不了瘾。而我得天独厚,曾经让父亲教我学唱过特别喜欢的《我的中国心》,因为他会五线谱,可算是“五音俱全”。那时候,为了节省些家用,父亲开始自写我们家的春联。这个时候,我往往都给他打下手,帮忙倒墨汁、压紧边纸或拉直纸张。等到父亲写完了一副或半副对联停下来,我就将其移到地板上等待慢慢晾干。初写时,父亲依规依矩,抄录一些古对联来写。为了教育我们,大门门框的对联好几年贴的都是“积德胜遗金处世当遵司马训 惟善以为宝省身宜法楚书言”的内容。2003年,我家将茅草房改建成为瓦房,父亲在大房门的墙中央留下位置,用红色油漆刷亮木板,亲自题写了“雅居”两个大字挂上。随着我们兄弟三人参加工作和伴随着我们儿子的先后出世,父亲心满意足,乐享天伦,欣然提笔篡改神堂对联为“发达不能忘祖泽 平安也要谢神恩”,并在庭院大门制作瓷砖题匾“东雅园”,将门柱的春联由“殷期东雅三槐秀 展望园中五桂香”改为“三槐挺秀千年喜 五桂飘香百代欢”。我想,这是父亲为我们祈求平安、祈福美好的心愿,也是父亲认为我们兄弟能够脱离“农”字的欣慰,而从中也可见其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邻居看到父亲自写自撰春联,为省点钱,也纷纷买来纸张请父亲帮忙。父亲也总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常常是在除夕那天会操劳到傍晚,甚至更晚而耽误了我家敬神拜年。特别是对于家珍叔公,每当他拿来纸张时,父亲总是视如座上宾,停笔起身,倒热水,搬椅凳,礼貌倍加。有时硬是留下他一起吃饭,或者顺便送些年货给他。往后几年,我家买纸张的时候,干脆也把家珍叔公的算进去,一并买回来书写好,让他省心省力。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村里人也常常请父亲帮忙写对联或登记贺礼。父亲做事认真,似乎没有差错过。父亲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不但用他乐于助人的精神,诠释了对乡亲们的一腔热情,而且用他知恩图报的品德,留给了我们后人一笔珍贵的财富。近年来,受父亲的熏陶,我接续书写自家春联,也希望能帮助邻里,似有6年。近年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也都尽量抽出时间,去探看曾经要好的几位同学的母亲,或者想办法给她们红包,争取在她们的有生之年,感恩她们过去的不嫌弃,偶尔留下我这个农村的孩子,在自家中吃几顿的饭、睡一夜的觉,解决了一时的温和饱。
记忆中,父亲坐享清福的时间不长,而遭受病魔困扰的时间却很长。他曾经许多年断断续续地拉排乳糜尿,整个人常年消瘦,精神不振乏力,后又肾气不足,腰腿疼痛至头痛。后来还生了过腰蛇,再后来是肾水肿,再后来又是交通事故撞破了头碰断了泪管,最后是三次脑梗导致偏瘫,至2013年8月不能正常行走,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而脑也萎缩得更快更厉害,以致心烦意乱,行为失常。为照顾父亲,从那时起,我戒了烟,戒了电脑游戏,几乎每个周六或周日,都会骑摩托车回乡下探看父亲,来回三十多公里。夏天,趁太阳还没有露面的时候,我就早早地起了床,然后驱车往乡下赶,心想能够尽早地给父亲露面。冬天,我却不想太早就回到老家,这不单是因为晨风刺骨,寒气袭人,更重要的是生怕会影响“倚门望子归”(节录父亲自作诗句)父亲的好眠。每次回老家,我都为他专买肉菜,专做饭菜,希望自己的那一点点心血和汗水,能换来父亲的早日康复。日子老了又新,新了又老,父亲的病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显露,而我这个形影匆匆的“侠客”,依然坚信前方一定会有那束微弱的光,继续尽力为父亲寻医问药,搜寻那希望之光之所在。不爱动是父亲的坏习惯,这成了他病情好转的大难题。接下来的几年,为了破解难题,每次回老家,我都极力劝说父亲多到院子里走动。大多时候,还亲自拉着他出去走,甚至当起“教练员”,给父亲讲解走路的动作要领,并不停地给他“一二一,一二一”地喊节拍。每当这个时候,父亲走起路来总是像模像样,有板有眼,极是令人高兴,心如灌蜜。但是每当想到,古稀之年的他还要重新不断地重复学走路,特别是当看到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酸楚。还有一次,没有学过“顶上功夫”的我,专心地给父亲剪起了头发。由于动作不熟练,手脚不利索,在他耳朵后面“剪”出了一道血痕。父亲既痛又气,一连吃力地大骂了我好几遍。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心里想,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美的发型。斗转星移。2017年7月,父亲在我县城的家中不慎跌倒摔破了股骨,从此常年卧床。那时由于手术的伤痛和安插尿管的不便,他在病床上不停地翻转,一刻都无法停下来,一直闹腾了36小时,真不知道那“神力”是哪里来的。我和弟弟、姐夫三人轮流看护,喝水喝粥都是直接往口里倒,不敢移开手多一会儿。出院后,我租借房子让父亲住下以方便照顾。春节临近,不得不送父亲回老家过年,也就将他留在了老家。因为经济问题,请不了保姆,我跟弟弟轮换看护,母亲只能帮忙做一点饭菜。后来,父亲又一次摔倒造成脑出血,住院期间发了高烧。我和弟弟买来冰块包裹严实,分别按压在父亲两边太阳穴、腋下和脖子等部位,坚持了整整一夜,坚守了整整两周。在老家照顾父亲,夜里一般都要起床换4次纸尿裤,特别是他无法安稳入睡,在床上颠来倒去,很多时候尿纸裤也不顶用,尿液从他的腿边流了出来。有时量多,不得不当即处理干净,好让他多睡一会。有时量少,懒着等第二天才处理,顺便也就给他擦身子、换衣服、捶腰背、按手臂、喂早饭……看护父亲的难处,有夏夜的蚊虫叮咬、冬夜的寒冷阴湿、长夜的孤寂难熬,更有长年累月的身心疲惫。父亲病情每况愈下,生命在苟延残喘,而看护的艰难与无助又让我感到无可奈何。“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在看护父亲的多个日夜里,我也曾用泪水洗亮黑夜的星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生命不可挽留,与其死后极尽哀荣,不如生前力尽孝心。我只能简单地这样想。
父亲将要离世,是在2019年的9月底,大概是24日吧。那一天,我早上上班时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他急促地说父亲吃不了饭。我毫不迟疑,连忙打120叫救护车赶回接送父亲到医院。下车后,我买了一份热粥端着给他喂吃。这时候,父亲张开嘴吃了起来,感觉他吃得很香,一会儿就吃完了。我心里一阵暗喜,猜想父亲还能活。可是住进病房后,无论我和弟弟煮了多么好喝的汤,多么好喝的粥,父亲再也没有把嘴张得大一点,只是微张口,用嘴唇一点点慢慢地舔着下咽。接下来的几天,就是依靠打点滴、吸氧气维持生命。父亲还拉过一次很稀很稀的黑便,后来听说这是人要走前的普遍迹象。我不懂这些,也不愿放弃。到了10月2日,因为国庆长假,父亲在私立学校教过的几个学生前来探望了他,大哥也从外地回到了县城。3日一早,父亲呼吸困难,再次打强心针进行了抢救。直到中午,我还没有放弃的念头,可是怎么也无法睡一会儿,心想起床回自家冲个凉,吃点饭,照常来换下弟弟。可是回到家,人却不自觉地往银行去取钱,然后赶往医院办理出院手续,再叫救护车赶紧将父亲护送回老家。夜里10点多钟到家,撤掉吸氧装置,我们守在父亲的身旁。夜,似乎很静。心,在害怕颤抖。时间,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母亲赶忙去找来艾草煮了一盆热水,让我和弟弟给赶紧给父亲洗个澡,然后穿上寿衣等套件。不多久,父亲呼吸艰难,嘴里慢慢渗出了白沬。但是,他似乎是神志清醒了过来,拼尽全力慢慢地举起右手,与我们不舍作别,眼里好像也有一点儿泪滴,一再显露出对于生的留恋和无奈,虽然活着的时候,他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父亲走了,走得安静而祥和。虽说“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但是“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没有父亲的家,是一线荒凉的横水渡。失去父亲的心,是一只漂泊的船。每当看到破旧的老屋、空荡荡的老家,我都不免眼眶含泪,不禁又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我想,父亲的一生,有如他亲手种在老家院子里的那几棵木菠萝、芒果、龙眼、石榴,不求长得高大挺拔,只求散发几缕馨香。或者王安石那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也可以作为父亲一生的写照吧。
愿天堂清香永续,陪伴父亲孤寂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