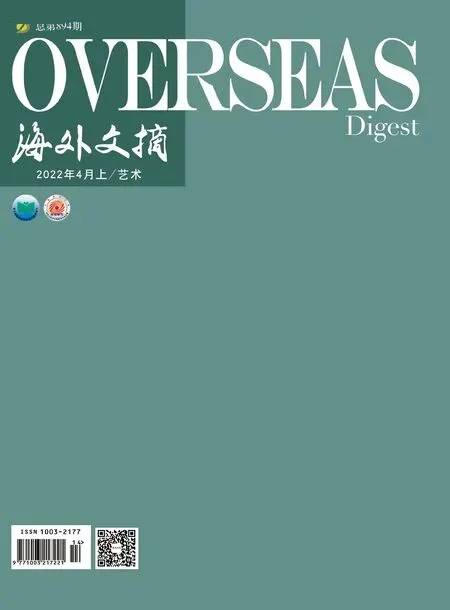17-18世纪朝鲜疫病及其文学形象化考察
——以《於于野谭》和《天倪录》为中心
2022-11-11张萌
□张萌/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与不安之中,已经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的我们尚且如此,那么在对相关科学知识缺乏了解的古代社会,人们对疫病的看法和态度值得研究。
1 朝鲜半岛疫病体验的文献记载
朝鲜半岛自古便饱受疫病侵袭。《三国史记》第二十三卷《百济本纪》中记载:“温祚王四年 春夏旱 饥疫 秋八月 遣使乐浪修好”,这证明朝鲜半岛自三国时期起就已经开始有疫病出现。《三国遗事》第三卷中有“感疠疾 二人相次发恶病”之语。高丽时代,旱灾、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不足,继而引发饥荒,百姓的免疫力日渐低下,疫病也因此流行。《高丽史》世家第五卷中记载了显宗时期“京城疫 人多死”,第十三卷中记录了睿宗时期“疫厉大兴 尸骸载路”。特别是到了朝鲜时代以后,疫病大肆流行。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疫病几乎贯穿了整个朝鲜时代。从太祖时期到哲宗时期共发生疫病641次。17-18世纪气候异变犹为严重,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霍乱、痘疮、猩红热等疫病肆虐,对朝鲜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对此,国家专门设置收容疫病患者的机构,对民众进行救治,并且下令编撰《谚解痘疮集要》《东医宝鉴》等医书,可见当时朝鲜国家层面对于疫病问题的高度重视。当时战争、饥荒和疫病的交织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有关于这些现象的民间故事被士大夫们采集收录于《於于野谭》《天倪录》《东稗洛诵》等笔记野谈集中。其中17世纪柳梦寅的《於于野谭》中最先出现了关于疫病的故事,18世纪初期任埅的《天倪录》对疫病相关故事收录最多。《於于野谭》与《天倪录》的作者皆属士大夫阶层,他们采集民间的怪谈传说、奇闻异事编撰成书,其中既渗透了17-18世纪朝鲜士大夫所代表的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也如实记录了当时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民风民俗。所以对17-18世纪笔记野谈集《於于野谭》和《天倪录》中的疫病故事进行考察,进而具体分析疫病在故事中的形象化特点,探究其文学形象化中蕴含的含义,具有很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2 1 7 -1 8 世纪朝鲜笔记野谈集中的疫病体验
《於于野谭》是由17世纪的文臣柳梦寅收集民间奇闻、异事、怪谈,编撰成书,此书创朝鲜后期野谈类文集之先河,也是最早收录疫病故事的野谈集。《天倪录》是18世纪文人任埅采集编撰的野谈集,是继《於于野谭》后最早的正式野谈集。朝鲜王朝在战争、饥荒、疫病的多重侵袭之下,人口大量死亡,与此相关的很多疫病体验都以奇闻异事的形式被收录在了《於于野谭》和《天倪录》中,接下来以其中的几篇为例对朝鲜笔记野谈集中的疫病体验进行观察。
《於于野谭》中的《黄辙者术士也》写道“佐郞金义元族侄合家,患妖疾,请辙治之。辙曰:‘是绿仇人屑人颅骨,撤之遍一家,故众鬼虐人,可符咒已之。’……又尝捉鬼,藏之箧而緘之,箧中窸窣有声,箧自跳跃,系石投之江,妖乃息。”当时,人们缺乏对致病原理的正确认识,把当时的疫病看做“妖疾”,请求拥有奇能的术士黄辙为其驱除疫鬼。
在《天倪录》的《出饌对吃活小儿》中“老人曰:‘吾本岭南某邑人也。死作痘神,今方行痘于此地’。”再现了当时头疮流行的社会情况。《操文祭告救一村》中“其友答曰:‘吾于死后,为痘神,行痘于世间……今兹逾岭,而所领小儿,皆畿甸痘化者也。’生谓:‘君素恺悌仁人,死后心性,亦岂异也?……其友愍然曰:‘此系时运,及渠之命道,非吾所自专也。’”故事基于当时头疮猖獗且儿童易染的社会事实,描述了在头疮猖獗的村落中,儿童大量死亡,而且将这些都描述为痘神所为。而痘神正是主人公士人金生去世的故友,于是金生极力请求痘神并向其祭出奠文,救活了那些被带去阴间的孩子们。
这些故事中包含着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疫病的流行是神怪所为。这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疫病病因论有关。在科学认识疫病的致病原理之前,人们对疫病的看法主要基于当时的几种疫病观。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姜尚顺教授将朝鲜时期的疫病病因论整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汉代儒教灾异论、天人感应论、性理学的阴阳理气论作为逻辑基础的易学病因论。第二类是经验性病因论。这种病因论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环境因素的作用。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经验了解到不洁的环境、污染的水源、战争和饥荒等都会成为疫病的温床,于是产生了这种病因论。第三类是神异病因论。这种病因论认为疫病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存在引起的。
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疫病还没有准确科学的认识,以上三种病因论是混合并存的。但是由于易学病因论倾向于人类的内省,经验病因论又因为现实条件的制约多为偶发性,所以这两种病因论想要在当时成为主流仍然存在局限。而神异病因论来源于根深蒂固的原始思维观念,属于当时朝鲜社会主流世界观的产物,自然最容易被大众相信并接受。所以在对于疫病的发生机制几乎没有了解的朝鲜时代,人们将骇人之疫病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神异力量。再加上当时的文学审美也偏好脱离现实的奇闻异事,所以17-18世纪朝鲜士大夫编撰的笔记野谈集中关于疫病的故事几乎都是超现实的神怪故事。
3 1 7 -1 8 世纪朝鲜疫病体验的文学形象化及其社会意义
《天倪录》的《一门宴顽童为疠》故事中,疫病是由积郁怨气的厉鬼蓄意所为。故事中主家宴席外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长相凶恶的狼狈顽童,“内厅帘外,忽有鬅头顽童植立,其状甚狞,年如十五六者……”其实这个顽童就是散播疫病的厉鬼。众人嫌弃顽童凶恶狼狈的外表,见赶而不走众人便动用武力合力驱赶顽童,“复使武人多力者五六人,共打之以大挺,尽力下击,势如压卵,声如霹雳,依旧不动一发,不瞬一目。众始大惊惧,知其非人也,共下庭,跪拜于其前,攒手祈祝,哀恳备至。良久,童忽莞尔一哂而出,才出门,卽无所睹。众益骇惧震悚,卽罢宴散归。自翌日,主人及参宴人家,毒疠炽发,其叱辱者,劝之挽者,劝之打者,武士奴仆下手者,未及数日先死,其头尽裂,与宴之人皆死,无一得活者。”顽童遭受众人的残忍虐待后向人们散布疫病,撒下灾殃。
与此相似,在《士人家老躯作魔》中乞讨的老妪被叫到书生家做工,老妪手艺精湛,劳心费力,最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遭到书生一家怠慢冷落。郁愤不平的老妪便叫来丈夫,令士人全家染疾而死。老妪的丈夫就是播散疫病的厉鬼,用疫病来以恶报恶。这个故事体现了当时人们认识体系中因果报应的道德观念。此外,厉鬼都是遭受怠慢或不公,怒而撒下疫病。朝鲜时代认为人暴死或冤死后怨气郁结,会化为厉鬼。出于对厉鬼的敬畏,朝鲜王朝效仿明朝实行厉祭,欲通过祭祀来得到庇佑,减少疫病之灾。作品中宴客和书生一家若能尽心招待顽童和老妪,故事的结局应该会有所不同。
相似的还有《天倪录》的《出饌对吃活小儿》。主人公隐瞒家中仍有食粮的事实,于是行痘疫的老人便让这家的孩子染上了疫病。主人公拿出食物诚心招待老人后,孩子的病才逐渐好转。朝鲜时代人们在采取祭祀等手段应对疫病,这种习俗在疫病故事中得到了投射,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情节设定,并且在疫病故事群中反复出现。故事中厉鬼与人的关系也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脆弱的形象化写照。这暴露了人际间缺少沟通交流,对相对弱者的蔑视、冷漠与暴力攻击等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从中思考和反省道德品行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前文提到过的《天倪录》中《操文祭告救一村》一文里,疫病是由行痘疫的痘神散播的。主人公金生去世多年的故友死后成为了痘神,在人间行痘疫,并道出疫病的发生与否是由时运决定的,并非他随意操纵。由此可以看出痘神只是执行天命的使者,散布疫病是天意赋予的不可违抗的运数。把疫病形象化为不可违抗的天意,反映了当时朝鲜社会核心价值观中敬畏并顺应天命的儒教意识。与前面的故事不同,这一故事里散布疫病的是执行天命者,而不是出于某种愤怒或恶意蓄意散播疫病的厉鬼,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疫病带来的不安与恐惧感。而后半部分“祭告救一村”的故事走向也反映了人类通过祭祀等努力减轻疫病危害的应对意识,也是当时仿效明朝实行厉祭这一民俗现象的文学再现。
《於于野谭》中《黄辙者术士也》一篇中,疫病由疫鬼所为,疫鬼受奇人压制。佐郎金义元的侄儿一家患上“妖疾”,术士黄辙前来驱鬼,“妖疾”乃息。同样,在《天倪录》的《西平乡族点万名》中,文臣韩浚谦的亲族是管理众鬼的奇人,为众鬼点名那夜“末梢一鬼,阙点后至,又一鬼逾墙而入。其人命捽入拷问之,后至者曰:‘果然食道为难,近行痘疹于岭南士人某家,远来赴点,以此后至,其罪无所逃。’逾墙者曰:‘果缘久饥,略行疠疫于京畿某人家,知有点簿,仓黄而来,恐未及赴,以致逾墙之罪云。’其人厉声数之曰:‘此鬼等违吾禁令,多行虐病,其罪已重。况此乃宰相贵家,而渠敢逾墙而入,其罪尤重。后至者杖百,逾墙者杖数百,俱枷锁,囚于牢狱。’”违反禁令,多行疫病的疫鬼受到了韩氏亲族的惩罚。朝鲜朝后期人们对于疫病的神异认识主要是基于巫俗信仰,认为疫病是由超自然的存在引起。当时人们对于疫病的应对方式也自然倾向于依靠巫俗的神秘力量,并通过神怪故事对其进行形象化。尽管故事中能够压制疫鬼的只是个别习得道术和获得奇能之人,但也能窥见当时疫鬼与人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不再是单纯恐惧的一方、受制的存在,而是开始实现与疫鬼共生,甚至是压制疫鬼。将疫病形象化为人类可控的存在,也大大缓解了人们心理上由于疫病而产生的恐惧与不安,同时体现出了当时人们面对疫病大灾难的遏止意识。
4 结语
朝鲜时代,处于疫病威胁中的人们被恐惧与不安包围。面对这种不安,首先应该把握疫病的原因,进而寻求应对疫病的方式。但在对相关科学知识缺乏了解的当时,通过尚未成熟的治疗方式只能勉强减少病亡,而利用当时的认识体系解释并接受由于疫病导致的死亡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基于朝鲜时代受到广泛接受的神异病因论,疫病体验在神异故事中得到多种多样的形象化,故事中疫病体验的形式丰富,相关的应对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共性是都展示了17-18世纪朝鲜时代人们对于疫病的神异认识观。通过将原本抽象的疫病具象化,大大缓解了疫病的未知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在民众间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治愈效果,为朝鲜王朝注入了积极承受和应对的力量。而这些超自然的神怪疫病故事中所表现的人际问题、道德观念、遏灾意识等也给了如今的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引用
[1] 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276.
[2] 一然.三国遗事[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 鄭麟趾,等著.高丽史[M].平壤:北韩社会科学院,1998.
[4] 杨惠景.通过文献记录来看我国疫病史的相关考察[D].大田:忠南大学校大学院,2004:28.
[5] 柳梦寅.於于野谭[M].申翼澈,李亨大,赵隆熙,等,译.首尔:石枕,2006.
[6] 任埅.天倪录[M].郑焕局,译.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社,2005.
[7] 姜尚顺.朝鲜时代的疫病认识和神异的想象世界[J].日本学研究,2015(46):69-97.
[8] 郑京民.孩童作为鬼神所具有的象征性研究—以《天倪录》所载的痘神故事为中心[J].韩国古典研究,2019(47):39-63.
[9] 李珠英.朝鲜后期笔记野谈所载鬼神谈研究[D].首尔:东国大学大学院,20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