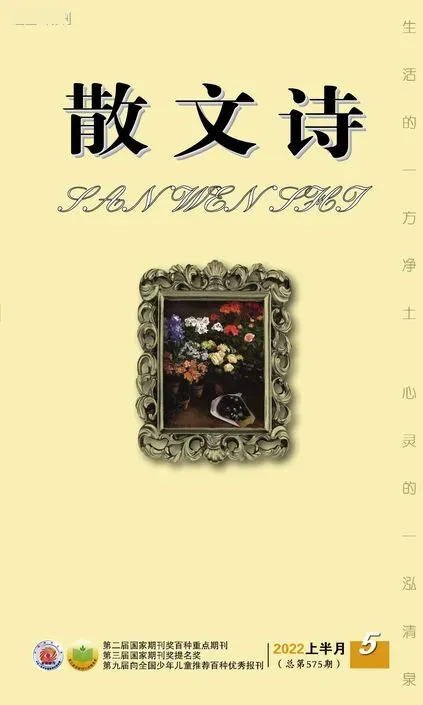诗是最后的身份标识(四)
2022-11-11◎草树
◎草 树
在茫茫的黑夜中,远远的家宅透出的那一盏灯火,是在守护、监视,也是在等候,好比铁路信号灯等待着一辆又一辆火车,好比一粒星星照耀着黑夜的大地上的家宅。由于仅有的那盏灯火,家宅具有了人性。它是一只睁着看黑夜的眼睛,像人一样地看。
它是守夜人的诗歌形象。守夜人,不是指林场的守夜人,也不是施工工地的守夜人,是在家宅这个地方守护死者亡灵的守夜人。守夜,在现代乡村或城市,是一个承担某种朴素使命的坚守行为,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守夜,更多意味着在虚无边缘对存在的守护,是为亡魂永留一盏不灭的长明灯,这是语言的家宅里那一盏最后的灯火。余怒的 《守夜人》看似简单,又诡异,实则是诗人作为一个守夜人的自况。“钟敲十二下,当,当/我在蚊帐里捕捉一只苍蝇/我不用双手/过程简单极了/我用理解和一声咒骂/我说:苍蝇,我说:血/我说:十二点三十分我取消你/然后我像一滴药水/滴进睡眠/钟敲响十三下,当/苍蝇的嗡鸣:一对大耳环/仍在我的耳朵上晃来荡去”。诗人当然不会拿起蝇拍,而是用理解和一声咒骂——用语言——去捕捉 (苍蝇),“我说:苍蝇,我说:血/我说:十二点三十分我取消你。”苍蝇之嗡鸣,是喧嚣的现实世界的隐喻。你理解苍蝇并叫出它的名字,它便不再困扰你了吗?你揭穿苍蝇的目的 (无非是嗜血),它就不困扰你了吗?你说十二点三十分你取消它,它就退缩了不再嗜血了吗?对于有用世界的嗜血性,诗歌在这里再一次被证明是无用的,也意味着拯救 “睡眠”的灵魂之难——一滴药水滴进睡眠,三十分钟过去,钟敲响十三下,苍蝇的嗡鸣仍在,像一对大耳环在耳朵上晃荡。
这是守夜人的荒谬困境,也是诗人的真实处境。
一个人的存在不可能是孤立的,是此在和他在的共在。一个诗人自然不能脱离传统而存在,与 “语言切断联系等于是与历史切断联系”。因此,如果要解决上述诸问题,仍然要回到词语。曼德尔施塔姆说,“最正确的方式,是把一个词当成一个意象,即是说,当成一种文字表述。……文字表述是现象的复杂合成物,它是一种联系,一个 ‘系统’。”这样一种对词语的表述是建立在对象征主义的批判之上,同时也和庞德关于意象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即 “在一刹那时间,在理智和情感的交织下呈现在想象中的复合物”。相比而言,曼氏的定义更科学,他为了破除象征主义——对应的僵化模式,剔除词语的意义,从中去掉了 “想象”,同时又以 “复杂合成物”予以表述。两点都十分重要,一是想象本身是可疑的,极容易夹带主观认知和意义附加,妨碍 “理智和情感”交织下诉诸于感官直觉的客观呈现。而复杂合成物意味着不是物理性的变化,而是有新的东西合成,这就彰示了诗歌整体上的隐喻性。依此,可以说词语是一首诗的发轫,由于 “把它当作文字表述”这样的解释,因而句子便可以说是它的协作部门。一首诗是依据词语的声音 (当然,对于汉语不能忽略汉字的形)运作而展开的语言运动,语言的运动犹如涌泉,汇涓流而成江河。
诗是从词语开始。词语是新生的语言。一种立足于词语的诗学的价值在于,既让词语从其意义和本义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对事物的命名功能,摆脱类似玫瑰——爱情、百合——纯洁的封闭结构,敞开,澄明,通过诗人的直觉唤起形象——在这里使用 “形象”而非 “意象”,有助于防止意象的某种附加意义的嫌疑——从而达成诗和世界某种相似性或差异性之诗性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形象由于其声学上的特点,可以唤起沉睡的传统中活着的词语,由共鸣而产生回声,达成共时性的 “对话”。由此,我们可以声称,诗,是相遇之地:过去和当下,记忆和即时,别处和此地。
意象作为写作主体赋予其思想情感的载体,不能有效地把“感想”这一词蕴藏的内涵分开,即感受、感觉和想法的混合物没有得到分馏,有附加意义的混入。而形象相对而言要纯粹得多,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 “神用象通”,接近了我们关于诗歌形象的界定,但形象不是局限于事物对应的物象,也不是先验的、主观想象的产物,更不是反映某种思想观念的意义载体。由于形象不是事物本身,因而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结果——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事物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形象的新颖性和独特性。而在形象的外延上,事实上当代诗歌的写作实践早已开拓了它的疆域,形象依据相似性原则扩展成为一个小说场景的描述、一场戏剧性的对话,甚至意识、情感、心理独白、片段交织的蒙太奇,它们因某种内在的联系、相似性或差异性,而共在一个词语的身份下,或因听从词语到来之前的某种声音的召唤而一起到来。形象之简单明确,赋予事物以容易辨认的身份,它是朴素意识的财富,不需要认知,只需要感受或者体会;对就其表述而言,它是新生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复合成为 “一捆”而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即这个复合物是 “一捆”,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任何一个词都是一捆,意义从它的各个方向伸出,而不是指向任何划一的正式的点”,(《关于但丁的谈话》)这就决定了诗歌形象的歧义性或多义性,同时,我们 “把一个诗行,一个诗节或是整个抒情作品视为一个单一的词”,决定诗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性的隐喻。
非现实性给予现实性的形象,使我们开启非理性的感知王国得以可能,也将恢复诗歌古老的神秘天性。梦想或许是一种让人性的家宅立身于喧嚣城市的途径,它让一座记忆中的家宅或一个精神的居留空间以具体的形式寄居于我们心中,来到诗人的语言中。家宅是可以紧紧 “搂住”的,是可以呼吸的,在抵御动物性的风暴袭击时,是具有母性的。
家宅的本质是爱,而家宅时刻亮着的那盏灯,是良知。
一个人要有一个身份,好比一个词语要有一个形象。没有身份的人在大地上行走,势必步履艰难。我曾在湘西凤凰见过一个青年,长发,清瘦,沉默寡言,喜爱哲学和电影,大学中途退学,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簿,每次去外地必须去派出所开临时证明。除了 “儿子”这一身份,他不再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身份。他潜身在湘西偏僻的腊尔山支教,那些眼睛明亮的孩子们是他唯一倾谈的对象。他不是不可以取得身份证,而是蔑视世俗身份的价值。在他那里,“我”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者,其余一切皆他者。他固执地认为,“我”和他者的交会即命运,而命运是不可把握的。他试图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自我救赎之途。他的梦想是否是一条可以接近道的真正的道路呢?或者他是否能在虚幻中为自我建立一种身份标识,以达成对世界的认识、命运的主宰呢?
一个人建立和人、社会以及世界的联系,首先依仗的是适当的身份,这是世俗层面的;在精神上,人的身份和价值,依凭各种荣誉、奖项照亮,在本质上仍属于世俗层面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体现在一种关联性之中。当一切世俗的身份卸下,人和世界的物质性关联丧失和精神关联逐渐模糊,诗是最后的身份标识。诗作为诗人的身份标识或 “证明文件”,和户口簿有着类似的形式,但其 “社会关系栏”里除了应该填写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以外,还应该写上世界、宇宙、语言。它的命名不是一次的,而是多次的;不是特定的语言符号,而是不同形式的崭新形象——当然,其新,是相对于俗见和常识,陈旧观念和惯常意义。它的出生时间永远是 “此时此刻”,像一个横坐标。在时间的横轴上,对应于它总会有一个或多个空间点,即纵坐标。因此,诗的诞生是以坐标的形式出现,就像一个人诞生于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出生地构成他关于其生命记忆的起点。而这些坐标点的移动,在时间的横轴上,也在空间的纵轴上,纵坐标随着横坐标移动而移动。这些点的连线,即是存在的轨迹。这个点在 “此时此地”,同时又无限延伸,过去、现在、未来共时响应于 “此时”,“此时”的横坐标上这个点,使诗具备了时间性。诗的时间性寓于语言和它的具体性、现实性和当下性之中,诗的站立与时间关联,而站在无限性中,就具有了寓言的特征。诗的空间随时间而来,就像在某个救赎的时刻会升起一座医院的大楼 (特朗斯特朗姆 《孤独》)。从身份标识的意义上看,诗的地方性与关于诗的坐标的这一观念并行不悖。在地方性的接口上,连着两个端口:一个是山水地理灵性,高山大河必给诗人以天赋般的启迪;一个是地理文化传统,包括人文的底蕴、古老的习俗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
诗歌的客观性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写作特点,跟诗歌的本质没有更多关系,即便在 “真理”和 “辩护问题”的意义上,也只是如何维护诗之真理,诗之所是。
生于叙利亚的萨莫萨塔,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讽刺作家琉善 (约125年-180年),在 《梦》一书中谈到他是如何选择文学生涯的:在一次梦中,他梦见了 “文化”,后者应允他:“一旦你去国外,即便你在异域也不会默默无闻或无人知晓,因为我会赋予你身份标识,谁看到你都会碰一碰邻居的肩膀,然后用手指指着你说:就是那个人!”据此,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重构了这样一个场景:“寂寂无名——在安条克的一个陌生人——这来自埃德萨的男子/写了又写。终于,瞧,/最后的诗章写就了。它一共包含/八十三首诗。但是写了这么多,/作了这么多诗,以希腊语从事/如此紧张的遣词造句,已令诗人疲惫不堪,/现在一切都向着他压了下来。//但是,一个念头突然使他从沮丧中振奋起来:/那句崇高的“就是那个人”,/琉善曾在梦中听到过。”这就是著名的 《就是那个人》(引自 《卡瓦菲斯诗集》,黄灿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新陆诗丛·外国卷),依据琉善的 《梦》写成,也是关于诗人写作的寓言。一个诗人根本的写作冲动是源于这种对存在感的古老眷念,对人的存在永存于语言的信念。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身份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觉醒,没有一个清晰的坐标,那么,其写作终是不能让 “文化”那么自信地 “碰一碰邻居的肩膀,然后用手指指着你说:就是那个人”的。诗是最后的身份标识。它的激光标志上隐藏着两个字:良知。那是从 《诗经》《楚辞》、李杜苏辛以来的伟大的传统赋予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