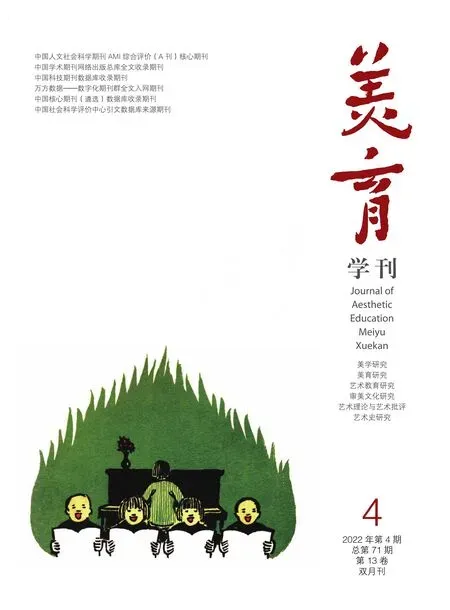《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的关系
2022-11-11李倍雷
李倍雷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艺术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范畴,这是学界没有争议的共识,艺术学理论下有艺术史等二级学科。我们这里主要探讨艺术史学的“三大体系”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史不应局限在某个门类艺术的范围内,否则无法看清某一门类在艺术史中的位置,看不到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考虑到其他门类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故需要避免以门类艺术史立场,仅看到独特性(局部性)而看不到艺术史的整体性的弊端。这是我们探讨建构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三大体系”中,以学科体系立心,以学术话语立道,以话语体系立命;建构当代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则需要立足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以及有关传统艺术经典文献,依“经”立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故此“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等相关经典文献支撑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的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立心)、学术体系(立道)和话语体系(立命)又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不是分离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是在艺术的范畴内专门探求艺术现象变迁和艺术史实的变化规律,立足于中国艺术谱系;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则是阐释与揭示艺术史学科的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系统理论知识,立足于时代精神;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则是对艺术史学科的系统理论知识,专业性的概念、词语的表述和诠释,其语言释名是话语体系观念、思想等的形式载体,立足于时代主题。我们主要分析和探讨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以及相关经典文献的关系。
一、《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的 学科体系
有关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在学界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但总体上说都认同中国艺术史是汇通各种艺术门类的整体、宏观、综合的艺术史,即通常说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所属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史,对艺术史的这种学科认知是我们探讨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包含有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曲艺、戏剧、影视、设计等多门类史学的横向交叉组成的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这是艺术学科内部学科横向的交叉关系;另外还存在艺术史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关系,如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等交叉的史学关系。在讨论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个与艺术史相关的“艺术学”的学科问题。对于“艺术学”的不同认知,就存在对“艺术史”的不同认知。
有些学者只要一提到“艺术学”,就立即与德国的一些美学家关联在一起,如马克斯·德索瓦尔(Max Dessoir,1867—1947)、乌提兹(E.Vtit,1883—1965)等,并以德索瓦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为“艺术学”建构的标志,认为艺术学的起点就是德国美学家所建构的“艺术学”。故此,只要提及“艺术学”,就言必德索瓦尔。不可否认,20世纪初德国美学家意识到美学无法解决艺术的问题或者说美学呈现出“穷途末路”的迹象,于是德国的美学开始转向艺术学,出现了具有终结西方传统美学意义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专论。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以德国为首的西方美学“转向”的变化,从而为西方的艺术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要注意到,20世纪初欧洲德语圈同时还出现了“比较艺术学”和“比较音乐学”并行不悖的现象。这种现象意味着20世纪初的欧洲,在有关“艺术”的概念中并不包含“音乐”,且“比较艺术学”中的“艺术”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说的“美术”,故称为“比较美术学”或许更为合适。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山本正男(Yamamoto Masao,1912—2007)将德语圈学者的“比较艺术学”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有关“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命名为《比较艺术学》,共六大卷,显示了20世纪初期、中期的“比较艺术学”实为“比较美术学”成果。我们这里提到这个现象,其意义在于说明20世纪初德国的“艺术学”是以“美术”为主体的“艺术”概念与内涵,且并不包括“音乐”“舞蹈”等内容,与我们所探讨的“艺术学”是不同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
我们提到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是1994年创建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原二级学科“艺术学”升为十三大学科门类后的学科名称,这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征和学科定位,即有着自己的艺术学理论定位的学科体系。它是在美术理论、音乐理论、舞蹈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宏观的和综合的研究,探讨艺术普遍性、共性和规律性的问题,“艺术史”的学科定位就是在这种整体、宏观、综合的“艺术学理论”框架下展开的史学研究,这是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基本定位。中国艺术史则也应该按照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所属“艺术史”的学科定位建构其史学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说,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同样是在汇通不同艺术门类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宏观和整体的艺术史研究,探讨艺术史的一般规律、艺术史的变迁、艺术史的普遍性和艺术史的原理等史学问题;有的学者也称为“跨艺术门类的艺术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但是要真正认识到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则需要与中国正史的《艺术列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谱系”史学视角认知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
所谓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指特定范畴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探讨、分析与研究对象的性质、规律所规定的学理要求。我们结合“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内涵和谱系来探讨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内涵范畴与谱系是当代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范畴与基础,由此所形成的对它们的性质、规律所作的规定的学理探究是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范围。在“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魏书·术艺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和《清史稿·艺术列传》。《魏书·术艺列传》在《方术列传》的基础上变迁并超越了“方术”内涵,在变迁为“术艺”的概念中丰富与发展了“方术”的内容与内涵;《隋书·艺术列传》有一个重要变化,其意义不亚于《晋书》用“艺术”概念立类传,《隋书·艺术列传》的意义在于对“艺术”作了分类,其“小序”云: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辨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来久矣。
《隋书·艺术列传》开始为“艺术”分类,形成“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六大类,是中国古代“艺术”谱系,也可以说是《艺术列传》中关于“艺术”的“体系”的正式形成。《清史稿·艺术列传》是“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收官”之传,它除了恢复《魏书·术艺列传》的内容和为“艺术”概念立类传以外,同时还将近代的科学技术、机械制造等内容,纳入“艺术”的范畴,是《考工记》有关“艺术”谱系的延伸。如将近代科学家徐寿(1818—1884)、戴梓(1649—1726)和丁守存(1812—1883)等及其活动事项列入其传,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范畴,也可以视为艺术史学科体系的重要特征。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绪言”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史范畴与体系。《清史稿·艺术列传》“绪言”云:
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
这段“绪言”阐述了中国文化系统中“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变迁路径,以及所包含的内涵与内容,实则也是“艺术”的谱系展示。《隋书·艺术列传》将“艺术”分为“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这是“二十六史”中对“艺术”的一个基本架构,到了“收官”类传的《清史稿·艺术列传》,是在此基础上积累性的演进与发展,重新建构了“艺术”的体系,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的基本结构,再纳入“书画、技击、工巧”,并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的基础上,形成“阴阳术数之艺”“医经卜筮之艺”“巧思术伎之艺”“礼乐书画之艺”“技击射御之艺”“音律歌舞之艺”的“艺术”系统和谱系关系,这是一个整体的、宏观的和综合的艺术体系,用今天的学科视野看,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但若对照正史《艺术列传》的整体、宏观和综合的“艺术”体系,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几乎没有建立在这个整体的、宏观的和综合的传统史学“艺术”体系的基础上,而是受到西方分类影响形成了音乐史、美术史、舞蹈史、设计史、戏剧史、影视史等分门别类的史学学科,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以“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
诚然,“艺术”概念的内涵与内容是动态演变的,时至今日,“艺术”概念与内涵所发生的演变以及分类系统,远离了中国传统艺术系统和内涵,但这种变化另有其原因。换句话说,今天的“艺术”内涵标准不是中国传统艺术系统建构起来的标准,更多的是在“Art”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标准,乃至一提到中国的“艺术学”就必言德索瓦尔为起点,看不到《艺术列传》的整体面貌。如果以“Art”为基础,无论怎样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都是在“Art”框架与脉络下的学科体系,难以成为真正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这是当前建构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最大的瓶颈。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是体现“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体系、脉络、谱系与内涵,实现的是整体的、宏观的和综合的艺术史观的学科体系,而不是切割为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极为简单的音乐史、美术史、舞蹈史体系。分门别类切割或细化学科的思维方式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其中显现出中国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特征。通常而言,整体、宏观和综合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必然呈现的也是整体、宏观和综合的“艺术”体系,虽然我们说《隋书·艺术列传》对“艺术”进行了分类,但仅仅是作为整体化的分类认知,而不是切割为不相关联的类别,在这些分类的认知系统中,往往是相互包容的。譬如《艺术列传》中的“医术”与“占卜”的关系就是“巫医”一体的系统;“卜筮”也不是孤立的,也与“阴阳”有某种关联,“卜筮”与“阴阳”的关系就在“数术”的系统中。再譬如“礼”“乐”“射”“御”“书”“数”在“六艺”系统中是一个整体关系,无论是纳入官学还是私学中都是作为整体的学习对象。又《后汉书·伏湛传》云:“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尽管“艺”与“术”是两个系统,但属于一个整体。无论是李贤对《艺术列传》的类别认知,还是对“艺术”的注释,都体现了对“艺术”整体认知的史学观念。所以,我们说《艺术列传》的整体性、宏观性和综合性的史学特征及其艺术内容,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坐标。当代有很多传统中没有的新的艺术形态出现,譬如“影视艺术”“影像数码”或“数字艺术”等与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艺术形态,但科技与艺术在《艺术列传》中本身就是天然一体,在该方面有其天然的艺术思维和思想观念,故此容纳当下新艺术形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纳入中国艺术史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的学科体系范畴中建设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看到了《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的必然联系。由此可知,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最大特征就在于汇通所有艺术门类,进行整体、宏观和综合的史学研究,探讨艺术史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律,包括艺术起源、艺术变迁、艺术流源、艺术特征、艺术产生、艺术考古、艺术文献,以及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关系的普遍性、共性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研究追问人类社会所产生的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二、《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的 学术体系
学术是将学科的本质内涵和内容作专门的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最终成为学科的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形态与方法形态,并形成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观念。学术体系要立足于时代精神。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是将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一种现代化、具体化、深入化、系统化与体系化的研究,形成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须以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为前提,融入新时代精神,方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换句话讲,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是在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基础上所形成的系统性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一个有新时代精神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上述我们说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如果成立,那么它必然是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有关联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也必然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基础上的。
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要高度地体现出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就体现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理论、观念与思想,体现中国新时代精神;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是在专门系统性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学科对象的学术体系的、相对独立的艺术史学思想、观念的学术体系。“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内容与内涵蕴藏着普遍性与特殊性、转折性与延续性的历史价值和史学意义,是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的基础,那么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必然也要体现出这个基础的历史文化的底色。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所显在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就应该蕴含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这是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的必要条件。以往在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照搬“他者”的学术体系的现象,这是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首先受到日本艺术史家的影响,模仿他们所撰写的艺术史的学术体系以及体例而撰写中国艺术史。譬如模仿日本艺术学者大村西崖(1867—1927)撰写的《东洋美术史》《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的史书体例,陈师曾(1876—1923)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中国绘画史》(1921),尽可能地保持了中国文人艺术的特征,特别是他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1921)显示了中国特征的艺术史研究的学术理论价值,当然首先使用了外来的“美术”概念名之为“美术史”,从内涵到概念并非我们说的“艺术史”。以后的学者所撰写的“美术史”多受到“改良中国画”和“革‘四王’画的命”等观念的影响,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一路向西,逐渐脱离了《艺术列传》的文化系统和艺术观念的底色,很多观念、思想和概念都采用了西方美术史的,譬如“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乃至“移情说”“意味说”等概念,架构中国艺术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时至今日,“阐释学”“图像学”“风格学”“叙事学”理论与方法风靡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领域,几乎都是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架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再譬如,探讨艺术起源必然是西方的几种起源说,即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并以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艺术的起源》为典范。然而,格罗塞考证艺术起源所用的材料多是他认为的“原始民族”,即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比较为落后的“野蛮民族”,而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远古社会的原始民族。格罗塞自己就坦言:“历史和考古学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从人种学里获取正确的知识。”他从人种学中去寻找他所需要的“原始民族”,即以文化或文明层次高低来确定“原始民族”,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原始性’分量的轻重问题,和该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问题,是同样重要的”。格罗塞的艺术起源说的前提存在问题,结论也必然存在问题。而有关中国艺术的起源说,以往编写的艺术史学几乎很少提及。这就是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需要重建和重新思考的问题。另外,有的艺术史学与艺术理论研究又回到了20世纪德国“前艺术学”的架构状态中,即再次用“美学”架构“艺术”,难以真正诠释和揭橥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美学”代替了“意境学”,导致中国艺术史学显示不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显示不出新时代的中国艺术史学的思想和艺术史学的观念与精神,即缺失了新时代精神的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
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的文化底色,是以“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为支撑,以“十三经”为基础,以中国史学“三大体例”为结构。我们这里重点提到“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是因为前面提出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有直接相关,那么其学术体系必然也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存在紧密关系,这也是我们重点探讨的内容。《晋书》是首次用“艺术”概念立类传的正史,它涉及我们探讨的学术体系范畴问题,我们先看《晋书·艺术列传》“小序”是如何阐述“艺术”的: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
《晋书》使用“艺术”概念立传并非没有基础,而是在“术艺”的基础上形成的,且前面还有“方术”概念和类传。我们曾经梳理过“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体系,认为其前身是《史记》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由此又变迁为《魏书·术艺列传》。中国的“方术”与天文直接有关,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阴阳”“占卜”“医巫”“数术”“巧思”等都与人类早期认识自然紧密相联,尤其是与天文、历法、地理等认知直接相关。譬如《隋书·艺术列传》在诠释“艺术”类型中的各个“祖师”时云:
然昔之言阴阳者,则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韦;晓音律者,则师旷、师挚、伯牙、杜夔;叙卜筮,则史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论相术,则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举、许负;语医,则文挚、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者,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咸诣幽微,思侔造化,通灵入妙,殊才绝技。
这里就不难看到艺术类型与天文历法存在极大的关系。言阴阳者自不必说,与天文关系非常紧密;巧思者则有奚仲、墨翟、张子平和马德衡等,奚仲造船之祖,墨翟光学之祖,张子平即张衡造浑天仪、地动仪等天文仪器,马德衡即马钧属于机械制造专家,制造翻水车、改进织绫机等。仅巧思类直接与天文联系的就是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地动仪,是古代研究天地规律的重要物质成果。有关造车船与中国古代“天地观念”的关系,在《考工记》中有详细记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可见中国古代机械设计制作与天地观念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天文”又转化为“人文”的文化观,从而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艺术。中国艺术对色彩的要求也与“天地观念”有关,同样在《考工记》中有诠释:“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黼;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足见中国的色彩观念与方位自然万物有关,是典型的“观念色”。另外,音律与“缇室候气”即“候气术”有关,这本属于天文历法的技术,但音律却因此也被测量出来,即“黄钟律吕”。如《后汉书·律历志上》云:“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通常说“十三经”之首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起点,而《易经》则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结果,文化源头来源于天文。《周易·贲》云:“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把“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说得很明白。我们为什么提到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这个问题,就因为传统的“艺术”学术体系与天文历法有关,更重要的是天文历法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没有“天文”就没有“人文”。在天文历法观中建立起来的人类知识体系,必然显示其“天”“人”关系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才建构出了“人道”与“天道”统一的“天人合一”的形而下“艺术”系统。因而《艺术列传》“小序”都隐含了这层意思,它以记叙的方式载录了从事各种“艺术”类型的人物及其事项活动。在与天文历法系统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艺术范畴、内涵及其理论,都隐含了传统艺术史学术体系的中国特征。我们所熟知的“气韵生动”“心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媚道”“含道暎物”“以神法道”“澄怀味象”“应会感神”“神超理得”“意象”“意境”等形而上的思想观念,以及在其构图形式上的“知白守黑”“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的形而下的技巧与创作观念,几乎都源于这个知识系统。《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在艺术结构的运用中,即可形而上又可形而下,来回往复其间,诚如中国艺术形态体现的正是《易经》所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形而上的观念意识。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为此有一个关于“言”“象”“意”的逻辑论证:“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却又用天文天象之“道”诠释形而下之“器”中所显示的具体巧艺,而中国传统“艺术”之名下的“器”又能进“道”,如《隋书·艺术列传》中的“艺术”分类即是如此。同时,“方术”“术艺”“艺术”“方技(伎)”上位概念下的各种巧艺之“名”(下位概念)的内涵和内容十分丰富,也不是当今“艺术”(Art)能够涵盖的。不仅如此,由“方术”到“术艺”再到“艺术”“方技(伎)”又再复出“艺术”之变化,显现了《艺术列传》富有内涵的谱系性的演变过程。“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正因为“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丰富的内涵和生动的谱系性的演变过程,彰显出中国传统艺术史学术体系的特征。
我们举一个有关“术”“艺”概念的实例所隐含的学术体系问题。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昔者孟蜀有一术士称善画,蜀主遂令于庭之东隅画野鹊一只,俄有众禽集而噪之。次令黄筌于庭之西隅画野鹊一只,则无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问筌,对曰:‘臣所画者艺画也,彼所画者术画也,是乃有噪禽之异。’蜀主然之。”《图画见闻志》中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郭若虚通过黄筌之口,将绘画分为“术画”和“艺画”。“术”与“艺”显然在郭若虚这里是一个层次问题,但也符合《术艺列传》到《艺术列传》演变的脉络话语体系的“术”与“艺”概念,而且郭若虚说的“术”与“艺”暗指画品,即“能品”(术画)和“神品”(艺画)。为什么我们说“艺画”属于“神品”而不是“逸品”呢?是因为黄筌属于宫廷画师,依然如郭若虚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是也,黄筌表达的是皇家气派与富贵,徐熙表达的是野逸中的隐逸与淡泊。关于“逸品”,唐志契《绘事微言》还有一个分类:“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很明显,有关“术画”“艺画”的概念隐藏在绘画史中的“画品”观念,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中的“术艺”观念有关。这些在艺术史中所形成的学术体系,不仅是我们要传承研究的,更是当今发展和创新的学术体系的基础。由此上述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相关的中国传统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是当今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的根基所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含了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方得文化自信。那么,在艺术方面的“复兴”,就是对中国传统早已建构的艺术体系的复兴,这既是我们复兴的对象,也是中国艺术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基于上述中国艺术的文化内涵、理论与方法,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有天然的联系,也与正史中其他列传、志和《易经》等文献有关系,这些联系与关系恰恰是中国艺术史学学术体系的构成基础,是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艺术史学学术体系的基础。
三、《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的 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表面上看去好像是一个话语表述的问题,但实际隐藏着“话语权”。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实则体现着一个“话语权”的主导性是否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问题。“话语”也是新时代的主题,所以话语体系建设要立足于新时代主题,从这个角度思考其建设问题,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的“话语体系”。艺术史学“话语”虽然不像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意识形态那么凸显,但艺术史学属于上层建筑,其“话语”同样存在意识形态的属性,更有鲜明的民族性的特征。故此,我们认为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隐藏着“话语权”,这意味着在建构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艺术史学的“话语权”,或者说建设艺术史学话语体系是新时代的主题之一。
当下有一种“话语”趋向是,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方法和概念时,往往是积极地“响应”而不是带有臧否判断的有力“回应”。譬如说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本体论”“神话学”“图像学”“阐释学”“风格学”“叙事学”“纪念碑性”“机械复制”“灵韵”“赞助人”等理论或概念,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学者是趋之若鹜、不厌其烦地诠释西方的这些理论、方法或概念,真正做到有力量的“回应”不多见。这种状态下的“响应”必然丧失的是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如果没有话语体系(话语权),那么所建设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就会成为“空壳”或者是“他者”的话语体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些问题,把这种只知“响应”而不知“回应”的现状称为“话语逆差”,并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与中国对西方的巨大‘话语逆差’相伴随的,是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不过是对西方话语掌握较为熟练的二道贩子,‘以洋为重’或‘挟洋自重’的不正常学术生态成为常态。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所遇到的问题为指向的西方学术话语,难以准确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样如此,用西方学术话语也解决不了中国艺术的当代实践,解决不了新时代的主题。因而,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理论、方法和概念需要的是“回应”而不是“响应”。“回应”就要“话语”建设,要“回应”西方理论话语,就需要在自身的文化系统中去寻找能够“回应”的理论、方法和概念。
“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是整体架构在“天文”“阴阳”“候气”等基础上对各种形而下的技巧以及掌握其运用能力的人的记述与诠释,即“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的类传,体现出形而上的普遍性(天文历法)和形而下的特殊性(各门巧艺)的融合关系。《艺术列传》从“日者”“龟策”演变为“方术”列传,又演变为“术艺”“艺术”列传,再变迁为“方技(伎)”列传,又复回为“艺术”列传,这里既体现出《艺术列传》的转折性,又体现了延续性的历史特征,这种“波澜壮阔”的演变正是“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历史价值与史学意义所在。正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不仅如此,“二十六史”《艺术列传》这里还有自身话语系统的历史价值和史学意义,如“天文”“历法”“阴阳”“候气”“音律”“日者”“龟策”“方术”“术艺”“艺术”“方技(伎)”“工艺”“巧思”“巧技”“巫医”“相术”等概念,这些概念所体现的也是中国艺术思想、艺术观念、表述方式及其语言特征——话语系统。《艺术列传》所体现的这些话语系统,对我们今天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构建当代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范式。
“艺术”这个概念的话语最早见于《后汉书》,《后汉书》有三处(安帝纪、伏湛传、刘珍传)提到“艺术”,这是个基本常识。我们前面提到了李贤对《后汉书·伏湛传》提出的“艺术”概念做了具体的内涵注释,即“书、数、射、御”与“医、方、卜、筮”。不难看出“艺术”属于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和特定内涵与内容,并在“二十六史”正史中用“艺术”立类传——《艺术列传》,这些事实构成了典型的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概念、内涵和特定的内容范畴。我们认为最早在《后汉书》中提出的“艺术”概念及李贤的注释,就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学术体系同时也是艺术的话语体系的体现,而西方“Art”的概念则是通过日本学者的翻译传布到中国,成为民国时期的学者用来与《后汉书》“艺术”进行对应,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词汇,但西方“Art”隐含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中国“艺术”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
鉴于上述史实,我们说“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的关系,从宏观上讲就在于立足“二十六史”,依“经”立艺之道,在弘传中国经典国学中立足于新时代主题建设自己的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笔者曾撰文《立艺之道,曰经与史》表达这个理念和理论,中国传统的“经”与“史”是建构当代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根本,尤以“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为建设当代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基础,换句话表述就是,将“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话语体系传承、发展与创新,构成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李贤对“艺术”注释的“书、数、射、御、医、方、卜、筮”既是艺术整体的内容,也是传统艺术表述和诠释的概念,而这些内容和概念在“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均有阐述和分类。如果说“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与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有关联,就在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的话语体系在今天看来就是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基础与资源。这也印证了人们常引用的那句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就是当代艺术史。当然,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直接将“历史”作为“当代史”,而是将“历史”继承发展为具有自己话语体系的“当代史”,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是无法成为“当代史”的,这才是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本意,而且这个“当代史”的核心实质就是新时代主题的当代话语、学术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权。
历史学者侯旭东认为:“史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证实事,还需要构建解释,这条路很漫长。对中国而言,目前恐怕首先要从基本概念的重新厘定开始。这些概念不应是盲目照搬西方,而要立足过去的事实潜心归纳与定名,‘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立基于此,逐步构建出关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种种解释,贡献于人类。”这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建设自己的艺术史学话语体系,首先基本概念就需要立足于传统史实,重新思考厘定、归纳定名出自己的概念,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概念和观念而冠名,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也应如此。“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开篇就是引用《易经》的“以卜筮者尚其占”话语,然后直指其内涵与功能是“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而这个“话语”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开篇作了传承性的建构,即“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二十六史”《艺术列传》这种“话语”随处都在被巧妙地传承。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言,“《易》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郭若虚这里主要说的图画“自古规鉴”问题,有意思的是《图画见闻志》还用了《历代名画记》中的话语“所谓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来结束。这表明了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的延续。
我们再看一个中国传统艺术话语建设的例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张璪的一句画理,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心源”属于中国古代画学话语的重要概念并折射出丰富的内涵,这句话反映出“视觉”转向“意觉”再转向“心觉”的艺术创作过程,故传统艺术文化中将绘画称为“心画”即是如此。同时,将音乐归为“心声”亦是如此。《乐记》说“音由心生”便是证明。《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史记·乐书》依《乐记》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经”“史”互证,阐述了音乐由心发,故为“心声”,这已部分提到了中国有关艺术起源的问题(有关中国艺术起源问题另文探讨)。这正印证了立艺之道,曰经与史。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在“论气韵非师”中说:“杨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对传统的“心画”“心声”进行建构性的阐释时,可以通过传统艺术的话语,如心画、心声、心源、造化、实景、真景、空境、神境、妙境、意象、意境等进行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而不是挪用西方艺术的话语。故此这个话语逻辑能在清人笪重光的《画筌》中得出:“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不仅如此,笪重光还为绘画艺术的“意境”提出了三个境界层次:“实景”“真景”和“妙境”。笪重光依据传统艺术系统建构性地阐释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境界)问题,这个阐释性的建构是有传统依据的,也是经得起实证的。我们可以概括为“视觉层面的视象——意觉层面的意象——心觉层面的心象(创象)——最终追求的是意境(境界)”,并可以视为当今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范畴。
苏轼云:“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认为在唐代已经建构成了一个包括诗、文、书、画的完善的艺术知识体系。苏轼的逻辑起点从“知者创物,能者述焉”开始,这是《礼记·考工记》中的阐述,同时也在《艺术列传》中作为“巧思”“工艺”有其阐述。这个论点由“知者创物”开始而累积与发展,到唐代的艺术知识体系已是“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从诗、文、书、画的各自脉络中,苏轼看到了艺术史的话语体系的完备建构均有其代表性的人物。苏轼的这个总结给我们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体现时代主题的生动案例,显示了传统艺术话语建设对当今艺术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与启示。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艺术话语的本质特征。一提到“本质”这个概念,也就涉及“话语”本身。晋代刘智《论天》:“言暗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荫,日光不至,谓之暗虚。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蔽,则大于本质。”“本质”这一概念的出处在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中,表明了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说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有关,不仅是传统资源问题,还在于赋予传统资源新内涵,从而体现出当代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赋予传统资源新内涵不是贴上一些西方概念和词汇就等于是创新或迎合了当代性。譬如在阐释艺术史的理论时,似乎离不开用“本体论”来阐释艺术,甚至认为本体论是建构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途径之一。但事实上,当我们在使用“本体论”时,其实已经失去了话语。“本体论”(Ontology)的词语表述首先由17世纪德国经院学者戈科列尼乌斯(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创用,“本体”或“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体系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我们常常陷入“本体论”“认识论”“功能论”“方法论”的路径中,提出建构某种学术体系或话语体系。当我们翻开有关探讨艺术史建构或艺术学理论建构的成果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脱离由“本体论”打头阵的著述,似乎不用“本体论”,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建构。假如以“本体论”打头阵建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那么到底是不是有骨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就需要质疑了。艺术无“本体”之说,也就无“本体论”了。其实,我们完全可用自己的“本质”的概念和话语。
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要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语言和中国新时代的主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体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的语言体系,体现中华民族语言、观念的表述范式的语言体系。自己的概念在话语体系中尤其重要;二是反映出中国当代精神照射下的艺术史学的话语建设,当然必须将传统文化脉络话语体系转化为与时代精神一致的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即体现新时代主题的话语体系。这两方面是形成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途径并使其能够在当代具有实践性。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在于它的实践性和学理的主动性,实践性是话语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史学的学术话语即是实践的产物,是建立在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学术话语。我们注意到一些艺术史家或艺术理论家,高谈阔论似乎还行,却没有一点艺术实践的经验,故而从概念到概念,极容易产生挪用或移植西方艺术概念和话语的现象,在艺术史学的话语中丧失自我。因此,完全没有艺术实践的史论家的理论话语,是无法证明其理论的真理性的,多数情况下套用西方话语体系强加在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中,用西方的概念强说中国的艺术。理论话语主动性亦即我们说的“话语权”,也因此我们说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的当代建设,还应该准确、充分地关注和反映世界艺术的核心价值以及人类精神共识下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同时要适应中国及世界艺术演变或发展的走向,而不是故步自封或刻意固守,实行单边独行而取代他国或他民族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建设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应该说这是中国艺术史学话语体系的新时代主题。
总之,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基本概念、观念和思想组成的,并且通过语言把这些概念、观念和思想连接起来。概念是人类理性认识、表达思想内容的词语形式,故而概念体现了人类思想、观念的基本内涵,反映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特有之属性。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就是由一系列概念形成基本语言,从而把思想、观念和学理连接起来进行诠释或阐述。在诠释或阐述当代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中形成表达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中国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应该由一系列的中国文化中的基本概念、观念和思想相互连接构成,用中国的概念阐释艺术史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内容,这就是我们说的艺术史学的话语体系。
四、结语
当今我们对中国艺术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就在于要回答中国艺术史学所面临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艺术史学的“三大体系”中存在“Art”的西化意识比较严重的状况,很多观念、概念、内涵及其原理不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脉络、路径、艺术谱系及其内涵,多数情况下“响应”或“默认”了西方“Art”的概念和观念的学科、学术和话语。同时,我们也很难看到真正的专业学术术语的表述,倒是看到更多概念化的词语表述,而这些概念化的词语在很多学科的话语表述中几乎同时出场,如主体论、客体论、本体论、认识论、先验论、功能论以及主体间性、客体间性等,这些概念不仅西方化话语比较严重,而且几乎都是哲学的词语概念,失去了艺术学的学术话语。坦白地讲,这些根本不是艺术史学的专业话语。不可否认艺术史学包含了哲学的思考,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阐明要以“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为基础建设“三大体系”,立足于中国艺术谱系建设学科体系,立足于时代精神建设学术体系,立足于时代主题建设话语体系,使中国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化、专业化和时代化。概括地说,中国艺术史学要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使中国艺术史学的“三大体系”相互印证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