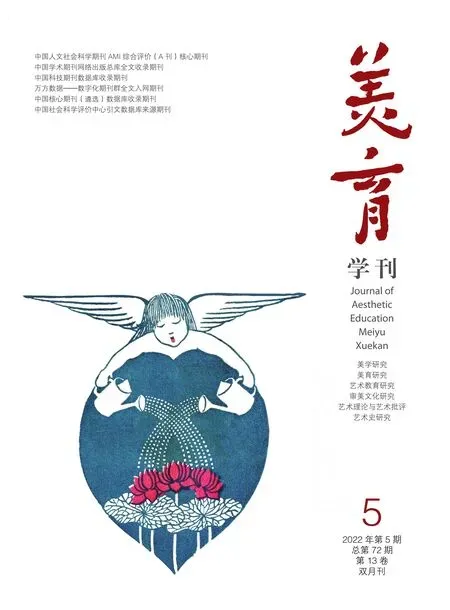历史·审美·观念:论音乐经典的确立
2022-11-11刘青
刘 青
(星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历史:核心保留曲目
“经典”(canon)概念最初是指由教会认定的与《圣经》相关的宗教圣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文本,后来拓展至文学领域,指由某位作家创作的、获得认可的世俗作品。从宗教圣典到世俗作品,前者是指由具有制定宗教法令的权力机构实施的、目标明确、不容增减的封闭性作品,后者则是非官方的、非确定性的公众共识的产物,一般认为,经典概念的世俗化发生在18世纪的下半叶,而这个时间点耐人寻味。
在音乐领域,经典的确立与核心保留曲目(the core of the repertory)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也是古典音乐形成的机制,即以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大师为核心的音乐方式作为美学原则与历史标准,只有完成了这一经典建构的过程才会出现所谓的经典。应该明确的是,在核心保留曲目真正确立之前,常演曲目(repertory)代表着这一传统,正如美国学者威廉·韦伯(William Weber)所认为的,现代经典的概念是由常演曲目逐渐衍变而来的,在经典概念出现之前,常演曲目作为替代是整个传统的根源。
首先,威廉·韦伯提出了三种经典:学术经典(scholarly canon)、教育经典(pedagogical canon)与表演经典(performed canon)。他认为,学术经典多指一些比较古老的、与科学和哲学相关的音乐理论,几乎不涉及音乐,其中一些与调律和乐律学相关,其观点和研究方法多来自音乐之外而不是音乐文化本身。关于教育经典,其历史从属于一种技艺(craft)原则,因为在16、17世纪,作曲上的模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最常见的是对前代大师的复调风格的模仿,不像音乐学术研究,学习此类音乐与智性生活相关,这种对过去风格技巧的专注也与当代趣味产生了一定距离。表演经典是指包括过去作品在内的一套常演曲目。威廉·韦伯提出的这三类经典分别对应了理论研究、作曲实践、表演接受三个维度,而现代意义上的经典一般指向的是表演经典,但在考察音乐经典起源与确立问题时,其他两类经典也不能越过。正如威廉·韦伯所言,这三种经典并不是严格的或恒定的,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关于作曲实践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从教育层面转向了理论层面。关于这一点莱斯大学音乐学教授玛西亚·希特伦(Marcia J.Citron)也有过论述,她将音乐经典分为两类:学科的(disciplinary)和曲目的(repertorial),这种分类一定程度上对应了威廉·韦伯的上述分类,希特伦认为,在音乐学领域,申克分析(Schenker analysis)、草稿研究(sketch study)、档案工作(archival work)等都是西方艺术音乐研究的学科范式,而曲目的经典顾名思义就是常演曲目,她认为这两类经典处于各自独立并相互作用的状态,如果没有惯常的学术音乐编辑传统,一些早期音乐如迪费的弥撒曲就不会成为经典。相对地,常演曲目也塑造了学科经典,假如贝多芬的音乐没有得到经常上演而被视为经典的话,也不会出现草稿研究。无论是威廉·韦伯还是玛西亚·希特伦都区分了几类不同的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直接将经典视为核心保留曲目的简单看法,而现代音乐经典的起源就与上述不同类别的经典相关。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音乐经典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但威廉·韦伯认为,在音乐经典化的过程中,浪漫主义所强调的“天才”“想象力”并不是音乐经典确立的基础,对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狂热也不是音乐经典的起源。因为在整个18世纪,很多作品已经成了保留曲目。
在18世纪之前出现的一些音乐实践不能被忽视,因为现代音乐经典就来源于此,威廉·韦伯列举了几点。其一,一些由于表演或出版而保留下来的作品,例如雅各布·阿卡德尔特(Jacob Arcadelt)的第一本牧歌集在他去世后的1572—1654年间再版了42次;也有一些原因会导致古老作品的复兴,例如多梅尼科·加布里埃利(Domenico Gabrieli)的《毛里奇奥》()在首演20年后的1707年又在弗洛伦萨上演。其二,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体裁作品,例如16、17世纪在酒馆演唱的多声部的轮唱曲(catches)。其三,一些在神圣日和世俗节日演出的作品,例如整个17、18世纪,阿格雷里(Gregorio Allegri)的《求主垂怜》()在复活节前一周的西斯廷大教堂就持续上演。其四,16、17世纪对少数作曲家的狂热而导致的作品持续上演,例如在帕勒斯特里那(Giovanni Palestrina)1594年去世后,他的作品仍在西斯廷大教堂得到上演。其五,在音乐学习和教育中出现的对个别作曲家作品的崇尚,例如在弗洛贝格(Johann Jakob Froberger)在世的1667—1720年间,他的键盘作品手稿被广泛收集并出版,但1720年他去世之后,风向发生了转变,拉莫的作品成为了新的风尚。这些实践虽然并未产生所谓的常演曲目,但现代音乐经典或多或少起源于这些传统习俗,旧的音乐实践变得常见并在音乐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品并不是简单地被尘封于当下的曲目库中,而是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并代表了最高的品位标准。
威廉·韦伯认为,音乐经典的发展存在两个阶段:首先,对古老作品表演的传统实践成为定期演出的常演曲目;其次,对这些作为经典常演曲目进行智识和仪式上的界定。在第一阶段,音乐经典起源于英国的教堂,包括一些圣歌的记录、教堂音乐选集和大师音乐杰作的出版,等等。然而,随着“古代音乐”(ancient music)一词在18世纪的出现,标志着从常演曲目到经典转变的开始,“古代音乐”的术语来自传统技艺和对大师的尊崇,其中的传统音乐技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宗教复调风格,根源于教堂。威廉·韦伯进一步指出,1726年“声音学会”(Academy of Vocal Music)的成立也是从常演曲目向经典过渡的标志性事件,该组织的成立使得许多常演曲目得以固定;1776年“古乐音乐会”(Concerts of Ancient Music)建立,这个组织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发起了1784年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举办的亨德尔纪念会,这也意味着“古代音乐”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包括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作品,而是意味着超过20年历史的、公众接受意义上的作品,“古代音乐”(ancient music)与“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成了同义词,作为常演曲目的古代音乐具有了重要的智识特征,先前的政治功能变为了艺术功能,世俗性取代了宗教性,即公众接受意义上的核心保留曲目取代了宗教仪式意义上的常演作品,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经典的形成。
能够达成共识的是,核心保留曲目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音乐经典的最终确立,核心保留曲目使作品得到了重复上演的机会,从此进入经典的曲目库成为典范与权威的象征。与之相应,核心保留曲目的产生也是由于“经典作品”的概念,因为它们凌驾于历史之上。核心保留曲目的出现与音乐经典的确立是同步的,因为音乐经典即代表着以核心保留曲目为中心的音乐行为方式。与此同时,维也纳古典乐派对于古典准则的确立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经典化的进程,1810年霍夫曼宣称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3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曲家,霍夫曼口中的“浪漫主义”就是我们所谓的“古典主义”,对于霍夫曼而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构成了经典。
科尔曼认为这一转向发生在19世纪,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保留曲目由当下时代或前一两代作曲家的作品组成,因此在17世纪的威尼斯,即使那时的歌剧院像现代的城市电影院,蒙特威尔第的歌剧也没有获得像费里尼电影一样的待遇,巴赫的音乐在他去世后跌出莱比锡保留曲目的速度也并不亚于他那些名声不那么显赫的前辈。而在1800年或1820年左右,新的音乐进入保留曲目的同时,旧的音乐也不再被排除在外,正如贝多芬和罗西尼加入进来,而不会再被取代。从此,逐渐增加的保留曲目具有了历史的维度,既向前追溯了那些过去的作品,又在历史的车轮下不断累积。
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在《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一书中将音乐作品概念确立的时间定位在1800年左右,在这个时间节点,创作和表演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作曲家身份意识觉醒,主动追求原创性的欲望凸显;表演被“固定”于作品之中,成为一种对创作的“遵从”;音乐的自律性得到肯定,器乐音乐因此获得了独立身份,并被视为所有艺术中最高形式的象征。在这种意义上,戈尔认为巴赫并不是一位真正的作曲家,而是一个拥有高超技艺的匠人(craftsman),巴赫“无意”谱写音乐作品,因此他的创作只能是“技艺—经典”。针对作品概念与音乐实践,戈尔提出两点:第一,1800年以前,作品概念隐蔽地存在于音乐实践中;第二,1800年以前,作品概念并不规范实践。如果将其中的“作品”换成“经典”,韦伯应该会赞同,因为他所关注的正是18世纪以及之前音乐经典的雏形——“常演曲目”;科尔曼也应该会赞同,因为戈尔认为的音乐作品概念确立的时间与科尔曼认为的核心保留曲目确立的时间是一致的,并且核心保留曲目的确立也在戈尔音乐作品的概念之下。
综上,韦伯关注了18世纪以及之前的音乐实践,即在“核心保留曲目”真正确立之前“常演曲目”的相关情况,他考察的是音乐经典确立的“前历史”;科尔曼则认为19世纪是音乐经典真正确立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刚好与戈尔认为的作品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合。因此,如果将韦伯、科尔曼、戈尔的观点串联,就形成了音乐经典确立的完整线索,因为经典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审美:绝对音乐观念
在音乐经典确立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转向,最鲜明的就是“器乐的独立”,即“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又称“独立音乐”或“纯音乐”)观念的确立,在此之前,声乐的地位一直高于器乐,与语词绑定似乎是音乐获得意义与价值的唯一方式,而器乐音乐则由于空洞的声响和缺乏实质容易遭到怀疑,正如达尔豪斯指出的:“在曼海姆乐队到巴黎凯旋之前,甚至最有教养的人也贬低器乐,将其斥为无生命的噪音和空洞的声响。”早在古希腊时期,音乐与诗歌就被视为一个整体,即诗歌是音乐的基础,音乐与文字的韵律不可分割,正如保罗·亨利·朗指出的:“希腊音乐的历史多半与希腊文学的历史相一致,因为二者是无法分离的整体。”声乐地位高于器乐的原因还要追溯到西方艺术音乐的源头——宗教,即音乐作为宗教礼拜仪式的附属,因为只有与赞美诗结合的音乐才能具备进入教堂的资格,进而得以流传。从那时音乐就被赋予了功能性,即“作为基督教奉献的体现,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
后来受到17、18世纪模仿美学的影响,音乐又被视为是对自然的模仿,器乐则被视为是乐音的描画。在著名的卢梭与拉莫之间关于“旋律与和声第一性”的讨论中,卢梭认为旋律中存在着某种“道德人格”与“情感力量”,具有模仿的能力,这恰恰是艺术中最尊贵的组成部分,而和声不过是一种哥特式的、野蛮的创造,从单旋律音乐向复调的转变严重毁坏了音乐,也破坏了旋律所具有的模仿性。为此,他区分了“模仿的”音乐与“自然”的音乐,前者“表现情感”或“形成意象”,后者除音乐本身之外别无他物,即是空洞的噪音。卢梭的论调显示了他对无标题器乐音乐的轻视,即认为任何不予“描绘”的器乐音乐都不值一提。总之,器乐音乐长久以来被视为不能“诉说”、不能“体现”的空洞噪音而低声乐一等。
这一现象在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反转,器乐音乐由于非语义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反而成了一种优势,这正满足了浪漫主义者对无限的渴望以及对永恒的追求。正如达尔豪斯所言,18世纪90年代对器乐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将“不确定性”解释为“崇高”而非“空洞”,器乐音乐的“机械”变成了“魔力”。这种转变与E.T.A.霍夫曼、路德维希·蒂克、瓦肯罗德尔、让·保尔等浪漫主义文学家不无关系,他们甚至在小说创作中凸显器乐音乐的崇高性,将它视为一种“语言之上的语言”,即语言的尽头是音乐,脱离了语词的器乐音乐承载了浪漫主义不可言说的诗意幻想。霍夫曼称器乐音乐是“真正的”音乐,不屑于借助、掺杂其他艺术。“脱离”语词和功能约束的音乐将自身进行“扬弃”或“擢升”,超越了有限,暗示着无限。对他而言,器乐曲是“所有艺术中最浪漫主义的——几乎可以说唯一纯浪漫主义的”,并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视为器乐曲的最高体裁。因此,对器乐音乐感召力的推崇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学的启发,音乐中令人困惑或空洞的东西被重释为崇高或神奇。
当然,在“绝对音乐观念”这一审美范式确立的过程中,哲学家们也加入其中。施莱格尔将音乐的形式比作哲学思辨,形式是精神,而不是情感再现或表现的外壳。叔本华认为,音乐跳过了表象,直达意志,音乐所表现的并不是悲伤、快乐、痛苦、平静,而是这些范畴本身,即“音乐所表现的并不是依附于世界的经验性显现,而是深入至世界的形而上本质”。甚至再后来,器乐音乐被视为了一种艺术宗教,它将情感从语词束缚的人生音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剥离掉世俗纷乱的情感文化,使之成为神圣化的永恒。进而,对器乐音乐的聆听与感知也如同宗教一般成为虔敬的审美观照,使听者遁入一种忘却自我和世界的凝神观照的状态。至此,器乐音乐以压倒性的胜利战胜了声乐音乐,成为“语言之上的语言”“形而上学的本质”,甚至是“艺术之中的宗教”。
器乐的独立是音乐经典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音乐朝向自律性过渡的关键性转折,更是美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埃格布雷希特在论述音乐古典概念时也将“器乐的独立”放置在了第一点:“器乐曲被提升为音乐的典范和‘她艺术上的独立性’,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纯音乐’的出发点和相关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器乐的独立是音乐自律性的一个方面,也是形式主义美学的肇始,语词不再被视为音乐的意义所在,甚至成为音乐的拖累,器乐曲才是纯粹的、自足的音乐。
不论如何,这一转向影响了以往的价值判断,其重心转向了音乐本身。如果以“本质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来看,器乐地位的反转是审美选择的变化,他提到了阿拉斯戴尔·弗勒(Alastair Fowler)的观点:“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由经典作品所代表的体裁有关。”“文体从来都不会均衡地,更不用说全面地,出现在每一个时代里。”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这一观点也暗合了王国维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于音乐而言也是如此,因此,经文歌等宗教作品之于中世纪、牧歌等世俗作品之于文艺复兴的意义便一目了然,歌剧、奏鸣曲、协奏曲等成为巴洛克时期的代表性体裁,艺术歌曲、钢琴小品、交响诗在浪漫主义时期的繁荣也成为时代之风潮。交响曲——这一与歌剧平起平坐的体裁不仅在古典主义时期成为中心,还彻底扭转了器乐的地位,进而勾勒了以“交响乐”为中心的西方音乐史。依布鲁姆所言,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这种体裁和经典的关系是审美的选择,那么以交响曲为中心的器乐地位的提升标志着音乐作为“美艺术”的合法性得到彻底确认,作品的价值仅仅涉及审美,别无其他,我们不得不再次品味布鲁姆的那句话——“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因此,“器乐的独立”是审美上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走向经典的必经之路。
三、观念:音乐博物馆
达尔豪斯在《十九世纪音乐》一书中指出,19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博物馆的世纪”,这其中存在着“进步观”和“经典观”的两种混合。“博物馆”一词充满了隐喻,博物馆本是陈列文物古迹、美术工艺、视觉装置等艺术的场所,那么对于音乐这种并非实体的声音艺术而言,博物馆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戈尔那里,所谓的“博物馆”是指音乐作品的概念,即剥离了地域、历史、世俗、功利,仅仅具有审美属性的音乐作品,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此视为音乐自律性的宣言,因此这个“博物馆”是想象之中的,在“作品”这一概念之下被“展出”,音乐厅则提供了“展出”场所,人们“观赏”的仅仅是其审美属性,正如戈尔所言:“随着音乐跻身于美艺术领域,音乐必须得找到一种可塑或等值的物品,一种宝贵而长存的产物,可以视同业已赢得敬重的美艺术的客体对待……这一客体叫做‘作品’。”作品概念的出现框定了音乐创作、表演、接受的行为,即人们开始将音乐创作视为涉及作曲和演奏的活动,音乐表演则是对乐谱的遵循而不是即兴发挥,听众的聆听行为是一种主动的凝神关照而不是礼仪程序或背景娱乐式的被动参与,因此作品概念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而这种规范性就促使了音乐博物馆的诞生,人们也渴望音乐艺术能够拥有一种如视觉艺术般的“展出”模式,福克尔就曾提出,“要使音乐艺术作品存之久远而不衰,最有效的办法无疑是在大庭广众公开演出……为真正的艺术家提供一座最富启示的典范的画廊”(当然他指的是巴赫的作品);李斯特也呼吁,“我们要求建立一座音乐博物馆”,当音乐作品得以定期在特定场合演出而面向公众时,它已经获得了同其他美艺术一样的独立身份,而这也标志着现代音乐经典的最终确立。
对于作曲家而言,为“音乐厅博物馆”而作则成为一个悖论:一方面,作曲家在原创性思维的主导下渴望逃脱“音乐厅博物馆”的禁锢,音乐厅不能沦为重复上演旧作的“博物馆”,而应成为鼓励新作的“试验田”;但另一方面,作曲家又渴望进入这一“博物馆”,他们希望成为留名青史的不朽经典。
除了音乐厅,音乐史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形的博物馆”,毕竟很多史书上记载的一些作品已很少被上演;录音、录像等音像制品又可被视为陈列“音乐标本”的“博物馆”,毕竟得以录制的一些作品也仅仅是“音乐标本”。不同种类的“音乐博物馆”其背后的指向也不尽相同,例如同为演出场所的歌剧院就与音乐厅略有不同,由于歌剧艺术演出成本较高,因此重复上演“旧作”是歌剧院的宿命与职责,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还存在新版本的制作问题,而音乐厅除了上演旧作之外还承担了推出新作的职责,但是反观当下,音乐厅舞台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那些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旧作,已过去近一百年的20世纪作品却很少上演。从这个方面来看,“音乐厅博物馆”具备了象征与隐喻的双重意义:第一,象征了那些具有永久价值的、能够重复上演的经典之作;第二,隐喻了那些过去的、保守的、陈旧的传统旧作。与音乐史、录音、录像相比,音乐厅这一“博物馆”毕竟是唯一具备现场感的形式,也是唯一确定核心保留曲目的方式。
“音乐(厅)博物馆”既有某种讽刺性的比喻,也包含了一种褒奖性的赞誉。在达尔豪斯看来,“博物馆”一词表达了一种对文化事物的厌倦乃至憎恨,因为它暗示着旧作对新作的一种阻碍,但他也承认“博物馆现象”遵循了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原则,即音乐作品开始以一种凝神观照的方式被欣赏。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伯克霍尔德看来,“博物馆思维”深深影响了作曲家的创作,他们在为“音乐厅博物馆”而作,这也是近百年来音乐中历史主义的主流,他认为理查·施特劳斯、勋伯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奥尔夫、巴托克等20世纪作曲家仍是为“音乐厅博物馆”而作,他们追寻着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大师的脚步,延续着以维也纳三位大师为重心的德奥路线。在此,“博物馆作品”并不是对因循守旧的批判,而是代表着作曲家所选择的主流的音乐实践,他们在规则与个性之间挣扎,在传统与原创之间权衡,他们以进入这个“音乐厅博物馆”为荣,因为这代表着持久的价值与后世的敬仰,正如伯克霍尔德所言,“对于作曲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悦当下的听众……而是如何在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古典大师’一起被永久地悬挂在墙上”。
四、结语
综上,音乐经典的确立经历了从“常演曲目”到“核心保留曲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俗性取代了宗教性,作品概念得以确立。音乐经典确立的背后更是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的变迁,大众音乐文化的兴起与“绝对音乐观念”为音乐经典的确立提供了群众基础与美学支撑,古典音乐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贵族艺术,也不再是依附于语词的附属产物。随着音乐会建制的出现,“核心保留曲目”逐渐走向音乐经典概念的中心,一方面作曲家以进入音乐厅这个“博物馆”为荣,另一方面音乐博物馆又隐藏了一定的危机,背后是作曲家希望留名青史的雄心与不可避免的曲目固化的现实。音乐经典——作为从文学领域“借用”而来的概念,其内涵与指向也存在着某些转向,正是这些转向导致了音乐经典这一概念的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