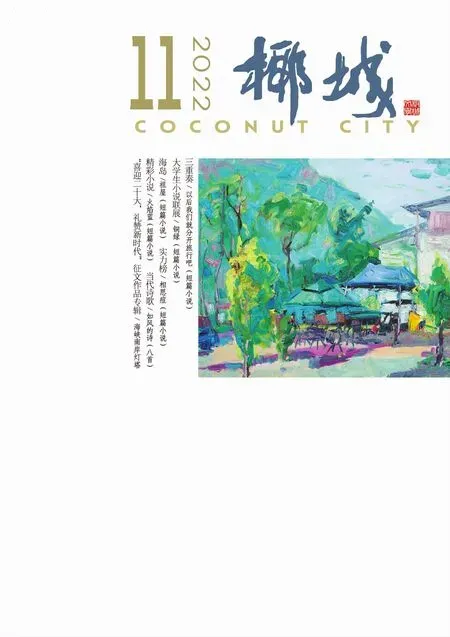祖屋(短篇小说)
2022-11-10金戈
◎金戈
作者简介:金戈,本名郑朝能,黎族,1983年生,海南保亭人。海南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6期民族班学员。现任保亭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诗集《木棉花开的声音》《钓一池好时光》《橄榄集》。
1
胡道全从村委会回来,告诉妻子:“鸿光他爸把祖屋登记在他名下了。”
妻子一听,立马大叫起来:“不可能吧?不应该啊!这是我们的房子,谁都知道的!当时是大姐给的钱,孩子他爷爷还从三脚灶旁边柴灰底下挖出他积攒多年的一叠钱,让我们去买砖买瓦片买横条建的,为的是让我们养老人,我们都住了那么多年,直到后来进了农场,他们才接着养爷爷。”
胡道全压低声音说:“小声点,四哥听到了不好。”
妻子反而提高了音调,故意对着四哥家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又不是什么密谋——这是我们的房子!不声不响就放到他名下,也做得出来啊!不行,我要告诉大姐。”
大姐是胡道全、胡道明的亲大姐,在县里当官,是家族的骄傲,素来代表家族的荣誉和权威,她的话家庭里没有人敢不听的。爷爷指的是胡道全、胡道明、大姐的老父亲,他们习惯从孩子那里叫爷爷。胡道全在家排行老五,是最小的儿子,也是爷爷奶奶最疼爱的儿子;他家有四个子女,大儿子鸿飞,大女儿鸿燕,二儿子鸿达,二女儿鸿雨。胡道明排行老四,胡道全叫他四哥,也有四个子女,大儿子鸿杰,二儿子鸿英,三儿子鸿光,老四是一个女孩叫鸿颜。
胡道全和四哥胡道明两家挨着,是关系最要好的血脉宗亲,平日没少互相帮衬,也经常在四哥家喝酒。胡道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入了农场,成为割胶工人,后来由于农场改革,大部分橡胶被砍伐,他没有承包土地做果园,而是选择进城,在市政所当一名事业单位的聘用职工,妻子则在一家幼儿园厨房做后勤,四个孩子在县城读书。
他们不在村里居住已经很多年了。
祖屋是爷爷奶奶的养老之所。说是祖屋,其实也不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建的带拱廊的三间砖瓦房,至今也就三十几年。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居住在这里,旁边的茅草房是厨房,胡道全的大儿子鸿飞在村小读书时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孙三人在祖屋里同食同宿。
祖屋的中间是爷爷的卧室兼客厅,右边是奶奶和鸿飞的住处,左边是胡道全一家的居室,常年上着锁。胡道全一家虽然常年在县城居住,但县城和村庄离得不远,平时有些婚丧嫁娶、祈福之类的民俗大事,都会回来参加,骑摩托车半小时就到了,每次回来也还住在祖屋的卧室里。
奶奶先于爷爷去世。爷爷住在祖屋中间一间。后来,胡道明的二儿子鸿英就带回一个女朋友,住进右边的一间。左边是胡道全的大儿子鸿飞和女朋友住的。
祖屋似乎已被分成了三部分。
鸿英住进了祖屋,胡道全夫妇没有反对,仿佛是默许。他们知道四哥胡道明的三个儿子都有了女朋友,房子不够住,所以也就默许鸿英和女朋友住进祖屋。这期间,胡道全的妻子倒是有说过,鸿英住进来只是暂住,到时还是要搬出去的。
这一住就是十年。
房子住久了,就感觉是自己的了。况且,胡道全并没有说过不让他们住,在四哥的眼里祖屋对于五弟一家似乎不重要了。兄弟这样想着,反正弟弟不在村里常住,子女也都在外面工作打拼,想来是不会在意这三间小瓦房的,两家关系又那么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今年农村登记办理包括房产证在内的不动产权工作一开始,胡道明就把这三间瓦房登记在自己名下。胡道明是这个村小组的组长,填报顺理成章。
前几年,政府落实了农村房屋援建政策,每家每户都按人头算平方给免费盖了平房,有些农户自己补贴了些钱,可以建大一些的,或加盖二楼。
胡道全家于是就在祖屋后面盖起了二层小楼。弟弟盖了新楼,旧房子就更应该不会争了吧。胡道明这样想着,便心安理得起来。
胡道全夫妇户口不在农村,属于非农业户口。可为什么在村里还有土地呢?其实,当初他们入场,农场限制超生,四个孩子只能随带两个入农场户籍,另外两个还留在农村。户籍留在农村的是鸿达和鸿雨。鸿达原先是跟着爷爷户口的,爷爷过世后他就成了户主。胡道全一家现在在村里的土地和享受的农村好政策,正是鸿达、鸿雨两个孩子的份额。可是,胡道全的两个儿子都在外打拼事业,不住村里,两个女孩也都远嫁外市县了。
人渐渐变老,思乡的情结愈加重了,胡道全和妻子就开始依恋故土。这落叶归根的规律,是没有变过的。这不,村里的新楼一落成不久,胡道全夫妇就隔三差五地往村里跑,工作之余努力打理自家的土地,种植槟榔和菠萝蜜树。自从新房子建成,胡道全一家每年都回乡下过年,过了小年十五才返城。他们在城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是政府的廉租房,才五十平,父母在一个小区,鸿飞在另一个小区,鸿达带着新婚妻子在外市县打工。
村里的房子大,房间多,够一大家人住。过年过节一家人回到乡下,能够好好团聚,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胡道全夫妇想着,以后大儿子鸿飞要是在外面混不下,回到村里住,是需要鸿达给宅基地建房子的,可是宅基地不好批——除非在原来的宅基地上重建。
祖屋于是成为胡道全夫妇未来给大儿子建新房的有利保障和基础。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2
话说胡道全的妻子给大姐打电话告状,表态说:“大姐,我是不会同意的。您知道,当初房子是您和爷爷出钱建的,我们出力,养老人,房子是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的,四哥那样做太过分了,事先也没有问过我们一声,就偷偷报了。”
胡道全打断妻子的话:“也不要说那么严重,还没报到县里呢,现在报表还在村委会那里,可以改,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明天我找四哥问清楚,把名字改回来就好了。兄弟之间别伤了和气。”
大姐在电话那头说:“阿全说得对,有事好商量,千万别冲动,骂架、打架都是愚蠢的行为,只会让人笑话。过两天我回去了解一下再说。”
第二天一早,胡道全去找四哥,可是一向早起的四哥竟然睡还没醒。到了九点多,胡道全再次到哥哥家,儿媳告知:“爸爸身体不舒服。”其实,胡道明昨晚听到弟媳喊话后,自知理亏,心虚,不敢面对,便故意不和弟弟见面。他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他本想暗中把房子归入自己名下,造成既定事实,那时就好办了,要改回来也就不好更改了,大不了给弟弟一些钱做为补偿,本是一家人也不至于死磕到底吧——平时弟弟多温和,也好说话。可是想不到,事情还没做成就被弟弟知道了——更想不到的是弟媳知道后严正地表达了不同意的立场!要知道,兄弟之间的事,一旦有女人从中掺和,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
胡道明人不坏,但他确实也有为子女考虑的算盘。他一夜无眠。此时的他竟然不知道如何面对弟弟。
到中午的时候,胡道明实在装不下去,饿了,起床后一走出房门就看见弟弟走来。他怔了一下,心里咯噔咯噔地打着鼓。他知道事情难办了。还没等弟弟开口问,他就没好气地说:“你们不同意,那就给你们好啦,统统给你们,什么都拿去!”言语之中满是怒气。他心里在埋怨弟弟跟自己争房子。
胡道全见哥哥生气,就说:“阿哥,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我就是想问问清楚,可能是村委会的人登记错了,我们一起去改过来就可以了。”他顾忌哥哥的脸面,想给哥哥一个台阶下。
胡道明不想搭理弟弟,走上走下,东翻翻西翻翻,也不知在找什么。弟弟看着哥哥,希望得到明确的回应,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气话,他只希望能把祖屋归属人的姓名改成他的二儿子鸿达。
胡道明心里此时也是一团乱麻,有些恼羞成怒,大声说:“功劳都归你们,苦劳留给我——是谁养老人养到死的?”
“那是两回事。”胡道全说。
关于孩子爷爷的赡养照顾,说来一波三折。胡道全自从举家迁出在外务工谋生,老人就独自生活了。那时两位老人还可以自己劳动、做饭。大儿子鸿飞在村小读书,和爷爷奶奶居住生活,分担了许多砍柴煮饭的事。过了几年,鸿飞考上城里的重点小学民族寄宿班,从此爷爷奶奶就相依为命了。那时胡道明一家住在旁边,是爷爷奶奶的邻居,生活上自然要关照得体贴,煮了好饭便会分一份给老人端来。奶奶去世后,爷爷孤零零一人,胡道明就在新建不久的平房里腾出一间屋子,安排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爷爷爱喝酒,早中晚三顿,喝酒时自言自语,醉了躺倒就睡。为了方便爷爷随时能喝酒吃饭,胡道明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他给老人家配置了一个煮饭用的电饭煲、一个热菜用的电饭煲,旁边还备了一桶水供他煮饭、煮菜和饭后洗漱。爷爷这样的生活一晃就过去几年。
年迈的爷爷病了。住院的时候,孙子们轮流值守,有时带他上街游逛。他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他逛街的时候显得异常开心,总是有说有笑的,他喜欢在街头大排档喝酒,看人来人往,和儿孙们聊天说笑。
大姐说,既然他喜欢城里,就让他和老五住在一起吧。于是爷爷就和小儿子胡道全住在一起,过了两三年城里生活。
可以说,在对老人养老的功劳上,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有功的,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这就不好说了。其实也没有必要分清楚。可是此时哥哥胡道明却把祖屋的归属权与照顾老人的功劳大小扯到了一起,这让弟弟不服气了。
但胡道全不想和哥哥争执,便说:“这样的话,那就叫上村委会的领导,我们当他们的面说清楚,到底是谁更有资格要这个房子。”
胡道全回了家。走时,胡道明叫道:“去就去,你能和我争吗?争得过吗?你斗不过我的。”
胡道全没想到哥哥这么硬气,会和自己争这个房子,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像有一把无形的刀毫无防备地从身后捅进他的心脏。
要知道,这些年来两家和睦相处,走得比任何一个兄弟都亲。家还是挨着的,连院子都是共用的,入户的路也是共用的。胡道全家在祖屋后边建了新楼房,路还是老路,必须经过哥哥的家门前。原本,他们都是一条路的,和爷爷住的时候是一个院子的。
今天两兄弟为了给各自的孩子争取祖屋又争了一回。其实,他们年轻的时候,也争过一回,还打过一回。弟弟比哥哥早一年娶得媳妇,爷爷开心,就拿钱给弟弟去买橡胶苗,种满了一片山腰。第二年哥哥也带媳妇回来,那媳妇就和哥哥说道:“让老人把一半橡胶给我们,你也出力了,谁不是爹妈的孩子啊,一碗水要端平,道全有橡胶,我们也要有。”哥哥和老人提出分橡胶的事,老人不同意:“那是我给你弟弟要钱买苗种的,他们夫妇二人种得辛苦,你当哥哥的就不要争了,钱我这里还有一点,你们再去买苗回来种。”
胡道明执意要分弟弟的橡胶。
胡道明受新媳妇挑唆,硬要分财产,分家。老人疼爱小儿子,坚决不同意分出橡胶,胡道明就像急红眼的一头狼,怒吼道:“必须要分!”老人还是不同意,胡道明气恼不过,跳起来就打了自己的父亲,还把父亲拖到门前晒谷场上,砸坏了父亲的手表。
瘸腿的父亲哪里打得过年富力强的儿子,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只好松口答应了。后来,四分之三的橡胶就被哥哥夺走了。
这都是因为胡道明的老婆孙德丽怂恿的。
十里八乡谁人不知孙德丽是个厉害的角色,是乡里远近闻名的毒蛇村妇、泼妇,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被她挨个骂了个遍。人们都说,胡道明是被孙德丽蛊惑坏的,他们家也是被孙德丽给败坏的。人们都叫她孙婆娘。
其实,把祖屋放到胡道明名下就是孙婆娘的主意。这时她听说胡道全为此事找上门来,就吵吵嚷嚷起来:“住城市里,争什么房子,我儿子没房子住你没看见吗?你们抢这破房子又不住,偏要和我们对着干,你说,你们安的什么坏心?”
胡道全不再争论,静静地走回家来。妻子见状,走出门来回应道:“四嫂啊,话别说那么难听,谁不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况且,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的,你们偏要争,那就等大姐回来评评理。”
孙婆娘说:“呸你的!谁怕谁,论功劳我们家最大。”
说着,她拿过一把铁铲,铲出一堆火灰,撒在胡道全家路口,念了咒语,说:“从此两家互不往来,谁跨过这堆火灰谁就眼瞎。”这是之前黎族农村的一种迷信陋习,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是一件晦气的事,更表明了当事人的怨恨之心。后来还是胡道全请当地的道公前来施法解除,这才安心。
3
胡道全对妻子说:“这事先不要和鸿飞说,他脾气大,我怕他忍不过就打架,兄弟闹起来多难看。”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村里的人已把两家争房子的事,告诉了鸿飞。
过了三天,大姐回村里来,召集家族代表在胡道明家的院子里,召开了祖屋争夺事件的调解会。大姐买回好多菜,让兄弟们准备家族晚宴。
胡道明三个儿子和胡道全的两个儿子都在场。气氛比较紧张,空气中满是火药味,随时一两句气话就能燃爆,引发血案。
最后大姐发话:“谁都没有发言权,这是我和爸爸出钱建的房子,房产权归我和爸爸,现在爸爸不在了,我说了算。这个房子,一开始就交给道全他们一家住,照顾爸爸妈妈,谁都知道的。他们是出去闯生活了,户口也在外面,可是他们永远是这个村的人,永远是我们家族的人,现在他们回来住了,房子还得归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所以道明,你们就别争了。就这么定了,好吗?”
有大姐发话,胡道明和孙婆娘心里不服,可嘴上也不敢说什么了,算是默认。倒是住在祖屋右间的胡道明的二儿子鸿英显得特别愤怒,吼叫道:“不住就不住,明天就搬出去,谁稀罕。”
旁边一众堂兄堂弟,也早对胡道明一家心生不满。他们是站在五叔胡道全这边的。堂兄鸿望看见鸿英放话,也做出了回应,说道:“兄弟们,我们回家去,在这个家吃饭怄气,不吃他家的饭!不认他家这个兄弟!”
孙婆娘骂道:“你阿望就这么厉害,道全给你们什么好处,你要帮他。”
鸿望高声说:“不想听你说话,你就是祸水。”
孙婆娘跳起来,抓起旁边的板凳就朝鸿望丢过去,被鸿望躲过了。
一旁忍着不说话的鸿飞此时火山一样爆发,指着孙婆娘大喝道:“够了!我忍你很久了!老太婆!”说着就要冲上去打她,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正要寻找发泄的沙包。
鸿英盯着鸿飞,他料不到一向温文尔雅的鸿飞会大发雷霆,并且要动手打自己的母亲,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
大姐制止道:“都坐下,冷静,我的话都不管用了吗?”
大家不说话,乖乖地又坐回各自的座位。
大姐说:“有事就不能好好商量吗,动什么粗,好好沟通才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房子的事不满意,干脆拆掉,谁也别想要。”她看看道明和道全两兄弟,看看孙婆娘和胡道全妻子,又看看鸿英鸿飞等人。
在场的族人个个惊愕,抬眼看她。他们知道大姐一向说话算数的。这时大姐却噗嗤一声笑起来:“看看你们,都急成什么样了,兄弟要打架,传出去名声很好吗?傻不傻?记住,心要放大放宽,不要为了一点好处结了仇。放下了才能得到,今天你放下这个,明天你会得到那个。都别发火了,该是谁就是谁的,争也争不来,争来了也不一定是福气啊。”
鸿飞冷静下来。可是他的心仍然愤愤不平。趁着大姑在场,他把压在心底的一件事抖了出来。
鸿飞说:“大姑妈,鸿英他妈心可毒了,我们家族因为她才多次闹得不愉快。我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那件事,我和我妈从农场回来看爷爷奶奶,在她家看电视的时候,我竟然被她诬陷偷她的钱,我一直哭着说没有,她不依不饶,连爷爷奶奶求情也不行。我妈妈就说‘小孩子不会说谎的’,她就对我妈破口大骂,拿出砍刀追我和妈妈,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满村子跑,最后被追赶无路可逃了,躲在村外的槟榔林里,后来学校老师腾出宿舍给我们过夜,这才躲过一劫。这个仇,今天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啊!”
鸿望跟着说:“他家占用道全叔的山地那一次,本来是要给我的,他们却要争,结果他们凭着三兄弟人多,拿刀要砍我,打了我之后把那块地拿去了。这事是不是也要清算?”
大姐和颜悦色地说道:“好了,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别提了,眼睛要往前看,不要盯着过去,那样怎么能得到幸福呢!”
一场祖屋归属权的调解会,变成了孙德丽一家的批斗会。
胡道明见情势不妙,站起来,手一挥,说:“好啦好啦,我同意了,明天就跟村委会说,房子改成鸿达的,你们满意了吧?我是给大姐面子才让出的,不是怕你们。”
祖屋就这样归到胡道全一家名下。事情眼看告一段落。
可是孙德丽那婆娘,祖屋的争夺计划没能得逞,还是不甘心,每当喝酒过后就借着酒劲对胡道全一家大骂一通。不过她是趁着胡道全一家不在的时候骂的,人家一回来她就闭嘴了。
自从上次鸿飞要打她,那怒气冲冠的样子和要吃人的眼神让她害怕,不敢在鸿飞面前撒泼。
对于孙婆娘的德行,乡亲们有目共睹,早已见怪不怪,只得由她骂了。
4
一个月后的一天,鸿飞开着小车从城里回村,路过伯父胡道明家,却被几根竹竿给挡住了去路。
胡道明正在和几个青年在院子里搭竹架,地上用白灰画着方形线框。
鸿飞走上前问:“伯父,这是做什么?”
胡道明回答:“做房子。”
鸿飞说:“那不是挡住我们的路了吗?”
胡道明指着边上不足一米的过道说:“给你们留了路,可以走过去。或者你们开直升飞机过去啊!你们开小车进开小车出,从我门前经过,压坏了我家多少财运。”
鸿飞知道这是杠上了。他血气方刚,见回家唯一的路都给堵上了,气不往一处来,径直走上前把竹竿踢开,扒开一条路来。
胡道明也不敢硬来。
看来,祖屋的事情解决了,可是两家的仇却结上了。
胡道全过来说:“路不给我们走,那我们得要新开一条路,各走各的道,谁也不碍谁的眼。”
胡道明说:“同意。我不要房子了,兄弟也不要了。”
胡道全说:“那我们的路怎么开?”
胡道明说:“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
胡道全指着前面不远的槟榔地说:“那就从前面过。”
鸿英从屋里走出来,大叫:“槟榔现在值钱,你们别想砍我的槟榔。地也不是你们的。”
鸿飞放好了车,过来理论:“你们是成心不让我们进出啊!”他指着鸿英愤怒地说,“你们现在这块槟榔地,那是奶奶的菜园,那时我还和爷爷奶奶住,你别忘了!实话说,这块地也是你们争夺去的!”
鸿英说:“以前是以前,现在已经确权,是我们的地,有确权证的。”
他们争论了一会,胡道明大概知道自己封了路又不给兄弟借地修路,是很过分的事,于是松口道:“好,留给你们从前面过。不过有一段,是旁边袍吉家的,他同意你修就修。槟榔树你要给我移植好。”
胡道全去找袍吉,说明了修路的事和原委。袍吉早就把两家的恩怨看在眼里,很同情胡道全家。
袍吉征得父母和妻子的同意,说:“修就修吧,我不同意你们就没有路了!需要砍几棵槟榔树就砍,入口处的两棵花梨木也砍了吧,免得碍路,不方便车辆进出。都是兄弟,应该帮忙,钱就不要了。”
袍吉一番话,说得胡道全心里暖洋洋的,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村里就来了人,量入户的道路长度。近些年来,乡村道路是村村通、户户通,政府免费把水泥路修到家。在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下,胡道全家全新的路终于修建完成了。
他们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路,通向幸福的路。
胡道全和哥哥胡道明一家,不再同一条路了。
很快,胡道全随后在祖屋前面砌起一道高高的水泥砖墙,兄弟两家划分了界限,把宗亲之情也分开了。
八月十五的月光,也被这堵冰冷坚硬的墙给切割成两半。想想爷爷奶奶健在的时候,他们兄弟两家同在这祖屋前的小院子里,大人喝酒、唱歌、划拳、下棋,小孩则一起吃月饼、猜谜,躺在溶溶月色里听故事,那曾是多么和谐温馨的画面。
而那幸福的时刻已不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出现了。
有些伤口虽然愈合,但还是会隐隐作痛。也许,他们心底那堵墙会有被拆除的一天……
也许不会。
5
又过了一月。
大姐突然给胡道全来电话:“阿全,鸿光他爸病重住院了,你不知道吗?”
“没听说呀!不知道。”胡道全说。
“你们两家住在一起,竟然不知道,还是不是兄弟啦?我们明天到省医院一趟,老四病重,现在躺在那里,不能说话,怕是要不行了。”大姐说。
胡道全和妻子一脸愕然。他们两家自从争祖屋那件事后,再也没有来往。当然,胡道全也好久没有和哥哥见过面说过话了,更不知道他生了病,还严重到住进省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他心中忽然闪过一阵剧痛。毕竟,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胡道全和大姐赶去省医院看老四。
那天夜里,孙婆娘自己在酒桌上喝酒,自言自语,带着哭腔。隔着一堵围墙,胡道全的妻子听得清楚孙婆娘说:“可怜我男人呀,你好人没好报哟,到底是谁做法害你,我要拿砍刀剁她,看她厉害还是我厉害。祖宗房被人争了去,她还不满足,还要人命,要你的命呀!什么世道呀,杀人不见血呀!怎么我们这么可怜。”
孙婆娘虽不点名,胡道全的妻子也听得出是在说自己,当即隔着围墙冲孙婆娘喊:“没有的事不能乱讲啊!谁搞你们啦?我们又不懂做法。”
那边安静了一小会,又说:“谁应就是谁搞。不懂做法不代表不能请道公做。”
就在这时,只听得“乓”的一声,胡道全家安装在自家二楼边角上的摄像头被石头砸碎了,碎片掉了一地,石头落下来差点砸到胡道全的妻子。胡道全的妻子受到惊吓,赶忙跑回屋里躲起来。她打电话告诉胡道全和大儿子鸿飞。
摄像头是被孙婆娘的二儿子鸿英砸的。
鸿飞担心母亲,第二天从城里赶回来。他跑过去孙婆娘家,看见鸿英在院子里抡着斧子劈柴,那孙婆娘在酒桌上喝酒。
他对鸿英说:“是你砸我家摄像头的?”
“是又怎样。”鸿英斜眼瞥了鸿飞,很不屑的样子,照旧在那里劈柴。
“为什么要砸,碍你们什么事?”鸿飞气冲冲地问道。
“你们安摄像头,对准我家,我们做什么都被你们监控完了。你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不懂吗?”鸿英用力劈了一截木柴,那干柴瞬间裂开,弹飞两三米远,半截斧头重重地砸进了木墩,他提三次都没有提出来,就丢在那里。就在他正要走到井边打水抹身时,鸿飞一个箭步跳上来给鸿英一记重拳。鸿英没注意,往后倒下去,嘴角流出了鲜血。怒火把鸿英拽了起来,毕竟是在部队当过三年兵,体格好,也会点功夫,他猛一阵左勾拳右勾拳和膝顶、高鞭腿连环出击,鸿飞猝不及防,也被干倒在地,整个身体重重地砸在一堆啤酒瓶中,咣啷一声,碎了几个玻璃。鸿飞的屁股和双手被玻璃碎片扎破,流了不少血。
此时的鸿飞哪里顾得上痛,像被某种意念控制的人偶,只想把对方打倒服软。他抓起一个酒瓶,砸碎,刺向鸿英的腹部,鸿英躲不过,划破左边的肚皮。由于用力过猛,鸿飞没能刹住脚,直接扑向两家之间那堵新建不久的围墙,还没等他转过身来,鸿英一把就提起木墩上的斧头,朝鸿飞头上甩来。有些事很神奇,人在生气的时候力气大得很,前面提不起来的斧子,这时只需一抓就上了手,轻轻松松在空中挥舞。说时迟那时快,鸿飞凭直觉把头往下一缩,躲过了,随即嘭的一声,那斧子把围墙砸出了一个大洞,要是砸在人的脑袋上,估计脑浆会像被拍碎的鸡蛋那样四处迸溅。鸿飞脑子里闪过电影里的一招锁喉功,左手手指勾起做成虎口状,一把就勾住了鸿英的咽喉,右手握紧拳头猛捶他的头部,那快准狠一步到位,仿佛练过一般。在那强大的力量压制下,鸿英动弹不得,气都快断了,流着鼻血翻着白眼。鸿飞突然意识到要死人了,赶紧松开了手。
孙婆娘在旁边叫嚷着,叫来了左邻右舍。鸿望等一众堂兄弟们都赶了过来,怕出人命,就把两人分开。
孙婆娘报了案。辖区派出所很快就来了,警车和救护车开进了小院。鸿英、鸿飞被戴上手铐,被民警带走。几个堂兄弟也跟着去了。
孙婆娘哭得撕心裂肺,又哭又骂,什么恶毒的语言都用尽了。
6
鸿英、鸿飞被拘留了十五天。拘押期间还花了不少医疗费,由各家买单。
他们回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伤。
话说胡道全和大姐那边。胡道明那日在省医院里,经过专家的科学抢救,终于醒了过来,有了意识,能说话,也能吃饭了,第二天还能够下地活动。
胡道全和大姐当时听说家里兄弟动起手来,发生了流血事件,第二天他们就赶回来,到看守所看了两个孩子。他们没有把鸿飞和鸿英打架被拘留的事告诉胡道明。
大姐把鸿飞和鸿英狠狠批评了一通。大姐说:“祖屋的事情都已经定了,房产证已经发了,你们还纠结。再说,那是我的房子,我决定给谁,你们两个小孩有什么资格争啊?要争,也是你们的老爸老妈争,你们瞎掺和什么,为了一栋破烂的旧房子竟然兄弟大动干戈,要是搭进一条命,把你们埋进祖屋里,你们就满足了?”
两人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这时候都疲软无力了。看来,看守所的管教起了不小的作用哩!
看着两人似乎有悔过之心,大姐继续教育:“两家人的恩怨不要放到下一代。你们都是新时代里的青年,一个当过兵,一个读过大学在创业,都是有理想有能力的男子汉,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充满希望的时代,你们有能耐就把各自的事业做好,赚到钱,花自己的钱盖它个三层别墅、在城里买大房子,带着自己的老爸老妈过日子,不让他们替你们操心,那才算有出息。我这当姑姑的,从小看你们长大,也没少帮助你们读书,我不求你们给我什么回报,只想你们懂得为咱们的家族争光,懂得感恩,说一声‘姑姑,谢谢你!’我就知足了。”
鸿飞和鸿英不约而同地流出了眼泪。
大姐趁机抓过两兄弟的手握在一起,说:“好了,别哭了,答应姑姑,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傻事了,好吗?你们都要好好的,记住,你们是家族的希望啊!”
鸿飞和鸿英两兄弟此时已经泪流满面,心中有说不出的空洞。他们知道自己为了争祖屋的事大打出手,真是没有出息。他俩也真心地握着手,都“嗯”了一声。他们和解了。
一个星期后,胡道明也出了院,回到家里调养。两家人还是各顾各的,不相走动,但是怨气已经消散了。
只有孙婆娘还时不时地指桑骂槐出气。
有一天,孙婆娘请来当地一个道公(法师)做法,说是给胡道明祈福驱灾。孙婆娘信鬼神,她认为丈夫病重,还有家里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弟弟一家请道公做法害的。这下,她是有意请来道公,要把灾祸转移给胡道全家,她的目的很明确:既然他们混得好,就害他们百事不顺、百业不兴、百财不留,看他们还得意不!
孙婆娘授意道公在胡道明家新修的路上“做法”。胡道全妻子留意了这个举动,也请道公来家里“做法”消除之。当然,这只是江湖术士的骗术,哪里会灵验,只不过是愚昧之人的迷信陋习而已。
他们两家平静了两年以后,又迎来一件悲哀的大事,那就是孙婆娘疯了,整日自说自话,在村里逛来逛去,总爱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不是坏人,她才是,我是好人。”她一会儿嬉笑,一会儿骂骂咧咧的。
从那以后,孙婆娘就变成了疯婆娘。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偷偷地溜进祖屋里面睡觉,睡在地板上。她家那只温顺的大黄狗总是跟着她,也陪她睡在祖屋。对于一个疯子,胡道全又能怎样呢,赶她出去她还是偷偷进来。后来干脆上了锁,疯婆子就睡在祖屋走廊里。
有时她从两家的隔墙那边探头看过来,说:“喝酒咯,喝酒咯。”似乎两家的仇怨就不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