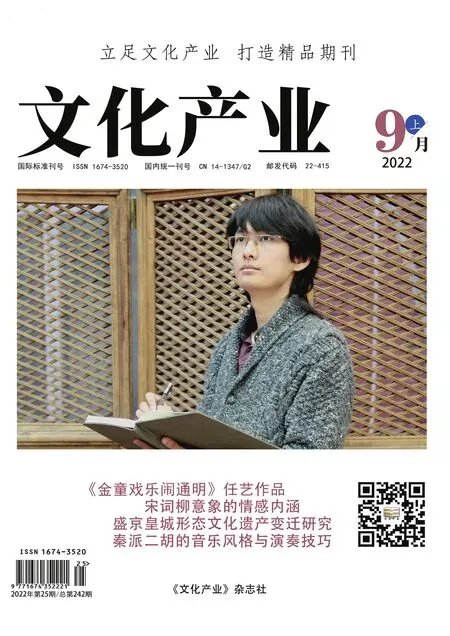盛京皇城形态文化遗产变迁研究
2022-11-10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李 雪 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按时间顺序分别从清太祖、清太宗、清圣祖、清高宗在位时期对盛京城市形态的改变入手,讨论盛京皇城的城市形态变迁。盛京城从一开始的边防军城,经历了城市规模的扩展,内部区域的重新规划,宫殿衙门等政治性建筑的建造与升级,最终蝶变成清代重要的陪都。其皇城气象一直延续至清王朝覆灭。由于城市地位的变化以及城市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脱离清王朝的盛京皇城被蚕食得几乎消亡。进入21世纪后其文化价值才重新获得重视与认可。
盛京皇城是清朝第一座皇城。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开始,这个城市就从明朝的一个卫城变成了一座皇城。盛京作为皇城的时间并不算太久,但由于清朝入关后把盛京作为有纪念性的陪都十分精心地养护起来,所以盛京皇城的城市形态在清朝时期一直以最繁华的状态陪伴着清王朝。盛京作为清朝早期的皇城,体现了清早期对皇城的规划与设计,整个城市蕴含着清早期的艺术与文化特色。因此,对盛京皇城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盛京皇城的建造初始—努尔哈赤对明朝沈阳中卫城的接收与改造
天命十年,即1625年。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第十年,他决意将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当时并没有更改城市的名称,因而古籍上记载的是迁都沈阳。沈阳是明代辽东镇的九座卫城之一,称“沈阳中卫”,它也是九座卫城中最大的一座。名称中的“卫”字显示出它的军事意义,也就是说,它原本是一座边防军城。
这座卫城采用了典型的方城形制,根据明代《辽东志》记载,沈阳中卫城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行过改、扩建,当时城墙全长九里三十步,高达二丈五尺。城外有两条护城河,两条护城河都非常宽且深。里面的河宽3丈,深8尺,全长十里三十步;外面的河同样宽3丈,深8尺,全长十一里多。根据明代的计量单位计算,沈阳中卫城的占地面积约为1.8平方千米。其四面见方,每座城墙正中开一城门,分别命名为“永宁门”“保安门”“安定门”“永昌门”,城内两条大路呈十字交叉,通往四座城门,构成整座城的中轴线。如今沈阳城内的北通天街,就是明代沈阳中卫城南北向的中轴大街的一部分。
据《全辽志》载:“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正对四座城门的是四座牌坊,分别为“靖边”“永宁”“镇边”“迎恩”。
这两条中轴大街将沈阳中卫城划分为四个大的街坊,它们又延伸出若干胡同,将大街坊分割成若干小街坊,其大小不尽相同。城中南部的人口密度较高,各种官府衙门也集中在南部。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它的四座城门上都有门楼以供士兵站岗,城门外筑有半圆形的瓮城,城墙四角还有四座角楼。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沈阳中卫城进行过一次修缮及加固,同时将北面的城门“安定门”更名为“镇边门”,与其牌坊同名。
由于清代建国初期还在与明朝争战不休,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军事方面,所以虽然迁都沈阳,但实际上并未对整个城市进行太多的改造,只是在南北大街相交的位置附近建造了汗宫、大衙门(即大政殿)和十王亭,作为其行政中心。
走向繁荣的盛京皇城—一座边防军城的蝶变
努尔哈赤迁都后不久便撒手人寰,由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国号天聪。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下令扩建沈阳中卫城,自此开启了清代第一座皇城的辉煌。
天聪及崇德年间——方城扩建及改造
皇太极对沈阳中卫城的扩建是从城墙开始的。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撰的《钦定盛京通志》第十八卷《京城志》记载:“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向者,左曰德盛,右曰天佑。西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向者,右曰福盛,左曰地载。池涧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钟楼一,在福盛门内大街。鼓楼一,在地载门内大街。八门正戴方隅截然。内池七十余处,水不外泻。城邑既定,遂创天地坛,壝营太庙。建宫殿,置内阁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
皇太极将沈阳中卫城原来的城墙加高到三丈五尺,加厚到一尺八丈,并在城墙上加筑了七尺五寸的女墙。城墙周长达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比明代的城墙增加了三百零二步,约500米,将整个城市的面积扩大到2.13平方千米。他没有按照原来的城墙那样设计四个城门,而是增加到了八个,分别命名为“抚近门”“内治门”“德盛门”“天佑门”“怀远门”“外攘门”“福盛门”“地载门”;将原有的护城河填平重新挖了一条,宽度达到十四丈五尺,周长十里二百四步,这样的宽度才能作为京城的护城河;城内建造钟楼、鼓楼;在八座城门外建造瓮城;在城内开凿七十余座内池,城内的水排入内池,不向外倾泻,这样做的好处是杜绝了敌人从排水渠偷渡进入内城的可能性。通过护城河、瓮城、城墙,以及不通向城外的排水系统的建设,来保证京城的安全,这是作为京城的安防系统所进行的升级改造。
城池安排妥当,皇太极便大兴土木地改造内城。他下旨建造了天地坛、太庙、宫殿、六部衙门、都察院衙门、理藩院衙门、学宫、阅武场等一系列建筑。而为了配合这些建筑,城内的街道设置和街坊设置都随之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原来的十字形街道变成了井字形,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在内的宫殿建筑群就处于井字最中心的部分。
按照《考工记》中王城“面朝后市”的设计方式,即王宫的前面应是办公重地,后面则是热闹的市集。比照京城的级别升级换代的沈阳中卫城便是如此设置的,宫殿南部是大量的衙门。而后面则是热闹的集市四平街,其是最中心的商业街,也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
至此,沈阳中卫城有了作为京城应有的一切政治、军事与经济基础设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将其更名为“Mukden”,这一词语是满语,它的意思是“兴起、盛、腾”,汉译为“天眷盛京”。盛京城,从这一刻起便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1636年,即天聪十年,也是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并于同年在城外建造了专为皇家所用的莲花净土实胜寺,亦称为皇寺。
1643年,即崇德八年,也是皇太极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下旨在距离中心庙五里的地方建造东西南北四座寺庙,每座寺中建造一座浮屠。由于清王室信奉藏传佛教,因此寺中浮屠均为藏式喇嘛塔。根据寺中碑文的记载,四座寺庙及佛塔分别命名为“永光寺”(东塔)、“广慈寺”(南塔)、“延寿寺”(西塔)、“法轮寺”(北塔)。
清代有学者认为皇太极下旨升级改造后的盛京城与《易经》中的理论十分相符。《易经》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沈阳中卫城中原本就有一座中心庙,而皇太极在修建宫殿时保留了这个中心庙,它便成了《易经》理论中所谓的太极,而钟鼓楼则是两仪,四象就是这四座佛塔寺庙,而八卦则对应八座城门。这种说法虽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因为皇太极本人并没有明确表明盛京城的改造是根据《易经》理论进行的,但这样的巧合无疑也让盛京城的初始规划具有了明显的汉文化意味。
顺治年间
1644年,即顺治元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旋即迁都北京。盛京作为留都存在,仍然在盛京设置各部,但皇帝的精力都投入在新都上,并没有对城池建筑等进行修缮或升级。
康熙年间——外关的修建
康熙十九年(1680),皇帝下旨修建了盛京城的外关。这个外关可以理解为进入内城的关卡,也同样建造城墙,称为关墙,但关墙不高,只有七尺五寸,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但关墙并不是方形的,而是呈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形。在关墙的东南角有河流流出,河面不能设置关墙,但仍需封闭,因此设置水栅。由内城的八座城门向外延伸,与关墙相交的位置设立八关,即“大东关”“小东关”“大南关”“小南关”“大西关”“小西关”“大北关”“小北关”。盛京城的城市范围达到11.9平方千米,这也显示了盛京城的繁荣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圆形的外关和方形的内城构成了藏传佛教中的坛城(曼陀罗)形式。虽然清皇室信奉藏传佛教,但也没有证据表明盛京城的城市规划确实是按照坛城的模式进行的。
康熙二十一年(1682)后,国库充盈的清皇室对盛京城多次进行修缮,使盛京城仍旧辉煌而荣耀,颇具京城风度。
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对盛京城的修缮也非常频繁,乾隆本人经常出巡到盛京城,足见清皇室对盛京城的重视。也是在乾隆年间,盛京皇城迎来了自己最后一次升级改造。
盛京故宫的最终形态是三组轴对称的建筑,分别为东路、中路、西路。努尔哈赤建造了大政殿与十王亭所在的东路,皇太极建造了崇政殿所在的中路,乾隆对中路进行了改动,并兴建了西路建筑。乾隆皇帝习惯了北京故宫的三路中轴对称宫殿建筑的模式,对颇具满族风格的不太对称的盛京故宫进行了改造,使其更符合其作为清朝发祥地的地位。这便形成了盛京故宫最后的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乾隆还对祭庙等建筑进行了修缮与重建。盛京皇城的蝶变至此全部完成。
盛京皇城与近现代盛京地区城市发展的结合与消解
从皇城向经济发展型城市的转变
盛京皇城作为陪都(留都),直到清朝末期都一直被精心地保护与修缮。至20世纪初清朝灭亡之前,盛京皇城仍旧保持着全盛时期的模样。巍峨的城墙、雄伟的角门与宽阔的护城河守卫着盛京皇城的安全。摄影技术的传入,也让盛京皇城留下了自己的“倩影”。
盛京城的经济日渐繁华,这一点从清代晚期的《陪都纪略》中可以得到证明。书中盛京地图的重点标识已从内城的宫殿衙门等行政场所转向关墙与内城之间的“关厢”区域,这一区域有大量的集市和市场,书中记载了大量世俗场所,盛京城的热闹场面可见一斑。并且,盛京城作为交通枢纽,其经济发展也必然十分迅猛。
近现代城市发展对盛京皇城的蚕食与消解
近代以来,随着盛京城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盛京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盛京皇城外建起了大量的建筑,街市得到了扩展,并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盛京皇城所在区域则作为旧时代文化的代表,不断被轻视。在战争年代,盛京皇城的建筑群不断遭到破坏。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残余的皇城建筑也持续被拆除,整座城墙只剩下一座破败的角楼和一小段城墙的残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座城市改回旧时称呼“沈阳”,工业化的进程如火如荼,作为重工业基地,沈阳的城市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城市范围也不断扩大,但其作为皇城的气象一去不返。
作为文化遗产的盛京皇城在当代焕发新生
值得庆幸的是,盛京皇城的宫殿建筑和一些祭祀场所毁坏得并不严重。近年来,沈阳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齐头并进,盛京皇城作为沈阳最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也在逐渐地被修复。2001年,残存的西北角门开始修缮,如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样子。2004年,盛京故宫(现称沈阳故宫博物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盛京皇城的文化价值并没有在历史的进程中被磨灭。2019年,盛京故宫太庙修缮完成。2020年,沈阳盛京皇城综合保护利用工程获批并开工,该工程将修复盛京皇城的两座城门、六条胡同、三座王府,以及若干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为文化遗产的盛京皇城,在新时期正蓄势待发,焕发新生。
盛京皇城从明代的军事边城沈阳中卫城一步步转化为清代第一座皇城,经过清太祖的接收与改造,清太宗的升级与扩大,清圣祖的修缮,清高宗的升级改造,完成了其历史中最辉煌的蜕变。作为陪都(留都)的那些年,其仍然保留着自己清朝第一王城的气度与样貌。同时,作为交通枢纽和陪都重镇,其经济发展也蒸蒸日上。直至清朝灭亡之前,仍不失其皇城气象。
清朝灭亡后,随着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军事地位的变化、经济产业重心的转变,以及战争的影响,盛京皇城逐渐被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新式建筑蚕食。21世纪以来,盛京皇城的文化价值重新被认识,并得到保护、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这显示了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与文化自信的提升。盛京皇城也必将在这样的努力下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