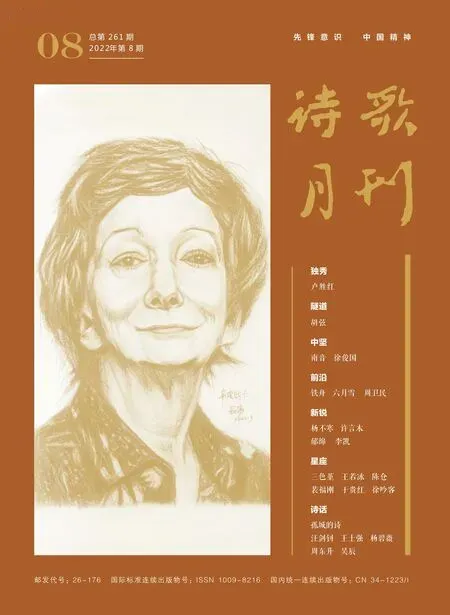总有出神的时刻(随笔)
2022-11-10卢胜红
卢胜红
谁能想到呢?我的亲人、我的邻居、我生活中的人,他们不会想到这个总是不爱说话、不爱交际、喜欢宅的家伙会写一种叫“诗”的东西,会是一个诗人。即便是我自己,在辍学之后的十几年里,在浙江的工厂打工的时候,在北方做小商品推销员的时候,在上海卖服装的时候,我又何曾想过,有一天我还会写诗,还能做一个诗人。
人的生命中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意外,太多的偶然,太多的巧。
2012 年的一个春日,我在上海的服装店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意外地刷到了“百度贴吧”的“现代诗吧”,偶然地看了几个诗帖,我想,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写呀!
我就开始写了。
碰巧遇上了几个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碰巧写出过几首让一些人喜欢的诗,碰巧在后来的写作中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遇见肯定我、鼓励我坚持写下去的陌生人。他们既有诗坛的前辈,也有普通的诗歌写作者和读者。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匆匆的过客、永远的朋友,感谢诗歌让我们灵魂的血脉相连。向意外致敬,向偶然致敬,向如此之多的巧致敬!
谁能想到呢?写诗,做一个诗人,是我十六七岁时的一个梦,我以为它早就随着学业一起破了、碎了、陌路了。我差不多已经接受生活就是年头出门、年尾回家,就是不停地赚钱养家,生儿育女。谁能想到我会在十几年后重新拾起这个梦,再把它做下去呢?
真是太巧了。
1993 年中考,我以1 分之差无缘省重点,只能进普高。我的妈妈,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做些什么呢?只能多方奔走,打听。枯燥的夏日,漫长的等待,蝉嘶日夜。差不多一个月后,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想进省重点需要交2400 元择校费。
真是太巧了,我们的家底差不多就这些。父亲出门不在家,妈妈为难了。就上普高吧,我说,哪里都一样。
真是太巧了,这是一所几年后就被撤并的中学,所有的人都在混日子,一年下来,老师不知道学生的姓名,学生不知道老师的姓名,大家相安无事。很快,我就和很多人一样,中途辍学了。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往事,回想起父亲谈及我的失学一脸自责和失落的时候,我已能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个事实。就像如今,我帮着妈妈收油菜,我帮着父亲给菜园挑粪水的时候,我想着这些都是为成就一个人而来——
那些粪水泼在地里,在阳光的暴晒下,散发出一种类似于臭豆腐的奇异香味。因此,当读到诗人那勺的《粪水之光》时,我不由得会心一笑。也许,生命的另一种成熟就是能闻到粪水的香味吧,也许诗歌的作用就是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嗅到奇异的香味吧。
在一年半的高中生涯里,我碰巧遇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纪弦、余光中、席慕蓉三人的合集。我读不懂它,可我偏偏就喜欢这种似懂非懂、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而在我更小的时候,我邻家的小表哥和他的同学坐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谈论着海子、顾城和三毛。他们的双眼充满着奇异的光芒,沉默地望着远处的天空,一动不动,像被什么东西抓取,掳走,长久地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情绪里。
真是太巧了,我喜欢——
神秘就像醉酒的男人酣睡如婴儿,脸上浮现奇异的光芒。就像下雨了就有写诗的冲动,仿佛宇宙的深处也有一个母亲在深切地呼唤,不能不去应答她。
这样的神秘还包括——十九岁的表哥(另一个,前面表哥的哥哥)意外去世不久,他家门前的一棵桃树很快也跟着枯萎了。桃花是他的灵魂吗?还是他的前世就是一棵桃树?人们都说,那年的桃花开得太旺,太晃眼了。
这样的神秘还包括——我二十岁时,给做电工的姨夫打下手,晚上一个人回家,总是要经过村西的菜园地,也是坟场。心里害怕的时候,我仿佛听到去世的奶奶的声音:谁也别欺负我的孙子!于是心中一片祥和:这从虚无中生出的无限信任究竟是什么?
这神秘还包括——在歇学的十几年里,每次做梦,梦中都是在读书、备考、考试。好着急呀,许多功课跟不上了,然后醒来,一片黯然。然而,当我再次接触诗歌后,这样的梦再也没有了,奇迹般的消失了!是因为少年的梦想在中年以后续接上了吗?是诗歌驻颜有术,能给人带来第二次青春吗?
这神秘还包括——夜晚,打开家门,走到院子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即便那个晚上没有月亮,也是如此。仿佛在出门的那一刻,突然接收一个秘密的指令,仿佛有人在耳边轻声说:抬头,抬头看看!这秘密的指令来自何处,又是谁下达的?
这神秘还包括——常常是在夜晚,狗突然对着黑暗狂吠起来,有什么是一只狗看到了而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有什么是羊群看到了而羊倌看不到的?
这神秘还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万物生长,包括头顶的星空。
我想正是在这些神秘中蕴藏着生命的意义,我想诗也正是这些神秘。我一边务实,认真地过我的世俗生活;一边务虚,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写诗,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互为掩体,充实的精神生活让我更能平静地面对世俗的名利荣辱,踏实的世俗生活让我更专注于精神生活。因为诗歌,我真正懂得了实也是虚,虚也是实。
然而,这是多少斗争、挣扎、妥协之后才最终达成的和解。在这写诗的十年里,我曾多次主动或者被迫中断写作,短的两三个月,长的达两年。甚至直到今日,我依然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生活的压力,因为对写作的自卑——毕竟我的书读得还是太少了。每当看到伟大诗人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毁“诗”灭迹,我总是一边写一边删。诗人、翻译家李以亮先生说诗歌与诗人的关系是击中与被击中的关系,一个被诗歌击中的人,无论停下多久,总会有重新开始的时候(大意如此)。我常常坚定地相信自己是那个被击中的人,也常常对此表示怀疑。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写,是一个深渊”。写,就意味着永无尽头,正如某位诗人所说,最好的诗总是下一首,等着被写出。然而,对于这个深渊,我的理解是,你能下潜多深,你就能站到多高,站立的高度和下潜的深度成正比。如同一棵树,底下的根有多深,地上的干才有多高。
所以,如果能,还是要下潜吧,俯身泥土,把根扎得更深一些,把梦继续下去。因为即便是悬浮,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也等于停滞不前。如果不能,那就活成诗,活成一首田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