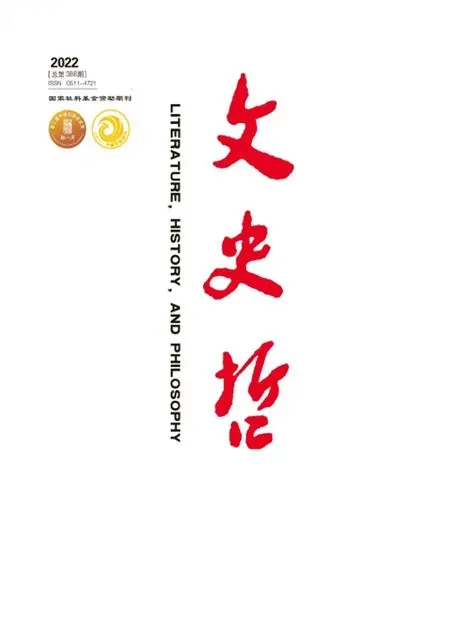中国史学现代脚注之确立:以《历史研究》与《文史哲》为中心
2022-11-08陈怀宇
陈怀宇
引 言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国和日本学者书写和发表论著的传统方式长期以来都是在纸上留出天眉地脚,以便读者做笔记,书籍出版都是直排,现代脚注传统也是域外所传,存在一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毕竟传统印刷方式不使用脚注也受到竖排的影响,西文是字母文字,横排看起来比较舒服,竖排的西文很难看,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涉及书写、印刷与知识的获得与读者认知的过程。比如,希尔伯特(Betsy Hilbert)注意到技术因素对学生尾注和脚注使用的影响。她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疏于计算页底预留做注的空间,常常与教授达成妥协使用尾注,但他们的方便却对读者造成困扰,因为人们不得不常常翻到后面去查看其注释。
正因为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存在各种注释形式,这种现代脚注形式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史学中被完全接受要迟至20世纪中叶以后。我的这一研究虽然受格拉夫顿《脚注趣史》一书的启发,但关心的问题和处理的材料完全不同,也不会像他那样专注于几个重要人物,且将讨论的时代拉长到三个世纪。我关注的历史时段大约是半个多世纪,主要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并按照我所理解和分析的脚注传统发展转折点(turning point)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即清末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期刊并没有统一的刊行格式,既有横排,也有竖排,既有使用脚注者,也有使用尾注者。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国家政权建设对新闻出版的规范化,脚注逐渐成为全国学界所使用的普遍格式。这其中的变化涉及民国旧史学向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逐渐转型,民国旧史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脚注的态度是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一转型中是否起了标杆作用?文字改革运动是否引发了出版技术对脚注的影响?随着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的密切,苏联专家是否在使用脚注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梳理。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里将主要分析5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史哲》两个个案,阐述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接受这种现代脚注形式;这种接受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奠定,为何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需要并能够奠定这种脚注形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脚注之使用乃是一技术问题,但其被普遍接受,应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经典论著的态度,也涉及民国旧史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学术规范化如何形成认同,中国史家与苏联史家的交往,政权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学术出版如何进行制度化规范等等。
一、《历史研究》与史学脚注传统之确立
中国史学如同西文文献一样使用脚注究竟从何时开始、因为何种因缘确立这种现代学术的规范?尽管现在的学术期刊都有严格的撰稿要求,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并没有现在这样严格的全国性范围内普遍认同的撰写和刊发规范。我想不妨从中国史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出版物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即《历史研究》从何时开始使用脚注,又是如何接受和确立这种学术规范。不过,《历史研究》并非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开始出版的学术期刊,如果和其他刊物进行比较,也许会有更为清晰的线索。因此,本节将引入50年代初创刊并迅速取得巨大影响力的《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进行比较,从而追溯脚注在学术刊物中得以确立的发展路径。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史学也受到政治大环境影响,开始与苏联史学密切接触,因此50年代中苏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也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脚注发展史也应该放在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主要领导人大多离开了大陆,所长傅斯年及考古组负责人李济迁往台湾,语言组负责人赵元任赴美任教,只有历史组负责人陈寅恪留在大陆,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史语所集刊》也迁到台湾。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并未立即设立历史所,而率先于1950年成立了考古所、语言所,前者由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领导,后者由罗常培负责,同时也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澜负责。1951年在北京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导的中国史学会,作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专业组织。1952年又进行了高等教育变革,全国各大院系重新调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被取消,各个科系并入新政府领导的学校,一些私立大学教师也被重新分配到公立大学,如陈寅恪从岭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任教。北京负责全国科研领导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直到1954年才成立了历史所第一所(古代史)和第二所(中古史),并将近代史所改为第三所。但《历史研究》最初并非是历史所的刊物,其创刊与历史所第一所和第二所的筹办基本上同时展开,中国史学会领导人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历史研究》刚刚创办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出任编委会召集人,尹达任主编,刘大年任副主编。郭沫若在组织编委会时力图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编委会成员以马列主义史家或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为主,如尹达、杜国庠、胡绳、吴晗、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等人,但也有三分之一可能并不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者,如向达、季羡林、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人。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亲自致信陈寅恪邀请他出任编委,1月23日陈寅恪复信表示应允。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家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作为中国史学界领袖的郭沫若当时仍然非常强调史学工作者要尽可能掌握史料,因此主张将一些在当时已经成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纳入编委会,也有利于建立中国史学的声誉。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时所发表的《征稿启事》只是强调了稿件的内容,包括五方面,即历史科学理论的阐发、有关中外历史的学术论文、重要历史事件的考证、重要史料的介绍、国内外史学界重要论著的评论或介绍等等,并未对稿件格式提出任何详细的要求。而且当时《历史研究》的出版采取直排方式,即使文章有注释,也不会是西文横排方式下的脚注,而是排在每一页左侧,应该称为“侧注”,算是一种页末注释格式,但这种注释方式与文章结束时才出现的尾注不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直排脚注”。直到1956年《历史研究》全面改版为横排,文章注释排印在每页页脚,脚注形式才最终得以确立。
让我们先来看看最早的《历史研究》刊出后如何在格式上使用注释。195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期共刊载七篇论文,即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冯家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其中胡绳、侯外庐和王崇武的三篇文章系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完成的论文,处理的主题属于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最瞩目的五朵金花中的三朵。这三篇马列史学论文无一例外都使用了“直排脚注”,其中二手文献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论述,引用这些文献的脚注都提供了所引文献的出版信息,包括作者、论著名称、出版社信息和页码。毫无疑问,按照现代史学的格式标准而言,他们的论文使用的正是标准的脚注格式。这也说明当时如果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必须给出详细的注释,可能是为了防止犯政治错误,同时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经典性、权威性、规范性。而这三篇论文引用一手文献特别是传统古籍使用脚注时,仅提供了作者、书名和卷数,并没有提供具体出版信息和页码,比如侯外庐引用正史、《唐文粹》《明夷待访录》《大清会典》等,以及王崇武引用正史、《滋溪文稿》《元典章》等,这种引用传统古籍仅提供书名和卷数的传统继承了1949年前的征引传统和格式。还有一些细节较为有趣,值得指出。第1篇胡绳的文章在涉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使用脚注更为规范详尽,除了列出作者、书名、出版社之外,还提供了页码,如《毛泽东选集》《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等;而对其他近现代学者的著作,仅列出作者、书名和出版社,未列出页码,如文中所引用的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等。这其中不少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华岗、范文澜的著作。这恰恰表明当时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尊崇,而对其他学者的作品则并不追求经典性和权威性的征引标准和规范。
那么,当时苏联史学在中国史学脚注传统确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有趣的是,《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发表了第一篇来自域外学者的论文,作者是苏联专家潘克拉托娃(Aннa Mихaйловнa Пaнkpaтoвa,1897-1957)院士,这篇文章题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主要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五十周年。该文使用了两条“直排脚注”,分别是《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列出了书名、卷数、俄文版、具体页码,但未列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并不算完整严格的脚注引文格式,可能因为俄文版《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当时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广为人知。潘克拉托娃刚刚在1953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主编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3年苏联科学院选举院士是一件大事,中科院的《科学通报》很快做了详细报道,并以《苏联科学院新院士介绍》为题对所有新当选院士的个人简介进行了连载。虽然当时中国史学界对苏联史的研究可谓是刚刚起步,但与苏联史学家已经开始交往。1953年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年即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在苏联科学院哲学历史学部举行报告会,由科学院老资格的副院长巴尔金主持,有潘克拉多娃院士、涅契金娜通讯院士等一百余人参加,刘大年(Лю Да-нянь)做了题为《中国历史科学现状》(Состоя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Китае)的报告,随后该文俄译稿刊载在同年第5期《历史问题》上。
从苏联回来之后,刘大年又将自己在苏联的一些见闻加上对苏联历史学的理解和感想,写成一篇《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上。限于工作报告体例,该文没有脚注,但有一些正文中的夹注(in-text citations),完全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述,不仅列出书名,也给出了版本和具体页码。比如第20页谈到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时引用列宁的教导“为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底全部深刻历史”(“《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682页”)。第21页讨论封建制度的概念以及封建时期分期问题时则使用了夹注(“《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本340页”)。第22页引用了斯大林在1931年与德国作家刘第维赫的谈话评论彼得大帝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斯大林:《论列宁》人民出版社本49页”)。第23页引用了列宁1921年对苏维埃国家的指示(“《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906页”)。同一页也引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总结报告中关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指示(“人民出版社本74页”)。第24页则引用了斯大林对民族运动的指示(“《列宁主义问题》80-81页”)。这些涉及夹注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直接引文,全都直接引到了页码,但偶尔也忽略出版社名称,只有简单的版本说明。无论如何,这篇刘大年的报告只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才给出具体注释,这和《历史研究》上论文的注释体例完全一致,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学家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时非常注意注释规范。
如果仔细看一下当时其他相关史料,将刘大年在苏联发表文章的史事放在当时中苏之间的学术交往语境之中,不难看出苏联和中国两国科学院互相发表对方的文章实际是中苏史学界的一种礼尚往来,即刘大年在1953年访苏时在苏联科学院的报告以俄译本发表在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科学院刊物《历史问题》上,潘克拉托娃访华在中科院的报告则以中译本形式发表于刘大年任副主编的《历史研究》。据当年《科学通报》报道,1954年10月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茶会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该团团长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团员中包括《历史问题》杂志总编辑、历史学博士、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潘克拉托娃院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代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把许多珍贵的苏联科学、历史、经济书籍赠送给中国科学院,潘克拉托娃在会上做了热情的讲话。苏联《历史问题》总编辑潘克拉托娃院士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主持的《历史问题》座谈会。在会上,中苏历史学家们相互介绍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和现状,并恳切地就如何进一步加强联系合作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潘克拉托娃院士还应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邀请作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和“苏联工农联盟的作用”等报告。尽管《科学通报》并未列出潘院士在中科院所作报告的详细内容,但其题目与《历史研究》上的署名文章题目完全一致,应该就是同一篇报告,借重刘大年的悉心安排刊发于《历史研究》。考虑到该文出自苏联权威史学家之手,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应当说这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一种标杆。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较,“旧”史家并不注重脚注形式和规范,而这些“旧”史家当中,当时最负盛名者之一无疑是陈寅恪。这里以在《历史研究》最早两期刊物上发表论文的陈寅恪为例。195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寅恪被提名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由刘大年负责聘请陈寅恪的具体工作,协助刘大年办理此事的人是北大历史系汪籛,陈寅恪昔日的学生。但汪先生未能说服陈寅恪北上,让刘大年感到十分惋惜。不过,陈寅恪允诺进入《历史研究》编委会并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托汪带回两篇文章《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与《论韩愈》。刘大年当时是《历史研究》副主编,遂安排将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和第2期。陈寅恪的文章全文无论是一手文献如四部典籍包括正史《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或《通鉴》《册府元龟》《李义山文集》等,还是二手文献,都如同他以前所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一样没有使用脚注,因此读者亦无从知道他所使用的版本以及准确页码,也使得复核其所引一手、二手文献变得较为困难。显然陈寅恪作为所谓“旧”史家,仍然坚持他自己长期一贯的做法,并无使用脚注的习惯。
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的邓广铭也采取了和陈寅恪一样的做法,并不特别措意脚注规范。他发表的《唐代租庸调法研究》一文同样未通过脚注或夹注形式提供自己所引文献如《唐会要》《通典》《文献通考》《旧唐书》等书的版本信息,仅根据论文的论述顺序增加了五个部分的小标题。他也引用了法藏和英藏敦煌文献特别是沙州敦煌县户籍残卷,但因为没有提供任何引用的残卷编号和版本信息,让读者无法对照原卷进行复核,除非是曾经看过这些残卷且非常熟悉其内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前人的研究如陈登原、铃木俊、玉井是博、仁井田陞、平野义太郎等人的二手文献,或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或仅提供书名。这些做法与当时同在《历史研究》发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所不同。
邓先生也属于所谓“旧”史家。按照翦伯赞先生的说法,当时北大历史系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来自1949年以前北大、清华、燕京历史系的残余势力,即北大胡适的旧部如邓广铭先生,清华蒋廷黻的旧部如邵循正先生,燕京洪业的旧部如周一良先生。邵循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即迅速转向了跟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史,他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表了《一九○五年四月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争》一文,只有一页,主要利用了《时报》《字林西报》等报刊资料揭示最早期中国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斗争。全文并无脚注,但在夹注中提示了报纸出版的年月日和页码。邵先生又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了《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一文,也只有一页,亦无脚注,主要使用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的军机处档案。同一期也有周一良发表的《论诸葛亮》一文,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诸葛亮,文中引用古籍都使用了脚注,但只有书名和卷数,并无具体版本信息和页码,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脚注。
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旧”史家之间,向达也许算一个异类。他并没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也不像胡适、蒋廷黻、洪业的学生和追随者一样很容易被翦伯赞视为他们的“旧部”。他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表的《南诏史略论——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探》一文并不涉及活学活用历史唯物论,但却在使用直排脚注上相当规范。这篇文章很“现代”,不仅有正、副标题,还有目录,很像当时一些海外西文刊物和海内《华裔学志》的风格,目录列出了四个二级标题:一、引论,二、南诏史上的民族问题,三、南诏和天师道、氏族、北方语系语言,以及吐蕃有关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四、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该文使用了大量“直排脚注”,而且往往篇幅很长,不仅提供了所引用的中文、西文论著和期刊论文及卷数乃至页码,还有很多辩难和解释,已经和当时最为规范的西文论文脚注一样。如引伯希和论文列出了冯承钧译本的页码,引用J.F.Rock的英文论著甚至标注了“60-61页的注四五”;只是引用传统古籍仍和其他学者一样仅列出书名、卷数、篇名,未提供版本信息。无论如何,他的文章在格式上是最为“现代”的,对与主题相关的中外二手文献可谓搜罗殆尽,这也许和他长期注意中外学术进展并虚心学习各种学术标准有关。1954年第3期上周一良、唐长孺、汤用彤、任继愈等人发表的文章虽然也有直排脚注,但都较为简单,这也表明是不是使用规范的脚注与这些史学家是否曾留洋或获得域外学位并无直接关系。
徐宗勉在当年的《科学通报》发表了《介绍新创刊的历史科学期刊——〈历史研究〉》一文,对马列主义史学以外的5篇论文作了评论,认为“发表有价值的史料性的文章,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掌握真实、有用的材料是做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根本条件,有时甚至成为解决历史研究中某些疑难问题的关键。因此,《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工作的某些重要方面将新发现的或是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分析和综合的有价值的史料发表出来,提供有关的史学工作者时参考,是对于整个研究工作的进展有好处的”。这包括陈寅恪、王崇武、浦江清、朱德熙、冯家昇等人的文章。他还指出《历史研究》第1期中看不见书评一栏,“大家都知道,书评栏对于一个学术刊物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研究》应该经常发表关于新出版的书籍以及那些过去出版的但现在还有必要提出来讨论的书籍的评论”。可见当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一些现代史学刊物的基本国际通例,即一个正规的刊物既要有论文,也应该有书评。不过,他对论文的书写和排印格式并无任何具体意见和建议。
二、《文史哲》开启史学脚注传统之先声
《历史研究》并非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刊的史学刊物,比它创刊更早且更有影响的刊物是1951年5月1日创刊的《文史哲》。《文史哲》不限于发表历史学论文,也有不少文学方面的论文。如同《历史研究》一样,该刊刚刚开始出版时,也是直排,并不要求稿件遵守一定的规范和格式,大多数文章使用文中夹注,少数文章使用尾注。1955年该刊改版为横排。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上一共发表了11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社论《“实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没有使用尾注或直排脚注,而是使用了文中夹注,引用了一些论著,但未提供具体版本信息,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一八四五年五月马克思给露格的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三七页”“列宁《论民族自决权》”等等。而这一期中使用注释的学者大多为历史学家,而且是已经比较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例如杨向奎、赵俪生、卢南乔等,他们在文章中都使用了尾注。杨向奎的文章《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是第1篇,不完全是史学论文,只是一篇记录学习毛《实践论》之后进行理论思考的文章,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尾注:“见《新建设》四卷一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落款为“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写完于青岛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另外两篇也使用了尾注的文章分别是赵俪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底反清斗争》、卢南乔《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赵文尾注有26条之多,并无任何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全都是史料,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刘继庄《广阳杂记》、王源《居业堂文集》等,但没有任何二手文献。卢文则有尾注10条,主要是一手文献如《明纪》《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续通考》等,但也引用了不少二手文献如《史语所集刊》第十七本王崇武《论万历东征岛山之役》《日本史讲话》《朝鲜通史》《日支交涉外史》等。同一期也有郑鹤声的《洪秀全状貌考》一文,引用颇多二手文献,包括外文文献,然而采用了文中注的形式。而吕荧译《列宁论托尔斯泰》一文则只有一个译者尾注解释“杜马”一词。这一期中其他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及文学研究,如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孙昌熙《鲁迅与高尔基》,都采用了文中注的形式。从第1期发表的论文来看,史学论文并无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的迹象,但理论文章中均有引用,但大多并未提供详细版本信息和页码。这一现象延续到1952年第1期,这一期主要是政治报告和政治理论学习文章。但1952年第2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更多学术文章。
早期《文史哲》上使用尾注最规范的文章其实是1952年第2期上日知发表的《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文,该文引了《马恩文存》和苏联学者的俄文参考资料,注1为《苏联东方学》1949年的文章,注出页码140;注2“《古代史通报》1950年第1期,116页”;注3为“苏联教育部批准的,阿夫箕耶夫编,《古代东方史教程提纲》第二十二,结论,1949年版”;注4为俄文;注5为“《中国古代社会史》页41”;注5“《马恩文存》俄文版,卷一,页285(1924年)”,非常规范,但看起来似乎是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因为他引了不少苏联学者的成果。紧随其后的是童书业先生发表的《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文,使用了文中夹注,马恩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引用注出了页码。同一期还发表了欧阳珍在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的读书报告《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使用了尾注,有极为详细的版本信息和页码。如“注(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转引自古柏尔等著吴清友译《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读书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中卷第二册B十五页”。注二是转引《学习杂志》第3卷第11期胡绳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注三引“《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一九五○年版第四页”。后面还有22个注释,都是引用此书。
尽管华岗在《文史哲》最早三期上都有文章发表,但大多是政治报告,可是到1952年第3期,他的文章出现了一些变化,不仅内容更有学术性,格式上也开始更为规范。这也许反映了作为校领导的华岗在学界日益规范的发展态势下也逐渐采用较为规范的学术格式。《文史哲》1952年第3期华岗《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文,有12条尾注,大多给出了详细的版本信息和页码,参考文献也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如第1条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一节”,没有出版社信息;第2条是“《共产党宣言》中国出版社译本第二○页”;第3条也是《共产党宣言》;第4条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运动大纲》”;第5条是“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演说”,后面还引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第一六二页)、《人民日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的报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这篇文章也是这一期中唯一使用了尾注的文章,其他文章主要涉及清除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习毛主席的语言和《矛盾论》等、批判胡适、批判康有为。1952年第4期主要是“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文章。第5期上使用了尾注的文章是赵俪生的《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问世一百周年而作》,有26条注释,主要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等人的著作,有版本信息和页码。
《文史哲》上第一篇使用“直排脚注”的文章是《文史哲》1953年第1期上马克思著、日知译《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这是日知译自联共(布)中央马恩列学院的俄译本。但文中的脚注并非是马克思原文版本中使用的脚注,主要是中译者注,还有少数几条俄译本编者注。显然中译者是追随俄译本编者注而补充了自己的注释。俄译本编者注主要是提供版本信息和页码,而中译者注主要是提供专有名词的中文译词与俄文以及其他西文原词的对照,如德国资产阶级史家尼布尔、罗马王政时代的路玛、罗马公民、村民、部落、村社、氏族等。第2、3期这篇文章连载完毕。这种直排脚注的传统似乎是因为中译本要提供简注而出现,比如类似的文章有《文史哲》1954年第2期斯密尔诺瓦作、吕荧译《伯林斯基的美学》,使用了脚注,也是中译者注,主要注出里面提到的人物和其他专有名词。同一期布拉果依作、陆凡译《普希金的创作道路(上)》也以脚注形式出现,都是译者注。其实除了中译本之外,在1954年第3期的原创文章已经开始使用直排脚注,如第1篇章世鸿《论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可能性向现实转变的途径——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使用了脚注,主要提供了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的引用信息、版本以及页码。而同一期殷焕先《谈“连动式”》一文也用了脚注,但并非全是参考文献的注释(bibliographical footnotes),而主要是解释性注释,只有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注释提到相当于西文脚注功能的书目信息“张志公先生的《汉语语法常识》第四编第四章‘动词连用’页谈到怎样辨认‘连动式’”,可以与正文参看。
1954年第4期对于《文史哲》来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期开始很多文章均使用了脚注。吕荧《人民诗人普希金》除了第一页几乎每页都使用了脚注,提供了所引用的俄文论著书名、卷数、页码,较为规范,尽管没有提供出版社名称。同期康特拉特叶夫作、黄嘉德译《苏联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论著》一文也使用了脚注,主要是译者注,注出主要作家的介绍。郑鹤声《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使用了脚注,注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文选》《毛泽东选集》、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等,这一篇文章引用文献颇多,脚注丰富。王仲荦《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也使用了脚注,虽然引了《方言》《尔雅郭璞注》《左传》《周礼》《墨子》《史记》等古籍,但仅有篇名,并无版本信息。项文和《对过渡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一文也使用了脚注,主要是《联共(布)党史》、斯大林的作品以及《毛泽东选集》,有详细的版本信息和页码,非常规范。吴大琨的《答项文和》一文同样使用了脚注。总体来看,这一期以后的文章脚注比较常见了,虽然不是每篇文章都有脚注,但脚注取代尾注已成定局。除非不用注释,否则一般都是用脚注,不用尾注,比如后来张传玺、杨向奎、赵俪生、谭丕谟等人的文章。
1955年《文史哲》改版为横排,所谓“脚注”才真正变成了页脚的“脚注”,这比《历史研究》改用横排要早。这种排版的变化不限于学术期刊,中央级报纸《光明日报》已经开始采用横排。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在全国报纸中由文字直排版改为横排版。在这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胡愈之的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指出横排的科学性,阅读方便、自然省力、不易疲劳。12月30日,文化部向全国出版界发出《关于推行汉文书籍、杂志横排的原则规定》的通知,指出“对横排书的版式设计,各出版社应该结合本单位出版物的特点进行研究,既要防止纸张利用率过低的偏向,又要照顾到实用美观的要求”。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而且自1956年起,全国性杂志如《历史研究》《文物参考资料》《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也都横排出版。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阿甫基耶夫著、王以铸译《古代东方史》即采用了标准的横排带脚注格式。
三、结 论
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无论是《文史哲》和《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学者之中,尽管也有向达这样很早就较为规范使用脚注的史家,但相比于民国“旧”史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比较遵守现代学术规范,使用了直排脚注,后来刊物变成横排时,使用了脚注,注出了作者、书名、文章篇名,偶尔也提供版本说明和页码,较为规范。“旧”史家大多遵守旧规矩,很少提供详细版本信息和页码,一般引用传统文献仅限于列出书名、卷数和篇名。之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表文章时较为规范,可以试加探讨,并提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当时史学界已经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史学家们开始以历史唯物论理解和解释历史。脚注的使用及其规范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支,历史科学的提法和理论探讨在50年代蔚然成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特别提示历史学乃是一门科学。当时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必然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俄文和中文译著,为了防止出错造成政治问题,更需要在意引用权威的版本,并注释到页码,以备读者查询。这种注释可以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著的经典性、权威性和科学性。格拉夫顿也非常简略地提到,东德的历史学家不顾字母表的顺序,为了表达思想上的忠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在引用文献列表的首位。
其二,随着当时中苏学者之间的密切交往,一方面中国学者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译介到中国,另一方面苏联专家如潘克拉托娃来华访问发表文章,在这种域外苏联史学进入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中国史学家不仅和苏联学者一样使用脚注,同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说明,也不得不使用注释,这些都构成脚注的基础。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郭沫若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以脚注的形式处理译者注。可见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对于脚注的使用早就不陌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史学论著中脚注使用的推广和确立,也奠定了中国史学全面接受国际史学学术格式标准的基础。
第三,脚注逐渐成为全国性出版规范,与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推行对全国新闻出版的制度化规范分不开。正是由于新中国政权的确立和稳定,国务院文化部才得以向全国出版界发出《关于推行汉文书籍、杂志横排的原则规定》,将出版规范化推广到全国,中国学术出版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在全国范围内主要使用简体横排和脚注的历史时期。